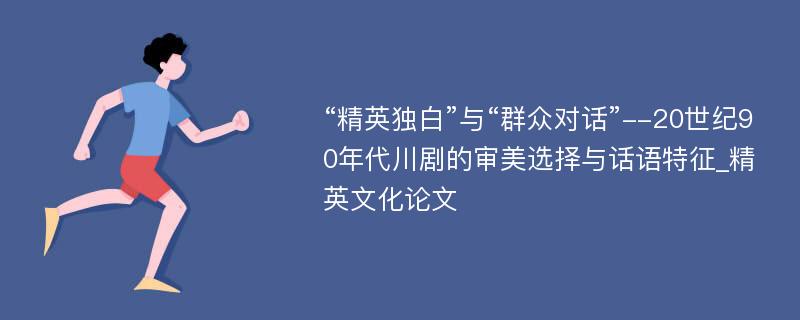
“精英独白”与“大众对话”——90年代川剧的审美选择和话语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川剧论文,大众论文,独白论文,话语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90年代川剧的审美选择之一,首先表现在作家主体意识的空前自觉和剧本文学地位的空前提高,因而在作品意蕴的刻意求深和对人物性格的锐意发掘上,也就显示出更鲜明也更可喜的思想深度和人文精神来。这,从80年代即扬名国内戏剧界乃至文化界到90年代仍一如既往保持良好创作势头、不断造成轰动效应的魏明伦、徐棻等人身上昭然可见;此外,在其他以其多年积累看似突然实则必然地展露头角于世纪末的川剧作家的创作中亦历历可指。
在90年代前期的川剧作品中,无论从剧场效应还是从超越剧场的社会反响来看, 魏明伦的《夕照祁山》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 该剧1992年5月来蓉参加振兴川剧调演即引起轰动,继而出川巡演, 上京进沪,一路激起旋风般的审美效应。由于种种原因,该戏无缘获得全国性的大奖,但它刻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迹,随岁月推移而辉光不减。多年后,沪上学者余秋雨仍断言:“《夕照祁山》是一部真正堪称重要的历史剧。魏明伦对诸葛亮这一历史人物的反思,触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要害部位,因为诸葛亮是历史上少有的把文人人格、官场人格和中国民间的世俗人格组合得最为完整的性格典型,只要轻轻摇撼他,就会牵动整个民族的神经网络。”(注:余秋雨《大匠之门——序魏明伦》,载《四川戏剧》1998年第3期。)
文化反思乃魏氏自80年代以来的自觉追求。从《潘金莲》肇其端到《夕照祁山》成其大,剧作家作为一个思想者的形象日臻成熟,由此窥豹,我们庶几也可感受到川剧观念现代化在作品意蕴方面锐意进取的可喜脉动。走出《潘》剧的“妇女问题”,《夕》剧的聚焦对象已跃升到“文化人格”,其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和思考无疑由此获得更普泛也更深刻的现代意义。“诸葛大名垂宇宙”,这位手摇羽扇道貌岸然的蜀汉丞相,其形象作为某种文化协议的产物,数百年前尤其是在《三国演义》中即被定格神化为大智大慧乃至能够呼风唤雨的“超人”。这个天下人共仰的“卡里斯马人物”(charismatic figure),其无上的神圣性和强大的感召力从来都是不可怀疑更不可动摇的。然而,最不容置疑处恰恰是最值得质疑处,敏锐的剧作者由此寻找到了向传统发难的创作突破口。“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联吴抗魏火烧赤壁,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一件件光辉业绩可歌可泣,无不铭刻着诸葛丞相一心匡扶蜀汉、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他有盖世的谋略和治国的英才,他有山人的清高和布衣的清廉,但是,正如剧作所揭示的,这位道德“超人”的人格中也有为臣事君尽“愚忠”的悲剧性一面。白帝城刘备托孤,从此,“智囊拜窝囊,雄才保蠢才”,诸葛亮全心全意、殚精竭力去扶那实在扶不起来的儿皇帝刘禅。凭个人感情论,他不负先帝之托保阿斗,堪称有德有义;就天下大势言,他指望扶庸君以兴蜀汉,又可谓不识时务。在道德评判席上,他处世为人之德义可褒可颂;在历史审判桌前,他为相执政之愚忠可憾可叹。展其才智,颂其德行,揭其弱点,哀其苦衷,将一代贤相暮年晚景的复杂性格和悲剧成因立体托出,并由此引出对知识分子传统文化人格的检讨、批判,此乃作为现代性思维代码的《夕照祁山》超越古今任何“三国戏”所在。
剧作家以卓尔不群的文本编码“背叛”了古典文学中那至善至美的“超人”形象,并非迎合大众的理性话语解构着世俗的传统观念,“迫使读者对自己习惯的法则和期望产生一种批判性的新认识”。(注:[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第96页,中译本1987年文化艺术出版社版。)难怪该剧一出,激赏与非议并起,“川剧怪才”再成舆论热点。魏氏的独创证明,现代人对历史的把握应是阐释而非复述的。历史题材对于今之剧作家,是有待解释的现象而非既定不变的公理,它务必在现代意识烛照下获得新的规定性,勃发新的生命力。如伽达默尔所言,“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在于对现实生命的思维性沟通”。(注:[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49页, 中译本198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版。)优秀的史剧创作绝非往古事实的罗列堆砌,就其实质言,它是展开在历史和现实、过去和今天的一场平等对话、一种精神沟通,并在这种旧话重提和意义再建中凸现出鲜明的现实性品格。
较之《夕照祁山》,崛起在90年代后期的《山杠爷》无疑要幸运得多,这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川剧现代戏,将当今国内剧界各种高级别大奖一一囊括而领尽风骚。虽然问世年代有先后之别,受到的社会待遇也不尽相同,但二者所表现出的理性自觉和反思精神,则是灵犀一点心相通的。《山》剧选择的审视对象,乃是至今仍作为活生生的存在的当下现实。
一部《山杠爷》,从小说到电影再到川剧,在国内艺坛激起很大反响,有人从中看见人治现实与法治理想的矛盾冲突,有人从中读出承续传统与推进现代化并行之路的艰难;有人惋惜山杠爷的入狱,亦有赞赏山杠爷的“铁腕”,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题旨多歧给观念带来了读解难度,但恰恰在这种常读常新的接受流程中,作品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赢得更大意义上的成功。
《山》剧的成功,首先得力于主人公形象不同于常的塑造。对于看惯了角色类型化的传统戏的观众来说,初识山杠爷也许会感到不习惯,因为,该人物性格的是与非、善与恶,绝非那种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值逻辑判断所能定性。堆堆坪——世界进入90年代之际中国边远山村的一个缩影,向观众展示出一种特定生存境遇中的生命状态。村民们的带头人山杠爷,这个堆堆坪的老支书,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全心全意替民办事,以他的正直人品和工作魄力,赢得上级好评、村民拥戴。为惩蛮治刁,他铁腕用“权”,自信“村规就是国法”,“我是书记说了算”,但心胸坦荡绝无半点私念,所作所为又是那么顺乎民情得乎人心:惩罚搞赌博的后生,关押抗交公粮的村民,将虐待婆婆的恶媳妇游街示众,诸如此类,办法虽“土”却下药对症有效得很。几十年他就是这样“管”下来的,村里人从未觉得有何不妥,堆堆坪还年年因此被评上了先进。可是,毕竟时代不同了,改革开放激活了中国社会也刷新了时代观念。此时此刻,老经验遇到了新问题,“村规”与“国法”发生了抵触冲突,转眼间,“治村有方”的山杠爷成了触犯国法的阶下囚。山杠爷的“铁腕”,治好了村又犯下了法,二者同样不可置疑。是耶?非耶?一辆警车带他而去,作品把一个偌大的问号留给了观众。堆堆坪堪称模范的乡约村规受到新时代法制文明的挑战,向来自信的“法”的化身竟然恰恰站在了“法”的对立面,这是一个何等怪异又何等深刻的悖论。对此,当事人想不通,村民们转不过弯,就连戏外观念情感上也一时接受不了。然而,正是因此“想不通”、“不接受”,作为群体而不仅仅是个体的我们民族文化人格底层那深藏的传统情性,才无可逃避地被作家以犀利之笔触动、挑开、曝光了。就此而言,《山杠爷》无疑给观众上了一场生动又警醒的法制教育课。可是,该作的启示不仅仅停留在此,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它还从更深刻层面上揭示着当下境遇中生活的悖论,就是“现实在呼唤法制的同时又不能不依靠人治,历史在抛弃专制的同时又不能不容忍专制,未来在求新的同时不能不守常”。这两难困境折射出何等尴尬的国情,而“陷入两难困境的,又岂止一个山杠爷,一个堆堆坪?从某种意义上说,《山杠爷》反映了我们民族面临社会转型之际的相当普遍的生命形态。”
透过对山杠爷命运悲剧的反思,“小说家和剧作家清醒地向我们揭示了建立在传统的生命形态基础之上的现代生命形态的历史局限”。(注:廖全京《〈山杠爷〉笔记》,载《成都艺术》1995年第3期。 )要知道,我们毕竟背负数千年宗法传统的沉重负荷,历史的阴影来不及随时代社会的匆匆演进从我们意识中一下子彻底抹去,顽固的思维定势还可能在我们身边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山杠爷式的悲剧,对此我们务必保持高度警惕。这是作家给当今国人的忠告和提醒,也正是由此,作品的人文思想深度得以彰显出来。
(二)
就反思意识和人文精神的张扬而言,90年代川剧无疑继承了80年代以来的优良传统,但同样无可置疑的是,前者将此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都大大拓展,并由此奠定了自身在当今中国剧坛幅面更宽也声誉更高的传播效应。此乃剧坛同仁礼赞有加的不争之事实。与此同时,我们务必看到,90年代川剧的审美选择固然以此为首要标志,却不是唯一标志。事实上,90年代川剧在舞台技艺的刻意追求上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同样是一道不容忽视的戏剧景观。这道景观,不仅仅属于地域概念上偏守一隅的川剧这一地方剧种,它甚至在整个当代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也留下有声有色的一笔。
“旧戏新探”是成都有关方面发起的不定期川剧演出、研讨活动,迄今已举办四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作为其积极成果之一,由多位作者合作的新编目连传奇《刘氏四娘》,在历年来众多“新探”剧目中无疑是尤当刮目相看的。缘起于《佛说盂兰盆经》并融合其他佛教文本内容的“目连救母”故事,早在唐代变文里己成型,自宋以来又以杂剧形式出现在勾栏瓦肆中,并经近千年流变演化出庞杂又恢弘的演剧体系,“搬目连”亦成为糅合宗教、民俗、娱乐等于一体的蔚为大观的戏剧文化现象。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示现“阴曹地府”装扮“牛头马面”的目连戏长期被视为禁区,无人敢贸然闯入。
改革开放打破了思想禁锢,人们豁然发现了这块被湮没已久的中国戏曲“活化石”的价值,研究自国内而海外渐掀热潮。“川目连”与“湘目连”、“闽目连”鼎足而三,统领于中华目连文化的整体中又各以其跟地域民俗息息相关的特色著称于世。也许是地处边缘远离中心从来就少于羁绊的传统使然,当小心翼翼的同行们还仅仅限于学术圈内对“活化石”作还原式舞台复现以提供研究对象时,川剧界的有识之士便以“吃螃蟹”的勇气,独领风骚地将一台以剧中女主角命名的新编目连戏热热闹闹展示在普通观众面前。“久违了,目连戏!”该戏一亮相便引来观众如潮,又正因是“新编”而非“旧演”(此前,“老戏老演”式搬目连在闽、湘等地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已屡见不鲜),它命定地要成为让渴望兴奋的剧坛兴奋起来的焦点。被调晋京献演,有研究者看戏后喜不自禁地说:“改编目连戏比改其他传统剧目要难上十倍。首先要有胆识,没有这个你就不敢碰……宗教戏的改编,我看戏不太多,我看《刘氏四娘》在我国算第一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最勇敢的人,他们为传统剧目、为宗教戏的改编闯出了一条新路。”(注:《薛若琳谈〈刘氏四娘〉》,载《成都艺术》1994年第3期。)难怪, 此戏会被文化部作为传统剧目改编的典范之一,向全国同行推荐。
既是“新编”,《刘》剧的取胜之道究竟何在呢?诚然,该剧要立在当今观念面前,首先必做的就是剔除封建迷信糟粕后的主题转换。改编本将刘氏形象作了彻底翻案,一个杀生开荤、不敬神佛而被打入地狱的罪妇,到今天作者的笔下,脱胎换骨成了为救儿子被迫杀生犯戒受苦受难的、浑身上下洋溢着无私母爱的正面人物。这样换固然成功,但是,若以之和上述同为翻案戏的《夕照祁山》对比,不难发现,《刘》的主题追求与其说是在走向哲理沉思,倒勿宁说是在努力寻求世俗情感上与大众的接通。这里,沟通观众心灵的除了普天下共同的母子亲情外,说不上有什么更高深更玄妙的寓意,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刘》剧在征服观众上走着一条不同于《夕》剧式的道路。事实上,真正使这出新编目连传奇吸引观众稳操胜券的更重要因素,恐怕还是从戏曲技艺角度对埋藏得太久太久的宝贵遗产的发掘与复活。庞杂的剧目形态和长期的演出积累使目连戏汇集了戏曲表演的诸多精华,它有如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资源库,其中为我们留存了大量在别的传统剧目中再也见不到的形象资料,诸如古百戏的遗存、戏曲化的佛道音乐、古巴蜀的民间歌舞以及独特奇异的造型艺术等等。从接受角度看,这些表演技艺因极强的奇巧性和赏玩性而有着直接取悦大众的普适性,其带给观众的当然不是如《夕》剧式的深沉乃至痛苦的反省和思考,而是世俗化的甚至不免被人认为有些肤浅的游戏式审美体验。即是说,这类作品玩技巧显然大于玩寓意。观众走进剧场,也不是来听文化精英式的精神布道,而是来参加全民娱乐的仪式化世俗庆典。《刘》剧每场开演前,热火朝天的敲锣打鼓衬托着逼真的抬轿迎亲仪式从大街上一直表演到剧场内,这故意打破场内外界限以求与民同乐的演出形式,不就是一个绝好说明么?
类似致力于技艺展演以尽可能满足观众娱乐心理的趋向,在比《刘》剧要早的新编神话戏《九美狐仙》中更其昭然。这出曾参加第二届中国戏剧节演出的剧目,源于京剧《青石山》,在主题和人物上都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但此改造并不以追求深刻的思想性为鹄的,也无心编织曲折复杂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有点像当今世界流行的音乐剧(此乃音乐艺术走向通俗化的现代产物),在一个通俗易懂的叙事结构中,将主要创作精力都投注于舞台表演之美视美听的娱乐氛围和观赏效果的营造上。变脸吐火,移烛提靴,徒手变花,藏刀亮刀,以及京剧“出手”乃至演员的借用,还有一个九妹三人演,等等,一台戏宛然梨园技艺的大荟萃大展演。想当年,该剧问世时,看戏者的反应也曾褒贬不一。有人惊呼此剧点石成金,甚至有“超越”川剧《白蛇传》之处;有人嫌其剧情内容简单,文本意蕴不够深刻而“有失偏颇”。其实,褒者固然褒过了头,贬者亦未必贬到了点子上,此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思维定势使然。
面对任何作品,人们首先总是习惯于用自己久已熟悉的某种定则或模式去接受、读解、评判之,而这种模式或定则往往又不免有相当的局限性和偏执性。一种传统又正统的理论教导我们,一出戏剧、一部小说倘若没有深邃的哲理、动人的情感或曲折的情节,要想抓住观念实在难上难。长期以来,人们对此都信守不疑且自以为是,以至当新时期国门初开时,面对自海外蜂拥而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派”什么的,竟有不少国人措手不及而力拒“异端”。眼下,当人们抱此观念凭此尺度去衡量《九美狐仙》时,自然也少不了感到失望。然而,看戏者们恰恰忘了,“这也是一种戏剧样式”,正如无情节非理性的荒诞派戏剧依然是戏剧一样,只不过对其裁判,再不能机械搬用亚里士多德时代那古代的模式和准则了。倘若摈弃任何先入之见,站在创作者也就是该剧自身而非“他者”(the other)的立场审视之,你就不得不承认, 《九》剧无论作为一种戏剧现象还是作为一个现实存在,都有其不可抹杀的合理性与独特价值。正如有的评论者指出:“哲理、情感、情节固然是评价一出戏的标尺,但却不是仅有的标尺,这些也不是戏剧的本质特征。因为其他艺术,如小说、电视、电影也离不开哲理、情感、情节之类的东西。
戏剧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直观性、当场性。戏剧是社会成员的一种群体性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直接交流的方式。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九美狐仙》为什么受到观众的欢迎,我认为《九美狐仙》的编导在创作这出戏时,在剧场性上大作文章,把着眼点放在吸引观众到剧场里来,似乎在张罗一次集会,这是对戏剧本体的一种再认识。剧作者不以哲理、情感、情节取胜,不是让观众去苦苦思考某一个带哲理性的问题,不是去淋漓尽致地抒发一种情感,也不去编织悬念叠生的情节。在这出戏中,哲理也好,情感、情节也好,都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哲理、情感、情节在这里起着一种载体的作用,为的是承载技巧,而技巧的展现仅仅是为了吸引观众,让观众裹卷到这场群体性的活动中来。实际上,哲理、情感、情节、技巧四者形成了一种合力,使演员与观众能进行活生生的当场交流。因此,追求一种剧场性是这出戏的重要特征,这种特征不仅不违背戏剧本质,而且体现了戏剧本质。当然,我们不能说其它戏曲演出都应走这条路子,但也不能否认,毕竟它是一种戏剧样式。”(注:雷兵《这也是一种戏剧样式——川剧〈九美狐仙〉观后》,载《成都舞台》1990年第4期。 )应当承认,此乃不失公正的客观之论。
(三)
追求主题意蕴的审美选择,赋予了川剧作家的创作以“精英独白”式的话语风格。这种“精英话语”,首先以思想的力度和深度取胜,在文化反省意识上明显带有超越传统、超越大众而独自领先的先锋式特征,绝非那种让普通观众一读就懂也一览无余的接受对象。从创作角度看,其来自属于少数(不可能是多数)文化精英层的“智者”灵魂深处的理性思考,他们熟读历史也熟读现实,再由此熟读升华出对传统对社会对人生的非我莫属的独特审美体验,并将同样是他人莫可取代的哲理性反思和批判性认识融铸其中。因此,这类作品所体现出的主体意识格外自觉也格外自信。这种自觉,是来自敏感又好思考的“社会良好”的自觉;这种自信,是基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信。在他们的创作中,有一种鲜明强烈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的精神,正是这种超越传统也超越现实的“忧患意识”和“终极关怀”,促使他们力图以即使当下不被理解而日后必得敬佩的标新立异思想去警醒世人激活社会,并由此凸显出一种宗教承当式无所畏惧的文化使命感。
当年,一部《水浒传》让“巴山鬼才”读得滚瓜烂熟。读来读去,他猛然发现,在此“为英雄好汉立传”的古典小说里,“笔伐女人确系太多太多”,从武松杀潘金莲到石秀杀潘巧云到宋江杀阎惜娇,等等,时时处处流露出“轻视、歧视、仇视妇女”、把女人目为“小人、庸人、贱人、坏人”、别有用心地将她们同英雄好汉对立起来的封建男权观念。出于义愤更出于文化反思的社会责任感,他决意“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认识潘金莲”,通过对潘金莲式妇女命运反思进而审视“当代婚姻家庭问题”。(注:魏明伦《巴山鬼话》第54—57页,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从《潘金莲》到《夕照祁山》,剧作者就是这样以他特立独行的翻案戏剧和震聋发聩的话语独白,义无反顾地树立起他那不同凡俗的、带有思想启蒙亮色的文化精英式话语权威。
诸如此类作品,之所以可称“权威”,并非说它跟政治意识形态权力话语有什么直接瓜葛,而是指它以其解构传统悖逆常规的文化先锋姿态毅然打破接受大众的“期待视野”(expectant horizon), 并终将迫使他们去检讨反思自己习以为常的东西。通常,它并不指望众口一辞的当下认同(因为任何新思想新事物在世俗的接受中往往要经历从“受阻”到“解阻”的渐进过程,而且,这过程有时还会很长),但时间老人最终会给它以公正回报,在精神史和文化史上记载下它曾领先于众的斑斑足迹。对此,刻意追求精英式话语独白的作家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他们远比普通观众更懂得自己作品的生命力。从接受角度看,追求精英话语式文本编码的作家,既然其以文化反思为目标,其心目中的“潜观念”也就是“隐含的读者”(the implied reader)必是跟自己在文化素质和修养上接近的同类。同类相求,同类相感,正是在与为数同样不可能太多太多的同类们心心相印的共鸣中,文化精英们树立起并增强了破旧立新的自信。同时他们也知道,由于素养和识见的差异,他们那多少带有先锋思想的作品刚出世总是难免招致众庶的冷眼或情绪抵触(且不说关于《夕》剧的褒贬不一迄今犹然,即使如《山杠爷》,在电影已捧大奖后再搞川剧也屡屡得到好心人的劝诫,因为它毕竟写了一个违法下狱的老共产党员);由于他们打破了常人的思维惯性(惰性),就像偏偏在讳言灯泡、亮光的阿Q面前说了发亮担忧灯泡, 故而他们不奢望在众庶面前获得当场赞许的世俗效应。就此而言,他们与其说是在俯下身子寻求与普通大众同等水平的对话,不如说是在以居高临下的姿态面对芸芸众生进行启蒙式的精神布道,也就是不求从众惟求出众,重在抒发作为思想者的作家体悟人生的内心独白。好在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开放宽松的时代,文化精英式的话语独白即使暂时不被理解,也必将随着时光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而获得更深刻的认同接受。也就是说,只要你写出了好作品,就不用担心会永世埋没。
追求舞台技艺的审美选择,赋予了川剧艺术的演出以“大众对话”式的话语特征。跟前一类型有别,此类作品并不刻意求取主题意蕴的深沉厚重,而是把艺术创造的激情和灵感都留给了舞台形式美的发掘与展示上,并由此在赏心悦目的大众化娱乐中寻求与普通观众更轻松也更广泛的心理沟通。可以说,这在话语形式上更趋近于平民化气质的“大众话语”。也许,有的习惯于“玩深沉”的素养较高的观众,看完热热闹闹一台戏(尽管看戏的当口也被台上的精彩火爆吸引得十分投入),走出剧场之后总觉到剧情内容少了那么些余味可品。但是,对于幅面更广的文化层次一般的绝大多数观众来说,他们走进剧场就为的是暂时隔断一下与日常生活的联系,通过“看热闹”式观剧的游戏化审美活动找找乐,放松放松绷紧的神经,调适调适自我情绪,一旦跨出剧场,他们马上就得返回自己的生活而再没必要纠缠在戏剧家所制造的审美梦幻之中。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戏剧当然就是有益无害再好不过的精神调节剂和心理慰藉品。
人与人不同,花有百样红。这个世界本来就五颜六色多姿彩,你大可不必把自己的眼光和心灵逼入一条狭窄的胡同,去只赞美朝阳的蓬勃向上而冷落夕照的余辉无限。“谈到趣味无争辩”,有人爱看悲剧也有人爱看喜剧,有人喜欢深沉也有人喜欢轻松。正视这点,承认这点,便意味着审美趣味修养上走向成熟。而用此成熟的心态去对待和评价当代川剧的种种现象,你自然就懂得尊重对象各自的特性,再不会茫然或者武断了。
事实上,像《九美狐仙》之类孜孜追求舞台形式美和娱乐观赏性的剧作,其编导者着手创作之初就已把心目中的“潜观众”定位在广大普普通通的受众。他们之所以在剧情内容和主题寓意上无意“玩深沉”,从根本上讲,与其说是不能勿宁说是不愿,因为,他们的创作初衷就是要以轻轻松松了无阻碍的游戏化审美形式单刀直入地征服观众赢得观众(权且生造“玩轻松”一词来称呼之)。既然不同的剧作承载着各不相同的艺术使命,那么,前述那种精英独白式的文本编码和话语风格在此情此景中不适用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也就是说,在戏剧审美中,“玩深沉”者自玩深沉,“玩轻松”者自玩轻松,各行其是亦各得其乐,没必要也不可能将此两条道上的车强拉在一条铁轨上,对此,有的看戏者未必如我们的写戏者那样心中有数。在话语选择上放弃了居高临下的精神独白,艺术家的创作便走下了布道的高高讲坛而溶入大众之中,以平易的姿态寻求着与后者心灵沟通的共同话语, 顺应着他们的认知图式( schema),满足着他们的心理期待,从而实现与之的精神对话。而且,恰恰是通过这种娱乐氛围的营造和平等对话的成功,“大众话语”式剧作的剧场号召力和艺术生命力方得以确证。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出“精英话语”式剧作与“大众话语”式剧作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效应:一追求不与人同的出众,一旨在世所认同的从众;一在超群拔俗中显露思辨的理性光辉,一在随众从俗中体现娱乐的游戏色彩;出众者重独白精神布道,从众者重对话式大众沟通;前者的取胜之道在张扬主体意识的先锋性与个体性,后者的成功之路在寻求大众审美的群体性与共享性……
上述两类作品,前者有精英艺术趋向,后者有大众文化效应,二者共存互补为满足当代观众日趋多元化的审美需求提供着可有偏重却不可偏废的精神消费对象,同时也为20世纪90年代川剧勾勒出丰富而绝不单一的多声部话语风貌。当然,作此区别仅仅是一种形态上的相对划分以便于论述而已,两者在当代川剧文化的整合格局中并不截然割裂更谈不上彼此对立(事实上,有的作者就兼跨两类,如《山杠爷》和《九美狐仙》就出自同一编剧之手)。此外,拈此两类作品来探讨当代川剧艺术的审美选择及话语风格,意在管中窥貌向同仁提供一得之见,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对川剧当下生命状态的丰富性与多面性的忽略或漠视。总而言之,跟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发展同步,二者或者说多元话语交织共生的90年代川剧更具备一种民主气息和包容精神,这意味着其在文化观念上的走向成熟。有此开放的心态和自由的选择,行将跨入21世纪的川剧必将创造新的辉煌。我们期待着。
标签:精英文化论文; 川剧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文学论文; 戏剧论文; 剧场论文; 精英教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