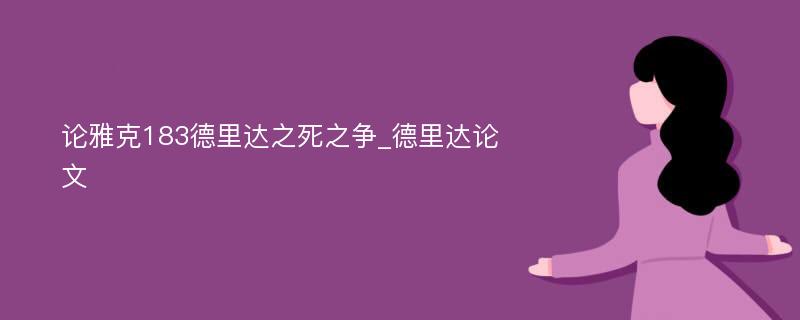
评雅克#183;德里达去世所引发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克论文,德里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10月9日,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因胰腺癌在巴黎病逝,世界各大报纸、电视和网站等媒体对此作了广泛的报道,有的对他学术观点和成就不屑一顾,甚至大加嘲讽和批判;有的则肯定和颂扬了他对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论的贡献。一时间对德里达的评论再次引发西方批评理论界对解构主义及其意义的争论,这不仅是两种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也是“文化之争”和“理论之争”的继续,是“9·11”事件后西方批评界各派别之间各种深层次矛盾的反映,值得我们关注、分析和研究。
一、德里达去世所引发的争论
美国《纽约时报》2004年10月10日在头版上发表了乔纳森·坎德尔一篇题为《晦涩的理论家雅克·德里达去世,享年74岁》的悼文。文章从标题便把德里达描述为艰深晦涩的思想家。悼文在报道完德里达去世的消息后,便以嘲讽的口吻来概括解构主义,说“这种研究方法认为所有的作品都充满混乱和矛盾,作者的意图无法克服语言本身的内在矛盾,因此剥夺了文本——不论是文学、历史或哲学文本——的真诚性、绝对性和永恒性”。(注:Jonathan Kandell,"Jacques Derrida,Abstruse Theorist,Dies at 74",The New York Times,Oct.10,2004.)接着他评述道:“尽管德里达有庞大的追随者,但他不仅是人们仰慕的对象,而且也是愤怒的对象。特别是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他是法国思想流派的化身,他们感到他的思想瓦解着许多古典教育的传统标准,是一种常与制造分裂的政治事业相联系的流派。”(注:Jonathan Kandell,"Jacques Derrida,Abstruse Theorist,Dies at 74",The New York Times,Oct.10,2004.)在评论解构主义方法的运用时,他说:“文学批评家将文本分成孤立的片段或短语去发现隐藏的意义。宣扬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和第三世界事业的人把这一方法视为工具,用来揭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弗洛伊德和其他西方文化中‘死去的男性白人’偶像的偏见和矛盾。”(注:Jonathan Kandell,"Jacques Derrida,Abstruse Theorist,Dies at 74",The New York Times,Oct.10,2004.)“令其他批评家感到不安的是那些毫不知名的学者可以通过找出索福克勒斯、伏尔泰或托尔斯泰杰作中的文化偏见和不准确的语言擅自诋毁他们。”坎德尔特别提到“德曼事件”和“海德格尔事件”来说明德里达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糊其词,遮遮掩掩。从上述的引语中人们不难看出,在坎德尔的眼里,德里达简直就是故弄玄虚、混淆是非、颠覆西方传统基础、制造异端邪说的危险分子,他的去世似乎是人类的一件幸事。
《纽约时报》的悼文一发表即刻引起美国学界的轩然大波,一些知名学者纷纷致函该报,一方面对这份自诩中立的报纸发表这样一篇偏见无知的悼文感到惊讶,另一方面则强烈反击美国右翼掀起的反知识分子浪潮。10月13日美国西北大学的塞缪尔·韦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肯尼斯·莱因哈特以及斯皮瓦克和米勒等几十位教授联名致信《纽约时报》,抗议该报发表这样一篇诋毁德里达的悼文。信中尖锐地批驳道:“乔纳森·坎德尔10月10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关于德里达的悼文既无知又心胸狭隘。把德里达——20世纪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描绘成‘晦涩的、极其令人费解的理论家’是运用了诸如简单或清晰这样的标准,这实际上是取消了刚过去的世纪中所有重要的思想家的资格,其中包括爱因斯坦、维特根斯坦和海森伯格。更糟糕的是,悼文以毫不掩饰的恐外心理把德里达的著作以及通常的解构主义描绘为另一个‘出自二战后法国的……时髦的、含混的哲学’。事实上,德里达的作品主要研究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从《圣经》到莎士比亚、康德和《独立宣言》的西方传统中的重要著作——他从未像坎德尔暗示的那样,提出把它们当作‘死去的男性白人’的作品而予以抛弃。德里达是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不倦的批评者。”(注:Samuel Weber and Kenneth Reinhard,"Weber Reinhard Letter",http://www.humanities.uci.edu,Oct.13,2004.)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修辞与比较文学教授朱迪思·巴特勒在10月13日撰文说:“乔纳森·坎德尔的那篇讽刺和诽谤性的悼文利用这位颇有造诣的哲学家逝世的机会来重新发动肯定是早已过时的文化战争。……如果说德里达对哲学、文学批评、绘画理论、传播学、伦理和政治学的贡献使他成为这一时期国际上最知名的知识分子,那恰恰是因为他思想的精确,他的思维方式总要表现出卓越的和出人意料的变化,因为他总是不断努力去思考道德和政治上的责任。坎德尔说德里达损害毁谤经典、抛弃真理,但是德里达却是通过阅读柏拉图和卢梭等人的著作而成名的,任何读过他近年来发表的著作的人都清楚,真理、意义、生与死的问题——哲学的永恒问题——都是他最为关注的。这篇极端无礼的悼文无法诋毁德里达,因为人们阅读德里达著作的热情将丝毫不会减退,它反而是给撰写和发表悼文的那些人蒙上一层阴影。为什么在这个迫切需要批评思想的关键时刻,《纽约时报》却要与那些反动的反知识分子思潮为伍?”(注:Judith Butler,"Letter to The New York Times",http://www.humanities.uei.edu,Oct.13,2004.)
美国威廉斯学院人文学教授马克·C.泰勒对此也感到愤慨,他撰写了一篇题为《德里达的原义究竟是什么?》的文章投给《纽约时报》。为表示公允该报在10月14日的专栏里发表了这篇文章。泰勒教授首先充分肯定了德里达一生的贡献,称其同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一样,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三位哲学家之一。泰勒说:“在过去的百年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像他那样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和不同的学科里对人们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哲学家、神学家、文学和艺术批评家、心理学家、史学家、作家、艺术家、法律学者甚至建筑师都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了极具洞察力的方法,这些方法使艺术和人文学科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出现了非凡的复兴。”(注:Mark C.Taylor,"What Derrida Really Meant",The New York Times,Oct.14,2004.)针对坎德尔指责德里达是晦涩的理论家,泰勒回应道:“对那些着迷于电视片段和头天晚上民意测验结果的人来说,德里达先生的著作似乎极其晦涩难懂。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不可能被轻而易举地归纳或简化为一两句打趣的话。然而他的著作的晦涩性反映了所有伟大哲学、文学和艺术著作所具有的难懂性和复杂性特点。”(注:Mark C.Taylor,"What Derrida Really Meant",The New York Times,Oct.14,2004.)
德里达的诋毁者把他视为颠覆西方道德、真理和价值观念的虚无主义者,是主张“怎么都行”的相对论者,声称他的思想让人躲避道德责任。虽然德里达质疑绝对真理和认识的存在,但他并未宣扬松懈伦理道德准则或怂恿人们随心所欲,而是要质问这些伦理道德准则,找出那些与普遍接受的看法不同的地方,认识我们思想的潜在局限性和矛盾。泰勒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在他的批评者眼里,德里达先生像一个威胁西方社会和文化基础的有害的虚无主义者。通过坚持认为人们不可能确切地认识真理和绝对价值,他的诋毁者认为他暗中破坏了做任何道德判断的可能性。他们认为,追随德里达,就是开始了走向怀疑论和相对论的下滑之路,必然会使我们无法负责地采取行动。这是一项重要的批评,需要我们认真地回应。像康德、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一样,德里达也认为我们无法把握透明的真理和绝对的价值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这样一些认知范畴和道德原则,如平等和正义、宽宏大量和友好感情,因为没有它们我们便无法生存。相反,认清指导我们行动的思想和准则中有不可避免的局限和内在矛盾是十分必要的。没有批判性的反思不可能有合乎道德的行动。”(注:Mark C.Taylor,"What Derrida Really Meant",The New York Times,Oct.14,2004.)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德里达逝世之机抨击他的媒体并非《纽约时报》一家。《华尔街日报》2004年10月12日发表了罗杰·金布尔题为《意义的无意义性——雅克·德里达去世,但他的有害思想将继续存在下去》的文章。文章说:“即使人们无法界定解构主义,但可以对其进行描述。首先解构主义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终身的保证,即对任何题目的讨论都变得让人无法理解。它通过语言的游戏来做到这一点。解构主义的一个重要口号是‘文本之外一无所有’。”(注:Roger Kimball,"The Meaningless of Meaning,Editorial Page",The Wall Street Journal,Oct.12,2004.)文章指责德里达用令人生畏的词汇和深奥的哲学用语包装自己,使自己成为学术明星。金布尔说:“解构主义向它的追随者承诺,不仅可以从真理的负担中解放出来,而且还有可能进行一种极端的活动。对语言合法性的打击也是对语言生存其中并产生意义的传统的打击。通过消解真理的概念,解构主义者也在消解价值的概念,包括已建立起来的社会、道德和政治价值观念。”(注:Roger Kimball,"The Meaningless of Meaning,Editorial Page",The Wall Street Journal,Oct.12,2004.)英国的《泰晤士报》2004年10月11日也以《德里达死了吗?——解构死亡的概念基础》为题发表了一篇嘲弄德里达思想的短文。文章开头便质问:“在雅克·德里达去世这件事上有任何确定性吗?悼文的作者们尝试客观地将他的生命置于有限的语境中,这不可避免地要受一种认知相对论的影响,即所有这样的科学理论不过是‘叙事’或社会建构。当然后现代主义者在解构它们的意义时肯定要质问先前科学的概念基础——其中包括德里达自身的存在——它们本身已变得问题化和相对化了。这种概念上的革命对未来具有深远的意义。上帝死了吗?”(注:"Leading articles",The Times,(http://www.timesonline.co.uk/),Oct.11,2004.)
二、争论背后的原因
对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批判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者便抨击解构主义是一种极端的运动,旨在破坏“规范、传统、西方文明、经典和真理”(注:Ross Benjamin,"Hostile Obituary for Derrida",http://www.thenation.com,Nov.24,2004.)等一切被大家视为神圣的东西。罗斯·本杰明在她的《充满对德里达敌意的悼文》一文中指出,“当时右翼分子在发动一场反对‘获高校终身聘任的激进分子’影响的战役,这个名称就是新保守主义者罗杰·金布尔1990年6月在《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冗长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德里达在艾伦·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1988)和林恩·切尼的《讲真话》(1996)中曾遭到极其严厉的批驳”(注:Ross Benjamin,"Hostile Obituary for Derrida",http://www.thenation.com,Nov.24,2004.)。美国保守主义者把解构主义同激进的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道视为影响美国学术界的有害思想,认为解构主义的出现使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如获至宝,使他们在公开抗议活动失败后把斗争的舞台转移到高校的课堂上。他们认为宣扬虚无主义和相对论思想的解构主义侵蚀着美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肌体,破坏着美国文化和道德的基础,因此要予以反击。
“德曼事件”和“海德格尔事件”使反德里达的浪潮达到顶峰,也使德里达和解构主义思想的声誉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德里达去世后几乎所有批评他的文章都重提这两件事,指责他为德曼开脱罪责。众所周知,德里达是犹太人,少年时曾被纳粹分子开除学籍,他憎恶和反对纳粹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并未因为德曼年轻时所写下的亲纳粹的文章而宽恕他,而是试图挽救德曼后期的著作,不想因此而将他对文学批评理论的贡献一笔勾销。本杰明在她的文章中还指出坎德尔现在重提这件事却没注意到“德里达一生写过不少文章论述犹太人身份和大屠杀对保罗·策兰和艾德蒙·杰贝斯创作的影响”(注:Ross Benjamin,"Hostile Obituary for Derrida",http://www.thenation.com,Nov.24,2004.)。至于德里达受海德格尔的影响,本杰明说:“人们很难找到一个白海德格尔发表《存在与时间》这部著作以来,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他影响的犹太哲学家,其中包括汉娜·阿伦特、赫伯特·马尔库塞和伊曼努尔·莱维纳斯。”(注:Ross Benjamin,"Hostile Obituary for Derrida",http://www.thenation.com,Nov.24,2004.)
德里达生前就是一个屡受抨击的人,他去世后有人利用这个机会对他大加诋毁可以说是意料当中的,然而正如个别西方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对德里达的嘲讽和诋毁绝不仅仅是针对他个人的。理查德·李在题为《相对的思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假如这种谴责只限于一个时髦的法国思想家,或许不会如此令人沮丧,但事实上,对德里达的攻击恰恰是对学术界人士和知识分子所发动的更为广泛战役中的最新一轮攻击。学术界被描绘为外国观念的温床,是那些不能直言不讳、不能正确思考、甚至不想尝试这样做的危险相对论者的场所”(注:Richard Lea,"Relative Thinking" ,http://books.guardian.co.uk,Nov.18,2004.)。自第一次海湾战争、特别是“9·11”事件以来,在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美国不断出现形形色色反“主义”和“理论”的浪潮。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思想的阐释和解构使他的思想方法被女权主义、少数族裔以及第三世界和其他受压制的群体广泛利用,成为斗争的武器,尽管他们或许并不完全接受他的思想。德里达在这方面的影响是其成为新保守主义者主要抨击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前美国对外实行强硬的单边主义政策,出兵伊拉克,威胁对某些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对内推行新保守主义政策,以“反恐”为名限制民众的自由。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学者公开谴责一些报纸对德里达的毁谤,实际上是对这起反知识分子浪潮的回应。斯皮瓦克在她本人致《纽约时报》编辑的信中说:“德里达确实是位有争议的人物。他关注的不是揭露错误,而是分析我们是如何创造真理的,这正说明他的工作就是坚定地追求正义和民主。当美国由于傲慢而受到世界的谴责时,你们的报纸发表这样一篇无知并带有恐外心理的文章,特别是当抨击对象已无法作出回应时,这与你们报纸的声誉是完全不相称的。”(注:Gayatri Spivak,"Letter to The New York Times",http://www.humanities.uci.edu.)特里·伊格尔顿也给《卫报》写了一篇短文,呼吁人们不要嘲弄德里达,认为他是战后法国最著名的一位思想家,是政治上坚定的左翼人士,并讽刺在《卫报》上对德里达去世做出糊涂和愚蠢反应的那些人的无知和偏见。”(注:Terry Eagleton,"Don't Deride Derrida" ,The Guardian,Oct.15,2004.)德里达虽然已去世,但是围绕他学说的争论还将继续。重要的是人们研究德里达时,还应关注他晚期的著作,他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认识以及他的宗教观,他对“9·11”等政治事件所作的评论,从演变和发展的角度来进一步理解和认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