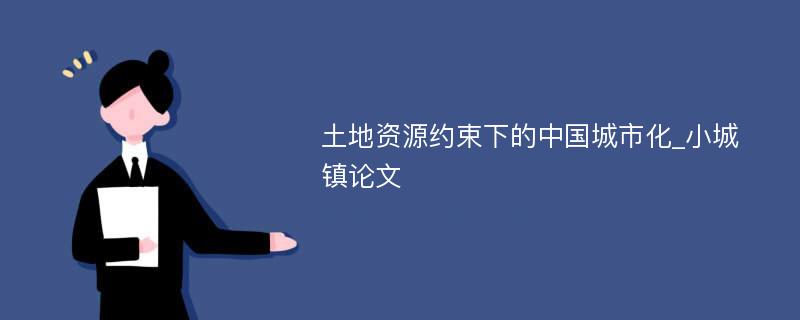
土地资源约束条件下的中国城市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中国论文,土地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化是指在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非农产业及其人口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逐渐聚集到城市,从而使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大,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和城市地域范围显著扩张的过程。城市化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变农村地域为城市地域,即城市化的数量过程;二是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等城市文明在农村地域的扩散,生产要素的聚集,经济结构的演进等,即城市化的质量过程。
从发展的类型上看,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大致可归结为三类:一是村镇转化型,依托乡镇工业、集市贸易或矿产资源开发等非农产业,人口向建制镇聚集,体现为小城镇的繁荣;二是大城市扩展型,依托服务业和都市工业,人口向大城市及其边缘地带转移和集中;三是中小城市扩展型,依托服务业和工业,人口向地市级城市或县城集中。与此相对应的是,理论界对中国城市化应该选择以小城镇为重点,还是以大城市为重点,抑或以中小城市为重点,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
实际上,城市化是随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前进的过程,一个城市的规模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地理、历史沿革等复杂因素。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显然是小城镇、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缺一不可,但无论是发展小城镇、大城市或中小城市,我们都必须考虑到土地资源的约束。因为,中国拥有全球22%的人口,却只有全球7%的国土面积,9%的耕地,6%的可更新淡水资源。人均土地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土地资源约束。
一、建国以来的20多年中,土地没有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约束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20多年中,非农产业占用耕地始终没有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屏障,其原因主要是推行单一的工业化战略。20世纪50年代,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推进,资金集中在直接生产部门,为了赶超型的发展战略,只有尽量减少“非生产性”的基础设施投入,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缓慢,没有形成巨大的用地需求。毛泽东在1953年讲过一句话:“我看城市大了不好,要多搞小城镇”。国家建委在1955年9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今后新建的城市原则上以中小城镇及工业镇为主,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建设少数中等城市,没有特殊原因,不建设大城市”。“新建的工厂应分散布局,不宜集中”。由此,控制大城市和分散布局,就逐步演变成中国的城市政策。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剧烈的跳跃和跌落。首先是1959~1960年超越客观条件的城市膨胀,仅两年时间城镇人口就增加了2352万,增长了22%,城市化水平提高了3.5%。之后,由于政策失误和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供给成为了大问题,减少城镇人口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政策。据1963年6月统计,城镇人口两年内减少2600万。
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到70年代,在国际环境变化和政治运动的背景下,200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和干部下放到农村,出现了“逆城市化”。
那个历史时期城市化政策的直接结果是:1949~1978年的近20年时间,城市化率从11.2%缓慢上升到17.9%,年均仅提高0.23个百分点。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城市数目是132座,到1978年城市数目仅192座。其中100万人及以上的城市13座,50~100万人的城市27座,20~50万人的城市60座,20万人以下的城市92座。[1]
二、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间,土地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约束逐渐显现
1978~1998年的20年中,中国耕地减少了5%,但粮食产量却增长了68%,即粮食单产水平提高了76.5%,说明体制、投入和科技进步促进了主要农产品的单产水平不断提高,可以保障国内农产品供求的大体平衡。在这样的条件下,虽然加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了大量的土地,但由于体制、投入和科技进步所保障的农产品供给,使得从农业中释放大量的土地资源成为可能,我们并没有明显的感觉到土地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约束。这同时也麻痹了一些人们的视野(尤其是那些没有遭受过饥饿的人),他们认为,“泱泱大国、天国上邦、物产何其丰富,占用点耕地并不算什么”。
但是在1998~2004年的这6年间,耕地面积减少了6%,粮食产量也减少了8.4%,说明通过体制、投入和科技进步促进粮食单产水平提高的潜力已经释放得差不多了,耕地保有量直接成为了粮食增产的约束。或许有人提议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增加进口来保障国内的粮食供给,何必非要自己生产。当然,如果从外汇储备单方面来看显然是可行的,中国有超过5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绝对能够买得起粮食。问题是中国这样的大国能否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样靠进口保吃饭。按目前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仅“十一五”期间就要再增加4000万人。目前的年人均粮食消费在380公斤上下(是在至少有5亿多自给自足农民条件下的消费水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膳食结构的改善、城市化率的提高,人均粮食消费水平至少会提高到400公斤(也只有中国台湾的水平,仅为美国的一半),那么到“十一五”后期中国的粮食总需求就将达到5.36亿吨。[2] 如果国内粮食的单产水平难以提高,耕地继续减少,国内粮食产量将很难保证到4.8亿吨,结果将出现近6000万吨的供给缺口。国际粮食市场的年总供给量长期以来稳定在2亿吨左右,早已被亚非国家的稳定需求所吸纳,国际市场几乎不可能满足我国的粮食缺口。我们再看远一点,有专家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规模将达到16亿,如果仍按400公斤的人均消费能力,届时将形成6.4亿吨的消费需求,显然更加不可能依赖国际市场来满足粮食供给缺口。
因此,在“十一五”期间,工业化和城市化将首次面临土地资源的约束。
三、土地资源约束下的城市化
1978~2003年,城市化率从17.9%提高到40.53%,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城市化速度约为改革前的4倍。相应的,城市的规模和数量获得了空前的增长,城市数量由1978年的192座增加到2000年的663座。在城市规模和数量增加的背后,是耕地资源的急剧减少,国土资源部的土地变更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耕地面积由1996年10月底的19.51亿亩,减少为2004年10月底的18.37亿亩,耕地净减少1.14亿亩,人均耕地由1.59亩降为1.41亩。同时,实现了耕地占补平衡的建设用地还没有包括在减少的耕地里面,数量上的占补平衡并不能代表质量上的占补平衡,如果从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看,减少的耕地实际上还不只这个数。国土资源部的土地变更调查结果显示:2004年各项建设占用耕地总体实现了数量上的占补平衡,但却存在着占优补劣的问题。比较建设占用耕地质量与补充耕地质量,2004年度各项建设占用的耕地中有灌溉设施的占72%,补充耕地中有灌溉设施的仅占34%;建设占用的耕地多数是居民点周边的优质高产良田,补充的耕地多来自未利用地的开发。
在耕地的数量急剧减少和质量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应该推进怎样的城市化?笔者认为:
1.通过城市化战略来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三农”问题全面解决的总体思路不能动摇。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在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的指导思想下,通过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把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和城市中,与此同时,把城市遭遇到的困难(如就业、食品供应、社会保障等问题)向农村转移,其结果是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典型“二元结构”,城乡差别非常明显。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三农”问题,从政策到资金上都对解决“三农”问题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但就其整体性解决和根本性解决的目标而言,目前尚有很大的距离。
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而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唯有靠实施城市化战略才能够最终完成。如果将现有农村人口从占全国总人口约60%的份额降低到25%左右,农村土地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才可能达到一定的程度,农业的科技含量和劳动生产率才可能有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才会发生根本性地变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才会实现,“三农”问题才能得以彻底解决。
2.发展大中城市,通过大中城市内容丰富的服务业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后,在农村率先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释放了农业的活力,农产品由紧缺变为丰富,农民的收入水平获得了极大地增长,形成了巨大的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的扩张和政策的松动,直接催生了乡镇企业的蓬蓬发展,以乡镇企业为推动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城镇化。在市场经济的初期,这一策略的确很好地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了20来年以后,大城市集约化经济的优势开始显现出来,它们能够迅速吸收和创造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孕育新的观念,形成巨大的生产和流通能力;它们能够有效地聚集各种要素和资源,形成现代服务业和知识服务业的产业集群,提供广阔的就业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效率,增进经济和社会效益,并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带动一大片区域的繁荣和进步。大城市的这些优势是小城镇所无法望尘莫及的,发展大城市也因此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乃至条件较好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趋势。
大城市的规模效益不仅仅体现在聚集资源、产业的创造和升级、扩大就业等方面,还体现在集约用地上。根据有关专家测算,按照城市建成区面积来统计,中国2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及20万左右人口的小城市和万人左右的小城镇比较,人均占地面积是1∶2∶3.1,[3] 小城镇占地面积比小城市多2倍,比大城市多3倍。中国现在的城市人口不到5亿,如果按照75%城市化率的现代化标准或按照每年不低于1%的城市化率增长速度来估计,未来还将有4亿左右的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如果让小城镇来消化,那得需要多少耕地?
另外,城市的景观、道路、交通、水、电、气、公园、教育、医疗等等,大多由政府投资兴建,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范畴,对于这些公共产品而言,使用的人越多、效率就越高,也越能够刺激政府增加投入,城市的功能越来越完善,品位越来越高,形成良性的发展循环。反观小城镇,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投入能力,也就难以提供足够完善的城市功能,从而进一步制约产业的升级和形成新的就业需求。
或许,有人会说发展大城市必然会引发“城市病”,并拿北京、上海的交通拥堵做例子。实际上,所谓的“城市病”是可以通过科学的规划与管理来克服的。中国澳门的人口密度和车辆密度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在澳门很少见到堵车的现象;中国香港每公里的汽车数也高于北京,然而香港也没北京那样堵车。当然,城市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它也有一个最优的规模范围,城市专家的测算表明:当城市规模小于10万人或大于1000万人时,它的规模效益都比较低;城市的最优规模是100~400万人口。
3.发展重点乡镇,推进撤乡并镇,加强土地整理。
我国1980年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以及1990年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小城镇大战略”的发展方针,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小城镇遍地开花,数量急剧膨胀。1949年,全国有建制镇2500多个;经过36年的发展,到1985年也只有2851个,加上未设建制的县城377个,共有3228个;而到了1992年,建制镇就达到14182个,短短几年时间就增加了近5倍。如果加上30000多个非建制镇,小城镇总数达到44000多个;到1999年,建制镇数目达到19000多个,加上非建制镇总数接近60000个(这是处于峰值时候的数据,此后开始回调)。[4]
建制镇膨胀最快的时期也恰好是中国乡镇企业发展最好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末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式的乡镇工业已经风光不在,依靠乡镇工业的发展而使经济腾飞的乡镇毕竟是少数,并且大多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如果把960万平方公里中的未利用土地(26%)、林地(24%)、牧草地(28%)、水域(4%)排除在外,仅剩下172.8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那么60000个小城镇的平均占地面积仅有28.8平方公里。如果再以这个小城镇数目来推进城市化,那耕地的减少会何其之快是不难想像的,况且,并不是每个小城镇都有足够好的资源、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来聚集人口,很多缺乏发展基础条件的小城镇是期望通过“圈地运动”、“造城运动”来塑造形象工程或发点“土地财”。因此,笔者认为,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很有必要实施撤乡并镇工程,着力发展资源、区位和产业基础较好的重点小城镇。
另外,原来的乡镇工业和小城镇发展战略并不能让农民在实现职业转移的同时,实现居住上的空间转移,这样也就限制了农村土地的有效流转和土地的重新整理。在人口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城市人口增加推动了城市的扩张,产生占地需求;相应的乡村人口必然减少,用地也理应减少,通过土地整理可以增加耕地供给。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用地比乡村用地更加集约,人均占用土地必然会产生差额;另一方面是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人均土地面积增加,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土地合并,减少部分机耕道或田埂等,增加耕地面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