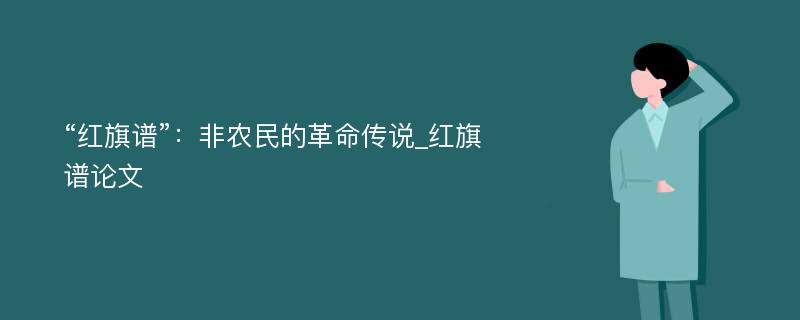
《红旗谱》:非农民本色的革命传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色论文,农民论文,传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7-0103-07
1958年1月,梁斌《红旗谱》的出版发行,无疑推动了新中国红色经典的创作热潮。这部洋洋80余万言的鸿篇巨制,以发生于冀中平原的革命风暴为时代背景,以朱老忠和严江涛为故事情节的主人公,气势磅礴地再现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在《红旗谱》问世后的40多年时间里,国内学界曾对其给予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义阐释——现代农民革命的“历史画卷”① 与“复制革命历史”的媚俗之作。②但无论人们是“褒”或“贬”,他们喋喋不休的争论焦点,主要还是有关“宏大叙事”的真实性问题。而我个人的阅读体会却完全与众不同:《红旗谱》并非是描写什么“农民革命”,“农村”与“农民”都只不过是一种艺术载体,作者自身的真实意图,是要表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理想。然而,“农民阶级”并不等于“无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故梁斌把朱老忠等农民直接写成“无产者”,则充分反映出了他本人理论修养的先天不足;“艺术想象”也不等于“历史真实”,这是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故论者不加分析地将两者机械“对位”,则又集中体现了他们审美判断的重大失误。因此,本文将以作品文本为事实依据,以“错位”与“移植”为理论视角,去客观还原《红旗谱》的创作理念,并附带谈一下这部“红色经典”的艺术缺陷。
一、“农民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概念置换
梁斌说他创作《红旗谱》,“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写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文本实践,又被归结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于多少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梁斌来说,他当然知道“中国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但由于参与革命者基本上都是“来自农村或农民出身”的历史缘故,所以他必须去大力提升农民“同盟军”的精神境界,以便使其具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文理想。③ 这应是作者艺术策略的高明之处。而新老论者却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他们将朱老忠等农民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英雄行为”,视为是“工人阶级崇高感情”的集中表现;④ 强调《红旗谱》雄浑悲壮的“革命叙事”,生动地揭示了落后农民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员的内在契机”。⑤ 由此可见,无论是作者还是论者,他们都有意识地混淆了“农民”与“工人”的阶级属性,并在概念混乱的逻辑关系中实现了“阶级”身份的相互置换,进而造成了人们对于《红旗谱》人物形象的判断失误。
《红旗谱》绝不是一部书写“农民革命”的英雄史诗,而是一部借助于农民形象去表现无产阶级政治理想的艺术读本。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哲学的理论核心,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马克思始终认为现代产业工人,由于被彻底剥夺了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所以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反观马克思对于农民的态度,却是十分悲观的,他在《共产党宣言》中不仅视农民为“保守”,甚至还认为他们的思想“是反动的”。⑥ 原因就在于“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故马克思反复强调农民如同散沙而“没有形成一个阶级”。⑦ 那么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革命,究竟是怎样“在缺少无产阶级基础的情况下使这项事业获得成功”呢?⑧ 这恐怕是所有外国学者都在共同关心的理论命题。其实,毛泽东早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初期,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农业无产阶级”的独特概念,⑨ 他将富有农民与贫苦农民划分为两大阶级利益集团,⑩ 进而根据“穷则思变”的逻辑推论,(11) 理所当然地赋予了农民以“阶级性”和“革命性”,并一再告诫党内人士:“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12)
梁斌对于毛泽东有关“农民革命”的思想理论,应该说是心领神会、揣摸透彻并且也表现得十分到位,《红旗谱》中那些“最聪明、最智慧”的普通农民,他们之所以“阶级意识非常清楚”,“具有那样坚强的反抗性格”与“高贵品质”,(13) 恰恰是艺术化地诠释了政治领袖的“农民革命”说。然而,梁斌从其动笔伊始就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现实难题:朱、严两家与“锁井镇”的多数农民,基本上都是些小有资产的“自耕农”,像朱老忠家有三间土坯房、几亩薄地和一头牛犊,严志和家有几亩“宝地”、一头耕牛以及房产,其他人如朱老明、朱老星、伍老拔等人物,也都有房有地、养猪喂牛、经济上自给自足,这些农民在毛泽东的阶级论述当中,显然还不是那种“穷则思变”的贫苦农民,而是属于安于现状的小资产阶级“中间”势力。(14) 也许梁斌写的的确是当时农民的实际状况,但是为了要真实地再现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原貌,就必须使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无产阶级化”,也就是说,必须对自己笔下的农民形象进行大规模的人为改造——“改造”不仅导致了农民精神品格的巨大变异,而且也导致了农民社会身份的严重错位。这是人们在评价《红旗谱》时,往往容易忽略的审美盲点。
首先,作者以无产阶级的集体意识,去置换落后农民的个人意识,进而全面遮蔽了他们自身思想的先天不足。《红旗谱》的故事情节,是从朱老巩与严老祥的“护钟”斗争开始的。恶霸地主冯兰池“砸钟”的真实目的,是要“存心霸占河神庙前后那四十亩官地”;故朱、严两家老辈人的“护钟”行为,也就变成了维护公共财产的英雄壮举。作品开篇就赋予了老辈农民以无产阶级所特有的大公无私的思想品格。而作者“把朱老忠从小就放进强烈的阶级冲突的环境中”,其主观用意就是要去培养他的“阶级意识”与“叛逆性格”。(15) 十分有趣的是,为了强化朱老忠与现代“革命”的必然联系,作者为其精心设计了一个因“破产”而外出“闯关东”的微妙伏笔——“流浪无产者”(尽管返乡后他仍然置地盖房、恢复祖制)的附加身份,使他获得了与无产阶级直接对等的社会地位;而打工淘金(当然是指古老而原始的集体劳作方式)的苦难经历,又使他具备了与无产阶级完全相同的政治素质。所以,重新回到“锁井镇”的朱老忠,其实早已是个“脱胎换骨”后的“新人”形象:“农民”只是他的外在躯壳,“革命”才是他的真实灵魂。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变得侠肝义胆、无私无畏,“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比如,他卖牛犊帮江涛到城里去读书上学,为的就是要让农民后代掌握文化知识,不再饱受地主恶霸的剥削压迫;他得知朱老明身染重病、卧床不起,二话没说“掏出十块钱,望炕上一扔”,“你先治病,别的我打发孩子们送来”;运涛被捕入狱,严家大难临头,关键时刻又是他挺身而出,“穷弟兄同生死共患难——天塌了有地接着,有哥哥我呢!”如果说朱老忠的豪侠之气,仅仅是一种人物性格的个例现象,那么我倒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当看到严志和与朱老明等人也都具有团结互助的高尚情操(如为了共同利益村民抱团与冯兰池打官司,即使是变卖土地、倾家荡产也再所不惜;又如大家慷慨解囊、纷纷出钱去资助江涛读书,即使自己揭不开锅饿肚子也毫无怨言等等),似乎“助人为乐”早已是“锁井镇”贫苦农民的阶级本能时,我们就不能不对其深表怀疑了。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阐释中,“产业工人”之所以不同于“落后农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无产无业”、无所牵挂,故其“集体主义”的生存环境,必然会造就“超越自我”和“利他主义”的精神境界;而“落后农民”之所以不同于“无产阶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产有业”、有所顾忌,故其分散农耕、独立经营的生活习惯,又必然会产生“自私狭隘”与“目光短浅”的“利己”根性。(16) 梁斌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品质去全面置换朱老忠等人的农民意识,这种置换虽然使其在艺术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却客观否定了他笔下那些“革命英雄”的农民本色。
其次,作者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去置换落后农民的保守观念,进而人为强化了他们自身缺乏的政治信仰。阅读《红旗谱》所得到的突出印象,就是“锁井镇”村民根深蒂固的复仇情绪。从朱老巩临死前吼出的农民与地主“势不两立”,到老驴头的姑娘春兰深知“天下老鸹一般黑”,他们身上朦朦胧胧的“阶级意识”,早以“抱在一块,永久不分开”的质朴形式反映了出来。这些长年埋头于土地的下层农民,他们痛恨地主恶霸的巧取豪夺,一直都在自发地进行着反抗斗争,用伍老拔的话来说:“这年头,没有发愁的事,就是打不倒冯老兰,是个发愁的事儿。”然而,无论是朱老巩、严老祥带头的“护钟”行为,还是朱老明、严志和领导的“抗税”运动,为什么都是以贫苦农民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呢?道理似乎非常简单,当“阶级意识”还没有被升华成为一种“政治信仰”时,它自然也就不具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17) 的巨大动能。因此,“党的领导”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参与因素,不仅使“锁井镇”村民去掉了鲁莽行事的人格弱点,而且还引导他们走出“自我”去放眼“世界”,原先那种盲目冲动的“复仇”情绪,也随之被转化成了高度自觉的“革命”热情。在《红旗谱》的故事情节中,客观存在着一个有关“寻找”的叙事结构:朱老忠听说运涛想要去参加共产党,便笑着对他说道:“共产党?我在关东的时候,就听人讲到过,苏联列宁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打倒资本家和地主,穷苦人翻起身来——你要是扑到这个靠山,一辈子算是有前程了!”对于朱老忠本人而言,“党”只是“听说”却并没有“找到”;而运涛这代年轻人却终于“找到”了,这又令朱老忠从内心深处“羡慕”无比。其实,作者暗示农民“找党”的艰难历程,就是要表现他们由“自发”到“自觉”的成长历程。“党”不仅代表着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所“办的是咱们穷人的事”;故“党”在农村所发动的一系列革命,也就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干!割了脖子上了吊也得干!老了老了,走走这条道儿!”(朱老明)“狗日的欺负了咱几辈人,咱可也不是什么好惹的!”(朱老星)“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你不跟我说,我还想去找你们哩!”(伍老拔)“锁井镇”村民熠熠生辉的思想亮点,无疑会给读者造成极大的审美错觉:只要农民接受了“党”的启蒙教育,他们就能强烈爆发出势不可挡的政治激情;只要农民参加了“党”的团体组织,他们就能彻底去改变自身落后的精神面貌。“农民”通过“党”的中介转换,不仅能够变成“无产阶级”,而且还能跻身于他们的“先锋队”之列——“农民”、“党”和“无产阶级”的思维模式,其实正是《红旗谱》作为“红色经典”的意义所在。
二、“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角色变异
既然《红旗谱》中的新旧农民,其阶级属性都已发生了质变;那么作为阶级斗争的对立面,反派人物的身份变异也就在所难免。冯兰池与冯贵堂父子两代地主,无疑是“锁井镇”上的坏人形象:“冯老兰是从封建的生产基础上生长起来,是封建思想的代表人物;冯贵堂受了资产阶级教育及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开始也曾热衷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后来便成为‘买办’型的农村资产阶级的代表。”(18) 梁斌如此去设计反派人物,无非是要保持阶级关系的高度平衡;尤其是冯贵堂这一新型地主的登场亮相,更是导致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直接对垒。这样一来,“锁井镇”村民的革命性质,自然也就符合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客观要求。
尽管梁斌本人认为反派人物好写,“作者爱给他打什么花脸就给他打什么花脸”;(19) 但我个人却觉得冯兰池这一土财主形象,明显要比那些高大完美的“农民英雄”写得生动逼真。青年时代的冯兰池,“长条个子,白净脸——穿着蓝布长袍,清缎坎肩——手里托着画眉笼子,画眉鸟在笼子里鸣啭。”这种“京城恶少”式的穿着做派,一露面就被作者赋予了土财主的外貌特征。冯兰池有“三四顷地”、“三层宅院”、“三四个长工”、“十几条牛”和“十几只猪”,实际上仅凭他的这些家产,至多就是个比朱老忠他们富裕的“大户人家”,而与他“呼风唤雨”、“遮天蔽日”的经济实力却极不相符,更谈不上如严江涛所说的那样“有的是银钱”且富甲一方。出于激化农民与地主之间阶级矛盾的主观考虑,作者一直都在极力凸现冯兰池奸诈阴险的“坏人”品性:一是霸占“河神庙前后”的那片“官地”,故才会导致朱老巩“路见不平”与他对决;二是想占有年轻姑娘春兰和珍奇鸟类“靛颏”,故才会导致青年农民对他“反动本质”的深刻认识;三是承包“割头税”从中谋取暴利,故才会导致“锁井镇”村民的强烈不满与群起反抗。这三件事梁斌写得很是用心却又很不得要领,因为“贪婪”是一切土地私有者所共同拥有的人格弱点,并非只体现在地主阶层身上,同样也体现在普通农民身上(像阿Q的“趁火打劫”与杨二嫂的“顺手牵羊”即是如此)。况且,冯兰池这些不光彩的“霸道行径”,并没有逼使农民走向经济“破产”,更没有达到“穷则思变”的革命状态。作者描写冯兰池的“吝啬”与“守成”,揭示其骨子里的“传统”与“愚顽”,而这些所谓“剥削阶级”的思想缺陷,恰恰又具有小农意识的普遍性质。当“锁井镇”村民聚集在一起,喝着“小酒”聊着闲天去猜想冯兰池“一天吃一顿饺子,吃咸菜还泡着半碗香油”时,这位土财主却正在以自己治家理财的切身体验,表情严肃地去开导他那个念过洋学堂的宝贝儿子:
你老辈爷爷都是勤俭治家,向来人能吃的东西不能给牲口,直到如今,我记得结结实实。看,天冷时候,我穿的那件破棉袍子,穿了有十五年,补丁摞布丁,我还照样穿在身上。人们都说白面肉好吃,我光是爱吃糠糠菜菜。我年幼的时候,也讲究过吃穿,可是人越上了年纪,就越觉得钱值重了。你不想,粮食在囤里囤着是粮食,你把他糟蹋了,就不是粮食了。古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哪!过个财主不是容易!
如果我们排除冯兰池的地主身份去孤立地看待这段话,其实就是位老农民与年轻后生大谈创业艰难的人生感慨,字里行间都充溢着农民对于土地田产的渴望情绪。冯兰池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强烈的农民气息,无疑把作者推向了一种不愿去正视的尴尬局面:“锁井镇”村民与冯兰池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其本质上仍未摆脱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历史局限;如果只把冯兰池作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那么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与意义也就无法得以体现。所以,冯贵堂这一新型地主人物的形象塑造,便从根本上解决了萦绕于作者心头的最大难题。
“冯贵堂高高身材,穿着袍子马褂,白光脸儿,满脑袋油亮亮的长发。他上过大学法科,在军队上当过军法官。上司倒了台,他才跑回家来,帮助老爹管理村政,帮助兄弟们过日子。”在作品文本的人物描述当中,“袍子马褂”与“上过大学”显然是带有强烈的暗示意义,它们分别象征着冯贵堂身上“传统”与“现代”两种因素的交叉重叠,但“现代”又是他思想表现的主体部分。当然,这种“现代”意识绝非是梁斌所理解的那种政治革命意识,而是指现代文明社会的经营理念与生产方式。他拥护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提倡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他主张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以“多施小惠”的“人道主义”去换取天下太平;他重视科学种田、提高农业生产力,反对父亲老是“在受苦人身上打算盘”。最能够体现他现代意识的闪光之处,自然是他对“集约化”生产与多种经营模式的浪漫憧憬:
这,我都打算好了。咱有的是花生黑豆,就开个大油坊。开油坊还不使那大木榔头砸油槽,咱买个打油的机器,把地里的花生、黑豆都打成油,再买几盘洋轧车,把棉花都轧了穰花,把棉籽也打成油,咱再喂上一圈猪,把棉籽饼喂牛,花生饼喂猪,黑豆饼当肥料施到地里。把豆油、花生油、棉籽油和轧的棉花,运到天津去卖,都能赚到一倍的钱。这样也积得好猪粪、好牛粪、好骡马粪,有了这么多粪,地能养不肥?地肥了,能不多打粮食?这样赚钱法儿,比登门要账,上门收租,好得多了!——
我还想,咱们有的是钱,少放点账,在街上开两座买卖,贩卖洋广杂货,真能赚钱!再说,到了麦前,麦子价儿大的时候,该把仓房里的麦子都卖了,过了麦熟,新麦登场,咱再向回买。
秋前卖谷子,春天卖棉花,都能多卖一倍的钱。我研究过了,比在仓房里锁着,强得多了!
冯贵堂想要在农村推广农业变革的前卫思想,不仅遭到了父亲冯兰池的强烈抵制,就连“那些老百姓——叫他们跟着学,他们还不肯。”依照现如今人们的认识水准来判断分析,冯贵堂有关农业现代化的开放性眼光,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在梁斌和他那个时代看来,冯贵堂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剥削方式,甚至于比他老子还要阴险毒辣且更具有欺骗性;冯贵堂所信奉的人道主义与改良主义,只不过是些资产阶级用以麻痹人民大众的精神鸦片;而冯贵堂所设想的经营理念与运作模式,也都是些资本主义发财观念在中国农村的机械翻版。为了充分揭露冯贵堂虚伪反动的真实面目,作者在保定二师的“学潮事件”中干脆让其直接出面,不仅写他与军阀官僚的狼狈勾结,而且还写他歇斯底里地大骂共产党人:“对这些人,不能‘怀柔’!”
冯贵堂取代冯兰池成了“锁井村”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朱老忠取代朱老巩成了“锁井村”中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他们各自以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去展开正面交锋时,《红旗谱》中政治革命叙事的基本性质也就悄然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个人认为,冯贵堂这一反派形象的文本意义,值得引起我们的重新认识与正确评价。
三、“落后农民”与“社会精英”的身份错位
冯贵堂这一形象出现于《红旗谱》中,不仅昭示着“锁井镇”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而且客观上也起到了一种催化作用:那就是新型地主的“知识化”,直接促成了新型农民的“知识化”,进而使敌对双方始终都保持着身份统一的均衡态势。
在《红旗谱》的文本叙事里,有一个奇特现象令我倍感诧异,那就是“锁井镇”的全体村民,都表现出了对文化知识的强烈渴望。朱老忠刚一出场便对严志和讲:“叫江涛多念几年书吧,咱就是缺少念书人哪!”故才会发生老辈农民倾囊相助,供严江涛进城读书的感人故事。而朱、严两家的那些后生,似乎也都个个争气:被革命者贾湘农称为“乡村知识分子”的严运涛,自学两年便能阅读《水浒传》等传奇小说;春兰虽然认不得几个大字,却能读懂荡气回肠的革命情书;就连没有文化的朱大贵,也都能识文断字自写家信。梁斌使“锁井镇”的新型农民全部“知识化”,其目的无非是要通过“知识化”去导入“革命化”,最终实现他们由“落后农民”向“政治精英”的彻底转变。我绝不怀疑梁斌美化农民的善意动机,但是这种违背常规逻辑的美化过程,其本身就意味着作者对中国革命“农民”本色的自我消解。比如,无师自通的严运涛到广州去参加北伐军,才半年多时间竟能写出这样铿锵有力的文字:“我要站在革命最前线,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政客,铲除土豪劣绅!”“南方不比北方,到处是欢欣鼓舞,到处看得出群众革命的热情,劳动人民直起腰来了。你们等着吧,革命军到了咱们家乡,一切封建势力,一切土豪恶霸都可以打倒!”其文法之整齐与文笔之流畅,无论人们如何去加以解释,都无法改变其自相矛盾的反讽味道。
“落后农民”通过“知识化”而走向“精英化”,这在严江涛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严江涛是《红旗谱》中又一英雄人物,从“卷一”后半部的“入团宣誓”开始,他就以“锁井镇”新型农民的当然代表,正式取代朱老忠成为了故事情节的真正主体。毫无疑问,作者描写严江涛的成长历程,就是农民“知识化”的转型过程;而这种身份与思想的巨大变异,又被作者人为地分成了两个步骤:
其一,是“落后农民”向“知识精英”的身份转变。作为朱老忠“一文一武”培养计划中“文”的理想人选,严江涛“性格比较柔和,做事细致、沉稳”,(20) 首先就被作者赋予了读书人的潜在气质。用朱老忠自己的话来说,“这孩子长得俊气!”“是念书人的材料儿!”严江涛果然不负朱老忠等老辈农民的良苦用心,不仅顺利地完成了六年高小的全部学业,而且还以全县第一的优秀成绩考上了保定第二师范,成为了“锁井镇”农民中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尽管我们从作品文本中根本找不到严江涛“刻苦学习”的任何细节,只是看到他走家串户鼓动农民起来革命的繁忙身影;但他“社会科学”的丰富知识与分析问题的推理能力,都足以证明他早已具备了知识精英的内涵修养。不过,严江涛进城读书而成为“知识精英”的故事叙事,又与他“家境贫寒”发生着难以避免的矛盾冲突:当严江涛“笑嘻嘻地把文凭递给”父亲时,严志和却满腹辛酸地感慨道:“这张文凭可不容易,白花花的六七十块大洋钱哪!”仅凭严志和这句话来判断,严家应不属于“贫苦农民”之列,否则他根本拿不出“六七十块大洋”去供儿子读书。贫苦农民读不起书,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而革命英雄需要文化,却是作者本人的主观想象。这种客观与主观、现实与想象的二元对立,使梁斌本人陷入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窘迫境地。为了解决自己在艺术构思方面的巨大失误,他让严江涛一再强调保定二师“是官费,膳、宿、讲义,都供给。只买点书,穿点衣裳就行了”(这与朱老忠卖掉牛犊以及全村农民纷纷捐款帮他上学的文本描述又严重背离)。作者此举无非是要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印象,贫苦农民的优秀子弟即使是很有才华,也只能去选读那些不用花钱的“官费”师范。可是与梁斌同乡且毕业于保定师范的作家孙犁,他的一席话却无形之中戳破了梁斌编织的莫大谎言:“那时候,只是一家单纯的富农,还不能供给一个中学生;一家普通的地主,不能供给一个大学生。必须都兼有商业资本或其他收入。这样,在很长时间里,文化和剥削,发生着不可分割的关联。”(21) 假如孙犁所讲的一切都是实情,那么严江涛进城读书自然就是虚构。因为像孙犁这样的富家子弟(家里开有“永吉昌”商号,主要是经营榨油、轧棉花和金融等业务),想要去求学深造都倍感困难,故严江涛进城读书的情节描写,也只能是违背现实生活的艺术“真实”。况且严江涛从“高小”越过“中学”直接进入到“师范”,其“成长”经历之神速更是令人大跌眼镜、唏嘘不已。对此,我们同样要保持足够的批判理性。
其二,是“落后农民”向“政治精英”的身份转变。作者让严江涛进城读书,绝不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那么简单,而是为其走上革命道路去预设伏笔。“进城”使他与县委书记贾湘农发生了直接联系,“读书”又使他懂得了农民反抗的重要意义;所以当他面对党旗庄严宣誓:“我下定决心,为党,为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战斗一生”时,不满二十岁的严江涛就已经具有了“政治精英”的一切素质:他把保定二师变成了与反动当局分庭抗礼的阶级战场,领导青年学生为全民族的自由解放浴血奋战;他“从学校到工厂、从工厂到农村,偷偷地把革命的种籽撒在人们心里,但等时机一到,在平原上掀起风暴。”《红旗谱》的“卷二”与“卷三”,就是围绕着两次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去描写严江涛从“学生”到“战士”的成长经历。“反割头税”运动充分表现了党组织的存在价值与意义——“有信仰”而“缺经验”的严江涛,按照书本知识去发动农民起来造反,没想到首先就在赤贫农民老套子那里碰了壁,此时贾湘农的多次出现、反复开导以及亲自坐镇,才使他重新振作起来调整了思路改变了方法,终于激发起广大落后农民积极参与的巨大热情,并带领“农民迈着有力的步伐,学生们唱着《国际歌》”,赢得了这场革命斗争的空前胜利。“保定二师学潮”则突出展示了共产党员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经过“反割头税”运动的洗礼与磨炼,严江涛的思想意志也变得愈加成熟而坚强,他不仅足智多谋提高了“斗争艺术”,而且还担当起了“保属”革命救济会“负责人”与二师学生会“主任委员”的重要职责。他领导学生和民众上街游行,揭露国民党“打内战”、“不抗日”的卖国行径;他组织同学坚守阵地武装护校,以生命为代价去唤醒全国人民的民族气节。当血腥屠杀开始之际,严江涛大喊一句:“同学们!北操场敌人冲进来了——拿起武器,战斗罗!”便率领青年学生手持大刀长矛冲向了反动军警,同他们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肉搏,俨然一幅革命英雄史诗的悲壮画面!严江涛在“党”的引导下,迅速完成了由“落后农民”向“知识精英”再到“政治精英”的身份置换与思想转变,恰恰暴露出了《红旗谱》创作的真正意图:农民只不过是中国现代革命的随从力量,而“政治精英”才是这场历史变革的灵魂人物。因为“以农民为基础的造反,迟早都会置于非农民分子的领导之下或非农民渗透进来。”(22) 当梁斌清醒地意识到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人物,确以知识分子为多”(23) 时,严江涛形象的存在价值与客观意义,无疑就是对他们共同“成长”经历的艺术书写。因此,《红旗谱》非“农民”本色的革命传奇,也几乎成为了所有“红色经典”的普遍现象。
四、“革命传奇”与“英雄史诗”的严重疏漏
长期以来,《红旗谱》作为新中国审美教育的经典之作,曾深深影响过几代人的思想成长,这是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然而,学界与读者除了对它一致叫好之外,却从未有人去关注其艺术上的重大疏漏,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悲哀。梁斌本人就曾坦率地承认说:“由于掌握材料不足,生活基础和斗争经验不足”,人物与情节都是“经过集中、概括,突出和提高了的”,故他一再强调“《红旗谱》故事不是革命生活的实录”,作品中种种自相矛盾的地方使其“局限性很大”。(24) 过去人们往往把这些话视为是作者的自谦之词,我个人倒觉得作者的确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反省意识。如果我们仔细去阅读一下《红旗谱》,就不难发现它是一部具有重大瑕疵的“红色经典”,其逻辑思维之混乱与艺术构思之粗糙,几乎足以颠覆人们赋予它的一切赞美之辞。因论文篇幅的制约关系,我在这里只举其两处最大的艺术败笔以正视听:
第一大艺术败笔,是阶级关系的模糊不清。冯兰池被作者定性为“恶霸地主”,是“贫苦农民”的革命对象,其主要根据有两点:一是来自于朱老巩的揭底,这“大半个村子土地都是你们冯家的”;二是来自于冯兰池的炫耀,“如今咱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升发起来,继承了祖业,成了方圆百里以内的大财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1951年8月颁发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冯兰池因占有使用土地超过全村土地的一半以上,理所当然应被看作是一个大地主。可作者对这一问题的交代与描写,却明显出现了前后矛盾的重大纰漏。“卷二”中严江涛在向县委书记贾湘农汇报“锁井镇”的阶级关系时,则说“论财势,数冯老兰,有的是钱放账,三四顷地,出租两顷多,剩下的地,雇三四个长工,还雇很多短工,自己耕种。”众所周知,“一顷”等于“十五亩”,“四顷”也就是“六十亩”,这其中还包括当初冯兰池霸占的那四十八亩“官地”。如果我们减去四十八亩“官地”,作品开端冯家最多也就只有十二亩土地,他不仅不是什么“恶霸地主”,甚至连一个“富农”都算不上,其家产恐怕与严老祥和朱老明他们也差不了多少(在同冯兰池打官司的过程中,严家就卖过一头牛而朱家则卖过五亩地)。如此推演,当年冯兰池与“锁井镇”村民的矛盾冲突,根本就不是什么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农民与农民之间的个人恩怨。与之相反,朱老忠、严志和等人被作者定性为“贫苦农民”,是现代革命的主体力量,其主要根据也是两点:一是都与地主冯兰池有着刻骨铭心的阶级仇恨,二是都身受地主冯兰池的阶级剥削和残酷压迫。第一个根据因冯兰池构不成“地主”而自然化解,第二个根据在作品中却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足够细节(冯兰池究竟怎样剥削、压迫农民并未加以交代)。最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光着屁股回家”的朱老忠,虽然全部家当只有一个“包袱”和一个“被套”,但他刚从“关外”返回“井锁镇”,就迅速地盖房置地、安家立业,并对穷苦乡亲广布施舍、救人危困;他给人造成的直观印象,绝非是一个“贫苦农民”之辈,倒像是一个外出淘金的“发迹者”。梁斌将朱老忠与冯兰池构成阶级对立的矛盾双方,却将那个最贫穷也最应该具有革命潜质的长工“老套子”写得觉悟低下,显然是作者对中国社会“阶级”的认识模糊,以及他艺术思维逻辑的极度混乱。
第二大艺术败笔,是革命场面的描写失真。作为中国现代革命的艺术缩影,《红旗谱》对“农运”与“学潮”等场景,描写得尽心尽责尤为用力,像“反割头税”的游行示威与保定二师的“武装护校”,都能令读者灵魂震撼、感动不已。然而,为了突出革命英雄的“高大形象”,作者过分去夸大其词,以至于使“革命”和“英雄”,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比如,警民在“反割头税”运动中发生了激烈冲突,“朱老忠看到两把刺刀,在江涛眼前闪着光,眼看要戳着他的眼睛,把大棉袄一脱,擎着两条三截鞭闯上去,两手向上一腾,光啷啷,把两把刺刀打落在地上。”而文质彬彬的严江涛也“掏出一把铜钱,对准那个人(警察,笔者注)的脸,刷地一家伙打过去,那人迎头开了满面花,流出血来。”朱老忠从小曾跟父亲习过几天“武”,其“武艺高强”还勉强说得过去;可一介书生严江涛也身手矫健好生了得,则明显是有悖常理难以置信。而最令人不能接受的一个事实,就是作者颇为得意的“二师学潮”:严江涛与张嘉庆等60余名学生,因宣传“抗日”被反动军警包围在校园之内,可是一个团的武装士兵即使“架上机关枪,架上大炮”,也对学生们束手无策始终进不了大门,仿佛那群荷枪实弹的“大兵”们,都是些纸糊泥捏的玩具摆设,此乃矛盾之一。为了振作精神、鼓励士气,“江涛站在南操场的桌子上,”与墙外的同学“互相用英语交换意见,江涛说:‘——打破饥饿政策,斗争就能胜利。’——严萍扬起手儿,说:‘同学们,努力吧!预祝你们在抗日阵线上取得新的胜利!’”“中师”在过去是很少开设英语课程的,即使开设也只是学些极其简单的语法词汇;而“二师”学生英语讲得竟然如此流利通畅,可见其教学水平早已不在北大清华之下,此乃矛盾之二。被困学生为了解决断粮和吃饭的生存问题,“张嘉庆绑好了鞋子,杀紧了腰,手里拿着红缨枪,带着十几个粗壮的小伙子,从门口冲出去,一出门口,叉开两条腿,瞪起黑眼睛,抖得那杆红缨枪滴溜溜转,枪尖上闪着明晃晃的刃光。”而士兵们“一看这个阵势,向回卷作一团,张嘉庆带着同学们朝岗兵们冲过去,追得骨骨碌碌,一直向南跑。”十几个青年学生竟能冲破千余军警的重重包围,几天里两次进城去购买粮食却毫发无损,这真可谓是应验了毛泽东那句至理名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此乃矛盾之三。诸如此类的艺术败笔,在《红旗谱》当中可谓比比皆是。
通过对《红旗谱》的重新论证分析,我个人认为梁斌的知识结构与艺术修养,远不足以去支撑其“宏大叙事”的虚妄理想;而如此艺术粗糙且充满矛盾的一部作品,却被堂而皇之地被称为“红色经典”,又充分反映出了学界不负责任的评判态度。我的看法则是:与其被动地等待后人来纠正我们的认知错误,还不如我们主动去纠正前人的思想幼稚!这才是一种维护学术真理的科学精神!
注释:
① 方明:《壮阔的农民革命的历史画卷——读小说〈红旗谱〉》,《文艺报》1958年第5期。
② 许子东:《当代小说中的现代史》,《上海文学》1994年第10期。
③(13)(15)(18)(19)(20)(23)(24) 《漫谈〈红旗谱〉的创作》,载《红旗谱》附录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④ 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年第18期。
⑤ 耿传明:《植根乡土的“革命叙事”:〈红旗谱〉与20世纪乡土中国的革命》,《人文杂志》2004年第6期。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1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7页。
⑧ 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合著:《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⑨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1日。
⑩ 《毛泽东选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78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16) 参见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思想导论》第5章“阶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21) 见《孙犁文集》第3卷,白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190页。
(22) 见西达·斯考切波著:《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