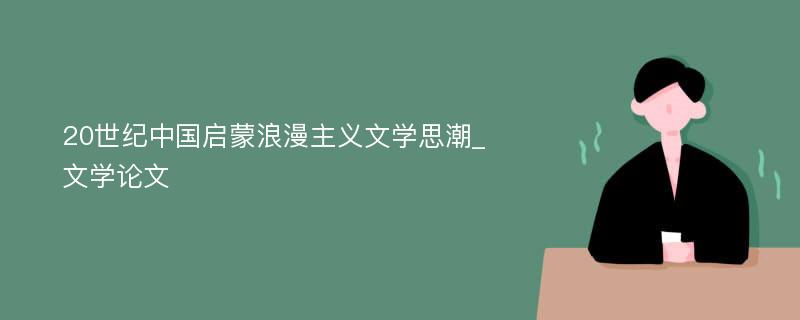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启蒙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漫主义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制度的更迭,时代的推移,文学的流变,在中国犹如万花筒。现在,20世纪快要结束,20世纪中国文学,包括它的创作和它的理论,已经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本”,为对它作整体思考的论者提供一个“存在”,一个“实事”了。
“面对实事本身!”是由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的座右铭。这个座右铭旨在排斥任何间接的中介而直接把握事实本身。它的最确切的注解,是《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1913)的出版预告和创刊号卷首所提出的“共同信念”这样一段话上:“只有通过向直观的原本源泉以及在此源泉中汲取的本质洞察的回复,哲学的伟大传统才能根据概念和问题而得到运用,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概念才能得到直观的澄清,问题才能在直观的基础上得到新的提出,尔后也才能得到原则上的解决。”〔1〕
其实,这是确立客观存在的“实事”“现象”——不作任何判断的“原本源泉”的实事和现象——的权威。这一权威的公正是无可争议的。这是极端理想型的把握世界、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但是,“直观原本源泉”并从中“汲取的本质洞察”获得的“概念和问题”,却是因人而异的,现象学的直观只是其中一种,并不能因此而建立独断的专横的“霸权话语”,从而获得“话语领导权”。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任何企图操纵“话语领导权”的做法,都是反科学的,因而也是不足取的。一切正常的学派,都是自信的、尊严的、平等的,既能坚持己见,又能虚怀若谷:可证伪。
面对20世纪文学现象,思考20世纪文学思潮,可以发现,现成的论断(概念与问题)与实际的创作与理论,常常脱节,使理论陷入尴尬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地。“现实主义”能否涵盖20世纪文学“主潮”,就是典型一例。这一论断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一位论者写道:“独尊现实主义和确保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是中国文学至今没变的根深蒂固的思想,诸如(指新时期)‘改革文学’、‘朦胧诗’、‘意识流小说’、‘荒诞小说’、‘新小说’等非现实主义的创作都被贴上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标签,现实主义文学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普泛体系。”〔2 〕另有论者从茅盾《夜读偶记》提出当代中国文学(不止当代)有一种“现实主义情结”;还有论者干脆提出“告别现实主义”、“打破现实主义神话”〔3〕。应该说,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中, 存在着现实主义这样一股思潮,从“五四”时期到新时期乃至90年代。人们对“现实主义”的反感,并不是对文学创作中这股潮流的反感,实际上,人们对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作品不但不反感,相反,还是赞赏的。人们的反感,是针对提倡现实主义的论者那种背离学术平等,背离话语平等,独霸“概念权力”,将学术争鸣置于非学理层面的“独尊”和“确保”。
现象学体系是个无底洞,深不可测。本文只是借助其方法论的一点皮毛,用以整体感悟20世纪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精神并“直观”之。
20世纪中国文学是从改良文学起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新派政治改良失败后,以梁启超为代表,开创文学救国(宣传改良主义理想)的道路。梁启超尤其推崇小说,并身体力行,创作了堪称改良文学奠基作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这部小说中,启蒙主义明白无误的动机,同浪漫主义主观激昂的创作方法,就是如影随形,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此,启蒙与浪漫,这个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学宿命,就相伴相随,时现时隐,又时隐时现,从改良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两结合”创作方法(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又到新时期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复苏,一直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过程。
启蒙浪漫主义,是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股重要的文学思潮。在这股文学思潮中,主观色彩很强的浪漫主义,是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功利性很强的启蒙主义的。启蒙要求制约着浪漫主义的主观想象,使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显出既承继西方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鼎盛期浪漫主义因子,又与之截然不同的独特性。
转型期中国文学的宿命探索与追求的双人舞
苦难,是近几百年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变法维新,尽管失败,毕竟带来20世纪熹微的晨光。此后,1911年辛亥革命形式上结束帝制,1919年“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为民族刻下精神皈依的“情结”,1949年新中国诞生使民族独立于世界之林。这一切,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从古代向现代的社会转型。
无论西方东方,社会转型期总是危机四伏的。中国社会转型,结束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帝制,而帝制的鬼影在整个20世纪当中,时时窥测风向,借尸还魂,危机更加深重。但是,任何危机都预示着转机,激发着生机,“五四”、抗战、新中国成立、四人帮粉碎,中华民族的精神解放和生命活力,曾一次又一次得以勃发。但很遗憾,这些勃发又一次再一次遭受精神挫折,生命复归于萎顿。20世纪中国时代进程、民族生命历程,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者,一次又一次地思考再思考,探索再探索,追求又追求。探索与追求,成了20世纪中国知识者,中国文学作家、批评家的宿命。犹如鲁迅笔下的那个“过客”。在现代转型没有完成之前,这种探索和追求,将一直延续到21世纪。
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是格外艰难的。20世纪眼看就要结束,而转型期并未结束,在一个“扶贫”面积还如此广大的国度,现代化仍然是一个漫长的梦。“直观”这种现状,20世纪整个世纪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本”,又是中国文学转型期的“文本”,这个“文本”的总体特征是:过渡性、过程性和未完成状态。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著名论断时,曾这样指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过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过程。”〔4 〕这一论断中“过渡”、“过程”诸词的有效性,依然存在,而“最终完成”的论断,则未免乐观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化过程,并没有最终完成,终点怕要推迟到下一个世纪了。
20世纪中国文学整个时段的过渡性、过程性和未完成状态,决定了20世纪整个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总体特征,这就是持续的探索,持续的追求;而探索与启蒙主义是一致的,追求则总是导向浪漫主义。所以,20世纪整个世纪转型期过渡性总特征,自然造成中国文学启蒙主义与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总是携手并行,蹁跹而舞了。启蒙浪漫主义也就势所难免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相当重要并且也十分突出的文学思潮了。这是时势使然、时代使然,由文学现象自然显示出来的。
虚实相生、以虚代实的浪漫主义
虽然早已有人发出警告:“谁试图为浪漫主义下定义,谁就在做一件冒险的事”。〔5〕尽管如此,做冒险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这也说明这一术语有不同含义,不同用法。浪漫主义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的,这并不排除二者彼此渗透。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不排除虚实相生,但最根本的特征还是以虚代实,乃至以虚为实。
一位西方论者在追溯“浪漫的”一词的起源时写道:“最初,‘浪漫’一词是与夸饰情感的、不可能发生的、夸张的、不真实的特点、旧传奇和骑士传说联系在一起的,总之,那是些与清醒、理性和生活观相左的因素。这样,它的涵义是‘虚幻的’、‘虚构的’、‘幻想的’。”〔6〕这大概是最接近词源学上的原义的。 一切形形色色的浪漫主义,无不从此发源。
20世纪的中国,旧的制度结束,新的制度如何才合乎理想?中国的知识者和中华民族,对合理、理想的制度,有高度的、美妙的寄望。不论时代如何起伏,历史如何坎坷,理想主义始终存在。由于现实同理想经常脱节,所以,整个世纪社会心态一直是浮躁的,一步到位、一次解决、一劳永逸的急功近利,和适得其反的结果,困扰着所有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确实不失为惊世骇俗的卓越论断。对中国来说,20世纪是浮躁的世纪,也是追求的世纪,不怕挫折,不息追求的精神,总是可敬的。但“浮躁”败坏了一切,也扭曲了一切。浪漫主义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与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理性精神截然不同的反理性,夸饰的情感,不可能发生的、夸张的、不真实的特点,虚幻的、虚构的、幻想的这些“浪漫”词源上的涵义,无不一一坐实在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创作实践中,其极端的表现,就是后半世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高大全”、“三突出”文学。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是根据启蒙/革命的名义对文学浪漫主义随心所欲要求的结果。值得深思的并不在此。值得深思的是这股启蒙/革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20世纪漫长岁月中的诞生、形成和发展过程。
从理论上看,中国浪漫主义较早产生,是20年代初茅盾最先引进的“新浪漫主义”概念。梁启超在本世纪初开创的改良文学,严格说还不具备理论形态,他的政治小说的浪漫特征,是马克思所说的最典型的“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7 〕在浪漫主义概念上,茅盾还有些模糊。在当时的探讨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是昔尘、谢六逸、田汉等人,他们的观点实际上已经为20世纪中国式浪漫主义即革命浪漫主义奠定了基础,也即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虚幻性、超验性、超前性特征奠定了基础。在这三个人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昔尘的观点,他的观点虽然接触到浪漫主义的“真髓精神”,但却把浪漫主义主观想象的权力推向极端“神秘境地”的“顶点”,虽然他的笔下还有“现实”字样,实际上,现实早被远远地放逐了,留下的只是主观浪漫精神的纵情狂欢!他认为新浪漫主义是“求那潜伏在这事实里面底神秘方面;依敏锐强烈的主观力,极力同这事实底真髓精神相接触”的文学,而“事实”其实已不重要,因为“眼见的世界已经不是现实,不见的世界也不是梦”,新浪漫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是“硬要爬上人类一生底顶点”,“顶点”却是完全虚幻的东西,“只存在于未知的神秘境地”。田汉补充了一点:新浪漫主义是“探知超感觉的世界的一种努力”〔8 〕。
在这里,“超感觉的世界”、“不见的世界”就是“理想界”的“顶点”,这“顶点”被极端地理想化、崇高化并神圣化了,这其实是某种先验观念的理想化、崇高化和神圣化。这种观念,后来发展成为作家可以无视现实的客观性,因为“眼见的世界(只要不符合先验的观念)已经不是现实,不见的世界(只要符合观念——如阶级斗争)也不是梦”,这使作家精神的扭曲已达到什么地步——这一点留待下边分析。但不幸的是,这一切后来都成为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实践的潜在的准则。
从创作上看,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这股特定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上半世纪的“旧社会”,被表现为完全没有光的黑暗;而下半世纪的“新社会”,又被理解为完全没有暗的一片光明,要有一点阴暗面的话,那也是“非本质非主流”的“陪衬”。在这种极端化的表现中,生活的复杂性、丰富性、多样性看不到了,显示出来的是夸张不实和先验的理念色彩。最近,在现代名作的重读精读中,不少学者读出作家创作前内在意念的先验性,钱理群认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内在意念是“带有必然性的历史命题”,“腐朽的封建制度与统治阶级必然被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阶级斗争所推翻”〔9 〕。实际上,往上推,20年代末蒋光慈的《田野的风》,往后移,50年代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等等一大批作品,无不是图解这一“带有必然性的历史命题”。当然,在这些优秀作品中,真实并未完全被放逐,这些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中,革命浪漫主义还是虚实相生的。而在一些二三流作家作品中,以虚代实的倾向就十分严重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7年中,许多新时期“重放的鲜花”,当年就因为接触社会某些真实而被当“毒草”批判,这就是迫使虚假浪漫主义恶性发展的原因。号称“革命现实主义”,其实是不敢正视现实的。
启蒙主义、蒙昧主义的相互追踪
20世纪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主观先验性特征,来源于贯穿20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潮。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这就是说,20世纪中国文学从内容上看,启蒙主义是主潮。
有人认为,启蒙有两类:一类是感性的、政治行动导向型的启蒙;一类是理性的、文化心态塑造型的启蒙,“前者是初级的启蒙,见效快而不彻底,可以在全民族文化素质低的基础上进行;后者是高层次的启蒙,见效慢而彻底, 只有在全民文化素质较高的基础上才能进行”〔10〕。我很欣赏这种区分。本文“启蒙浪漫主义”中的“启蒙”, 正是包括了这两类启蒙。简言之,第一类可叫政治启蒙(主要是阶级启蒙),全部革命都在此类启蒙中,故这类启蒙可以用“革命”代之;第二类可叫文化启蒙。20世纪中国,前半世纪内忧外患兼而有之,后半世纪内忧为主。摆脱帝制仕途经济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初衷是文化启蒙,但现实的严峻迫使选择政治启蒙(救亡的需要等等),救亡压倒启蒙的选择,迎来革命胜利、民族扬眉吐气,确实是“收效快”。革命中民族、阶级、国家、集体的强调,一度弘扬了群体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但也带来个性主义的失落,民族中个体人格的萎缩,乃至发展到文革个性毁灭、人性沦亡。
政治启蒙的弘扬,文化启蒙的失落,带来了启蒙主义为新蒙昧主义所取代(新时期刘心武笔下的谢惠敏就是新蒙昧主义的典型人物),以至新时期开始后的80年代不得不重举“五四”启蒙主义旗帜。20世纪“蒙昧——启蒙——新蒙昧——新启蒙”,出现轮回的现象。20世纪中国文学主潮强烈的社会性、时代感,自然使文学思潮与之密切相关。
作为20世纪中国重要文学思潮的启蒙浪漫主义,由于两种启蒙兼而有之,因此,可以称为“启蒙/革命”浪漫主义,启蒙要求浪漫主义服务于启蒙任务,革命(尤其是后半世纪对文学的行政方式)更制裁着浪漫主义唯命是从,这就使20世纪中国启蒙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不能不违背艺术家的良知,而放纵为“坚定正确方向”所允许并鼓励的主观想象,在指定的艺术天空中——远离现实或将现实理想化的天空——翱翔。虚幻性、虚构性(浩然式由现实之恶劣变艺术之超优良)〔11〕、幻想性,五八年将地球当球踢的超级想象力,文革经济频临崩溃时的大写《金光大道》。虽然这一文学思潮也产生过一些鼓舞人心的优秀作品,但在一种反常的时代中,更大量产生的却是无益有害的作品。
浪漫主义是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它诞生于生气勃勃的反封建禁锢、反古典教条、张扬个性的精神要求。启蒙主义是开启科学民主向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启蒙浪漫主义本应是积极的文学思潮,但由于20世纪中国严峻的现实,探索与追求都无法在正常轨道上进行,以至造成20世纪启蒙/革命浪漫主义这股重要的文学思潮更多产生的是负面的影响。但即使如此,在80年代新启蒙影响下的新浪漫主义,像张承志的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还是在维护人的尊严意识和道德精神上,在抗击伪解构主义的执著上,为启蒙浪漫主义在世纪末写下精彩的一笔。1993年所引发的人文精神讨论,是对启蒙失落引起人文精神失落的世纪性忧思。这一切,也许将预示着21世纪中国文学中启蒙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新生面。
注释:
〔1〕《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第2—3页。
〔2〕黎风《呼唤“浪漫”——关于新时期浪漫文学的忧思》,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文艺理论》1995年9期112页。
〔3〕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文艺理论》1995年3期殷国明文;1996年2期杨春时、宋剑华文。
〔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第1页。
〔5〕〔6〕利里安·弗斯特《浪漫主义》,英国梅休因公司出版“批评术语丛书”,昆仑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页,第1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9卷第573页。
〔8〕昔尘《现代文学上底新浪漫主义》,东方杂志17卷12号; 田汉《新罗曼主义及其他》,少年中国第一卷12期1920年6月, 转引自《文学评论》1994年3期《20年代中国新浪漫文学论》一文。
〔9〕钱理群《“新的小说的诞生”》《文艺理论研究》1997 年第1期。
〔10〕董健《新时期小说思潮和小说流派》“序”,第5页。
〔11〕李辉《清明时节——关于赵树理的随想》,《收获》1996年4期第79页。
标签:文学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浪漫主义文学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