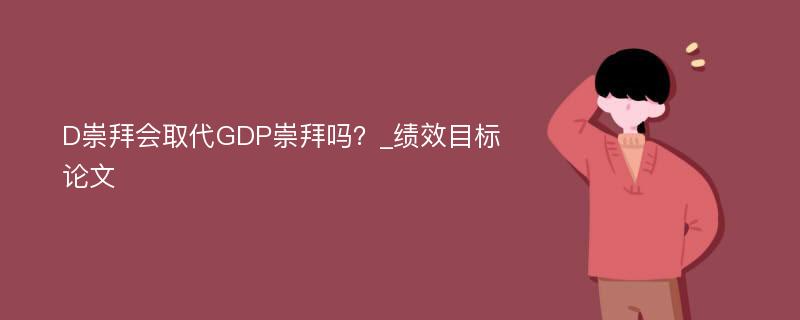
Ramp;D崇拜症会不会取代GDP崇拜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崇拜论文,会不会论文,Ramp论文,GD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的GDP崇拜,已经给就业、社会治安、环境污染、道德水平、社会保障等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诸多问题。由于对发展速度的重视超越了发展质量,出政绩的GDP增长给社会经济发展本身留下很多隐患,从2005年开始,已经有许多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有意调低了经济增长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央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正在变成地方的自觉行动,GDP 崇拜的高温开始有了消退的信号。
急切的冲动往往来源于过度的饥渴和向往,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如果目标是合理的,人们往往只会考虑手段的直接性而鲜少冷静地考虑手段的科学性。 GDP崇拜的产生,无疑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长期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缺少足够的分量有密切的关系,但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在政策制定上前瞻性的缺乏。有错能改固然是好事,但无错或者少错岂不是更为经济?
2006年的“两会”将“建立创新型国家”提到一个比以往更高的高度来认识。这一目标是决策者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审时度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高瞻远瞩而提出的,是力图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实施循环经济、构建和谐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彻底摆脱GDP崇拜,自主创新之路是必由之径。
然而,这一目标能否实行以及实行的绩效如何,取决于手段的科学性。细细解读当前各级政府的创新政策,我们不难发现,在促进创新能力提升的急切愿望支配下,很多问题被简单化处理了,各类文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无一例外是加大研究和开发(R&D)投入,奖励创新企业、使R&D占GDP的比例达到多少多少等等, 这不得不令人产生忧虑。
一、GDP崇拜过去了,会不会出现R&D崇拜?
在创新能力的培养和竞争水平的提升过程中,系统而有针对性的研究开发活动(R&D)是必不可少的。 从国家政策层面上认识到这一活动对一国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的重要性,并将促进社会研发作为政府的职责之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美诸国。20世纪60年代的电子技术革命和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是世界范围内R&D活动迅速发展的两个时期,进入全球化时代, 伴随着各国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提高,R&D更是被视为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和促进创新绩效的必要途径。
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创新有其内在规律,人们只有遵守这些规律,才能取得预期的创新绩效。随着创新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创新与R&D 的关系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就促进创新而言,R&D固然重要, 但不是数量上的重要,而是结构和内容上的重要,仅有R&D 投入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创新绩效的优化。然而,由于创新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创新赶超愿望,创新的内在规律往往被忽视,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R&D崇拜症。
R&D崇拜症往往将R&D的复杂含义简化为R&D的数量指标。即用R&D占GDP的比重、R&D的绝对量以及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值,来衡量国家和地区创新水平的高低,用R&D的数量和比例替代了R&D的内容与实绩。 结果造成了这样一种理解:如果该地区的R&D增长了,该地区的创新水平也提升了;如果政策制订者没有保障R&D的支出增长,那就是不重视创新的表现;如果一国和地区与发达国家的R&D水平缩小了, 那么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差异也缩小了。R&D崇拜症认为,只要有足够的R&D投入,创新问题就迎刃而解。在这种数值崇拜的理念支配下,很少科学地冷静地审视R&D 投入的内容、结构和方向,其结果往往是一国和地区往往付出了大量的投入,但并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
R&D活动作为一个重要的创新手段, 在使用过程中必须遵循创新的基本规律。手段的“多”和“巨”并不等于目的的“美”和“全”。重温二战以来各国的技术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那些曾经处于技术后进地位的发达国家,在赶超过程中所投入的R&D,远远不能与当时的领先者相比, 典型的案例就是日本的汽车行业的技术赶超。就投入而言,整个日本汽车行业的R&D投入都无法与福特一家公司相比,但日本仍然取得了较好的创新绩效,反过来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与学习对象;同样,两个技术起点相近的国家在同一领域内展开的创新竞争,胜出者也不是因为在R&D投入的数量上超过失败者。韩国和印度当年在液压挖掘机上的竞争,印度的R&D投入远超过韩国,但由于韩国合理区分了引进和自创技术的分布比例、用配套产业政策营造了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从而最终在这一领域确立了自己的领先地位。这些事实都说明,R&D数量的大小并不意味着创新的绩效,对创新而言,R&D本身的性质、目的、内容和方式远远比R&D的数量重要得多。 在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摆脱R&D崇拜,正确认识R&D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树立科学的研发观。
二、正确认识R&D的性质
R&D具有双重属性。就促进创新而言,R&D是重要的手段;但就R&D的持续来源而言,它又是一种结果。R&D崇拜症只看待了R&D作为手段的一面,而没有看到R&D作为结果的一面。R&D投入不是某一个时点上的外部注入,而是创新与价值实现的反馈环中的自然流动,因为创新必须是一个连续性的、不断实现新价值的过程,实现新价值的同时,也是为下一期R&D作准备。R&D的这种双重属性要求我们在评价R&D时也应持双重标准,一是对R&D投入效率本身的评价,即研发活动所得到的知识、技术、发明与投入之比;二是对知识、技术、发明这些R&D投入的直接结果最后有多少转换为现实生产能力的评价,看R&D的投入是否最终导致了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是否给企业创造了新的附件值,是否延长了企业的价值链。只有将技术转换为现实生产能力并以此确立了一定的竞争优势,R&D投入的持续追加才成为可能。创新能力强的国家之所以具有较高比例的R&D,在于R&D活动与国民经济之间形成了一种正反馈。R&D活动既是下期创新的手段,又是上期创新的结果,这样, 越是创新能力强,经济绩效越好,R&D投入也越来越多。R&D双重属性得到实现的过程,也就是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过程。要实现这种循环,就需要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在鼓励和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促成科学家、发明家与企业家、金融家、消费者的结合。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R&D的双重属性,仅将创新的重点放在R&D的投入上,而不重视研发结果是否能转换成为现实的价值,其后果是R&D 活动的持续性难以得到保障。
三、正确认识R&D的内容
在R&D活动中,研究开发什么比研究开发投入更为重要。 不能正确定位研究开发的内容,往往导致R&D的大量浪费。R&D崇拜常常伴随着这样的理念:一是认为创新是为了做出新产品,而不是用新的方法去生产既定的产品;二是认为技术越多越好;三是认为高精尖的技术才是最好的技术,越复杂的技术越好。这些理念往往诱导出R&D饥渴症,却难以取得好的效果。 世界各国创新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证明,合理确定R&D内容是决定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
首先,在创新过程中,“怎么做”比“做什么”更重要。无论是成功实现技术赶超的国家,还是已经处在技术领先地位的国家,研究开发的主要内容并不是新的产品,而是新的方法和工艺。即使在国际大型公司中,公司的研发也更多地关注现有产品,而不是新的产品。通用公司在研发投入上的80%也是用于现有产品的工艺创新,只有20%用于长远和理论化的研究。
其次,技术多并不等于创新绩效好。相反,创新绩效好往往源于少而精的技术,成功的竞争者往往通过少而精占领技术高地,而后才展开蔓延和扩散,如果一开始就以多为目的,势必导致大量的R&D浪费。作为一种市场导向的活动,R&D从来就不是自娱自乐,研发者不能沉溺于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技术圈子,创新出一个又一个让自己惊喜的新技术,而应选择合适的立足点专心发掘。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在过去10年中,苹果公司发布了1300项专利,经常产出奇异、高贵的产品,但一个技术如此多的企业,其利润方面却一再濒临危险的边缘。
最后,R&D也不应该盲目追求高精尖技术,而是基于自身的技术基础,从细微之处做起。好的技术并不要求其本身有多引人注目,但必须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能保障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附加值的提高。一次性尿布、方便面、卡拉OK都不是什么复杂的技术产品,但它同样是市场公认的创新;这即是说,创新问题并不需要人们试图以更为复杂甚至全新的技术方案去解决问题,相比产品技术的重大飞越,产品和制造工艺的微小改进并不是值得忽视的事情。历史上,所有取得较好的技术创新绩效的国家,无一不是从细微之处做起,经过长期的积累逐步占领技术高端市场的。美国技术创新最初就主要集中在纺织行业,目的是解决一般生活问题,如织布技术的改进等,然后逐步过渡到铁加工和铁铸造、蒸汽发动机的制造、铁路设备和航运设备的技术引进和更新,此后才在电力工程、电动机械等领域取得了全面突破性进展。日本也是一样,纵观整个日本技术创新过程,并没有什么划时代的重大创新,但没有人否认日本在技术创新活动中获得的收益。
四、正确认识R&D的方式
企业应成为R&D活动的主体,对此,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企业如何成为R&D活动的主体呢?R&D崇拜症的又一表现,就是为了使企业R&D比例迅速上升,不断采取激励和诱导措施,但与此同时却忽视了另一个关键因素——竞争。R&D活动的原动力应该来自市场,而不是政府,真正有效率和有目的的R&D 活动是“逼”出来的,而不是“奖”出来的。在重视激励和诱导的过程中,为了使企业成为有目的有自我驱动性的创新主体,政府更要重视竞争性市场的构造。对于R&D活动而言, 竞争既是一种动力机制,也是一种发现和筛选机制。不注重“逼”单纯依赖“奖”不仅削弱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易于引发各种形式的寻租行为,造成R&D 投入的浪费。
作为一种手段,R&D是弹性的、灵活的、相机抉择的,它并不要求包揽, 而是要求根据需要进行合理分工。由于各类特定技术的知识含量显著增加,企业要在多个技术领域内开发并保持自己的专门技术已经极其困难,企业所需的,主要是关乎核心能力的研发。当这一过程遇到相关缺口时,企业明智的选择不是自己开发,而是外包开发。通过研发分工,研发单位既能节约研发费用,也能缩短研发到商业化的时间,同时取得较好的研发效果。
五、正确认识R&D的参照对象
R&D崇拜症经常将发达国家和地区作为自己的参照系, 不能正确地对待不同国家和地区R&D数量的差异,以少为耻,以多为荣,以超为胜。R&D比较并非完全没有必要,在定位自己的发展阶段时,进行历史比较找出差距是很有意义的,但不必将R&D视为一种投入竞赛。因为技术后进者的R&D支出和技术先进者的R&D 支出在构成上完全不一样,所要求的目标也不一样。技术后进者不必因自己的R&D 费用只占发达国家的一个零头而焦虑,也没有这个必要。追随者的研发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方向是明确的,因为领跑者为其提供了一个研发参照系。而导致技术领先者研发成本大大增加的原因,正是因为创新中的不确定性。
科学技术的进步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技术后进国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弭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创新的空间。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表明,既不存在完全渐进式的技术发展,也不存在完全跳跃式的技术发展。技术进步的过程是一个渐进与跳跃相结合的过程,跳跃式的重大突破往往发生在具有长期创新传统和知识积累的国家,一旦发生,它就等同于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开辟了一个边界和规模都不确定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有创新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在这个边界不确定的世界里开辟发现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顶端地位,从而确立自己在该领域中有利的分工地位。汽车、无线通讯、石油化工,网络技术,推开这些产业领域大门的往往只有很少几个国家,但这并不排斥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在这个领域内也可以有所创新,后来者的成功创新不仅使自己在该领域中有一席之地,也扩展了整个领域的边界。
在前些年的GDP崇拜热潮中,一些地方官员在急功近利的政绩观支配下, 把“发展是硬道理”异化成了“GDP是硬道理”, 这种简单化的理解已经有了许多深刻的教训。在建立创新型国家成为公众和政府的一致性目标时,如果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忽视创新的内在规律,也会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这一意义深远的目标异化为简单的“R&D是硬道理”,行动上必然体现为“悠悠万事,唯R&D为大”,后果堪忧。
R&D崇拜的源初动机,是对创新的关注、重视和热切, 但也反映出对创新这一具有深刻理论和实践意义活动的简单化、庸俗化、标签化的理解。创新是追求效率的,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要注重R&D的投入产出问题。不能树立科学的研发观,不能科学认识创新的内在机理,R&D投入有可能成为一种烧钱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