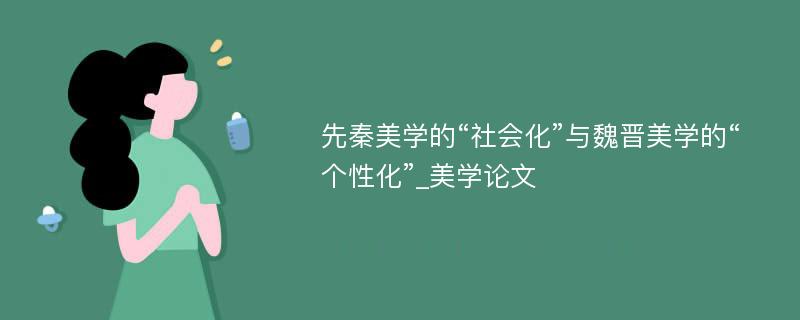
先秦美学的“社会化”和魏晋美学的“个性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先秦论文,魏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79(2000)02-0019-05
关于“社会化”,心理学给它的定义是“个体学会以社会允许的方式行动,从一个生物个体转成一个社会成员”。[1](P2)个体社会化是一个贯穿于生命全过程并呈矛盾状态的双重运动,即个体不仅要获得与他人更好的联系,同时又能更好地区别自己与他人,因此社会化与个性化是个体发展中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这里之所以借用心理学中的两个概念,是因为中国古典美学一直就存在着如何处理好艺术社会化与个性化问题,即艺术活动究竟是要抒发审美个体的情感、意趣,满足个体身心感性需求(个性化),还是强调社会整体伦理道德的理性内容(社会化)。以强调社会化为代表的先秦美学与以关注个性化为特征的魏晋美学,分别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两种互补的美学形态——儒家美学与道家美学的基础,而这两种互补相成的美学形态又显示出中国古典美学以社会化与个性化的和谐统一为主要特征。
(一)社会化与先秦美学
先秦的文化思想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之势,但由于政治统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儒家思想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儒学的核心内容是仁。什么是仁?克己复礼即为仁,而克己复礼说白了就是要克制私己,取消个性,使个体回复到符合社会规范的礼中来。李泽厚先生认为,儒家理想中的社会是一个按照严格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社会,但又是人际间彼此关爱的社会,在这里个体与社会是能够且应该统一的。一方面个体通过社会与他人和谐相处得以发展;同时社会又因个体之间的亲和无间得以发展,而达成这一理想社会的关键是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具有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的伦理道德情感。[2](P71)儒家认为只有通过审美活动这一手段和途径来影响、形成个体的社会化情感。
1.礼乐。要构建以“仁”为核心的理想社会,关键是以礼乐制度规范、约束个体的行为,并使这一规范内化成个体心理内容,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巩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所谓“制礼作乐”,可见礼乐本是可分开的,《乐论》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3](P61)“礼”是祭祀、军事、政治乃至日常生活所规定的礼仪之总称。由于涉及到活动者的仪容、举止等等活动形式,它就与美有关了。在一系列与美相关的活动中,它对个体做出强制性的要求、限定,有意识地培养训练个体的集体性、秩序性的行为、观念,从而达到个体情感观念社会化的目的。
“乐”则不同,《乐论》中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3](P60)可见,与外部强制活动的“礼”不同,“乐”是一种内部情感的表现形式,通过它可使群体的情感得以交流,引导其中的个体和谐一体。苏珊·朗格说:“音乐能够通过自己动态结构的特长,来表现生命经验的形式,而这点是极难用语言来表达的。情感、生命、运动和情绪,组成了音乐的意义。”[4](P42)可见音乐具有一种普遍性情感。“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喑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5](P242)此处正是通过音乐来陶冶性情,塑造情感,以获得个体规范化的情感,这正是先秦美学的特征。
2.和。那么怎样的情感才具有普遍性、社会性而不仅是个人的独白呢?这里儒家美学提出一个标准——“和”,即“乐从和”。“和”做为中国古典美学一重要范畴包括审美中主观感受的“和”与客观对象的“和”,按照“和”的标准,要获得真正的美感首先要将味、色、声等粗野鄙陋的感官快感从中区别出来,因为这些粗鄙的感官刺激与产生美感的生理基础不符,如“(钟声)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则和于物,物和则嘉成。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窕则不感,槬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5](P18)这是说钟声只有大小适度达到“和”方能产生美感。“和”从生理感官到心理精神,再进到整个自然社会,而自然与社会之“和”乃是中国古典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中国古人看来最美莫过于此。“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草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乐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夫有平和之声,则有蕃殖之财。于是乎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5](P7-8)自然与社会合乎规律的发展乃是“和”之最高境界,它不仅具有生理、心理的美感,更重要的在于它具有使自然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社会功能。反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若没有统一和谐,也就不存在美。具体到个人则应遵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即所谓“温柔敦厚”。喜怒哀乐之情不可过度,否则既有损个体身心,又不利于社会和谐。因此“和”既可满足个人情感需要,又可作为一种标准规范塑就个人情感。那些过分强烈的欢愉、忧伤、情欲均被排斥。总之,先秦美学主张任何情感及一切艺术均要符合社会整体之和谐。
3.诗言志。歌曲、舞蹈、音乐本是三位一体、彼此相通的,因而诗(歌)也就很自然地承续了“乐”之服从伦理政教的特征,这一特征集中体现在“诗言志”。“诗言志,歌咏声,声依永,律和声。”[3](P11)这是对“诗”最古老著名的界定。关键是“诗言志”究竟是说诗歌是用以抒发个人情感的呢,还是做为政教道德的宣扬工具?这个问题可以在与《乐记》思想一脉相承的《毛诗序》中找寻答案。“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6](P182)乍看这段话,似乎显示“诗言志”乃是抒写个人情怀的(“情动于中”),但只要将乐与诗联系起来看,进而考察乐与诗的功能就会发现,这里的“志”实是指社会所要求的政教伦理。李泽厚先生在考察了诗的演变过程后指出“诗言志”乃是“载道和记事”。[7](P242)故而它才能“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3](P130)这里显然表明了诗歌表现的是被伦理道德规范了的情感,即社会化的情感。
此外,与“诗言志”思想相近的是“兴观群怨”说。它表明先秦美学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即将强制的伦理规范内化为个体自身的需求,通过个体情感的社会化来实现社会的和谐一致。
先秦以来确立的以强调政教伦理之理性功能为主要特征的儒家美学,经由“美刺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文即是道”(朱熹)的发展、延续,一直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全部进程。
(二)个性化与魏晋美学
宗白华先生曾说魏晋艺术呈现的是一种“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8](P184)这种“哲学的美”就是它的美学灵魂——魏晋玄学。魏晋玄学崇尚的“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因而魏晋玄学乃是道家思想演化的产物。源于先秦之时的道家思想得到了魏晋时期忽然声势大振,成为那个时期的思想主流。魏晋亦是历史上一个极为混乱苦难的时期,儒学的那一套伦理规范在这个动荡纷扰、人命如蚁的社会丧失了价值与意义,人们开始觉悟到人生意义不在于功名利禄、学问节操,而是个体内在精神与情感的完美。而道家则充分肯定个体生命的价值,认为正是儒家宣传的仁义道德误导人们追求功名欲望,终为外物所累。它认为要达到生命的自由、个性的张扬,最佳途径莫过于审美,只有在美的境界中才能获得生命的畅游。
1.人物品藻。与先秦时期关注个体行为、情感的道德规范截然不同,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强调个体形体外貌的飘逸清丽,气质个性的超然洒脱,这些均与理性伦理道德毫不相干,而是纯粹的生命感性的追求。《世说新语》以其传神笔触记载了一群潇洒飘逸的人物形象:“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9](P332)“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9](P336)黑格尔说过,人的躯体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自然存在,更能从形状、构造上表现出内在的精神生活。[10](126-127)因而,个体的气质个性比之外貌更受重视,并成为审美活动中的重要部分。这一点突出体现在曹丕提出的“文气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11](P2271)这里的“清”是指个体秀逸俊美的气度个性;“浊”则指个体低俗平庸的气质个性。可见,他以“气之清浊”即气质个性的优劣作为评价审美主体及其作品优劣的标尺,而丝毫不涉及到伦理道德等社会内容。刘勰也说:“吐纳英华,莫非性情。”“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深寂,故志隐而味深……”[12](P857)他所讲的“性情”,所看重的文人以及他们应具备的“才”、“气”、“学”、“习”均不关涉社会所要求的伦理道德,而是个体之感性的内容。文人如此,画家亦不例外,“戴安道中年画行象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语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尽。’”[9](P376)只因作画人气质平俗,缺少超然的风韵,旁人的评价(对人对画)就大打折扣。由此可见,魏晋美学将外貌、性情等个体独具特色的个性层面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澄怀味象。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澄怀味象”这么一个美学命题,他说:“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而有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3](P177)这里的“澄怀味象”实质已涉及、涵盖了当时许多重要的美学范畴。首先,“澄怀”乃是对老子“涤除玄览”的承续,也即是庄子说的“心斋”、“坐忘”,总之是要求审美主体须保持虚静空灵的心境,以一种超功利的心态去参与审美活动,对此刘勰认为:“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12](P247)他强调抛开一切伦理是非,进入轻松、淡泊的状态是进行审美活动的重要前提。而他的“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和则舒心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12](P370)则进一步强调不要让外在事物束缚个体情感的抒写。在此,不论“澄怀”、“坐忘”、“虚静”均排除了现实尘世的纷扰杂乱对审美活动的干扰,就更不必提束缚个体自由情感的伦理道德了。其次,“味”原本是指生理感觉,如“五味令人口爽”。[13](P84)后来又有“‘道’之出口,淡乎无味”,[13](P135-136)用无味来形容最高境界的“道”。魏晋时“味”则完全成为一个美学范畴,如“夫曲用每殊,而情之处变,犹滋味之美,而口辄识之也。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14](P81)这里将欣赏音乐之美感比成享受的美味。又如“繁采寡情,味之必厌”,[12](P289)“理过其辞,淡乎寡味”。[15](P37)这里将缺少情感、辞采的文章比成滋味寡淡。而“至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12](P29)“深文隐蔚,余味曲苞”,[12](P356)这些文采俊美、喻义深远的文章如好滋味不绝于口。到了钟嵘的“滋味说”则将“味”这一由生理快感转为心理、审美快感的体验,视为文艺创作与欣赏的审美标准,“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15](P46)从中不难看出,有“情”、“辞”(采)才能有“味”;相反,如果审美中过分注重社会伦理的理性内容(“理”),而不关注以感性形式表现出来的个体情感,则会丧失美感,即“无味”。最后,“象”乃源自王弼的“得意忘象”,它作为一种感性形式是为体现理性内容的“意”而存在的。表面的感性形式是次要的
,而直达深层的本质才是最终目的。因而审美就不应为具体、有形的观念、概念、形式所约束,而是去把握宇宙、生命的意义。因此,“味象”的涵义就是从“象”中体味出人生的意义,而不拘限于某一种具体的伦理道德观念上。至此可见,“贤者澄怀味象”、“山水以形媚道”已完全不同于孔子充满伦理色彩的“仁者乐山,知者乐水”,这里突出了山水自身的妩媚形态,用以表明此道非彼道,此乃自然之道,而非伦理道德。魏晋美学所强调的乐山乐水完全是出于个体感悟生命、探询自我、追求情趣的心理需要。
3.缘情说。与“诗言志”相对的“诗缘情而绮靡”表明魏晋美学已不再将审美活动看成政教的工具,而完全是个体内在情感的宣泄。首先,它将个体情感视为审美活动的动力。如钟嵘有“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15](P35)“……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5](P48)之所以“陈诗”、“长歌”只是为了抒展、驰骋个体为物感荡的性情,而不是出于伦理政教的要求。刘勰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12](P332)“人禀七情,应物斯感。”[12](P409)表达了个体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是审美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础与前提。魏晋美学不仅强调个体情感的价值、作用,而且关注情感对个体自身的意义。并不在意个体情感是否合乎伦理政教,“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9](P339)“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9](P77)“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9](P395)在《世说新语》中类似“恸绝”、“大恸”不绝于目,而这些个体情感的自然流露,极大的悲痛与哀伤均与儒家的“温柔敦厚”格格不入。先秦美学中即使有情亦要“发乎情,止乎礼义”,而魏晋美学则不为“名教”所缚,任意抒写人生的感伤、忧嗟。
魏晋美学表现出的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求,对个体情感价值的肯定,正是道家美学的精髓所在。这一精髓亦通过“发愤著书”(屈原)、“诗穷后工”(欧阳修)、“不平则鸣”(韩愈)、“失童心说”(李贽)、“惟情说”(汤显祖)、“性灵说”(公安派)延展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
(三)结语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所谓的先秦美学的社会化特征和魏晋美学的个性化特征都不是绝对的,均是相对而言。因为我们知道,审美活动中审美对象之所以具有审美性质,乃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产物,即一定社会的审美意识的凝结物,是当时社会审美意识的集中代表,而这些社会审美意识不能直接附属在某一对象上,必须经由审美主体这一中介最终获得。可以这样讲,任何审美活动皆具有社会化与个性化两种特征,先秦美学与魏晋美学概莫能外。另一方面,由于各个时代社会背景的不同,每个时代的审美活动、审美意识在社会化与个性化程度上必有差异,要么社会化特征更突出,要么个性化特征唱主角,但不论是哪一方占上风,另一方都同时存在,这样才有了千姿百态的美学形态。先秦美学的社会化特征与魏晋美学的个性化特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纵观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进程,我们也确实看到分别具有这两种特征的儒家美学与道家美学作为这一进程中的两个互为补充的美学形态,从来不以单一形态出现,因而不论是社会化抑或个性化极少偏执于一方。在中国古典美学发展过程中,一旦社会化特征过于突出,立刻会有个性化来冲淡它,如先秦美学之后继以张扬个性的魏晋美学,又如明清美学个性解放的呼喊阻抑了宋明美学对“文以载道”的过分强调;另一方面,个性化特征也从未走得太远,如韩愈在鼓吹“不平则鸣”的抒情论调之同时,却又再三著文强调“文以载道”。再如宋代虽盛产声色娱乐的艳词逸曲,同时又不乏儒学卫道士们的书斋情怀。正是由于社会化与个性化的相互和谐统一,才使中国古典美学所呈现的既非一味正襟危坐的生硬面孔,也非一泄千里的情欲躁动,而是一种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独特魅力。
收稿日期:1999-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