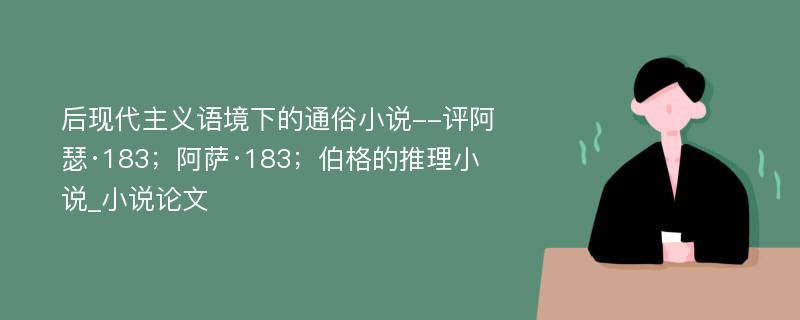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通俗小说——浅论阿瑟#183;阿萨#183;伯格的推理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语境论文,推理小说论文,通俗论文,伯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7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8)03-0071-06
阿瑟·阿萨·伯格(Arthur Asa Berger)(1933—)是当代美国后现代主义传媒理论家,美国通俗文化学者,也是一位多产作家。在3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他撰写出版了60多部著作、100多篇论文以及不计其数的书评,涵盖大众传媒、通俗文化、幽默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类题材,在美国传媒理论和通俗文化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他的作品还被译成了多国文字,如德语、瑞典语、意大利语、朝鲜语、中文以及印度尼西亚语。他本人也曾到很多国家讲学,如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芬兰、丹麦、瑞典、挪威、巴西、泰国、中国以及朝鲜。近年来,他又以独特的方法将后现代主义、大众传播、社会学等理论融入侦探小说,创作出别具一格的系列学术推理小说①:《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Postmortem for a Postmodernist,1997)、《哈姆莱特谋杀案》(The Hamlet Case,2000)、《乐极生悲》(Die Laughing,2000)、《亚里士多德案》(The Aristotle Case,2001)、《学术会议上的惨案》(The Mass Comm Murders:The Mass-Comm Murders:Five Media Theorists Self-Destruct,2002)、《涂尔干死了》(Durkheim Is Dead:Sherlock Holmes Is Introduced to Social Theory,2003)等。
本文拟就伯格的《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和《学术会议上的惨案》展开讨论,意在通过对小说的情节构建、叙述方式和人物塑造的分析,展示一种寓理论于娱乐的新型小说,它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21世纪西方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一种跨学科的多元倾向。
一、荒诞情节的构建
《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和《学术会议上的惨案》是伯格系列学术推理小说中的两部作品。前者是处女作,后者是近期之作。两部小说虽然在创作时间上相差5年,且情节独立、人物各异,但都以亨特探长及其搭档威姆斯作为串联线索的人物,从而暗示了两部作品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讲述了一位被称为“后现代主义之父”的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艾托尔·格罗奇在自家的餐室里被人神秘地同时用四种方式杀死。当时,教授正与其妻、同行、女研究生和女访问学者等人筹备一个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学术会议。在《学术会议上的惨案》中,五位大众传播理论教授,以特邀演讲者的身份,出席一个关于大众传播的专题研讨会。一位名叫让·乔治·西缪尔的教授在结束其精彩的演讲时,被人从背后用刀捅死,其余四位教授也在阐释了各自的理论之后,相继神秘地死亡。亨特探长与其搭档威姆斯先后对这一连串怪异的凶杀立案调查。然而,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他们却陷入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大众传播理论话语的重重迷魂阵,侦破结论也出人意料。《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的破案结论充满了后现代主义话语的含混和悖论:谁都不是凶手,但谁都参与了谋杀。《学术会议上的惨案》中貌似连环凶杀案的真正凶手正是这五位德高望重的传媒理论家,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都是间谍,其中一位还是个双重间谍。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些凶杀案的起因。在《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中,参与格罗奇教授谋杀的嫌疑犯中有他的妻子、同行、研究生、访问学者,他们的杀人动机则源于对教授的诸多不满:背叛婚姻、剽窃同行观点、性剥削、学术上的专横跋扈等等。《学术会议上的惨案》中这些教授的互相残杀也并非源于间谍的使命感。著名传媒理论家、世界一流高等学府的客座教授古克为昔日遭遗弃之辱一刀捅死西缪尔;沃洛西诺娃为古克曾阻挠她获得哈佛客座教授之位将其毒死;拉瑟特因沃洛西诺娃撞见他男扮女装在街上招摇过市而残忍地将其枪杀;斯法德因怀疑拉瑟特的双重间谍身份将其推下窗户坠死;西缪尔因与斯法德彼此间的嫉恨和猜疑预先设置炸弹将后者炸得尸肉横飞。我们发现,这些离奇且凶残的谋杀的起因大多只是些常见的人际纠纷,伯格小说的情节也因此而显得既荒诞又令人毛骨悚然。它似乎在告诉人们:任何事都可以让人采取极端行为,铤而走险。杀人变得极为随意,人们可以以任何理由将自己讨厌的人随意杀戮而没有丝毫的犯罪感,我们的安全感也随之丧失,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变得既凶残冷漠又不堪一击。
伯格小说的独特之处尚不止如此。尽管两部小说自始至终紧扣追捕凶手这一主题,但小说真正的主旨是通过凶杀案嫌疑犯的叙述,从不同角度向读者展示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大众传播的不同理论和哲学观点,而这一点有赖于小说的叙述方式和人物的塑造。
二、情节作为理论的载体
从整体看,两部小说采用了同样的结构模式。每章开篇是一段有关后现代主义和大众传播理论的片断引文,大量后现代主义和大众传播的理论和思想则蕴含于情节的构建之中。利奥塔、哈贝马斯、杰姆逊、波德莱尔、德鲁兹、克里斯蒂娃、德里达、福柯、拉康、伊塞尔、艾埃尔、曼海姆、弗雷德森、诺拉·纽曼、麦克卢汉、麦加埃尔、休尔斯、施瓦兹、西奥多、奥沙利文等现当代著名后现代主义和大众传播理论家的名字因不断重现而令读者不再感到陌生;那些晦涩难懂的重要理论术语,如,元叙事、合法化、宏大叙事、通俗文化、仿真、超现实、同一性、符号学、传播过程、传播中的对话因素、沉默的螺旋式发展,在小说中俯拾即是。作者采用人物对话模式,对后现代主义、大众传播,元叙事等都作了简洁明了的阐述,从而使警察在调查取证过程中与嫌疑犯的对话成为介绍理论的一种载体,其结果,这些理论话语与故事情节互为交织,构成了整部作品的意义内核,使侦破过程变成了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阐释过程。毫无疑问,这种推理小说已不再是我们熟悉的传统的推理小说。
通过这种形式和内容别出心裁的巧妙结合,作者将艰深的理论阐述编织进小说情节,借人物之口,用日常生活事例或浅显易懂的语言,使理论深入浅出。在《学术会议上的惨案》中,西缪尔用符号学理论对日常生活现象如麦当劳汉堡、汽车旅馆化、汽车、家用电器、冰箱的购置等加以解读;再比如,在《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中普罗普与亨特的对话中,通过日常用语,使后现代主义、叙事和元叙事三者关系的阐释变得通俗易懂:
叙事并不是如我们在书中所读到的,在电影里、电视中所看到的那些简单的小故事,从叙事中我们得到有关生活以及死亡的许多东西……我们的生活趋向于我们所看到的电视节目,把广告、肥皂剧、情景喜剧、动作片等等难以列举的节目融合在一起,这些叙事,这些模拟的东西对人往往有一种颠覆的作用。[1](59)
许多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争论说,在后现代社会中,我们放弃了过去常为我们解释事物的那些伟大的哲学信仰体系,如马克思主义,它揭示了社会如何形成这种现状,或者弗洛伊德主义,它说明了人的精神活动,或神话,它们解释了人类是如何产生的。这些信仰体系我们称为元叙事,现已不再被接受或者被提出疑问。[1](60)
后现代主义反映在今天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折衷主义中,瞬间的念头、不同的时尚、美食、发型,各种音乐,性伴侣的基础上。拼凑成一种个人风格……。[1](65)
小说中另一人物阿伦·费斯在日记中的一段话也精辟地概括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主要特征:
今晚我写下:它确实有分裂生殖、东拼西凑的特点,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特点,表现为线性而不是突发性,比如说视觉艺术的作品。后现代强调狂欢和旅游,看重像主题公园、林荫路及体现后现代文化和社会生活水平主要方面的场所……[1](199)
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反对人为地在所谓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划分界限,伯格用通俗的推理小说作为阐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载体不仅使作品兼具趣味性和可读性,而且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取得了完美的结合。
伯格小说的另一大特点是对多元叙述的运用。小说的叙述者不单单局限于某个具体的人物或视角,而是一个全知叙述视角、客观叙述视角和人物有限叙述视角的混合体。不仅如此,人物有限叙述视角又被分解为小说中不同人物的叙述。作者借助这种不同视角互为交织的混合视角,一方面从不同角度有效地向读者介绍后现代主义和大众传播的各种理论的要旨和研究动向,另一方面也从多个侧面展示了这些不同国籍、不同种族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和价值取向。请看以下几个采用不同视角叙述的小说片断:
1.格罗奇的猝死使巴西尔·康斯坦特震惊,他注意到自己的膝盖在微微颤抖。阿伦·费斯也感到腋窝下出汗了,浸湿了他的棉布衬衫。斯拉佛默·普罗普忍不住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对不起,”他说,“我得吸氧了。”他起身一摇一晃地进了浴室。[1](13) (黑体系笔者所加)
2.当灯光再次亮起来的时候,艾托尔·格罗奇的脑袋正垂在桌上,脑门上有个红色小窟窿,血一滴一滴地在向外淌。一把银色短剑的剑柄露在背上。银剑四周的运动服上浸着深红的血迹。一把长长的木镖,末端系着黄色的毛,射进他的右颊,离嘴只有几英寸,他刚开始喝的那杯酒洒满了桌布,正微微冒出硫磺味儿。
奇怪的是,他的脸上居然凝固着一种像是微笑的表情。[1](5)
3.他向米哈伊拉转过身去,对她说:“你看上去越来越漂亮了。真是越长越漂亮,可我……”
“行了。”米哈伊拉笑着打断了他。她知道自己漂亮,她穿着紧身衣服,这更凸现它充满性感的身材。她非常苗条,身高大约5.8英尺,上身穿着饰有金属饰片的黑色高翻领毛衣,配以灰色超短裙和浅蓝色长筒袜,一头蓬松的红发几乎垂至腰际。[2](8)(黑体系笔者所加)
4.跟许多变得秃顶的男人一样,以利亚将两侧的头发留得很长,并用梳子将它梳到另一边来遮住秃顶部分。这使他看起来既愚蠢又自负,甚至还有点阴险狡诈。[2](9)(黑体系笔者所加)
从上述片断看,片段1显然不能被单纯地认为是全知叙述者在讲述故事,更应被看作是全知叙述和人物有限叙述两个视角的相互交替,尤其是黑体部分中的动词明显是透过被当作主语的“他”、“阿伦·费斯”、“斯拉佛默·普罗普”三位人物的视线而被感知或看到的。片断2是小说第一章的全部内容,虽然第一句中的“艾托尔·格罗奇”表明全知叙述者在场,但接下来的细节描写更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场景的客观描述,除了“奇怪的是”这个短语外,没有其他表示主观臆断或评论的只言片语。片断3中的黑体部分显然是透过“他”(斯法德)的视线观察到沃洛西诺娃身上的这些细节的,观察如此细致入微,这对于一个日趋衰老却仍春心萌动的斯法德来说既合情合理,又令人生厌,沃洛西诺娃在他的耳边悄悄说他是“十足龌龊的老头”[2](15) 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此,人物的有限叙述视角在这个语境中运用得恰到好处,它既展示了沃洛西诺娃令人欣羡的美貌,也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斯法德色迷迷的丑恶嘴脸。片断4很明显采用了全知叙述视角,其中的黑体字部分是对斯法德的消极且略带揶揄的评价,无疑,这不可能是出自人物斯法德本人之口。总之,此类例子在小说中不胜枚举,因限于篇幅,笔者只选择了上述片段来阐明作者在小说中采用多元视角或称混合叙述视角。
这种多元或混合叙述视角的另一功能是为小说制造了别具一格的悬念。借警察调查取证之机,作者有意识地让这些教授、学者、研究生、作家阐述其各自的理论和思想。表面上,这种做法似乎与案情没有直接关联,因为枯燥乏味的理论阐释本应属于学术研讨会,然而,饶有意味的是,作者不仅使临时审讯室成为演讲厅,让教授们畅谈后现代主义和大众传播理论,而且还利用信件、日记和讲课的形式,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来演绎和发表各自的见解。其结果是,作者以这种方式,不仅没有使理论阐述变得枯燥乏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延缓情节、制造悬念的目的,使读者既心急如焚又欲罢不能。在枯燥的理论阐述过程中,时不时点缀式地插入一些与案件相关的问答,来维持和延长读者的兴趣,同时也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之中对后现代主义和大众传播理论有所了解。
三、类型性人物形象的解构
伯格小说的人物建构也颇为独特。首先,作者套用了家喻户晓的侦探人物亨特探长,这使人联想到侦探片《神探亨特》中的那位智勇双全的探长。不仅如此,小说中的亨特不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侦探,而且还与搭档威姆斯一起担任了这些教授的听众。换言之,小说中的理论阐述主要是在亨特、威姆斯和教授之间进行的,大多情况下,是以问答或答疑的形式展开的。显然,对警察形象的刻画超越了传统模式。他们不只是冷静的推理专家,而且对抽象深奥的后现代等学术理论问题也似乎具有罕见的领悟力和想象力。难怪普拉尔对亨特说出这样的话:“作为一名警察,你有些看法很有趣……对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者有一种很好的概念。”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对小人物威姆斯的刻画。在伯格的笔下,威姆斯是一名中士警官,亨特的得力助手,但他心胸狭隘、固执己见,喜欢直来直去,对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后现代主义者没有好印象。作者正是借这个人物之口,来揭露并讽刺了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威姆斯偏激的点评将学术界种种腐败和荒谬暴露无遗:学术会议的哗众取宠,学术出版物的苟且草率,同行之间的嫉妒、争名夺利和明争暗斗,使笼罩在学术权威身上的神圣光环荡然无存,因为正是这些腐败和荒谬导致了小说中惨案的屡屡发生。因此,威姆斯这一人物不仅仅只是幽默的点缀,更重要的是,他还起到了解构教授、学者的传统刻板模式的作用。刻板模式就是指“通常经过高度简化和概括的符号对特定群体和人所进行的社会分类。这些符号或隐或显地再现有关群体和人的行为、特征或历史的一系列价值观、判断和假定。”[3](299) 根据哈密顿和特罗利埃的定义,人物的刻板模式是“一种认知结构”,这种结构“包含了观察者对某个人类群体的知识、信念、以及期望。”[4](15) 因此,对人物刻板模式的解构是这两部小说的另一大特征。
此外,从传统意义上讲,两部小说没有主人公,因为自始至终它们没有围绕某个人物展开情节,虽然从表面上看,《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的主人公应该是格罗奇,但小说一开篇,就宣告了他的被杀,尔后的一系列的调查询问虽由他而起,但其中心主题多是围绕不同人物对后现代理论的阐释。可见,格罗奇只是引发这些理论阐释的线索。《学术会议上的惨案》更无从说起谁是真正的主人公。这一点从小说均匀的谋篇布局足以表明。如果说亨特是主角的话,那也只是因为他从中所起的纽带作用:一是作为作家的系列推理小说的纽带,二是作为作家传递理论的工具。但小说结局似乎颠覆了以亨特为主角的解读:《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的破案结论是:谁都没有杀格罗奇,谁都参与了谋杀,而《学术会议上的惨案》的真相是:谁都杀了人,谁又都被杀。换句话说,最终,谁也没有因杀人而受到亨特所代表的法律的制裁。由此可见,作者并不关注某个具体的人,相反,他似乎更重视群体形象的塑造,这个群体形象具体体现在这些教授、学者等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上。
伯格笔下的这些人物大多是著名学者,在一流大学任教,著书立说,穿梭于世界著名大学的讲台之间,在后现代主义和大众传播领域里声名显赫、影响巨大,他们是斯法特认为的“有重大贡献、被注视、被聆听的大人物”[2](6)。表面上,他们德高望重,道貌岸然,实际却是冷酷凶残的杀人犯。在他们中间,有魔鬼般贪欲的性掠夺者,有婚外情者,有可疑的同性恋者或两性人,有狂热的女性主义者,有势利小人,有狂妄自大者,有疯狂的复仇者。他们相互仇视,相互诋毁。如,沃洛西诺娃嘲弄地称斯法德为“十足龌龊的老头”,一个“好色之徒”,说古克年轻时“非常放荡”,把西缪尔精彩的演讲看作“胡言乱语”,“恶心得要吐”;斯法德暗骂古克教授是“十足的母狗”,骂西缪尔是“蠢货”,视拉瑟特为“英国白痴”;沃洛西诺娃“是一个受了过多教育的农民”,鄙夷之情不言而喻;费斯说普罗普是“禽兽”,普拉尔“不太聪明”且能“算计”,富士宫是个“病态的说谎者”,普罗普评介富士宫“也很肤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绝对没有感情”,普拉尔评价普罗普“相当粗俗……地道的妄想狂”,富士宫是“同性恋”,“古怪的人”,费斯“很讨厌”,斯拉佛默是个“又胖又丑的老头”,巴西尔“很放荡”,等等。实难让人相信,这些充满人身攻击的不雅之言竟出自这些所谓的高知或社会精英之口。不仅如此,这些有着众多头衔、有着神圣光环的教授学者还是些庸俗、贪婪的市井之徒。他们热衷于免费的旅游、美酒佳肴,感兴趣于他人的隐私,却无心教学,厌烦学生,对他们来说,学校不再是传播知识的殿堂,而是“像监狱或陈尸所,”“有一种令人压抑的氛围”,里面关着“宠坏了的学生,失意的教师。”[1](84)
显然,在伯格的小说中,教授已不再是“人人都以为与人无害的教授,因为他们整天云里雾里地埋头于研究和做学问”[2](100),而是一群心灵扭曲、道德沦丧、怪诞可怖、极其危险的间谍和杀人犯。普罗普对亨特说的一席话揭露了学术界的刀光剑影:“学术界充满了志趣相投的小派系。他们把一切时间都用来攻击那些与他们信仰不同的人——有时以一种比较温和文雅的方式,而有时则人身攻击,甚至会用恶劣粗暴的方式。教授们有聪明才智,但他们并非总是彬彬有礼,毕竟……我们是人。而人并不总是文雅的动物。”[1](59) 《学术会议上的惨案》结束时亨特对威姆斯讲的一番话也发人深省:“很遗憾,他们对人际交流所知甚少,缺乏包容之心,无法宽恕和忘却。”[2](153) 由此可见,伯格所塑造的教授形象不再是人们头脑中那个隐性的传统的教授形象。此处所谓的“隐性类型模式”是指“关于某一社会类型成员所独有的特征的一系列社会共享的信念”[4](14)。换句话说,教授通常被认为知识渊博、不谙世故、心不在焉。当然,伯格并非是第一位关注教授、校园、学者的丑陋等议题的作家。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戴维·罗杰就以他的“校园小说”温和地嘲弄了他作为其中一分子的学术界以及教授的生活。比如,在他的《小世界》里,罗杰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学界内近乎残酷的竞争以及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种种丑行:嫉妒、婚外情、虚伪、自私、势利等等,从而表明,那些自命高深、往往被普通人奉为神圣的教授们,其实也不过是一些凡人。然而,伯格所塑造的教授学者形象似乎更趋极端、疯狂。伯格将卓有建树的教授与冷酷残忍的杀手融于一体,成功地拆解了关于教授的传统概念,极大地冲击了传统价值观。此外,伯格的人物具有国际文化背景,他们中有俄国人、法国人、以色列人、美国人、德国人、英国、日本人、意大利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以滑稽的方式塑造了不同国家人物的刻板形象。结合小说中某些真实人名和地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效地展示了后现代语境下的教授的“众生相”。
在《学术会议上的惨案》的“作者的话”里,伯格写道:“无论从文字意义还是从寓意上讲,我都会说这些推理小说是赢得和教育学生的新途径”。[2](1) 可见,对伯格来说,小说是传授或传递理论的载体,而情节结构和人物建构只是衬托。然而,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两部小说所达到的境界显然已经超越了作者的本意,因为它们在寓理论于娱乐的同时,似乎也间接地提出和暴露了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向学术理论和传统价值观提出了挑战。
首先,两部小说颇为相似的结局颠覆了是与非的道德价值观,暗示了是非界限的模糊。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隐性地揭示了后现代的西方社会的道德沦丧和传统价值观的缺失。小说叙事本身也向我们提出了关于爱情、婚姻、诚信、职业道德诸多问题。换言之,在对一切传统理念和价值观提出挑战和质疑的后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元叙事的传统道德观是否已经过时,爱情、婚姻、诚信是否已没有价值可言?难道正如小说人物富士宫所说的:“爱已令人难以置信地贬值了”,“道德只不过是句空话”?[1](104) 在后现代社会里,那些被称之为“元叙事”的伟大的哲学信仰体系不再被接受或者被提出疑问或遭拒斥放弃。但问题是,如普罗普所言,“没有它们,我们如何既理解我们自己又理解这个社会呢?”[1](60) 难道追逐名利、满足私欲、自私自利将成为后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吗?
其二,伯格通过把学术理论具体地编织在小说的情节并融入人物的话语中,让深奥晦涩的后现代主义等现当代理论从高高的理论圣坛步入通俗文化领域,将神圣的理论、权威与学界的腐败、犯罪杂糅在一起,这在某种意义上堪称创举。通过这种近乎戏谑的方式,作者不仅解构了教授学者的传统形象,而且尽情嘲弄并挑战了理论和权威,其中不乏作者本人的某种心理投射。作为一名以美国研究为学术背景的教授,伯格并不被学界所重视,正如他自己所言:“大多数美国研究的学者都有一个严重的自卑情结。这是因为传统学科的教授对拥有美国研究学位的人嗤之以鼻,认为后者对什么事都略有所知而又都不甚了了。”[5]他在2005年秋《美国通俗文化杂志》举办的一次访谈中谈及其职业、美国研究、通俗文化研究等问题时对记者说:“我写了不少黑色幽默、讽刺、充满敌意的学术推理小说。”[5] 他接下来说:
一位同事曾经这样评论我,“我们以为他是一个荒诞主义者,但结果他是一个荒唐的人。”这位同事对我说我所有的书都不适合出版。当我问他为什么他从不发表任何文章时,他对我说他的文章“太好了以至于不发表。”有—位教授在对我的一本书的书评的开头写道:“你怎么评论一本永远不该出版的书呢?”类似的评论解释了我为何在我的推理小说中那么喜欢杀死教授。[5]
正是这种情结给他的创造力提供了格外的动力,并由此表达了他“对理论的反感”[6],乃至对学术权威的蔑视。
其三,伯格的推理小说模式——理论与故事情节的结合——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当代文化的一种跨学科的走向。换言之,跨学科研究方法不仅体现在对文学作品研究上,而且也反映在不同文类或文体、不同领域之间的整合,预示了一种理论通俗化的趋势,即,通俗文化正在成为新世纪的主流文化。
收稿日期:2007-06-18
注释:
① Mysteries是作者阿瑟·伯格用来命名他的系列小说的专用词,此处将其译为推理小说,是根据陆谷孙主编的《大英汉词典》。本文中还使用了侦探故事(detective story)这一术语,其含义与推理小说相同。根据大英百科全书2005年Deluxe版的界定,“实际上,侦探故事(detective story)和推理小说(mystery)是同义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