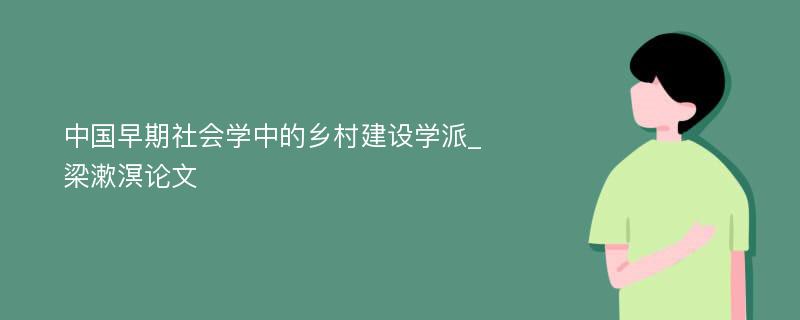
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学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中国论文,乡村论文,学中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不少地区兴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事业,学术界一般称之为“乡村建设运动”。提倡和参加乡村建设的人员,既有一批进步的社会学者、经济学者、农业专家和有志青年,也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中的改良派,还有一些则是国民党政府大大小小的官员。主办乡村建设的机构,有的是学术机关,有的是高等学校,也有的是民间团体,还有一些是政治机构。乡村建设工作所侧重的方面,有的侧重平民教育,有的侧重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有的侧重于农村经济事业,也有的侧重于乡村自治,可见,从事这场乡村建设事业的成份是极其复杂的。
本文不打算对这场乡村建设事业进行面面俱到的介绍与讨论,而仅仅拟对其中起核心作用的“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与实践作一概略的考察。“乡村建设学派”是我们的新提法,于一门学科发展史的研究中,这样的提法或许更准确些。再者,我们提“乡村建设学派”也是由于这场乡村建设事业主要是由一些学术界知识分子提倡、引导与参加的,而其中的核心人物,如晏阳初、梁漱溟、李景汉等,都是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知名人物。他们在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中,形成与借鉴了中外各种社会学理论学说,然后以此为指导,从事实际的乡村建设事业。“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是不彻底的,实际工作是社会改良性质的,是对旧中国农村社会恶性运行的现实的修修补补,但这一学派所作的探索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乡村建设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
乡村建设学派的产生,有其客观必然性,它是当时中国社会所陷入的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的产物。
从经济上看,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封建国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多数,依靠农业和传统的手工业,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然而自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农村昔日的宁静,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逐步走向破产;西方廉价工业品的大量涌入,又破坏了中国农村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民国初年以来,农村连年发生的灾荒和军阀混战的不断加剧,更使中国农村经济雪上加霜,进入二、三十年代以后,其蓄积的问题更加严重了。据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一书中所提供的资料,华洋义赈会于1922—23年间对冀皖苏浙一带农村状况进行了调查,各地农户年收入在150元以下的达67.9%, 其中河北各县达到80%;农户年收入不足50元者达28.8%,其中河北各县达62.2%。华洋义赈会这次调查,反映了各地农村灾患的特殊情形。另据后来对我国北部农村地区所作的调查,农户每家平均年收入为217.6元;对东部农村地区的调查,每户年平均收入为315.5元。孙先生认为, 这大概反映了当时中国各地农村家庭收入的一般情形。在农户家庭年生活费支出中,全国农村平均用于食品支出所占比例高达59.9%,其中河南开封达到76.7%,新郑达75.1%;安徽来安县农户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最低,亦达48.7%。以恩格尔定律来衡量,饮食支出占家庭总支出59%以上者属于贫困;此项支出介于50%—59%之间的属于勉强度日的家庭。那么,当时中国农村家庭,除极少数地区外,绝大多数地区属于贫困线以下。
以上数据仅仅反映了二、三十年代农村家庭经济生活的一般情况。实际上中国农村当时实行的仍是封建土地占有与分配制度。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对江、浙、陕、豫等省农村状况的调查,自己不事耕作的地主虽只占总户数的2.3%, 每户平均拥有土地却高达132.9亩,拥有田亩百分比为26.8%;而占总户数64.7%的贫雇农, 每户平均拥有土地仅占4.6亩,拥有田亩百分比为26.3%。 地主家庭拥有的土地每人平均达19.6亩;农户家庭人均则不足1亩。 (注:以上所引数据参见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4—69页。)因此,当时占总户数绝对多数的贫雇农家庭必须向地主等拥有大量土地者租地耕种,才能勉强维持生计,为此,又要接受地主的残酷剥削。结合农村封建土地占有与分配制度加以考察,则农户家庭所经受的困苦难以想象。
从1931—1935年间,全国每年都有半数以上的省份发生水旱灾害,其中1931年发生的江、淮、运河流域的大水灾,灾区延及十六省,灾民达五千万,财产损失达二十几亿元以上。农民冻饿而死和外出逃荒者大量增加。1931年至1936年,全国因灾荒死亡的人数达698.08万人,逃荒人数更是不计其数,其中1935年仅据全国1001个县上报的数字,农民离村人数至少在2000万人以上。(注:据鲁振祥:《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初步考察》,载《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4期。)
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与国内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加上连年灾荒与军阀混战,中国农村经济迅速走向破产。这种状况引起了不少知识分子的思考,他们力求通过自己的探索,找到中国农村衰落的原因,提出拯救农村乃至拯救整个中国的办法,并通过实验而加以推广。
乡村建设学派的产生,亦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鸦片战争以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近代中国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救亡图存运动。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等,其目的都在于挽救垂亡的国运。然而,民族危亡的征象却是一天比一天的增加和暴露。其中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这场大革命曾震撼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地位,然而,由于国民党方面蒋介石、汪精卫等人背信弃义,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此后,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的民族危机依旧,国内地主阶级与农民的阶级矛盾依旧,甚至更加尖锐。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仍面临着严峻的抉择。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对当时社会性质的深刻分析,选择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血腥镇压,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起义,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和组织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武装夺取政权,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在中国的统治的道路。土地革命消灭了农村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得到了农民的拥护,迅速发展扩大,到1930年,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区域已达到湘、鄂、赣、皖、豫、浙、陕等许多省份。在苏区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农民抗租、抗税、抢米等暴动不断发生与蔓延,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在农村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与苏区土地革命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国民党统治区内不少不满于现状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不赞成对中国农村实行资本主义改造,认为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一方面又不赞成或不敢主张采取共产党人激烈的革命方式,消灭农村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他们希望通过改良,找到某种折衷方式或第三条道路,以挽救农村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并以此为基础,挽救整个中国社会的危机,建立民主政治。这些知识分子从以往历次运动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造只注意于上而不求统一于下,当下他们所应当做的,是推进国民的能力与知识的增进,培养他们的新政治习惯,让国民自主地掌握社会发展的方向。正如梁漱溟所指出的“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从基础做起,就是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村一乡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注: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二、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探索
乡村建设学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晏阳初等,在从事实际的乡村建设实验前,以及实验过程中,对当时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出路各自都进行了理论探索,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看法,这些成为乡村建设实验的理论根据。
(一)梁漱溟的“中国文化失调与重建”理论
梁漱溟是中国社会学史上“乡村建设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国内外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主要著作有《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1)、《乡村建设理论》(1936年)等。梁漱溟倡导与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主要理论根据,是他所提出的“中国文化失调与重建理论”。这一理论是贯穿于以上所列梁漱溟主要著作及其他著述与言论中的一根主线。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他通过比较研究,认为现在的东西方文化不是在同一个发展层次上的,而是体现了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路向。他把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演进过程依次分为三条路向,即第一条路向,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发展为其根本精神;文化发展的第二条路向,即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合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第三条路向,为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梁漱溟有关文化发展三种路向的划分,主要是从文化的精神层面的特征为着眼点的,他认为西洋物质文明远较中国及印度发达,但就精神生活而言,中国文化高出西洋文化,而印度文化又超出中国文化。
梁漱溟由文化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到对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探讨。这种探讨,仍属于其文化探讨的一部分,因为,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的文化,要以其社会组织构造为骨干,而法制、礼俗实居文化最重要部分。他在对社会组织结构的探讨中,注重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他认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与西洋中古及近代社会皆有不同之处。西洋近代社会是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而传统的中国社会则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所谓“伦理本位”,就是整个社会受着“伦理关系(情谊关系)”,“义务关系”的支配,这种关系始于家庭,并表现于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所谓“职业分立”,就是在中国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不存在两面对立的阶级。(注:参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邹平乡村书店,1936年版,第18—28页。)然而,自西洋文化进入以后,中国的这种“伦理本位”与“职业分立”的传统社会组织结构被破坏了。其结果并未象西洋那样进入“个人本位”与“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是陷入一种所谓的“旧辙已破,新轨未立”的境地,这种境地,便是文化的失调,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状态,社会问题丛生。这种文化失调突出地表现于西洋“都市文明”对中国传统的“乡村文明”的破坏。在他看来,中国原为乡村国家,以乡村为根基与主体,而发育成高度的乡村文明。中国这种乡村文明近代以来受到来自西洋都市文明的挑战。西洋文明逼迫中国往资本主义工商业路上走,然而八十多年来除了乡村破坏外并未见都市的兴起,只见固有农业衰残而未见新工商业的发达。这是梁漱溟等所最感到痛苦的事。
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既已崩溃,那么,就应当考虑如何构建新的社会组织。这种新的社会组织为何种模样?梁漱溟对此作了勾划:“中国如果有一个团体组织出现,那就是一个中西具体事实的融合,可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这个团体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而以人生向上为前进的目标(这两项很重要,西洋人亦将转变到这里来。)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所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邹平乡村书店,1936年,第175页。 )对西洋文化的接受,主要是接受其先进的物质文化;而中国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精神生活则是高出西洋人的,应保持不变。亦即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接受西洋文化,并将其融汇于中国文化之中。鉴于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的组织结构在城市已被摧残殆尽,所以梁漱溟认为,构建新的社会组织必须从乡村入手。由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的特点及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西洋人所走过的工业化与都市化道路,于梁漱溟看来,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应走出一条不同的路,这条路即是从农村引发工业,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
梁漱溟还具体谈到了他以上构想的实现所依靠的力量,在于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的合作。他说:“中国问题的解决,其发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要研究的是他们以如何方式构合成一力量。……要研究的是他们以如何方式构合成一力量。那自然就是我们乡村运动这一条道了。”(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邹平乡村书店,1936年版,第344页。)
(二)晏阳初等人的“愚穷弱私论”
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人,1913年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前身),1916年秋转至美国耶鲁大学,主修政治学与经济学,1919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主修历史学,翌年获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1923年与陶行知、朱其慧、蔡元培等人在京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任总干事。1926年开始在河北定县主持乡村改造实验工作,并因此而名闻遐迩。以后又在多处主持平民教育、乡村实验及为乡村建设培养人才的工作。著有《平民教育概论》(1928年)、《农村运动的使命》(1935年)、《十年来的中国》(1937年)等书。
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理论依据,是他及平教会提出的“愚穷弱私论”。晏阳初等人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主要是农村问题,其根本问题则是人的问题。晏阳初等人通过详细研究,发现在中国人身上存在着四大缺陷,这就是“愚”、“穷”、“弱”、“私”。所谓“愚”,即是指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是目不识丁;所谓穷,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就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根本谈不到什么生活程度。所谓弱,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无庸讳言简直就是病夫,现代科学医疗,公共卫生等,根本谈不上。所谓私,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不能团结,不知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现代公民知识的训练。(注:参见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载《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第56—57页。)由于中国人身上存在以上病症或问题,因而他们缺乏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中国的一切建设,亦无从谈起。
针对以上四大病症,晏阳初与平教会提出实施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主要措施包括推广平民文学、平民艺术、农村戏剧三项,解决农民“愚”的问题;以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包括农民生计训练,向他们传授各种农业技术,推广合作组织,改良动植物品种,提倡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等,解决农民“穷”的问题;以卫生教育培植强健力,通过设立县级系统的卫生保健制度,普及卫生知识,养成卫生习惯,开展传染病防治等,解决农民“弱”的问题;以公民教育培植团结力,通过合作精神的教育和公民知识的传授,解决农民“私”的问题。在“愚穷弱私”四大问题中,“愚”的问题是最基本的,因此,晏阳初等人特别强调“除文盲”的意义,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他们并提出学校式、家庭式与社会式等三大教育方式,以适应“四大教育”的需要,其中“学校式教育”是主体,通过普遍设立平民学校来进行。
在晏阳初等人看来,近代以来历次自救运动之所以没有达到民族自救的目的,原因在于没有发现对大多数中国人的教育问题。因此他们要发动一场新的自救运动,即“平民教育运动”,以弥补以前历次运动的缺陷。晏阳初等人所讲的“平民教育”,就其具体内容与实施方式而言,实际上就是社会学理论上所讲的对“再社会化”的工作。这项工作涉及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项全面的农村建设。
三、乡村建设学派主持及影响下的社会改良实验
乡村建设有时称“农村建设”或“乡治”、“村治”,称谓虽有不同,实质却是一样的,都是有关农村社会的改良而言的。早在清朝末年,米迪刚等人就在其家乡河北定县翟城村从事过“村治”实验。民国以后,山西阎锡山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亦通过“编村”和“整理村范”的办法实施过所谓的“村治”。北伐战争时期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不少知识分子于探索民族自救的途径过程中,走上了乡村建设实验的道路。这一时期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内乡村建设事业非常发达,其中以梁漱溟主持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及晏阳初主持的河北定县乡村建设实验最为有名,对全国的乡村建设事业起到了示范与推动作用。
(一)梁漱溟主持的邹平乡村建设实验
梁漱溟选定山东省的邹平县实施其乡村建设实验计划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1928年梁漱溟曾到广东,准备于广州开办乡治讲习所,后因缺乏支持而未办成。回到北方后,1930年与彭禹廷、梁仲华等人在河南办村治学院,出任教务长,他写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对学院内部进行了规划,并兼任北京出版的《村治月刊》主编。其后他又与村治学院一班人到山东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院址就设在邹平,并选定该县作为乡村建设的实验县。梁漱溟之所以选择邹平,是因为该县离济南不远,又靠近胶济铁路,地理位置较好,交通方便,本身规模又比较适中,在该县从事乡村建设实验,搞起来相对容易些。
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目的在于“研究乡村自治及一切乡村建设问题,并培养乡村自治及乡村服务人才,以期指导本省乡村建设之完成。”(注:据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三册,第78页。)研究院主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乡村建设研究部,每年从大学毕业生中招考四十人,学习与研究乡村建设理论等课程,两年后分配到各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组织与指导工作。第二部分为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该部的任务是招考初高中毕业生开办训练班,每县10—20名,学员花一年时间学习乡村建设理论、农业知识、农村自卫、精神陶练及武术等科目,结业后,回到各县担任乡村建设的骨干。第三部分即乡村建设实验区,选定邹平县进行实验。实验县县长、县政府隶属于研究院,其中县长由研究院提名,省政府任命。研究院成立之初仅设邹平为实验县。1932年国民党政府在各省推行县政实验方案后,研究院又于1933年增设荷泽为实验县,以后实验范围扩大到山东省内三个专区三十个县,但其他实验县皆以邹平实验县作为范本。
邹平实验县县级组织即县政府,县长直辖“一室五科”,即秘书室及分管民政、武装、财政、交通通讯、教育等一室五科。“一室五科”的负责人,不少就是研究部的学生。县政府另设户籍、承审、公报、民众问事、金融流通等处所。县以下辖十四乡,每乡辖若干行政村。梁漱溟主持下的邹平乡村建设实验是以组织乡农学校为出发点的。乡农学校成员,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乡村领袖,二是成年农民,三是研究院结业学生。其开办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先由研究院结业学生到乡村去,从各地乡村中寻找有声望有力量的人士,通过他们组织乡农学校董事会,董事会聘请当地知识品行较佳者担任校长,办理招收学生等一切事宜。乡农学校的教师,一般由研究部结业学生担任。学校分普通与高级两部,未完成国民教育及目不识丁者入普通部,小学毕业者入高级部。高级部课程注重史地及农村问题;普通部课程除各校共设的识字、音乐、唱歌、精神讲话等之外,为各校因地制宜而设置的课程,后一类课程,各校不求一致。
后来,为改造乡村组织,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在邹平实验县取消原有的乡公所和村公所,将原先的乡农学校改办成乡学与村学。几个村或十个村有一乡学。乡学设学董会,学董会推选学长,由地方乡绅名流担任,县政府下聘书。学长位居众人之上,起监督协调作用。学董会推选一人为常务学董兼理事,处理乡级日常行政事务。乡学还设有教导主任一人负责管理教育工作。为在各项工作中贯彻乡村建设宗旨,研究院派来辅导员一人指导与协助乡理事和教导主任工作。乡学还设有乡队部、户籍室、卫生室等组织机构。乡学以下设村学,其组织结构和乡学大致相似。乡学村学的学员来自乡村全体农民,被称为学众。从乡学村学的组织结构看,它们实际上都是政教合一的机构。
梁漱溟等人取消乡村公所等自治组织而以乡学村学取而代之,并不是不要自治组织,而是要借助乡学村学训练乡下人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及活动力,培养乡民的新政治习惯,锻炼乡村自治组织的能力。在他看来,一旦乡学村学真正发生组织作用,乡村多数人的注意力与活动力均得到启发,新政治习惯培养成功而完成县自治,研究实验县的大功就算告成了。而研究实验县的成功对于中国地方自治问题的解决,则不啻发明了一把锁钥。“中国将来的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本着这么一个格局,这么一个精神,这么一个规模发挥出来。”(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260页。 )乡学村学在培养乡民新政治习惯时,梁漱溟尤其强调应符合中国的传统伦理精神。这种伦理是从情谊出发,以对方为重,这样,人与人的关系可以作到联锁密切融合无间的地步。他于中国传统的“五伦”之上,又加上个人对团体与团体对个人一伦,这二者之间亦应互为尊重,互有义务。
乡学村学在将一盘散沙的乡农组织起来,注意培养他们新政治习惯与团体合作精神的同时,也推行了一些社会改良的工作,如禁烟、禁赌、兴办合作社、鼓励妇女放足等等。此外,乡民通过接受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教育,也推动了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先进农业机械的运用与耕作方式的改进,有利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从而带动农民生活的增进。
梁漱溟以“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八个字来概括他在邹平实验县所开展的乡村建设工作,并号召全体村民“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这些正好体现了他所主张的中国新的组织结构的形成应以中国固有的精神为主,同时吸收西洋文化科学技术的长处的精神。
(二)晏阳初主持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
晏阳初主持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一般称作平民教育实验,盖因为这项实验是从实施平民教育开始的,实际上这项实验后来发展成整体的乡村建设计划。1926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确定该县翟城村为实验区。前已述及,清朝末年已有米迪刚等人在翟城村搞过村治实验,有一定的基础。至1930年,平教会向全县推广该村的实验计划,设立定县实验区。
平教会所开展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是以晏阳初等人所提出的“愚穷弱私论”为理论依据的。其工作的进行,分为调查、研究、实验、表演与推行五个步骤。以除文盲为例,其五个步骤大致是:1、 对全县文盲与非文盲人口进行调查;2、 对非文盲所需最低限度的文字知识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编写《千字课》课本;3、 在实验学校对《千字课》的适用与否进行实验,并作修改;4、 以修改后的课本在表演学校进行示范表演;5、向所有平民学校推广。
1930年定县乡村建设实验开始的时候,曾拟定出一个十年计划,打算前三年完成全县的文艺教育,再用三年完成全县生计教育,最后用四年时间完成全县公民教育。而卫生教育贯穿整个十年计划中。但实际工作开展起来以后,他们发现十年计划将四大教育基本分开进行效果并不理想,于是,1932年他们放弃了十年计划, 而改订一个六年计划, 自1932年7月开始至1938年6月结束。六年计划规定实验区研究实验工作由村而区,由区而县进行;从农民生活中发现问题;运用并连锁四大教育,以求得问题的解决。平教会并拟以这六年为研究实验期,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过渡到表证训练期,以全国为范围,全面推广定县乡村建设经验。和邹平实验县普遍设立乡农学校并取代乡村公所的做法有所不同,定县的实验一方面提倡设立各种平民学校,以培养训练地方乡村建设人才;一方面对原有的乡村小学加以改造,使小学教育与平民教育相结合,共同推动乡村建设事业。另外,定县的平民学校也不代行乡村行政组织的职能。
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工作并没有按计划所设计的那样进行下去并向全国推行,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整个实验工作便停顿下来了。
(三)邹平、定县乡村建设实验影响下的全国性的乡村建设实验事业
邹平、定县两地乡村建设实验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至抗战爆发以前,全国各地所开展的乡村建设事业,比较重要的多达七十多处。(注:据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三册,第74页。)其中有注重乡村社会整体改进的,亦有专注于某一方面的乡村建设活动。前者除邹平、定县实验区外,还有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江恒源、赵叔遇等人在江苏昆山县徐公桥乡开展的实验、冷遇秋等人在江苏江宁黄墟主办的实验以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许仕廉、杨开道等人在北平昌平开办的清河实验区等。至于专注于乡村生活某一方面的实验活动,就更多了,其中有注重经济事业的乡村建设,注重地方自治的乡村建设,注重一般设施改进的乡村建设,等等。各地所开展的乡村建设事业历史有长有短,范围有大有小,工作有繁有易,动机不尽相同,但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乡村建设学派所主办的邹平、定县实验的影响。这些实验至抗战前大多停止,也有少数延续到抗战开始以后。
四、乡村建设学派的局限与贡献
(一)乡村建设学派的局限
从二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乡村建设实验,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基本上结束了。实际上在此之前,乡村建设实验早已困难重重。1934年10月在定县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注:从事乡村建设事业的人士为了相互沟通,交流经验,促进工作的开展,举办过三次全国规模的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讨论会1933年7 月在山东邹平实验县召开,到会70余人,代表35个乡建团体;第二次于1934年10月在定县实验区召开,与会150余人,代表76个团体,来自11省;第三次于1935年 10月在江苏无锡举办,到会169人,代表104个团体,分属18省。这以后由于乡村实验所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特别是由于抗战爆发,讨论会终止。)上,晏阳初向会议汇报平教会定县实验工作时指出:“定县的全部实验工作,起始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五年经过,其成功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实难断言。因为第一是人才问题。这种改造全生活的实验,关系的方面太多,无处供给所需要的各种人才。第二是经费问题。在这民穷财尽的时候,很难筹措这百年大计的实验费。第三是社会环境的问题。现在全国方在一个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环境中,国难如此严重,大家容易误认这种工作为不急之务。第四是时间问题。这种改造民族生活的大计划,决不会一刹那间就能成功。有此四种困难,平教运动的前途,殊可傈傈危惧。”(注: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三册,第91页。)
梁漱溟1935年10月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讲演中也谈到实验工作中的两大难处:第一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府;第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关于第一点,梁漱溟认为,政府最代表惰性、不进步性,要完成社会改造,就不应当接近政权,就应当否定它。既不否定它,并顺随它在它底下活动,甚至依附于它,这本身就表明实验者失掉了革命性,社会改造工作亦就无从谈起。关于第二点,梁漱溟以定县与邹平的实例作了说明:“定县平教会,定县人并不欢迎,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和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至少是彼此两回事,没有打成一片。即如我们邹平,假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征求乡下人的意见——乡村建设研究院要搬家了,你们愿意不愿意?投票的结果如何,我亦不敢担保。……走也不留,不走也可以,真正的老乡恐怕就是这个态度的。这个就足见你运动你的,与他无关,他并没动。……乡村运动天然要以农民作基础力量,而向前开展;如果我们动而乡村不动,那有什么前途呢?”(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附录,第3—4页。)
乡村建设实验也引起社会学界其他人士的批评。其中陈序经的批评比较有代表性。他指出,乡村建设本来是一项非常实际的工作,然而,从十余年来的乡村建设工作来看,远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历次乡村工作讨论会及出版的各种乡村建设文献、报告,多是空谈计划、偏重理论的。从各实验区来看,从事实际工作的寥寥无几,往往是宣传工作多于实际工作。从乡村建设工作的四个方面即教育、卫生、政治、农业等方面来衡量,未免使人失望。针对各地乡村建设实验机构庞大,工作人员众多的情况,陈序经更尖锐地指出,“乡村建设的目标是救济乡村农民,然结果却变为救济工作人员”。因为,在他看来,“乡村运动之在今日,好象差不多要到了专为着维持工作人员,保存乡建机关而工作的地步。对于乡村,对于农民,精神方面固少有建树,物质方面更少有改造。”乡村建设工作如果照此下去,恐怕今后会养出一个吃乡建饭的新阶级来。(注:参见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载《独立评论》196号,1936年4月12日;《乡村建设运动平议(三)》,载《农村建设》一卷四期,1939年3月。)
从乡村建设学派代表人物的分析及其他人士的批评中可见,乡村建设工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可以说是失败的。之所以会如此,当时的一些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如千家驹、孙冶方、薛暮桥、李紫翔等作了深刻的分析。千家驹等人在分析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缺陷时指出:“他们只看到了社会现象的表面病态——愚、穷、弱、私,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究中国农民为什么会愚,会穷,会弱,会私?他们根本不了解埋在这‘愚、穷、弱、私’底里的帝国主义之侵略与封建残余的剥削,才是‘愚穷弱私’的原因”。(注:千家驹:《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载《中国农村》二卷一期,1936年1月1日。)梁漱溟以文化问题代替其他一切问题,用“伦理本位”与“职业分立”否定阶级区分,其错误亦是不言而喻的。在分析乡建学派理论缺陷的基础上,从唯物史观出发的这批学者进一步指出,在整个民族陷于沦亡危机的时候,中国的乡村建设不能离开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而单独进行。中国的问题,是整体性的,想由农业引发工业,以农村复兴振兴都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仅就乡村问题本身而言,其最根本的方面是土地分配问题,仅从农业技术、农业改良、农产品运销、金融流通等枝节问题上下功夫,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之苦。
正是由于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与实际工作存在着以上根本缺陷,因此,他们拯救农村、复兴民族的目的根本不可能达到。即使在他们实验区的范围内,也并没有使农民摆脱贫穷破产的命运。相反,在不根本触动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的统治与剥削地位的前提下从事乡村重建工作,从客观而言,有利于维护既存的统治秩序,方便了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与经济侵略。
乡村建设学派理论与实践中所存在的以上缺陷,主要是由于知识分子本身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在政治上,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并非看不到中国农村破产、民族危机的真实原因,李景汉先生在《定县土地调查》(发表于《社会科学》第一卷第1—2期,1936年清华大学出版)报告中,甚至提及了农村问题之核心的土地问题。(注:参见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第181—182页。)梁漱溟也不满于“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府”,认为依靠国民党政府而实现社会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由于知识分子自身的软弱性,他们于实际工作中又不敢触及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的统治,不敢触动农村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不得不依附政府的经费而实施具体的实验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乡村建设工作就陷入了不可克服的矛盾:“他们想不谈中国社会之政治的经济的根本问题,但他们要解决的却正是这些根本问题。他们不敢正视促使中国农村破产的真正原因,但他们所要救济的却正是由这些原因所促成的国民经济破产与农村破产”。其结果便是“实验自实验,破产自破产”,甚至有朝一日“破产的浪潮会把实验的一点基础也打击得粉碎”。(注:千家驹:《中国农村建设之路何在》,载《申报月刊》三卷十期;参见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史》,第165页。)
乡村建设学派的局限性也表现在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上。尽管他们希望与农民打成一片而开展实验工作,但实际上,他们与农民的沟通存在着许多障碍。对此,李景汉曾经指出:“与农民打成一片,话是很容易说的,志愿也容易定的。等到实行的时候,问题可就发生了。”“起初你愿和他打成一片,他们躲避不愿和你打成一片;等到后来,他愿和你打成一片时,你又受不了,不愿和他打成一片”。“因为他本人的气味,使你不舒服;家内炕上的不洁净,使你坐不住,食品的粗劣,使你难下咽,其他种种不卫生的状态,和拿时间不算回事的和你应酬,都是使你不大受得了的,就是能够居然作下去,也免不了是很勉强的,痛苦的。”(注:李景汉:《深入民间的一些经验与感想》,载《独立评论》,第179号,1935年12月1日。)李景汉的这些话算是给梁漱溟“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根源从一个侧面作了比较生动、形象的注脚。
(二)乡村建设学派的贡献
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与实践虽然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从总体上看是失败的,这也说明了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改良主义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具体而言,乡村建设学派也有不少值得肯定之处。著名学者孙本文认为,该学派“值得称述”之处,主要有两点:“第一,他们认定农村为我国社会的基本,欲从改进农村下手,以改进整个社会。此种立场,虽未必完全正确;但就我国目前状况言,农村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农业为国民的主要职业;而农产不振,农村生活困苦,潜在表现足为整个社会进步的障碍。故改进农村,至少可为整个社会进步的张本。第二,他们确实在农村中不畏艰苦为农民谋福利。各地农村工作计划虽有优有劣,有完有缺,其效果虽有大有小;而工作人员确脚踏实地在改进农村的总目标下努力工作,其艰苦耐劳的精神,殊足令人起敬。”(注: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三册,第93—94页。)
我们认为,乡村建设学派的工作值得肯定之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乡村建设学派的工作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但在发展农村教育,培养农村人材,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农村合作及其他公益事业等等方面,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从成立到1936年,研究部共办两期,培养学生58人;训练部共办三期,培养学生1040人;其他短训班四处,培养学生1300余人,总计2400余人。邹平实验县所办的乡农学校,从1931年6月开始至1932年2月结束,共成立96校,学生近4000人。1932年冬,乡农学校已遍布于济南周围近三十个县,共有71所学校,164个班,学生5000余人。 平教会在定县推广平民教育的成绩更加突出。自1927年以来,该县所开办平民学校毕业学生人数,总计在十万人以上。这种减少文盲的工作,在当时全国1900余县当中,是首屈一指的。邹平、定县等实验区在推广农业技术,改良作物与家禽品种,开展农村合作事业方面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注:以上数据据鲁振祥:《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初步考察》,载《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4期;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三册, 第80页。)乡村建设学派的这些工作甚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不少国家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乡村建设与社区重建中,注意借鉴中国乡村建设学派的一些具体做法。乡建学派的著名代表晏阳初50年代以后应邀赴菲律宾、非洲及拉美国家介绍中国的乡村建设工作经验,并从事具体的指导工作。(注:参见李善锋:《乡村建设运动:一个社会学的考察》,载《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5期。)
第二,乡村建设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追随者,大多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如晏阳初、梁漱溟等,“他们有的是学历、资格、地位,他们原可以在都市中高官厚禄地享受物质生活,但是他们宁愿跑到农村里去吃苦,他们忠于自己的理想,懂得民族的主要力量是在农民,他们企图在这工作中能替国家开出一条大路来。不管他们宗派怎样,不管他们的理想是天上的还是人间的,不管他们的理想是否真能为农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光明,他们的动机总是纯洁的”。(注:孙晓村:《乡村运动大联合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国农村》第二卷第十期,1936年10月1日。)这些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 本人的地位与所受的教育,使得他们与乡村农民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屏障;他们与农民的接触过程中,正如前面引述的李景汉的几段话所显示的,内心里实际上是很痛苦的。然而,他们为着自己的理想,仍然勤勤恳恳,勉力为之,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直到今天,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第三,乡村建设学派的探索引起了社会学界的争论,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事业。梁漱溟等人所提出的由农业引发工业,以农村振兴都市的观点及其通过乡村建设重建中国“伦理本位”的传统文化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吴景超在其所著《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一书中,不同意梁漱溟的观点,提出“发展都市救济乡村”这一针锋相对的看法。他认为在当时兴起的乡村建设的潮流之下,很少有人从发展都市着眼去救济农村;甚至还有许多人把都市看作农村的仇敌,认为都市对于农村,不但没有贡献,反可使农村的破产加深,等等,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是应当加以矫正的。他提出应当从都市着眼去看待乡村问题。通过发展都市以达到解救乡村的目的。发展都市包括兴办工业,发展交通,扩充金融事业等等。兴办工业可以将一部分农民迁入都市,留在乡下的农民因争食者减少,其生活自然可以舒适一些。发展交通可以方便农产品向都市的运输,因交通成本减少农民因此而得到好价钱。扩充金融机关则可以使农民得到比较优惠的贷款以兴办农村事业。如果能够做到都市与农村共存共荣,那么农村虽然现在经济萧条,农民破产,将来总有繁荣一日。当时社会学界另一知名学者陈序经在其所著《中国文化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一书中,批判了梁漱溟提出的在构建中国新的社会组织时要以中国儒家固有的文化精神为基础去接受西洋文化的思想。他说:“梁先生劝中国人去做孔子的生活与全盘采纳西洋文化不能同时并行的;而况根本上孔教化,……是不能和西化相容的。”(注: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80页。)陈序经以近代西洋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优越且接受西洋文化是当时的世界性的趋势出发,提出了中国要全盘西化的主张。纵观吴景超、陈序经等人有关中国出路的看法,虽然与乡村建设学派不同,但依然是改良主义性质的。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且不去管它。我们所注重的是,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以上看法,从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由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与实际的乡村实验工作所引发出来的。乡村建设学派在推动中国早期的社会学研究事业上的贡献功不可没。
第四,乡村建设学派的社会改良实验的最终失败,亦从反面给从唯物史观出发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以有益的启示。拯救中国社会不能走改良的道路,而必须走革命的道路。
标签:梁漱溟论文; 晏阳初论文; 邹平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培养理论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生活教育论文; 社会组织论文; 经济论文; 农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