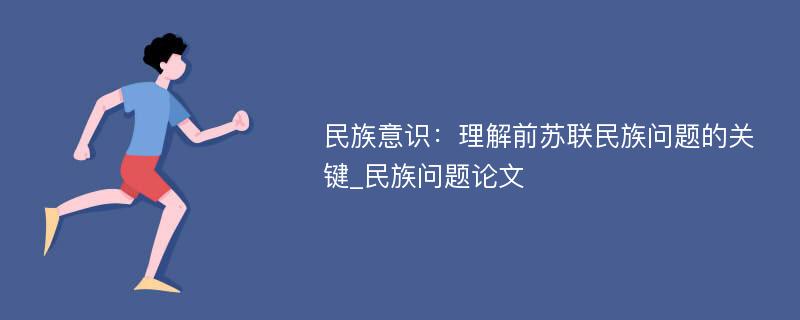
民族意识:理解前苏联民族问题的关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前苏联论文,意识论文,关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认为,前苏联的民族问题固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关,但这些因素最终都是通过民族意识来发挥作用的。民族意识以共同的心理素质为核心,并带有不容否认的两面性。正是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加上前苏联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经济形势的恶化、政治上的公开性和民主化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使其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得以畸形发展,进而演化为民族主义的行为。
关键词民族意识 心理素质 民族主义
前苏联曾经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强国却在突然间崩溃瓦解。前苏联的崩溃并不是由于长期以来它所忧虑、防范的外敌入侵和热核战争,而是由于其自身民族问题的火山式爆发所致。其民族问题的根源何在?学术界对此著述甚丰,其立足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且各有侧重。笔者认为,前苏联民族危机的全面爆发,是由于民族意识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畸变所致,这是前苏联民族问题的深层根源。
一、对民族意识规律性的认识
所谓民族,就是“相信他们自己具有同种文化遗产的共同体。”〔1〕作为这一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民族意识是在其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在与其他“共同体”的相互交往中,归属于某一民族集团的成员所形成的内部认同意识,以及由此将自己所属的民族集团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外部分界意识,其功能在于对民族利益的认识、追求和维护。民族意识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反映着民族存在这一客观现实。
民族意识是在民族共同体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变化演进的。在人类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氏族部落间的合作成为一种自然要求。在此合作过程中,通过日益密切而广泛的交往联系最终形成了“民族”这一历史群体。这一过程在他们思想中的反映就是对其特点和利益一致性的认识。这是“民族”得以产生的心理基础。与此同时,民族意识又随着民族共同体内部与外部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但民族意识一经形成,就有着较大的稳定性,它与民族存在的变化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即使散居各地,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同一民族的民族意识仍然有着不可否认的同一性。
民族意识的核心是民族心理素质。毫无疑问,共同的语言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沟通思想、达成理解、保留共同文化遗产的巨大作用。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出现了同一语言为不同民族所采用,同一民族使用不同语言的现象;此外,同一民族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固定地域,不同民族杂居的现象随处可见;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更是有目共睹。从横向来看,没有任何民族可以把自己孤立起来。从纵向来看,也没有哪个民族总是处于同一个发展水平之上,民族经济生活的多样化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四项要素中,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已不能作为判断一个民族的共同标准了,只有“共同的心理素质”才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特征。
共同的心理素质表现在共同的文化特征——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历史传统、文化艺术等方面。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它是一个民族的“恒定表现形式”,通常“被看作是民族的关键特征,是导致某一民族的成员透过自己文化价值的棱镜审视其他民族‘我们——他们’两分法的根源。”〔2〕前苏联学者科兹洛夫对此作了更为精辟、通俗的论述。他指出,每个人都是在一定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生活和社会化的,“他们早在童年时代就掌握语言和文化,还接受人种观、价值观和思维定势,所有这些成为一种棱镜,接着透过这面棱镜来理解周围世界,包括外来民族集团等等;简言之,人们从童年起就成为自然的民族中心论者,并在人口再生产中将这种本性传给子女”。 〔3〕正是民族文化的这一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民族意识的稳定性。
民族意识对民族集团及其成员的行为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它所包含的内部认同意识和外部分界意识的层次性导致各民族及其成员在态度和行为上“内外有别”的特点。就成员个体来说,对本民族成员,他会表现出“接纳、理解、维护、信任的行为”,对其他民族的成员,“一般表现出礼貌、热情,但与本民族成员相比,又缺乏理解与维护的心理,”〔4〕而就整个民族集团来说, 它一方面要维护本民族成员间的和睦、团结,促进本民族的强大、繁荣,另一方面,对其他民族则表现出“戒备”、“防范”的行为。在这种意识的作用下,民族成员往往把自己与本民族集团的整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本民族的价值观念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念,并自然地关注本民族的兴衰、荣辱与得失,坚决地抵抗本民族所面临的外来压力与威胁,以维护本民族的尊严与生存。这种观念来自客观存在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
然而,正如前苏联学者杰缅季叶夫所指出的,“从心理学来说,民族特点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差别”。 〔5〕在多民族共存的情况下,民族差别可以增强民族内部的凝聚力。但另一方面,在某些因素的作用下,也可能使民族的分界意识得到强化,导致民族意识的畸变、扭曲,引发民族集团的排外性和对其他民族的误解、不满、怀疑与敌对
二、前苏联各民族意识的增强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民族意识最终将趋于消亡。但在消亡之前,必然要经历一个从自发、朦胧到自觉、觉醒的发展过程。这是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不断发展的结果。前苏联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
1.民族构成的复杂性是前苏联民族意识得以存在、加强的客观因素。前苏联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之一,民族构成极其复杂。据1989年统计,前苏联共有大小民族130余个,人口数量相差悬殊, 其中仅有19个民族的人口超过100万。 前苏联民族构成的复杂性还在于各民族杂居的状况。多民族的存在与杂居带来了各民族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面对外部环境的各种压力,各民族本能地要为维护自身的历史传统、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根本特征而斗争,而且表现得特别强烈、执著,民族意识随之得到加强。但这同时也埋下了民族关系紧张的种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罗伯特·康奎斯特指出:“人们普遍认为,在以某种方式决定苏联未来的诸种力量中,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民族力量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6〕
2.非俄罗斯民族政治地位的历史性提高从根本上唤起了它们的民族意识。沙俄曾经是“各民族人民的监狱”,非俄罗斯民族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十月革命后,苏俄(苏联)政府实行了以民族平等为核心的民族政策。各级民族自治体的建立,民族事务机构的健全,特别是1923年最高权力机关两院制的实行,都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利益与要求。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还通过一系列高等院校和各级党校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班子,主要由民族干部组成,他们甚至还可进入苏共中央核心机构。这样,各少数民族不仅拥有了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力,而且也参与了整个联盟的管理工作。此外,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舆论宣传也使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存在与活动的法律依据和政治意义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和切身体验,从而在历史比较中认识到了本民族存在的价值,民族自尊心得到满足,这成为促使它们进一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强大推动力。
3.非俄罗斯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刺激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叛乱斗争胜利后,苏俄(苏联)政府全面展开了消灭各民族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等状况的斗争。政府首先确立了因地制宜发展民族经济和向非俄罗斯地区倾斜的政策,同时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全力支持,使得各少数民族共和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自己的工业基础,农业经济状况也随着土地改革和集体化的实行而大为改善。民族教育也由于废除学校等级制度和民族限制,实行普遍义务教育,建立多层次多种类民族学校等措施而得到迅速发展,民族知识分子队伍随之成长起来。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类的需要有高低层次之分。高层次需要的提出以低层次需要的满足为前提,低层次需要的满足又可以促使高层次需要的萌发。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状况的历史性改善,这为他们提出更高层次的需要提供了物质基础。特别是随着民族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少数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价值、民族的发展前景充满了希望,对民族的前途更为关心,民族凝聚力得以加强。各民族间因经济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日益接近,也产生了维护其语言文化等特点的强烈欲望的反效应。这与民族团结的要求一样,都是民族意识增强的重要体现。
三、前苏联民族意识向民族主义的转化
民族意识的增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本身并不是什么消极现象。但从80年代中期以后,前苏联的民族意识却日益强烈地演化为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与民族意识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民族主义从其本来的含义讲,就是对其所属的民族共同体的忠诚以及对其命运的关注,这是一种思想意识、思想感情。然而,民族意识也有着不可否认的两面性,正如周恩来同志所指出的:“当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民族感情可以发挥团结人民的作用。……但是还要承认也会被反动阶级利用,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7〕可见,民族意识、民族主义如同一柄双刃剑, 一方面,它的正常发展可以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民族主义是以民族特征、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和民族利益为基础的,因而很容易在各民族之间造成猜疑、仇恨、不信任之类的隔阂和对立,也容易激起民族的狂热情绪,从而造成国家之间或一国之内不同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8〕甚至可能发生畸变而成为极端的民族主义。在前苏联, 这种状况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
1.民族政策的失误和对民族问题认识的超现实性造成了民族意识的扭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前苏联获得了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性机会,而且成效显著。但从30年代中期以后,它的民族政策却日渐偏离列宁主义轨道,如处理民族关系时以行政命令方法取代民主原则;对少数民族持不信任态度,把自然的民族自豪感贬斥为“民族主义”;对大批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清洗;强制移民,强制推广俄语,排挤少数民族语言;过多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片面渲染俄罗斯民族的先进性和历史进步作用,造成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抬头却视而不见等。这些错误作法严重伤害了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受压抑感使他们认为自己面临着外来压力与威胁,加深了历史所形成的心理鸿沟。
但前苏联领导人对民族关系状况的认识却严重脱离现实,片面夸大了所取得的成就。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报告中称,在苏联已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历史性共同体,即苏联人民。”勃列日涅夫甚至把这一观点载入1977年宪法。这就人为地制造了民族关系上相安无事,天下太平的虚假局面,从而弱化了他们的敏感性和警惕性,许多问题未能及时解决,民族情绪也难以得到正常表达。在民族情绪不断遭到压制的情况下,民族意识的扭曲就不可避免了。
2.经济的停滞恶化与不平衡性对民族意识产生了消极作用。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前苏联长期奉行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点的经济战略,农业和轻工业倍遭忽视。70年代中期后,国民经济又陷于停滞。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虽制定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但经济状况却日趋恶化。同时,前苏联长期把欧洲地区作为发展经济的重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未得到足够重视,从而带来了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民族地区经济的落后状况。这种经济状况的停滞恶化带来了社会的动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地方对中央的不满,带来了经济利己主义和共和国相互间的矛盾。这最终成了族际关系紧张与分离主义要求的肥沃土壤。
3.“民主化”与“公开性”导致了民族意识的进一步变形。长期存在的民族问题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凸显出来并最终产生爆炸性后果,绝非偶然。戈氏上台后展开了全方位改革,并把改革的成败与“民主化”、“公开性”联系起来。他虽然也估计到“可能有高谈民主,高谈公开性,并加以歪曲的情况”。〔9〕但他的正面强调仍是主要的, 对它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则估计不足。在这场巨大的历史性变革中,人们被动员起来投入了新的社会政治生活,社会的“透明度”越来越高,但保障“公开性”正常进行的制度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来。于是“公开性”偏离了原来为它设计的轨道,变成了向政府进行总清算的工具。其结果是,舆论失控,思想混乱,无政府状态以及形形色色的政党的涌现。与此同时,戈氏却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最终在1990年2 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决定实行多党制,取消了宪法赋予苏共的领导地位。这就使各民族失去了凝聚力的核心,失去了联盟得以维系的纽带。
在此情况下,一些民族反对派形成了。他们在局势失控的前苏联“既起着社会不满情绪的催化剂作用,又扮演着反系统运动的急先锋”,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系统的不稳定”。〔10〕他们以民族问题为武器,借苏共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煽动民族狂热和民族仇恨,民族间的历史矛盾日益激化突出。他们还借改革与“民主化”走上了“某些加盟共和国的前台”,“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发号施令,”〔11〕不仅要求经济自主,而且要求在政治上另起炉灶,脱离苏联。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挑战,传统的体制和秩序被打破,从而出现了“社会心理上的涣散和沉论颓废”,而这“又反过来形成对新的认同和忠诚的要求。”〔12〕这样,已发生畸变的民族意识便急剧膨胀,由维护民族的发展与繁荣最终走上了分离主义道路。
4.外部因素所发挥的催化剂作用。一个民族的行为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内在需要,同时也受着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戈氏上台后提出了国际政治“新思维”,使东欧在1989年剧变后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控制。这极大地刺激和鼓舞了前苏联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内的民族反对派。他们提出了日益强烈的独立要求,正是它们率先脱离苏联而独立。
从客观上讲,前苏联各民族的独立情绪是有较大差异的。但各民族间相互影响、相互仿效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了民族危机的总爆发。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对立的各少数民族,在反对俄罗斯化方面却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追求。另一方面,任何民族为维护自身权益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对其他民族来说,都是一种启示和诱惑,因而会予以支持、仿效。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的行动成了其他各共和国仿效的样板,进而引发了前苏联民族问题上的一呼百应的“多米诺效应”。
国际反苏势力在此过程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舆论媒体为他们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工具。在苏联解体前,共有40多家电台用27种语言对苏广播,每天累计达200个小时。 其中有些电台以批判集权主义为借口,以民族关系史上的阴暗面为材料,宣扬为“斯大林主义的牺牲者”进行应有的评价,煽动民族主义和民族仇视,竭力制造不稳定因素。作为对抗前苏联的一种软手段,西方的舆论媒体发挥了军事手段所难以发挥的巨大作用。
总而言之,前苏联的解体有着一系列复杂因素,但民族分离主义却是它的直接原因。而民族问题的总危机又在于民族意识的作用,在于民族意识向民族主义的转化。虽然这一转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完成的,但受前苏联政治、经济、文化等实际状况的影响,这一转化绝不是偶然的。前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重要的是要奉行一种正确而一贯的民族政策,确保少数民族的平等政治权力及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强化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这样才能确保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与繁荣。
注释:
〔1〕〔2〕〔6〕罗伯特·康奈斯特:《最后的帝国》, 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第50页、第1页。
〔3〕(苏)科兹洛夫:《民族问题:范式、理论和政策》,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1年第1期,第18页。
〔4〕参见孙玉兰等:《民族心理学》,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第20—30页。
〔5〕(苏)杰缅季叶夫:《论民族冲突心理》,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1年第5期,第32页。
〔7〕《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2页。
〔8〕陈林:《善御之自强,不善御之自伤》, 《世界知识》,1996年第7期,第9页。
〔9〕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第92页。
〔10〕(苏)加尔金:《社会稳定:某些理论观点》,《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第32页。
〔11〕(苏)洛吉诺夫:《有无摆脱危机的出路?》,《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6期,第15页。
〔12〕(美)塞缪尔·享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89年中文版,第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