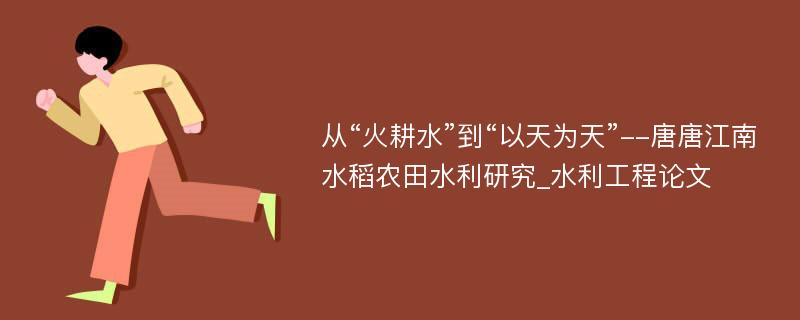
從“火耕水耨”到“以溝爲天”——漢唐間江南的稻作農業與水利工程考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火耕水耨论文,江南论文,水利工程论文,漢唐間论文,溝爲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江南”的地域範圍及“火耕水耨”的本質特徵 《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地理志》所謂“江南火耕水耨”的“江南”(或稱“楚越”、“越楚”、“江淮以南”),①大略相當於漢代的荆、揚二州刺史部。②此即漢代“寬泛”意義上的“江南”。③《隋書·地理志下》所謂“江南之俗火耕水耨”的“江南”,④卻是《爾雅·釋地》“江南曰楊(揚)州”的“江南”,《禹貢》“淮海惟揚州”的“揚州”的同義語,約當“吴越”故地,即《尚書》孔傳所謂“北據淮、南距海”,⑤《禹貢》荊州之地則被排除在外。大致範圍爲淮河以南、今長江下游迤南抵嶺南、迤東至海濱的東南地區。 本文中的江南取《隋志》義,而以其中的長江下游三角洲地區爲中心,約略相當於唐元和方鎮中的淮南、宣歙、浙東、浙西四道。⑥韓愈“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的“江南”,杜牧“今天下以江淮爲國命”的“江淮”,⑦皆是這一區域的概稱。該區域以長江爲界可大體分爲江淮間、江南兩大部分,即舊史中所謂“江西”、“江東”。由於江南、江淮又是本文所論地區的概稱,爲免混淆,下文指稱以上兩分區時,通常作“江淮地區”、“江東地區”。 據上引《史記》、《漢書》,古代江南的飲食結構爲“飯稻羹魚”,與之相應的產業結構則是“火耕水耨”式稻作農業和以魚爲主的水產品采捕業並重。 關於火耕水耨的自然、社會環境,⑧首先是地廣人稀,沒有條件在稻作生產上投入大量勞動力。又因有“川澤山林之饒”特別是“三江五湖之利”,“地埶饒食”尤其是水產品豐富,故“食物常足”,⑨從而也沒有必要在稻作生產上投入大量勞動力。火耕水耨最適宜的地區是瀕海傍湖的水澤之地和沖積扇狀的河谷盆地,這裏水源豐富卻有季節性漲落,並非長年積水。秋冬枯涸可以火耕,春夏多水可資水耨。 所謂火耕水耨式稻作的本質特徵,即是在耕耨環節上勞動投入少,卻有相對較高效益。但火耕水耨既不能做到完全“不煩人力”,仍需要對水、火尤其是水有一定程度控制,也就是有一定的水利設施如陂、堰,還需有水產捕撈業爲其補充——毋寧說是保障,這就決定了火耕水耨式稻作需要有相應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條件,從而構成了它發展的瓶頸。 那麼,在東漢六朝間的江南,相對於火耕水耨,是否還存在另一種更先進的稻作法?學界有不同意見,筆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即至遲東漢以後,便存在以完善的農田水利設施爲特徵的先進稻作方式,用時人的話即是“[水]田制之由人”。⑩以下分江淮、江東兩個地區,對漢唐間江南的稻作發展與水利的關係,在前人基礎上略加考論。 二 東漢六朝時期江淮地區稻作發展的曲折過程及其特點 淮水流域的陂塘灌溉自古號稱發達,其中期思陂、芍陂最爲著稱,前者甚至被認爲是中國水利史上有文獻可考的最早的大型農田灌溉工程。(11)兩漢時期在前代基礎上又有顯著發展,最有名的是淮水及其支流汝水之間的“鴻隙大陂”。西漢成帝時因洪水漫溢,朝廷采納翟方進建議而“決去陂水”,以致“陂下良田”“無溉灌,不生秔稻”,只能種植豆芋等旱作。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汝南太守鄧晨起用長於水利技術的許楊爲都水掾,主持修復鴻隙陂,“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在原基礎上似有擴展,故“數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12) 據《水經注》,鴻隙陂“陂首受淮川”,與淮水支流慎水上的燋陂、上慎陂、中慎陂、下慎陂,慎水支流汶水上的南陂、北陂、同陂、窖陂、壁陂(汶水出慎水,而流入汝水),作爲淮水支流的申陂水所發源之申陂,淮水另一重要支流汝水以及汝水衆支流上的黃陵陂、蔡塘、葛陂、鮦陂、橫塘陂、青陂、北青陂、東塘(屬青陂一部)、馬城陂、綢陂、牆陂等等大小陂塘,皆相互通連,所謂“水積之處,謂之陂塘,津渠交絡、枝布川隰矣”,從而組成一個以淮水及其支流爲脈絡、以鴻隙陂爲中心、陂塘串連有如“長藤結瓜”、縱橫交結宛若蜘蛛結網似的灌溉系統。(13)自此以東,淮水兩岸特別是淮北,類似的陂塘灌溉系統非止一處,此不贅述。 以上所述皆在淮北。淮南支流則以窮水、沘水、泄水、肥水諸水入淮口段(包括各水支流),以及其上的諸多陂塘,匯成一個以大型水體芍陂爲中心的陂塘系統,其規模差與淮北鴻隙陂灌溉系統相比擬。 兩漢時期淮河流域的水利建設,淮北的發展遠過於淮南。從《水經注》可見,淮水流域北岸許多陂塘至北魏猶存,故酈道元能一一指按,“據以爲說”。(14)但淮水南岸支流決水下游原期思陂所在地區,幾乎未見該水利設施的任何遺存。《水經注》作者酈道元曾“因公至於淮津……次於決水”,親訪當地百姓、官員,乃知當地的水文面貌、水道名稱,已“與古名全違”,(15)他在《水經注》中對期思陂亦隻字未提。又芍陂水利系統中西邊窮水所“流結”之窮陂,據《水經注》載:“塘堰雖淪,猶用不輟,陂水四分,農事用康。”(16)可見窮水作爲自然水體雖仍在發揮其灌溉功能,但其原有的灌溉設施卻早已淪廢。不過芍陂主體及其灌溉設施、功能,《水經注》仍能確指,包括其方位、面積乃至“吐納川流”的五個陂門等,(17)表明芍陂遺迹,至北魏猶存,這可能與後世的維護、修治有關。據北宋人記述的當地傳說,西漢羹頡侯劉信曾在其封地即淮水支流沘水上游的“龍舒之地”興修水利,“以廣溉浸”,(18)曹魏劉馥所修七門堰即是憑藉其基礎而成。沘水流域塘堰本屬楚國創立的芍陂水利系統,劉信所建灌溉設施或是修復舊迹。但劉信之事不見於北宋以前文獻,文獻中所載最早修復芍陂水利系統的,是東漢前期的王景,《後漢書》本傳稱: 明年(章帝建初八年,83),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19) 王景在東漢明帝朝因成功治理黃河而“知名”。章帝時他在廬江太守任上“修起蕪廢”,實即修復芍陂水利設施。若水利系統“蕪廢”失修,不能有效發揮排灌功能,則“芍陂稻田”非淪爲沼澤,即乾旱拋荒,儘管其中部分地帶如濱湖之地或可利用水勢的季節性漲落從事廣種薄收的“火耕水耨”式稻作,或改種適合粗放管理的豆芋等旱作——有如當年鴻隙陂廢決後當地民謠所描述的,(20)但這必定會影響糧食產量,導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在修復水利設施的基礎上,王景又將犁耕引入到水稻生產中。北方旱作在兩漢業已進入犁耕時代,但就南方稻作而言,這可能是傳世文獻中最早運用牛耕的明確記載。數年後王景卒官於廬江,他死後是否人亡政息,不得而知。 此後直到漢末獻帝時,專擅朝政的曹操任命劉馥爲揚州刺史,建安五年(200)到任。《三國志》本傳稱劉馥在任上:“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吴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21)馥建安十三年卒官揚州。十四年曹操率水軍“出肥水,軍合肥”,“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22)可見劉馥卒後,曹魏在芍陂的屯田及其水利興建仍在進行。劉馥在揚州前後九年,《三國志》本傳記其死後“揚州士民益追思之……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可見劉馥之興治芍陂卓有成效,遺惠於西晉。而據《太平寰宇記》等記載,茹陂、七門、吴塘等,晚至宋代遺迹猶存,功能不廢。(23)建安十八年,曹操又任朱光爲廬江太守,率衆數萬“屯皖,大開稻田”,次年爲吴軍攻滅,劉馥所修吴塘即在此地。(24)魏文帝即位初,豫州刺史賈逵在汝水流域“造新陂”,“通運渠”,鄭渾在“蕭、相二縣界”即泗水支流睢水、獲水間“興陂遏,開稻田”,(25)均各有建樹,但二者都屬偶然的個例,且有人亡政息之虞。曹魏時期在淮水流域所興修的水利工程中,最有代表性的還是鄧艾屯田。 魏齊王芳正始(240-249)年間,鄧艾提議並主持的大規模淮上屯田,在執掌朝政的司馬懿支持下得以按計劃施行。(26)對於六朝時期淮河流域的農田水利及稻作生產來說,這次屯田影響深遠。其一,相對於此前王景、劉馥之興復芍陂,雖同樣是由官府組織,但前者是“驅率吏民”服役,水利效益亦由官民分享——“官民有畜”,後者卻是“軍屯”,以帶甲之士“且田且守”,或者準軍事化管理的士家屯田,以世襲兵戶“出戰入耕”。屯田所得,“計除衆費”即在生產成本和將士俸祿廩賜、士家生活開支之外,均充軍糧,以資伐吴。(27) 其二,其屯田區域規模空前,規劃嚴密而有系統。“於陳、項以東至壽春”,尤以貫通黃、淮水系的淮水支流浪蕩渠、潁水一線爲中心,淮南則集中在以壽春芍陂爲中心的淮水支流沘水、肥水流域,“淮南淮北皆相連結”。淮北以潁水流域爲重點。潁北的陳郡陳縣有溉灌城、集糧城、柳陂,均爲鄧艾“開廣漕渠溉良田”時所築,其中柳城即因“鄧艾營稻陂時柳舒爲陂長”而得名,可知陂塘的修建、維護皆有專人負責。(28)潁北宋縣還有占地“萬三千餘頃”的泗陂。(29)潁南的汝南郡項縣有磚城,史稱“鄧艾於此置屯種稻”,築此城以“圍倉廩”。(30)僅潁南、潁北陂渠,即“溉田二萬頃”。(31)汝水流域的西平縣,有鄧艾所置“二十四陂”,(32)而此地正是兩漢鴻隙陂水利系統所在。淮南“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五萬屯田軍士中“淮南三萬人”),而此地正是芍陂水利系統所在,(33)史稱後“鄧艾重修此陂,堰山谷之水,旁爲小陂五十餘所,沿淮諸鎮並仰給於此”。(34)鄧艾建於淮南的另一處大型水利工程,是淮水下游的白水陂,鄧艾“於此置屯田四十九所”,“開八水門”,“溉田萬二千頃”,後世還在陂上立有鄧艾廟。(35)淮陰縣南還有石鼈城,亦爲鄧艾築,“以營田”。(36)白水陂本“與盱眙縣破釜塘相連”,而鄧艾曾在盱眙縣北的軍山“營堰澗爲塘,以溉稻田”。(37) 其三,由於實行軍事化的組織管理——設置屯營,統一調度——如“引河流通淮潁”、“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集中大量的强壯勞力——現役兵士即有五萬之衆以及不少於現役兵士的屯田兵戶(士家),加之主管其事的鄧艾“矯然彊壯,立功立事”,(38)有很强的領導能力,故而屯田效率高,成果豐,溉田動輒以萬頃計,“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水利工程所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是政治軍事效益。史稱“自壽春到京師”,淮南淮北“農官兵田……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39) 其四,鄧艾屯田以及曹魏此前的許下屯田,幾乎全是稻作,故上引史籍載鄧艾之興修陂塘徑記爲“置屯種稻”、“以溉稻田”,所建陂塘則徑稱作“稻陂”。正是由於有水利設施的保障,鄧艾屯田纔取得很高的生產率。以“常有四萬人”(五萬兵士“十二分休”即五分之一番修)“歲完五百萬斛”計,每個士兵年提供軍糧多達一百二十五斛,即使加上屯田士家,共約“十餘萬官兵”,(40)亦人均五十斛,況且這些人都有軍事任務在身,足見其稻作產量非常之高。傅玄曾稱“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41)我想鄧艾在淮上的軍屯,就其大修水利、大量勞動力投入而言,堪稱“務修其功力”,加之又是水稻,故產量之高是可以理解的。我以爲傅玄正是基於曹魏許下特別是淮上屯田所取得的稻作生產成績,纔提出“陸田者命懸於天”、“[水]田制之由人”的觀點的。(42) 鄧艾能夠在淮水流域推行如此大規模的軍屯,還有一個不可或缺的背景,那就是三國時南北對峙,“曹(操)、孫(權)之霸,才均智敵”,徐、泗、江、淮爲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無復民戶”,(43)從而出現大量的拋荒田土,這就爲大規模屯田、興修水利提供了基本的條件。 但軍屯的根本目的是爲了積蓄軍糧,服務於軍事,屯田過程中戰禍兵燹更是在所難免。如劉馥修治芍陂未久,廬江屯田即多次受到孫吴的攻擊,不得“安屯”。(44)又如吴赤烏四年(241)孫權遣將攻魏淮南,“决芍陂”,(45)焚燒糧倉。芍陂成爲戰場。鄧艾屯田後不到十年,曹魏相繼爆發淮南三叛,屯田淮上的兵士、士家全部捲入內戰,並招致吴軍深入,對屯田及其水利設施的破壞可以想見。屯田的兵士、士家由於“且耕且戰”,“出戰入耕”,常有生命危險而幾乎沒有經濟收益,生產積極性與日俱減,史稱其“怨曠積年”。(46)加之曹魏後期屯田,“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產量不斷下降,“或不足以償種”,甚至於“成穀”也被有意“損棄”。(47)一方面由於“務多頃畝”特別是爲了擴大水稻面積,曹魏淮上屯田不顧地形水勢,不惜淹沒現有農田(“傷敗成業”),大修陂塘以溉水田,甚至將部分“陸業”也改爲水田;另一方面則由於“功不能修理”,所以興修的陂塘多不堅牢,“每有水雨”便潰決成災。(48) 農田水利工程創建不易,維護尤難,因爲它需要經常性的爲數巨大的人力、財力支出。前述翟方進奏請決破鴻隙陂,“省堤防費”即爲重要原因之一。東漢時汝南“郡多陂池,歲歲決壞”,用於維護和修復的經費,“年費常三千餘萬”。(49)西晉時僅芍陂的維修,年徵用民夫即達“數萬人”。(50)而且這種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和維護,端賴官府組織實施,因而與國家的治亂,地方官員的責任、能力,關係尤大。即使是承平時期,大型水利工程也往往因地方財政難以支撑,地方官不作爲,而興廢不常。諸如鄧艾在作爲南北(魏吴)對峙、爭奪之中間地帶的淮河流域進行軍屯,(51)則主要出於對吴戰爭需要,因而帶有特殊性和功利性:即當地空荒無人從而有大量的無主田地,在屯田的勞力集結和組織實施上依賴强大的軍事動員能力和嚴格的軍事化管理,而一切以有利於更快更多地屯聚軍糧爲旨歸。在鄧艾屯田後三十餘年,即晉武帝咸寧(275-280)年間,當時因東南諸州連年“水澇”成災,原淮上屯田區的地方官胡威、應遵皆上疏要求決壞曹魏新修陂塘,朝廷最後接受杜預的建議並施行之:凡屬“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因其“堅完修固”,故皆保存之,其中“當有所補塞者”,則修復之;凡“魏氏以來所造立”的“兗豫州東界諸陂”,因其不牢固而連年潰決,“大爲災害”,且因數量太多而致“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殃“延及陸田”,故“皆決瀝之”,“隨其所歸而宣導之”;凡原爲“漢之陸業”而爲曹魏改爲水田者,一律恢復旱作。(52)杜預上疏《通鑑》繫於咸寧四年(278)七月,次年冬,晉大舉伐吴,再次年之三月,吴平,則杜預建議當在平吴之後實施。 曹魏時期以鄧艾軍屯爲代表的大規模屯田,使淮河流域的稻作生產及相應的陂塘建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它既表現在稻作面積的擴張上,淮北潁水流域的部分旱作甚至被改爲稻作;也表現在稻作技術的進步上,特別是在勞動力投入(“務修其功力”)和陂塘灌渠的營建上。然而這都是在南北對峙背景下仰賴軍事動員、舉政府之力實施屯田的特定情況下出現的。曹魏後期,淮上屯田已出現向落後的火耕水耨稻作方式回歸(“務多頃畝而功不修”)的傾向,隨着西晉平吴天下重歸一統,因“吴平,民各還本”(即還居江淮間),(53)曹魏淮上屯田的特殊背景及條件已完全喪失,以杜預上疏爲契機,當地的稻作生產重新回歸到東漢時代的常態。這種回復,也是以西晉滅吴,南北一度重歸一統爲前提的。 然而如所周知,西晉的短暫統一很快被打破,自晉室南遷,直到隋唐重歸一統前,淮河流域又重新成爲南北政權間爭奪、對峙的中間地帶。其間雖沒有像鄧艾所主持的那種大規模軍屯,但南北政權在所控制的中間地帶內興修水利、實行屯田的事例卻不乏史載,即如芍陂,東晉、南朝宋、齊、梁及北朝北魏,均有修治芍陂、屯田種稻的記載,其例甚多,兹不贅舉。其中除梁裴之橫係私人屯墾(實亦有官方背景)外,(54)均爲軍屯,以戍兵及田兵爲勞動力。其耕作方式或粗放或精細,但都對芍陂水利系統有所修復,重墾熟荒,且有充足的勞動力投入。但總的來說,有如東晉殷浩遣將“開江西疁田千餘頃”,即利用秋冬枯水季節在熟荒田裏燒草,修治、利用原有的芍陂水利系統灌水,然後種稻,帶有明顯的火耕水耨特徵。東晉初應詹上表稱“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實亦采取這種“疁田”形式。(55) 總之,在東晉南北朝時期作爲南北爭奪的“中間地帶”的江淮地區,水稻生產及其農田水利工程,主要是耕墾熟荒和修治、利用已有水利灌溉系統,采取軍屯形式,目的在於提供軍糧,以減輕轉漕負擔,帶有很强的軍事性、權宜性、特殊性。隨着所控制地區的易手,戰局的變化,軍隊駐屯地點的改變,所墾稻田及其水利設施亦隨之而拋荒,稻作生產方式亦返於粗放。這與同時期江東地區稻作生產的發展有着顯著的區別。 三 東漢六朝時期江東地區稻作的顯著發展及其特點 相對於江淮地區,江東地區的稻作技術和水利建設的發展,起步要晚得多。本文所言江東相當於魏晉時所謂三吴,(56)大抵可分爲三個板塊,即寧鎮丘陵的丹陽(西晉分置晉陵),太湖平原的吴郡、吴興(西晉分置義興),寧紹平原的會稽。春秋時吴、越就曾築堤圍塘,用於農業灌溉,如吴有世子塘、野鹿陂、吴錫陂(塘),越有富中大塘、鍊塘、吴塘等,(57)“每一處塘,其實就是一片從沼澤平原上改造過來的耕地”,(58)不過溉田頃畝看來都不大。江東地區歷史上最古老的大型農田水利工程,當推東漢時興建於會稽的鑑湖(當時稱鏡湖),(59)位於今浙江紹興縣境。縣境內從東南到西北,爲會稽山脈所圍繞,發源於山脈諸丘陵分支之間的許多自南而北的河流,分別匯入曹娥、浦陽二江下游,流入後海(杭州灣),在北部形成廣闊的沖積平原(山會平原),整個地區呈現出“山—原—海”的臺階式特有地形。雨季的山水盛發造成的曹娥、浦陽二江下游洪水泛濫,錢塘大潮致富含鹽分的海水經由二江倒灌,造成平原北部的嚴重內澇及鹹漬化,瀦成無數湖泊,洪水季節則淪爲一片澤國。東漢永和五年(140),會稽太守馬臻主持修築鑑湖。該工程的主體是圍堤,即在山會平原北端亦即分散的衆多湖泊北緣,修建了一條以會稽郡城爲中心,向西向東分別延伸到浦陽江、曹娥江側近,總長一百二十餘里的長圍堤。堤南河湖因遭攔截而形成一個巨大的長形水體,即鑑湖,亦因其形狀而得名長湖。工程的另一重要部分是由斗門、閘、堰、陰溝組成的水利設施系統。劉宋時會稽山陰人、曾官會稽太守的孔靈符所撰《會稽記》稱: 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水高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水少則泄湖灌田,如水多則閉湖泄田中水入海,所以無凶年。其堤塘周迴三百一十里,都溉田九千餘頃。(60) 又《水經注疏》卷四○《漸江水》亦稱:“浙江又東北得長湖口……沿湖開水門六十九所,下溉田萬頃。”(61)上引可知,鑑湖的攔蓄滯洪能力和豐富蓄水,使鑑湖以北的山會平原解除了洪水威脅,擁有了充分的灌溉用水;有門閘堰溝水利設施系統,加之“山—原—海”臺階式地形,使灌溉方法相對簡便,並降低了灌溉成本;從而使山會平原北部的沼澤地,被改造成爲旱澇保收的優質稻田。這近萬頃穩產高產稻田,可能是當時江南甚至是中國南部最早也是最大的一塊成片的優質稻田。鑑湖在北宋湮廢之前,曾爲這一大片良田提供水利服務達八百年之久,成爲寧紹平原經濟開發的標誌工程和基礎建設。 鑑湖的創立及其巨大的灌溉效益背後,還隱含着一些已露端倪或可以推知的背景及問題。前文談到山會平原北部的內澇,是因曹娥、浦陽二江的山洪和潮汐所致。溯二江而上的鹹潮,不僅侵入到山會平原北部的內河水系,甚至乘勢上溯平原南部,高程與海平面接近的平原北部瀕海地區,更爲鹹潮所直擊。故而通過築堤圍塘蓄淡禦鹹,已經成爲當時山會平原發展農業生產的前提因素。據說春秋時代,山會平原北部沿海地區已開始修建局部的海塘,以拒禦鹹潮。(62)建立於山會平原南部的鑑湖不僅滯緩了山洪北下的速率,而且基本上解決了“蓄淡”的問題,而這正是以平原北部已擁有一定的水利系統從而能夠“拒鹹”、“用淡”爲前提的。(63)然而要做到有效“拒鹹”,則必須在山會平原北部沿海一帶,建立一條擋潮拒鹹的完整堤塘;而要做到充分“用淡”,就要進一步優化、整合平原北部的河流、溝渠系統。這些構成了鑑湖創立之後山會平原農田水利亟待解決的中心課題,同時也是江東沿海地區提高稻作水平所必須解決的普遍性問題。 山會平原南部的開發程度本來超過北部,如前所述,大型陂塘的建築勢必要淹沒一部分現有農田,所以當馬臻決意在山會平原南部修建長達一百二十餘里、周長三百五十多里的鑑湖時,他一定知道如此大範圍的築堤蓄水勢必會損壞當地居民的現實利益,如淹沒田宅,他也一定對此舉的影響——爲北部帶來水利效益而給南部造成經濟損失,作了權衡、取捨。往後的歷史證明他的決策是正確的,創立鑑湖所帶來的巨大、長期效益遠過於給南部造成的損失。然而馬臻也爲自己的決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據上引《會稽記》記載: 創(鏡)湖之始,多淹塚宅,有千餘人怨訴於臺,(馬)臻遂被刑於市。及臺中遣使按鞠(鞫),總不見人,驗籍,皆是先死亡人之名。(64) 這些“怨訴於臺”者,自然是山會平原開發較早的南部地區亦即鑑湖所在地區人氏,新創立的鑑湖,淹沒了他們的住宅、祖墳,當然還有他們的耕地;他們在訴狀中之所以不提耕地,是因爲創立湖陂,耕地被淹是題中應有之義,但“塚宅”被淹,則可歸咎於創立者行事專橫,特別是在組織湖區民戶遷移方面動員不力,措施不到位,强行造湖而傷害民生,激起了民憤。這些“怨訴於臺”者至少上訴的組織者,應是當地的大姓豪强及其代表——即必然由他們出任的郡縣長吏。(65)會稽郡治山陰,東距首都洛陽三千八百里,(66)“千餘人”的上訴團不可能都遠赴中“臺”,大多數人不過是在訴狀上簽名而已。然而當“臺中”遣使到會稽來調查、刑偵時,卻找不到這些簽名者,核查戶籍,纔發現這些人早已死亡。看來這是一起山陰地方勢力制造的寃案,後世亦認爲“(馬)臻之爲湖不利於豪右,故相與訟之,而假死者以爲名”。(67)前述西漢成帝時翟方進因連年洪水而上奏建議決破汝南鴻隙陂,以及東漢初許楊主持修復鴻隙陂,都受到當地“豪右大姓”的攻擊,許楊亦因之而下獄。(68)馬臻以生命換來了“山陰界內比畔接疆無荒廢之田”,“九千頃之田千餘年無水旱”,故“越人”直到趙宋時仍“廟祀之”。(69) 馬臻蒙寃事件,充分顯示出東漢時期會稽山陰地區大姓豪强勢力的强大,以及他們在當地農田水利工程建設中的影響和作用。上文談到江東稻作農業生產對水利建設的需求,一是蓄淡、滯洪,一是拒鹹、捍潮。東漢時期在拒禦鹹潮方面也有建樹。《世說新語·雅量》“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條注引《錢唐縣記》: 縣近海,爲潮漂沒,縣諸豪姓,斂錢雇人,輦土爲塘,因以爲名也。(70) 按《錢唐縣記》,一作《錢唐(塘)記》,爲劉宋元嘉年間劉道真所著,(71)蕭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時距《錢唐記》成書未遠,與孝標同時的北魏酈道元注《水經》“漸江水”,亦曾引載此書,但提供的卻是錢塘建立的另一版本: 《錢唐記》曰: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許,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一斛土石者,即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於是載土石者皆棄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錢塘焉。(72) 這一版本的故事,《太平御覽》多次引録,其中《資產部·錢》所引最詳: 《錢塘記》曰:防海大塘。郡議曹華信象家(家豪)富,乃議立此塘,以防海水。信始開募,有致土石一斛,即與錢一斗。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誦(譎)云不復取,於是載土者皆棄置而去,塘以之成。既遏絕湖漁(潮源),一竟(境)蒙利,縣遷治餘姚。王莽時,縣名泉亭,於是改爲錢塘。百姓懷德,立碑塘所,至今猶在。(73) 按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已指出錢塘“秦時已有此名”,(74)不待東漢時華信以錢募人築塘而得名。又受募者已將土石運至塘所,華信卻“譎”稱不再需要而拒付勞酬,有如兒戲,既不近人情,又不符事理,當時“塘未成”,如此不講信用豈能蕆事完工?這顯然是後世添加的情節,使之更具故事性、趣味性,從而訛傳成真,及至唐代李吉甫始“疑所說爲謬”。然而這一故事仍蘊含着重要的歷史信息。其一,這個拒潮的大型海塘的主持修建者是錢塘縣“諸豪姓”,可能是以擔任會稽郡議曹的華信爲首,所以後一個版本中的主持修建者就變成華信一人了。其二,海塘修建的資金來源爲縣“諸豪姓”集資(“斂錢”)所得,可能是因爲華信家“豪富”,出錢最多,所以後一個版本中其他集資人就省略不提了。《太平寰宇記·杭州》所引《錢塘記》,甚至徑稱“鄉人華信將私錢召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云云。(75)其三,該工程的運作方式是通過市場,以錢雇傭勞動力,包括土石的收集、運輸,當然也包括塘的修築。可能是在交易過程中,買方憑藉其大姓豪强的身份、地位,導致買賣不公,纔導致第二個版本的故事,但從中仍可見賣方對自己的勞動力和土石仍有自由處置權。總之,錢塘防海大塘在中國捍潮海塘建築史上具有開創意義,它與鑑湖最大的不同在於,後者是官辦工程,官方投資,以徭役方式集結勞動力,在土地徵用及移民、徭役方面是强制性的,而前者是在當地豪族主導下完成的民辦工程,民間投資,勞動力、土石及工程建設,都是通過市場交易,買賣雙方自願。這是一個私人集資興辦、造福一方(“一境蒙利”)的地方公益工程,因而“百姓懷德,立碑塘所”,至劉宋時猶存。若就當地大姓豪强在地方水利事業興建中的重大作用而言,錢塘防海大塘與鑑湖都是同樣的,惟後者更爲典型、其作用更加凸現而已。 東漢孫吴時期,鑑湖之外,江東地區很少看到官辦的大型農田水利工程,但“漢時舊陂”、“故堰”,“舊遏古塘”,其遺迹仍所在多有,“非惟一所”,(76)不過其規模有限,其創立者鮮見記録,推測可能多爲“山谷私家小陂”。(77)《三國志》卷六四《吴書·濮陽興傳》: 永安三年(260),都尉嚴密建丹楊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保成,惟興以爲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78) 按“塘”,“堤也”,以“堤堰水也”。(79)“建丹陽湖田”,(80)即是在浦里,自然是湖灘或淺水沼澤處,築塘堤圍湖,然後排乾湖水整治稻田,此即後世所謂圍田、圩田。當然還要修建堰、閘、溝、渠等排灌設施。如果浦里塘能興築成功,那將是江東地區又一標誌性的大型官辦農田水利工程。然而在孫吴皇帝專門爲此召開的“百官會議”上,與會者一致反對,認爲“用功多”,而湖田未必能夠造成。建議者嚴密官止郡都尉,然而他的建議卻得到了“身居宰輔”的衛將軍、“平軍國事”濮陽興的贊同,於是工程還是在滿朝文武的反對聲中開張了。濮陽興還親率衛將軍府的兵士參與築塘。(81)結果卻一如百官會議所預料,“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兵民役死者衆多,“百姓大怨之”,丹陽湖田終於沒能建成。(82)十年之後(建衡元年,269),小吏奚熙又向吴主孫皓建議“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83)但遭到大臣反對。這一工程終吴之世未能成功,反映了孫吴國家對官辦大型工程的謹慎態度。除了事關軍國的漕運交通路線及其設施,孫吴時期幾乎看不到大型的官辦農田水利工程。如前所述,這類工程往往會損及當地大族豪强的田宅,而孫吴時江東豪族勢力以强大著稱,浦里塘最終未能建成很可能與他們的反對有關。 東晉南朝時期,江東地區官方主辦的農田水利工程數量激增。如東晉初晉陵內史張闓,因“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84)東晉吴興太守殷康於烏程縣“瀕湖之地”築荻塘,圍田千餘頃,後太守沈嘉重建之,改名吴興塘,劉宋時太守沈攸之,蕭齊時太守李安民,又相繼整修。(85)又成帝咸和(326-334)中虞潭任吴郡太守,“修滬瀆壘,以防海抄(沙),百姓賴之”,(86)滬瀆爲松江入海口,乃鹹潮洶湧之地,此壘當是拒鹹防潮工程。南朝江東地區見於記録的農田水利工程,以梁朝最多,如梁朝盧陵王記室參軍柳德威於普通(520-527)中在金壇縣東南造南謝塘、北謝塘,“各灌田千餘傾”,縣境內還有梁時所修謝塘、莞塘。(87)上舉張闓、柳德威所立塘,旨在蓄水灌田;荻塘則是在瀕湖地區築堤圍湖造田,(88)虞潭所築則是爲了捍拒鹹潮。總之,江東地區發展稻作所迫切需要的水利工程,如蓄淡、拒鹹、築堤圍湖以及排灌系統等,東晉南朝時各級地方官均有興作。 如前所述,官辦大型水利工程因勞役繁重、淹沒農田,很容易激發當地大姓勢力的反抗。張闓建新豐塘,《晉書》本傳稱“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興造免官”。我懷疑張闓被免乃當地大姓勢力上告朝廷所致,故“黜免始爾”即復官升職。(89)宋孝武帝時,丹陽尹孔靈符以“山陰縣土境偏狹,民多田少”,上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這實際上是到寧紹平原東部沿海地區築堤圍湖造田,孝武帝“使公卿博議”,然而發議者無一贊成,都主張“適任民情,從其所樂”。然而“上違(衆)議,從其(孔靈符議)徙民,並成良業”。(90)這一工程的規模、效益等細節,因文獻闕載,不得而知,但從中可知,大多數官員都對官方主辦大型工程持反對態度。 梁中大通二年(530)春,朝廷爲解決吴興郡連年水災的問題,將“發吴郡、吴興、義興三郡民丁”,“漕大瀆以瀉浙江”,昭明太子上書,以重役勞民,建議“權停此功”。(91)實際上關於吴興郡的排澇問題,早在劉宋時就已非常嚴重。《宋書·二凶傳·劉濬》載揚州刺史劉濬元嘉二十二年(445)上疏: 濬上言:“所統吴興郡,衿帶重山,地多汙澤,泉流歸集,疏決遲壅,時雨未過,已至漂沒。或方春輟耕,或開秋沈稼,田家徒苦,防遏無方……州民姚嶠比通便宜,以爲二吴、晉陵、義興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故處處湧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紵溪開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穿渠浛必無閡滯。自去踐行量度,二十許載。去(元嘉)十一年大水,已詣前刺史臣(劉)義康欲陳此計,即遣主簿盛曇泰隨嶠周行,互生疑難,議遂寢息。既事關大利,宜加研盡,登遣議曹從事史虞長孫與吴興太守孔山士同共履行,准望地勢,格評高下,其川源由歷,莫不踐校,圖畫形便,詳加算考,如所較量,決謂可立。尋四郡同患,非獨吴興,若此浛獲通,列邦蒙益。不有暫勞,無由永晏。然興創事大,圖始當難。今欲且開小漕,觀試流勢,輒差烏程、武康、東遷三縣近民,即時營作。若宜更增廣,尋更列言。昔鄭國敵將,史起畢忠,一開其說,萬世爲利。嶠之所建,雖則芻蕘,如或非妄,庶幾可立。”從之。功竟不立。(92) “從武康紵溪開漕谷湖,直出海口”,即東南直通杭州灣,這個工程頗類似於上文談到的後來梁朝擬建的“漕大瀆以瀉浙江”,旨在解決“松江滬瀆壅噎不利”的問題,這應該是當時太湖東南側競建堤塘溉田所引發的新問題。上引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規模宏大的水利工程的發起者,乃是在野的“州民姚嶠”。這是一位熱衷於鄉邦農田水利事業的民間專家,他以一己之力,費時二十餘年,實地踏勘,測量,並據以設計出擬修渠浛路線。元嘉十一年(434)吴興發大洪水,姚嶠乘機向時任揚州刺史的彭城王劉義康提出建議。義康遣主簿盛曇泰與姚嶠一同踏查,結果二人意見不合,“議遂寢息”。但後任揚州刺史劉濬,通過派遣議曹及吴興太守到實地考察,認定姚嶠建議可行。爲穩妥計,劉濬又請先開一條“小漕”以“觀試流勢”。但試開小漕,就要“差烏程、武康、東遷三縣近民”服役,整個工程用工之巨可以想見,這應是“功竟不立”的主要原因。武康姚氏爲當地大姓,(93)姚嶠的舉動也反映了江東地區“豪族富室”對官辦水利工程的積極介入,而且他是少見的持支持態度者。 正是鑑於地方大姓勢力的强大,官府擬舉辦大型水利工程,也要考慮到地方社會的態度。南齊建元三年(481),丹陽尹竟陵王蕭子良上表,擬全面“修治”丹陽境內的“舊遏古塘”,預計用功“十一萬八千餘夫”,“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其根據是他派遣屬吏到諸縣進行了踏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並村耆辭列”。(94)所謂“村耆辭列”,即是當地民衆特別是地方社會代表人物的大姓豪族,他們是通過書面陳辭正式向官方提出訴求的。 地方社會勢力的介入還反映在水利工程的管理上。《南齊書·王敬則傳》稱敬則爲會稽太守時,“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臺庫以爲便宜,上許之”。(95)對於王敬則將塘役改爲納錢並上交國庫的做法,竟陵王蕭子良上啓反對,他根據自己任會稽太守的經驗,指出: 其一,會稽郡“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即陂塘等水利設施常須維護、修治,儘管會稽郡甲年或者郡境內甲地水利設施“堅完”無損,全年無須服塘役,而乙年或者乙地,水利設施“毀壞”,當年即須維修,但郡內所有男丁,無論士庶,也無論災年豐年、有水利設施毀壞地區或者無毀壞地區,每年都須服“塘役”或者交代役錢(所謂“僮恤”),(96)主事者可將甲年或者甲地未用之塘丁或代役錢,調用於乙年、乙地,此即所謂“均夫訂直,民自爲用”。用之仍有餘,則民自保管,以俟後用,但“本不入官”。 其二,王敬則將未役塘丁一律納見錢,包括結餘未用的代役錢,全部上交國庫,這等於“租賦之外,更生一調”,且因“錢貴物賤”等因素,大大加重了百姓負擔。更重要的是,塘丁一律納錢代役,交納國庫,遂使水利設施的維修既無服現役的塘丁,又無雇丁力的資費,帶有自治性的“民丁無士庶皆保塘役”制度既遭破壞,故導致“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劇”。 其三,蕭子良建議“塘丁一條,宜還復舊”。但“上不納”。(97) 蕭子良在宋齊之際出任會稽太守,可知會稽郡塘丁錢“本不入官”、“民自爲用”,在宋代即是如此。王敬則在蕭齊初年正是繼蕭子良出任會稽太守,並成爲破壞該郡自治性“保塘役”之制的始作俑者。降至齊末東昏侯時,曾因後宮費用不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爲直,斂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由是所在塘瀆,多有隳廢”。(98)則王敬則所創塘丁錢入官在南齊朝得到了更廣泛的推行。 在東晉南朝,一如其他朝代,動員勞動力多至十萬二十萬、範圍橫跨數郡的大型水利工程,非官方主辦不可。這類工程對於改變六朝江東地區的水文面貌,完善農田水利系統,提高稻作生產率,以及對於改善普通民衆的再生產條件,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官辦水利工程中,我們仍能看到地方大姓豪族勢力的重要作用及影響。(99)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水利設施的維護上采取民間自治形式。這使我們自然聯想到中國傳統的里社組織,以及敦煌文書中所反映的唐宋之際當地種類繁多、功能各異的民衆結社,其中也包括水利工程興修及其管理方面的結社。(100)但南朝管理水利設施的民間自治組織,則是對全郡的塘丁錢集中保管,統籌使用,此前似不見於他地。然而該自治組織的主持者是誰?他們是如何產生出來的?統一保管的塘丁錢放在何處?這些都不得而知。推測仍是照例由地方大姓豪族出任的郡府屬吏代爲保管的,所以王敬則纔能將其輕易地收歸國庫,從而也使南朝官辦大型水利工程,很快就陷入毀壞失修的狀態中。這也是中國古代官辦大型水利工程的宿命。 東晉南朝江東地區的地方大姓豪族勢力,不僅在官辦大型水利工程中發揮着重要作用,而且他們自己也積極地圍湖造田,私建陂塘。《宋書》卷九一《孝義傳·徐耕》稱元嘉二十一年(444)“大旱民飢”,晉陵境尤爲嚴重。然而“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實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101)這些“並皆保熟”的“承陂之家”,所承陂塘,可能是對官辦水利工程的壟斷性、破壞性使用,更大的可能則是自家興造的私人陂塘,從“處處而是”可見其爲數甚夥。有實力造陂者,多是“溫富”、强豪。他們中有吴姓土著,也有僑姓名族。前者如張昭。《元和郡縣圖志·江南道·潤州》“上元縣”條:“婁湖,縣東南五里。吴張昭所創,溉田數十頃,周迴七里。昭封婁侯,故謂之婁湖。”(102)“周迴七里”,應是張昭圍築的湖塘周長,用以蓄水,並通過排灌設施澆溉周圍的數十頃田產。婁湖田產劉宋時爲吴興大族、朝廷重臣沈慶之所得。《宋書》本傳載其“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閈焉。廣開田園之業……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103)沈慶之在婁湖“廣開田園之業”,自然包括水利設施的建設,而他是有足夠的勞動力——“奴僮千計”,來舉辦這些工程的。 前面提到上表建議徙民會稽郡東“墾起湖田”的會稽大族孔靈符,《宋書》本傳稱他“家本豐,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104)這段引文常被引爲南朝時期山澤占領與開發的典型史料,(105)所謂“含山帶水”,即爲沖積扇山間盆地,要在此類地區耕種,特別是稻作,必須修築陂塘蓄水以溉田。東晉南朝時期開發山林湖澤的主力,無疑是南遷的僑姓大族,他們常常被迫到尚有空荒的會稽東部瀕海之地“求田問舍”,謝靈運常被引爲典型。他曾上書請求在“會稽東郭”的回踵湖決水爲田,“又求始寧岯崲湖爲田”,均遭到太守孟顗的强硬拒絕。於是他只好憑藉父、祖所遺留的雄厚家資,充足的勞動力(衆多奴僮及數百門生義故),在“傍山帶江”的會稽郡上虞、始寧間立墅,“鑿山浚湖,功役無已”。據所撰《山居賦》及其自注,其中有山丘,更有川流湖沼;有園林,更有農田;農田有旱田,更多水田。其中“苾苾香秔”的水田,有塍埒、導渠、支溝等完備的水利灌溉系統,亦兼有旱作。靈運在賦中自注稱:“上田在下湖之水口,名爲田口……西溪、南谷分流,谷鄣水畎入田口……東溪,逶迤下注良田”;“白爍尖者(山峯)最高,下有良田,王敬弘經始精舍。曇濟道人住孟山,名曰孟埭,芋薯之疁田”。(106)日本學者關尾史郎特別注意到這裏的“良田”、“疁田”之別,他指出前者即是有完善水利設施、勞動集約化程度高的稻作,後者則是指專種芋薯等耐旱作物的火耕陸作。而疁田也不排斥稻作,西晉陸雲《答車茂安書》所謂“火耕水種,不煩人力”云云,就是描寫毗鄰靈運山居的會稽鄮縣的火耕水耨式稻作。這種稻作也必須有一定的水利設施,惟其設施簡陋,排灌調節能力低下,故主要仰賴自然資源。(107)所謂自然資源,即指降雨及河流季節性漲枯平穩適時,或瀕湖臨河不易旱澇。按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會稽大旱,因“鄞縣多疁田”,太守豫章王劉子尚上表“至鄞縣勸農”救荒,(108)當因鄞縣山谷間沖積扇盆地原本存在着自然條件極好、稍加工力即回報甚豐的水利化稻田,以及簡便易爲的火耕旱田。太湖平原早在春秋時的吴國就有“疁田”,按吴都(今江蘇蘇州)周邊水網密佈,其疁田應屬火耕水耨式稻作,而有別於肥沃的“塘田”、“稻田”。(109)不過此後這一地區不再見到疁田。《說文》釋“疁”爲“燒穜(種)也”,後世字書亦釋爲“田不耕,火種也”,(110)故疁田通常被理解爲火種陸田。然而魏晉以降疁田也指水田,故有“田非疁水,皆播麥菽”之稱。而唐人何超《晉書音義》又釋“疁”曰:“案通溝溉田亦爲疁”,(111)則印證了前述火耕水耨式疁田稻作(疁水)也需要一定的控水設施,而疁田稻作技術似乎也在與時俱進,既有完善的水利設施,就不一定是火耕水耨,故唐人覺得有必要對“疁”重加界定。上引陸雲《答車茂安書》,贊揚會稽“鄮縣上地”,說那裏“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鈒成雲,下鈒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112)我以爲“燔茂草以爲田”,可能是指火耕山田,有如上引謝靈運《山居賦》自注中所謂“孟埭,芋薯之疁田”。“遏長川以爲陂”,則是水稻種植,卻並非以往人們常認爲的火耕水耨式稻作(疁田),而是有較完善水利設施,排灌“任意”,“不煩人力”的“上地”良田,即高產穩產稻田。 “良田”總是與水利設施相聯繫的,且多爲稻田。(113)反之,若“少陂渠”,則“田多惡穢”。即使芍陂號稱“龍泉之陂,良疇萬頃”,一旦“陂遏不修,咸成茂草”。(114)前面談到率軍北伐的東晉大臣殷浩曾遣將“開江西疁田”以積軍糧,即是采用火耕水耨式稻作法耕墾原芍陂灌區內的熟荒,這意味芍陂“良田”退化爲“疁田”。而就江東地區而言,在東晉南朝相對安定的政治統治下,伴隨着官私農田水利工程的興修,僑姓大族競相占領山澤、圍湖捍海,代表着水利設施完善、勞動投入集約化程度高的先進稻作方式的“良田”,正在穩步擴展,而代表着原始粗放的火耕水耨式稻作的“疁田”,正在相應地退縮。《宋書》列傳第十四末“史臣曰”: 江南之爲國盛矣……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既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及孫恩寇亂,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115) 沈約稱頌江南爲國之盛,特筆提出會稽郡“帶海傍湖”的數十萬頃“良疇”。這應該是江東甚至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一塊如此大面積的“良田”(優質高產稻田)。在這數十萬頃良田的形成過程中,首先是鑑湖的創立,在山會平原北部湖沼地形成了萬頃良田。東晉南朝時期以陳郡謝氏爲代表的僑姓大族在寧紹平原東部山間河谷盆地的開發活動,由孔靈符發議的移民於鄮、鄞等會稽東部瀕海地區圍墾“湖田”,使這些地區先後成爲“良業”、“良田”。會土“膏腴上地,畝直一金”的數十萬頃良田,使《禹貢》下下之地的揚州終於在經濟上超越上上之地的雍州,相對於“五胡亂華”以來長期淪爲戰地的關中,史臣謂江南“鄠、杜之間,不能比也”,絕非虚飾溢美。 東晉南朝時期,江東地區的丹陽郡,因其爲都城所在,僑舊大姓所聚,自然得到充分開發。“會稽舊稱沃壤”,亦是當時共識。吴郡作爲先秦吴國舊都,素稱發達之區。吴興雖號稱“塉土”,(116)但在南朝時期,興建了多種水利工程,並力圖解決因“松江滬瀆壅噎不利”常致內瀆的問題,開發正在加速。總之,隨着東晉南朝大批水利工程的陸續興建,包括蓄淡滯洪的陂湖,捍拒鹹潮的海塘,以及圍墾湖澤的堤堨,良田正在迅速增加。兹舉太湖東北側的常熟縣爲例。《隋書·地理志下》“吴郡常熟縣”條:“舊曰南沙。”《元和郡縣圖志·江南道·蘇州》“常熟縣”條:“本漢吴縣地,梁大同六年(540)置常熟縣。”(117)而據《光緒常昭合志稿·水利志》“敍”稱: 高鄉瀨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資灌溉,而旱無憂;低鄉田皆築圩,足以禦水,而澇亦不爲患。以故歲常熟,而縣以名焉。(118) 這雖爲後世追述,但唐人即稱常熟塘“實由灌溉之利,故縣取常熟,歲無眚焉”,宋人亦稱“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揚子江”云云,(119)則《合志稿》所載自有根據。那麽,至遲在蕭梁時,原吴郡南沙一帶即因其水利工程發達、旱澇保收而得常熟之名。這是“良田”向瀕江沿海的擴展。 南朝時期江東地區大片良田的出現,是以完善的農田水利設施爲特徵的先進稻作方式對南方傳統的粗放原始的稻作方式的勝利,易言之,是“良田”、“[水]田制之由人”對“疁田”、“火耕水耨”的擠壓和驅逐,這也是南方稻作對於歷史上長期居於領先地位的北方旱作的局部、初步勝利,從中隱約可見中國歷史上經濟重心南移這一重大變動的發軔。而在這一重大變動中,江東地區地方社會勢力在水利工程修建中的重要作用,值得特別注意。 四 唐代江南稻作的發展及其意義 憑藉六朝以來數百年的開發積累,唐代江南地區的稻作農業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安史之亂以後,由於黃河流域迭遭戰禍,强藩割據,以江南爲主的長江中下游流域幾乎獨力擔當了李唐王朝的財賦供給,這是意義深遠的重大變局。對於江南地區來説,在建都於北方的統一王朝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一變局的深層背景,仍是基於江南稻作農業生產的發展,而江南稻作農業的發展,則是以水利事業的發達爲基礎的。 關於唐代江南稻作農業及其與之相應的水利事業的進步,相關研究積累極其豐富,(120)爲免重複,本文擬在前人基礎上略作歸納。 六朝時期江南稻作農業之逐步擺脫火耕水耨,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水利工程的興建,時至唐代,農田水利建設的數量、規模、技術及管理水平均超過以往,雖然不同學者統計的口徑、資料來源、江南範圍以及具體數值不盡相同,但統計結果都一無例外地證明了這一點。 據冀朝鼎所製“中國治水活動的歷史發展與地理分佈的統計表”,大體相當於本文江南而範圍稍大的江蘇、安徽、浙江三省,春秋至隋共有水利活動四十五次,而唐代卻有七十四次,相當於前此時代本地區總數的164%。(121)表明唐代江南的水利建設活動,相對於前此時代,呈高速增長態勢。 陳勇根據所製《唐代長江下游地區水利工程興修表》,指出相當於本文所言江南的長江下游地區,以安史之亂爲界,前期水利工程爲二十九次,後期爲八十三次,是前期的2.86倍。其中溉田千頃以上的水利工程十五項,有十二項修建於中唐以後。(122)據另外學者統計,唐代十道灌溉面積千頃以上的農田水利工程有三十三項,其中江南一道即獨有十項,占全國30.3%。(123)可見唐代江南地區的水利工程,相對於中唐前,中唐後呈加倍增長態勢,這種態勢在大型水利工程的興建上表現得更爲充分。 筆者曾據《新唐書·地理志》對中唐前後南北水利工程數量作過統計比較。唐代水利工程總數爲二百六十一項次,修築時間不詳的二十五項次除外,中唐以前共一百五十三項次,北方諸道一百零三次,南方諸道五十項次,僅占總數32.7%。中唐以後凡八十三項次,北方諸道十二次,南方諸道七十一項次,占總數比例高達85.5%。(124)以上統計表明,在中唐以後北方水利事業的興辦迹近停止之時,南方水利事業持續上升,發展速度大大超過前期,占同期全國水利工程總項次的比例,由前期遠遠落後於北方,到後期遠遠超越北方,表明全國水利工程的興辦重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 汪家倫等對唐代十道中的江南、淮南二道(相當於本文所言的江南)的農田水利工程作了統計,前期有二十六次,占全國同期工程總數的17.2%,後期有五十四次,占全國同期的63.5。(125)可見在中唐後全國水利工程興辦重心的南移過程中,江南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六朝分裂時期,江淮地區作爲南北爭戰的中間地帶,農田水利工程常修常毀、修少而毀多,隋唐重歸一統以後,加之隋滅陳後長江下游的政治中心從建康移至江北的廣陵(今江蘇揚州),揚州富甲天下(揚一益二),江淮地區的水利興修也取得長足進步。隋文帝時趙軌任壽州總管府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126)東晉南朝,芍陂灌溉良田少則數千,多則上萬,(127)隋代時尚未恢復到最高水平。《水經·肥水注》載芍陂“周百二十許里”,而唐代芍陂周長達二百二十餘里,(128)則面積有所擴大,溉田面積亦當相應擴大。江淮地區內東漢以來一些常修常毀的大型水利工程在唐代大都得到修治而發揮功能。如東漢陳公塘(即愛敬陂),唐貞元初淮南節度使杜亞增築堤岸,新作斗門,“化磽薄爲膏腴者不知幾千萬畝”。曹魏時鄧艾所修白水陂,隋煬帝時一度涸竭,武后時重新恢復,肅宗、穆宗朝先後在白水陂周圍大興屯田,致使其灌溉面積大增。唐代在江淮地區新創的水利工程也不少。如貞觀中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譽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餘頃,貞元中淮南節度使杜佑又“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爲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又如元和中淮南節度使李吉甫在揚州高郵築富人(民)、固本、茅塘、盤塘、柘塘、裴公塘、麻塘等陂塘,僅富民、固本二塘即“溉田且萬頃”。(129)總之,唐後期江南在農田水利建設中所取得的巨大進步,與江淮地區逐漸擺脫六朝時期水利工程建設中的軍事性、權宜性,而步入從恢復到新創的發展軌道,是有着內在的關聯的。 江東地區,如上所述,在唐後期已成爲全國水利工程興修的重心所在。其成就和特色特別體現於如下數端,限於篇幅,加之前人所論已詳,故僅列其目,或略述梗概。 其一,東漢以來的一些重要的水利工程,均在唐代得到修復或擴建,並發揮其效益。不少水利工程雖創修於六朝,但真正發揮重大農田水利作用則是在唐中葉以後。 其二,規模空前的海塘工程的興建。 其三,唐代江南區創建了許多新的前此時代鮮見的特色水利工程。如長慶四年(824)杭州刺史白居易主持建築的錢塘湖工程,廣德元年(763)所開蘇州嘉興屯田。後者“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澤之政”,“畎距於溝,溝達於川,故道既堙,變溝爲田”。“旱則溉之,水則泄焉,曰雨曰霽,以溝爲天”,此即“天工人其代之”,“旱則溉之”代天降“雨”,“水則泄焉”讓天放晴(“霽”)。“全吴在揚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130)這是中唐時太湖平原東南部新出現的一大片優質稻田(吴郡、嘉禾屯田),這依然是水利工程的貢獻,是“[水]田制之由人”、“以溝爲天”的生產寫照。總之,哪裏有陂塘堤堨(遏)及排灌設施系統,那裏就有穩產高產的優質稻田,火耕水耨式稻作就從那裏退出。 其四,前文談到東漢六朝江東地區水利事業興建中地方大姓强族的重要作用,在天下一統的唐代,地方勢力的作用首先表現爲私人水利工程的普遍興修,其次表現爲對公共水利工程的壟斷性、破壞性利用。 其五,唐代江南稻作生產的進步,與水利工程的發展相應的,還有土地的墾殖與稻田面積的擴大,以江南龍骨水車爲代表的排灌工具的改進,以江東曲轅犁爲代表的耕作工具的進步,以插秧技術普及爲代表的水稻栽培技術和田間管理方面的進步,輪作、復種制的出現,等等,這些前人論述既詳,此不贅述。 總之,漢唐間江南稻作農業的發展過程,在東晉南朝是一個節點,其重要標誌是,“帶海傍湖”的“會土”(寧紹平原)出現了數十萬頃依賴農田水利保障的“膏腴上地”,這是以完善的農田水利設施爲特徵的先進稻作方式對南方傳統的粗放原始的稻作方式的勝利,易言之,是“制之由人”的“良田”即水利田對“火耕水耨”式稻作如“疁田”的擠壓和驅逐。若就六朝江南水利事業的區域特色而言,江東地區地方社會勢力在水利工程中的重要作用,與江淮地區水利工程建設中極强的軍事性、權宜性,適成鮮明對照。中唐是又一個重要的節點,中唐之前,除個別地區,南方稻作農業相對於北方旱作農業的優勢總體上還處於潛在狀態,中唐以後,江南出現興修農田水利工程的高潮,全國水利工程興修重心移到江南,特別是其江東地區,“以溝爲天”的水利田面積急劇擴大,犁耕、農作、插秧、灌溉諸方面的進步,使稻作相對於旱作的潛在優勢逐步發揮出來,與這種發揮相應的,是南方社會經濟開始超越北方,經濟重心由北而南移動的正式啓程。當此之際,長江中游地區也在迎頭趕上,(131)爲移動增加了助力。農業史上的這一重大變遷即南方稻作農業的崛起,對中國前近代社會的階段性演進或曰發展,提供了新的經濟活力。如果説北方旱作農業在唐代已接近其發展巔峯,那麽,以江南爲中心的南方稻作農業所蘊藏的深厚潛力纔剛剛開始發揮,它表明中國前近代社會所能容納的生產力還遠未到衰竭的地步。 ①《史記》卷一二九,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3270;《漢書》卷二八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666。 ②《鹽鐵論》卷一《通有》載鹽鐵會議上文學發言,有“荆、揚……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云云。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41—42。《周禮注疏》卷三三《職方氏》列敍九州五穀所宜時,只有揚州、荆州“宜稻”。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頁862上,中。 ③周振鶴《釋江南》,《中華文史論叢》第49輯,1992年,頁141—147。 ④《隋書》卷三一,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886。 ⑤《尚書正義》卷六《禹貢》,《爾雅注疏》卷七《釋地》,十三經注疏本,頁148中,2614下。 ⑥關於“江南”地域概念的界定,范金民總結爲三種,其二爲“長江下游三角洲地區”,其具體地域範圍略當本文所說的元和方鎮中的淮南、宣歙、浙東、浙西四道,詳見氏著《江南社會經濟史研究入門》“前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陳勇《唐代長江下游經濟發展研究》中的“長江下游”,即指此四道,詳見陳著第一章“導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1—4。地在江北、駐節揚州的淮南道在唐代“始終被當成江南來看待”,說見上引周振鶴《釋江南》。 ⑦韓愈《送陸員外出刺歙州詩序》,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啓》,《文苑英華》卷七一七,六六○,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6年,頁3706下,3391上。 ⑧限於篇幅,本節以下論“火耕水耨”的自然社會環境、本質特徵,係綜括筆者另文《“江南火耕水耨”再思考》(《中國農史》2013年第6期)而成。 ⑨分別見《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八下》,頁1666,1668;《史記·貨殖列傳》,頁3270。 ⑩《太平御覽》卷八二一引《傅子》,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頁3658上。原無“水”字,據馬總《意林》卷五引《傅子》補,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72册,頁272上。 (11)說見何浩《古代楚國的兩大水利工程期思陂與芍陂考略》,載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楚文化新探》,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119。 (12)《漢書》卷八四《翟方進傳》,頁3440;《後漢書》卷八二上《方術傳·許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710;《水經注疏》卷三○《淮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2507—2508。 (13)《水經注疏》卷三○《淮水》,頁2507—2509,卷二一《汝水》,頁1779—1791;《中國水利史稿》上册稱“‘長藤結瓜’的水利工程型式在南陽和汝南地區有着悠久的歷史”。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79年,頁145—147。 (14)《水經注疏》卷三○《淮水》“又東過新息縣南”條引熊會貞按語,頁2507。 (15)同上書卷三二《決水》,頁2666。 (16)《水經注疏》卷三○《淮水》,頁2519。 (17)《水經注疏》卷三○《淮水》,頁2518—2519;卷三二《決水》,頁2659—2666;同卷《沘水》、《泄水》、《肥水》,頁2667—2679。 (18)劉攽《七門廟記》,《全宋文》(69),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196—197。 (19)《後漢書》卷七六《循吏傳·王景》,頁2466。 (20)《漢書》卷八四《翟方進傳》,頁3440;《後漢書》卷八二上《方術傅·許楊》,頁2710。 (21)《三國志》卷一五《魏書·劉馥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463。 (22)同上書卷一《魏書·武帝紀》,頁32。 (23)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五《淮南道·舒州》,卷一二六《淮南道·廬州》,卷一二七《淮南道·光州》,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475,2497,2516。 (24)《三國志》卷五四《吴書·呂蒙傳》,頁1276;卷四七《吴書·吴主傳》,頁1119。 (25)同上書卷一五《魏書·賈逵傳》,卷一六《魏書·鄭渾傳》,頁482,511;《晉書》卷二六《食貨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784。 (26)《三國志》卷二八《魏書·鄧艾傳》,頁775—776;《晉書》卷一《宣帝紀》,卷二六《食貨志》,頁14,15,785—786。 (27)詳見黃惠賢《試論曹魏西晉時期軍屯的兩種類型》,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與資料》,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28)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八《河南道·陳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14;《太平寰宇記》卷一○《河南道·陳州》,頁190,192。 (29)《晉書》卷二六《食貨志》,頁789。 (30)《太平寰宇記》卷一一《河南道·潁州》,頁210。 (31)《晉書》卷二六《食貨志》,頁785。 (32)《太平寰宇記》卷一一《河南道·蔡州》,頁203。 (33)《晉書》卷一《宣帝紀》,卷二六《食貨志》,頁14,15,785,786。 (34)祝穆《方輿勝覽》卷四八《淮西路·安豐軍》,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859;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二一《南直·壽州》,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024。 (35)《太平寰宇記》卷一六《河南道·泗州》,卷一二四《淮南道·楚州》,頁315,2463。 (36)《通典》卷一八一《州郡十一·淮陰郡》,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8年,頁4803。 (37)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四四《淮南東路·盱眙軍》,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92年,頁1791。 (38)《三國志》卷二八《魏書·鄧艾傳》,頁796—797。《三國志集解·鄧艾傳》盧弼評艾云:“農田水利,軍資兵謀,無一不操勝算。孤寒之子,有此壯猷,不減淮陰,真異才也。”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頁665。 (39)《晉書》卷二六《食貨志》,頁785—786。 (40)《三國志》卷二八《魏書·諸葛誕傳》,頁770;參見黃惠賢《試論曹魏西晉時期軍屯的兩種類型》。 (41)《晉書》卷四七《傅玄傳》,頁1321。 (42)《太平御覽》卷八二一《資產部·田》,頁3658上。 (43)《宋書》卷六四《何承天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707;《三國志》卷五一《宗室傳·孫韶》,頁1216;《宋書》卷三五《州郡志一》,頁1033。 (44)《三國志》卷一四《魏書·蔣濟傳》,頁451。 (45)同上書卷四七《吴書·吴主傳》,頁1144。 (46)《三國志》卷一四《魏書·蔣濟傳》,頁453;《晉書》卷二六《食貨志》,頁787。 (47)《晉書》卷四七《傅玄傳》,頁1321。參見黃惠賢《試論曹魏西晉時期軍屯的兩種類型》。 (48)《晉書》卷二六《食貨志》載杜預上疏,頁789,788。 (49)《後漢書》卷二九《鮑永傳附子昱》,頁1022。 (50)《晉書》卷四六《劉頌傳》,頁1294。 (51)我們把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政權沿秦嶺、淮水一線爭奪、對峙的地帶稱爲中間地帶,雙方勢力在這一地帶內互有進退從而其軍事控制線作相應的南北推移。詳見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第1章第1節對“中間地帶”的界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4。 (52)《晉書》卷二六《食貨志》,頁787,788,789,790。 (53)《資治通鑑》卷八○晉武帝咸寧四年七月條,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2550;《晉書》卷四七《傅玄傳》,頁1321,1322;《宋書》卷三五《州郡志一》,頁1033。參上引黃惠賢《試論曹魏西晉時期軍屯的兩種類型》。 (54)《梁書》卷二八《裴邃傳附裴之橫》,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417。 (55)《晉書》卷七七《殷浩傳》,卷二六《食貨志》,頁2045,792。關於疁田,詳見下文論述。 (56)“三吴”具體所指,歷有異說。兩種代表性的說法,其一爲《水經注疏》卷四○《漸江水》,以吴郡、吴興郡、會稽郡爲三吴(頁3323),其二《通典》卷一八二《吴郡》,以吴郡、吴興郡、丹陽郡爲三吴(頁4827)。《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江南道·蘇州》(頁600)同《通典》。本文所謂江東地區,即包括上述兩說所指地區,即今江蘇南部(長江以南)、浙江北部。 (57)李步嘉《越絕書校釋》卷二《外傳記吴地傳》,卷八《外傳記地傳》,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30—32,199—202。 (58)陳橋驛《紹興水利史概論》,氏著《吴越文化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401。 (59)關於鑑湖的研究成果極多,其中陳橋驛《古代鑑湖興廢與山會平原農田水利》,是最全面、最權威、最早的成果,參氏著《吴越文化論叢》之《鑑湖研究概況綜述》。本文關於鑑湖的論述,主要參考該書而成。 (60)《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典·會稽郡》,頁4832—4833;又見《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六《江南道·越州》,頁619,《太平寰宇記》卷九六《江南東道·越州》,頁1926。《太平御覽》卷六六所引略同,稱引自《會稽記》,頁315上。“如水多則閉湖泄田中水入海”句,《通典》、《元和志》、《太平寰宇記》均作“閉湖”,《太平御覽》作“開湖”,似以“閉”爲是。 (61)《水經注疏》,頁3305—3306。 (62)陳橋驛謂《越絕書》所載“石塘”(《越絕書校釋》卷八《外傳記地傳》,頁202),“是我國有歷史記載的第一條海塘”,見上揭陳著《古代鑑湖興廢與山會平原農田水利》、《紹興水利史概論》。 (63)詳見上揭陳橋驛《古代鑑湖興廢與山會平原農田水利》。 (64)《太平御覽》卷六六,頁315上。《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典·會稽郡》(頁4832)、《太平寰宇記》卷九六《江南東道·越州》(頁1926)所引略同。 (65)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7年,頁73—99,108—122,145,348—359;唐長孺《東漢末年的大姓名士》,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5—33。 (66)《續漢書·郡國志四》,頁3488。 (67)《嘉泰會稽志》卷一三《鏡湖》,《宋元方志叢刊》(7),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90年,頁6942下。 (68)《漢書》卷八四《翟方進傳》,頁3440;《後漢書》卷八二上《方術傳·許楊》,頁2710。 (69)《嘉泰會稽志》卷一三《鏡湖》,卷二《太守》,《宋元方志叢刊》(7),頁6941下,6942下,6740上。 (70)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359。 (71)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頁199—201。 (72)《水經注疏》卷四○《漸江水》,頁3297。 (73)《太平御覽》卷八三六,頁3735下。同書卷七四、卷一七○、卷四七二所引略同而稍簡。據《太平御覽》卷七四《地部·塘》所引《錢塘記》(頁346上)補正。“華信象家富”(“象”爲“豪”之訛,“象家”爲“家豪”之倒),據《水經注疏》段熙仲之校注當爲“華信家豪富”,見《水經注疏》卷四○《漸江水》,頁3379—3380校注[一八]。 (74)《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江南道·杭州》,頁603。 (75)《太平寰宇記》卷九三《江南東道·杭州》,頁1865。 (76)《晉書》卷七八《孔愉傳》,頁2053;《南齊書》卷四○《武十七王傳·竟陵王子良》,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頁694。 (77)據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中所列“兩浙地區的重要水利工程”表(方健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219—236),見於文獻的漢代所建爲數不多的湖塘中,相當數量爲私人所建,規模都不大,如餘姚西北的魚浦湖,上虞西北的任嶼湖,慈溪北的杜湖、北洋湖,溉田少則僅十餘頃。 (78)《三國志》,頁1451—1452;事又見同書卷四八《吴書·三嗣主傳·孫休》,頁1158。 (79)《說文解字·土部》,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3年,頁290上;《後漢書》卷八二上《方術傳·許楊》李賢注,頁2710。 (80)丹陽湖地望,見《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南直·應天府》,頁986,982。 (81)《三國志》卷六四《吴書·濮陽興傳》,頁1451;許嵩《建康實録》卷三《吴景皇帝》,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82。 (82)《宋書》卷三三《五行志四》,頁951。 (83)《三國志》卷六一《吴書·陸凱傳》,頁1403。 (84)《晉書》卷七六《張闓傳》,頁2018;《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頁592。 (85)《嘉泰吴興志》卷一九《塘》,《宋元方志叢刊》(5),頁4855下—4856上;舊《圖經》載殷康等“開塘溉田”,《嘉泰吴興志》作者南宋談鑰考辨認爲該地“瀕湖”,“形勢卑下”,應稱作“築塘圍田”,所言甚是。 (86)《晉書》卷七六《虞潭傳》,頁2014。按“以防海沙”原作“以防海抄”。《欽定四庫全書考證》卷二五《史部·晉書》謂:“‘修滬瀆壘,以防海沙’,刊本‘沙’訛‘抄’,據毛本改。”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498册,頁72下。故清奉詔所修《江南通志》及《御定佩文韻府》,皆作“以防海沙”。皮日休《開元寺佛鉢詩·序》即稱西晉末“漁者於滬瀆沙汭”獲佛鉢(《全唐詩》卷六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6年,頁1553中)。我以爲“海沙”即指水豐沙富的長江口挾沙而上的海潮。 (87)《至順鎮江志》卷七《山水·塘》,《宋元方志叢刊》(3),頁2720中。 (88)關於湖田,參中村圭爾《六朝時代三吴地區的開發和水利的若干考察》,初刊於1981年,後收入氏著《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 (89)《晉書》卷七六,頁2018。 (90)《宋書》卷五四《孔靈符傳》,頁1533。 (91)《梁書》卷八《昭明太子傳》,頁168—169。 (92)《宋書》卷九九,頁2435—2436。 (93)孫吴時有太常卿姚信,“有名江左”,隋唐間著名史家姚察、姚思廉父子即其後裔。詳見《陳書》卷二七《姚察傳》,頁348—354;《舊唐書》卷七三《姚思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2592—2593。 (94)《南齊書》卷四○《武十七王傳·竟陵王子良》,頁694。 (95)同上書卷二六《王敬則傳》,頁482。 (96)詳見唐長孺《魏晉戶調制及其演變》,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55年,頁80—81。 (97)《南齊書》卷二六《王敬則傳》,頁482—484。 (98)同上書卷七《東昏侯紀》,頁104。 (99)關於江南水利工程建設中地方勢力的影響和作用,中村圭爾《六朝時代三吴地區的開發和水利的若干考察》最早予以注意,並加以具體論證(如與之密切相關的“塘丁”)。本文深受中村氏研究的啓發,並力圖在其基礎上有所發展。 (100)關於漢唐社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寧可《漢代的社》、《述社邑》是最早、最爲簡明扼要的成果,見氏著《寧可史學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郝春文《中古時期社邑研究》則是最爲系統、全面並充分利用敦煌文書的最新成果。臺北,新文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101)《宋書》,頁2251—2252。 (102)《元和郡縣志》卷二五,頁595。 (103)《宋書》卷七七,頁2003。 (104)《宋書》卷五四《孔靈符傳》,頁1533。 (105)關於東晉南朝的山澤占領,詳見唐長孺《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占領》,氏著《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1—26。 (106)《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頁1776,1775,1760,1757,1759。 (107)《全晉文》卷一○三,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58年,頁2049上;關尾史郎《六朝時期江南的社會》,載《歷史學研究》1983年別册特集《東亞世界的再編和民衆意識》。 (108)《宋書》卷八○《孝武十四王傳·豫章王子尚》,頁2059。 (109)《越絕書校釋》卷二《外傳記吴地傳》,頁30—31。關於疁田,渡邊信一郎《火耕水耨的背景——漢、六朝的江南農業》對之有深入的考察,本文多有參考。渡邊氏文載《日野開三郎博士頌壽記念論集·中國社會、制度、文化史諸問題》,福岡,中國書店,1987年。 (110)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田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年,頁695下。 (111)《宋書》卷八二《周朗傳》,頁2093;何超《晉書音義》卷下,中華書局點校本《晉書》附載於書末,頁3277。 (112)陸雲《答車茂安書》,頁2049上。 (113)參《後漢書》卷三二《樊宏傳》“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陂渠灌注”下李賢注引《水經注》,頁1119—1120;又見《水經注疏》卷三一《淯水》,頁2614;並參《漢書》卷八四《翟方進傳》關於鴻隙大陂的紀載,頁3440。 (114)《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江南道·潤州》,頁592;《晉書》卷九二《文苑傳·伏滔》,頁2400;《南齊書》卷四四《徐孝嗣傳》,頁773。 (115)《宋書》卷五四《孔季恭等傳》,頁1540。 (116)《南齊書》卷四六《陸曉慧傳附顧憲之》所載憲之於齊永明中之議,頁809。 (117)《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吴郡》,頁877;《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江南道·蘇州》,頁601。 (118)《光緒常昭合志稿》卷九《水利志》,《中國地方誌集成》江蘇府縣誌輯2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11上。 (119)劉允文《蘇州新開常熟塘碑銘》,《全唐文》卷七一三,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3年,頁7324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紹興二十八年九月己巳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327册,頁542上。 (120)玆列出代表性著作數種。冀朝鼎著,朱詩鼇譯《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修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張澤咸《漢晉唐時期農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同氏《試論漢唐間的水稻生產》,《文史》第18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上揭陳勇《唐代長江下游經濟發展研究》;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等編《古代長江下游的經濟開發》,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上揭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等編《中國水利史稿》;汪家倫等《中國農田水利史》,北京,農業出版社,1990年;拙撰《唐代長江中游的經濟與社會》第2章。 (121)冀朝鼎著,朱詩鼇譯《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頁36。 (122)陳勇《唐代長江下游經濟發展研究》,頁60—63。 (123)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等編《中國水利史稿》中册,頁25。 (124)拙撰《唐代長江中游的經濟與社會》,頁75—77。 (125)汪家倫等《中國農田水利史》,頁236—237。 (126)《隋書》卷七三《循吏傳·趙軌》,頁1678。 (127)《晉書》卷九二《文苑傳·伏滔》,頁2400;《宋書》卷四八《毛修之傳》,卷五一《宗室傳·劉義欣》,頁1429,1465。 (128)唐代芍陂面積,記戴頗不一致,此取汪家倫等《中國農田水利史》(頁240—242)所考,即周長二百二十四里。按《後漢書》卷七六《循吏傳·王景》李賢注稱:“(芍)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頁2466)按陂直徑百里,周長至少當在二百里以上。李賢唐人,所説唐芍陂面積應該可信。 (129)以上詳見汪家倫等《中國農田水利史》,頁242—245;陳勇《唐代長江下游經濟發展研究》,頁46—50。 (130)李翰《蘇州嘉興屯田紀績頌并序》,《全唐文》卷四三○,頁4375下,4376下。 (131)上揭拙著《唐代長江中游的經濟與社會》第2章,頁9—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