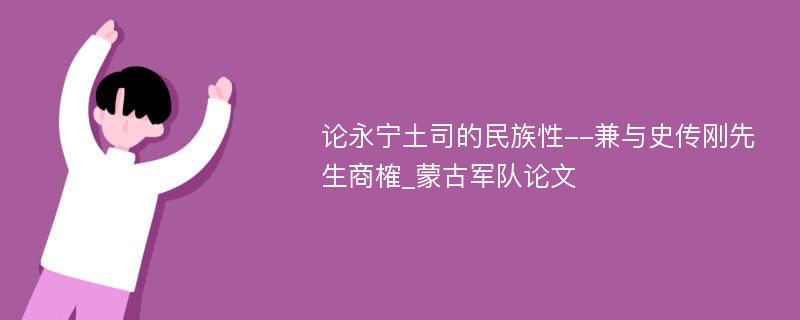
也论永宁土司的族属问题——兼与施传刚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永宁论文,土司论文,施传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2)12—0020—07
在川西南至川南的四川和云南两省交界地带,历史上有两个受中央王朝册封、在西南乃至中国诸土司中算得上比较有名、影响较大、府衙名为永宁土司府的土司,一个是泸沽湖西岸的永宁(今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境内)阿氏①土司(以下简称“阿土司”),另一个是赤水河畔的永宁(今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境内)奢氏土司。关于阿土司的族属问题,美籍华人、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文化人类学家施传刚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永宁摩梭》一书中,以“永宁土司的民族认同”为题专门作了论述,并作如下结论:“总之,永宁的土司家庭既不是摩梭人也不是蒙古人的后代,他们很有可能是蒙古军队里的一位西番军官的后代。当然,他们在摩梭地区生活了600多年,因为摩梭女性为他们生育后代,所以血统几乎完全变成摩梭人了。”[1](P.39)此结论笔者不敢苟同,以己之拙见,施先生就该结论在文中的分析而言,其理由是不充分的,至少不很充分,有些逻辑推理没有如是的必然结果。而且,在历史上阿土司所辖区域及其相邻地区,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民族识别工作时原本就遗留了比较大的问题,并且导致今天在民族关系方面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在此情形下,施先生此观点的提出就显得更不适宜。本文拟就施先生的观点提出笔者的不同看法,以就教于施先生和方家。
一、关于阿土司领地的地望及其他有关情况
(一)领地地望
原阿土司领地在今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北部,西与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隔金沙江相望,东北部与四川省盐源县和木里藏族自治县相邻,南部与本县的原蒗蕖土司领地相连。原土知府治所在面积约70多平方公里的永宁盆地,距闻名于世的泸沽湖近20公里,泸沽湖面积约三分之一是其领地;该地正好也处于横断山区民族走廊,即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藏彝走廊”中川滇交界的盐茶马古道商贸通道上。历史上,这里是南诏与吐蕃、吐蕃与唐朝以及唐朝与南诏交战时拉锯式争夺的地带之一。元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率军平大理国时,他亲自带领中路军途经永宁,并相对较长时地驻军于永宁日月和②。该地也可谓军事要道和兵家争地。
(二)历史沿革
永宁州昔名楼头赕,吐蕃东徼,地名答蓝[2](P.9);唐朝时“麽些蛮祖泥月乌逐出吐蕃,遂居此赕”[2](P.9),宋时属大理国,元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率军平大理国时,他亲自带领中路军经永宁,并驻军日月和,是年,泥月乌31世孙和字内附,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置答蓝官民管,“十六年置永宁州,属丽江路北胜府”[3](P.16);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州官卜都各吉率部归附明王朝,仍授为土知州。永乐三年(1405年),州管各吉八合入京朝贡,命袭父职,次年升为土知府,府附设四个长官司[4](P.431);清代,仍袭土知府,之后也未改土归流,且较为强大,屡屡参战上级指令的军事行动。1950年,时任土司尚小,辅佐其政,执永宁府总管之职的阿少云开明能干,永宁土司府衙决定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入永宁,府属地内和平解放,1956年民主改革即本府历时682年③的土司执政终结。
(三)社会经济制度
明代时,阿土司领地境内地广人稀,土司属民主要为摩梭和西番(普米支),经济以畜牧业为主,也有农业和渔业。清代,社会安定,生产有较大发展。抗战时期,在商业贸易方面有较快发展,为川滇之内地与藏区间的边贸集镇,马帮运输业较发达,远至拉萨,乃至南亚的印度等地,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交流。甚至当地喇嘛都热衷于做生意。较早使用铁制工具,能产水稻但土司恐汉人大量迁入而禁种,产稗子、小麦、玉米、燕麦、洋芋、大麻等。手工业以家庭式作坊为主,织麻布、酿酒、榨油等,解放前有制革制鞋的皮匠村(街),且略有规模[4](P.433)。
(四)政治制度
永宁土司执政严格实行“父死子袭,兄亡弟继”制,主要是长子继位任土司,土司的次弟必当喇嘛,并为喇嘛寺堪布,以掌教权。境内平坝地区直接由土司“斯毗”亲属阶层“阿毗”们统治,领地其他交由地方由伙头或总伙头④管治。衙门内有一套严格的组织:土司→总管→把事→师爷(汉文秘书)→管家等。有监狱、土司常备兵等。
当地盛行藏传佛教,土司次弟堪布为教权最高长官,属地内建有黄教等不同教派的寺庙,其中有些具有相当规模和较大影响,历史上从当地到拉萨入佛界的僧人有转世为哲蚌寺活佛的,有考上大格西的。另外还有原始宗教“达巴教”,专司人死后念送魂经⑤、祈福等原始宗教活动。
土司有一套关于社会习俗、自然资源及环境保护,以及土地和农牧渔业等方面管理的法律制度。在土司执政后期,当是近似“政教合一”的治理局面。
从上述概况可以看出,阿土司历史悠久,政治、经济和社会已发展到相当程度。连并其邻近的川滇交界较大区域内本民族的十多个大小土司一起,使该区域发展到了封建社会水平,社会发展超越于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唯有泸沽湖畔在较多家庭的婚姻方面却保留着母系大家庭制和走婚制的习俗,此乃一谜。这一滞后于当地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却又比较协调地客观存在的家庭婚姻形态究竟是古俗的延续还是后来特定原因下新出现的?对此,当地传统宗教“达巴经”、当地民众和外界学者各有说法,值得深入研究。
二、关于阿土司族属的不同认识
关于阿土司的族属,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一是过去阿氏家人都说自己是蒙古族,或说蒙古人的后代,其他有些人包括一些学者、周边的藏族⑥等民族也认为阿土司是蒙古人的后代;二是现在更多的人(也包括很多学者)可能是依据新中国成立后对原阿土司领地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政府最后将该地区自称“纳人”的族群确定为纳西族,因而自然认为阿土司是纳西族(或说摩梭)。对原永宁阿土司和原蒗蕖州⑦阿土司(应是与永宁阿土司同宗)领地、现宁蒗县籍这部分族群民族成分的确认,是由基层呈报并于1990年经云南省人大审议通过,确定称他们为摩梭人(这个改称的原因及过程,因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在此不作论述,此族称未通过中国政府的最后认可)。现在很多人自然就认为阿土司是摩梭人了;三是上文所述施传刚先生的观点——他认为阿土司可能是蒙古军队里一位西番军官的后代。
在此,笔者主要针对“西番说”的不同看法与施传刚先生作初步商榷。
(一)首先应当理清历史上特定时期该区域内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
分析研究阿土司的族属,首先,不能不分析历史上在阿土司领地和泸沽湖周边较大区域内蒙古人、摩梭人和西番(普米支)人这三个民族之间各自的双边关系,简略地说,他们的关系应该如后所述。
1.蒙古人与摩梭人(包括纳西人)的关系
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军经四川木里、盐源县和云南宁蒗县永宁一带,在金沙江的永宁段内乘革囊渡江,取道丽江南征大理,分封古摩梭部落大酋长和字、麦良等为土官,给沉寂了五百多年的古摩梭——纳西族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讲,忽必烈远征大理经过纳西族地区客观上为木氏家族及整个纳西族提供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5](P.231)1276年(有些资料记为1275年),元在丽江设军民总管府,统领一府七州一县。后罢府置宣抚司,总官与宣抚司均由麦良的子孙承袭,使古摩梭有了一个从容不迫、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古摩梭地区自此开始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古摩梭各部落也在这一时期逐渐走向统一,势力更迅速地发展,从此开始了一场宏大的民族文化体系的构建。丽江木氏土司的势力在明朝晚期曾臻鼎盛,滇、川、康、藏四省区交界处的较广大区域均被其攻占。纳西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在这一时期均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这同木氏土司先祖从元王朝时开始得到中央王朝的扶持,自此便积极依附中央王朝,大张旗鼓地吸纳各民族的先进文化,以先进的生产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等举措是分不开的,从而使得古摩梭从历史上处于被动地位成为主动进取的角色,在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不同凡响的影响⑧。
总的来说,蒙古人的到来促成了古摩梭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壮大,古摩梭民族取得了如何在保持自己特点的情况下认同并依靠中央王朝保护和发展自己的经验,从此,其深明并始终践行“认同中央王朝,维护国家统一”的正确道路。当然,当时也有因蒙古人而使古摩梭人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或直接受损的情形,如,明朝军队彻底打击反明的蒙古人、建昌(现西昌及周边广大区域)指挥使月鲁帖木尔部时,参与、协助、掩护或隐藏反明蒙古人的一些摩梭部受损;又如,后来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遏制并击退了木氏土司的扩张,使古摩梭的发展受到影响,等等。但是,这些只是一些特殊情形。忽必烈途经和驻军于永宁日月和、元王朝治理包括当时属于云南管辖的建昌,以及蒙古人扶持兴建木里等地佛教寺庙等举措,都使包括永宁在内的古摩梭人愿意拥戴和保护蒙古人。
2.蒙古人与西番(普米支)人的关系
就西番(普米支)的来源,无论口传还是文献记载均说法不一,相当流行的一种传说是源自蒙古族。传说宁蒗县托甸乡西番(普米支)的郭姓始祖原居蒙古马察多儿,后迁居咱布草原,然后又迁居故察,最后迁居宁蒗县的布杜鲁古;宁蒗县原三区裤脚乡西番(普米支)“韩规”(巫师)宋官补还能说出祖先离开蒙古后所传31代的世袭[6](P.67)。不仅有以上口头传说,原丽江县三仙姑西番土把总和目始祖的墓碑上刻有“随元世祖革囊渡江,留守关塞。而世守其地。”[7](P.14)清代余庆远《维西见闻录》载“又名西番,亦无姓氏。元世祖取滇,渡自其宗,随从中流亡至此者,不知其为蒙古何部落也。”[7](P.14)“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蒙古兵与当地西番妇女婚配而融合于西番。”[7](P.14)总之,从以上材料看,忽必烈取滇时,一部分西番(普米支)参与到了蒙古人征战大理国的战斗,并且加入到蒙古大军中是有很大可能的。按西番(普米支)自己的说法和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西番(普米支)人参与到蒙古人征战大理国并使其渡过金沙江进入到金沙江以西的云南。但普米族源于蒙古族之说倒不应当如是,留居该特定区域中的这两民族大都是经青海、甘肃等地来到此当是必然。要指出的是,若古摩梭《东巴经》中的“白沙之战”是指纳西和普米之间的战争,则蒙古人把西番(普米)人带入金沙江以西云南之说就不尽然了。另外,后来蒙古人扶持兴建木里、永宁等地佛教寺庙等,也使西番(普米支)人愿意拥戴蒙古人。更主要的是,在盐源、木里和宁蒗等县的广大西番(普米支)人中,还广为流传着西番(普米支)人请蒙古人来管理他们的传说:西番(普米支)人中有这样的传说:原来,他们的社会里没有当头目的,后来人多了,分居多处,互相不服,械斗打冤家,很不安宁。此时,适逢土司家的祖先由(盐源县的)盐井而来,普米人见他能办事,又会与汉官打交道,就请他为包括有西番(普米支)人的地区主持办事,担任各民族和部落联盟的首领。后来,有个叫沙边的家支,人口发展较快,想争当首领,便向土司进攻。可是,沙边家不得民心,因此西番(普米支)群众不服沙边管,反而支持土司。此后,土司的势力强大起来,得到了更大的政权。土司从沙边的不得拥护中得到了教训,很注意与西番(普米支)的团结,经常强调双方的联合关系,土司在谈论有关两族话题时总将西番(普米支)提在前面,以示尊敬和友好。
总之,在这个特定区域内,蒙古人与西番(普米支)的关系是友好的,有时在礼仪性的场合甚至彼此互称“兄弟”。
3.摩梭人(包括纳西人)和西番(普米支)人的关系
西番(普米支)人所有的对外民族关系中,其与摩梭人(包括纳西人)的关系最为亲密。历史上,两族先民之相当部分当是共同起源于古氐羌族群,西番(普米支)的古老传说中称自己与藏和纳(包括纳西在内的古摩梭)是同胞三兄弟。西番中普米支的“普米”意即“白人”(主要指崇尚白而非仅指颜色),称摩梭人(包括纳西人)为“纳米”,意即“黑人”(同样主要指尚黑,而非指颜色),两族当至少在1000多年以来就交错居住,往来密切。历史上,在永宁阿土司和泸沽湖畔的左所喇土司,乃至周边其他诸土司领地内,这两个民族很早以前就生活在一起,他们有的还互结姻娅,有了娘舅般的亲密关系。最主要的是他们相互间结为了紧密的“巴-纳日”联盟,哪怕古摩梭《东巴经》中的“白沙之战”是指“纳西和普米之间的战争”一说成立,也仍然存在“巴-纳日”联盟关系,这是主流。当然,两族关系也并非持续的一帆风顺和亲密无间,丽江本土的普米族学者胡文明认为“白沙之战即是纳西和普米之间的战争,此战的爆发使普、纳和亲的纽带断裂。”⑨另,从明朝中叶景泰年间始,丽江木氏土司北进统治木里直到其最后退出期间⑩,古摩梭中的纳西与木里西番之间也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相互对立,后随着对立关系的结束,两族关系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从该区域蒙古人、摩梭人和西番(普米支)人三个民族之间各自存在的双边关系,可见三者间的关系总体是较为友好的。既然如此,那么,在永宁土司的族属认识中存在超乎常理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不能完全按常理来认识了。
(二)关于《土官底簿》记永宁知府卜都各吉为西番人问题
从“永宁土司阿氏世系表”[4](P.436)看,和字于元宪宗三年(1253年)降于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年)后,下传的记录缺载,至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才始有卜都各吉率部归附的记载。相隔105年,历经改朝换代而任的卜都各吉一定是泥月乌及其31代孙和字的后代吗?对此未见有载,无从证实。也就是说,卜都各吉的族属也有可能非摩梭。若卜都各吉果真是“麽些蛮祖”泥月乌及其31代孙和字的后代,那他无疑是摩梭,若是摩梭土官,那他面对明朝廷就没有必要隐讳自身族属而写成西番。另一方面,在通常情况下,自唐代以来“西番”一词未与“么(麽)些”一词混淆过,但也有将川西及川西南的几个民族或族群统记为“西番”的情况。再者,正如施传刚先生所说,从《土官底簿》的成书过程看,《土官底簿》的记载是值得信赖的,若是摩梭一般来说就不可能记为西番。所以,综合分析可以同意施先生原文中前一段的结论,即“卜都各吉的族属并非摩梭”。问题是在当时(明初)的永宁及相邻的较大区域内,有势力或地位可能成为统治者的主要就是蒙古人和摩梭人,此时的卜都各吉若不是摩梭就只能是西番吗?完全没有是蒙古人的可能吗?其中没有隐讳自身族属而有意促成记为西番的可能吗?显然,他也有可能是为了躲过刚刚从元蒙统治者手中接管云南的明军的怀疑,从而导致实为蒙古人的卜都各吉在自己决然向明军诚心俯首称臣的同时,又对明军是否会信任自己心存疑虑,加之该区域内三个民族间具有如上所述的复杂关系,于率部归附明王朝的当年或之前,他本族单方或与其他两族中的一方,乃至三方共同计谋,来隐瞒自己的蒙古人身份,以此取得明军和明皇帝的信任及“欢喜”。更何况,早在明洪武初,像月鲁帖木尔那样的蒙古高级将领都在邻近永宁的“建昌(现西昌及周边广大区域)仍不属明王朝之时,依然在建昌与明王朝建立联系,于洪武七年秋,故元左丞阿里遣夹失伯里等(向明王朝)纳款”[8](P.408),在卜都各吉率部归附明王朝的次年,即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二月,曾得明皇帝以“月鲁帖木尔为建昌卫指挥使,赐以绮金带,月给三品俸赡其家。土官例无俸,此特恩也。”[8](P.409)
另外,从《明太宗实录》(卷120)可见,到了永乐九年都记有“西番土官月鲁铁(帖)木尔孙喇马拍及其侄孛里贡马”[9](P.315),说明对蒙古族高官月鲁铁(帖)木尔都有要么误记为西番,要么隐瞒为西番的情况。后来由于明朝的统治更加强大,明王朝加大了对建昌当时所属白、黑二盐井(即今在盐源县境内)的开采等,极大地削弱或损害了月鲁帖木尔等旧势力的政治、经济权益,月鲁帖木尔才被迫反叛明朝。所以,于1383年就被明朝征南将军任命为“土知州”的永宁阿土司卜都各吉若是蒙古人,也完全可能隐瞒族源,并像邻近自己的月鲁帖木尔和建昌故元左丞阿里那样,与明朝建立联系,然后归附,以真诚赢得明军的信任。
到了清朝,特别是罗卜藏丹津叛乱后,蒙古族几乎彻底失去在横断山区民族走廊区域的统治权力,一些时任土司可能更不敢公开蒙古族身份,或许又要隐族埋名,以免被清王朝清剿。
(三)从周汝诚先生那份很好的民族志报告何以见得是施先生观点的“最有力的证据”?
纳西族民族志学者周汝诚于1936年在永宁作田野调查后留下遗稿称,其中称:“西番(普米)曾有功于地方,为土司所爱。”[1](P.34)并描述了永宁老土司逝世、新土司承袭时,西番(普米支)人进土司衙门后的一段表演(11)——笔者认为那充其量只是一场反映友好部属前来悼唁老土司的一种方式和仪式的表演。周先生的遗稿最后说:“所以,西番族对于永宁土司,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受到特殊的尊荣。”[1](P.35)施先生据此分析得出结论:“普米作出的贡献的确非常特殊,因为那就是土司家庭本身。”[1](P.34)施先生是否寓意土司本身就是有功于地方的西番(普米)人呢?但从周先生遗稿中的字里行间是无法推出此结论的。这里,出现普米人的那段表演,我认为与以下三个原因有关。其一是如上文所述:西番(普米支)人民间普遍认为土司是他们请或“买”蒙古人管他们的说法。对此,其他在该区域做民族志田野调查的专家也有所闻。比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龙某某研究员于2009年在昆明召开的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第十六次大会一个专题研讨会上听了笔者的交流发言后,向笔者说到他在调查过程中也获悉这个民间说法。既然西番(普米支)人认为土司是他们从外族请来或“买”来管他们或“服务”于他们的,那么,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有权利也切身关注老土司为何而死,因为他们意识到老土司的死和新土司的袭任都事关西番(普米支)的切身利益,因而有那场“表演”也就顺理成章。
其二就是涉及当地的真实人物——永宁土司府第11代第14任土司牙玛阿(汉名阿镇麒)的民间传说,该传说反映了阿土司为什么要给西番(普米支)人以优待或特权。现将该传说附于后:
丽江木土司入侵永宁时,把知府牙玛阿及其他族人困于永宁扎美寺后的山上,眼看即将被虏,这时,牙玛阿的外甥即木土司的儿子尊其母命,用箭把一封信射给舅舅,叫他化装后从后山小路逃走。知府牙玛阿逃出包围,途中遇到有胆识的西番(普米支)青年尼玛甲泽,知府向他讲述了不幸遭遇,尼玛甲泽建议知府到京城告御状,并愿陪同前往,两人遂前往京城。
有一天,他俩走到(现盐源县)盐井时,一群摩梭妇女正在河里洗麻线,当她们知道事情的原委后,非常同情他们,其中一个名叫优珠姆的妇女便把自己佩戴的手镯、耳环、戒指等物送予他俩作路费。知府表示如果他活着回来,决不忘记报此恩情。经过3年的艰苦跋涉,牙玛阿和尼玛甲泽到了京城,在朝廷大臣的帮助下,他圆满地回答了皇帝提出的三个问题:天下什么最大?道理最大。什么最可怕?最怕头场春雨下得不合时令。你吃什么?穿什么?吃泥巴,穿麻布。回答了问题后,皇帝叫知府牙玛阿把佩剑拿上来,知府恭敬地用双手把带鞘的剑柄献给皇帝,他的行为使皇帝很喜欢。对被传到京都对质的木土司,皇帝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可木土司的回答使众人捧腹大笑:天下什么最大?官最大。什么最可怕?胖不过肥猪壮牛(误听怕为胖,丽江一带通常将“胖”发成“怕”的音)。你穿什么?吃什么?穿百姓,吃百姓。皇帝向木土司要剑时,他自己拿着剑柄,把剑鞘的剑尖递过去,这举动激怒了皇帝……牙玛阿打赢了官司即向皇帝辞谢,皇帝问他想当什么官,他回答说:“别的当不起,当个泥巴官”。皇帝便封他为土知府,令其世代统治永宁。
牙玛阿回到永宁后,让人们休养生息,使永宁又得以和平宁静。随后牙玛阿托布商到盐井找到优珠姆并娶她为妻,带她巡视永宁各地。百姓们纷纷献以酥油、猪膘肉、鸡、酒、麝香、熊掌、麻布、筛子、簸箕、黄板等土特产及金银。同时,牙玛阿及土司府认为陪同告状的普米人尼玛甲泽有功,给他封了官职,并规定所有普米人在永宁必须受到特殊的优待和地位。因此,后人说的“普米人寡妇也收三斗租”便由此而来。
其三,永宁土司从卜都各吉称起的第20代土司阿应瑞的生母是木里的西番(普米支)妇女[10](P.286)(12),由此,也可见西番有功于阿土司家,从此,土司去世时西番(普米支)人来作那场“表演”也当自然。
由此可见,上述三个原因有极大的可能就是普米人做那段“表演”和享有“撒羊毛疙瘩”[1](P.37)权利的原因,而不是因为阿土司本身是西番人。
(四)对阿氏家族认同自己是“蒙古后裔”之说应有的态度
作为学者,对于阿氏家族认同自己是“蒙古后裔”之说的评说应持全面客观分析的态度,而不能在未作深入分析研究即简单地说是“附会”或“攀权贵”。其实,到了明清时期,于横断山区民族走廊乃至西南地区的蒙古族来说,早已无“权贵”可攀。所以,对于已发现并能支持“蒙古后裔”之说的原因或素材应作全面深入研究后方作结论。
青年学者曾现江博士曾以“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为题写作博士论文并公开出版。作者通过对蒙古族在藏彝走廊地区活动的研究,对论文命题作了一些深入研究,并对此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其中,对明初遗留在藏彝走廊地区的残元势力、川滇边地各民族的蒙古族祖源传说等问题作了研究,从这些研究可以分析阿土司为什么说自己是蒙古后裔。
美籍奥地利植物学家、人类学家约瑟夫·爱弗·洛克(1884-1962年)在其所著《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一书中写道,他于20世纪20年代初到永宁考察时,受到了阿土司时任总管、精明能干的阿云山的会见和热情接待,后来他们俩成为挚友;书中也有多张阿土司与阿云山总管等的个人照和家庭合影,以及阿云山和洛克的合影等照片;书中还说到阿云山向洛克表明自己就是蒙古人:“已故永宁总管阿云山是土司的一个近亲,他和永宁所有阿姓的人一样,宣称自己是忽必烈于公元1253年征服云南时留下的蒙古官员的后裔。阿氏人多次告诉我说他们是蒙古人,而他们的体格、相貌都能证实他们的话。”[10](P.254)洛克在其《中国黄教喇嘛木里王国》中又记道:“再翻过最后一座横亘于金沙江和永宁之间的大山脉,我们就到了蒙古族的首府了……在一座……木屋里,几个蒙古族人隐藏在哪里,把守着通道……这里是三个土司(永宁、左所和前所土司)活动的中心,他们的祖先是蒙古人。”[8](P.36~37)
笔者曾于1990年夏到云南省宁蒗县参加了一个盐源、宁蒗两县蒙古族和摩梭人的座谈会。会上,笔者亲耳听到阿云山的儿子、1926年6月生于宁蒗县永宁、曾是拉萨哲蚌寺甘丹赤珠第五世活佛、时任政协宁蒗县副主席、后来任政协丽江市副主席、市佛协名誉会长的洛桑益世活佛作了大意如是的发言:他从小听家里的大人说自己是蒙古人,但这个历史他个人因从小只学佛念佛而不太懂,也没研究过,现在大家说是摩梭人,可能也好吧……活佛的这段话发人深省。
其他与永宁阿土司同族的前所阿土司、阿撒土目等阿氏后人也称自己为蒙古后裔。
总之,对于阿氏家族的人及其他人关于阿土司是“蒙古后裔”之说,应当深入研究,毕竟可能事出有因。
另外,施先生在其著作中“永宁土司的民族认同”部分还写到“清代(1644-1911年)以前的文字并无四川盐源县土司的记载……从这些官职的头衔可以看出,中央政府直到清代才正式承认四川盐源县的土司”之类。仅从下述就可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例如,郭大烈、和志武先生著《纳西族史》盐源“五所四司三码头”中记载:《元史·地理志》中有“柏兴府(元时今盐源县的名称)……元十四年(1277年)立盐井官民千户。”[2](P.440)又载,《明史·四川土司传》中有四川盐源县泸沽湖畔的原左所千户在明朝初年至嘉靖年间极为活跃,曾与云南土司发生长时间冲突。明代第一任土司喇兀(喇他、喇玛塔)立过战功,第二任土司喇玛非曾进京见过皇帝。[2](P.442)“打冲河守御中左千户所,其土千户剌(喇)兀,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征贾哈喇……其子剌(喇)玛非,复贡马赴京,受本所副千户,永乐十一年(1413)年升正,以别于四所。”[2](P.441)该书还记载了“左所土司喇(剌)氏世系表”[2](P.447-448)。从元初柏兴府的情况分析来看,至元十四年(1277年)设立的盐井官民千户有可能就是后来的左所喇氏千户。明朝时蒙古人建昌指挥使月鲁帖木尔在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反叛明朝后,左所土司内部出现了参与月鲁叛乱和反对参与叛乱的激烈分歧,后发展到在明军征剿月鲁中,反对叛乱的喇兀(喇他、喇玛塔)被迫参加到了反叛征战中并立战功,连并后来的发展,使左所土千户成为盐源诸土司中最早受封为副千户,率先升任正千户,历史比较久远,实力比较强大,所管属民较多,社会制度比较典型的一个土司。[2](P.441)
因此,笔者认为施传刚先生在其著作中关于盐源土司设置情况的推断也是不恰当、不正确的。
综上所述,施传刚先生在《永宁摩梭》一书中对永宁土司的族属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笔者从各种史料、与西番(普米支)人的接触和了解、对当地民族关系的实地考察,以及民间传说等诸多方面综合分析认为,永宁土司不可能是西番(普米)人。至于“蒙古后裔说”和“摩梭说”孰然?当是可以深入研究而明晰之的。
注释:
①过去,该阿姓的读音不发a[33],而是读作ηa[21],若用汉字注音,找不到与该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②笔者注:在永宁盆地西,现有遗址。
③从至元十一年即公元1274年算起。
④大伙头是针对大村而选任。
⑤指送死者灵魂于远祖故乡的《指路经》。
⑥永宁北面、木里县紧邻甘孜州稻城亚丁的藏族称永宁、左所和前所等土司为“梭部绛波。”
⑦即永宁南面现在的宁蒗县城一带,宁蒗县名就是历史上的永宁和蒗蕖两土司地的合称。
⑧参看“百度”中关于“纳西族”的词条。
⑨参见云南省民族学会主管的内部资料:云新出(2009)准印字第093号《普米研究》2008年12期胡文明《浅析普米族与纳西族木氏土司之关系》一文。
⑩具体退出时间多认为在藏汉文献中均明查无记,唯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在其《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中认为:“根据《木里政教史》的上述记载,至少可以确定木氏土司退出木里的时间在1647年至1661年之间,极可能在17世纪50年代中期。
(11)施先生也把直到1986年周先生去世后才得以出版的遗稿中,涉及此表演的几段话转摘于其《永宁摩梭》一书,(见该书P34-35)。限于篇幅,本文不再摘录。
(12)洛克书中记录阿应瑞的父亲阿恒芳所证的一个材料则反映阿应瑞是自己的原配程氏所生。若阿恒芳的包括原配程氏在内几个妻子都未生儿子,后来与西番妇女生的阿应瑞改称为原配所生,以便继位,这样权宜之计的改称也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