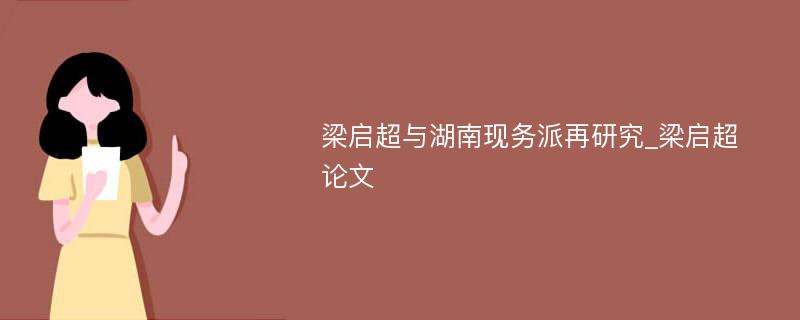
梁启超与湖南时务学堂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务论文,湖南论文,学堂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5-0139-06
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维新思潮在京沪等中心城市迅速发展,并逐步影响内地,湖南及一些内陆省份在开明官僚主持下,不仅迅速回应京沪等中心城市的维新思潮,而且在自己主管的辖地内进行了维新变法的局部试验。
湖南是中国内陆地区最有特色的一个省份,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湖南向以保守而著称,但湖南深深介入了这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甲午战争中,战争的结果深刻地刺激了湖南人,所以在后来的变法维新运动中,湖南总是走在时代前列。
一、湖南时务学堂的创办
甲午战争中吴大澂率领的湘军的失败是湖南人的奇耻大辱,但湖南人并没有在这次失败之后一蹶不振,而是很快形成一种寻求变革、追求进步的新风气,并与京沪等中心城市的维新思潮遥相呼应。1895年10月,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由于他的开明引导与鼓励,湖南维新运动较其他内陆省份更早发生。
在开发经济的同时,陈宝箴更注意文化观念的转变和教育制度的更新。他和1894年出任湖南学政的江标一起,提倡经世之学,以改变士风、开创新的社会文化风气为己任,着力整顿旧式书院,购置不少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方面的书籍和实验仪器,设立舆地、算学、方言等学会,试图将旧式书院改造成培养新式人才的基地。
与湖南官方倡导变革几乎同步而行的,是湖南民间势力的自发维新运动。1895年7月,在外漫游多年、具有维新思想的湖南青年谭嗣同致函乃师欧阳中鹄,提出在湖南进行变法维新的系统主张,以为中国的变法必须先从改变中国知识人始,只有知识人的知识构成发生了大的变化,才能带动中国社会大变化;而要改变中国知识人的知识构成,又必须先从改变传统科举制度始,“从士始,则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1]基于这种认识,谭嗣同建议欧阳中鹄及江标先从一县进行改革试验,造就有用的人才。
根据谭嗣同的建议,欧阳中鹄在湖南积极筹备,准备将浏阳县原有书院改为习格致诸学,并以算学为入手,计划将南台书院直接改为算学馆,但遭到了反对。谭嗣同得知这些情况后,迅即邀请具有维新思想,并在湖南学界略有影响的唐才常、刘善涵等人联名禀请湖南学政江标,希望转饬浏阳知县同意将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这一建议合乎江标的主张,江标遂于1895年9月批准了这一方案,决定在当年的乡试中“搜取试卷中之言时务者拔为前列,以为之招”。[2]但浏阳知县仍借故拖延拒不执行,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的计划似乎并没有成为现实。
有了江标的支持,欧阳中鹄、唐才常等开始自行筹款,于浏阳文奎阁创办算学社,聘请新化晏孝儒为教习,开始讲授算学。最初入学者仅16人。人数虽少,但这是湖南境内开始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最初起点。“省会人士始自惭奋,向学风气由是大开。”1896年,浏阳算学社的规模继续扩大,欧阳中鹄等人遂将算学社改名为算学馆,制定章程,规定公推七人主持馆务,馆中设山长一人,监院一人,负责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规定入学生员除学习规定的算学外,“余时温习经史,阅看外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学、格致诸书及各新闻纸。其有心得及疑义,与夫应抄录以备遗忘者,即随时分类录入杂记。每日杂记,无论行楷,总需过百字。有分数可相比较者,列为图表。有变通可须发挥者,即作论说、杂著。”[3]
谭嗣同、欧阳中鹄等人创办算学馆、改革旧式书院的想法与做法既合乎当时的思想潮流,也合乎清政府的政策。从思想潮流方面说,在甲午战争之后,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内的所有进步思想家在反省中国失败原因时,差不多都追因于中国旧式教育体制已远远不能满足时代需要。在清政府高层中,也有一些人比较早意识到中国旧有教育制度必须改变,西方新式教育体制应有计划地引进。如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向清政府建议令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在京师设立大学堂。1897年3月,安徽巡抚邓华熙奏请各省在省会另行设立格致等学堂。清政府同意了邓的建议,此后各省兴办新式学堂蔚然成风。
至于湖南时务学堂成立的具体背景和直接原因,还是湖南乡绅王先谦等人所从事的实业活动所促成的。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之后,对于湖南省的实业开发采取鼓励和支持态度。1896年,王先谦联络黄自元等人,集股创办官督商办性质的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宝善成公司成立之初,购买有各种机器,且有小锅炉马力一具,铇床、车床各一台,计划制造电气灯、东洋车等,1897年在长沙创设了湖南第一家发电厂,从此湖南省城开始有了电灯照明。
宝善成公司在经营实业的同时,也注意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投资。1896年冬,王先谦、张雨珊、蒋德钧、熊希龄等公司负责人为了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向陈宝箴申请三万两资助,陈在申请报告上批道:“公极则私存,义极则利存”。这两句带有多重涵义的批语使王先谦等人极不高兴,以为未办事而先受申饬,遂改为少用公款而多用民间资本。嗣后不久,参与其事的蒋德钧更觉得宝善成公司“迹近谋利”,不太合乎他们原先创办该公司的宗旨,于是提议在机器制造公司之下也即宝善成公司之下设立时务学堂,推广工艺。[4]这大概是创办湖南时务学堂的最早动议。
蒋德钧提议创办时务学堂归属于机器制造公司即宝善成公司,这个学堂的创建目的似乎也只是为了推广工艺,计划招收二三十名学生,常住局中学习制造,计划聘请一位通重学、汽机等相关学科的老师主其事,“俾日与诸生讲解制造之理,并随时入厂,观匠人制造。”[5]似乎带有为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培训人才的意味。
机器制造公司创办学堂的计划,由公司负责人王先谦等领衔上报湖南巡抚陈宝箴,这一计划与陈宝箴的思路不谋而合,陈宝箴于1896年底将这个计划批准立案,并将之命名为“时务学堂”。此时务学堂的性质似乎也由此而变,因为陈宝箴在批准创办时务学堂的同时,还同意每年从湖南省矿务赢利中划拨三千两作为学堂常年经费,并经清廷批准,援天津、湖北武备学堂先例,每年于正款项下划拨一万二千两,酌充时务学堂和湖南武备学堂常年经费。[6]这样一来,时务学堂虽由王先谦等人动议创办于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之下,但实际上成为湖南省政府下的一个机构,享有与官办武备学堂同等的待遇。
二、办学方针的确立与改变
熊希龄接手时务学堂的管理责任后,遂邀请谭嗣同、黄遵宪等人参与其事。黄遵宪为新任湖南按察使,他在刚到长沙得知时务学堂的创办时,即向陈宝箴、江标竭力推荐《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务报》翻译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
对于湖南方面的邀请,梁启超很有兴趣。他于1896年4月2日致信汪康年,称湖南居天下之中,士气最盛,极具改革思想的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或许在陈的主持下湖南能够有一番作为,“或者天犹未绝中国乎”?他计划如果汪康年不能将《时务报》顺利创刊,就只好转赴湖南,投奔陈宝箴。他恳请汪康年利用与湖南方面的密切关系,“望一为先容”。[7]
汪康年或许按照梁启超的请求为之介绍了湖南方面的关系,于是梁启超对湖南的政情动态更为关注。7月11日,梁启超再次致信汪康年,对于湖南在中国未来政治中可能发生的作用有一很好的估计。他认为,在“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气最为可用,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于他省,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对于汪康年的朋友江标督学湘省,梁启超亦寄予厚望,称“此君尚能通达中外”,建议汪氏利用这层关系致信江标,鼓励他着手改革湖南省内的考试制度,“令其于按试时,非曾考经古者,不补弟子员,不取优等。而于经古一场,专取新学,其题目皆按时事。以此为重心,则禄利之路,三年内湖南可以丕变矣。此事关系大局非浅,望酌行之。”[8]对陈宝箴主导的湖南新政寄予无限希望。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再加上自1897年初以来就与汪康年在《时务报》内部的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关系略为紧张,所以当梁启超收到湖南方面的邀请后,便义无反顾地离开上海,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
在梁启超抵达长沙时,时务学堂在陈宝箴、熊希龄、黄遵宪等人的筹办下已经成立,常年经费也已落实,办学所需图书仪器或已购置,或正在置办,筹办工作已大体完成。在这种情况下,遂由陈宝箴出面发布《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介绍时务学堂设立的原委,鼓励青年学子勇于报考。陈宝箴的号召在湖南省境内各府厅州县获得了广泛反响,至9月24日正式考试时,诸生投考者至四千余人。[9]经过较为严格的考试,最后录取了40名,陈宝箴原计划第一批录取60名并没有实现,似乎坚持了宁缺毋滥的原则。
当湖南时务学堂的招生正在紧张进行时,梁启超还没有离开上海,但他与熊希龄等人之间书信往还,就学堂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人员配置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梁启超根据自己追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经验及所知广雅书院、两湖书院的教训,坚持分教习必须由学堂总教习自主聘任,否则总教习与分教习发生分歧,或观念差别太大,势必影响学堂的教学质量。熊希龄等人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同意梁启超以总教习的身份聘任其同门好友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三人为中文分教习。在教学方法上,梁启超认为新办的时务学堂应该兼容旧式书院和新式学堂二者的优点,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新式学堂的教学方法进行讲授;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旧式书院的教学办法进行传授。他觉得既然准备在时务学堂花费一二年的日力心力,那么就应该尽量多培养出一些有用之才,所以在招生规模上主张尽量多地扩大招生规模,以为教授四五十人与教授一二百人所花费的日力心力相去不远,所以在招生数量上不必太保守,而应该多多益善。[10]梁启超的这些建议在后来的实践中逐步成为时务学堂的主导思想。
1897年11月14日,梁启超偕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及西文总教习李维格从上海抵达长沙,稍事准备,即于11月29日正式开学。
梁启超尚未到长沙时,就在上海参照康有为在长兴里和万木草堂的办学经验为时务学堂拟定了章程。到了长沙后,他又对这些章程进行了修改,正式公布《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共十章[11],以此作为时务学堂的办学原则。这十章内容分别是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从形式上看,这个章程更多继承了传统儒家尤其是宋明儒学的讲学遗风,强调个人修养的“内圣”功夫,然后再以“内圣”开出“外王”,培养出合乎时代需要的人才。但实际上,这个章程在继承儒家思想精华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了向西方学习,即便是在“经世”的层面,也强调学生在深通儒家六经制作之精意的同时,证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求治天下之理。显然,在梁启超的心目中,实际上是期望时务学堂能够成为即将到来的变法维新运动的人才基地。
对于时务学堂的功课,梁启超也有比较独特的设计。他将这些功课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所有学生入学后半年必须修的博通学,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通识教育,其中包括儒家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历史地理以及比较浅显的自然科学基础等。这门课所用的教材主要有《孟子》、《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荀子》、《管子》等儒家经典和先秦诸子。其教授方法,主要是指导学生反复研读这些经典,仔细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如《孟子》中的民权思想,然后指导学生用中外政治法律进行比较参证,使学生充分理解变法维新的历史必然性。经过大约六个月的所谓博通学的训练之后,学生将按照各自的志趣和特长选择不同的专门学,从而学有专长。专门学主要有公法学、掌故学、格致学及算学等。只是在学习专门学时,学生仍应就博通学中一些书目进行学习。
在要求学生所读书目中,由于种类太多,梁启超又将之分为“专精之书”和“涉猎之书”。专精之书由总教习或分教习负责全部讲授,循序渐进,仔细体会,认真研读,此类书约占每天学习时间的十分之六;涉猎之书,则由教习指导略加浏览,约占全部学习时间的十分之四。不论是专精之书还是涉猎之书,梁启超都要求学生随时写札记,每日将所读之书,按照书名、篇名等详细注明,或写出自己的阅读心得,或抄录书中的内容。这些札记每隔五天上交一次,由总教习和各位分教习批阅评定。
梁启超刚到长沙时,受到湖南各界的一致欢迎,到达当天,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湖南学政江标、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时务学堂代总教习皮锡瑞以及湖南官绅、社会名流邹代钧、熊希龄、唐才常等前往迎接,学堂全体师生更是齐集学堂门前燃放鞭炮予以欢迎。第二天,又在北门内左文襄公祠堂设宴为梁启超一行洗尘。此后几天,梁启超的住处每天都是宾客盈门。湖南文坛大佬、乡绅领袖王先谦在梁启超刚到时,也是发自内心感到高兴,对梁尊礼有加,曾专门张宴唱戏,以示欢迎。[12]换言之,在梁启超初到湖南时,包括后来所谓旧派人物在内的湖南各界真诚欢迎,“诸人倾服,自是实事”。[13]然而没过很久,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三、异端与正统的冲突
在《时务报》主持笔政时,梁启超就有意于宣传乃师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和新学伪经说,只是受制于张之洞一系的压力以及与《时务报》创建诸人的约定,梁启超在宣传乃师主张上,还显得比较谨慎和克制。然而到了时务学堂,他觉得这些约束已不复存在,故而敢于放言高论,无所顾忌。他在重印康有为的《长兴学记》时,有意鼓吹康有为创立新孔教的意义,提出“推孔教以仁万国”。[14]为了指导学生阅读《春秋公羊传》和《孟子》,梁启超还著有《读春秋界说》和《读孟子界说》两篇文章,前者借用乃师康有为的观点,强调《春秋》为孔子托古改制而制作以教万世的著作,《春秋》为明义之书,非记事之书。《春秋》立三世之义,其目的就是为了明了古往今来天地万物递进的道理。后者将孟子视为儒学正统,以为孟子所传的大同之义,都属于儒家思想最有价值也最有现实意义的内容。至于《孟子》中的民权思想,梁启超也作了极致发挥,以为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民权思想具有相似或相近的地方。这显然也是康有为大同学说的翻版。
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更激烈的言论并不在自己写作的文章中,而是体现在他所批阅的学生读书札记中。梁启超借鉴过去书院培养学生的经验,格外强调学生自学及写作札记,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思考。而梁启超在学生札记中的批语发表了许多在内地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思想异端。比如在谈到民权问题时,梁启超在批语中强调西方的民权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土壤和实现的基础,因为儒家经典中的大同学说,其实就是东方的民权观念,与西方的民权思想具有相同意义。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人的民权思想非常丰富,如果将六经中关于民权的文字汇集起来,肯定是洋洋大观,不输于西方。这显然与正统见解有很大差别。
有学生在札记中提及当时中国政治中还比较忌讳的议院制度和议会主张,梁启超也就此多有发挥,积极提倡。他认为,和民权思想一样,议院制度虽然创制于西方,但在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也多有类似或相近的意思,只是中国的君主专制时间太长,议院制度在中国就没有从思想转化为制度,转化为实践。这是非常可惜的,但这也表明中国社会有接受议会政治、议院制度的潜质与可能。
还有学生在札记中倡言中国礼仪制度的改革,建议废除不合乎时代的跪拜礼。梁启超对此深表赞同,甚至强调中国如欲变法维新,就应该从天子降尊始,如果不先废除跪拜礼仪,上下仍习虚文,就不仅为外国人所嘲笑,也无法建构合理的政治体制。这在跪拜仍是中国君臣之间交往的主要礼仪形式的时候,其异端色彩浓厚。
政治改革在当时的知识人中已经有人进行讨论,但政治改革的方向、范围,似乎并没有什么定论,改革后的大清王朝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谁也不清楚。于是有学生在札记中讨论这个问题时,借用中国古人的智慧,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改正朔、易服色在古代中国具有改朝换代的象征意义,这可是现实政治中的大忌,而梁启超在批语中并不回避,而是大笔一挥,直抒己见,不但将改正朔、易服色与即将到来的维新变法运动联系起来,声称“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由此引申,梁启超毫无顾忌地声讨清兵入关后残杀汉人的野蛮行径,称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15]这显然已不是帮助清政府“自改革”,而蕴含有推翻清廷、改朝换代的意味了。
梁启超的这些极端言论均在时务学堂内部发表,而由于时务学堂的学生全部住校,这些极端言论发挥作用的范围也只在学堂的内部,学堂内部的空气日日激变,而学堂外并无人知晓。所以,在时务学堂开学后最初几个月里,湖南各界对时务学堂很恭维,比较一致认同梁启超对时务学堂的改革与改造,相信时务学堂在梁启超的操持下总算走上了正轨,教员比较卖力,学生也知道用功,官府和学生家长都比较满意。
然而到了春节放假时,来自全省各地的学生返回家乡过年,就在这个短短年假,这些学生将他们在时务学堂学到的这些异端思想用最快的速度传播出去了,家长震动,官府震惊,“全湘大哗”[16],“引起很大的反动”[17]。
1898年3月3日,梁启超因故暂时离开长沙。随着梁启超的离开,攻击时务学堂的流言蜚语开始在长沙知识界散布。6月30日,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杨宣霖、黄兆枚、刘翊忠、彭祖尧等上书山长王先谦,以维护纲常名教、忠孝节义为名,肆意攻击黄遵宪、徐仁铸,主要目标对着时务学堂和梁启超。
宾凤阳等人在这封具名的检举信中指出,梁启超等人所用以蛊惑人心的,不外乎什么民权、平等这些似是而非的口号,而中国及湖南目前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平等之说,蔑弃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者!”他们还搜集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读书札记上所作的批语,专门挑选那些具有异端倾向的文字提供给王先谦,请求王先谦利用自己在湖南知识界的影响力,出面要求湖南行政当局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辞退梁启超等教习,另聘品学兼优者。[18]
因为南学会等方面的原因,王先谦已经对梁启超等人肆意传播康有为的异端邪说有所不满,所以当他收到宾风阳等人的检举信后,大为震惊。他认为,清政府鼓励开办新式学堂的目的是为了采纳西学,但并不是让中国人去信奉西教。西教的流行,在中国已有不可阻挡之势,但真正的西教也有其合理的地方。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今日所以惑人,自为一教,并非真的西教。其言平等,则西方国家也并没有完全做到平等;言民权,则西方国家或有君主,或有总统,也并不是将国家权力交给人民。王先谦说:“康梁谬托西教,以行其邪说,真中国之巨蠹,不意光天化日中,有此鬼蜮!今若谓趋重西学,则其势必至有康梁之学,似觉远于事情。且康梁之说,无异叛逆,此岂可党者乎?彼附和之者,今日学堂败露,尚敢自号为新党乎?”[19]在王先谦看来,梁启超在湖南放肆鼓吹康有为的异端邪说,就不仅仅是思想学术论争,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关系到大清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等大问题。
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先谦联络湘籍士绅叶德辉、张祖同、孔宪教、刘凤苞、蔡枚功、汪概、黄自元、郑祖焕、严家鬯等人,于6月10日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呈递了一封联名信,并附上宾凤阳等人写给王先谦的检举信,控告梁启超借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之机,“承其师康有为之学,倡为平等、民权之说”,“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使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始自会城,浸及旁郡。虽以谨厚如皮锡瑞者,亦被煽惑,形之论说,重遭诟病。而住堂年幼生徒,亲承提命,朝夕濡染,受害更不待言。是聚无数聪颖子弟,迫使斫其天性,效彼狂谈,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
王先谦等人的检举义正辞严,似乎应该能够获得陈宝箴的同情和支持。然而陈宝箴觉得此揭帖“丑诋污蔑,直是市井下流声口,乃犹自托于维持学教之名,以图报复私忿。”[21]王先谦闻讯后极为恐慌,立即致函陈宝箴进行辩解。双方往返信函多次,陈宝箴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22]
四、时务学堂的终结
王先谦等人并没有就此停止对梁启超等人的攻击,他以岳麓书院山长的身份联络城南、求忠两书院,以三书院学生的名义邀请全省士绅出面订立所谓《湘省学约》,进一步攻击时务学堂和梁启超等人,企图通过《学约》中所标明的正心术、核名实、尊圣教、辟异端、务实学、辨文体、端士习等内容以纠正康梁学说对湖南知识界的影响。
康梁学说在湖南确实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已经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这个势力面对反对者的挑战也进行了顽强抵抗。当王先谦等人《湘绅公呈》送达陈宝箴之后的第三天即1898年7月13日,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联合湘籍户部主事黄膺、翰林院庶吉士戴展诚、前广西知县吴獬、候选训导戴德诚等,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呈递“整顿通省书院”的请求,针对全省书院的积弊,提出从七个方面进行整顿,即一、定教法,聘请纯正博学、兼通中西的著名学者编定教法章程;二、端师范,书院不再由庸陋之绅士占据山长位置,而是聘请明正通达之士担任;三、裁乾修,即将那些挂名的山长或出工不出力的山长,或不称职的山长,统统裁撤,至少要废除他们所领取的工薪;四、定期限,规定书院山长不能任意决定到院时间,凡山长住院每年以十个月为度,不得视书院为传舍,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致负朝廷殷殷教育之至意;五、勤功课,厘定各书院课程,规定书院课程虽不能照新式学堂那样中西并学,亦须令学生每日必呈札记一条,由山长亲自评阅,不能再托人点窜;六、严监院,改革书院内部管理制度,废除由学生选斋长的办法,改为任命本地教官为监院,或以绅士充当,限令住院,申明条规,免滋流弊;七、速变通,从前山长多半守旧、不通时务之人,若听其主持书院,则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应仿江苏另延山长的办法,将本年束脩全行致送,另筹款项,邀请博学者主讲,以免旷时驰业,致误学生前程。[23]这些建议不仅切中湖南各书院的弊端,而且其预设的攻击目标就是岳麓书院,而岳麓书院的山长就是王先谦。
熊希龄等人的反击固然有助于湖南知识界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和新势力的增长,但湖南巡抚陈宝箴出于息事宁人、平衡大局的考虑,不仅对王先谦欲辞去岳麓书院山长的职务加以挽留,而且在事态基本平息后,下令免除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的职务,稍后又免去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人的分教习职务。这显然是为了慰抚王先谦等士绅。
时务学堂的人事调整,大致平息了因梁启超的异端言论而引发的所谓湖南新旧冲突,湖南知识界大致恢复到时务学堂创办前的均衡。湖南的维新势力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力因此受到严重打击。
然而湖南时务学堂的开办,极大地刺激了湖南省内各府县开明士绅改革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的热情,在此之后不久,岳州府巴陵、平江、临湘、华容等县士绅郭鹏、姜炳坤、方傅鸾等仿照湘省校经书院章程,改岳阳书院课程为经学、史学、时务、舆地、算学、词章等六门;宝庆府武冈士绅陆孝达、王佐龙等将鳌山、观澜、峡江三书院,一律改课实学,课程分为经义、史事、时务、舆地、算学、方言、格致等八门。浏阳士绅也计划将该县六个书院合并为一所规模较大的致用书院,后因县内守旧势力的阻挠没有成功,只能将南台书院辟为讲舍,进行新式教育。郴州士绅在新式教育影响下,也集资创办了经济学堂,致力于培养通达时务的新式人才。所有这些,都应该说是在时务学堂的影响下发生的。
即便从时务学堂自身的办学成果看,也为湖南乃至全国培养了一批对西方近代以来的新思想、新学说有相当体会的新型知识人,为湖南和全国正在开展的维新变法运动输送了一大批人才。首批40名学生在此后十余年间大半死于国事,在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反袁斗争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为这些政治变革立下了不朽功勋,有的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如自立军起义时牺牲的林圭、秦力山,反袁运动中的领袖人物蔡锷等。
但是,时务学堂在梁启超的主持下,改变了创办之初的宗旨,成为其宣传个人政治主张的阵地,激起了湖南正统学者的激烈反对,并引发了所谓新旧思想的冲突。梁启超等人的这些做法对于开通内陆省份湖南的社会风气,无疑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然而一百多年之后重评梁启超等人的言行,则正如孔子两千多年前所说,欲速则不达。
标签:梁启超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时务报论文; 陈宝箴论文; 熊希龄论文; 王先谦论文; 谭嗣同论文; 康有为论文; 湖南发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