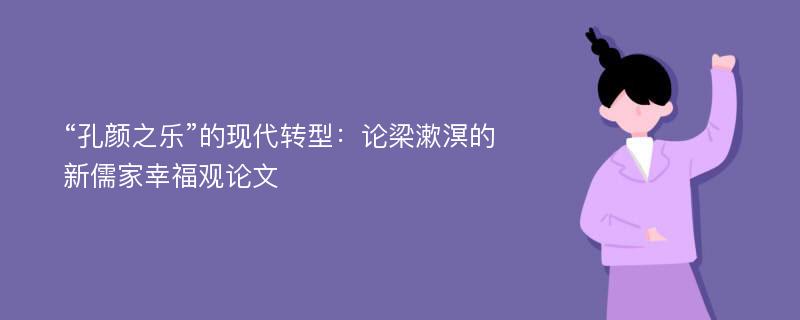
“孔颜之乐”的现代转型:论梁漱溟的新儒家幸福观
张方玉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摘要: 梁漱溟先生以传统儒家的“孔颜之乐”为根基,凭借深刻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开启了现代儒家幸福观的哲学建构。其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开放性视野,鲜明的“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意识,为现代儒家幸福观的建构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框架。生活儒学的主旨转向,道德视域中对儒家精神的现代阐释,重新确立了“乐的生活”在儒学中的价值与地位。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的融入,“个性伸展”的向上创造,“自然浑融”的生活态度,诸多对于经典人生理论的重新诠释,使儒家德性幸福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式进路与现代转型。
关键词: 梁漱溟先生;孔颜之乐;新儒学;德性幸福
梁漱溟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人物。作为 20世纪中国的重要哲学家,梁漱溟先生常常说自己终身受“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的支配,“中国式的人生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自然确立,他对现代人生幸福的探寻贯穿其生命的始终。在其早年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不仅有“人生三路向”的标题,而且有“孔子生活之乐”的专论;在其中年的代表作《中国文化要义》中,“向里用力之人生”也赫然出现在章节标题中,称“向里用力”是中国式人生的最大特点;其晚年的代表作《人心与人生》更是直接以人生主题为书名,探讨人心、心理、性情、理性、境界、道德、宗教等诸多问题。“孔颜之乐”是先秦儒家德性幸福的典范,“寻孔颜乐处”是宋明理学家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梁漱溟先生以其对儒家精神生活的深刻体悟与文化自觉,重新阐释了传统儒家的“乐学”“乐天”“乐命”,并试图把儒家“乐的真味”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先生开启了现代儒家幸福观的崭新建构。
周三公司开例会,当主管看到沙莉的记事簿时,大加赞赏,说她第一页就工工整整记着所有同事的电话,这样既有条理又有利于融洽人际关系。一种被排挤的不快压在我的胸前,可沙莉的脸上每天都带着微笑,与同事软言温语地打招呼。早晨刚上班时,她悄悄地将桌上的绿萝换换水,然后又不声不响地坐在电脑前整理资料。
一、文化比较中的人生幸福论
提及人生幸福论,学界通常把古希腊文明中的幸福伦理学作为人类对幸福探索的思想源头。雅典七贤之一的梭伦提出“最有钱的人并不幸福”“幸福在于善始善终”,他因此被视为古希腊对幸福范畴展开理论思考的第一人。之后,苏格拉底的“正确的生活”、柏拉图的“人生的真幸福”、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就是至善”更为学人所熟知。相比之下,先秦诸子的文化典籍中并未将“幸”“福”二字连用,因此没有直接出现西方或者现代意义上的“幸福”词语。然而,从《诗经》《易经》中频繁出现的“福”“禄”“吉”“喜”,从《尚书》中的“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到原始儒家的“孔颜之乐”“君子之乐”,再到宋明儒学中的“孔颜乐处”,儒家文明无可争议地以自己的方式展开了对于人生幸福的探索。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自序中,梁漱溟先生声明要研究“孔家生活”,要把自己看到的“孔子人生”贡献给世界,要引导人们走“孔子的路”,实际上就是明确了以儒家的“孔颜之乐”作为现代社会幸福观的理论根基。“孔颜之乐”是儒家德性幸福的典范,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安贫乐道的个体人生幸福,有着强烈的道德精英主义的色彩。而在梁漱溟先生那里,孔子的生活之乐极其宽泛、极其平常。生趣盎然、天机活泼是生活之乐,“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也是生活之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生活之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也是生活之乐。进一步而言,儒家传统的生活之乐是从偏重道德个体安身立命的角度展开的,而梁漱溟先生的现代儒家幸福观则偏重民族意识和社会关切。“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1](241)于是在梁漱溟先生那里,儒家的人生就成为解决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中的问题的一剂良药。
两千多年前,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希腊、印度、中国的古老文明是在相对隔离、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西学不断涌入中国思想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科学、民主、启蒙、救亡开始奏响时代的强音,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西文化展开了激烈而深刻的探讨。东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研究,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持续且热切关注的时代课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与理论背景之下,梁漱溟先生的现代儒家幸福观就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对照的广阔视野。把中国人生幸福观的建构置于文化比较的视野之中,或者说是在人生幸福观的对照中进行东西文化的比较,这是梁漱溟先生新儒家幸福观的明显特质。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正式出版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赞誉者有之,批评者有之,笔墨纷争四起。文化现象纷繁复杂,胡适先生批评梁漱溟先生的文化哲学“武断”“笼统”“全凭主观”,不无道理,然而,梁漱溟先生在文化比较中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似乎更值得重视。梁漱溟先生没有对西方文化史的整体进行考察,而只是抓住科学和民主这两个要点,以此作为文化批判的主要对象,这自然会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形。梁漱溟先生提出西洋人生哲学或崇尚理智,或强调功利计算,或强调知识经营,或强调绝对且严重的理性,甚至得出西洋实在不曾有什么深厚人生思想的结论。在这些有失偏颇的表述的背后,有着深刻的中国问题意识,梁漱溟先生的真实意图是复兴中国自己的人生哲学,进而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在对西方和印度人生幸福论进行猛烈的文化批判之后,梁漱溟先生郑重提出中国人应该树立正确的态度:①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②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③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在这里,把中国儒家、孔子的生活贡献给全世界的人类,成为梁漱溟先生充满自信的文化使命。可以发现,在梁漱溟先生那里,孔子的东西、儒家的学问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只有复兴了儒家积极的人生态度,才能使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由此可见,梁漱溟先生所倡导的儒家人生哲学已经不是少数精英安贫乐道的“孔颜之乐”,而是更加宽泛的大众化的中国人生幸福论。
疟疾是由人类疟原虫感染引起的寄生虫病,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对外经贸和交流,因而导致热带、亚热带的疟疾疫区国家的人口进入我国,因其在疫区感染后携带疟原虫入境,导致我国的疟疾发病率不断增加[1]。乍得位于非洲中部,常年疟疾流行。作者参加中国第十三批援乍得医疗队,对中乍友谊医院疟疾确诊者进行临床特征分析如下。
在购置实验教学仪器设备之前,应该有详细的购置计划,尽量避免购买重复的实验器材,合理地利用实验建设经费,在列采购清单前一定进行以下几项:首先,查看现有的实验设备是否满足实验需求,其次,统计实验室提出的设备购置申请,最后请专家按照教学大纲合理地对采购清单进行审核修改,交到财务部门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给予采购。
二、生活儒学视域中的“孔颜之乐”
齐海峰心里酸溜溜的,这是明目张胆耍流氓啊,他做英雄的机会来了。他一个箭步冲上去,不由分说地揪起那男青年的衣领,朝对方脸上狠狠地来了一拳。
梁漱溟先生阐释孔子对于生活之赞美,不遗余力地推崇孔子生活之乐,对今天的道德哲学而言,其重大的启示意义就是德性幸福的建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时期,梁漱溟先生独能以赞叹孔子的姿态出现,充分展现了复兴儒家的理论勇气;而梁漱溟先生能在“孔家生活”“生活之乐”的儒家人生幸福处着力阐释,则更是展现了他超凡的理论自觉,他要复兴的是儒家的生命与智慧。人们常将幸福与义务、良心、荣誉、公正放在同一序列中,视其为伦理学研究中同等重要的范畴,但实际上人生幸福论涵盖了义利、公私、理欲、荣辱、理想、境界等诸多问题,有着更为根本的意义。梁漱溟先生言简意赅地指出,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儒家要达到的是生机盎然的“乐的人生”。为此,他批判汉代的经学只算是研究古物,对孔子的生活精神却不在意,是只有外面的研究而没有内心的研究;他称赞宋明理学的“寻孔颜乐处”,因为宋明的儒者懂得去寻找孔子的生活精神,要求顺天理无私欲实现乐的人生。“儒家盖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6]即便是对于当时学界崇尚的民主与科学,梁漱溟先生也明确提出只有踏实奠定一种郑重的人生态度,才能真正吸收融合民主与科学之下的种种学术思潮。他认为新文化运动若是离开郑重的人生态度,也无法取得积极有益的结果。可以这样认为,现代新儒学中人生幸福论的地位与价值,在梁漱溟先生那里被重新确立起来了。
第一,以梁漱溟先生自身所展示的个性特质而言,生活维度是其思想与实践的基本立足点。梁漱溟先生自述对生活极其认真,所以他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一个整体。比如他早年倾心佛教生活,就既不吃肉食也不娶妻生子,时间有八九年之久。而在生活思想发生变化之后,他便毅然决定搁置佛家的生活,开始倡导孔家的生活。梁漱溟先生声称别人可以没有思想见解而生活,而他若是没有确实心安的主见,是根本不能生活下去的。因为他的性格就是如此的严谨,他的生活、行事从来不肯随便。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自序中,梁漱溟先生说道:“我要做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许我没有为生活做主的思想;有了思想,就喜欢对人家讲;寻得一个生活,就愿意也把他贡献给别人。”
人们常常在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哲学宗教等方面展开文化考察,而梁漱溟先生则直接把文化归结为生活,进而把生活归结为意欲的满足状态。于是,一种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的精神生活,比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的社会生活,以及饮食、起居、利用自然界等物质生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差异就深入地呈现为生活方向、意欲方向的比较。“梁漱溟先生正是从人生实践体验的角度来感受和构筑他的文化理论的。因此,我们对梁漱溟先生文化理论的分析研究,无论是其提问方式还是解答问题的方式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都不应离开其人生实践。”[2]在梁漱溟先生看来,所谓的西方化就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是一种向前奋斗的态度,并由此形成了科学与民主的文化精神特征。中国人的生活观念是安分知足、随遇而安的,因此中国文化是以意欲的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对于种种欲望都持禁欲态度,遇到问题往往考虑彻底取消问题,因此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的。这样,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的生活就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路向——向前、向后、调和。梁漱溟先生提出,考察西方文化不能仅仅着眼于显性的科学、民主与征服自然,而应当考究其人生态度与生活路向。西方文化就是要努力追求现世幸福,虽有巨大成就,但渐渐沦为利己、肉欲、淫纵、骄奢、残忍、纷乱。而印度文化违背生活本性,饥饿不食、投入寒渊、用火炙烤、赤身裸露等行为荒谬离奇,形成了精神生活上的畸形发展。从中可以发现,梁漱溟先生对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的考察,实际上是对西方和印度人生幸福论的文化批判。梁漱溟先生认为这才是在根本或本源上的文化思考。
第二,以梁漱溟先生所看重的大事而言,乡村建设是他一生为之奔走的重要社会运动,而乡村建设运动所蕴含的理论也正是生活儒学。梁漱溟先生讲乡村建设的事项虽然很多,但是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大方面,即经济、政治与文化教育。进一步而言,梁漱溟先生明确讲“虽分三面,实际不出乡村生活的一回事”。这就清楚展现出乡村生活建设的重要性,因为乡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共同汇聚于乡村生活建设。具体而言,儒家的礼仪、习俗、伦常、惯例所构成的日常生活,儒家道德共同体与西方民主相结合而形成的政治生活,儒家关乎人心人性追求意义境界的精神生活,这些复兴传统儒学并与现代世界接轨的生活实践构成了乡村建设的一套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乡村建设运动也正是生活儒学落实到现实社会的建设实践。
作为现代新儒学开风气的人物,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朝话》等著作中多次表述了强烈的文化使命意识,即要为中国儒家做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那么,梁漱溟先生所说明的儒家到底是何种儒家?此种儒学又是如何与现代学术接头的?
色谱条件:色谱柱为HP-88(100 m×0.25 mm,0.20μm film thickness,J&W Sci.USA);进样口温度250℃,载气He,流速1 mL/min。采用程序升温方式,由室温升至160℃保持2 min,然后以2.5℃/min升至250℃,保持2 min,不分流进样。
在一些学者看来,在传统儒学与现代学术接洽的不同类型中,梁漱溟先生的儒学是一种“注重心理学诠释的现代儒家哲学”,其基本进路是心理学的;而熊十力先生的儒学是一种“注重宇宙论建构的现代儒家哲学”,其基本进路是宇宙论的[4]。这种观点是以《人心与人生》中的心理学诠释为依据的,然而就梁漱溟先生的整体思想而言,其心理学部分的意义要明显逊色于生活儒学的向度。根据以上所列举的理由,我们可以认为梁漱溟先生的儒学乃是一种“注重生活儒学的现代儒家哲学”,复兴生活维度的儒家哲学是其重心所在。问题向前推进一步,既然已判定梁漱溟先生的儒学是“注重生活儒学的现代儒家哲学”,那么此种儒学所倡导的“郑重生活”究竟是何种形态的呢?对此,在梁漱溟先生的著作中是可以找寻到线索的。在宽泛的意义上,梁漱溟先生所阐述的“从来的中国人生活”即为此种“郑重的生活”;在更加具体的意义上,此种“郑重的生活”也就是孔子的“乐的生活”。由于先秦时期“孔颜之乐”对后世儒家的幸福观影响深远,所以这里我们把梁漱溟先生生活儒学的核心要义规约为“道德理想主义的孔颜之乐”。
关于“从来的中国人生活”,梁漱溟先生以极强的文化自信对之推崇有加。在物质生活方面,梁漱溟先生指出大多数中国人虽然不能达到孔子那样的自得状态,但是多能安分知足,享受现实眼前的生活。尽管这样的生活始终是简单朴素的,一切衣食住行享用都赶不上西洋人,但中国人在物质上所享受的幸福却比西方人要多。这是因为中国人通过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获得了一种从容享受,而西方人不满足现状向前追求以致精神苦闷。在社会生活方面,尽管中国人个性得不到伸展,社会性也不发达,但是在家庭、社会中处处有一种温情,而不是冷漠、敌视和算账。在精神生活方面,中国人与自然浑融一体,从容享受生活,人与人之间敦厚礼让,极其可贵。尽管中国人现代科学知识极其匮乏,但文学、艺术、孔子那样的精神生活自有其可贵之处。“我们再看孔子从这种不打量计算的态度是得到怎样一个生活。我们可以说他这个生活是乐的,是绝对了的生活。旁人生活多半是不乐的;就是乐,也是相对的。何谓相对的乐?他这个乐事系于物的,非绝关系的,所以为相对;他这个乐事与苦对待的,所以为相对。若绝关系而超对待,斯为绝对之乐。”[1](155)在“孔子生活之乐”的标题下,梁漱溟先生不仅重申了先秦儒家的“孔颜之乐”,而且论及宋明理学中的“寻孔颜乐处”,并且竭力称赞晚明时期的王艮父子。王艮以乐为教,写作有《乐学歌》:“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梁漱溟先生对此大加称赞,认为泰州王艮颇有儒家圣人的样子。“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这种达观产生宽宏的怀抱,能使人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天知命地过生活。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一个人有了这种自由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地享受快乐的人生。”[5]由此可以发现,在人生幸福论的意义上,梁漱溟先生的生活儒学就是要把孔子“乐的生活”和“生活之乐”复兴起来。
三、传统德性幸福的现代转型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不妨对儒学的历史发展进行简略的梳理。原始儒学确立了“仁”与“礼”两个核心主题。孔子之后,儒学沿着不同的进路展开,《韩非子·显学》划分为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思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传统儒家的学问逐渐以“内圣外王之道”的形态为世人所接受。“内圣”即是修身养性,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经历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的昌盛之后,儒学在近代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困境。而在当代儒学的研究中,哲学儒学、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制度儒学、生活儒学、道德儒学等各种样式异彩纷呈。纵观儒学发展的历史线索,立足于儒学研究的当代视域,不难发现,梁漱溟先生所要复兴的儒学乃是生活儒学。
第三,以梁漱溟先生思想体系中的基本理论而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朝话》《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著作均呈现出明确的生活儒学指向。在文化哲学中,梁漱溟先生直接把文化归结为生活,称一种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生活的三种路向——向前、调和持中、向后,决定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差异。在《朝话》中,梁漱溟先生进一步提出“逐求、郑重、厌离”这三种人生态度,并认为“从反回头来看生活而郑重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发挥郑重。这条路发挥得最到家的,即为中国之儒家”[3]。梁漱溟先生讲儒家的人生态度亦甚简单,就是教人“自觉的尽力量去生活”。在梁漱溟先生那里,儒学的根本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
在当下的幸福伦理学的研究中,人们还经常使用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个体幸福与群体幸福、实现幸福与享受幸福的提法,而这种习惯性的表达却容易遮蔽幸福的道德底蕴。因为物质幸福、个体幸福、享受幸福也可能是道德的,而所谓的精神幸福、群体幸福、实现幸福也可能并不具备充分的道德合理性。尽管“德性论”与“幸福论”在道德哲学中为人们所熟知,然而提及德性幸福时,人们却又认为这是相对陌生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作为一对概念来看待,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德性幸福不是要摒弃功利幸福,而是不以功利为直接目的,是对功利的超越。“孔颜之乐”是儒家德性幸福的典范,这是一种安贫乐道的人生幸福。但是在孔子师生那里,不仅有相对纯粹的“孔颜之乐”,还有相对抽象的“曾点之志”,甚至还有相对现实的“子张之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早期儒家那里便已经出现了纯粹德性幸福、抽象德性幸福、现实德性幸福等三种形态[7]。梁漱溟先生的人生幸福论是以儒家的生活之乐为基础的。“孔颜之乐包含道德生命的愉悦,因此,他的乐观主义有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8]在梁漱溟先生那里,“德者得也”“德得相通”,道德成为生命的和谐、生命的艺术,“成己”与“成物”内在相通,道德与人生幸福内在一致,呈现出清晰的德性幸福的致思路径。
在道德与幸福的关系上,梁漱溟先生以现代学者的视角提出诸多深刻的见解。关于道德的概念,梁漱溟先生提出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其一是在社会学方面,其二是在人生方面。这种见解与黑格尔关于道德、伦理的区分非常接近。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道德虽然有时可以呈现为不平常的事件,但即便是不平常的事件,道德也仍然是平常人心里都有的道理。所以梁漱溟先生讲道德并不以新奇为贵,是“庸言庸行”。在此基础上,梁漱溟先生进一步提出道德并不是所谓的拘谨或束缚,而是一种生命的力量,力量是道德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于是道德与人生幸福内在地联系在一起,道德便是“生命的精彩”,是“生命发光的地方”,是“生命动人的地方”,是“让人看着很痛快、很舒服的地方”。儒家的圣人正是因为具有深厚的道德底蕴,所以生命中时时得到和谐、精彩与生意盎然。在其晚年的著作《人心与人生》中,梁漱溟先生充满信心地预言:“道德发乎人类生命内在之伟大,不从外来。人类生活将来终必提高到不再分别目的与手段,而随时随地即目的即手段,悠然自得的境界。此境界便是没有道德之称的道德生活。”[9]由此,梁漱溟先生实际上传承创新了儒家“德福一致”的理路,这深刻启示着现代德性幸福的精神建构。
身处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大学,梁漱溟先生并非一位封闭守旧之卫道士。在人生幸福论的讨论中,当然不能不提到梁漱溟先生对于西方生命哲学的吸纳。梁漱溟先生的著作论及中西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叔本华、柏格森、奥伊肯、罗素、克鲁泡特金、泰戈尔等人的思想均成为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其中,对梁漱溟先生影响最大的当属法国生命派哲学家柏格森。梁漱溟先生吸取了柏格森关于“生命”“绵延”“直觉”的思想,认为孔子的精神生活似宗教而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与西洋近代的生命派哲学非常相似。梁漱溟先生对于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吸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尽管他晚年对于生命哲学有所检讨,但实际上,梁漱溟先生在生命哲学与儒家人生思想相互印证、相互诠释的致思路径上并没有根本改变。罗素也是梁漱溟先生表彰的重要思想家,因为在他看来,罗素的“自由生长”与孔家的“不碍生机”具有相同的旨趣。梁漱溟先生倡导从根本上启发一种人生,既涵容了向前的态度,又能超脱个人的为我、物质的计较、功利的目的,达到从内在发出真正的生机来。这也是与罗素所谓的“创造冲动”相一致的。梁漱溟先生认为只有这样向前的态度与行动,才能拥有生命的力量与生活的乐趣,从而弥补中国人向来的短处,且能避免西洋文化的弊病。
在儒家人生幸福观的现代建构中,梁漱溟先生赋予传统的概念范畴以新的意义,增加了许多富有时代意义的新内容。关于儒家的“仁”,梁漱溟先生提出“仁”是极有活气且稳定平衡的心理状态,是内心的敏锐直觉。“仁”就是对于生活的由衷赞美,对于自然的饮食男女的本能情欲并不排斥也并不计算;顺理有度,生机活泼,自然流行也就是“仁”的状态。关于儒家的“刚”,梁漱溟先生竭力推崇,认为“刚”统括了孔子的全部哲学。在梁漱溟先生的思想中,“刚”是内在用力极其充实的活动,“刚的动”是真实的感发。这就是要提倡一种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并且同时要排斥那种不断向外追求物质的扩张野心。梁漱溟先生认为真正的儒学中有符合现代精神的因素,“这种‘刚’的精神足以弥补中国文化中的主流——那种多少带有消极意义的‘自得’态度之不足”[10]。关于“创造”之于人生幸福的意义,梁漱溟先生在晚年讲,追求享受、名利的人不过是受身心牵累的庸人,奔赴理想,努力创造才能带来人生的幸福。拥有强大生命力的人从不甘心于在狭小的自私中混来混去,生命就是“向上创造”,就是“向上翻高”,就是“往广阔里开展”。梁漱溟先生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认为从生物的进化到人类社会的进化,都是宇宙大生命的无限创造,所以人类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创造。除此之外,梁漱溟先生还批判了传统伦理社会中人的个性和社会性的缺失,提倡“人的个性伸展”和“人的自由”,并且实现“社会性发达” ——倡导建设个性不失的社会组织。这些思想显然是传统儒家的人生哲学所不曾具有的。
综上所述,梁漱溟先生以传统儒家的“孔颜之乐”为根基,凭借深刻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开启了现代儒家幸福观的哲学建构。在文化哲学层面,其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开放性视野,鲜明的“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意识,为现代儒家幸福观的建构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框架。把中国人生幸福观的建构放置于文化比较的视野之中,或者说在人生幸福观的对照中进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这是梁漱溟先生新儒家幸福观的明显特质。在儒家思想层面,生活儒学的重心转向,道德视域中对儒家精神的现代阐释,重新确立了“乐的生活”在儒学中的价值与地位。梁漱溟先生的儒学乃是一种“注重生活儒学的现代儒家哲学”,复兴生活维度的儒家哲学是其重心所在。在具体的人生幸福层面,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的融入,“个性伸展”的向上创造,“自然浑融”的生活态度,以及对于儒家经典人生理论的重新诠释,使儒家德性幸福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式进路与现代转型。在梁漱溟先生那里,“德者得也”“德得相通”,道德成为生命的和谐、生命的艺术;“成己”与“成物”内在相通,道德与人生幸福高度一致,现代德性幸福的理念已经呼之欲出。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先生的新儒家幸福观是现代中国德性幸福论的重要源头活水。
参考文献 :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2]郭齐勇, 龚建平.梁漱溟哲学思想[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72.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 第 2卷[M].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83.
[4]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211.
[5]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3.
[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7: 136.
[7]张方玉.追寻君子的幸福[M].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4:23.
[8]顾红亮.儒家生活世界[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259.
[9]梁漱溟.人心与人生[M].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4: 250.
[10]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M].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127.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us-Yan’s Happiness":On neo-Confucianism eudemonism of Liang Shuming
ZHANG Fangyu
(School of Marxism,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Liang Shuming, by taking as the basis "Confucius-Yan's Happiness" which is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and by resorting profou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pened the philosoph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Confucian concept of happiness.The open horizon of comparing eastern culture with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distinctive awareness for “Chinese problems” and “life problems” provide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onfucian concept of happiness.The focus shift to Life Confucianism and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spirit in the moral horizon, re-established the value and the status of “happiness Life” in Confucianism.The integration of the western modern life philosophy, the upward creation of a “personality extension”,the life attitude of “natural harmony”, and the multifarious re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 theory of life, all have made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virtue happiness present a new kind of approach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Liang Shuming; Confucius-Yan’s Happiness; neo-Confucianism; virtue happiness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9)04−0013−06
DOI: 10.11817/j.issn.1672-3104.2019.04.002
收稿日期: 2018−05−06;
修回日期: 2019−04−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儒家德性幸福的现代转型研究”(17BZX063)
作者简介: 张方玉(1977—),男,江苏句容人,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道德哲学,联系邮箱: zhangfangyu2000@163.com
[编辑: 胡兴华]
标签:梁漱溟先生论文; 孔颜之乐论文; 新儒学论文; 德性幸福论文;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