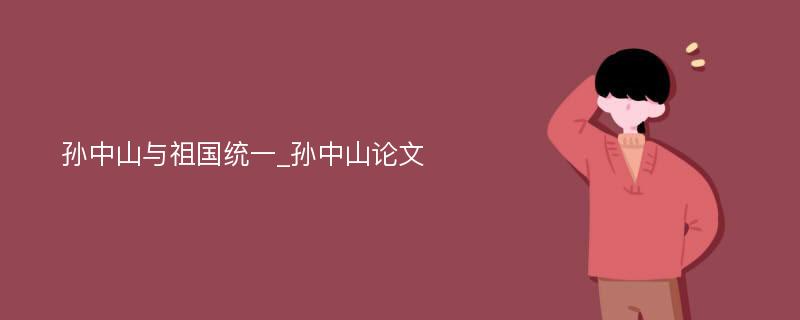
孙中山与祖国统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为振兴中华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本文拟探讨孙中山维护祖国统一的实践和理论,分析孙中山祖国统一观的特点,以进一步加深对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的认识。回顾孙中山为祖国统一而进行的斗争,有助于我们继承和发扬爱国革命的传统,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
(一)
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之初,中国已经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日趋严重。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爱国救亡成了孙中山进行革命的起点。
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写道:“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孙中山明确指出,兴中会之创立“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①]1900年北方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之际,孙中山从策略方面考虑接受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的建议,就组建华南联邦共和国或两广独立共和国一事与李鸿章等人接触。但与此同时他又在致卜力书中明确提出,中国应“立一中央政府,以总其成;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并将这条置于平治章程六则之首,催促英方尽早表态。[②]7月24日孙中山获悉港督与调任直隶总督北上途径香港的李鸿章会谈的内容后,一针见血地揭露港督所言“盖系欲以两广为英国属领,以扩展其利益范围”[③],至此对英国策划的两广独立阴谋持明确反对的态度。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华民族的灾难更加深重了。孙中山认为,“八国联军之役以后,列强把中国看成一条肥猪,天天在宰割。……清廷必牺牲国家领土、换取小朝廷以图苟活”,[④]救亡图存迫在眉睫。因此孙中山于1905年创立中国同盟会后接连在华南组织和领导了八次反清武装起义,力图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以消除内乱和瓜分。1910年11月中旬他在槟榔屿召开筹备广州起义的会议上强调:“际此列强环伺、满廷昏庸之秋,苟不及早图之,将恐国亡无日。时机之急迫,大有朝不保夕之概”[⑤],维护祖国统一的责任感和急迫感跃然纸上。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当时清政府还没有完全垮台,南北议和尚在进行。一美国记者别有用心地试探孙中山,称“假如你们与北方协议把国家划分为二,每边各自建立一个政府,你们就会得到承认”。政治上高度敏感的孙中山当即抵制了这一划江而治一国两府的方案,答称“不,那不行,我国人民的感情是一致的。所有的人都反对满清,都站在我们一边。北京并没有政府。”[⑥]同年6月他对《南清早报》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上述方案“诚为无意识之谈,……此等卑劣之言,无事鄙人之辩驳。……乃属美人之意见,非华人之意见也。”[⑦]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祖国的统一,孙中山于1912年8月毅然接受袁世凯“共商国是”的邀请。他对报界宣布北上宗旨和政见时明确表示,“南北不可分离”,“大局急求统一”[⑧]。孙中山事后回顾说,“余自共和告成以来,竭力从事于调和意见,维持安宁,故推袁世凯为总统。”[⑨]孙中山在民国初年还对英、俄加紧侵略我国西藏、蒙古地区保持高度的警觉,坚决反对西藏、蒙古地方的分裂主义倾向。他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大力倡导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宣布要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政统一和财政统一[⑩]。
1912年8月孙中山对《大陆报》记者发表谈话称,若中国人于数十年后不能恢复满蒙领土,“则华人无保存国家之资格”[(11)]。同年秋他在北京与袁世凯的会谈中多次提及蒙藏问题。孙中山认为“此次蒙、藏离叛,达赖活佛实为祸首”,建议袁世凯“广收人心,施以恩泽,一面以外交立国,不宜徒以兵力从事蒙、藏,……反激其外向”[(12)]。孙中山还认为“西藏之向背,关乎蒙古之独立与否”,“欲使蒙古取消独立,必先平西藏,以为取消库伦独立之预备。西藏平,则蒙古之气焰息矣。”[(13)]鉴于此,他向袁世凯提议,“用激烈之武力解决蒙、藏问题,借儆反侧,兼以杜外人狡启。俟一大致解决,再派善于词令深悉蒙、藏语言者,前往宣慰,较单纯用剿者,似易收效。”[(14)]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北京政府后来对藏采取“先剿后抚”的方针,派川军、滇军出征,防止了藏、蒙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1917年夏至1923年初,孙中山在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期间同样十分注意祖国统一的问题。1922年8月他向上海报界明确指出,最近六年护法之举之目的“实为统一,统一固不得谓非吾国现在最切要事。问题是护法运动所争取的统一是真统一、民主统一和共和统一”[(15)]。在孙中山看来1917年9月开始的南北战争“是一场全国性的军阀主义与民主的斗争,是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北方人民自发组织示威游行和抵制运动,反对支持这些卖国贼的外国压迫者。这一事实表明,北方人民是同情南方,并与南方合作的。”[(16)]南方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列强的劝告与北京政府开始议和,“务求根本之统一与和平”[(17)]。1919年5月南北议和因遭北京政府的破坏而失败。9月孙中山等人从大局出发致电徐世昌等人,指出“国际联盟瞬将开会,国内统一则不可迟,利在和,而且利速和”,要求对方“遴择适宜之人,使之充当总代表促成和议”[(18)],再次表示了谋求统一的良好愿望。1922年6月6日孙中山鉴于北方直系诸将有服从国会的表示,发表《工兵计划宣言》,指出“数年以来,国内战争乃护法与毁法战争,绝非南北战争。”他提出如果直系诸将能将所部半数改为工兵,留待停战,“本大总统当立饬全国罢兵,恢复和平,共谋建设。”[(19)]次年1月26日孙中山在平定陈炯明叛变后又发表了《和平统一宣言》,再次表示“文于抚辑将士及绥靖地方外,当竭尽心力以敦促和平统一之进行,并务以求达护法事业之圆满结束。”[(20)]《宣言》称,“文今为救国危亡之计,拟以和平之方法,图统一之效果,……必使和平统一期于实现。”[(2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孙中山在国民革命一开始就把祖国统一放在议事日程上,国民党一大宣言郑重宣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22)]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孙中山决意发动北伐。同年9月18日他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代表《北伐宣言》,谴责北洋军阀“实继承专制时代之思想,对内牺牲民众利益,对外牺牲国家利益,……以酿成今日分崩离析之局。”宣布“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以统一全国,实现真正之民权制度,以谋平民群众之幸福。”[(23)]11月13日孙中山应在京发动政变的直系将领冯玉祥之请北上与之商讨国事,行前三天在广州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并预言国民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24)]11月19日孙中山途径上海时对新闻记者宣称,“这次单骑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大家可以料得我狠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去冒这种危险,大家做国民的人便应该做我的后盾。”[(25)]这说明为了祖国的统一、人民的幸福孙中山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在临终前对汪精卫说,“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为痼疾所累,行将不起。……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26)]次日上午这位为祖国的统一而奋斗终身的伟大的革命家在京溘然长逝,在爱国救国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切爱国者为振兴中华而继续奋斗。
(二)
孙中山关于祖国统一的思想是深刻的。他在历次谈话、演说中从历史、国情、民情等各个角度多方面地论证了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阻挡。早在本世纪初,孙中山就向日本人表示,“吾国自有史鉴以来,数十余朝,每当易朝,有暂分裂者,有不分裂者,而分裂者多,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故中国有识之士”喜闻保全之论,而恶分割之言也。”[(27)]至1903年他又明确指出,“就支那民情而论,有无可分割之理”,“且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国虽有离折[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土地几如全瓯之固,从无分裂之虞。……文字俗尚则举国同风。……是支那民族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28)]进入民国以后,孙中山在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封建割据作斗争时仍坚持他的上述观点。1922年8月孙中山发表宣言再次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29)]。1924年4月他在著名的民权主义演说中强调,“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统属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为什么要把向来统一的国家再来分裂呢?”[(30)]
孙中山还从民国政治的现状出发论证了人民拥护统一反对分裂的道理。1921年他对苏俄记者说,“中国人民对连续不断的纷争和内战早已厌倦,并深恶痛绝,他们坚决要求停止这些纷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因而,我们正在尽力完成赋予我们的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31)]后来他又在《和平统一宣言》中描述南北纷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痛苦时说,“年来南北纷争,兵灾迭见,市廛骚扰,闾里为墟,盗匪乘隙,纵横靡忌,百业凋残,老弱转徙,人民颠连困苦之情状,悚目恫心。”[(32)]在这种情况下,祖国统一社会安定为百姓最大的期望和心愿。孙中山深深懂得这一点,他在1924年11月北上途径日本神户时用十分简洁通俗的语言对日本记者宣称,“‘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33)],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真实地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
在维护和实现祖国统一的长期革命实践中,孙中山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及他们所支持的军阀是中国统一的大敌。他在晚年清晰地指出,“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34)],真可以说是一语中的,说到了要害处。
早在辛亥革命前夜孙中山在领导革命派批判康有为等人革命即召瓜分论的同时,也清醒地预料到“列强终将不会轻易听任我们革命的成功,甚至要予中国革命以阻挠与干涉”[(35)],民国初年他向袁世凯妥协让权,很大程度上出于防范列强乘机分裂中国的考虑。孙中山在民国期间不断地揭露帝国主义破坏中国统一的行径,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指出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是我们的卖身契”[(36)],而治外法权和海关握于他国之手使中国“不成其为国家,真为殖民地之不如。”[(37)]孙中山还指出,“帝国主义者本着‘分而治之’的原则,豢养中国军阀,嗾使他们互相混战”,认定“中国人民最恶毒、最强大的敌人是帝国主义”[(38)],“中国非完全排除此等外力,则国家之统一不能永久”[(39)],反之,“要中国永久是和平统一,根本上便要……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40)]1915年3月他及时揭露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紧侵华的图谋,指出若再退让“则将来欧洲战事完结之后,列强相继而来,效尤日本,则中国瓜分之惨祸立至,尚何疑义?”[(41)]1918年11月孙中山又明确提出,“目前中国南北对立是日本助长起来的,日本如果改变援助北方派的政策,北方派就会不攻自灭。”[(42)]孙中山还多次对海内外人士讲,列强“不愿见中国团结统一”[(43)],“不许中国统一”[(44)],并科学地分析了其原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平等条约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护身符,“在中国的外国人……,怕中国统一了,便用公文向外国政府要求废除,……断绝他们在中国的生路。”[(45)]为了维护和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列强总会处心积虑地在中国制造分裂,破坏统一。反过来,中国孱弱分裂的状态又使列强得以肆无忌惮地逞凶肆虐,耀武扬威。
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军阀的倒行逆施,孙中山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认为军阀也是实现祖国统一的障碍。孙中山坚决反对军阀拥兵自重,各占一省,自谋利益,残民以逞。他认为“清朝式驻防政策,不为中国不统一之主因”[(46)],辛亥革命后“满清皇帝虽推翻,而数十个小皇帝代兴。故人民不能得安乐,反觉痛苦。”[(47)]他指出“像唐继尧割据云南、赵恒惕割据湖南、陆荣廷割据广西、陈炯明割据广东,这种割据式的联省,是军阀的联省,……不是有利于中国,是有利于个人的”[(48)]。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若实行联邦制“最终只能导致我国分裂成为许多小的国家,让无原则的猜忌和敌视来决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49)],削弱祖国统一的意识。
孙中山还多次揭露日本支持皖系军阀、英美支持直系军阀对中国实行分而治之的侵略方针,指出“这几年来,无论那一个军阀的事,背后总有几个外国政客的帮助。”[(50)]“军阀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援助”[(51)]。1917年9月他对日本人河上清说,日本如能提供武器军火和贷款,南方政府就能“迁移到华中的某一战略要点,然后,向北京进军”,完成统一[(52)],1920年4月孙中山又对美国银行家拉蒙特宣称,只要美方给2500万元扩充南方政府军队,中国南北方之间“就可以迅速得到和平。”[(53)]孙中山的上述言论固然反映了他对列强尚存幻想对祖国统一大业的艰巨性认识不足,但同时也表明他已经看到了各系军阀依赖帝国主义才得以分裂祖国的实质。
(三)
孙中山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的祖国统一观是符合中国国情独特的统一观。他主张和平统一,但并不排斥在特定的条件下用武力来维护国家的统一。
1917年7月段祺瑞平定了张勋复辟后,坚持废弃《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孙中山为了“达民治之统一,反对专制的统一”[(54)],毅然发起了护法运动。8月11日孙中山对广州各报记者称,“段祺瑞在支持共和政府的幌子下,无视宪法,窃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力。……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在广东建立南方政府和成立国会,以此与段分庭抗礼。这是反对段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并应尽快实施。”[(55)]同年9月他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11月间当日本寺内内阁插手中国“南北和谈”并诱骗中国联合日本对德宣战时,孙中山当即指出“寺内决定方针,使中国南北调和,利用我人众物力以攻俄国,此事若成,中国其高丽矣。……此时救亡妙策,在南北分离,庶不致为寺内利用,劫持中央,以临各省。我能分立,寺内无所施伎,中国不与寺内一致,寺内当不敢建攻俄之策。”[(56)]孙中山以政治家的远大眼光识破了日本的侵华新阴谋后,及时作出了依靠南方的革命力量以抵御日本侵略的对策,在当时无疑是从大局出发的妙着。孙中山本人对于这一与北洋军阀决裂的举动一直引以为豪,并认为这是符合国家最高利益的。1920年7月他对《大陆报》记者谈及此事时称,“向使余不设法使南北分裂,则中国今日早为日本之附庸矣。今日中国北方已为日本所控制,若南北不分裂,则中国全国将归日本掌握。”[(57)]同年8月孙中山又在对美国议员团的谈话中回顾说,在日本政府强迫北京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参加欧战后,“我所能够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把中国拉开做两半,那北京政府已是因为盲从日本,给他缚住了。我就在广州建立一个政府,果然能够牵制着日本军阀的计划。”[(58)]在孙中山看来,统一是应该有原则的,这就是必须服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如果违反了这一最高利益,即使动用武力在所不惜。
对于祖国的统一手段问题,孙中山作为一个政治家在许多公开场合多次表示为了维护祖国的最高利益,不丧失国权,在必要时采用武力手段统一国家外,还主张和平统一,“素来主张中国南北和平统一”[(59)]。他还发过不少声明、宣言,主张以和平的方式统一祖国。但孙中山心目中的和平是有原则的,即和平必须实行法治,尊重国会,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国民所蕲望之平和,为依法之平和,为得法律保障之平和。”[(60)]他清醒地意识到要达到这种真正的和平,“统一南北,必以革命之道行之”,“武力统一是自己的真意”,但因人民主和,故顺从民意”[(61)]因此在实际操作时孙中山并没有放弃武力,也不讳言战争。1917年10月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正式出师北伐。1919年11月孙中山对《大陆报》记者坦率宣称,“南北战争系余发起,……余之惟一条件,为国会必须有全权行使职权。北京政府一经接受余之条约,和平可以立成。”[(62)]1924年春孙中山下决心为了统一中国发动新的北伐。他在对驻广州滇军的演说中强调,“我们此刻在广东,一定要北伐。中国的存亡,就在我们此次能不能北伐。……如果不能北伐,革命便要失败,中国便要亡国。”[(63)]同年9月18日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发表北伐宣言,郑重宣布“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北伐之后将“重新审订一切不平等条约,……以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64)]11月间孙中山在应冯玉祥之请北上和谈时也丝毫没有放松北伐的努力,他把统一的根本立足点放在军事上,要求已进占江西大庾、赣州的北伐军继续前进,力争攻克武汉。即使在他生命垂危时依然十分关注北伐战事,要身边的同志向他报告前线的战况。孙中山并没有认为和平统一是祖国统一的唯一方式,他在公开呼吁和平统一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诉诸武力的努力。同样,孙中山也清醒地认识到,“对于欧洲人,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要请在亚洲的欧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象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65)]事实上他在1923年末1924年初的“关余事件”、1924年秋的广州商团事件中一再顶住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并且做好了以武力相对抗的准备,最后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以获胜而告结束。斗争的实践使孙中山懂得了与帝国主义打交道,必须以武力为后盾,舍此决无出路。
综上所述,孙中山祖国统一的思想的要点应当是:一、统一、和平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有原则的,不是无原则的。凡是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统一与和平是真统一、真和平;反之是假统一、假和平。二、革命党应力争真统一、真和平,反对假统一、假和平,不可为抽象的统一、和平而放弃原则,停止斗争、妥协退让。三、争取祖国统一的途径或手段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武力的,决非仅限于和平一种而自缚手脚。至于何时何地采取何种手段争取统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可一概而论。
注释:
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⑤《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3页,第494页。
③ ④《孙中山集补集》第129页,第1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⑥ ⑦《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40页,第388页,第2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⑧《孙中山集补集》第611页。
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5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11)《孙中山集补集补编》第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 (13) (14)《孙中山外集》第181页,第186页,第189页。
(15)《孙中山集补集补编》第298页。
(16) (18)《孙中山集补集补编》第262页,第239页。
(17)《孙中山集补集》第468页。
(19)《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47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20) (21)《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49页,第5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22)《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3) (24) (25)《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75—77,297—298,331—34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6)《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638页。
(27)《孙中山全集外集补编》第14页。
(28)《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2至223页。
(29)《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28页,529页。
(30)《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04页。
(31)《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27页。
(32)《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49页。
(33) (34) (36) (37)《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3页,第338页,第337页,第421页。
(35)《孙中山集补集补编》第388页。
(38)《孙中山集补集》第303页。
(39) (40) (44) (45)《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7页,第421页,第375页,第375页。
(41) (43)《孙中山集补集补编》第163页,第421页。
(42)《孙中山集补集》第236页。
(46)《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94页。
(47) (50) (51)《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16页,第381页,第378页。
(48)《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04—305页。
(49)《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28页。
(52) (53)《孙中山集补集》第228页,第246页。
(54)《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31页。
(55)《孙中山集补集补编》第205页。
(56)《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56页。
(57)《孙中山集补集》第247页。
(58)《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99页。
(59) (61)《孙中山集补集补编》第332页,第259页。
(60)《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2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62)《孙中山集补集》第242页。
(63)《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649页。
(64) (65)《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76至77页,第4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