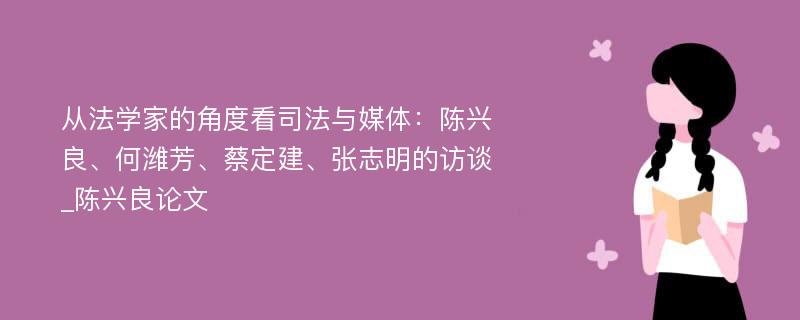
法学家视野中的司法与传媒——陈兴良、贺卫方、蔡定剑、张志铭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学家论文,视野论文,司法论文,传媒论文,蔡定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的继续深入,传媒将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态中蹒跚前行。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历史进程中,理想的传媒功能应该如何定位?在世俗社会的喧哗与骚动中,传媒是否坚守了正确的信息把关与传达?传媒的报道和管理应该如何与时俱进?带着这样的疑虑和思考,笔者采访了法学界4位知名学者:
陈兴良: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张志铭:国家检察官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这4位学者不仅在法学领域的研究中建树颇丰,而且对传媒问题颇多关注并发表过相关论文。旁观者清,希望传媒能从法学家们对传媒问题学理的探究、睿智的审视中有所启发和收获。
一 学者与传媒的互动与冲突
4位学者都表示与一种或几种传媒保持较为密切的接触。与一般受众与媒介的接触不同,学者们能够以专家的身份参与到传媒活动当中,参与形式通常为接受记者采访、为传媒撰写评论、参加电视节目、发表网络作品等,参与内容多是就一些热点法学问题或社会问题谈自己的看法。
传媒与学者的关系呈现出互动,一方面传媒为学者提供最新信息,学者也借助传媒得以向社会发表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见解。在这一意义上,蔡定剑将传媒视为“关注现实的学者的窗口”;另一方面,学者因此成为公众人物,其生活会或多或少受到影响,由于某些传媒的不实报道,更会使学者受到伤害。比如陈兴良因为从一个法学家的角度在刘涌案中讲了几句公道话而受到媒体的大肆攻击,一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社会声誉受到一定影响。①
学者与传媒既能相互合作,又存在现实矛盾。贺卫方认为,这一矛盾来自于媒介形式与学者自我期许之间的冲突。具体体现在:传媒工作者不尊重学者从专业角度发表的意见,在不征得学者同意的情况下就任意增删学者的文章及标题;或断章取义起一个哗众取宠的标题;或采访中设下圈套,之后玩弄编辑技巧,歪曲学者意思;或采访之前就给学者暗示一个调子,只许学者说与该调子一致的言论,对于其他言论则不予采用。
学者观点与媒体表达之间的冲突被认为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蔡定剑的某些文章甚至被改得面目全非;有些标题经编辑处理后达到了哗众取宠的“效果”,意思却南辕北辙。比如1999年他应国内某著名法治类日报所邀撰写的一篇文章,原题为《实施宪法比修改宪法更重要》,报纸出来后却发现题目被改成了《现行宪法需要修改吗?》结果引起很大的争议和麻烦。陈兴良也有类似的遭遇,《中国青年报》记者就刘涌案对他的电话采访,稿件见报前只让他审查了内容,见报后的主标题为《刘涌案改判是为了保障人权》,他对该标题很不满意,认为有些哗众取宠,很容易成为被攻击的靶子,“应该取一个更中性的题目,因为很多读者文章内容不怎么看,主要看标题”。也正是这篇文章,使陈兴良陷入了被舆论围攻的境地。
对立与冲突的原因在张志铭看来,是因为媒体对学者在专业问题上的尊重和耐心还没有建立起来,记者在采访前已经有某种主导性的观念,暗示学者顺着这种观念去讲;或者学者讲了许多话,记者只取其中一句有利于证明自己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的,朝着某一个方向在引导舆论。
学者与传媒之间的张力还体现在两者表述的语言风格有时不太合拍,造成言与意的矛盾。学者用语讲究严谨、准确、到位。而大众传媒因为有读者对象的考虑,为了保证通俗易懂,语言上可能就欠准确,况且一些复杂的学术思想是很难用媒体语言表达尽意。
学者与传媒的互动关系状况会影响学者的媒介选择。不负责任的传媒很可能导致学者的不信任并最终丧失他们的学术支持。
总体而言,学者和平面媒体接触最多,其次是电视,广播、网络再次之。至于电视,上述学者们都表示最初与之接触较多,但后来渐渐与之疏远,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
1.学者意见在电视节目中不仅得不到充分阐述,还往往被限制和删改。具体体现为:
(1)电视节目容量有限,缺乏深度。通常学者们精心准备了很长时间,说了很多话,但经过剪辑之后,出现的只有短短几分钟的画面和片言只语。比如央视的“今日说法”节目,“总共是十二三分钟,讲故事讲了一半,剩下6分钟左右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的对话,主持人还老抢话,给学者留下的时间太短了。”(贺卫方)另外学者们还认为电视节目的专业性不强,无法满足他们的一种专业诉求,有些电视记者提的问题也太浅显,问不到点子上,抑制了学者的表达冲动。
(2)制作方希望学者言论与节目立场一致,往往对学者加以诱导,“你经常要被歪曲,因为你的空间很小。我有时候经常会提前被暗示,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所以你就会很反感。”(贺卫方)张志铭也经常遇到这种暗示诱导,而他认为“学者想问题不太愿迁就”,所以他对电视采访基本持拒绝态度。
2.电视节目受众与学者在认知层面上的差异使两者不易形成互动。学者们是很希望在传媒的受众中找到一种来自内行的回应,而电视的受众面恰恰是最难产生这种回应的。
3.做电视节目比较麻烦、费时。比如张志铭就认为每次做电视节目都要精心准备穿着,浪费时间,而且在荧光灯下的感觉很不舒服。
平面媒体在这几个方面表现较好,学者因而愿意与之打交道,但对某些明显缺乏新闻性、信息反应滞后或者宣传色彩过于浓厚的报纸,学者们普遍表示没有阅读兴趣。
二 司法报道的现实困境
学者们基于自己与不同传媒打交道的经验,坦陈当下司法报道在媒体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1.新闻报道缺少信息量,缺乏个性、宣传色彩浓厚。这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是“泛政治化”(陈兴良语)的语言仍频频见诸报端,特别是法治新闻报道用语经常出现一些类似“鼠头獐目、狼狈逃窜、狗急跳墙”等比喻,忽视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而非黑即白、脸谱化的新闻表达方式依旧为许多媒体采用(贺卫方)。其二是,事实与意见的界限模糊。陈兴良认为没有把客观事实和社会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完全区分开,是目前新闻传播过程中存在的较大问题,将会对社会价值评判带来很大影响,有时会使公众产生误判。张志铭则认为当前国内的新闻报道不仅在内容上重复,而且在形式上也趋同,叙述手法单一、模式化。
2.庸俗化倾向:煽情、炒作、跟风。学者们都认为这一点在2003年的刘涌案报道中比较突出。当时媒体的信息源单一,只能根据控方提供的材料进行报道,因此连篇累牍的报道中出现的一些情绪化色彩强烈、倾向性鲜明的词语将刘涌妖魔化。“大家并不一定对黑社会了解多少,但是说起这个黑社会来,那大家的情绪马上就被调动起来了,媒体也愿意去把这种情绪调动起来,以强化自己的力量。”(贺卫方)
喜欢炒作的传媒被陈兴良比喻为“瞪着眼睛在寻找目标的狼”,时刻设想着主导社会的关注力。蔡定剑则认为某些新闻事件是媒体自己炒出来的,“比如2001年媒体疯炒所谓‘三湘女巨贪’蒋艳萍。她远远不是中国最大的贪官,媒体之所以趋之若鹜,其实就是抓住她以色相勾引看守所所长这一点大做文章。”
煽情的传媒报道固然有时可以宣泄某种民间蓄积的情绪,但是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比如在对有关弱势群体的报道上,传媒还是有偏颇的。首先,弱势群体是一个一般性的且面积很大的群体,媒体只关注那些具有轰动效应的个案,而忽略了该群体中更具普遍性的为数众多的人群(张志铭)。② 其次,对弱势群体只有同情是不够的,还要关注有关制度建设(陈兴良),并且对该群体的保护要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不仅仅是一个仗义执言的问题,还应该有一些法律的标准和水平”(蔡定剑)。
3.媒介权力的滥用:媒介超越了它本应该扮演的角色,突出表现在“媒介审判”的问题上,表现在司法报道中就是在法庭没有宣判之前,媒体先行给当事人定性、定罪,这是学者们普遍认同的当代传媒存在的一个弊端。比如曾经轰动全国的典型案例:四川夹江“造假者状告打假者”案、郑州张金柱撞人案、刘涌案、沈阳宝马车撞人案等等,媒体报道广泛存在“过网击球”、干扰司法审判的现象。
造成上述司法报道不良表现的主要原因,学者们认为集中于以下3点:
1.社会转型期的混乱和对市场利益的追逐。一方面,对订阅量及最大限度广告利润的追逐导致媒体的炒作;另一方面这种炒作也是我国民主法制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对此,陈兴良借用“法制乱象”的概念予以说明:像刘涌案等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传奇性的整个社会公众参与的事件,也不全是媒体炒出来的,“这些事情说明我们整个社会秩序处于转型期,在向法制化发展的进程当中出现的这么一种混乱的现象”(陈兴良)。
2.由传统文化积弊所导致的社会人文精神的缺失及公民媒介素养的缺陷。比如,贺卫方谈到在我国古代法律文书中一向用形容动物的能指来指称人;蔡定剑则认为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非常粗的源于儒家文化的所谓大是大非的善恶观,善人、恶人界限分明,至于恶人,是人人喊打,没有任何权利而言。这些文化集体无意识也影响到传媒工作者和受众,表现为新闻语言的诸多问题,以及传媒的煽情和公众的易被煽动,对被批判的对象往往揭露得一塌糊涂,毫无人格尊严等等。
3.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良莠不齐。学者们普遍感觉当前新闻工作者总体专业水平不高,尤其是很多司法报道记者法律专业知识相当匮乏,影响了报道的深度和准确性。贺卫方对某些记者在报道“严打”时频频使用“风雷震荡”、“出重拳”、“扫六合”等词语表示不满,因为从法律专业的角度来审视“有失严肃,而且缺乏水准”。陈兴良则认为有些记者知识产权意识薄弱,比如电话采访后缺少主动强调审稿的意识,占用学者大量时间却不付任何报酬等,更有甚者将学者稿件改头换面后变成自己的劳动成果,实际上反映了国内媒体的采访规范化程度存在严重缺陷。
三 冲突与平衡
贺卫方认为,“媒体就是反映这个社会的真实状态的一种折射,一面镜子”,是知识分子将其狭窄的学术的知识运用到分析社会事务中去、实现其“坐着写、起来行”的理想的手段。它不是第四种国家权力,而只是一种满足人民的知情权基础之上的延伸出来的权力,这种权力在客观效果上有时候甚至会起到比某种国家权力在某个时段更大的一种效果,更大的一种力量。
理想的媒介状态:
新闻的客观真实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陈兴良认为新闻真实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真实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实,所以具有相对性。同样,客观性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媒体报道的倾向性是不可避免的。追求客观与表达倾向并不矛盾,媒体首先应该努力去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比如消息中对客观情况的介绍,在反映真实的前提下,再把自己的倾向性表达出来。媒体可以反映学者意见或其他人的意见,“但要给读者自己的判断提供一些空间。”(陈兴良)
贺卫方认为要求一个媒体完全代表一种所谓的客观、公正、无私的形象,这是过于苛刻的要求。因为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纯粹客观的世界,“你自己个人的观念、价值不同,这个世界呈现在你面前是不同的面貌。媒体本身应该是这个观念越来越多元化、利益越来越多元化时代的客观折射,它本身也应该有多元化的一种。”所以在他看来,客观性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现实的情况是,即使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报纸,“还是有一种倾向性,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东西在里面。绝对的客观公正是绝对不可能”。
客观真实性的现实操作:
其一,区分事实与意见。陈兴良认为,如果把加入很多价值评判的东西当作事实呈现,会使读者产生误判。张志铭认为,事实或信息层面上的东西是没有举证责任的。而意见或评价是有举证责任的,在新闻报道中进行评价或提出观点必须提供证据,因此传媒应当特别注意区分事实与意见的界限。
其二,实现媒介意见的多元化和多元意见之间的平衡,对此4位学者一致认同并特别强调。贺卫方认为既然媒体报道中倾向性难以避免,关键在于有一种合理的法律框架让社会各类群体均有表达意见的机会,而且机会要平等,这在客观上能起到真实反映整个社会观念、利益、价值追求的状态和效果。在法治新闻报道中,就是要注意原被告之间的平衡。
在我国,传媒的法治报道对司法进步起到了一定
的推动作用,比如揭露社会问题,维护公民的知情权,促进法治、权利、正义观念的实施等。但二者在协调合作之余,表现更多的是冲突和对立,比如上述文章中提到的“媒体审判”现象等等。这种冲突在张志铭看来缺乏有序性和规则制度层面上的约束,一方面表现为媒体审判干扰正常的司法程序;另一方面,司法对传媒也采取排斥甚至打压的态度。
贺卫方认为,传媒如果超越了监督的合理界限,就可能导致侵犯司法独立,造成传媒而不是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的情况。比如,直呼犯罪嫌疑人为“罪犯”,把检方的指控当作实际发生的情况,无所顾忌地使用煽情的和各种带有倾向性的话语等等。③
司法与传媒关系严重对立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广东法院封杀6名记者事件”。④ 对此,贺卫方曾经亲自撰文予以批驳,因为“‘不能禁止新闻界报道在法庭上业已展现的事实’。这是现代普通法早已确立的准则,所谓司法独立,应当包括司法独立于媒体的影响。⑤ 这次封杀行为依据的是当年6月广东省高院会同有关部门下发的《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该规定的一些内容对新闻报道与司法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一些具体的界定,例如“依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对事实和法律负责,并且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等。他认为,司法权力是人民委托司法机构来行使的权力,要受到人民的监督、评判,怎么可以说不允许媒体进行独立的、不同于司法判决的评论呢?而且法院作为一个司法机构,它本身并不享有制定规则的权利,只有国家立法机关才有权利来制定调整媒体与司法之间关系的法律,所以广东省高院的这个所谓规定完全超越了司法机构行使权力的范围。
造成司法与传媒不正常关系的原因:
陈兴良认为关键是我国的司法独立性有待进一步加强;贺卫方认为是双方的职业化程度都不高所致;张志铭则分析了媒体因自身固有特性而产生的局限:报道者缺乏必要的法律训练;新闻求速,而案件的处理需要时间,具有新闻价值的案卷材料可能卷帙浩繁,一味求快,就难免顾此失彼,忙中出错;新闻报道倾向于把案件作为一个整体“事件”,更注重其概然层面,而非具体细致的事实层面;新闻报道即使关注具体事实,也更近似于常识意义上的“自然事实”或“客观事实”,而非经法庭确认、证据意义上的“法律事实”。
学者们认为传媒与司法之间的正常关系应是合作的而不是对抗的,“双方是一对难兄难弟,谁也离不了谁,需要搀扶着向前跑”(贺卫方)。关于如何平衡司法与传媒之间的关系,贺卫方认为首先是这两者的职业化程度都要逐渐地提高,其次是各自遵循各自的逻辑并且都要尊重对方不同的逻辑。张志铭认为在二者产生冲突之后,应该建立一个有效的、健全的机制来平衡与考量。这样的制度建立之后,双方之间的纷争就可以定性并且可以有根据地解决。
解决上述媒介传播与司法报道中存在的诸种问题,专家们一方面寄希望于渐进式的媒介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强调要重塑媒介的伦理道德,实现市场机制下的媒介行业自律和共同体意识。
学者们认为,由于存在许多体制上和传统文化上的障碍,新闻体制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新闻体制改革与中国的民主法制进程有一个同步关系,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针对当前出现的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滑坡现象,学者们认为这属于媒体内部的行业自律问题,应该主要是由市场来监督媒体,不需要出台专门法律进行规制,触犯法律可以根据已有的相关法律条文提起诉讼。“在市场机制的激励下,传媒业不得不自律,提升自己的职业化程度,形成自己的行规,否则就没有市场,就无法生存。在一个建构良好的职业群体中行规的效力有时候不低于法律的规范。”(贺卫方)
注释:
① 参见万兴亚:《陈兴良教授:刘涌案改判是为了保障人权》,《中国青年报》2003年8月29日。
② 参见张志铭:《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从制度原理分析》,《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
③ 贺卫方:《传媒与司法三题》,《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
④ 2003年11月2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广州海事法院、广州铁路运输两级法院下发了《关于禁止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粤高法[2003]252号,以下简称《通知》)。依据这份《通知》,从2003年11月20日至2004年11月19日,分属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3大报业集团6家报社的6名记者将被禁止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见金凌云:《广东法院“封杀”六名记者》,《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12月8日第45期。
⑤ 贺卫方:《为什么法院不可封杀记者》,《中国法律人》2004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