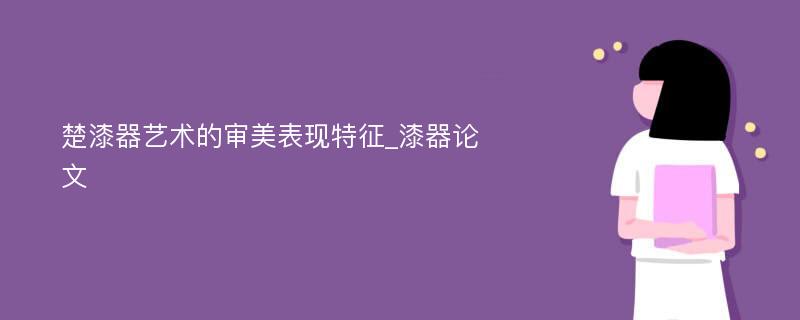
楚漆器艺术的审美表现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漆器论文,特征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楚漆器艺术以天然生漆为原料,髹饰在特制的木、竹、皮、骨等胎体上的集雕刻、绘画、装饰、髹漆工艺于一体的综合性静观艺术。历览迄今出土的数以千计的楚漆器,人们沉浸、神往于那些圆融贯通而又奇玮诡谲的器形,那些缤纷繁饰而又意味深长的纹饰,那些对比强烈而又浓丽斑斓的色彩,在叹为观止之余,人们免不了被那个时代楚人独特的创作情思所吸引,究竟是什么成就了楚国漆器艺术如此辉煌灿烂的历史?也许人们不曾想到,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和审美价值的楚漆器,在历史上只不过是与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用器具,它们或者是楚人的日常器皿,或者是为死者引魂守灵的陪葬,或者是具有其它精神性功能的工艺器物。在创作动机上,它们要么依附于某种宗教信仰,要么依附于某种丧葬习俗,要么依附于某种工艺装饰的需要,是典型的普通的工匠艺人之作。但正是这种民间创作,凝聚着更为普遍的楚民族文化心理,更为深刻地体现着楚民族的审美意识。从发生学意义上讲,它们是楚民族原始思维特质的精神逻辑顺序的显现。本文拟对楚漆器艺术的审美表现特征作一尝试性探讨。
列维·布留尔曾对“集体表象”作出如下解释:“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它们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情感。它们的存在不取决于每个人。”(注: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5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也就是说这个“集体表象”是一个民族处在一个时代中的艺术的原生物,它可以派生出许多亚形式,从而构成一个民族的多层次的、有机联系的审美观念群。楚漆器艺术正是楚人“集体表象”派生出的许多亚形式中的一种,其中隐含着深刻的功利目的,但同时也显现了某些审美意识。在一般的日常器皿、工艺等装饰性漆器中皆包含了楚人宗法、宗教以及巫术等精神性方面的意蕴,而在宗法、宗教、巫术性器具(例如丧葬用器)之中也包含着楚人装饰、美化意图的表达。我们对楚漆器艺术的审美表现特征的考察就以此为基点展开,着重对楚漆器的造型方式、纹饰体系、色彩观念进行透视。
造型:圆融贯通的构成方式
历史上的楚国是一个富于独创性特质的诗的、艺术的国度,氏族社会的光圈始终顽固地投射在它的身上。楚人对周围世界的审美观照和表现往往是采用直观的、想象的、甚至是神秘的巫术的方式去把握、去表现。因此楚漆器的造型不能不受到楚民族固有的审美心理定向和深沉积淀的影响,它们常常表现为以一种圆融贯通的构成方式去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雕刻与彩绘相结合。
我们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中常常可以感受到雕刻与彩绘相结合手法的雏形,这种造型方式在楚漆器制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如江陵马山1号楚墓的彩绘着衣木俑, 整体形象是雕刻与彩绘相结合形成的立体圆雕。其躯体与四肢用木板雕刻而成,五官仅雕出耳、鼻,而眼睛、口唇等细部则是彩绘出来的,特征鲜明,整体效果也较为和谐完整。雕刻与彩绘的结合使楚木俑既有立体形象的体积感,又有绘画般的笔墨情趣和色彩美感,能同时给人以丰富的审美感觉,使楚漆器艺术获得了那种单纯强调立体感的严格意义上的三维空间艺术所无法获得的艺术效果。
楚人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日趋完备的胎骨制作工艺,大胆地利用各种质材,如木、竹、骨、角、铜、皮革、脱胎等制胎。在这些质材中,木材因性能良好、取用方便,成为楚漆器的主要胎质。胎体的雕刻法也体现出一种圆融贯通的特性,有斫制、镟制、锯制、圆雕、浮雕、透雕等。镟、斫、挖、雕等多种手法的灵活运用,使器物的某些部分在雕刻中趋于精致化,也使楚漆器木胎的造型极富变化,对比因素丰富,形式感极强。楚漆器中有许多木胎雕绘的座屏、虎座凤鸟、镇墓兽、卧鹿等等,往往是采用圆雕、浮雕、透雕及榫卯结构、粘接工艺等综合手法制成的。江陵雨台山471号楚墓中的蟠蛇卮, 乃整木挖成,技艺精湛;雨台山楚墓中另一件漆器鸳鸯豆,豆身内壁挖制,外表雕刻,豆柄及豆座又采用镟制工艺;江陵楚墓中的“镇墓兽”胎骨制作,一般在面部用圆雕、浮雕手法完成,而器身则采用砍、削、粘接等工艺制作。在这个造型体系中,最具审美素质的是透雕。这种手法不仅以镂空部分的前后遮掩、虚实相生、明暗恍惚来造成一种丰富的层次感,而且依靠这些因素反复闪现而具有了灵动感,从而富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如江陵望山1号楚墓中的彩绘座屏, 透雕技巧的娴熟运用和榫卯结构的严整精密的处理,使本来就颇具神秘色彩的动物群雕更加神乎其神。雕刻技法中的斫、剜、挖、凿、镟、磨等手法对木质材料的加工可使自身特质逐步完善,在它们共同协调过程中形成了雕刻系统,把木质本身的各种优美素质按审美主体的要求显现出来。这样制作出来的胎骨,无须彩绘就已尽显意趣,彩绘后则更令人喜爱。
楚漆器的彩绘是在雕刻基础上萌生出来的兼具实用和审美的表现手法。出于适应功能的需要,必须对雕刻好的胎骨进行通体涂饰,这也是木质材的雕刻品出于防腐防渗防酸的功能目的,顺理成章地走向生漆彩绘的必然结果。髹漆的过程包括打底、上漆、彩绘三个步骤。打底、上漆只是功能意义上的表现,在底色上彩绘花纹、图案则是为了满足审美的要求而进行的。彩绘花纹大部分采用加油精制漆绘在脱水精制漆髹成的面漆上。脱水精制漆髹成面漆纯正、庄重、深沉,与加油精制漆绘出的明亮、鲜艳的花纹形成对比,相得益彰,获得了极好的装饰效果。
雕刻与彩绘结合是楚漆器重要的造型手法,其功能意义在于,绘在造型表面上的纹饰使二维造型方式和三维造型方式、色彩的绚丽和素面的淳穆结合起来。这样,由于彩绘本身比雕刻手法更为流畅松动,又使二维造型和三维造型之间的转换更为自由;绘制线条、色块本身的宽窄、刚柔、缓急等形体和力度的变化会增强或减弱雕刻手法所带来的某些造型因素,促使这些因素导向更为符合整体造型意识的方面。彩绘所带来的色彩光泽不仅使造型凭添一些更为优美的素质,而且由于色彩本身的刺激性强,当然就会增强器物和审美主体之间的关系,形成审美主体强烈的审美感受。
2.模拟自然物象的拟形器把动物造型与容器合而为一,使实用和审美和谐统一。
模拟自然物象,一方面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其面貌,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与作为容器之“容”的特征合而为一,这种融通性成为楚漆器艺术造型的一种追求。楚人对造型整体各部分之间以及整体的转折关系、起伏关系、与容器的性能关系,不仅凭他们敏锐的感觉来处理,而且依靠一定的理智来调整。正是这种“完形”的结构观念和敏锐的感觉结合起来,才使得楚漆器艺术的造型不仅在外在形体上洋溢着一种活泼的生命力,而且依靠构成的融通性而具有坚实的稳定感和良好的实用性能。
彩绘鸳鸯漆豆是模拟自然物象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器身是一只扭头缩颈、敛翅收足的鸳鸯,被笼统地概括在一个近似鼓形的体积内,形态憨厚又不失生动。同时又很好地保留了豆的实用功能。豆座的造型更富于诗意,如倒扣的喇叭,豆身与豆座联为一器,构成上粗、中细、下粗的起伏轮廓。如此造型具有升腾感和流动感。此外,双虎漆盾、蟠蛇卮等漆器也都是模拟动物形象的融造型于实用器具之中的经典之作。这类器具显然是实用和审美交融的创造心态的物化形式。这种创造心态往往会主动地从对象身上寻求既有满足实用性功能质所需要的东西,又能从其中抽出和谐的形式结构,使创造心态有可能在心理视象水平上完成造型审美两种特质。也就是说,从原型上抽取出的神态充溢于和谐的形式上,而整个器身在模拟原形的同时,又使“容”的功能作用表现得相当完备。
凤形双联杯是反映上述致思倾向的又一件拟形器。整个器形是凤鸟负双杯状,在凤鸟的双翅部位,制一对桶形杯,双杯有孔相通,便于器中之物融通无碍。凤鸟昂首挺胸,口衔一珠,尾翼翘起,可作手柄之用。最为叫绝的是两桶形杯之下各有一只憨态可掬、正在顶抬杯底的雏凤作器足,弥补了器物的稳定感,又有强烈的装饰效果,增添了喜庆祥和气氛。此杯以凤鸟为原形,而凤鸟是原生鸟图腾的演化神物,远古的图腾崇拜,在春秋战国时的楚族中已转化为更为深沉的集体无意识,楚族后裔用图腾物象作创作题材,其趋吉意向是不言自明的。在楚漆器的大家族中,以凤鸟为母题的造型和纹饰,大都寄托着楚人美好愿望,皆可视作楚人趋吉意识的产物,此不赘述。模拟自然物象的造型方式也就是古人所谓的“观物取象”,“观物”是观察方式,“取象”是视觉思维方式,又是造型的要求和中介环节,由此而“象形”而建构,能很好地将动物形象与容器结合,融实用与审美于一体,使楚人生活的广阔场景的某些部分借这种造型凝固而得以保存下来。
3.综合自然形体的造型方式,营造神秘、虚幻的精神氛围。
楚人“无羁的想象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形象构成方式。他们常常把来自现实的若干自然形体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组合起来,并赋予某种神秘的特定的含义,这些自然形体在局部的表现形态上虽然仍然是实在的,但新的综合体已经超越了各形体的自然性质,从而带上了浓郁的虚幻、神秘色彩。在数以千计的楚漆器中,此类漆器造型非常突出。例如“镇墓兽”,兽的造型就综合了多种动物如天禄、麒麟、辟邪的形象,然后将有角类动物的角组合,巧妙地利用角的枝桠张扬的向上伸展、向四周扩散、辐射的抽象形式意味以及扑朔迷离、灵动多变的视觉印象来渲染神秘的氛围,以加强“镇墓兽”这一神怪的超自然力量。如江陵天星观1号墓的一件双头镇墓兽, 其造型方法是将相同质的自然形体以怪异的方式组合起来,雕成龙面的背向的双头曲颈相连,颈下端合而为一垂直地插入覆斗状的棱角分明的方形底座正中。恣意夸张的龙角与简明单一龙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四棱柱的龙体与稳重厚实的方形底座构成一个相当神秘的氛围。角的张扬、龙体的灵动与方形基座沉实的体量相互生发,共同显示强大的动感和力度,让人真实地感受到这个虚幻神怪的魔幻力量。
虎座凤鸟是楚漆器中常见的造型。这类造型可分为虎座鸟架鼓和虎座立凤两类。其造型原则一般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原形的质在形象的整体上加以混合,由于不同质的混合,使形象的造型具有了两种以上原形的因素,虚幻性的审美氛围得以显现出来。虎座立凤是楚漆器中最具“集体表象”特征的作品。凤鸟造型一般是长颈、长腿、曲颈昂首、尾翼短小且上举、体态呈流线型,双足立于一只伏虎背上,双翅作展开状,背上还插上一对枝桠张扬的角,使整体造型产生轻灵的升腾感和虚幻感的同时,显然也为欣赏者创造了一个无限辽阔的意象空间,使人感到神秘莫测。楚墓中随葬虎座立凤,据考证意在引魂升天(注:参见张正明《楚文化志》。),从其审美意象看也许不无道理,至少反映了楚人对生死的看法。虎座鸟架鼓在造型上与虎座立凤类似,只不过虎座鸟架成对相背而立,凤背无角,代之以鼓悬挂其间。虎座凤鸟漆器的意象组合都带有一种怪诞不经的虚幻色彩,某种难以确知的神秘意义支撑起整个虚幻的形体。是楚人对国家强盛的祈祷,还是对冥冥之中掌握人的命运的某种神秘力量的恐惧和崇拜,抑或是对某种超自然生命力的向往?也许就在这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中使人们领略到了一种神奇的魅力。
“镇墓兽”、虎座凤鸟等漆器所表现的神秘感、虚幻感是楚民族艺术意志的客观化,它反映了楚民族“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此所产生的“尊敬、恐惧、崇拜”等情感。综合自然形体是人类早期艺术常用的手法,它将某一物的自然属性附会到主体物的身上,旨在强化主体物的神性,体现了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中外神话传说中许多怪兽往往都被赋予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它们实际上是各种意象混沌综合起来的结果。布留尔称这种意象综合为原逻辑思维,他认为这是原始民族的思维特征,并且认为原逻辑是一种不像我们的思维那样必须避免矛盾的思维(注: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5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原始艺术就是这种原逻辑思维的产物,它们完全打破各组合物体的自然性和逻辑性,从而使作品带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当然楚漆器艺术决不是原始艺术,但在其审美效果的追求中,楚国工匠艺人却很好地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思维特质。
4.因材取象,使艺术形式尽可能地依附天然形貌。
楚人极善于因材取象。许多楚漆器多为因势象形之作。例如木雕辟邪就是依据根质材料的天然形貌而创造出来的代表作。楚人凭着独特的灵性和对自然生命形态的体察,采用一支完整的天然树根雕刻成辟邪,其抽象感极强。这件辟邪除头部雕刻成具象明确的虎头外,四条长腿依树根的天然分叉而伸开,右侧两足在前,左侧两足在后,其游走扑腾之姿妙趣天成。四足的如此分布看似矛盾,然而由于树根本身自然弯曲成反“S”形,楚人根据空间透视效果,利用了这一特性, 使这一形象生动自然,全无别扭抵牾之感。这种依据质材料天然形貌的巧妙加工,看似是一种最简便的呈形方式,且对主观想象有一定限制性,使构思似乎局限于材料的天然形态上,而实际上因势象形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灵活性,因为质材本身的千姿百态的天然形貌常常能诱发人的灵感,使人产生偶发性构思。如何融通质材的天然形态使之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从而使客观的无生命之物含蕴无限丰富的生机和意趣?楚人在木雕辟邪的造型上可以说作出了完美的回答。
纹饰:“有意味的形式”
作为楚民族文化心理在器物上的投射,楚漆器纹饰生动地记录了楚民族生存活动的连续性篇章,其深度意蕴所指一直指向楚民族“永恒精神的永恒往昔”(荣格语)。从原型批评和原始思维的角度来看,楚漆器上的纹饰的神秘、虚幻性特征很可能与沉积在楚人心灵和思维深处的巫术观念和原始宗教意识有关。因为在原始先民的集体表象中,与原始人现实生活相关的许多自然物象都被他们赋予一定的神性,即“万物有灵”。列维·布留尔把这种精神状态归结为一个特别的定律,即“互渗律”(注:“互渗”是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使用的概念,指人在并无必然联系的事物之间感到有神秘的联系的思维特点。)。这个定律是以原始意识在极其多样的人和物之间确立的神秘关系为基础的。由于“互渗”观念的影响,原始人似乎可以听命于一草一木之消息,国运也可以维系于一吉兆纹象,并由此而引发了一整套天命符应体系。而纹饰的表述形式正是基于对自然物象神化的天命符应体系的,神化和纹化都是出于一个共同目的,即对人自身生命生存的保佑和祝福,这是先民生存努力的一种形式。在远古先民的卜兆行为中特别突出地表现出对“纹”的迷信崇拜心理和特殊观念情感,成为其后蕴贮在一切装饰纹样中的生命生存意识。他们相信,由纹样装饰的器物富有神性,能给自己带来好运。因此纹饰就成为生存的一种保证和象征,具有了生命的意义。也正是在这种观念意识的支配下,人们能够克服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热衷于器物装饰,把纹样饰满器身。这绝不仅仅是为了表现,而是为了与生存相关的神圣目的,这就是纹饰的根本动机(注:参见李砚祖《纹样新探》,《文艺研究》1992第6期。)。 当然我们不能说在审美表现体系上已经发育得相当完备的楚漆器纹样就是这一原始动机的体现,但我们却可以从楚漆器纹饰的神秘意蕴中受到某种启示:浸润过炽盛巫术意识的楚人在“观物取象”追求形式美的过程中,被布留尔称之为原逻辑的思维不能不渗透到楚人的创作心态中去,这至少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由此看来,楚漆器纹饰的神秘性、虚幻性审美特征既是楚人观察、理解和把握物象的结果,同时也是楚人原始思维中“集体表象”世代相传、积淀的结果,此二者的相互渗透,必然要化为一定的“有意味的形式”。
1.运用抽象、变形手法,体现楚味浓郁的装饰趣味。
楚漆器纹饰的一个很大特点在于,它把一种自然原形的各个因素经过主体审美心绪的规范化处理后使之符合某种空间的秩序感。在这一过程中,变形和抽象是常用的两种手法。这在规则形器和不规则形器中都有所体现。规则形器所饰纹样指广泛绘于盘、案、豆、壶、奁、盾、耳杯等易于概括为规则几何形器上的纹样。这些纹样抽象化程度高,多采取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方式组合。直线纹、卷涡纹、圆点纹及各种凤纹、龙纹和蟠螭纹是最基本的构形元素。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变形,创造出回纹、波浪纹、孤边三角带涡纹、连云纹等,它们变化多端,少有雷同。楚人似乎特别钟爱回纹,几乎在每件漆器上都能找到它的影子。这可能是模拟了青铜器上蟠虺纹、蟠螭纹、云雷纹并加以变形改造的结果。这些纹样单元多呈向心卷曲的卷涡,它们琐碎地并列重复着,在一个平面范围内,乃至在整个器身外表上组成细密的纹饰。尽管楚漆器的装饰纹样还有人物、动物等其它形式,但这种基本特征却是较为普遍地、主导性地存在着。例如曾侯乙墓内棺纹饰的鸟形、人形,其翅膀、犄角、手脚都呈回纹式的弯曲倾向。回纹不单独构成纹样,而是与其它花纹组合,有的在某一花纹内用回纹装饰,有的在某一花纹边缘地带饰以回纹,或将数个回纹相连,不同向的两个组成一对,再以二方连续的形式组成一圈,环状相连,前后呼应,大小均匀,间隔有致,其精密程度前所未有。长沙楚墓的狩猎漆奁,人与兽明显小于上下三条装饰带中的回纹,人、兽的动态也被限制在周围纹饰的规范和约束之中。彩绘盘、豆、耳杯上的凤纹的嘴、翅、尾、颈毛,龙纹的角、尾、爪等处都有回纹修饰,呈现出浓郁的楚风楚味。不规则形器主要是一些拟形器,此类漆器不易概括在规整几何形内,彩绘时必须根据所拟物象的皮毛结构来处理,花纹的组织则全靠创作主体随意发挥,但基本上都有现实依据,且在工艺制作过程中已形成一定的模式和规律。例如虎座立凤和虎座凤架鼓上凤鸟的纹饰,非常重视凤鸟各部位羽毛走向、大小、形状的差异,所有纹饰都经过严格提炼,象征意味浓厚,分布周密、谨严,恰到好处。也有一部分纹饰与现实差距较大,甚至不切实际,最终走向奇异和神秘。当然,此处的纹饰已不仅仅是表象的概念,可能负载着某种文化信息,蕴涵着更为深刻的精神的、观念的表达。例如“镇墓兽”上的纹饰就很难从现实生活中找到实物和它对应,让人难以理解,这些更加重了“镇墓兽”本身的神秘虚幻色彩。
在纹饰的处理上,经过变形使对象中主体强烈感受到的部分也即标示着存在方式的特征部分进一步趋于简括、单纯、活泼、灵动。经过抽象之后可排除对象繁复的外部特点,使杂多无规律的外部表现因素导致统一,符合空间的平衡对称感及整齐一律。经过抽象、变形之后,其整体意趣更浓,更有地域性特征和创意。这是楚漆器纹饰最突出的特点。
楚漆器上的纹饰,合理地吸收了商周青铜器、玉器上的那些兽面纹、蟠螭纹、云雷纹的表现方式,但已完全摒弃了商周器物中以兽面纹、蟠螭纹为主体,以细密规则的云雷回纹为底的威严、狰狞的程式化作风,而代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活泼轻盈洒脱得多的新风格,令人不得不佩服楚先民大胆支配传统的气魄和再造传统的胆略与智慧。因为这种新风格的产生,乃是将传统的怪兽、龙凤形象的分合转化,予以变形,再重新根据装饰、表现或象征的需要组合起来,造成全新的艺术境界和神秘情调。与青铜纹饰相比,楚漆器纹饰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彻底驱散了阴霾之后的云蒸霞蔚的气象。
2.重视线的表现,巧妙地传达出器物的节奏感、流动感、韵律感。
线条是最具抽象性和概括性的表现手段。观物取象,以线明象的方式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造型方式。以线条的组合和流转变化,概括地表现大千世界的美的形式和形式的美,使中国艺术在审美特征上与西方艺术相比大异其趣。线条能给人以空灵的立体感,是需要借助于主观精神联想补充的三维空间。线条概括物象的形态神情,能获得圆满的立体效果,这效果不在表现实在的形态上,而超乎形表之外,它产生于观赏者的头脑,是一种由主体精神补充上去的立体空间感。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线的艺术,正如抒情文学一样,是中国文艺最发达和最富民族特征的,它们同是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表现。”(注: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在楚漆器纹饰中,线条的运用是其主要的构形方式,纹饰的意蕴美、韵律美、节奏美和流动感全靠线条来传达。例如曾侯乙墓中鸳鸯盒腹部两侧的撞钟击磬图、击鼓舞蹈图,可谓是线条艺术的杰作。表现对象皆用简练流畅的线条来表现,粗线显得浑厚,细线显得飘逸。简练流畅的线条将万千气象尽显方寸之中。绘在漆棺上的一些线条也有同样魅力,线条本身也起到了装饰作用,有一种特有的韵律蕴含在其中,形象本身的美感和生气也通过这些线条的韵律得到充分的流露。
值得说明的是,楚人所运用的线条大多是曲线,对曲线的运用往往明显地胜过对直线的喜爱。这一特点在纹饰的表现上似乎格外明显,可以说重视曲线的表现和对流动感的追求是楚纹饰又一大特点。楚人在运用直线和曲线时常常寓直于曲、曲直分明而又互为一体,含有较多理性成分。同时这种曲与直的结合又能将人引入一个奇异的境界。例如在两个回纹间以直线相联,再变换方向前后连贯,形成迂回、周密而有序的路径,引导观者的视线,从而展开丰富的想象。通过流畅而富有节律感的曲线可以巧妙地传达出充盈在宇宙万物间的运动感、律动感。这种线气势非凡而又优美无比,与“天人合一”的思想相一致,常常用来体现生命运动的本质和大自然中各种神秘的力量。这种线能曲能伸,时疏时密,与动势同在,充满生机;它简洁洗练,但不纤弱,反映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风貌。
楚漆器纹饰中,这种以流畅曲线传达出来的运动感显得更为鲜明、强烈,更加活跃生动,也更富于变化。这与楚人对生命运动形式的喜好,对生命活力的崇尚有关。纹饰中流动感、韵律感、节奏感极强的艺术图式可以说是与楚人一般精神状态同形同构的一种视觉样式。那种节奏轻快、如行云流水般的音乐感,那种飞扬流动、意气风发的舞蹈感,正是楚人乐观开朗、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的视觉形式的显现。
3.灵活随机地运用各种表现手法。
楚漆器纹饰的表现技巧是对前人艺术经验的总结和自身艺术探索的大胆尝试。他们善于灵活地将各种表现要素巧妙地组合起来,诸如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对称、同心圆构图等等都是最基本、最普通的手法。除此之外,环带花纹的装饰、正负形的借用、变异形的组合、虚实线块的搭配在楚人那里也同样运用自如,甚至作了超水平发挥。环带花纹的装饰在规则形器上运用较多,几条环形线可以将整个器身划分为几大区域,线与线之间可以看成另一条环带。荆门包山楚墓的彩绘漆奁的聘礼行迎情节画就是一条出色的连环画式的环带纹饰,以图案绘画法记叙了楚贵族婚嫁出行场面,艺术性之高令人称奇。正负形的借用则可利用底色以外的一种色漆制造出奇异变幻的视觉效果,模糊了底色与表色、正负形的界线,达到前所未有之高度。如凤鸟纹漆盘内壁中心的圆形主题纹样,其外围是红漆地上四只卷涡状黑色凤纹,而随着凤翅的延伸,纹样中心渐渐出现四只黑漆地红色凤纹样,这显然是有意留出。变异形的组合主要针对龙纹、凤纹等具体形象又经过夸张变形的纹样。其中保留了某些象形的部分而使人心领神会。其表现方法是采取二方连续、四方连续或对称的组合方式,不仅仅是借用,还采取加绘、夸张、变异等方法,营造出神奇、瑰丽、理想化的世界,虽不符合现实,但能满足视觉需求。如变形龙凤纹漆盾,虚实线块的搭配避免了单一线块的出现,线与块一虚一实、一静一动,搭配得当,能相互映衬。所有线条均依赖块面的存在而存在。如将三角形一角或两角绘成卷涡纹,块与线并置排列,也能起到虚实相生、动静结合之效,还能减少单调乏味感。如果龙凤面积较大,则绘象征皮毛的花纹于其上,线块兼有,虚实相生。对虚实的处理还体现在纹样的透气性上,如在大面积实心花纹中开窗以露出漆地,或常在圆形、三角形色块中留出点状,如此能减轻花纹之重量,达到轻盈、律动、飘逸之视觉效果,避免了沉闷感。此三种方法在楚纹饰中或单独使用,或相互渗透,充分制造和利用各纹样彼此间协调,“幻象与真象交织,抽象与具象并用”,这是楚人追求自由精神境界的产物,也是楚人自然观、宇宙观之反映。
楚漆器纹饰主要采用平涂填充和线条画相结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平涂填充一般有两种方法:点缀和穿插。点缀方法的运用是由于器表本身已髹上了黑色或红色的底漆,不便于过分追求繁密,只需根据审美需要和器物的形制来活跃大面积底色,强烈的色彩对比使器表装饰效果更加醒目。如曾侯乙墓的漆木鹿身上虽然仅画了一些分量很小的梅花瓣纹,却让人感觉其通身都有装饰。穿插也是楚漆器纹饰的常用之法。楚漆器上的纹饰,转折起伏较大,灵活的线条可以交接穿插于较大空间,使上下左右联系、呼应起来,甚至显得错综复杂,难于分辨,以变形龙凤纹为最。如曾侯乙墓漆器上大量出现的蟠螭纹既活跃了器面又维护整体美。线条画一般是用毛笔彩绘出来的,其线条显得格外流畅生动。有些变形龙凤纹,与其说是龙凤的变形,不如说是卷曲的云、雷、水波等易于产生运动联想的形态,体现出了楚人崇尚生命的运动活力,强烈向往自由的文化精神。
楚漆器上这些彩绘纹饰,既非对大自然的单纯模仿,也非单纯的自我艺术表现,而是一种自由生命形象的创造。虽然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和“情感的符号”,它们可能是远古楚族人图腾的孑遗,也可能是某种神秘狂热的宗教情感的宣泄,但它们穿透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时空所展示的,则首先并不是它们曾经有过的象征意蕴,而是一种生命自由精神,是自由生命之本身。(注:参见皮道坚《楚美术论纲》,《文艺研究》1994年第4期。 )这乃是楚漆器艺术为我们创造的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也是它能让我们最先把握的一种感性特征。
色彩:神秘玄远的生命观念
楚漆器大多色彩绚丽,红与黑是其主色调。红色鲜明发散,黑色深沉内敛,红与黑互衬,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红与黑搭配也是髹漆工艺的传统之法,《韩非子·十过篇》有“墨染其外,朱画其内”之说。红色活泼跃动,黑色沉寂冷静,二者结合,对比强烈,大方庄重,因而具有浪漫情怀的楚人以红、黑二色作为楚漆器的基调。然而楚人无时不刻在追求着新奇和变化,在色彩的表现上也是如此。即使同一纹样,他们也会采取不同色多层勾勒之法来达到目的。为了追求色彩斑斓、富丽堂皇、精工高雅的格调,还把黄、蓝、金、银诸色并用,使漆器亮丽绚烂。他们出色地运用黑色所具有的调和性,将众多饱和暖色调和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倾向。注重色彩的整体统一是其基本原则。不论多么复杂的色彩搭配,都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完成的。楚漆器中为什么大量使用这两种颜色呢?这一方面可能与楚地红黑二色颜料的取用特别方便有关;另一方面还可能与楚民族的文化积淀有关。有的文化史学者如此解释,说是由于楚人崇凤,楚俗尚赤的结果(注:参见张正明《楚文化志》。)。崇凤,是因为楚人以凤鸟为祖先祝融之化身;尚赤,也与楚人先祖祝融氏在远古之世掌观象授时、燔燎祭天之职有关。楚漆器以红黑两色的强烈对比为基调,可以使彩绘纹饰达到“生成天质见玄黄”之艺术效果。在此基调上再敷陈五彩,深邃、幽远、虚玄、斑斓、缤纷、眩目;深沉的哲理感与愉悦的感官刺激、心灵的震慑与感官的享受奇特地交汇融混在一起,产生了惊采绝艳的色彩效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楚人的远古图腾观念和祖先崇拜意识。
楚人先祖祝融氏是高辛的火正,是司火之官,火正的职责主要有三项:一是观象授时;二是点火烧荒;三是守燎祭天。可见,祝融是和火相联系的,生当火官之长,死当火官之神,楚人祖先崇拜的实质是对火的崇拜(注:参见张正明《楚文化志》。)。火能带来温暖,带来光明,带来维持生命所必须的能量,从而火与生命之间关系便密切地联系起来。同时,火是红色,维持生命的鲜血也是红色的,由此推论而及,楚人对火的崇拜又可以旁及对生命的崇拜。在楚先民的观念中,一切非生命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第一个被楚先民看做是生命体或生命现象的可能就是火。这不但因为火在形态上与人的生命十分相似:火燃烧时红色使人想到代表生命的血,火的燃烧(红色)和火的熄灭(黑色)使人想到出生和死亡,火焰的飞跃跳动使人联想到自己活动的身体等等,还因为火的利用是人类生存方式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火不仅在寒冬和黑夜明亮温暖自己的“家园”,而且它也是人类猎取加工肉类食物和“刀耕火种”的生产工具。火之于人既如此重要,楚先民对它产生一种热爱、崇敬、感激甚至畏惧之情,也就不足为怪了。根据列维·布留尔的“互渗”理论,火的意象与生命意象“互渗”,这一观念积淀在楚先民的“集体表象”之中以至于代代相传。因此在楚艺术中楚人对红黑二色的偏好无疑表现了一种原始冲动,与其说因其颜色(燃烧时呈红色,熄灭时呈黑色)而使楚人觉得美,毋宁说它之所以特受重视,就在于它是生命的象征,表明了楚人对生之向往和对死亡的回避。
楚人特别偏好红、黑二色,从楚漆器色彩大范围使用红、黑两色作为主调的情况来看,其象征的内涵是不难发现的。红色在造型符号中的稳定性除了视觉选择的因素外,还主要来自楚祖先的生存行为和自然的恩赐,从而导致红色在视觉经验中的稳定性。因此,红色形成了稳定的象征功能,成为主体英勇、悲壮、激烈、旺盛等精神状态的标志和温暖、喜悦、圣洁、庄严的象征,红色的象征内蕴被一代代楚人很好地继承下来并运用到他们的日常的创造行为中。
黑色在楚人的意识里,其象征意蕴或许是作为红色的背景、支撑甚至对立面出现。在楚人的生存观念中,对自然压迫恐惧的主要部分是对生命生存的对立面的恐惧,即对死亡、对黑暗的恐惧。黑暗对生命构成的威压对楚人来说可能是神秘不可知的。黑色具有深、广、高、大、密的意义,这些意义都表现出黑色的神秘不可知、不可企及的神秘特征。因此,在楚人先祖那里,黑色很可能是被作为一种具有崇高性质的色彩而出现的。
楚漆器上以红、黑两色为主色调的色彩表现观显然是楚人先祖原始思维特质的延续。从它们所提供的视觉样式来看,是基于一种抽象的生存意识。楚人在色彩表现方面的艺术追求倾向,与其圆融贯通的造型方式,追求以富丽精工的纹样传达“有意味的形式”的纹饰方式在本质上一致起来,其共同的心理特征和美学基础是超越静观的模拟,超越视觉表象的构成,把不可见的东西借色彩创造性地表现出来,从而使我们从中领略到楚人健康乐观的生命意识、丰富的情感创造和崇高的审美理想。
楚漆器虽然以红、黑二色为主调,但其总体的色彩效果却是浓丽斑斓、惊彩绝艳的。楚漆器普遍施用了红、黄、赭、蓝、灰、绿、黑、金、银等色,绘出了繁缛的卷云纹、漩涡纹、蟠螭纹、龙纹、凤纹、回纹、蝶纹等,有“五色杂而炫耀”的美感。一般说来,不规则形漆器比规则形漆器用色多,几、案等家具用色较单纯。例如漆奁、木雕座屏、彩凤双联杯、鸳鸯豆等多以黑漆为地,绘以朱红、枣红、灰绿、翠绿、金黄、棕黄、银白等色,精工富艳,浓丽斑斓,幽深玄妙。它出色地运用黑色所具有的调和性,将众多饱和暖色调和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倾向。即使是同一纹样,也采取不同色多层勾勒等方法来达到目的。但不论多复杂的色彩搭配,都是在色彩整体统一的基本原则下完成的。
综上所述,楚漆器艺术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里产生的中国工艺史上的明珠,它表现了楚人非凡的艺术智慧和独特的创造精神;它是楚人心灵历程和楚国时代精神的生动形象的记录;它凝聚着楚人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具有代表着中原礼仪文化的青铜器艺术所罕有的活力和灵性。楚漆器艺术在其造型、纹饰、色彩方面所表现出的那种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那种神秘、虚幻性的审美特征,正是楚人卓越的艺术表现力和其具有原始思维特质与精神逻辑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结果。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创造情思使楚漆器艺术具备了原始社会无法企及的工艺水准和文明社会难以袒露的艺术真情,这将给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里的每一个艺术工作者以无尽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