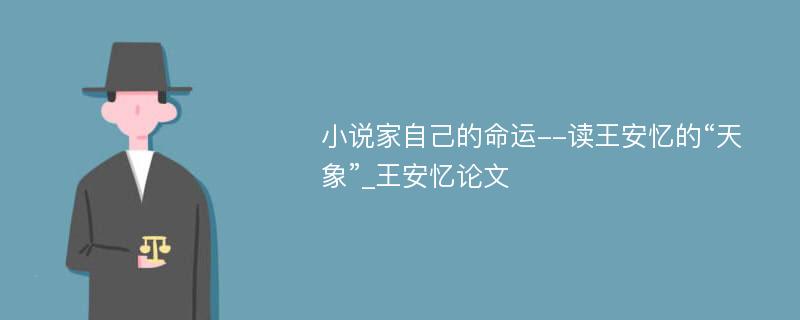
小说家自己的命运——读王安忆《天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己的论文,小说家论文,天香论文,命运论文,王安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小说的最后时刻,活跃着那些小说家自己的命运
大约十年前,在关于《长恨歌》的一次访谈里,王安忆就曾把写作比喻成刺绣:“我觉得创作其实更像做手艺的人。我小时候很喜欢绣枕套,我觉得创作有时就像做绣花工作,今天一朵花明天一朵花的,但整个布局心里早就有谱了,虽然不是十分的明确。”这样的思考萦绕于心,加之早年间对顾绣的留意,积累到一个恰当的时机,便有了《天香》——造园,绣画,都是在隐喻写作这回事。写作本身成为小说的主题,是20世纪以来的一个趋向,这与所谓后设小说的技巧无关,而是关乎小说家对自身的思考。“在小说的最后时刻,活跃着那些小说家自己的命运。”我们可以试着把罗兰·巴特的这句话移到王安忆身上:在《天香》的最后时刻活跃着的,也正是小说家自己的命运。
工匠/小说家
创作小说是一门手艺,小说家是一个匠人,这在王安忆,绝非一种浮泛的隐喻,而早已是自明的真理。它暗暗指向两个传统,一是诗学的传统,在古希腊,“技艺”(tekhne)一词,即用来表示按照固定的规则和原则从事生产,而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将写诗也视作如做鞋一样的制作或生产过程;二是劳作的传统,只有通过匠人一般的艰辛劳作,并且是连续性的,才可能有好的写作,这几乎是19世纪以来伟大小说家的共识,巴尔扎克就曾抱怨,“当只有一两个小时的空闲,是绝不可能工作的”。也正借了对这两个传统的个人理解和汲取,王安忆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小说创作的“四不”: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风格化;不要独特性。在文学和理想被打压之后的时代,她致力要对抗的,不仅是残存的批判现实主义那套“典型”美学,还包括方兴未艾的种种先锋美学。这“四不”即便在今天,对于小说作者也嫌苛刻,但王安忆就要这般将自己逼得无路可进,好返身退回讲故事人的行列,在那里汲取生机。
狂暴的必然伟力伴随极度的偶然惊奇,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互补共生,善恶美丑的平等相处,诸如这般的造物主品质,却不属于王安忆心目中的小说家
王安忆愿意做个讲故事的人,“现在和将来我都决定走叙述的道路”。叙述的当然是故事,但在王安忆这里,这故事不再是民间的口口相传,也并非来自远方,而仅仅是小说家主体的精神投影。
所以就有了“心灵世界”的提法。王安忆之“心灵世界”自有其特殊性,这特殊性却不在于脱离现实,不在于“心灵世界”这个名词上,而在于附加在其前面的动词和代词。这个动词是“制作”、“构造”抑或“筑造”,在王安忆的词典中,它们毫无贬义,几乎都等同于“创造”;这个代词是“一个人的”,这小说,这心灵世界,是小说家一个人的世界。这两点都非常耐人寻味,可以看出来,在王安忆对小说家的理解中,处处都暗含着“一个工匠”的喻体。
更具体一点,在致力思考写作和刺绣这门手艺关系之前,王安忆喜欢的譬喻,是“建筑”。她在复旦的课堂上援引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中的话:“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材料当然是很真实的,但却根本不是一般所公认的整体,而是一摊杂乱无章的东西,作家对这摊杂乱无章的东西大喝一声‘开始’,霎时只见整个世界在开始发光、融化、又重新组合,不仅仅是外表,就连每一粒原子都经过了重新组合,作家是第一个为这个奇妙的天地绘制地图的人,其间的一草一木都得由他定名。”随后她进一步予以解释:“就是说这个材料世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在我们眼睛里不是有序的、逻辑的,而是凌乱孤立的,是由作家自己去组合,再重新构造一个我所说的心灵世界。”
我感兴趣的,不是纳博科夫对小说的理解,而是王安忆对纳博科夫这段话的理解。仔细琢磨一下纳博科夫的原话和王安忆的解释,会发现之间暗自有一个极大的跨度。
在纳博科夫那里,作家只干了三件事:大喝一声“开始”,绘制地图,为每一件事物定名,而材料的发光、融化、重新组合成奇妙新天地的过程,具体究竟如何运作,由谁运作,纳博科夫对此是沉默的,犹如神对造物七日的细节是沉默的,在这段明显模仿《圣经·创世纪》的话中,暗藏着一个“小说家即造物主”的隐喻,造物主不仅创造出必然和确定性,也为无数的偶然和不确定留出了空间,比如夏娃会偷吃禁果,又比如该隐会杀死亚伯,都不在其预想之中,世界万物有其自行发展的力量,造物主只设置规则,并不干涉每一件事的发生,小说家亦然。
狂暴的必然伟力伴随极度的偶然惊奇,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互补共生,善恶美丑的平等相处,诸如这般的造物主品质,却不属于王安忆心目中的小说家。在王安忆这里,造物主从天上来到人间,转身成为一个精益求精的工匠,从草图到成品,他严格掌控每一道程序,每一个细节,每一声欢笑每一滴泪水,在一个丧失理想的现实世界外,他努力要建成一个按照理想蓝图设计的心灵世界。
一个美好的乌托邦。一个可怕的乌托邦。在各色各样的乌托邦里,有一点是相同的,那便是只允许有一种心灵的存在,无论其来自小说家,抑或哲人王。
造园/格物
要写顾绣,先要造一座园子,那园子唤作“天香”,来自古籍出版社赵昌平先生的提醒,南宋王沂孙的《天香·咏龙涎香》。那是首咏物词,而王安忆写小说也立意格物造物,这是相合之处;然而王沂孙志不在物,他是满怀的生命疼痛需要找一个实物安放,王安忆却当真要格物造物,好来安放她心仪的旧时女子,此为相悖之处。
格物甚难,因先要弄明白物之理,而世间有万物,天香园虽是小世间,举凡园林、木石、器物、制墨、书画、美食、花草、节令……少则有百十种物事要去一一琢磨,但这又不算难,因为还是知识。王安忆是极认真和用功的人,在和杂志编辑就《天香》作品的对谈里老老实实交代:“基本是写到哪查到哪。写到哪一节,临时抱佛脚,赶紧去查……其中那些杂七杂八的所谓‘知识’,当然要查证一些,让里面的人可以说嘴,不至太离谱,因生活经验限制,其实还是匮乏。”好在还有赵昌平先生鼎力,一一帮忙查缺补漏。种种这些“造园”时的局促、匮乏、尴尬,王安忆毫不讳言,这是她为人极好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对于知识,她本就没有百科全书派小说家的热诚。况且对于百科全书式小说谈论的知识,我们一直有误解,对此张大春有一个极好的说法:“百科全书式小说的书写传统,是发现或创造知识的可能性,而不是去依循主流知识、正统知识、正确知识、真实知识甚或知识所为人规范的脑容量疆域,而是想象以及认识那疆域之外的洪荒。”这一点,王安忆并没有多少体认,她只是很素朴地遇山开道,逢河搭桥,不会就补,不懂就问,错了就改。在她心里,小说家所需要的知识,就是主流知识、正统知识、正确知识、真实知识,也正由此,她自然就会觉得,对小说家而言,知识并非见功夫的地方,小说家是要筑造一个自己的心灵世界,而这些知识,这些个物,不过都是材料,甚至不过只是黏合剂。
倘若物只是材料,格物只是明白材料的正确知识,那么在如今这个资讯丰富的时代,大概没有什么物是不能被迅速格出的。然而王阳明对着竹子格了七日,大病一场,却并非因为当时人对竹之物理一无所知。这又是为何?
且不要上网搜索,因为搜索出来的,也还是知识。
胡兰成《中国的礼乐风景》:“中国原来的教育方法是出自汉民族的智慧,即孔子说的仁知二字,仁是感、是格物,知则是致知,感而知之,故无论学哪一行,皆是师少教,要你于无教处亦自己会得看风头颜色,感而知之。而且学无论哪一行,都是一个完全,如木匠陶匠的学徒要扫地捧茶敬师敬来客,虽一艺亦是成于世事的全面,所以学会了制器,制的一几一瓶皆有人世之思。因为中国文明是一统的,一器亦有人世之思,所以木匠陶匠二十岁出师,便有质朴而深广的人格。”
关于格物,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本来想引个意思自己讲,但终究觉得还是先一字不动地照搬过来,更显得对得起人。格物并非只是知道些物的正确知识,而是对物有所感,“感而知之”,无论哪一行,哪一件物事学问,都是如此,是生命先对此有兴动,有感应,那些知识才能进入你的生命,化成你的人世之思,然后随你制作还是创造,是模仿还是虚构,都能得一个完全。
王安忆《天香》笔致极好,只是作者与天香园内外的不少人、物相知尚不够深,本来,假如不先把格物认作知识,也许写着写着,慢慢就和这些人、物有所感应,从而感而知之,那也说不准,因为“好文章是随着写作一路明白过来”(胡兰成语)。而最后明白过来的,是自己。瓦莱里讲:“如果每个人不能了解自己的生活以外的其他许多生活,他就不能了解自己的生活。”我们读小说,去了解另一些生活,原来是要据此了解自己的生活;写小说的人,其实也是如此。《天香》里,闵师傅问众姑娘,塑像最难什么?小绸说是眼睛,因为里面要有精气神;希昭却说是衣裥,因为要有风。闵师傅打圆场,说眼睛里的精气神是人为,衣裥里的风是天工。而写小说,造一座天香园,进而筑造一个心灵世界,却也要知晓有几分属于天工,那天工就是万物的风,呼呼地吹向自己。
但退一步讲,这天香园即便有百般的不真切,它依旧能建造完成,却因为里面有两样还是真的:一样是刺绣;一样是闺阁。
绣画/制物
“天香园绣”,始作俑者是闵女儿,但到了第一卷第6节才露面,这是作者操控大场面的耐心。闵女儿来自扬州织工世家,父亲闵师傅是花本师傅,掌管织工中最精密的一道工序,然而织工千万,单凭闵姑娘这点家底,似乎还没理由成为大匠。所以,还要安排一个人先在天香园里住下,那就是小绸。
小绸是申家长房柯海的媳妇,七宝徐家的女儿,徐家祖上南宋时就是王官,书香门第。小绸刚进天香园,妆奁中即有一箱书画,一箱纸墨,“不愧是世家,有文章的脉传”(《天香》第3节)。闵女儿有家传绣艺,小绸有世代诗心,只是这两个人就这么好好地搭在一起,要说能开创出什么新的绣艺,似乎还缺点什么。
因为大凡好的艺术,不单有世代家传,尚还要有此时此地这个人的心事。闵女儿是柯海胡闹时纳的妾,却令小绸大恨,再也不与他说话见面,柯海极爱小绸,对闵女儿原只是一时热情,如今闹得夫妻反目,又惭又恨,也就渐渐不理闵女儿,成天在外云游。于是闵女儿来到天香园,不但带来绣艺,也让这个园子增添了许多人世的寂寞伤心。
所以闵女儿开始捡起妆奁里的针线,支起绣花棚,绣自己的心事。小绸也伤心,在作她的璇玑图,只是比起闵女儿的绣活,这璇玑图显得做作,开不出什么大局面,小绸腹里有些诗书,但其实微薄,要化到绣里面,才算个好出路。小绸恼恨的是柯海,对闵女儿,其实并没有现代女子的那般不容,但她心性强,一定还要有一个中间人于其中周转。
柯海有个弟弟叫镇海,这个中间人,就要镇海媳妇来担当。她一定要是个心细又耿直的人,心细,才能照应两边的心事;耿直,才能担得下斡旋的粗活。这一段镇海媳妇发心让小绸与闵女儿互通款曲,写得极好,那些人世儿女的细密委曲,王安忆明明白白。
闵女儿和小绸两人通了气,却依旧不贴心,人与人之间怎么贴心?得要有一件珍贵东西同搁在两人心里。镇海媳妇活着,是闵女儿和小绸的桥,但桥总归还有两边,两边的人真要贴心,还得再把桥拆掉。所以要安排镇海媳妇早早病逝,让闵女儿和小绸心里所有的怨彻底爆发一次,哭完笑完,就真成了割头不换的姐妹。
大凡好的艺术,不单有世代家传,尚还要有此时此地这个人的心事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天香园绣”就此成名,但好归好,终究还是前人遗技,小绸和闵女儿虽还年轻,但心已老,要开出一个新天地,还要寄望下一辈的女子。
这下一辈成就大事的女子,还不能和自己太亲,近亲繁殖,总成不得大器,最有出息的徒弟,往往不属嫡传。各门技艺,都是如此。所以要让闵女儿和小绸都命中无子,几个女儿迟早出嫁,不算天香园里的人,还得再找一个女子进天香园,落地生根。这便再引出希昭。
希昭是镇海儿子阿潜的媳妇,镇海媳妇过世后,镇海遁入空门,阿潜是跟着伯母小绸长大,所以希昭其实和小绸关系很近,却又没有名分上的亲,若即若离,这就给了希昭自由,这自由也是一切艺术的营养。她可以迟迟不学绣,先学画。她之于天香园绣,是“见过于师,方堪传授”,所以能“集前辈人之大成,青出于蓝胜于蓝,推天香园绣而至鼎盛”(《天香》第41节)。
这一层深一层,一环扣一环,非得逐个拈出,才见得王安忆之细密周到,且看她调经治纬,把对小说这门技艺的体会经营成天香园绣画兴盛的故事,一笔一划,宛若一针一线,有现实的底本,亦有内在的逻辑。
对写实的偏爱,对逻辑的强调,王安忆一贯的这种小说美学,恰恰与绣画这件具体的手艺密合。刺绣都先有画本,针线也自有程序,增减不得,也想象不得。刺绣属于女红,《礼记·内则》中说:“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紃,以供衣服”。“婉娩听从”四字,是古时的妇德,也是女红的根本,所以举凡纺织、缝纫、浆染、刺绣、编结、剪花,都是有样学样,不能逾矩生造。刺绣虽是衣裳宽裕之后的闲活,也还是如此,希昭绣画,以及后来的蕙兰绣字,都还得依仗现成被认可的书画,不能像男子那样,自由想象,无中生有。旧时的士大夫,在政治高压下常选择作咏物诗,而旧时的家常女子,则唯有制物以为诗。因她们永久性地生活在这样的高压下,那些才华灵气,是要在婉娩听从和家常器物中挣扎出一个向上的呼吸空间。
这制物的空间逼仄,条条框框无数,于万般不自由中,却仍留有两条自由之路,一是工夫,一是选择。闵女儿绣件棉袍,乐意费去二三个月的光景,因为存着要与小绸好的心意,这是工夫:希昭绣四开屏画,精心挑了“昭君出塞图”做样本,暗藏对阿潜远走的埋怨,这是选择。
理查德·罗蒂曾经断言:“一旦失去言论自由,创造能力势必枯竭。”然而,在古老的中国,习惯失去言论自由的人们,却每每能化相克为相生。此中的秘诀,王沂孙晓得,天香园的绣史们晓得,而《天香》的作者呢,或许也晓得。
因她们永久性地生活在这样的高压下,那些才华灵气,是要在婉娩听从和家常器物中挣扎出一个向上的呼吸空间
设幔/生意
《天香》选择闺阁中的女子作为主人公,却并不在爱情上落墨,因为旧式中国人于婚前男女情爱之外,更重婚后家庭人伦之爱。王安忆自己也曾有言:“爱情只是很小的故事,爱情背后有很多很丰富的故事。”正是她身为中国人的一个体认。
《天香》写了三代女人。第一代的小绸、闵女儿和镇海媳妇,是妯娌之间的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第二代的希昭,自成一家,是从生活到艺术的飞跃;到了第三代,有蕙兰将绣艺带入寻常百姓家,并牵引出戥子、乖女,是设幔授徒的生意盎然,重新又回到凡俗的生活日用。这三代人,分占了小说的三卷,前两卷的人物多在天香园内,第三卷落笔在天香园外的小户人家。
“天香园绣可是以针线比笔墨,其实,与书画同为一理。一是笔锋,一是针尖,说到究竟,就是一个‘描’字。”(《天香》第24节)前两卷人物场景无数,若比作书画,可算描出了一幅“清明上河图”。但即便如此,其实还算不得最高的褒奖。因为一方面,“描”已非书画高境:另一方面,“清明上河图”也绝非绘画的最上品,其价值更多在画外。更何况文字和绘画本就不同,其中差异,莱辛《拉奥孔》早有明言。他赞扬荷马,“荷马描绘的是持续的动作,他只是用暗示的方式去描绘物体”,并批评哈勒,“我从每个字里只听到卖气力的诗人,但是看不到那对象本身”。《天香》的前两卷,多少也有一点这样的问题。
在《清明上河图》里,那些买东西卖东西的,都不得已停滞在某一个固定姿势里,这是绘画的先天限制,然而,这种限制却被作为小说的《天香》所继承,《天香》就好比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幅,人事纷繁,细密生动,却大都定格在一个个特定空间里,没有各自在时间层面的持续性。在《红楼梦》里,每个主要人物都是慢慢老去的,而在时间跨度将近七十年的《天香》里,美女到老太婆的转变却每每令我们惊骇,因为其间缺乏精神层面的持续发展,只有逻辑和知识层面的年龄推算。《天香》里众多的角色,都定格在推动画幅按逻辑缓缓展开的瞬间,随后他们就“阅后即焚”,只残存在作者的人物年表中,被后来出场的人偶一提及。
但到了第三卷,小说面目却为之一变。天香园绣能不能放下身段,该不该让外人学去,又当怎么个学法,这是第三卷重点要讲的故事,其矛盾集中,人物少,发展性强,又有悬念,环境也从楼阁大观落到了市井小屋,凡此种种,与前两卷简直大相径庭。
王安忆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自己觉着第三卷最好看,写的时候几近左右逢源,说服申家绣阁里的人,同时也是说服我自己,极有挑战性,自己和自己对决,过了一重难关又遇一重难关,小说最原初又是最本质的属性出来了,就是讲故事,把故事讲得好听。”
依旧是《拉奥孔》里,莱辛解释荷马为何要用一百多行诗句来描述阿基琉斯的盾牌:“荷马画这面盾,不是把它作为一件已完成的完整作品,而是把它作为正在完成过程中的作品……我们看到的不是盾,而是制造盾的那位神明的艺术大师在进行工作。”《天香》的第三卷也可作如是观,我们看到的终于不再是一件件眼花缭乱的物事,而是时间的纵深,行动的持续,随着这个过程,终于开始有了人之为人的精神发展,如将绣艺带到天香园外的蕙兰、如执意要学绣的丫环戥子、如最终欣然接受现实的希昭,她们都是在努力尝试突破自己固有的格局,不断地向上走。小说末尾,希昭登门与蕙兰论绣,见得绣幔内几个常伦之外的孤苦女子,并未损“天香园绣”的声誉,反倒有刚强进发的意蕴,她觉得欣慰,“希昭从花棚上起身,四下里亮晶晶的眼睛都含了笑意,几乎开出花来。光线更匀和温润,潜深流静,这间偏屋里渐渐充盈欣悦之情”。
这匀和温润、潜深流静的,是生命的光辉。无论前面有多少艰难曲折,在《天香》最后的时刻,生命的光辉终于如玉和白瓷一般,静静地从里面透出来了。只是,倘若这样的光辉不是被小说家费劲心力地描出来,而是听凭读者自行体认出来,抑或是罢卷许久后,忽然地会心一笑,那就当真完美了。而小说家唯有能做到这样的听凭,他才能真正步入强有力的创造者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