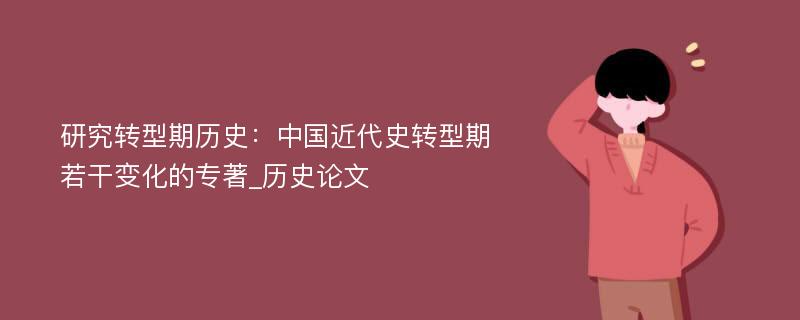
要多研究转型期的历史——专论中国近代历史转型期的某些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专论论文,历史论文,要多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1)05-0036-07
历来对中国史的研究大多不外通史与断代史,而于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则很少专门性研究。所谓转型期的含义,我认为是指朝代与朝代间,社会形态与社会形态间的转换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如宋元之际,明清之际,封建社会转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等等。在这种转型期往往发生许多足以引起人们注视的变化,甚至是巨变。但我们研究通史时常常一掠而过,研究断代史时则多用力于主朝,较少涉及易代鼎革的变化,甚至出现空白。至于研究转型期历史的专著则极为罕见。
最近读到唐德刚教授所著《晚清七十年》,这是专门论述中国近代前期七十年历史的转型期历史著作,是我第一次读到的这方面专著。由于匆匆读过,对书中的论述尚未深入思考,所以还不能提出任何商榷性意见;但作者对转型期的诠释是颇具启示性的,而勇于实践自己想法的精神更是值得钦佩的。唐教授说:“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在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瓶颈会发生淤塞现象,历史本身就要求冲破淤塞而发展,唐教授解释这种冲出瓶颈的程序是“在哲学上叫做‘突破’,在史学和社会学上则叫‘转型’——由某种社会模式转入另一种社会模式,以图继续向前发展”。唐教授俯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七十年的近代历史转型期,沿着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八国联军,一直到辛亥革命诸重大政治事件这一脉络,讲述了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历史巨变。本文则专论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刚进入近代转型期时社会经济方面所呈现的种种变化,以证明多研究转型期历史的必要性。
一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积淀物堵塞的瓶颈被第一次鸦片战争所冲开而进入中国近代历史转型期的开端,外国侵略者悍然侵入,中国社会呈现社会危机,开始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以英国为主的外国侵略者们胁迫清朝政府订立江宁条约等等不平等条约之后,随即放手掠夺各种权力与权利,从而发生了异常兴奋的情绪。英国的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广泛而动听地宣传中国这个新市场的美景,他们痴迷地认为这次可以“一举而要为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需要效劳了!”甚至幻想“祗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注:1847年12月2日,香港中国邮报社论(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下,见《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他们完全沉醉在广阔市场和巨大利润之中了。从1842-1845年英国对华输出工业品的数额一直处于涨势,从下表可以看到:
1842 969381镑
1843 1456180镑
1844 2305617镑
1845 2394827镑(注: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页62,附表。)
这种增长一方面固然表明了“鸦片战争替英国商业开辟了中国市场”(注:马克思:《对华商业》,见《马恩论中国》页185。)的事实;但在另一方面它却与中国市场的消费实际并不相合,1846年以后这种不相合的状况日益明显,当年英国对华输出总额降到1836年1326388镑(注:马克思:《中英条约》第一篇,见《马恩论中国》页104-105,页112。)的水平之下,以后未见起色。1852年,港督府秘书密切尔在一份报告书中曾哀叹贸易十年的结果:这个人口大国对英国商品的消费还不及荷兰一半,赶不上法国和巴西,只比比利时、葡萄牙稍微多一点(注:1852年3月密切尔报告书(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下,见《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这种输入与消费不相称现象的形成,主要是当时“中国社会底基本核心是小农和家庭手工业”,所以“还谈不到什么外货的大宗输入”。(注:马克思:《中英条约》第一篇,见《马恩论中国》页104-105,页112。)英国人也承认这一事实说:“中国人久已利用他们自己的资源,花费很便宜的成本,掌握了一切生活必需品和绝大部分的奢侈品。”(注:史当登:《中国杂记》1850年增订第二版页10-11(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下,见《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
这种不相称的另一原因是鸦片的大量输入。鸦片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成为一种既非明令禁止,又无税则规定的“合法走私品”,所以鸦片输入量增长很快,如1842年为33508箱,到1850年激增至52925箱。外国侵略者在输入大量工业品和鸦片的同时,还从中掠取以茶丝为主的原料,据统计,茶在1843年由广州一口输出量是17727750磅,1844年由广州、上海两口共输出70476500磅,1849年两口共输出达82980500磅;丝在1843年由广州一口输出量是1787包,1845年广州、上海两口共输出达13220包,1850年两口共输出达21548包(注:H·B·morse:《The Internationalrel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V,1页556附表。)。侵略者更利用条约中的优惠条件,廉价掠取原料,甚至甩开中国商人的中介而亲自到产地采购,如上海所产木棉,原由闽、粤商人转手,后来“即由西人自为采售”(注:王韬:《瀛壖杂志》,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输入工业品、鸦片和掠取原料是外国侵略者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所采取的主要侵略方式,这些侵略活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化。虽然外国工业品当时尚不能畅销,但不能认为对中国社会毫无任何作用。外国经济势力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打击和初步瓦解了五口附近地区的自然经济,如厦门在开埠后的1845年,即因洋布的输入而使“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浙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注:1845年春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敬奏,见《历史研究》1954年第3号。)。在战前一直是棉布业中心的苏松一带也感到了严重的威胁。1845年,著名经世学家包世臣在致前大司马许太常的信中说:“今则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是以布市消减,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商贾不行,生计路绌。”(注: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7。)广东的织工也感到“棉花输入的增加,剥夺其妻子们绩棉纺纱所得的利益”。(注:P·Amber,China An outline of its goverrment &police。)这种影响也延伸到内地省份,如湖北的棉布原行销于滇、黔、秦、蜀、晋、豫诸省,甚至到东南吴、皖地区。但是,自通商互市以后,洋布盛行,各布销场乃为之大减。(注:《湖北通志》卷24,物产3。)“独立手工业也遭到一定的破坏,如广东佛山的铁工业,战前相当兴盛,铁钉、土针等业都是工人多至数千规模的作坊,战后则都呈现凋敝,铁钉业因洋钉输入而制造日少,土针业也以洋针输入而销路渐减。”(注:《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实业志·工业》。)对家庭和独立手工业的这种破坏,虽然对某些地区的自然经济有一些初步瓦解作用,但主要的是阻止了中国手工业向工业正常发展的可能,更严重的是制造了一大批失业的手工业劳动者,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动荡危机。
失业者远远不止这些。战前清政府一直执行广州一口贸易的限制政策。在广州附近和从广州到内地去的湘粤大道上,有不下十万的运输劳动者,以及依附运输业的有关服务行业人员,总数在百万人左右;五口通商以后,由于“广州商利遂散于四方”(注:彭玉麟:《会奏广东团练捐输事宜折》,见《彭刚直公奏稿》卷4。)致使这百万失业大军中的大部分人生计维艰,被迫走进流浪者队伍中去。又如福建之漳州、泉州、兴化、福宁和浙江之宁波、台州、温州等府,“地多滨海,民鲜恒业,沿海编氓,非求食于网捕,即受雇于商船”,但是,“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该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注:闽浙总督刘韵珂片,见《史料旬刊》36期,地319/320。)
失业的手工业劳动者、湘粤大道上失业的运输工人、沿海的失业船户和居民,再加上从土地上被赶出来的农民,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将组成一支威胁封建社会稳定、安宁的流浪者队伍,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动荡。
和工业品同时大量输入的鸦片,其毒害不仅使中国的财政金融陷于厉害的破坏状态,更严重的是戕害人体,扰乱社会。当时闽浙总督刘韵珂在致金陵三帅书中描写浙江黄岩遭受烟毒的惨状说:“黄岩一县,无不吸烟,昼眠夜起,杲杲日出,阒其无人。月白灯红,乃开鬼市。通商之后,烟禁大开,鬼市将盛。”(注:《广东夷务事宜》,见《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3册,页361。)
工业品和鸦片的大量输入,纵使有日渐增长的茶丝输出品,也难抵补逆差,由此导致大量白银外流,加上战费和赔款,终于造成“银贵钱贱”的严重社会现象。1842年银一两可兑钱1572.2文,到1849年银一两已可兑钱2355文了(注: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页37,49。)。银钱比价差额的增大,必然严重影响财政金融和国民经济。
外国侵略者从1843年开始在五口谋求立足,在港口与地方官吏接洽,租屋居住或划定一定地区作为“租借地”。如上海自1843年11月27日正式开港后,英国首任领事巴富尔即不满足于租赁中国官方指定的栈房暂居,而是积极图谋攫取一块土地作据点。经与清政府苏松太道宫慕久商洽,最后通过“永租”方式,于1845年11月29日订立了《土地章程23条》,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租与英人建筑房舍并居住。次年9月24日又确定了四至即:东至黄浦江,南至洋泾浜,西至界路,北至李家庄。全部面积约830亩,作为“租界”,1848年又扩大为2820亩。(注: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页37,49。)这些“租界”不仅作为经济侵略据点,还建立一套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殖民地制度,进行种种犯罪活动,成为中外罪犯的逋逃薮。大批侵略分子在口岸和附近地区为非作歹。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阿利国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说:“来自各国的这群外国人,生性卑贱,无有效之管束,为全中国所诟病,也为全中国的祸患。”这些人是“欧洲各国人的渣滓”,(注:严中平:《五口通商时代疯狂残害中国人民的英美“领事”和“商人”》,见1952年6月20日《进步日报·史学周刊》76期。)他们最堪痛恨的罪恶活动是掠夺和贩卖人口。其残酷悲惨不忍卒闻,清政府大吏李东沅曾著《论招工》一文描述称:
频年粤东、澳门,有拐诱华人贩出外洋为人奴仆。名其馆曰招工,核其实为图利,粤人称之为买猪仔。夫曰猪等人于畜类,仔者微贱之称,豢其身而货之,惟利是视,予取予携。……且粤省拐匪先与洋人串通,散诸四方,投人所好,或炫以赀财,或诱以阚赌,一吞其饵,即入牢笼,遂被拘出外洋,不能自立。又或于滨海埔头,通衢歧路,突出不意,指为负欠,牵扯落船。官既置若罔闻,绅亦不敢申述,每年被拐,累万盈千。其中途病亡及自寻短见者不知凡几。即使抵埠,悉充极劳苦之工,少惰则鞭挞立加,偶病亦告假不许,置诸死地,难忘生还。(注:葛士:《皇朝经世文续编》卷86,刑政3。)
外国侵略者还在各口岸地区豢养和扶植一批原来称为通事的“买办”,这些买办的前身就是战前给外国人做中介人并兼管其商业事务的人。过去人数不多,经济力量亦较薄弱,在社会上还起不了大作用。战后,他们继续被选用做各口岸的商务代理,推销商品,搜购原料,靠外国经济侵略活动而发“百无一失”的大财,当时人已称他们是“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注:王韬:《瀛壖杂志》,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这些买办商人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日益强化而日益扩大,由商业买办扩大到金融买办、矿山买办、工厂买办等等;由经济买办扩大到政治买办、文化买办而最终形成中国近代转型期中的买办阶级。
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近代历史转型期的开端年代里也试探着进行资本输出。如1843年,英国资本在上海经营墨海书馆;1845年,美国在宁波经营美华书馆等印刷出版业;1845年,英国大英轮船公司职员柯拜在广州建立柯拜船坞的船舶修造业;1850年,英国在上海经营字林报馆的新闻业(注:孙毓棠:《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上海人民出版社。)。这些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它们都是转型期变化的产物。尤其让侵略者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企业中吸引了一部分中国劳动者,这就是中国近代无产阶级的开始。
二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内部也由于近代历史的转型而发生巨变。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史学家梁启超比较敏锐地惊呼过这种巨变。
这种巨变首先表现在土地集中的情况日益严重,有人曾经引证各种资料,历举冀、苏、浙、晋、鄂、陕、鲁、赣、闽、广、桂以及满洲等十四省土地集中情形,证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全国土地有40%-80%集中在30%-10%的少数人手里,60%-90%的多数人没有土地(注:王瑛:《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见《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3卷1期。)。这种严重情形究竟如何形成?它仍然是战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从下面三点来分析。
(一)战火的蔓延,不仅致使直接接触地区如江苏、浙江沿海州县“转徙流离,耕耘失业”(注:《东华续录》道光46,道光54,道光49、52。),就是内地省份如湖北也因“粤东不靖,大兵自北而南;军书旁午,露布星驰无旦夕;官吏征民夫递送;军装、钱漕、力役,三政并行,追呼日迫,卖儿鬻女,枵腹当差,道馑相望,流离之状,令人恻然!”(注:邓文滨:《苦雨》,见《醒睡录·初集》卷2,申报馆本。)道光二十二年湖广道监察御史吕贤基在其指陈时弊的奏折中更揭示官吏乘战争之机勒索搜刮的恶行说:
比年以来,地方官不能上体圣意,每于近海之区,藉防堵以派费;于征兵之境,借征调以索财,以及道路所经,辄以护送兵差,供给夫马为名,科敛无度。近闻湖北、湖南、安徽等处,皆有加派勒捐之弊。又闻直隶、山东亦然。(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5,页17;卷67,页44-45;卷40,页33-34。)
战败的赔款也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无力承受沉重的负担,丧失经营农业生产的能力,只能离开土地,穿州过县去求生计。
(二)各种浮勒的加重。战前的农民负担本已很重,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为数不多。经世学者章谦在其《备荒通论》一文中曾根据农民生产的必需支出、缴纳地租、春耕时的高利借债,秋收时的减价卖谷等项目折算后得出一个结论,即农民“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三焉”(注: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39,户政。)。战后,情形尤为严重,农民除了沉重的赋税和由于银钱比价差额所造成的暗增之赋外,还要遭受种种浮勒,如江苏就利用“催科之术”,“以帮费为名,捐款为词,假手书役,任意浮收。甚至每米一石,收米至三石内外,折钱至十千上下;每银一两收钱至四五千文”(注:道光二十三年耆英折,见《史料旬刊》35期,地291/293。)。浙江又有“截串之法”,即“上忙而预征下忙之税,今年而预截明年之串”。(注: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见《曾文正公奏稿》卷1。)
必须指明,这种浮勒,一般绅富不仅不受影响,还可从中取利,如江苏,“向来完漕,绅富谓之大户,庶民谓之小户。以大户之短交,取偿于小户。于是刁劣绅衿,挟制官吏,索取白规。大户包揽小户,小户附托大户,又有包户之名。以致畸轻畸重,众怨沸腾”(注:《东华续录》道光46,道光54,道光49、52。)。相反的情况是,农民如果不接受这种浮勒,就要遭到官吏的迫害。道光二十三年,耆英曾叙述过江苏勒征的情形说:“设有不遵浮勒之人,书役则以惩一儆百为词,怂恿本官,或指为包揽,或指为交;甚或捏造事端,勾串棍徒,凭空讦告,将不遵浮勒之人,横加摧辱”(注:道光二十三年耆英折,见《史料旬刊》35期,地291/293。)。咸丰元年曾国藩陈述了更多一些地方的惨状说:“州县竭全力以催科犹恐不给,往往委员佐之,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藉。”(注: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见《曾文正公奏稿》卷1。)严刑之下浮勒可能满足,正税往往积欠,在《石渠余纪》中记载道光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五、二十九各年各省地丁实征数都不足额征数。正税与浮勒像两条鞭子一样,交替抽打着农民,迫使其离开土地,即使富庶如苏松,也“竟有以所得不敷完纳钱漕,弃田不顾者”。(注:道光二十三年耆英折,见《史料旬刊》35期,地291/293。)
(三)人祸不已,天灾频仍。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国内遇到极大的灾荒,灾区面广,灾情严重,灾种也多。据《东华续录》的记载,从1841-1849年间,几乎每年都有灾情,灾区几遍全国,种类包括水、旱、雹、蝗、风、疫、地震、歉收。其中道光二十七年河南的两次水灾和一次旱灾,二十九年浙江、安徽、湖北等省的大水灾,都是灾区宽广,灾情异常,灾民颠沛流离的大灾,农民生计无存。
由于上述几点原因,大批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沦为流浪者。他们或则涌进城镇去讨生活,一些中小城市也未能免,如福建的延、建、邵三府,本不是什么大城市,到了四十年代末也出现了“外乡游民麇集,佣趁工作”的现实;或则参加反抗行列去求生路。各地普遍发生的抗粮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问题。农民的大批离乡,当时商品经济的某些发展和货币地租的流行,为土地兼并提供了可能。
其次,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冲击了中国的自然经济状态,使农产品的商品化日趋明显。它意味着农民已经不只为自己一家人生产生活必需品,而是把自己的生产和市场逐渐联系起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把农产品卷入到商品经济的潮流中去。这种现象在沿海地区表现得较为明显,如棉茶丝等经济作物在战后更加商品化,福建农民在种植一般农作物之外,还生产一定数量的蔗糖,春天时,农民“把糖运到最近一个海口去卖给商人,商人则在东南季候风的时节,把糖运到天津或其他北部港口去。至于拖欠农民的糖价,一部分用货币支付,一部分则用带来的北方棉花来归还。”(注:1852年3月密切尔报告书(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下,见《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这个记载表明农民已经划出一定土地种植甘蔗,并利用甘蔗原料进行为供应市场交换的手工劳动,制成商品——糖。商人则通过两种农产品把两个遥远地区联结起来。近代思想家王韬曾在其所著《瀛壖杂志》中记载上海、闽、广的木棉交易情形说:
沪人生计在木棉,贩输远及数省,且至泰西各国矣。在沪业农者罕见种稻。自散种以及成布,男播女织,其辛勤倍于禾稼而利亦赢。”“粤则从汕头,闽则从台湾,运糖至沪,所售动以数百万金,于沪则收买木棉载回。
葛元煦的《沪游杂记》中也有这类记载说:
松沪土产以棉花为大宗,村庄妇女咸织小布为养瞻计。每日黎明,乡人担花挈布,入市投行,售卖者踵相接也。交冬棉花尤盛,行栈收买,堆积如山。(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
王、葛二人所述开港后上海地区将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商品接连成链的发展情况正说明上海附近的木棉植区相当大,产品大部分上市,市场交换频繁,交换量亦大,并且有行栈一类的商业性机构收买。不仅沿海如此,内地也有类似情况,如道光二十二年左宗棠在《上贺蔗农书》中曾描述了安化农产品与商业资本的不可分的关系说:
安化土货之通商者,棕、桐、梅、竹而外,惟茶叶行销最钜,每年所入将及百万,一旦江湖道梗,则山西行商裹足不前,此间顿失岁计。有地之家不能交易以为生,待雇之人不能通工以觅食。今年崇阳小警,行商到此稍迟而此间已望之如岁矣。苟其一岁不至此,十数万人者能忍饥以待乎?(注:左宗棠:《上贺蔗农先生》,见《左文襄公书牍》卷1。)
由于经济作物的面积日增,粮食作物的面积自然日减,当时已有人做出估计,认为桑、棉、蔬、果、烟草、杂植等非粮食作物要占全部农田的“四之一”(注:汤纪尚:《食货盈缩论》,见《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4册,页689。),产量面积相应缩小,因此有些地方需要从外地采购粮食,如前述的湖南安化“民食半资宝庆、益阳”,湘阴地方“丰年犹需买谷接荒”(注:左宗棠:《上贺蔗农先生》,见《左文襄公书牍》卷1。)。随着商品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货币的作用日强,3000万两左右的地丁需用货币缴纳,额外勒收的帮费需要折银,商品的诱惑刺激了地主绅富对货币地租的贪欲,然而农民力田所得是米,所以要持米售钱、但又遇到“银贵钱贱”的厄运,而陷入米价苦贱,银价苦昂的困境。曾国藩在一篇奏疏中难以掩盖地陈述了这种困境说:
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注: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见《曾文正公奏稿》卷1。)
从这段文字的背后可以看到,劳苦农民将肩挑更多米粮拖着沉重的步子到市场求售的悲惨图画。
第三,手工业生产日渐走向独立性劳动,主要表现在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主副关系正起变化,如福建农民虽然仍是自己一家人来完成“自清、自纺、自织”的全部织工工序;但是他们已“很少光为自己家庭需要而生产”,他们已经能“为供给邻近城市与水上人口生产一定量的布匹”。他们已把织布当做季节活动的主要劳作,而且已经不止动员自己的妻子儿女,乃至雇工在家从事纺织。(注:1852年3月密切尔报告书(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下,见《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农民已不仅为交换而进行简单的商品生产,而且还和商业的关联日益密切。他们不仅把自己的手工制品当做商品卖给商人,还为商肆进行手工加工,王韬的《瀛壖杂志》中曾记称:
沪上袜肆甚多,而制袜独工,贫家子女多以缝袜为生活,敏者日可得百钱,每夕向肆中还筹取值,较之吾里擘垆,劳逸迥殊,女红自纺织以外专精刺绣。……所织之布则有小布、稀布,以丈尺之短长为别,其行远者为标布,关陕、齐鲁诸地,设局邑中广收之,贩运北方。(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
这说明商业资本已在直接组织手工业生产了。在这种发展情况下,具备手工工厂规模的手工业也在恢复,以采矿业为例,战前虽已开始,并有较多数量矿工,容留了不少外来劳动者,但却受到种种限制,甚至被命令停闭。战后情况有较大变化,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和六月先后两次谕令开矿,表示了官为经理、任民自为开采的态度,劝谕商民试行采办,并严厉禁止种种阻力。当年五月间开采了广西北流县铁矿,七月间又开采了广西恭城县铅矿。(注:《东华续录》道光46,道光54,49、52。)手工业生产向独立性劳动途径迈进,对于自然经济的瓦解起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第四,商业活动的日趋频繁和发达。战前的商业已相当发达,曾出现所谓“四聚”的商业中心。战后原有的商业城市更加繁荣,如所谓“四聚”之一的北京,据道光二十五年刻印的《都门杂记》中所记称:
京师最尚繁华,市廛铺户装饰,富甲天下,如大栅栏、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行宵,非他处所可及也。
《都门杂记》是当时专为商人服务而刻印的一种书,作者在例言中称:“是书之作原为远省客商而设,暂时来京,耳目难以周知。故上自风俗下至饮食服用,以及游眺之所,必详细注明,以资采访。”(注:杨静亭:《都门杂记》风俗、例言。)从这里也反映出当时北京商业活动的频繁,所以才有为商人导游刻印专书的必要。
在旧商业城市更加繁荣的同时,新的商业城市也出现了。如上海,由于“道光间,中外互市”,而成为“通商总集”(注:葛元煦:《沪游杂记》。),成为“南北转输,利溥中外”(注:王韬:《瀛壖杂志》,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的新型商业城市,而且还随之兴起了一批与商人有关的服务性行业,如客栈、饭馆、舞榭、歌台、秦楼、楚馆等等,供商人生活必需及游乐挥霍。城市居民也复杂起来了,不仅有“南闽、粤,北燕台、天津”,也有“出外洋,往各国”的商旅,因之,“轮船到埠,各栈友登舟接客,纷纷扰扰,同寓之人,亦五方杂处”。除了商人以外,上海还有许多粤东、宁波之人,靠在“船厂、货栈、轮舟、码头、洋商住宅……计工度日”。一批游手好闲的游民也到这里来讨生活,他们或则“遇事生风”来讹诈,或则“串诈乡民孤客,或乘局骗,或无债取偿”以取财(注:葛元煦:《沪游杂记》。)。随着城市居民成分的变化,城市风气亦有所变化,一般是趋向于奢靡。所谓“风俗日趋华靡,衣服僭侈,上下无别”,而“负贩之子,猝有所获,即御貂炫耀过市”,“衙署隶役,不着黑衣。近直与缙绅交际酒食,游戏征逐”,而缙绅先生也竟然肯纡尊降贵和负贩之子与衙署隶役来往,而“恬不为怪”(注:王韬:《瀛壖杂志》,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更不为一般人所习惯。但是这一变化却表明,旧的上下有别的封建等级关系,已在开始破坏。
商业活动的范围也日益宽广了。道光二十三年耆英在奏折中说:“查闽、粤、江、浙等省商民,每多出入海口,贩运土产,上至盛京,下至广州,往来贸易,其所运货物除茶叶、湖丝、绸缎外,均非西洋各国所需。”(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5,页17;卷67,页44-45;卷40,页33-34。)沿海地区通过贸迁有无似乎已经形成一个全海岸线进行商业活动的市场,甚至扩大到内地,如湖北的棉花原来只销本省和川滇等省,自开埠以后洋商争来采购而与沿海发生联系(注:《湖北通志》卷24,物产3。)。
市场范围的扩大推动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与商业的关系也进一步密切起来,人们价值观的变化更为明显。有些人已经靠商业发家致富,如沪之巨富不以积粟为富,最豪者一家有海舶大小数十艘,驶至关东,贩油、酒、豆饼等货,每岁往返三四次。”(注:王韬:《瀛壖杂志》,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有些人已单纯依靠商业或为商业服务为生,道光二十一年浙江沿海封港三月,就“商贾不通”,停止了商业活动,于是“本省之货物,日久停滞,朽蠢堪虞。他省之货物,日渐缺乏,腾贵滋甚,商民已属交困”,至于沿海那些原“以起运客货为业,全赖商贩往来,方获微资糊口”的“挑抬货物之脚夫”以及一些舵工、水手、渔夫等不下数万人,也因封港而“悉皆失业,数月之后,坐食山空,饥寒交迫”(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5,页17;卷67,页44-45;卷40,页33-34。)。由于商业活动频繁,风险变化也很大,黄式权的《淞南梦影录》记载了上海商人发财与破产的变化说:
海上为通商口岸第一区花天酒地,比户笙箫,不数二十四桥月明如水也。其间白手起家者固属不少,而挟厚资,开钜号,金银珠玉,视等泥沙,不转瞬而百结鹑衣,呼号风雪中,被街子呵斥者亦复良多。(注:黄式权:《淞南梦影录》,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
商业的这种发展,对当时社会经济的作用是使生产愈益从属于交换价值。这就是说,商业的发展,既吸收了农民更多地进行手工业生产,而使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关系有渐渐分离的变化;同时,也刺激了土地所有者对工业品的贪欲,而向农民榨取更多的货币地租。归根结底,二者得到同一结果,即自然经济在日益瓦解,新的经济因素在日益增长,从而给封建社会带来了撼动的危机。
三
当然,近代历史转型期所发生的巨变,不止是上面论述的社会经济方面,他如在政权体制上酝酿建立适应中外关系机构,终于在六十年代初正式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同文馆等;在社会思潮方面由于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知识者对现实要求改革的朦胧想法已经渐渐清晰起来。对外开放,要求改变封闭落后的思想形成为一股强而有力的社会思潮,于是人们开始探求新知,著书立说,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两部开端著作。这两部书都是为了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情况,尤其是为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便采取对策而编写的。接着,姚莹的《康輶纪行》、梁廷枬的《海国四说》、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等书,相继问世。这些著作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艺和民主政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述和探讨,以求外御强寇,内事改革,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在阶级关系上也出现了新的形势,那就是官民夷关系的变化,当时的形势是:“民犯夷则唯恐纵民以怒夷,夷犯民则又将报民以媚夷,地方官员知有夷不知有民。”(注:《广东夷务事宜》,见《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3册,页361。)他们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反知府斗争、反进城斗争等大规模抗争上。与此同时,以反抗剥削与压迫为目的的抗争也在全国各地普遍爆发,根据《东华续录》的记载,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几乎连年都有这种性质的反抗活动。这些方方面面的反响决非一篇文章所能包容,本文只是选择社会经济变化的这个侧面来论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应该跳出原来的构架,多深入研究些转型期的各方面问题,以扩大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视野。
标签:历史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论文; 清朝论文; 商业论文; 手工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