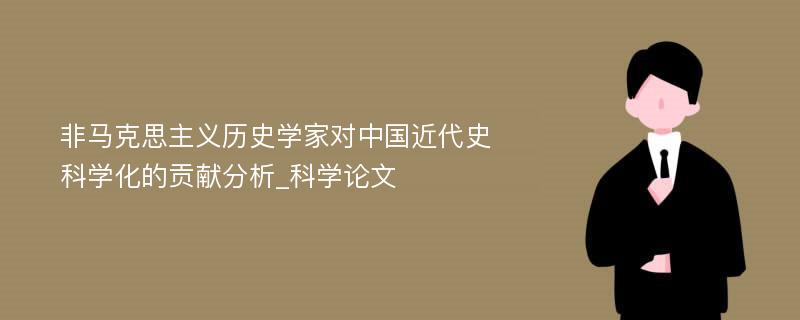
试析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家论文,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近代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2)01-0026-05
十九世纪是“科学的世纪”,由于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对于自然的宇宙的整个观念改变了”(注: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中译本,第283页。),主张将自然科学研究中发展出来的方法推广用以认识宇宙万物及与人类有关的一切。到十九世纪末,这种观念开始在国内传播,至五四运动时期,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随着科学的进步,“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注:陈独秀:《敬告青年》,见《新青年》1卷1号,1915年9月。)。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历史学当然也不例外,逐渐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史学的科学化主要表现在唯物史观的传入与确立、具体的史学观念的变化以及史学方法的更新三个方面。以往人们在研究史学科学化时多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作用,而忽视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作用。本文拟从以上三个方面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在这个过程中的贡献进行阐述。
一
科学的历史观的确立和指导是历史学科学化的根本标志。在这个过程中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理论上,他们首倡唯物史观并主张新史学要贯注社会进化的原理,强调史学要以历史哲学为指导;在实践中,他们也力求以此为己任,加以贯穿实施。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历史哲学才在中国兴起。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形成、发展并同各种唯心主义史观斗争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以李大钊、郭沫若、侯外庐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但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时传播唯物史观的主体也并非马克思主义者。
在中国最早提到唯物史观理论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马君武。1903年他在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便涉及到马克思和唯物论:“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注:《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在《唯物论二巨子(底得娄、拉梅特里)之学说》中他又对唯物主义哲学大加赞赏:“伟矣哉,唯物论之功乎”(注:《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认为“欲救黄种之厄,非大倡唯物论不可”(注:《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主张要挽救中国命运,须以唯物论解释历史。第一位在中国提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论断的朱执信则认为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由空想发展成为科学,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唯物史观的发现。他在1906年发表的《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中便表现出了应用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社会历史问题的意向。另外在《德意志革命家列传》中,他又对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进行了介绍,意识到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阶级斗争的根基,指出“社会革命之原因,在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注:《朱执信集》上集,第56页。)。此外,在当时一些倾向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出版物中,也有一些涉及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论著。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无论是马君武还是朱执信,他们的历史观在本质上都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而且他们对唯物史观的传播也不是自觉的。因此,他们对唯物史观的内容和实质不可能完全把握,更不可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加以选择。且这些介绍大多从救亡图存的角度出发,偏重于政治方面,而对如何将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相结合,却没有涉及到。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缺陷而否认他们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在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引入中国的同时,受严复传播的英国经验论和归纳法的影响,国内一大批学人开始以西方知识思考人生的道德原则,他们纷纷发表文章,对近代西方各派哲学的观点进行系统地探讨,批评传统道德性命之学的先验论。如梁启超先后发表《霍布斯学案》、《培根学说》、《笛卡儿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说》、《天演初祖达尔文之说左右世界》等文章,指出近世与上古、中古的主要区别是思维方法和世界观的革新,认为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推理演绎法是近代文明的基础,并相信这二者可以为中国学术史研究带来广阔的前景。因此,主张中国国民应吸取西方归纳和推理的认识方法。这对科学历史观在中国的确立无疑有凿山之功。
在具体的实践中,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多力求以此为己任,努力付诸实践。他们倡导新史学必须有进化的历史观为指导,以国民文化史为核心,注重历史内容的因果关系,并依据历史进化论对中国历史上的种族、职官、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学术流变等作了研究,认为旧史著作虽然叙事繁复,但没有总结历史演变的原理;传统史学宣扬的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不能“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方向之所在”(注:陈独秀:《新史学》。),从史著中看不出社会演变过程。他们指出“中国自秦汉以降,史籍繁矣,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纪述,非抽象之原论”(注:章太炎:《哀清史·附中国通史史略例》。),即使象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类专门的典志体著作,也只是“缀列典章、恺置方类”(注:章太炎:《哀清史·附中国通史史略例》。),仅限于对典章制度源流的详细叙述,对其演变原理却没有进行归纳。因此章太炎提出新史学必须以“哲理”为指导,无论是民族史、典志史、还是地理史、学术文化史都可贯彻社会演变的进化之理,“熔冶哲理,以逐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注:章太炎:《哀清史·附中国通史史略例》。),使读者能真正地“知古今进化之轨”。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则对历史哲学的作用大加宣扬,指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矣。历史与历史哲学殊科,要之,钩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主张撰述历史,必须体现历史的演变规则。并在实践中力求以进化观点来研究历史,将旧史的循环论改造为历史进化论,把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与西方进化论糅合形成具有中国当时特色的历史进化论——三世六别论,一改以往旧史全面铺陈的传统,使新史学条分缕析、因果分明。其他学者如夏曾佑、刘师培也积极倡导用进化的观点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明确主张在编写中国历史的过程中要有一套系统的哲学原理,以历史进化论贯穿其间。
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在这个过程中所标明的历史发展观、新史学的史学主体意识,标志着近代历史哲学正式进入其自觉的理论建设时期。虽然他们没有全面地展现历史发展规则,但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在推动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二
历史哲学的科学化必然导致一些具体的史学观念的科学化,这集中表现在治史态度的变化以及史料范围的扩大两个方面。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在这两方面也颇有建树,他们所倡导的纯客观的治史态度、无所不包的史料观无疑是冲破封建旧史观的巨大动力,为科学的新史观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在治史态度方面,李大钊指出:“所谓的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家即以此二者为宝贵的信条”(注:李大钊:《史学要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1980年校印本,第14页。)。也就是以理性的、批判的态度对待前人的记载和研究成果,不能轻信和盲从。“以批评的眼光、严密考察史料的全部或一部,推翻许多向所认为可信的著作”(注:衡如:《新历史之精神》,见《东方杂志》19卷11号,1922年6月。)。即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使研究的结果尽可能地接近或符合实际。
早在李大钊以前,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便提出了“尊疑”、“重据”的主张,他们受西方近代科学主义的影响,以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为治史基本原则,认为历史学可以成为一门科学,但主要或首先是一门史料考据科学。为了增强史学研究的客观性,新史家们主张治史要以求真为目的,而不应为现实功利所干扰,即所谓的“非功利主义”的主张。1915年,任鸿隽发表《科学精神论》一文,指出“科学不以实用始,故亦不以实用终。夫科学之最初何尝以其有实用而致力焉,在‘求真’而已。真理既明,实用自随,此自然之势,无庸勉强者也”(注:任鸿隽《科学精神论》,见《科学》1915年2卷1期。),驳斥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许多人读科学目光均不脱物质利益”的说法。他的观点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王国维则认为“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00页。)。胡适认为“做学问不应时势之需,不当存狭义的功利观念,而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注:胡适:《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9页。)。顾颉刚也主张“在学问上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注:顾颉刚:《古史辩》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4页。),否则,就象古人那样,把史学服务于现实政策了。傅斯年的观点更加明确,认为治史不是去扶持、推倒这个运动、那个主义,而应超然于政治,作“无用的研究”(注:《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5页。);认为历史学家应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应消灭自我,“客观地处理现实问题”(注:《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352页。)。在他们看来,治史要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不为古今中外任何先见、成见及任何主观因素所左右,以理性、客观的眼光对待一切史料与学说。过分地强调功利性,易掺入主观偏见,从而干扰其求真与纪事目的的实现。“科学态度在于抛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跟着事实走”(注:胡适:《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9页。)。
这种非功利主义的学术观,正是“科学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诚然这种“为历史而历史”,认为学术研究可以完全排除主观因素而趋于纯客观的看法是不现实的。因为,作为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任何史家都不可能摆脱周围环境的客观影响,更无法摆脱主观意志的局限。但这种倡导客观的求真态度,在推动史学摆脱传统史学的束缚,向科学化迈进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新史家们所倡导的纯客观的态度,否定了旧史学以维护封建统治及纲常礼教为务的功能观,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知识界破除迷信、追求真理和科学的勇气。
其次,史料范围的扩大方面。史学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使史学研究的范围由原来单一的政治史扩展到思想、文化、经济、社会和生活等方面,这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方法的局限,建立广阔的史料观念,拓展史料的搜集范围。既要注重与所研究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史料,又要注意各种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史料。
古代史著虽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但由于旧史学的记叙重心在君主,对平民的社会生活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因而遗漏了很多重要的史料,反映的并不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全貌。到这一时期,由于史学价值观念的变更,新史家大多主张撰写能够反映社会进化的全面的文明史,对史料的眼光也更加开阔。认为史料不能像旧史著作那样只注重与君主有关的部分,还应收集关系社会文明的各个方面的资料,甚至是文字出现以前的史料。因此,他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注:章太炎:《哀清史·附中国通史史略例》。),即要从旧史料中发现那些有价值的材料,不能墨守成规;同时还要把视野放宽,对于“皇古异闻,种界实迹”以及“外人言支那事者”(注:章太炎:《哀清史·附中国通史史略例》。)均应收集。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然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注: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叙》,《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也就是应该放宽史料范围,不但要注意正史资料,举凡遗文别集都可以证史,出土文物文献同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同时,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能力有了提高,判断史料的能力也相应的提高。一些自然科学方法被用于鉴别史料的真伪,许多过去被认为是没有史料价值而被人们忽视的材料,这一时期被当作史料而运用于史学研究。如梁启超从西方学者用神话资料研究各民族早期思想和宗教观念中受到启发,主张从神话中寻找地方风俗和社会心理资料,从《山海经》中观察古人的某种思想,从讳书中考察古人的宇宙观,从传统节目和地方节目中寻找民俗史料。顾颉刚则主张将戏剧、歌谣、神道等人们所熟悉的民俗材料作为史料,引入历史研究。陈寅恪对史料的运用更广泛,年历学、古代碑志、宗教经典、回纥文、蒙古文、满文等各种书籍,无不被他用作史料,还将小说、诗文作为史料引入历史,产生了“以诗证史”的研究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更将史料范围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历史研究法的最高水平。这种史料观念对于打破经史子集的界限,提高野史笔记金石碑刻的地位,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加速了史学的科学化的步伐。同时也奠定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具体史学观念科学化过程中的地位。
三
科学观念的传入,使中国学人“对于本国学术之地位有自觉心”(注:《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1919年1月1期。),“对于治学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注:顾颉刚:《古史辩》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1988年版,第25页。),觉悟到“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尤然”(注:《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2页。)。新史家在对旧史学的精神实质进行批评的同时,对旧史学的方法也作了深刻的反省,提出了新史学的方法论设想。
在当时中西文化冲撞、汇合的背景下,各派史家莫不力求融合中西,贯通新旧,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素质为己任,认为“历史上的事实各有比较的关联的位置,所以我们不能用主观的神学的、玄学的或国家主义的观察去研究历史。我们要用客观的、科学的方法考察历史的真象”,建立起“科学的东方学”(注:陶孟和:《新历史》,《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他们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供文学家炫示舞文弄墨的伎俩,所记都是耸人听闻的琐碎事,或撼动天地的大变乱,或是记帝王卿相的行为和政治事迹”(注:陶孟和:《新历史》,《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的旧史,认为新史家必须为人们提供了解社会的工具,更应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联系,“不但须究其然,并应究其所以然”(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首先,新史家们纷纷地运用科学的观点对传统的治史方法进行批判。早在19世纪末,严复就指出,近代学术的本质在于“黜伪而崇真”,其方法在于“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在于“内籀外化”(注:严复:《论世变之函》,《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74页。),即归纳演绎法的运用。王国维则认为:“我国学术尚未达到自觉的地位”,原因在于中国人缺少“思”与“科学”的思维方式,太过于“实际”、“通俗”、“具体”而不擅长“抽象”、“分析”(注:严复:《原强》,《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49页。)。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对科学的含义进行了阐释,并将“科学”作为批判传统的工具,认为“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步步皆踏实地”(注:《敬告青年》,《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135页。)。胡适也认为中国人传统的“盲从”、调和的思维习惯使得中国古代学术“无条理”、“无头绪”、“无系统”,而科学的特点是“尊重事实和证据”;在实际运用中,则主张以“大胆的设想、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和态度,以求真实的历史。钱穆在倡导先进的史学方法的过程中也比较激进,他认为,“过去的乾嘉汉学,诚然已具有科学精神,但终不免为经学观念所范围,同时其方法还嫌传统,不能算是严格的科学方法。要到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而言”。“除非学到西方人的科学方法,中国终将无法自存,而中国那套传统的文化理想,亦将无法广播于世界而为人类造福”(注:钱穆:《东西接触与中国文化之新趋势》,《思想与时代》第32期,1944年3月。)。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有关历史研究法的著作,如:姚永朴的《历史学研究法》(商务1914年,长沙商务印书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收馆1922年),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商务1927年)等,都详细地论述了从史料采集、鉴别、整理到史实分析、史著编写的方法。这对于现代史学方法在我国的进一步系统传播和运用,起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在西方各种史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新史家也提出了一些超越于传统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将中国的历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他们积极主张“用客观的科学方法考究历史的真相”(注:陶孟和:《新历史》,《新青年》第8卷,第1号。),努力将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和西方的科学治史方法相融合,使中国的实证史学具有封建史学所不能企及的水平。方法论是胡适史学研究的核心,他曾讲过:“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点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注:《胡适口述自传》,第5章《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在实践中,他试图把传统史学方法的近代化归结为逻辑实证化,这无疑有助于近代史学方法的科学化。傅斯年则明确地提出了史学科学化的主张,“要把历史学语音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注:傅斯年:《历史语言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为了把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体现出来,在实际中,他力倡“科学比较法”和“历史语音研究法”,力图把历史研究建立在严密考辨和形式逻辑上。其他一些史家也围绕着客观、科学的目的创建起一系列相关的方法与手段,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垣的“史源学”和“版本校勘学”、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法”等。
史学方法科学化的另一表现则是自然科学等其他一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史学领域的运用。新史学观念的拓展,史料范围的扩大,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大,要求历史研究具备各种学科的不同层次的知识和技能。在研究的过程中,新史家们认识到:“历史本身的范围既广且搏,而与之有关之学科亦复不少”(注:谷风池:《历史研究法之管见》,《史地丛刊》第1卷第3期,1922年2月。)。“研究历史,非有新科学为之基础,则无以说明历史之真相”(注: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58页。)。主张将考古学、人类学、比较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物理学、化学乃至动物学的研究方法引用到历史学中,“解释许多历史学家解释的历史上的现象”(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7月,第84-85页。)。梁启超就提出,西方社会学、热力学、心理学、伦理学、语言学、逻辑学、天文学等学科的成就和方法,可以帮助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章太炎、刘师培也认为语言文字学和逻辑学、神话学的观点和方法可以益人心智,有助于解开历史材料之迷;傅斯年的观点则更加激进,他认为:“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者以工具”(注:傅斯年:《历史语言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上述关于具体研究方法的观点对于条理古代学术研究的各种具体研究方法、总结其基本规律,提高运用的自觉性起了推动作用,为史学方法的科学化铺平了道路。
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国史学也完成了它科学化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所倡导的进化史观、客观的治史态度、广泛的史料范围和严谨的治史方法在奠定我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新格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标签:科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学论文; 新史学论文; 敬告青年论文; 新青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