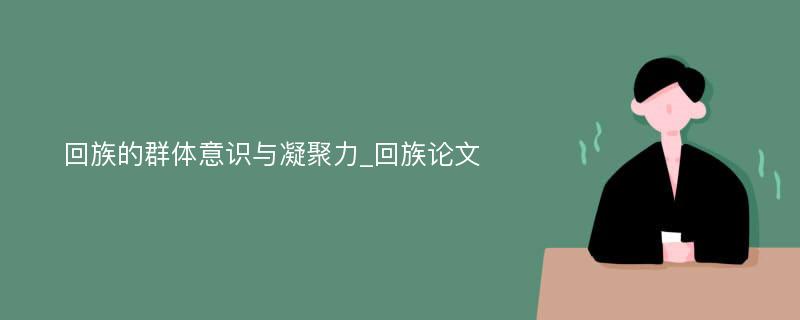
群体意识与回族凝聚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凝聚力论文,群体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1)04-0035-04
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心理特质的核心部分,是民族存在的反映,是维系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回族是一个民族凝聚力极强的民族,同时也是民族群体意识相当强烈且相当外露的民族。
一、群体意识在回族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群体是本质上有共同点的个体组成的整体。“群体——在一个相当有规律的基础之上相互影响的人和有共同特点的意识的人的集合体”。[1](P392)
一位西方哲人以形象的语言如是说:“大凡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念,所以如此不如彼,没有什么别的理由,只因为他们生在若干社会群体(Social Groups)里面。[2](P2)另一位西方心理学家对于群体所表现的特征是这样表述的:“不论组成群体的是什么人,不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职业、他们的性格,或他们的智力是否相近,他们已转化为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具有一种集体心理,使他们以一种他们各自独处时完全不同的方式感受、思考并行动。”[3](下册,P312)而中国回族学者对于群体的认识更加具体,“每个社会群体,都在为自己创造着共同文化。共同文化铸造着共同心理素质和共同的生活模式,从而使社会群体得以保持着相对的统一和稳定。”[1](P19)
每一个人都分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群体中的个体都有着相同的群体意识。这是第一层意思。
由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一个单个的个体,往往会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分属于若干个群体(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每一个不同形式的群体中,又都会有相应形式的相同的群体意识。这是第二层意思。
作为一个回族人,既是其家族群体中的一分子,又是所在社区群体中的一分子,同时作为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一分子,最后还是回族中的一分子。在上述4个群体中,这一回族个体扮演4种角色,在不同的场合下,他会有4种相对区别的群体意识。
在其他民族人眼中,回族的民族性格当中最为突出的是什么?当然是“抱团”。换言之,也就是回族群体意识极强。说爱“抱团”是回族的民族性格,虽然概括得不够确切、全面,但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同,回族人自己也不否认,有的还引以自豪。
“抱团”鲜明地反映了回族群体意识的客观存在。在回族当中,“天下回回是一家”成为许多人的一句口头语,它的出现频次相当高。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亲不亲,回回人”、“回回见面三分亲”、“回回心力齐一”、“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声色兰化知己”等。一般认为,回族穆斯林的“抱团”是一种本能,即它是与生俱来的、天然的能力,与回族穆斯林的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个穆斯林的道理一样。回族穆斯林的喜爱“抱团”往往是不论前因、不计后果的,更多的是下意识、条件反射式的。极强的群体意识,为回回民族高度凝聚力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上关于回族喜好“抱团”的记载代代有之。如明代称回回同类“相遇亲厚,视若至亲”;“党护同类”,“行赉居送,千里不持粮”;[5](P16)“夷人党护同类,固其性同然,而回回尤甚”。清代官吏在给皇帝的奏折中称(回民)“且种类遍满天下,声令周通远近,凡行客出处,以诵经咒为号,即面生无不相留,虽千里不携斧资”。民国时期亦有报道称回民凡“同教之人,在宗教的感化下,相亲如父子兄弟”。[6](P2)以上的记载,大都出自于汉族文人之手。除了“诵经咒为号”不甚确切外(实际上是回族穆斯林见面时,道问候语“色俩目”),其余的应当说还是比较真实的。
回族文献对自己民族的这种群体性也有描述,如清代马注称回民,“婚丧不振,互相资助,贸易缺资,众力扶持,小弟不能念经者,代为供膳。恩不求报,德不沽名”。[7]“天下回回是一家”实质上是伊斯兰教“穆斯林皆兄弟”的翻版。受伊斯兰教义的熏陶,回族自古历来就有互相帮助的民族传统美德。荒年扶贫济困,战时救死扶伤,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我国很多回族穆斯林地方,都有回族的慈善公益组织,在回族穆斯林遇到困难时,众人出来相助。
回族爱抱团的群体意识,一方面是因为回族的血缘关系的作用,“一个村子的多数居民都因血缘或姻亲关系而沾亲带故,”[1](P175)这使得人际关系相对稳定,形成天然的血缘群体。不过这并不奇怪,因为这种现象太司空见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回族的民族心理的作用,形成非常明显的民族凝聚力特征,这是与人们通常所见到的不同之处。
回族人口众多,地域分布广阔,早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血缘群体,也不再拥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因此回族的民族意识便更多地表现在心理素质之上的群体意识。群体意识从过去使一个较小的群体得以维系不散的精神因素,逐渐转化为回回民族这一庞大社会群体得以维系不散的精神因素。
群体意识在回族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如何?著名回族评论家李佩伦说:“数百年基本上相互隔绝的状况,却使这个命运多舛的民族始终保持同一性。遥隔千里万里的回回人,尽管语言上有差别,却没有文化上心理上的隔膜。回回见回回,哪怕无共同的乡音,而诚挚的乡情、骨肉情却无比炽热。这种内聚力,是回族得以久而不亡的原因之一”。[4](P120)
回族的群体意识产生于回族群体活动,即一种集体的活动之中。 说群体活动是集体的活动即指回族的许多民族生活是通过集体活动来实现的。如回族的民族节日,回族的婚丧嫁娶活动都是集体活动。在西北,每当有著名的回族人物(如回族的宗教领袖)归真时,往往会在一两天之内,迅速聚集起几万甚至十几万回族穆斯林,其白帽如云的宏大场面,往往令人叹为观止。甘肃临夏市每年开斋节、尔德节都要举行“荒郊会礼”,因为当地没有一个能够容纳几万、十几万人同时礼拜的清真寺。因此这种万众同声高赞“真主至大”的会礼,也就成为当地回族穆斯林群体意识的最好展示。如果有幸看到甘肃临潭西道堂群众建造清真西大寺时,那种千百人齐心协力搬运大木梁,男女老少齐上阵彻夜浇注混凝土的劳动场面的人,无不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每年一度的迎送“哈吉”前往朝觐以及朝觐归来的场合,也堪为回族穆斯林的盛大节日。
更重要的是回族一旦遇到异民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凌辱时,通常都是采用集体抗争(甚至不惜以武力抗争)的态度。例如清代陕甘回民大起义时,几乎西北地区的回族都义无反顾地参与其中。其中陕西回民起义受挫后,当地回民义军连同家属整村、整地区集体迁徒,转入甘肃董志原和宁夏金积地区,与甘宁青的回民汇合起来,继续战斗。经过清同治年间的这场悲壮的搏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是惨死疆场,或是远离故土,再也没有回去。
二、群体意识与回族凝聚力
群体意识与回族凝聚力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
首先,是从回族精神上有着寻求自身生存安全的需要。早先,回族作为一个外来民族,人数较少,因为征战、经商而散居于中华大地各个角落。社会环境对他们而言是极其陌生的,文化氛围也与其故土大相迥异,语言、心态的隔膜,足以使他们在事实上陷入生存的困境。因此,“自然形成的被包围的态势,以及面对被消融的强大压力,要生存发展,必须依赖群体,形成合力”。[4](P15)群体的存在,为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心理上的保障。
其次,从精神生活中,回族还有一个共同宗教信仰的需要。群体不仅为他们提供了精神慰藉,而且方便了他们的日常宗教礼仪生活。
再次,是回族人共同物质利益的需要。许多回族人生活在一个群体中,也因为他们可以共同分享一些实际上的物质利益。“对于基本需要满足匮乏的人来说,周围世界充满危险,就像是生活在莽林中,”[8](P52)而群体的存在无疑为那些生活上孤立无援的人提供了帮助,生产、生活上可以相互照应。对于物质需求的失意者而言,群体更是个体的心理慰藉力量的源泉。“群体对个人行为方面的要求,必须寻求完全的个人满足与个人利益受到抑制时而产生的失望所达到的程度之间的平衡”[9](P23),也许群体的深层次的魅力就在于此。
既然是群体中一员,每一个体的群体意识是必不可缺的。个体的群体意识的强弱与整体的民族凝聚力强弱是相一致的,有什么样的群体意识,就大体上有什么样的群体凝聚力。
首先,正是由于回族个体的群体意识普遍比较强烈,所以回族的整体民族凝聚力也非同一般。回族个体成员的群体意识,是一块块的砖瓦,搭建了回族宏伟的民族凝聚力大厦。
同时,回族的民族凝聚力,又通过民族群体的各种社会化过程,把群体的合作、互助、监督、约束,施之于每个群体成员,使得每一个群体成员更加置于群体的有效监护之下。
群体的凝聚力,离不开“从众心理”——即与大家保持一致的心理作用。如遇有非群体意识导致的个人行为发生以后,群体意识便可能对这种个人行为施加要求从众的压力。因为一旦发生个别人的非群体意识的个人行为以后,其他人的从众压力也会下降,所以任何一个群体都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的发生。“当一个人与大多数人态度不一致的时候,他必然会感受到极大的压力,这压力甚至足以使之改变观点,迎合多数。实践生活也说明,那些令人讨厌的‘偏离者’,往往会受到团体的排挤和各种直接或变相的惩罚”[10]。在一个群体当中,某一个体成员的与众不同,往往会使其他所有的成员感到不适、不安和不习惯。为了群体的凝聚力,严惩偏离者的举动是受到大多数群体成员拥护的,它符合全体成员的利益。
三、回族需要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
从根本上说,民族凝聚力是由民族群体及其群体成员共同创造的。但是,外界刺激——包括自然界或社会的刺激,都会对群体意识产生作用,并对民族凝聚力产生作用。回族历史也充分证明:历史上的许多次外界的刺激,在很大程度上不断地促进了回族群体意识的强化,并不断促进了回族民族凝聚力的巩固与强化。
(一)回族的民族内部凝聚力的加强,从总体上看,其积极因素是应当肯定的。
首先,民族内部凝聚力的强化,可以使得回族内部结构更加严密。“可以给予其成员支持与安全,以及伦理精神对于心理的安定力,而这些即可以阻止失望、被遗弃现象的出现”。[9](P299)一个个运转有序的回族小社区,支撑着稳定的大社会。
其次,民族内部凝聚力的加强,有利于激发奋发向上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成就需要的精神,这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因为,一个民族的“成就需要与各个文化、社会和政府的发展和命运之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关系”[11](P275),一个民族的成就需要愈高,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就愈好;相反,如果一个凝聚力很差的民族,一盘散沙,死气沉沉,缺乏活力,缺乏进取精神,那么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不啻是一个悲剧,因为它必然要拖滞整个社会前进的步伐。
回族需要不断强化民族凝聚力,这似乎与回族已经具有较强的民族凝聚力这一论点相悖。其实不然。
一方面看,回族的内部凝聚力是强的,“天下回回是一家”是客观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回族内部因局部的世俗利益而形成的形形色色小群体,却无时不在破坏着、消蚀着回族的内部凝聚力,“心理结构中沉淀为并非完全理性的(对小群体的——引者注)认同与服从”[4](P41),回回善于“窝里斗”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历史与现实生活表明:“天下回回是一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天下回回是一家’是一种不稳定的共同心理,它不具备永恒的超越一切的普遍的真理价值”[4](P36)。在以往阶级社会里,回族仍然需要以阶级分析的观点,超阶级的“回回一家”是没有的。历史上回族内部矛盾、纠纷不可谓不多。那时倘要“抛弃前隙,为教徒的自己自律,实现他们间的大团结,也并非像社会上的所宣传的那样是件容易的事”。[12](P17)至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已经消灭了阶级,但依然有不同利益阶层的问题,若想实现“回回大同”亦非易事。
(二)回族需要理性的民族凝聚力及民族心理素质。
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一方面是民族间的交流大大增加,促进了民族间的亲密关系;同时,另一方面也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各个民族自身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内部的凝聚力也在逐渐增强,这都是令人可喜的现象。
回族需要不断强化民族凝聚力,但是这种强化必须是理性的,要给予正确的方针引导,不仅仅是利己的,更重要的是利他的。简言之,回族的民族凝聚力的强化,必须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利益出发。回族强化自身的内部凝聚力,在维护自身民族的群体利益的同时,不能损害其他民族的群体利益;要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关系,而不能破坏民族团结,损害民族关系。
民族内部凝聚力的强化,如果是建立在一种不健康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就非常危险,可能导致恶劣的后果。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思想,往往会使群体中的人诱发民族利己主义情绪,它所强化了的“民族凝聚力”,将是非理性的、盲目的、狭隘的,不具有建设性。实践证明:“当社会群体增大时, 个人的行为变化更为明显。当人们置身于一大群人当中,他们似乎更易激动,更无理智,并且他们的行为更趋向于随从”。[11](P464)这种民族凝聚力支配下的群体,是极端情绪化的,容易偏激、盲从和冲动。例如,虽然有时“与外群体的冲突会增强内部的凝聚力”[13](P73),但也可能转向野蛮、仇视和狭隘——犹如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悲剧一样。这种民族凝聚力,不但无助于本民族的发展,而且往往断送一个民族的前途。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证明,要维护中国的统一,必须建立良好的、稳固的、和谐的民族关系。
建立这样的民族关系,必须使中国的各个民族都具有健康的民族心理。而回族自身具备这样健康的民族心理尤为重要。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回族中即有先进的知识分子指出:“各信各教,各享各自由,井水不犯河水,何苦无故结怨为仇呢?”[14]基于“五族共和”的思想,认为包括回族在内的“五大族的人民,应当留心政治学术,发达生计,注意建设问题,以期国基之巩固”,岂可因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致伤彼此的感情呢?”[15]近百年前,回族中人就有如此高的思想境界、如此健康的民族心理实在难能可贵。
但是,“文化之间由于地理上与种族群体间的距离,导致不同文化之间无法客观地彼此认识和评价”。[9](P23)因此要使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都培养健康的民族心理,确非易事。
历史上造成的回族与汉族、回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的悲剧数不胜数,除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有意离间、肆意挑唆以外,也与回族和相关的民族不同程度地存在民族关系上的认识误区有关。包括回、汉等民族的人们在内,此一群体的人们往往误认为自己对彼一群体的观点是千真万确的;此一群体与彼一群体的差异被无限地夸大。即使是如今也不能完全消除这种认识误区,旧有的误区不能消除,于是它便经常作祟,结果使得“历史上的民族纠纷往往影响当前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而社会主义某些时期,由于党和政府在政策上出现的某些比较严重的失误,把很多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这也使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产生了严重的逆反、抵制心理。有的群众由于狭隘的民族心理,走不出历史的阴影,因而也往往在“现在生活中民族关系紧张”时,“容易纠缠历史上民族纠纷的旧帐”,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进一步损害了民族关系。
民族政策的失误、民族工作的失误,也在某些方面给少数具有不健康民族心理的人提供了口实,使得这些人的民族情绪恶性膨胀,甚至个别坏人乘机兴风作浪 ,破坏民族团结。
回族的长期苦难历史,造就了一部分回族人对于外部的刺激极为敏感,也确有不少回族人的心理发生某些扭曲。回族社会人为的封闭性、排他性便是例子。但是,不仅非回族不以为然,回族中的有识之士亦指出:回族的“封闭性、排它性、似乎是自怜自爱,实质上是画地为牢,近于自我扼杀”。[4](P11)
回族从本质上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民族、心胸开阔的民族,正是这种思想开放与心胸开阔的特质,才使回族不断成长、发展、壮大。我们也看到在开放与开阔的过程中,虽然会产生一些文化间的相互吸收现象,虽然会带来某些文化特征“损耗”的现象,但从总体上看,这是值得的。因为没有思想上的开放,没有心胸的开阔,依然在文化上坚持绝对的自我封闭与排它,就肯定没有今天的回族。
民族他识意识与民族自识意识一样,同属于民族内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民族他识意识在内的回回民族内部结构,是影响回族与其它兄弟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内因。民族内部结构的调整,是促进民族关系正常发展获得动力、协调力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当代回族应该发扬先辈思想开放、心胸开阔的精神,调整好民族内部结构,树立健康的民族心理,谋求与其他兄弟民族的长期和睦相处,集中精力发展本民族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实现与兄弟民族的共同进步。
我们应当在全体回族人民当中牢固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即协调民族关系必须以兼顾自身民族利益和其他民族利益为基础。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利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但同时也要承认其他民族同样有着维护人家自己民族利益的权利。因而,在不同民族之间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做出某种妥协,某种让步,换言之,就是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时,要适当地承担某些自我牺牲,承担某些责任和义务。
收稿日期:2000-1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