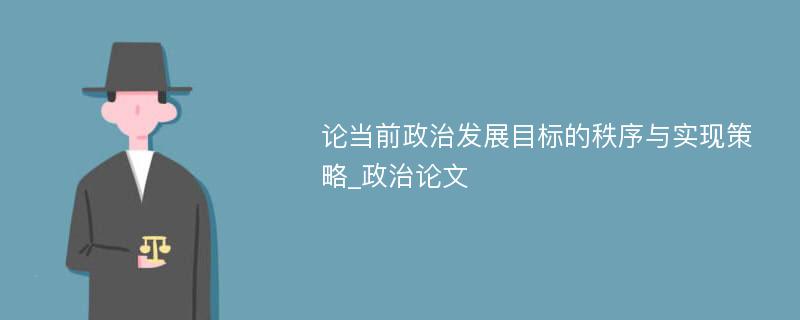
论当前政治发展目标的次序和实现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次序论文,发展目标论文,策略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类迈向21世纪时,中国的社会转型也进入了最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政治发展领域的任何变革都影响深远,非常敏感和复杂,因而必须对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次序和实现策略进行厘定和设计。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通过扩大政治参与的水平和层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另一方面,“现代性有助于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则孕育了不稳定。”(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转型时期是政治不稳定的高发期,对于中国这个正处在现代化关键时期的超大社会来讲,现实地存在着许多影响政治稳定的危险因素,而没有政治稳定,经济政治发展就失去了首要的前提条件,因此,“稳定压倒一切”,政治稳定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也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提、也因之成为首要目标。正确处理扩大政治参与和维护政治稳定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当前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之一。
维护政治稳定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对于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而言,一个强大的政党是实现政治稳定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同有强大政党的体系相比,在没有强有力政党的政治体系中,更容易出现暴乱、骚动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不安定。”(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397页)对于政党数量、政党力量和政治稳定的关系,亨延顿认为:“在高度现代化的国家,政党数量多寡无碍于它拥有强壮之势;而在低度现代化国家,一党制可强可弱,但多党制却毫无例外都是软弱的。……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稳定的多党制。在发展中国家,一党制要比多党制稳定得多。……在现代化中国家,多党制与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以及政治安定是不能共存的。”(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08—410页)简言之,亨廷顿的逻辑是,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需要政治稳定,政治稳定需要政府权威来保障。政府权威又源于强大的政党,强大政党往往产生于一党制国家。对中国而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本支柱,是实现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保障。
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和利益的多元化,坚持党的领导必然要求对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进行转换。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不管如何给界定,其基本含义是人民对政治权威的信赖、认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普遍支持和拥护。但这种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获得方式和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党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础与获得方式也是不断发展转换的。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政权,确立了自己的政治权威,其合法性与合理性是通过革命方式取得的,是一种“革命的合法性”。取得政权以后,党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全面进步,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人民群众普遍受益,党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这时候,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实际上已经建立在其领导绩效基础上了,是一种“绩效合法性”。但是,这种建立在政策有效性基础上的权威,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因为,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始终如一地保持良好的绩效,这不仅是因为政府施政难免存在失误,而且由于经济运行周期自身的变化也使政府绩效时有起伏。退一步讲,即使始终能保持一定的政策绩效,也不可能让所有社会群体普遍受益。因此,必须对这种建立在政策绩效基础上的领导合法性进行转换。江泽民同志最近也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更好地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展的重大变化,来深入思考这个重大问题。”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考这个重大问题的方向之一是将政府领导的权威通过公共选择也就是通过量化的民意:体现出来并合法化。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直接民主选举的拓展与深化。显而易见,这对党的领导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是对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一种形式上的挑战,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的一大特点就是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
至此,我们可以把当前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节”化约为:稳定是政治发展的首要目标,要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就必然依靠中国共产党的整合作用,而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的领导,实现政治稳定的可持续性,就必须拓展实质性的政治参与,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而这又可能使党的领导地位受到一定挑战。这就决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目标的多元性、复杂性甚至冲突性;既要扩大政治参与,又要保持稳定;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扩大直接选举。在当前这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这种复杂情境,必须对政治发展目标的次序和实现策略进行权衡。主要是:
一、发展党内民主重于发展党外民主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党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党内民主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处于核心和关键地位。邓小平历来非常重视发展党内民主,重视党内民主对于整个社会主义民主的推动作用。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就指出“(民主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首先要从党内造成。……如果党内造不成,国家也造不成。我们党一定要造成这样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内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6—307 页)他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多次提出“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0、155页)他的一个基本思想是, 用党内民主的发展来推动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思想无疑是深刻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因为,党是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执政党的地位决定了党内生活民主化对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决定性制约作用。从党的任务看,党的大事也就是国家的大事,党内重大问题能够民主决策,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就有了基础。从历史经验看,什么时候党内民主正常、活跃,社会主义民主就发展得快而好,什么时候党内民主遭到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必定受挫。从党与社会的关系看,党是先锋队,“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民主的模范。党内民主发展了、健全了,全国人民就会学习、效仿,整个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程度也会随之大大提高。从可行性看,党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标的集团,成员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高,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推动整个社会的政治民主,成本是最低的,风险也是最低的。
二、发展基层民主重于发展高层民主
虽然发展党内民主非常重要,但如果民主发展只局限于党内也是不现实的。社会政治民主发展也必须有所推进。那么,社会政治民主推进的重要方向是由上之下还是相反?十五大指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也就是说,由下至上地发展社会政治民主是一个符合社会转型关键时期情境要求的、理性的现实选择。
中国民主建设社会的基层开始,具有重要的意义。民主是人与生俱来的政治权利,而民主权利的行使是有条件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 页)只有适合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大多数民众乐于接受、能够具体操作的民主,才是最积极、最有效的民主形式。缺乏经济基础及由经济基础所制约的其他社会条件的支撑,即使借用现代民主的一些形式,也是徒有民主的空壳。对中国这样一个基本没有民主传统的社会而言,民主只能是一种初创型的民主。(邹树彬“从村自治到基层政权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夏季号。)这一现实,决定了必须通过实际的民主训练逐渐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也就是说只有民主的实践才能建设民主。基层民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就是民众不断学习关于民主政治知识的过程,正是在民主实践和民主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公民的民主意识才会发展起来,提高政治认知程度,增强民主意识,培养民主习惯,学会民主管理。基层民主制度的设计及其运作是在其熟悉的活动空间内进行的,且与其个人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如从基层起步,渐次积累,整个社会的民主化的逐级演进才会有足够的资本,且实施成本也比较低。同时,中央政府还可以通过发展基层民主,借助民众的监督,抑制基层地方官员的牟利行为,增强权威中心的向心力。
目前,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核心内容的村民自治已经成为发展民主的伟大实践,但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而不是政权组织,所以村级民主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民主。必须在村民自治发展完善的基础上将村民自治的精神和逻辑提升层次,引入到至少乡镇一级的基层政权中。值得一提的是,从1999年开始,全国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进行完善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探索,(刘喜堂“关于发展乡级民主的调查与思考”,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2 期)例如四川隧宁县步云乡直接选举乡长、四川南部县公推公选副乡镇长、深圳大鹏镇用“两票制”推选镇长等,虽然这些探索的具体操作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根据现行法律,选举乡长是乡镇人大的职权,所以步云乡的直选乡长有违宪之嫌。)但需要肯定的是,这些探索所包含的精神和价值符合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要求,应该有组织地进行试点和推广,例如可以采用全国人大特别授权的方式进行乡镇长直选试点,使民主政治有步骤地由下至上推进。
三、遏制腐败蔓延重于发展政治民主
在当前,对中国政治稳定威胁最大的因素,不是政治民主化程度不高,也不是“人权记录差”,而是腐败的蔓延和扩散。最近10年以来,反腐败取得了较大成绩,但腐败的蔓延和扩散的态势一直未能得到遏制。如果说中国出现“认同危机”或者说“合法性危机”,必然首先是来源于人民群众对惩治腐败的失望。因为,“腐败浪费了一个国家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源,即政府的合法性”。(约瑟夫·纳伊“腐败与政治发展:成本—效益分析”,载《腐败与反腐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1页)不仅如此,腐败还破坏政治关系,阻碍政治过程, 毒化社会政治心理,动摇和瓦解政治制度的阶级基础,阻挠政治发展。(羊龙“反对腐败的政治学思考”,载《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2期)最近, 李光耀在1999《财富》全球论坛上以“第三只眼睛”展望中国的发展趋势时就指出:(对中国发展)“危害最大的问题是已深入行政文化的腐败难以根除。腐败不仅严重阻碍经济发展,更危险的是它已成为政治(稳定)的火药桶,对腐败的不满会很容易集聚起反政府的情绪。”(李光耀“中国——经济巨人?”,见《大公报》1999年9月30日A7版。 )因此,在当前的政治发展中,惩治腐败比发展民主更重要,更迫切,更具有现实意义。虽然从学理上讲,扩大政治参与,加强人民群众对干部的监督也是消除腐败的重要对策,但对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社会而言,通过大规模地扩展政治参与来遏制腐败可能是一个陷阱。在惩治腐败的问题上,香港的经验或许有启发性。在九七回归以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港督高度专权,政治管治不以香港市民的同意为基础,根本没有民主可言,20世纪60年代香港也是“遍地贪污”,但自廉政公署成立以来,香港惩治腐败的工作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其成功经验主要是:(1)政府高层的肃贪决心;(2)反贪机构的独立性;(3 )广大市民的支持;(4)调查、防范、社区教育“三管齐下”的工作方法;(5)强大的法律权力;(6)足够的资源等。(杨奇《香港概论》(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在我们这个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基本价值理念的国家,有效遏制腐败蔓延应该说比香港更具有有利条件。因此通过改革纪委领导体制,增强反贪机构的独立性等措施,确实遏制腐败的蔓延也是可能的。
四、提高政府能力重于扩大政治参与
阿尔蒙德曾深刻地总结到:“要人民参政首先政府必须具有能力。如果没有办事的方法,参与办事也就毫无意义;如果没有实施决定的方法和能力,参与决定就没有必要。”“要分配就必须先有经济的增长,要有福利就必须先有财富。如果没有产品和服务用的资料,就没有什么可分配的。”(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罗荣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363页)在当前这个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发展经济是最大的政治。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水平,促进社会公平,对于维护政治稳定和保持政府的合法性与权威至关重要。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政府的能力和有效性是关键。正如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D·沃尔芬森在1997 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所指出:“历史反复地表明,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须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199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另一方面,现阶段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动机主要是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着眼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因此,通过行政改革(转变职能、精简机构、依法行政、反对官僚主义、提高公务员素质、加强政府决策的科学化等)提高政府能力(如社会动员与调控能力)、政策创新与贯彻能力、整合能力等)促进经济发展是减缓政治参与压力的重要策略,也是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