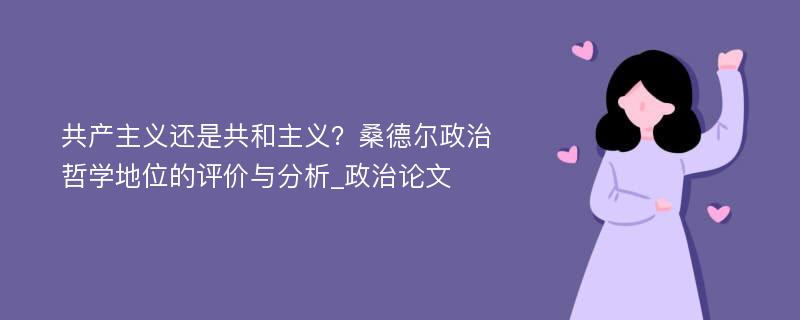
共同体主义还是共和主义?——桑德尔政治哲学立场评定与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共和论文,共同体论文,德尔论文,立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一、何种立场?何种主张?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是罗尔斯众多批评者中的代表性人物。在其成名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中,桑德尔对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及其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有力批评。并正是因为这本影响广泛的著作,桑德尔同其他几位政治哲学家,如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查尔斯·泰勒、迈克尔·沃尔泽等人一起,被西方自由主义者们冠以“共同体主义”① 之名,并掀起了势头强劲的“自由主义-共同体主义”之争。
在桑德尔看来,罗尔斯的选择性的自我及“自我优先于其目的”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是非常有害的。它错在:这种静态的、孤立的自我观念与我们的自我知识不一致;它的有害性在于:它在自我和世界之间拉开了距离,并预先排除了一些重要的个人的或政治的可能性。“如此彻底独立的自我排除了任何与构成性意义上的占有紧密相连的善(或恶)观念。它排除了任何依附的可能性,而这种依附能够超过我们的价值和情感,成为我们的身份本身。它也排除了一种公共生活的可能性,在这种生活中,参与者的身份与利益或好或坏都是至关重要的。它还排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共同的追求和目的能或多或少地激发扩展性的自我理解,以至于在构成性的意义上确定共同体。”② 因而罗尔斯式的这种抽象的、无设定的自我肯定也是一个空洞的、在道德意义上不能自知的自我。而且,这种自我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完全是一种臆想,现实生活中的任何自我都必然受到各种归属的制约。
此外,桑德尔还进一步反对了那种以抽象的自我观念为基础的权利之优先性理论。依桑德尔之见,新自由主义在“自我优先于目的”这一理论基础上认为权利在以下两种意义上优先于善:第一,权利优先意味着不能因普遍的善而牺牲个人权利;第二,界定这些权利的正义原则不能建立在任何特定的良好生活的观念之上。桑德尔指出,这第二种意义上的优先性主张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正确的观点应当是:权利以及界定权利的正义原则都必须建立在普遍的善之上,善优先于权利和正义原则。
由此,桑德尔强调“自我”与共同体之间的纽带,强调“自我”不能脱离于或逻辑在先于其所赖以生存的共同体:“自我”总是某个共同体中的自我,总是要受到共同体纽带的型塑与影响;共同体是身份与道德义务的源泉,“自我”不可能像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优先于目的”,自我的选择必然要受到共同体的制约。同样,个体的权利也不能脱离于共同体的目的及善观念而获得正当性证明;共同体的善观念逻辑在先于共同体成员的个体权利。正是这种对于共同体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强调,桑德尔获得了“共同体主义者”的称号。然而这一称号却异常尴尬。其一,这一称号并非出自桑德尔的本意,而是来自于他人。他主要反对罗尔斯式的抽象的、无设定的自我以及“自我优先于目的”的论断,却并没有意图要将对共同体的强调上升为一种主义并加以发展。“共同体主义者”其实是他人——主要是桑德尔的批评者——对他的称谓(其中不乏讥讽意味)。其二,桑德尔本人也并不满意于“共同体主义者”这一称号,相反,他异常谨慎地仅仅在某一方面认为“共同体主义”这一术语能够描述他对共同体的考虑和强调。“由于我的部分论据是当代自由主义缺乏对于共同体的考虑,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共同体主义’这一术语适合我的这本书。”③ 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他认为“共同体主义”这一标签具有误导性,并竭力刻意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从来都没有用过‘共同体主义’来形容我自己的观点,而是其他人用它来形容我的观点。我之所以不用共同体主义是因为,共同体主义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共同体主义经常意味着,正义和权利仅仅依赖于那些恰好在某些特定时刻、在某些共同体中盛行的各种价值观。这并不是我所接受的正义观和权利观,因为,如果将正义和权利仅仅与那些在某个特定时刻盛行的价值联系在一起,就会使得正义和权利完全变成一种传统、变成一种恰好所是的东西;这也剥夺了正义和权利的重要特征;更会导致‘多数主义(Majoritarianism)’。我不赞成‘共同体主义’这一术语所暗含的多数主义倾向,因此我拒绝用‘共同体主义’来描述我的思想。”④
如果说,桑德尔在《自由主义及正义的局限》一书中所体现出来的对共同体的强调,使他无意间获得了他自己并不满意的“共同体主义杰出代表”这一称号;那么,他在十余年之后出版的另一本引起广泛讨论的《民主的不足》(Democracy’s Discontent,1996)一书中,则是有意与“共同体主义”拉开距离。正如理查德·达戈尔(Richard Dagger)所说,桑德尔在《民主的不足》里完全站在共和主义的立场之上,并将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立起来,这成为《民主的不足》一书的主旨之一。⑤ 桑德尔在本书中回顾与梳理了美国政治和宪政历史的发展脉络,并试图向我们表明:美国当今占据主导地位的程序自由主义并非唯一的公共哲学,它取代公民共和主义成为主导公共哲学实际上只是近些年来的暂时胜利。美国有着悠久而深远的公民共和主义影响,而且当代美国也需要公民共和主义来弥补程序自由主义的不足。
桑德尔试图向我们描绘这样一幅充满悖论的美国政治图景。一方面,程序自由主义取代公民共和主义,成为主导美国公共生活(包括制度和实践)的公共哲学,具体表现为:个人权利的伸张,不受限制的、意志论的自我形象的膨胀。另一方面,在公共生活领域中,人们又逐渐丧失自主性,挫折感也随之增加,如传统社群的瓦解,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失望等等(这就是所谓的“民主之不足”)。进一步说就是,自由主义的自我形象与现代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组织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即使当我们作为可以自由选择的、独立的自我而思想和行动时,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依然受到非人化的权力结构的支配,这种权力结构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和控制。对此,他建议重新振兴美国历史上的公民共和主义思想,用一种“公益政治”和“美德政治”来代替当前的“权利政治”和“中立政治”。
在明确了其对于公民共和主义的追寻之后,桑德尔更加鲜明而坚定地讨论共和主义的具体主张。在2009年9月出版的新作《正义:何谓正当之为?》(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一书中,桑德尔继续明确而集中地反对功利主义和罗尔斯式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并大力提倡第三种正义观以及共同善的政治。
桑德尔在此书中通过各种历史实例和政治争论描述了三种正义观:一种是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它认为正义就意味着效用或福利的最大化,也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它认为正义意味着尊重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这包括尊重人们在实际自由市场中所作出的选择,也包括在假想的原初状态中所作出的选择;第三种观点认为正义应当涉及德性的培养以及关于公共善的论证。在桑德尔看来,前两种正义观都有缺陷。功利主义正义观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它使得正义和权利变成一种算计,而非原则;另一方面,它将人类善转换成单一的、关于价值的制式衡量,这样就使得人们对各种价值等量齐观,而没有考虑到各种价值之间质的区别。以自由为基础的理论克服了功利主义的第一种缺陷,而保留了第二种。自由主义的正义观看重权利,并坚持认为正义不仅仅是一种算计。然而它却并不要求我们质疑或挑战我们带入公共生活中的那些偏好和欲望。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所追求的目的的道德价值、我们生活方式的意义以及我们所共享的公共生活的特质,都在正义的领域之外。桑德尔认为这两种理论都是错误的。在他看来,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功利最大化或保障选择的自由,就能达到一个正义的社会;我们必须通过共同讨论良善生活的意义以及建立一种公共文化来接纳那些不可避免的分歧,才能达到一个正义的社会。此外,正义不可能不作判断,而且正义问题注定要与不同的荣誉观、德性观以及认知观绑定在一起。在桑德尔看来,正义不仅仅关涉正确地分配事物,同时也关涉到正确地评价事物。
基于这种正义观,桑德尔提出了“共同善的政治”,并为这一新型的共同善的政治设定了四个主题。第一,如果一个正义的社会需要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感,那么它就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教导公民为总体考虑、为共同善做贡献,培养他们的公民德性,并反对将良善生活的观念私人化。第二,为市场设立道德界线。因为市场化社会行为能够腐蚀人们的道德,因此我们需要公开讨论如何为市场设立道德界线。第三,桑德尔提出了与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的另一种反对不平等的理由,即认为贫富之间的差距破坏了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团结。因此他主张这种新型的共同善的政治应当向富人征税以建设和完善各种公共设施及服务,以给不同阶层的人们创造共同活动的空间,培养他们的共同体感。第四,这种新型的共同善的政治需要更多的公民道德参与。在桑德尔看来,道德参与的政治不仅仅是一个更加理想的政治,它也为正义社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从以上对于桑德尔主要政治哲学思想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他的政治哲学思想涉及“共同体主义”和“共和主义”这两种思潮,而且他甚至还是“共同体主义”这一标签之所以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他本人及其在后期所表达出的政治哲学都明确表明,他排斥“共同体主义”,而坚定地站在公民共和主义的立场,并为之提出了具体的论证和辩护。
二、为什么要排斥或转换?
评定桑德尔的政治哲学立场并非本文的主要目的,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进一步剖析为什么桑德尔要排斥“共同体主义”这一标签,而更加愿意选择共和主义的政治哲学立场。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桑德尔政治哲学的具体主张,就可以看出,他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所引发的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罗尔斯认为正当优先于善,政治、正义独立于各种道德善观念。而桑德尔则认为政治无法脱离道德,他所担心的是:如果正当优先于善,而且政治正义真的中立于各种不同善观念的争论、独立于各种“道德善观念”之外,那么,政治就会变成一种无道德的政治。而无道德的政治不仅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在道德上也是不应该的。因此,可以说,桑德尔政治哲学主要集中于一个主旨:试图复兴共和主义所倡导的政治与美德的关系。
然而,“共同体主义”这一思潮由于其自身的内在缺陷和发展困境,它无法代表或实现桑德尔政治哲学的主旨。这是因为:
1.从总体上来看,“共同体主义”本身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概念,它在当代的复兴主要是为了反对自由主义、尤其是罗尔斯正义论的“普遍主义”、“个人主义”及其自我观、权利观和正义观。被称为“共同体主义者”的几位代表人物并没有自己明确而系统的,关于共同体主义的理论主张;即使是在对罗尔斯及其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进行批判时,他们也没有清楚地、系统地进行论证,而只是从不同的维度强调:社会制度安排以及权利、正义都不能忽视共同体的作用和地位。正如艾米·顾特曼(Amy Gutmann)所指出的:共同体主义的唯一贡献,就是它明确地强调要关心共同体,这是对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补充。⑥ 当代西方的共同体主义从总体上来说,都相信共同体的构成性作用,即认为共同体完全或根本地构成我们的身份,以至于“我们是谁”首要地并不可避免地取决于我们对某一特殊共同体之生活方式的参与;它们都强调各种形式的共同体、各种类型的历史和各种文化传统或道德谱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作用与意义,以及其他特殊的社会文化因素对人们行为的复杂影响、对社会制度安排的内在制约、对社会普遍正义及其实现的限制,如此等等。但是,当代西方的共同体主义一方面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按照其他几种“主义”的定义标准来看,共同体主义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甚精准。因此可以说,共同体主义其实不能算作一种“主义”。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主义”在理论上因为不成体系而容易受到各种诟病,同时也没有实际的倡导力。
共和主义与此不同,它有着悠久的理论渊源,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亚维里,启蒙运动时期的卢梭,再到后来的列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直至当代的波考克、菲利浦·佩迪特等等。共和主义虽然几经波澜,却一直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和政治主张而活跃于人类的思想和政治生活之中,并成为唯一一种能够与自由主义分庭抗礼的主义和政治理论。根据桑德尔在《民主的不足》一书中所指出的,共和主义传统在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自由主义取代共和主义传统而在美国社会占据主导地位,也只是近些年所发生的状况。共和主义本着整体主义的、反个人主义的精神,明确地强调政治的目的性,强调国家本身,强调爱国主义与社会的共同善;它主张社会优先于政府,主张公民社会以及公民美德的优先性,主张多元一统的整合原则,主张道德主义的政治、法治;共和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哲学基础是:国家神圣原则以及任何政治、法律都不仅要具备政治合法性,也要符合道德正当性。
由此可见,共和主义的理论主张及其精神与桑德尔的政治理论诉求十分契合。只有进一步运用和发展共和主义的理论资源,才能达到桑德尔将政治重新与道德联系起来的政治理论目标。这种理论力量是“共同体主义”所不具有的,这就是为什么桑德尔避共同体主义而就共和主义的原因之一。
2.从对于公共善的理解来看,共同体主义自身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而经常受到诟病。按照共同体主义的主要理论关注点,它强调共同体的价值,强调对于共同善的维护。它认为,权利的正当性辩护,应当依赖于特定时期在特定共同体内盛行的各种价值观;正义和权利仅仅也依赖于那些恰好在某些特定时刻、在某些共同体中盛行的各种价值观。也就是说,共同体主义的这种对共同体以及公共善的强调,会导致人们根据共同体的价值观来界定权利,那么,“公意”或公共善就仅仅依赖于该共同体的传统,共同体主义因而也就具有传统主义或大多数主义的涵义,它们采纳任何恰好体现于传统之中的各种善观念,并试图根据这些善观念来统治。而这种意义上的共同体主义则有可能允许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如果我们的权利仅仅是我们的共同体所恰好支持的各种权利,那么,该共同体中的大多数就没有尊重某些特定的权利。如果我们赖以确立权利和正义制度安排的公共善,就是共同体所恰好尊重和重视的善,那么,这种公共善就仅仅取决于共同体的传统,同时也具有相对性和压迫性的危险。在我们这样一个民主多元且自由平等权利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这种公共善不但不能将政治与道德粘合起来以实现桑德尔政治哲学的初衷,反而正是自由主义者要将政治与道德分开,强调政府中立性的根本原因。
共和主义对于共同善的理解与此不同,其最重要的假设是:最高的政治目标在于对“公共善”的追求,而“这种共同利益不像我们今天可能会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构成共同体之特殊利益的交叉总和。它毋宁本身就是一个实体,先在于集团和个人的各种私人利益,并与之相区分。”⑦ 易言之,在共和主义者们看来,善观念不仅仅取决于共同体中此刻所流行的各种价值观。在一种独立的观点上,他们还可以批判某些盛行的观念。共和主义的善观念与培养公民德性有关,这些公民德性将使他们能够很好地商议公共善,并去关心公共善,而不仅仅是个人利益。共同体主义的观念可能并不包括这些价值,它可能完全依赖于那些作为一种习俗而恰好存在于该共同体的传统之中的价值观。共和主义的善观念体现出某种自由理念以及那种最佳生活方式,即:共享自治。关于公共善以及这些善目的商议,并不一定要体现于该共同体或传统之中。那么,共和主义的善观念和自由观就可能与该传统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之中,它不会仅仅接受那些恰好流行的各种价值观。因此,共和主义为那种在许多社会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政治,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视角。
共和主义的这种对公共善的理解,及其衍生出来的对公民德性和公民参与的强调,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批判性的视角,是桑德尔力图摆脱“共同体主义”的标签而发展共和主义的主要原因。理查德·达戈尔看到了桑德尔的这种刻意的回避,在他看来,桑德尔在《民主的不足》一书中继续反对权利对善的优先性,然而他更加明显地将自己定位于一个认同构成性的政治、培养自治所需要的公民素质的共和主义者的立场,而不是一个认同在特定时间、特定共同体内流行的价值和偏好的共同体主义的立场。毕竟,这些价值和偏好可能会养成野心、贪婪、懒惰以及其他一些完全不同于,甚至是与自治所需要的相反的品质。因此,“桑德尔将自己与共同体主义拉开一段距离是十分明智的,更明智的是他接受了共和主义对于形塑公民以及培养公民德性的强调。”⑧
3.从对于自由和权利的理解来看,共同体主义在这两个重要方面的模糊立场,也导致了它无法切实有力地将道德与政治联合起来而实现桑德尔政治哲学的初衷。
正如斯蒂芬·考茨所指出的:“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中的许多争论,实际上是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争论的复兴。共同体的观念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来说是这些民主或共和争论的一种新的融合:即将民主所关注的平等以及共和所关注的德性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一种新的共同体观念。”⑨ 这种融合而成的共同体观念,可能吸收了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这两种理论的优点;但也有可能会因为要融合而丢失了两种理论所具有的独特立场。一方面,共同体主义虽然反对自由主义的个人观及其对共同体的忽视,可是它又接受或不排斥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及其衍生出来的个体权利观;并且,它没有具体地论述个体权利,也没有提出自己的自由观和权利观。另一方面,它在力图复兴公共善的同时,又不愿意或不明确地接受共和主义的强版本的自由观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对公民性权利的强调。可是,如果信奉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观,就很难切实地强调对共同体这一维度的关注,强调对公共善的考量。因为一个信奉自由主义个体权利的人,很难会考虑到公共善,很难为共同体的利益而损失或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样一来,对共同体的维度,对公共善的强调也就会流于形式而无法实行。这也是共同体主义自身的尴尬之处。
虽然当代的新兴共和主义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即在强调公共善和公民参与、公民德性时,要如何应对那些广为流传的,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和权利观;可是,在共和主义的传统中,却有着与自由主义不同的权利观和自由观。首先,共和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自由观或市场中的自由、消费的自由而赞成公民的自由观,认为参与公共事务、参与自治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作为公民所行使的自由,要比我们作为消费者所行使的自由更为重要。这种公民的自由观涉及对公共善的商议、对公共事务和共享自治的商议。由这种自由观出发,共和主义从团结、成员观念的立场对权利进行论证,而不是像康德那样,从那种尊重人的立场出发而进行论证,并由此赋予以下几种权利以优先权:参与自治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意志自由的权利、宗教自由的权利以及享受某种教育的权利——这种教育将使每个人都能商议公共善。由此可见,在共和主义的理论中,公民们享受着自己的公民自由,行使那种参与讨论公共事务、公共善、进行共享自治的权利,并获得那种培养参与公共讨论之能力的教育,这样一幅图景,正是桑德尔所期望的景象。在这幅政治景象中,政治不可能中立于道德;因为在商议社会制度安排和正义观念时,公民们不可能避免讨论什么是公共善、什么是良善生活;并且他们不赋予任何权利以特殊的优先权,而是以一种反思的态度去讨论商议各种权利和制度安排;此外,公民从公民教育中也会获得那种与公共善和良好生活方式相关的,参与政治参与商讨的公民素质。这是桑德尔所需要的政治理论,它比共同体主义的要求更加明确、立场更加坚定,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提出各种明确的途径,如公民参与自治,参与讨论公共事务、公共善,追求某种良善生活以及进行公民教育等,而能够切实可行地使政治无法脱离于道德,以还原政治生活、政治制度的道德维度。
三、共和主义能否胜任?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共和主义应该更契合桑德尔的政治哲学理想,更容易将政治与道德粘合起来。这也是桑德尔为什么避共同体主义而就共和主义的原因。尽管如此,当代的共和主义却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其自身也有着尴尬之处。它是否能够实现桑德尔政治哲学的理想,要取决于他所支持和代表的共和主义对以下几个难题的态度或解决之道。
第一,当代共和主义如何面对那普遍盛行、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深入人心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及其权利观?
我们在当代社会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我们既关注隐私,又渴望共同体;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由主义者,然而我们又希望逃脱那种既具有解放性又能腐蚀我们的现代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而且我们也不可能返回到传统的共同体之中。因此,在现代这个“德性之后”的社会,我们是否可能复兴道德共同体或共和主义的公民,而同时又不放弃我们的这样一种共识,即我们是一个个的个体,我们无法逃避自由主义的精神诉求,而且它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令人艳羡的。正如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要依赖于一种共同体感以及公民参与,当代共和主义也不得不接受或包容自由主义某些原则和权利的认同,如宽容、公平竞争以及尊重他人权利等等。那么,该如何既坚持共和主义的基本立场,而同时又融合某些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和权利观呢?这是当代共和主义所必须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当代共和主义者们,如桑德尔,没有明确地具体论述共和主义的具体权利条目或形成系统的新共和主义理论体系和理论主张的原因。
第二,在如今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如何达到共和主义所强调的公共善以及良善的生活方式?
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问题是:文化多元化和文化价值观念多样性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事实,这种多元性“不仅是民主社会的基本事实,而且也是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因为正是民主社会所奉行的自由开放信念和自由民主之社会制度的激励,多元化的文化传统和多种多样的文化价值观念或道德伦理谱系才可能在民主社会里获得自由生长和发展的自由空间。”⑩ 那么,作为社会整体的国家如何在社会基本政治结构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制度层面,达成关于公共善的认识,形成普遍有效的政治的正义原则以及推进某种良善生活观念?古典共和主义是整体论的和一元化的,受当时地理因素的影响,公民们在城邦内经过商议容易形成对于公共善、正义原则以及良善生活方式的认识。然而,当代的多元社会,凸显出了古典共和主义的那种整体论和一元化的局限。而且,在政治理论多元化、民主形式多样化、自由主义思想影响较为广泛和深刻的现代社会,我们很难在信奉不同价值观的公民中间就公共善达成共识,也很难推进一种良善生活。
此外,传统共和主义认为,公民身份和公民美德对于公民能否参与自治以及能否很好地实现自治、能否商讨公共善而言,十分重要。因此,公民必须具有某些卓越品质——具有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美德与能力,对公共事务的判断力以及关心集体等。于是政府和各种社会机构应该加强公民教育,而且考虑到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要求,成员的范围越广泛,培养德性的任务就越紧迫。然而,正如许多自由主义者所合理地担心的那样,这种强制性的、灵魂塑造般的公民教育有着强迫的危险,它与平等、自由的共和主义理念背道而驰,而且其成效也令人怀疑。
第三,共和主义如何解决民主与平等的问题?
即使我们能够从政府或公共机构所进行的公民教育中获得那种参与政治、参与商讨的公民德性,并且理想地就“什么是公共善、什么才是值得追求的良善生活”达成了一致意见,那么,这种公共善的观念,形成普遍有效的政治的正义原则以及良善生活观念,就是可欲求的吗?它是否是一种由政府认可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呢?
古典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卢梭强调公共善,号召公民绝对服从于“社会公意”,进而导致了其自身哲学的尴尬境地。卢梭的共和主义后来成为人们将共和主义与集权联系起来的主要原因。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卢梭的原因;而实际上,民主与平等、民主与自由之间本身就暗含着一种张力。如果通过民主商议而达到对公共善的认识,形成普遍有效的政治正义原则和社会制度安排,那么,就总是有可能忽视或压抑了少部分人的意见和利益。因此,卢梭的共和主义、他对社会公意的极致强调,正是对共和主义理论自身所具有的危险的一种极致的表达。当代共和主义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中要发挥作用,要真正地复兴以在政治领域纳入道德的维度,就还要考虑这样的问题,即它应该如何面对并化解自身所存在的这种内在张力。
注释:
① Communitarianism,国内又译社群主义。
② Michael J.Sandel,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2,p.62.
③ Michael J.Sandel,Public Philosophy:Essays on Morality in Politic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52.
④ 此部分内容源于笔者就这一问题对桑德尔教授本人所进行的访谈。
⑤ Richard Dagger,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61,no.2,Spring 1999,p.182.
⑥ Amy Gutmann,“Communitarian Critics of Liberalism”,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4,no.3,Summer 1985,pp.308-322.
⑦ Wood,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8,p.59.
⑧ Richard Dagger,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61,no.2,Spring 1999,p.183.
⑨ Steven Kautz,Liberalism and Communi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Ithaca & London,1995,p.2.
⑩ 万俊人:《罗尔斯问题》,《求是学刊》,2007年第1期,第18页。
标签:政治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桑德尔论文; 政治哲学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