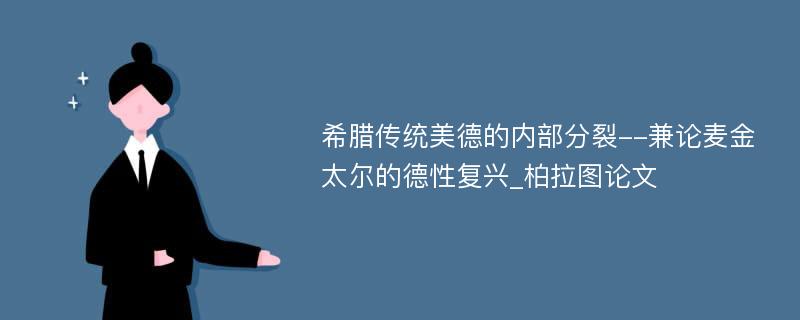
浅析希腊传统德性的内在分裂——兼论麦金太尔的德性复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性论文,希腊论文,传统论文,兼论麦金太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2)06-0083-05
在麦金太尔看来,现代社会对传统德性的摒弃使自我因丧失了德性的根基而丧失了自我的完整性,最终使现代人沦为了欧文·戈夫曼所描绘的角色之衣借以悬挂的衣架。麦金太尔认为希腊传统德性具有超越城邦政治的一般人类实践的普遍意义,因此,他呼吁向希腊传统德性回归以拯救当代自我的失落,从而走出现代西方的道德困境。尚且不论这种回归是否可能,仅就这种呼吁所要返回的希腊哲学而言,它是否真能承载起这种理想的光环?以下我们将尝试性地做出分析、解答。
一 德性内涵在希腊传统语境中的逻辑演变
德性概念最初源于希腊文的“arete”,并与“physis”相关。在希腊文中,“arete”指的是事物的功能、特长;“physis”指的是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原因,指向“being”的结构,与“缺失”相对。在古代希腊人看来,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功能和特长,这种功能和特长就是该事物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事物能够成为该事物的原因。如果事物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那么就可以说这些事物具有了德性。因此,在希腊传统思想看来,德性最初是以潜能的形式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就人类而言,这种以潜能形式存在的德性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德性,而只是一种类比意义上的德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种德性是一种自然德性。
在希腊传统语境下,作为潜在德性的自然德性是人类德性的基础和前提,包含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人的存在本身指向自身功能的完善,二是人自身具有成就善的能力。也就是说,自然德性为人的存在设定了某种善,并为人提供了实现这种善的能力。“善”在希腊传统哲学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对于善的规定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目的”。苏格拉底认为自然万物之中都蕴涵着内在的目的,这个内在的目的就是善,是一切事物追求实现的目标;具体到人身上,善就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德性。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也写道:“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①因此,自然德性为人的存在本身设定了某种善,也就为人的存在设定了某种目的。这样一来,每个人就都有了自己对于善的追求。与此相应,自然德性为人类实现这种善的追求提供了一种自然能力,即一种成就善的理性能力。苏格拉底的“知识”便是一种因“自知其无知”而获得完善自身的理智能力,柏拉图在《美诺篇》中宣称德性并不是善本身而是获得善的能力,亚里士多德则将自然德性的这种理性能力直接命名为一种以识别善为对象的洞察力。因此,自然德性在为人类设定善目的的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成就善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性概念在希腊传统语境中也被理解为一种力量。
在希腊传统看来,人类正是在自然德性设定的善目的的指引下,依靠自然德性赋予的理性能力使自身的德性潜能实现为一种现实的德性。这样一来,德性概念就成为了人的自然德性在社会群体生活中获得成熟与完善的标志,体现了人在超越自然本性时所显示出的独特性与人的理性尊严,赋予了人在共同体中与他者相通并彼此尊重的能力。正是基于此,德性概念在希腊传统语境下又被理解为一种可称赞的品质,是对体现了人的内在卓越与优秀的实现活动的称赞。如此,德性便成为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然而希腊传统认为,人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人必须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遵守法律和正义才能获得其本质力量的存在,实现其内在的卓越与优秀。然而,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人作为政治动物的本质被表征为一种“公民”身份。这样一来,在政治群体的生活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与完善便同“公民”和“德性”这两个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希腊传统语境下,德性概念是从道德善的角度体现人在政治群体生活中的理性尊严,公民概念则从政治善的角度表征人在群体生活中的身份特征,两者都是对人在政治群体生活中的本质规定,追求的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卓越与优秀。由此,希腊传统对于人的德性的探讨在具体的城邦政治生活中便转向了对公民德性的探讨。
在探讨公民德性的问题上,希腊传统是从具体的社会角色的职责要求的角度来谈论一个公民应该具备怎样的德性,即公民德性指的是公民履行社会角色所应具备的品质。在希腊城邦时代,对一个人进行判断的主要依据在于他对城邦职责的履行程度。因此,在希腊语中“善”最初是用来描绘贵族们履行角色的术语,并不涉及道德价值的善恶判断。如荷马史诗中记载,当阿伽门农打算占取阿喀琉斯的女奴时,内斯特对他说:“虽然你是善的,但不要夺走他的姑娘。”②在这里,仅仅凭借阿伽门农对盟军职责的履行就可以对他做出善的评价,而对于他是否凭借权力将他人的女奴占为己有则可以忽略。因此,在希腊传统看来,公民德性是公民履行城邦职责所应具备的品质,体现在公民履行他的角色所要求的行为当中。这样,在希腊传统语境之下,公民德性的内涵便与公民职责密不可分了,可以说是公民职责设定了公民德性。在古希腊人看来,在城邦中担当什么样的角色,承当什么样的社会职责,就会有什么样的德性被规定与之相配。由此而来,对一个公民进行道德善恶评价的根据就在于他是否具备了其职责所要求的品质。一个公民如果具备了其职责所要求的品质,他就是善的;反之,则是恶的。至此,德性内涵在希腊传统语境中完成了其自身的逻辑演变,然而,这种演变逻辑本身隐含了德性自身的内在分离。
二 德性概念在希腊传统语境中的裂变
如上所述,自然德性、德性与公民德性是在希腊传统语境中理解德性内涵的三个关键性概念。在这三个概念的演变逻辑中隐含了德性自身的内在分离,这种分离始于自然德性设定的目的与手段的分离。
自然德性为人的存在设定了善的目的,并为人提供了实现这种善的理性能力。这样,在自然德性设定善目的与成就善的能力之间实际上就隐含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然而,由于希腊哲学的目的论传统,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在自然德性内部是以分离的形态存在的。在希腊哲学传统看来,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有着某种目的,一切的存在都是为了趋向某种目的,宇宙万物尤其是人都将追求善视为自身的目的。苏格拉底以善的目的作为一切存在之所以存在的根本理由,柏拉图以善的理念规定一切存在追求的终极目的,亚里士多德则为人类的实践行为设定最高的善目的。在这种哲学目的论语境之下,自然德性为人类提供的理性能力不过是作为实现善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在自然德性内部实际上隐含了目的与手段的分离,而恰恰是这种目的与手段的分离决定了希腊传统语境中智慧德性对人类实践的超越。
希腊传统对于德性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对具体德性条目的理解③,在这些德性条目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智慧德性。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命题直接以知识理解德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智慧德性作为其他德性的决定性因素,亚里士多德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基础上,做出了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哲学智慧与实践智慧的划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德性需要借助于理智德性的明智,而明智作为一种实践智慧,又须仰仗于哲学智慧。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在调解智慧与实践的初衷之下却进一步提升了哲学智慧的地位。如果说苏格拉底、柏拉图抬高智慧在德性中的地位,这种抬高也只是就智慧作为一种成就善的理性手段而受到重视。因为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命题,虽然把知识与德性直接等同,这种等同也仅是因为有了知识就知道如何行善;柏拉图的智慧作为协调灵魂各项功能以实现正义的关键因素,也仅是作为一种理性的调节手段而独受青睐。到了亚里士多德这里,智慧则被明确区分为哲学智慧与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是指导人类道德实践的一种实践理性,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智慧、柏拉图的智慧德性也仅是就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实践智慧的层面而言。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智慧只是灵魂中较低一级的德性,它需要仰仗于哲学智慧的努斯才能发挥对人类道德实践的指导作用。哲学智慧作为实践智慧的指导,思辨的是不变的永恒的事物,因此,在目的系统中,哲学智慧是最高的目的。对于这种哲学智慧的沉思也就成为了最高的善,是人类应当追求的接近于神性的最高幸福。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以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哲学智慧与实践智慧的区分来调节智慧与实践关系的初衷却只是最终确立了智慧在目的系统中的至高地位,加剧了德性内部目的与手段的分离,促成了智慧德性对人类实践的超越,最终导致了希腊传统德性概念中“好人”德性与“好公民”德性的分裂。
希腊传统把公民德性理解为公民履行城邦职责的品质要求,对于公民德性的探讨就被转换成了怎样才是一个“好公民”的问题。在古代希腊,“好公民”应当具备的德性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荷马时代是英雄崇拜的时代,因此,勇敢是一个“好公民”的首要德性;公元前8世纪-6世纪,随着城邦体育竞技的发展,体能的卓越就成为了“好公民”的主要内涵;到了公元前5世纪,智者派则将论辩的成败作为衡量“好公民”的标准,进而将论辩的技术作为了衡量是非善恶的准绳。至此,希腊传统的公民德性就完全沦为了公民履行政治职责的一种技艺,与道德善对人的规定彻底地分离了。面对智者派制造的这种混乱,苏格拉底从普遍善的角度寻求德性的根本性规定。但是,苏格拉底的这种寻求只是就人的一般德性而言,即只就“好人”的德性而言。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则直接宣称:“假如全国都是好人,大家会争着不当官。”④因此,他们在解决智者派在公民德性问题上制造的混乱时,把对人的德性的探讨从政治领域退了回来。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把德性与公民的身份、职业和技艺等非道德因素相分离,具体讨论了“好人”德性与“好公民”德性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具有一个善良的好人应具有的德性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不能要求城邦中所有的公民都具有完全的德性。但是,可以要求公民中的统治者具备完全德性。然而,这种同时具备了“好人”德性与“好公民”德性的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是一种理想的人格,近似于柏拉图的哲学王。在《欧台谟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有德之人分为“好人”与“品德高尚的好人”两种类型。“好人”指的是为获取生活必需品而行善的人,“品德高尚的好人”是为行善而行善的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家甚至还不完全配称为“好人”。至此,亚里士多德得出了“好人”德性优于“好公民”德性的结论。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在努力寻求城邦政治生活中人的德性的根本性规定即人的内在自我与社会角色的统一时,却不过是完成了希腊传统德性内在分裂的自我确证。
三 希腊传统德性裂变的根源
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希腊传统德性的这种内在分裂,根源于希腊哲学的目的论传统。如前所述,古希腊人从哲学目的论的认知视角对自然德性的理解使得自然德性中隐含了目的与手段的分离,由此奠定了希腊传统德性内在分裂的逻辑起点,而促使希腊传统德性完成自身分裂逻辑的社会根源则在于古希腊哲人们超越政治群体生活的价值取向。
古希腊哲人们超越政治群体生活的价值取向源自希腊传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并在解决由此导致的自由问题的过程中得以最终形成。在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上,希腊传统分别从人的社会性与人的理性认知的角度来进行理解。从社会性的角度而言,希腊传统认为人生而具有合群的天性,不能离开共同体而独立生活。他们由此坚信,人在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必须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才能获得其本质力量的存在。“凡是本性上(而不是偶然的)不属于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超人就是鄙夫。”⑤另一方面,由于希腊自然哲学家专注于对自然的研究和对纯粹真理性知识的追求,使得他们又把人理解为对真理的个体沉思者。也就是说,当希腊传统从理性认知的角度来考察人的本质时,又形成了人本质上是哲学的动物的思想。⑥作为哲学的动物,爱智慧的理性赋予了人追求独立与自由的天性,而城邦的政治生活则是对这种人类天性的束缚。因此,就人的哲学本质而言,追求独立与自由的天性必然要求独立于群体的政治生活之外,而人的政治本质又要求人必须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这样一来,在希腊传统语境下,就出现了人的哲学本质与政治本质、人的个体自由与政治群体生活的冲突。这种冲突为希腊传统德性从目的与手段的潜在分离转向人的德性与公民德性即个体的内在自我与社会角色的分离提供了契机,而最终促成希腊传统德性走向彻底分裂的现实根源则在于古希腊哲人们在这种冲突中解决自由问题时所形成的价值取向。
在古希腊哲人们看来,在政治生活中不可能实现人的自由,人的自由只能在哲学中通过人的理性精神的独立来获得。在希腊哲学史上,即使第一个关注城邦社会问题的苏格拉底,他的一生也对政治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过的是一种只为确证德尔斐神谕的哲学生活。柏拉图虽然构建了一个哲学王的理想国,但他依然认为最高的人类活动是哲学而非政治,只有哲学才是教化人类心灵本性、实现人类自由的真正学问。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不会选择去统治别人,他只是被迫去统治、参与政治生活。因此,这种被迫之下参与的政治生活显然毫无自由可言。亚里士多德虽然把城邦的善视为最高的善,但是,在对哲学家与政治家的生活进行了比较之后,他还是倾向于认为哲学家的生活优于政治家的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哲学是仅仅为了自身而存在的学科,因此,只有哲学才是自由的,人的最高自由就在于对这种哲学智慧的沉思。在希腊城邦时代,哲人们主要是借助于对纯粹真理性智慧的这种哲学追求来实现人在政治群体生活中的个体自由。当希腊化帝国摧毁了希腊人的这份闲暇之后,他们对于个体自由的保存则从对纯粹真理性智慧的沉思转到了对人自身的沉思,转向了一种心灵哲学。这样一种心灵哲学不再像希腊城邦时代那样在哲学与政治、个体自由与政治群体生活之间徘徊挣扎,而是完全走向了对政治的决裂。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还试图在政治框架之内构建一个哲学的王国,那么芝诺的《理想国》已经没有了任何政治色彩,几乎成为了犬儒学派与政治决裂的理论表达。因此,斯多亚学派虽然认为人对政治生活负有责任,但是却把政治领域视为对于人类无关紧要的东西,甚至以放弃生命的冷漠来摆脱世俗政治的羁绊,从而实现其人格的独立与自由。伊壁鸠鲁学派则要求个体从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完全脱离,回到人的内心寻求一种完全脱离政治群体生活的独立与自由。
这样一来,古希腊哲人们在以人的哲学本质超越政治本质,以个体自由凌驾于政治群体生活的过程中,形成了超越社会群体生活的价值传统。这种价值传统为德性在城邦政治生活中的进一步分离提供了合理性的辩护,促成了希腊传统德性从目的与手段的潜在分离转向智慧与实践的现实分离,并最终走向人的内在自我与社会角色的彻底决裂。至此,希腊传统从哲学目的论的认知逻辑与超越政治群体生活的价值观出发,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其在道德领域中的价值决裂与取舍偏向。
四 从希腊传统德性的裂变看德性复兴论
麦金太尔认为,现代的自我被分解成了一系列分离的角色,人被不同的角色所分割,散落在社会的不同领域之中。在麦金太尔看来,正是因为现代社会对传统德性的摒弃使道德变成了纯粹的规则,导致了道德理论的混乱和支离破碎,使自我因为丧失了德性的根基而丧失了自我的完整性,最终使人在不断扩张的工具理性中陷入了“自由着”的奴役状态之中。因此,麦金太尔立足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德性论诊断当代西方社会的道德病症,呼吁复兴希腊传统德性以走出人类道德的当代困境。
在麦金太尔看来,希腊传统德性之所以能承载起拯救现代社会的使命,就在于希腊传统德性所具有的超越城邦政治的一般人类实践的普遍意义。麦金太尔认为,希腊传统德性思想把做一个“好人”与“好公民”相联,这样而来的德性要求正是被当代遗失了的自我。然而,如前文所析,恰恰是希腊传统德性超越城邦政治的理想设定成为了希腊传统德性内在分裂的逻辑起点。希腊传统“好人”德性与“好公民”德性的相联是以这种分裂为前提的,因而这种相联恰恰意味着希腊传统德性实现了内在自我与社会角色的彻底决裂。这种决裂可以说是麦金太尔意义上的现代自我分离的最早形式。只是希腊传统的这种自我分离是建立在人的哲学本质优于政治本质的基础上,导向的是人的精神个体与实践个体的分离,并最终以人的精神存在超越了人的现实存在。因此,以希腊传统这种内含了自我分离的德性作为挽救当代丧失了精神的自我,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仅无法拯救分离的自我,甚至还会因形上的精神自我对形下自我的否定而使自我丧失存在的现实根基。此外,希腊传统德性的内在分离实际上导向了对独善其身的幽居生活的追求,催生了一种明哲保身的人生态度和消极的生活方式。在这样一种生活哲学陶冶之下的个体,往往缺乏直面社会现实、担当社会责任的勇气和积极进取的精神,甚至还会酿就弃绝生命的极端悲剧。因此,以这样一种传统德性造就的个体不仅无法实现内在自我与社会角色的统一,对人类社会而言甚至还犯下了一种不公正的罪行,正如罗马时期的西塞罗所评价的,“诚然,他们保持了一种公正,即他们的确没有伤害任何人,但是他们却违背了另一种公正;因为他们……对他们应当去保护的那些人的命运则漠不关心……他们或则由于一门心思致力于自己的事业,或则由于对世人的某种厌恶,声称他们独善其身,似乎不会对任何人有任何伤害。但是,他们虽然避开了一种不公正,却陷入了另一种不公正:他们是社会生活的背离者”⑦。
麦金太尔回归希腊传统德性的主张不仅忽略了希腊传统德性的内在分离逻辑,甚至也不追问这种希腊传统德性当初为什么会被抛弃。如前所析,内在自我与社会角色的分离恰恰是希腊传统德性的内在逻辑结果。因此,在现代性的条件之下,对于道德问题的思考,不可能再重返传统的道德模式。传统道德模式的有效性是以理性的一致为前提的,麦金太尔的回归理论是建基于对人类理性达成一致的预设之上的。然而,麦金太尔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寰宇之中唯有理性思维着的动物最难以在理性上达成一致。现代性乃至后现代的崛起,更是从根本上瓦解了这种一致的可能性。也许,这才是现代道德困惑的病根,也是希腊传统德性的有效性难以维系的根源所在。
①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第3-4页。
②参见荷马:《荷马史诗·伊里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③虽然苏格拉底寻求德性的根本性规定,但他的这种寻求建基于对具体德性的探讨之上,并且最终以“知识”即智慧德性来作为德性的根本性规定。因此,笔者以为希腊传统对于德性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对具体德目的理解。
④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31页。
⑤汪子嵩等主编:《希腊哲学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1053页。
⑥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毕达哥拉斯是最早提出“哲学”和“哲学家”的名称并自称为哲学家的人。在毕达哥拉斯看来,最好的人乃是寻求真理的沉思者,而哲学家则是这样的人。因此,可以说毕达哥拉斯最先从哲学考察人的本质;而亚里士多德“求知是所有人的天性”、“人是理性的动物”的命题则概括了希腊传统以爱智慧的哲学本性来考察人的本质特征。因此,可以说哲学的动物与政治的动物是希腊传统分别从人的理性认知与人的社会性两个角度对人的本质的考察。
⑦西塞罗:《论老年 论友谊 论责任》,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101-1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