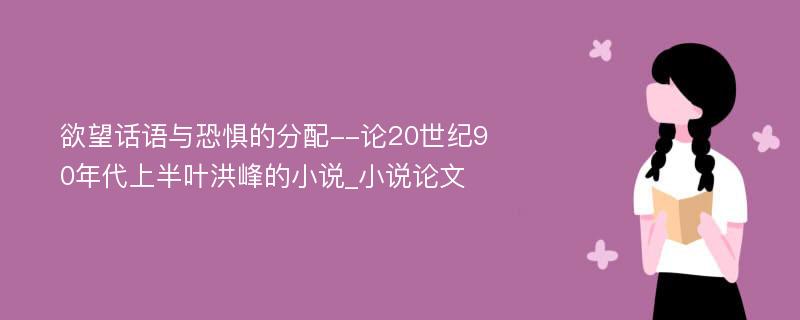
欲望话语与恐惧分布——90年代前半期洪峰小说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恐惧论文,欲望论文,年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趁太阳照着的时候晒好干草
——民谚 转引自爱默生《自然沉思录》
洪峰1990年以来发表的小说,比起他在八十年代中晚期的作品,给评论界出了更加费解的难题。在评论先锋小说的评论文章中,我们再难从一长列名字中找出洪峰,尽管他本人也许并不在乎。曾有评论家把《东八时区》当成“新写实长篇小说”来读〔1〕,不失为一种机智, 因为“新写实”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先锋性,但新写实小说并非先锋小说,这种归类就等于把这部洪峰苦心经营的长篇小说开除于先锋小说的阵营。只有大型文学杂志《江南》1994年第1期曾在“中国当代新小说专号”中推出他的长篇小说《喜剧之年》(另有北村、韩东等人的中短篇作品)。这种判决无疑有些残酷。事实是,把洪峰简单地归类,会给他的小说带来相当大的破坏性。洪锋又不向流行的“款式”靠拢,结果就成了评论追踪之外的浪子。
洪峰的小说在结构历史的外部形态上,的确具的通常的写实小说的倾向,但在精神基质以及展开这种精神基质的方式上,仍具有先锋小说气派。特别在“欲望话语”的层次表达上,比一般被普遍看好的先锋小说代表作,甚至走得更远一些。
洪峰的欲望话语是通过几种“恐惧”表达的,如此细密地分布恐惧于小说的空间形式之中,是对“消解深度”企望的消解,小说在洪峰笔下正在走出单纯的技术狂热,更加专注地走向人类精神的深广地带。
欲望话语为人所特有。欲望之中有破坏欲也有修复欲,有性欲也有爱欲,统统建立在一个“生”的欲望之上。恐惧就恰恰产生于人不能很好地“生”,这“很好地生”的标志是生存场所的温暖和性爱所能达到的美好。在洪峰那里,叙述层次的递进,为欲望话语的表达提供了生动的对方。
一、怀乡恐惧
洪峰90年代的小说写童年、青少年时期的故乡的故事,表面上似乎依然还在复述他的《奔丧》、《瀚海》等名作里的老家,仔细认读,就会发现,作家不再带着文化寻根的愿望去讲述近乎局外的乡野里的生命故事,而是带着更多的温情陷在命运所规定的生命停泊地上,明明知道那里不再会给自己带来童年、青少年所向往的东西,却偏偏要让自己的梦做在那里也破在那里。那里是巨大的力的漩涡,整个故乡是一个大的磁场,它梦魇一般粘住了作家,越挣扎反而粘得越牢。怀乡的时候,没有逃离的自由。逃离是一种徒劳。剩下的只有摆脱这种滞留而不得的恐惧。洪峰的每一部新作几乎都写到了被恐惧吸附的生命历程,种种为生的欲望而挣扎的大小故事袭向童年、青少年的“我”,“我”的故园并不是“诗意的栖居”之所。
洪峰在1989年的一部中篇小说中,有一句很显眼的话:“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小心和努力地活下去并且尽可能活得长久——虽然我们的把握并不很大。”正是从此,洪峰对于写作的技术性的追求不再十分强烈,他巨大的热情已投入到对生命及其居所的悲剧性表达里。这篇小说的标题:《重返家园》(《青年文学》1989.2)。他此后的小说中,人物大都没有这“并不很大”的把握。
丑恶的、凶狠的、肮脏的往事,为童年回忆的屏壁上涂满了淋漓的污物。《年轮》(《小说家》1991.3)中徐奶奶往房墙上拉屎的形象,深寓了怀乡的象征意味。“我真不愿意讲肮脏的往事,我和大家一样不喜欢,但那件事留给我的印象过分深,它可能使我形成了如今的洁癖,或者是病态的”。看来“印象过分深”的往事,即使“不愿意讲”、“不喜欢”也还是不能不讲的。比如“打人”的故事,这里有精采的笔致:一向专横霸道、骂人不眨眼的徐奶奶,被第二任儿媳的一顿耳光搧得突然从此顺从起来,失去了生气。小说中“我”遭父亲痛打,为怀乡带上了强刺激的烙印。最鲜明地体现“挨打”的刺激的是《九路汽车》(《鸭绿江》1991.4),兄弟亲情中饱含着哥哥因个头矮遭受欺凌、毒打的经历。于是“我”发誓练就一双铁拳,在凶暴面前决不退缩,以致中学毕业后无业就去打架。这里,以暴力反抗暴力,是一种对暴力的恐惧记忆的应验,暴力便具有一种新的深度:
暴力:恐惧/反抗
↓↓
以心
以拳
行为的反抗是内心恐惧的补偿与释解,但反抗仅仅是恐惧的变形,并不是恐惧得到根治的对症之药,“反抗必然增加疯狂世界的恶”,〔2〕只能使恐惧的发展走向终端,即把生的欲望变形为死的欲望。
也许是作家意识到了这种行动的无奈,在其后的长篇小说《和平年代》(《花城》1993.4)中,主人公段和平认为,“以邪恶对邪恶,以流血对流血不符合人的要求,一个现代人的最根本标志是承受生活给你的一切。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小说中段和平不仅不是一个行动的人,几乎连言语都处于淤滞状态,“不管哪种情况,都无法诉说了”。他思想着,却难于表达。这部有着多重恐惧又埋藏着巨大的对温暖美好生活渴望的长篇,充溢着对人类所居处的这个世界的不可挽回的无望感。它跨度极大地写到朝鲜战争、中印战争、越南战争、中苏之战、阿富汗战争及海湾战争,它们构成主人公生活的“和平年代”的毁灭性的背景;它又直接展现着永远伴随人们的一种“政治”的灾难性祸根,亲爱的人的死和苦难无不与此相关,这是小说揭示给我们的此岸的现实家园,这一切让我们的“怀乡”情绪更加无依无靠没着没落,“怀乡恐惧”也因此变得更为具体更为不可救药,它使生存其中的人像段和平一样面对茫然失措的世界无语地迎接着猝亡的危险。“怀乡恐惧”的表征演进为这种“厄运的循环”——从段方到段援朝/段和平再到段忘,三代人的命运是在战争/政治的阴影和圈套中今日人类灾难性存活的寓言。
叙写暴力故事曾是余华前期小说的拿手好戏,冷静而诡异的过程叙述中隐藏着内心恐惧的反应,暴力的主动性其实是叙述者被动的恐惧心理使然(90年代中后期余华也转向了温情的生命关怀)。苏童的《刺青时代》却走向了反面,争霸与反争霸的乡间少年的暴力故事游戏一般地伤人至死,没有内心的颤栗。与洪峰颇具传统写实味道的《九路汽车》相比,余华、苏童们的历史故事与寓言形式暴露出某种刻意而为的“新概念化”倾向。也许米兰·昆德拉没错:“这种精彩的反随波逐流的动作后面,是最平庸的媚俗精神。”〔3〕在洪峰那里, 摆脱媚俗的方式是注定的无家可归的恐惧,以及恐惧所指向欲望的最终结局——死亡。
二、性爱恐惧
长篇小说《东八时区》在《收获》1992年第5期发表后, 我曾经匆匆地写下一些评论文字,〔4〕是一种被感染的结果。 我一直觉得:“对性爱的敏感,是洪峰最为突出的天真,他的小说始终在寻求着这种敏感的全部丰富性。”
18岁的卢小兵为写小说,写爷爷奶奶的传奇经历,走访当年的老兵。这时小说写道:
……。这是一个要为爱情献出许多东西的女孩子。……
卢小兵抬起手臂,把长长的头发拢向脑后,她的额头光滑滋润,一双眼睛忧郁地睁开,卢小兵感觉出衣服对乳房的压力,泪水悄悄地涌进眼眶。
为什么,光阴啊,那欢欣的时刻
如此飞快地消逝?
当朝霞突然升起时
那轻柔的夜色为何渐次退走?
为什么你,月儿,匆匆溜走,
沉没在明亮的天际?
为什曙光忽然一闪?
为什么我和亲爱的要分离?
18岁的卢小兵在这一时刻忽然记起了普希金的诗,她默念着它,让眼泪流进口腔。
这实在是洪峰小说最美的片断。这种青春的感伤,带着诗意,带着梦影,悄悄地在洪峰笔下的丑恶、死亡之上含泪微笑,它该是洪峰所有作品的精魂与核质。但在时空压榨下的命运,决定这远远构不成世上的生态,因而感伤愈加无可避免地沉郁。倾注这种感伤最多的是王路敏(卢小兵的小姨),她的每一步,无法判断对错,却都令人热泪盈眶。洪峰在这个可爱的人物身上深深地埋藏了诅咒,这种诅咒是他所体味的优秀与卑劣的全部实质——他恨透了那种无爱的“做爱”的道德,结果,在美与爱上,恶狠狠地加入了肆虐。关于这一点,《东八时区》里老实慈爱的面孔下实则心肠骚狼恶狗一样的“贫下中农”老刘头,《活动房屋》(《鸭绿江》1993.10)里生性粗暴的“姐夫”等, 作为性角色的如此惨烈的经历,足以唤起对于性的恐惧,这种恐惧属于“显在”。我们再看,《东八时区》是洪峰少有的第三人称作品,但卢景林(甚至魏迪、王先佩、朱力)那里都跟别的作品中的“我”有某种相近相似的东西,或者是某种性格或精神线索上的相通。小说一再有主要人物几近近亲相恋的关系:卢景林与妻子的小妹王路敏(《东八时区》)、“我”与表妹(《九路汽车》)、我与堂姐玉兰(《活动房屋》)。作者陷入了一种读者的接受尴尬之中。那种爱欲是一种极有可能的事实,所以读者是容易被领入故事的,但又太难以体认这样可能的真实。洪峰恰恰以一腔柔情对待这一切,由此也把性爱恐惧推到不可能美好的结局。这种危险带来的恐惧是一种强大的“隐在”。
情爱,在“外人”那里不容易保持,而更多的是摧残;在“亲人”这里不可能最终实现。这已经是一个在很危险的刀刃站立了很久的局面,本能的性与人之爱填加欲望的份量,已经达到足以摧毁这持久的绝望折磨的程度。于是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麻木起来,不再钟情,有欲无爱地活下去,走向鄙俗的肉俗人生;二是像玉兰姐那种用刀根除绝望的机体,以死灭保持对性爱的向往和梦想。洪峰小说选择后者。
当性爱成为一种青春的本能时,它所附着的情韵是有可能生动感人魅力尽现的,但当性爱变成一种命定的欠债偿还的仪式和过程时,便产生恐惧性的效果。《和平年代》里“援朝”与“和平”这两名字属于一个人,却寓示了上一代的遗弃所带来的巨大的人生欠缺与下一代的无法弥补。这里直接关涉“援朝”与父母的悲剧以及“和平”与恋人、妻子、情人的性爱,段忘的出生延续的是性爱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却正是又一代悲剧的重复的开头。人生的激情被性爱的无所作为所消磨,也是洪峰的别一重深意。
三、死亡恐惧
对死的不露声色的详细描写,是洪峰作为先锋作家的一大特色:《东八时区》里王路敏细细地分布每一小块炸药,《年轮》中麦子对刘姥姥上吊的无动于衷及麦子自杀时紧紧匝匝地往自己身上捆石头,《离乡》中目睹李晓红的死,《活动房屋》里玉兰用刀片结束全家人性命……
死亡,因有怀乡恐惧和性爱恐惧的铺垫,是在劫难逃的。以往,笔者主要着眼于《东八时区》所展示的宿命性,可以看见,洪峰小说的时间标码具有相当的精确度,年月日俱全,而且不断地出现在叙述的中途。但,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必死无疑的宿命性对人的提醒,一种对生命的催逼,时间并不表现世道人心的变化。“几十年前的生活也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显现出和现在的不同”(《活动房屋》),有的只是欲望的劫难,恐惧的迭加。
在洪峰的小说中,怀乡恐惧大致可以看成缘于留住童年欲望的破灭,性爱恐惧大致可以看成缘于拥有青春欲望的破灭,而死亡恐惧可以看成缘于把握命运欲望的破灭。但有一点必须清楚,这里的“死亡恐惧”并不是“恐惧死亡”而是恐惧导致死亡的情形或过程,如《活动房屋》里可怕的玉兰婆婆对芍药花的诅咒,《东八时区》中老刘头对王路敏的暴行。死亡恐惧其实是一种恐惧的前置状态或先释状态。小说里写道:“面对死亡的时候,青年作家依然可以睁开眼睛一声不响地迎接。当然,这是他极度恐惧的特殊表演,没人知道”(《活动房屋》)。写作这种恐惧,而且达到异常的冷静,正是一种对于生存恐惧的逃离,这里的逻辑是:因恐惧而逃离,因逃离而自由,因自由而再次接近恐惧。于是洪峰一再精心地琢磨各种各样的死法,周密地设计导致死亡的细节。
洪峰去不掉也舍不了温情的浸染。不光洪峰,其他先锋,其他先锋作家也在渐渐地注入温情的东西于小说中,作为欲望话语的健全组织。但其他人走的是“活着”一路,洪峰却执着于“必死”一路,恐惧的来由及程度也就有了很大的差异,这不仅仅是策略问题,而更是本质问题。
四、记忆恐惧
这是上述几种恐惧方式的一个原点。
洪峰的小说在80年代中后期被许多人所津津乐道,那些中短篇小说可以更为自由地变换技术层面的因素,而且也更容易刺激读者或评论者在智力上的反应,尤其是洪峰那种貌似武断强大的反向判断语式,适应了人们长期以来常规的逆反心理。在那些涉及洪峰创作的言论中,很少有人注意其中柔弱细腻属于情怀的真东西。其实,《瀚海》里就隐藏着那么一股北方草原近于俄罗斯地貌的旷野的地气,它是粗砺的,但更是温柔的,它左右着生长于此的人性状态。直到1990年第4 期《收获》杂志发表了洪峰最重要的中篇小说《离乡》,这一直隐为背景的内核才得以生发它应有的光亮。这是对于“乡土”与生俱来的记忆的唤醒。对人的爱是这块乡土给予作者的第一个道德记忆的规定性,《离乡》像我们期待于洪峰的特有态度一样,不可能是一曲田园牧歌或乡土挽歌,他带着所有的仇恨和诅咒都源于对可爱的人的真情,这是带着地气的心灵感应。情感是有所依托的,但眼看着人的生命毁灭和爱的不可能完好,却往往找不到可以交手的敌人。还击的无可依托酿成的是记忆恐惧,这不仅开启了由《离乡》开始的中短篇小说的温情的加剧,也开启了《东八时区》、《和平年代》、《喜剧之年》这几部长篇小说对于记忆恐惧的逐渐深入的体验和述说。
《喜剧之年》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归为知识分子小说,其人物群落的活动恰恰在一个近十年来最敏感的那个年份。洪峰揭示了这一群落不可救药的颓落,众多的现实人物的活动之中,温情和离群索居构成唯一的抗争,只有父爱和旅行构成拯救或者安抚心灵的作用,其中的性爱和死亡都变得平淡缺少震撼。对这一年的记忆中,实实在在的东西几乎都与最沸腾的观念失去沟通,与其说这是记忆对于“天下大事”的遗忘,不如说是记忆对于知识者无聊状态的观照。洪峰展示的这一年的人生回忆,是通过对作为民族精华的知识者群落的卑琐灵魂的展示,揭开梦想遗失的事实:“和平年代里的人们以软磨硬泡的方式浪费着生命,以批判政治的方式充当政治的走狗,也以繁荣文学的名义屠杀自由的心灵。”因此,他还说:“在我的价值体系里,这一年无聊至极,这一年的中国知识分子超越无聊接近了无耻。”〔5〕
忧伤的情绪和冷冷的愤慨,几乎填满了《喜剧之年》,这是恐惧的一个变形。心灵和情感被冷漠所冻结,这是比猝死更可怕的恐惧状态。
《和平年代》是性爱与死亡恐惧的集成,“记忆的恐惧”及“在恐惧中承受”构成了几乎难以支撑生命的冲突。“人的全部意义在于他有记忆,生命存在而记忆存在,记忆存在就不可能遗落所有经历过的事情”(段和平语)。秦朗月在段方与援朝之中所承受的记忆恐惧构成小说的基调,这种恐惧渗透了段和平(援朝)的各个侧面的生活,也使他人生的各种恐惧都来自秦朗月对于段方的回忆,而援朝及其妻儿、恋人、情人之间也荡漾着这种回忆的气息,并构成对于幸福生活愿望的直接阻断力量,一个人的一生有开始有终结,但恐惧却在循回,洪峰这时的小说曾试图以爱整合布满创伤的历史和记忆,实际上在“必死”的信仰下,自身永远没有把握,却总是处于被把握的境地。这是记忆予人的悲怆。从人道意义上说,段和平的“求生”欲望里包裹着严肃、纯净的英雄情怀,尽管他更像个无所事事的零余者。
平静的生存通向平静的死。不能平静的记忆使死之平静成为不可企及的事。德国当代神学家E ·云格尔说:“接受死亡恐惧始终意味着接受恐惧者的生。”〔6〕
生即经历,经历对于个人来说便是留在记忆中的一切,这是作家的宿命也是人的宿命,各种恐惧在生的欲望中奔突不止,逐渐地靠近或猛然抵达一个大限,都是生命的可能性。人总要不可避免地放置生命于这个永恒的“死结”之中。但是记忆因恐惧的挤压反而有可能鲜活起来,鲜活地找寻生的平安和平静。“如何使一个人的生命在临近大限时有一次安静的微笑,肯定是一个诚实的人最关怀和向往的时刻。”〔7〕
从这种悲观之中的乐观判断上看,应当说,洪峰90年代前半期的小说深入了心灵的底处,在那里,文学与人生取得了本质上的击掌相和。
注释:
〔1〕《文学评论》1993年第5期宋遂良文
〔2〕加缪《鼠役》第29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3〕《小说的艺术》第151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4 〕拙作《感伤的渊薮》、 《爱之劫数》, 见《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2期,《吉林日报》1993.1.27
〔5〕〔7〕洪峰《在四年后回忆》,《当代作家评论》1995.1
〔6〕《死论》第11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