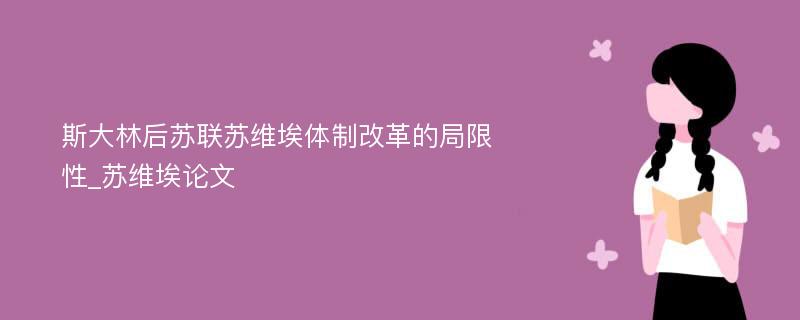
斯大林之后苏联苏维埃体制改革的局限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维埃论文,斯大林论文,苏联论文,局限性论文,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8)06-0071-05
一、苏共代替苏维埃工作的状况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斯大林体制中最核心的部分,即党政不分的领导制度,仍然被继承下来了。在这种体制下,有关苏维埃的改革也就不能不最后流于形式,因为党仍然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机构。以1977年宪法的制定为例,其工作主要是在苏共中央的层面上进行的。对宪法草案,苏共中央全会讨论2次,政治局审议5次,书记处研究18次,中央全会对宪法草案提出700多条修改意见和建议,然后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而最高苏维埃开了十天会,92名代表发言赞同,宪法就通过了。[1](P559)勃列日涅夫承认:“政治局和我这个总书记本人所处理的问题比西方领导人广泛得多。我们实际上要考虑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考虑到我国广大幅员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里既包括党和社会的思想生活,也包括经济、社会问题,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真是不胜枚举。在国际事务上也要付出很大的精力。”[2](P268)
党代替苏维埃不仅是纯粹事务性的越权,而且有其结构性的“依据”。党的领导人差不多都兼任政府和苏维埃的主要职务,这在权力结构上注定了党号令一切、干预一切的局面无法根本改变。最高苏维埃是权力机关,而最高苏维埃相当多的代表是党和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军队和其他部门任要职的人物。这些人虽在最高苏维埃中工作,但因公务繁忙,不可能长期脱离岗位参加苏维埃会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最高苏维埃中许多委员会的主席又恰好是各部的领导人和苏共中央书记,这样,最高苏维埃无论如何也不再能作出实质性的决议或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了。刚刚由苏共中央或部长会议(又通过党中央直接或间接地审议)讨论过的决议和法案,再拿到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来讨论,而参与讨论的又几乎是原班人马,或者主要由原班人马所操纵,这种讨论当然也就成了纯粹的走过场。在代表中也有普通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职员、教师、医生等,但这些代表在会上最多不过是举举手或发一通不痛不痒的赞誉之词而已。其他各级苏维埃的情况大致类似。
理论上也一直存在着为党取代苏维埃的工作辩护的倾向。勃列日涅夫以总书记身份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时,称“这绝非是一个徒具形式的行动”,而是“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它“首先是共产党领导作用不断提高的表现”,也反映了“日常工作的实际情况”,这“将得到理所当然的规定”。[3](PP181-182)契尔年科称勃列日涅夫这一兼任“是党的领航作用和指导作用及威信提高的新表现”,“是党关心和完善国家政权机构活动的鲜明体现”,“符合苏联社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工作提高到崭新的阶段”。[4](P294)在提名安德罗波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时,契尔年科也说是“符合我们社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它证明党和国家的威望不可分割”。[5](PP411-412)当契尔年科作出同样的行动时,戈尔巴乔夫的解释是,这一兼任的依据是“最近几年党和国家建设的经验”,它体现了“苏联宪法载明的苏共在我国社会中的领导作用”。[6](P86)戈尔巴乔夫后来还更加详细地论证过党的书记兼任各级苏维埃主席的必要性:第一,有助于以党的威信来提高苏维埃的威信;第二,有助于加强劳动人民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第三,任何国家都是执政党组织政府,在各级行使执政权,作为执政党的苏共作出这种兼职是顺理成章的。[7](PP49-50、111)据此,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作出了推荐相应的党委第一书记担任苏维埃主席职务的决定。按照这一决定,各级苏维埃主席职务由同级党委第一书记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则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
在结构组织上使党取代苏维埃成为事实的国家权力机关而在理论上又为它提供辩护的情况下,所谓彻底根除党对苏维埃包办代替之说已经变成了一种无力的呻吟。而当苏维埃变成了实质上的装潢门面机构的时候,再去呼吁“利用党对苏维埃工作施加影响的所有方法,以提高它的工作效率,消除一切形式主义的东西”[5](P484),这无论对党还是对苏维埃都多少有些滑稽的味道了。
二、苏维埃无力遏止管理机构膨胀与行政僭权
苏联历史上曾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裁减管理机构,但其结果却是机构越来越多,管理人员也大幅度增加。1985年苏联的管理人员已达1860万人,[6](P169)即平均每10-11个苏联公民中就有1个行政管理人员。执行管理机构的膨胀有其客观合理性的一面,但就苏联拥有如此庞大、臃肿而又效率低下的管理机构而言并不都是合理的。首先,这是苏联国家管理机构长期依靠过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依靠行政命令方法进行管理从而日益官僚化的结果。这个庞大管理机构只要遇到新情况或问题就会增加机构和人员。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中央仍在源源不断地收到各地有关建立各级新的管理机构和划拨补充编制人员的请求;[8](P6)其次,管理机构与人员的不合理膨胀也是苏联过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下粗放式经营的一种反映。像苏联这样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粗放经营占很大的优势,经济的专业化、协作化很不发达,服务业也很落后,这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就必然要求行政管理机构承担大量的、庞杂的管理职能,建立起从生产到运输、供应、修理、生活等一系列部门,必然会形成庞大臃肿的管理机构。最后,各级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部门的本位利益都驱动这些单位扩大机构,增加编制。面对增长过快和过于庞大的行政机构,苏维埃无力起到监督制约作用,它既无力阻止行政机构的持续膨胀,也无力阻止行政僭权。
三、苏维埃机制内民主流于形式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维埃体制自身系统的建设,从立法规范到制度设施,就其形式而言已臻于完备,但也仅此而已。精致化的形式往往被用来论证苏维埃民主的彻底性和真实性,而恰恰是精致的形式下面掩盖着苏维埃机制的弊病和问题。
苏维埃代表选举的全过程都充斥着形式主义的东西。按照宪法和选举法,提名代表候选人的权利属于苏共、工会、共青团的各级组织、合作社及其他社会团体和劳动集体以及部队的军人大会,事实上候选人的提名都是由各级党委决定的。当选代表往往是被看成一种荣誉的象征,即你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承认;或者是出于某种工作上的需要。例如,当需要有一些人或多或少了解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问题时,阿尔巴托夫、普里马科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就被选中了。[9](P304)在这种情况下,选举人便对选举失去了热情,候选人也没有特别高的积极性,因为事实上不存在代表对选民的责任问题。
苏联的选举法及各级选举条例并不排除一个选区推举几个候选人的可能性。选举法或选举条例都要求选民“在每张选票上留下他所选举之候选人的姓名而涂去其余的姓名”,甚至在选票上也写着“请在选票上只留下一名你赞成的候选人,其余的请划掉”的要求,但在实践中通常一个地区只登记一名候选人,选票上通常也只有一名候选人。[10](PP195-196)[11](P94)由上级等额指定代表候选人事实上完全剥夺了选民的选举权。这种领导定名单,群众画圆圈的选举徒然浪费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引起人民群众的冷淡和反感,除了宣传上的功能之外,已失去了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事实上,选民甚至失去了不参加投票的自由。因为投票率已是一种象征,重要的不再是投谁的票,而是要保证广大群众在某个地方投票表示对这个制度的支持和赞同。因此,如果投票进展不顺利,鼓动员或积极分子会被派出去召集、提醒那些尚未投票者,要求他们履行公民的义务。为了应付投票或为了保证投票率,丈夫代妻子投票,女儿代母亲投票,甚至选举委员会成员代替迟到或不到的选民把选票投入票箱,或在选举日由居委会为在规定时间内不到的选民开出大批病假证明或外出证明,都是见怪不怪的事情。[12](PP165-166)为了保证投票,医院、火车、轮船上都有流动票站,宣传称这是为了保证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旅行者不是投其居住地候选人的票,而投旅行地的票,因此便可能出现投票率超过100%的情况。[10](P197)苏联每次选举的投票率都出奇的高,赞成票也总是在99.3%-99.9%之间,[13](P129)但到底这种高投票率和高支持率中含有多少水分就值得推敲了。宪法和选举法都规定了秘密投票权,但是在投票时,选举委员会成员和宣传鼓动部门的代表坐在一边,秘密投票室设在一旁,在同一地点还放着投票箱。由于选票上只有一名候选人,所以投赞成票的人无需到投票室去,而到投票室去的仅仅是那些想划掉选票上的名字的人;不管谁进去,他都处于众目睽睽之下,况且还刚刚在投票簿上签名登记。[12](P170)[14](P107)而且使用这种投票室还会“被看做是‘不文明’的行为”,因为“苏联人民用不着在他的爱国同胞面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他对苏维埃的忠诚”。[13](PP128-129)且不说选民改变选票上的名字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按照法律只有社会团体、组织才有提名权),单单无法行使秘密投票权这一点已足以让选民失望了。
代表的构成被看成是苏维埃民主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重要指标。几乎每一位苏联领导人的有关讲话,每一本有关苏维埃的论著,每一篇宣传材料都无一例外地要举出一长串数字来表明苏维埃代表中有多少工人、多少农民、多少党员、多少妇女、多少少数民族代表等等,以此来论证苏维埃民主的无与伦比的广泛性、群众性、人民性。这是形式主义的又一类表现。首先,这种代表比例的构成不是由真正的选举自然生成的,而是党政部门层层下达有关当选代表年龄、职业、性别等的指标和规定的结果,是为了保持代表比例平衡而人为干预的结果。其次,代表机构的实质在于它的代表性,代表机构不是协商会议,不是劳模会,更不是干部会。选民挑选代表的标准首先应该是他的代表性,也就是代表能不能、敢不敢、愿不愿替选民说话,群众性、广泛性是代表性的延伸和扩展。离开代表性而片面强调广泛性和群众性,用群众性等同于代表性,是对代表机构和人民代表的涵义和实质的歪曲。
定期召开的各级苏维埃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同样难有作为。一方面,这些会议基本上是按事先准备好的脚本进行的,与会者的发言都是事先定好的调子,而倡议,尤其是批评都经过了剪裁。非常认真而热烈的辩论是从不会出现的。[14](P347)[5](P487)另一方面,代表即使想有所作为,客观上也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第一,几天的会期要解决许多重大问题,每一个问题都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展开讨论,只能举举手,走走过场。第二,来自各个生产岗位上的非脱产的代表对大量的立法问题是陌生的,对政府官员提供的许多法案、议案来不及熟悉,这也决定了他们除举手表决外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当然,在会议之前,有时代表们也可能会接到要求必须发言的电话,但这种发言是绝对不能出“格”的,甚至有人会把已经拟好的发言稿给你。[9](P305)代表的质询也是如此,一方面许多代表无能力进行质询;另一方面则是以事先安排好的象征性的“质询”做做样子,而事实上人民群众关心的大量问题却得不到解决,[5](P490)苏维埃本身也沾染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恶习。为健全和完善苏维埃,活跃苏维埃的工作,勃列日涅夫时期建立了许多机构和组织,人们被吸收进各式各样的组织中去,成了各种组织的成员,这被看成是人民群众参政规模扩大、参政意识提高的表现。但从整体效果上看,许多东西事实上都是纯粹形式意义上的,事实上解决的问题并不多。[5](PP478-479)
四、苏维埃法治化任重道远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是苏联法制建设获得较大发展的时期。30年时间里,苏联通过废除、更新、创制和修订完善了立法制度,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基本上摆脱了无法可依的状态,并着手完善和改革执法和司法制度,在公民中进行普法教育。法制化的成就为民主化的进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制度基础。但也应该看到,与过度集权、民主化流于形式的状况相伴随,当时苏联的法治化进程还处于起步阶段。法制化相对于无法制状态是一个进步,但毕竟法制还不等于法治。“法制”是个纯粹法律的概念,只要有法律,有秩序,这个国家就可以说是有法制,不管它依的是什么法,存在的是什么秩序。但“法治”则不单单是法律的概念,而且还有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意蕴在里面。法治需要有完备的法制,但它又高于法制,内涵着某种价值要求和价值选择。[15](P227)受法律工具论传统的影响,苏联一直把法律看成是国家意志的工具,是国家政策的规范化。在俄国人的观念里,法制就意味着“强化国家”、“加强秩序”,而不包含限制国家权力、保护个人权利的涵义。法律被看成是用以增进国家利益的工具,而法院、检察官则只是为了保证法律的实施。[10](PP250-267)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法律的权威性很难真正树立起来。因为为了某种意志它可以随时随地被重新解释、被修正、被抛弃或被取代。政策的地位甚至高于法律,而政策本身则是多变的、指导性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即使它有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也还是不能说这个社会是法治的社会,因为在法律之外存在着某种力量,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它可以随意地处置法律。一旦法律屈从于某种外在的力量,法律的执行就必然会打折扣。法治首先要求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它不仅要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依靠法律来调节,不存在法律规范之外的“死角”和“盲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要求维护法律的尊严,高扬法的至上性,即“法律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执法人员和公民团体只应在法律(通则)所及的‘个别’事例上有所抉择,两者都不该侵犯法律”。[16](P192)法律的至上性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平等不单单是公民个人之间的平等,还包含有任何组织、政党、团体都不得超越法律之上的意思。它要求司法机关不受任何干涉,独立地适用法律。从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引申出来的法治的另一个涵义是“政府守法”,即近代的宪政观念。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固然要求每一个人都服从法律,但它首先要求的是政府守法,因为相对于个人而言,政府是强者,它远比公民更容易滥用权力。政府守法是法治的真谛。因此,近代以来的立宪要求的核心便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和限制政府的权力,“宪法并不是政府的法令,而是人民组织政府的法令”。[17](P250)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警察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变,政府权力已从“守夜人”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几乎全部领域,它几乎变得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越来越容易成为一种失去控制的力量,政府守法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对“法治”一词的具体内容如何界定存在着困难,但权威性的一般看法仍然是存在的。即(1)根据法治原则,立法机关的职能就在于创设和维护得以使每个人保持人类尊严的各种条件;(2)法治原则不仅要对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能有效地维护法律秩序以保证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的生活条件;(3)司法独立和律师业自由是实施法治原则必不可少的条件。[18](P82)以此标准来衡量苏联的法治化水平,无论在立法机关的职能、行政权力的防范还是司法独立的程度方面都远不是能令人满意的,更遑论事实上尚未纳入法律规范之下的党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少数领导人的超越于法律之上的个人权威和个人专断的权力了。至勃列日涅夫时代,准确地说,苏联已经不能称为没有法制的国家了,但却完全有理由认为它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19](PP3-60)而没有法治化,民主化就只能停留在理论和逻辑的层面上。
五、结语
总体上看,斯大林去世后的三十多年里,苏维埃体制虽几经变动,但旧的骨架依旧矗立着,所不同的只是装饰经过了整修,漏洞经过了填塞而已。由于苏维埃地位的衰落和长期得不到恢复,人们逐渐产生了对苏维埃的冷漠、疏远和失望。当斯大林的三十年过去时,人们仍然存在着希望,而当又一个三十年过去时,苏维埃一如既往,人们必然会怀疑,为什么又是一个三十年?如果第一个三十年是因为斯大林,那么这一个三十年呢?是不是要再等一个三十年或者更长?还是要无限制地等待下去?恰恰在人们的怀疑和失望日渐增长的时候,长期封闭的状态一朝打破,外面的世界如万花筒般地展现在面前,令人头晕目眩:多党制、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总统制、竞选等等纷至沓来。被展示的并不是西方议会民主的整个现实,人们接受的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模型,然而,这个模型却是被人们看做现实世界而奉为圭臬。这是对长期片面性否定和批判西方民主的反动和无情的“报复”。长期被歌颂的引起了极度的失望,而长期被贬抑的却带来了巨大的憧憬,两相比较产生的心理落差足以摇撼最坚定的信仰。此时,面对“全盘引进”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冲击,苏维埃必将陷入极端被动的境地,这便是戈尔巴乔夫后期改造直到终于彻底放弃苏维埃体制的社会心理基础。
收稿日期:2008-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