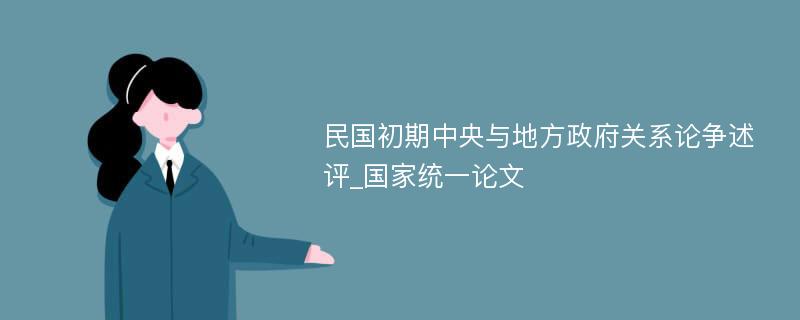
民初国会制宪中中央与地方关系论争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述评论文,国会论文,中央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3)01-0122-06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是民国史研究的难点之一。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宪法中的有关规定,但有时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论争更多地表现在宪法制定的过程中。笔者力图通过考察民国初期国会制宪过程中的有关论争,以全面分析当时人们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识程度。
一、《天坛宪草》制定时期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揭开了议会制宪的新篇章,也揭开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但早期的临时参议院并非正式的国会,它所制定的也仅仅是临时性的根本法——《临时约法》。从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规定来看,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只规定了中央政权机构的组成和大概的职权,对于中华民国地方政权的组织原则和结构则完全没有涉及,对于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相互关系也没有任何规定。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迅速统一,建立中央政府。另外,局势还未稳定,各地制度也不一致,很难就中央与地方关系达成一致意见。这就使实际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缺乏规范,客观上加剧了双方的冲突与争夺。
1913年4月国会正式宜告成立后,两院各选委员30人,组成了以汤漪为委员长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因会址在天坛祈年殿内,故人们称此次制宪为“天坛制宪”,它标志着国会正式制宪的开始。此时,政党是国会政治的中心,国会议员的政见多反映了所属政党的政见。讨论此时期国会制宪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论争,笔者拟以各政党的政见为考察对象。在所有这些政党中,影响较大的是国民党和进步党。这两党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张有相同之处。
第一,他们都排斥联邦制。民国建立之初,舆论普遍认为主张联邦制既不利于国家统一,也不利于外国承认。进步党特设了宪法问题讨论会,其宗旨即为“绝对的排斥联邦主义,以保国家统一”[1]。梁启超所拟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一条为“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共和国”,他解释说:“共和上加统一两字者,示别于联邦制也。”[2]国民党在其政见宣言中也提出对于政体主张单一国制,而不是联邦国制。
第二,两党都赞成对中央与地方关系采取调和的办法。籍忠寅认为中央集权、地方分权“二者非主义之相悖,乃程度之等差,合而行之,其国乃治,偏而一之,其政始乱。”[3]国民党认为:“实则集权、分权,皆由人之成见而生,如外交、海陆军,不容有地方分权。其他利民之事,不容有中央集权。盖须相因而行”[4)(P534),采两者之所长。
但两党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分歧。首先,进步党强调以国家为本位。梁启超强调以国家为本位,政府应该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既是针对立法与行政关系而言,也是针对中央与地方关系而言。籍忠寅强调国家对地方“无一不指导监督之”。梁启超和吴贯因所拟宪法草案都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在于国家。国民党则强调民治、地方自治。宋教仁曾讲:“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治之地方分权亦不宜,谓宜折衷。……其地方制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行,以重民权。”[5](P271)王宠惠拟定的宪法第二条是:“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其次,地方制度是否规定于宪法。梁启超、吴贯因所拟宪法草案,皆无地方制度的规定。梁对此特别说明:“不别立地方制度一章者,认地方制度以法律定之而已足,不必以入宪法也。”[6](P1359)而王宠惠所拟定的宪法中则把省制列入其中,开创了中国制宪史上省制入宪的先河。再次,高级地方官吏的产生方式。进步党主张高级地方官吏不宜由民选,如果采用选举法,“则内外之维全裂,长属之系尽破,省自为政,道自为政,县自为政,乡自为政,我中国分为百千之土司耳,复何国家之可言。”[7]国民党主张省长民选。另外,国民党中一些人还提出以政务性质及施行的便宜为标准,把政务在中央与地方间进行分配。王宠惠把省的事项分为四大类:省有权办理的事项;可以按照政府划一法令办理的事项;经政府的允许才可办理的事项;受政府的委任而办理的事项。国会中的其他政党多以国家主义相号召,如大中党、公民党等。公民党实质上是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它主张的扩张国家权力,不仅是主张中央集权,而且是支持袁世凯的个人集权。
在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宪法过程中,开始时曾决定到宪法大纲讨论完毕后再讨论地方制度。第二十一次会议大纲讨论完毕,有的委员提出中央与地方权限、地方制度问题。在第二十二次会议时,委员长声明将此问题缓议。三读会时,讨论地方制度应否入宪法,进步党汪彭年主张地方制度关系重大,然而没有具体的提案,所以不能加以讨论。新共和党吴宗慈主张地方制度可以由单行法规定,不必拘泥于宪法规定,获得大家的赞同,所以《天坛宪草》将此重大问题搁置未定。
应该指出的是,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缓议、搁置,并非是由于这一问题无足轻重。实际上,正是因为此问题的复杂性、重大性,不是短时间所能解决,故许多委员主张缓议。另外一个原因是时局的影响。对于国会制宪,袁世凯极尽干涉之能事。在三读会时,解散国会的风声已传播开来,根本无暇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这样繁杂的问题。委员们迫于形势,急于制定一部宪法,结果在1913年10月31日一天就完成了三读。宪法起草委员长汤漪曾说:“当本会讨论宪法大纲之际,固曾提议及此,因国民期望宪法成立之切,本会自不得不以最短之时间,编成此案,以付国民之希望。对于地方政府之组织,遂付阙如。固非主张此种问题,不当规定于宪法也。”[8](P11)作为起草委员之一的吴宗慈也说:“解散国会之风声已传播,乃无暇晷可以讨论此繁复问题。……而民国二年之宪法草案遂将此重大问题无形搁起矣。[9](P58)宪法草案通过后不久,袁世凯便找借口破坏国会。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发布停止国会议员职务令,国会制宪被迫终止。
二、国会第一次恢复与继续议宪时期
袁世凯悍然称帝,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16年6月,袁氏在众叛亲离中暴死,黎元洪继任总统,继续召集国会。8月1日,国会议员齐集北京,正式开会。这样,1913年成立的国会得以重开,史称国会第一次恢复。国会恢复后的最重要工作是继续制宪,因为天坛制宪时期只是完成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起草工作。国会继续议宪后,中央与地方关系成为焦点问题,各方常常因为此问题争辩不已,并引起了激烈冲突,上演了一场国会大斗殴。1917年6月13日,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制宪事业再度停顿。
这一时期,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论争主要集中在省制问题上。关于省制的争论又主要体现在“省制是否入宪、省长是否民选”两个问题上。在省制是否入宪问题上,宪法研究会、宪法讨论会、宪法协议会持否定态度,其中尤以研究会最为坚决。宪法商榷会、益友社、丙辰俱乐部、韬园、平社等则持赞成态度,但在何时提出省制大纲加入宪法问题上则有所分歧。如商榷会提出于二读会期内,益友社、韬园提出于二读期终了。在省长是否民选问题上,反对省制入宪者都反对省长民选,并主张自由任命,但赞同省制入宪者并非都主张省长民选,其中丙辰俱乐部为主张民选者,益友社、商榷会、韬园、平社则表示省长民选并非其绝对的主张,在省制入宪的前提下,可牺牲此主张。益友社还曾提出,赞同省长任命,但条件是必须有省议会的同意。在各政团协商时,双方争论的还有省议会弹劾省长、省长解散省议会如何规定的问题。最后,各政团经过协商达成的地方制度案反映了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首先,各方已同意把地方制度案作为一章定入宪法。其次,规定省长由大总统任命。此外,它规定了省议会于不抵触中央法令的范围内所应有的职权。它虽然没有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但也给省的权限一个粗略的法律界定。
在国会制宪过程中,宪法研究会曾有省制另定宣言书,其成员李芳也曾有反对省制加入宪法意见书,研究会的汤化龙、讨论会的孙润宇更是反对省制入宪的健将。他们反对省制入宪的理由如下:(1)省制问题极为复杂,若将其加入宪法,必然经过长时间之讨论,将延迟宪法产生,难以符合国民期望宪法早日公布的心理。(2)宪法属硬性,省制属软性,属硬性者将垂之永久,属软性者时有变更,以时有变更之省制加入永久不易之宪法,则将来无伸缩的余地。(3)“模糊说”。汤化龙认为省在历史上甚为模糊不定,现在也争论甚多,“与其模糊奠定勉强加入以损害宪法之威信,无宁详细研究,俟时机既至再行规定之为愈也。”(4)将惹起外间政治上的恶潮,并累及宪法的前途,这是对于国家和国会的不忠。(5)妨害国家统一,不顾蒙藏。他们认为“倘若将省制加入宪法,则是分裂国土,破坏统一,反使省之地位省之人格不能确定,且生出蒙藏问题,于国家之领土国家之统一均有妨害。”[10]宪法研究会的省制另定宣言书中也指出,在宪法中仅规定省制,而不规定未定名为省的地方制度,是同为国土,而有加入不加入之别,是不顾特别区域,如蒙藏等。(6)认为定省制于宪法之中是采用联邦主义的先声。他们反对中国采用联邦制,故反对省制入宪。(7)将使中央与地方产生种种冲突,并会使中央受省的拘束。(8)他们担心省制入宪将带来省长民选,等等。反对省制入宪者多主张另以普通法律规定省制。
赞成省制入宪者对反对者的主张进行了反驳。首先,他们从历史、事实、法律各方面强调了省的地位的重要性,批驳了关于省的地位模糊的言论。程修鲁认为,在我国,省上有中央政府,下有无数州县,幅员之广,人口之众,可比欧洲一国。无论从历史还是事实来看,省的地位都很重要。以法律而论,省应具有法人资格。所以,他认为省区域固为国家行政同时兼有地方行政,应列入宪法。韩玉辰也强调,省已构成中国最有力之中心点,是最高自治团体兼国家行政区域,地位并不模糊。其次,张我华批驳了汤化龙的“政潮说”和“不忠说”。他说,岂能以各省几个督军省长来电反对即害怕而不敢规定省制于宪法之中呢,“既以省制规定宪法之内为不忠,岂受各省督军省长电报之指挥而不规定宪法之内即为忠乎?不忠于宪法而忠于督军省长,本席实不知此种理论作如何解释也。”[9](P292)第三,他们分析了省制入宪与联邦制、省长民选或简任之间的关系,认为规定省制于宪法之中并不等于规定联邦。同样,规定省制于宪法之中也不等于非省长民选不可。第四,他们反对用普通法律规定省制。因为用普通法律规定,省的地位和人格将常常动摇。第五,他们认为统一在于精神而不在于形式,规定省制入宪乃是划分双方权限,并非单纯为了扩张省的权力,所以,它并不会破坏统一。
除了上面提到的省的地位与人格要求将省制入宪外,赞成省制入宪者还有如下一些理由。第一,使中央与地方关系有宪法作为保障,减少双方的争论。韩玉辰指出,中央与地方的争论已有多次,“规定省制大纲之主旨,是使中央与地方之权限清晰,不至再因权限问题而发生革命之风潮故也。”[9](P295)第二,有利于国家的强盛和宪法的稳固。焦易堂认为:“如将省制列入宪法,则地方人民视国事如家事,无不自行负责。各国之强盛,全由地方人民权力扩张,中国孱弱,俱由地方人民无法行使权力。”程修鲁认为,省制既入宪法,则已承认省权有法律的根基,有独立的生活,因承认而订定关系条件,则互相对峙,互相维系,而宪法立于不败之地。第三,可扫除国家政治上的浑沌之弊,中央与地方可以分别负担国家责任。程修鲁认为,中央与地方权限划清,省长虽有才能不至攘夺中央,若省长平庸者又不能推诿于中央,省议会议决事件得以宪法为依据,议决范围得以宪法为标准,如此可以扫除国家政治上的浑沌之弊。第四,共和国家以人民为本位,应对人民自治权利有明确的规定。第五,省制入宪,省自治可以发展,不至于随着政局纷扰及国家的治安情况而受影响。第六,许多国家有将省制入宪的先例。
综合观之,这一时期的争论集中在省制问题上,并曾就省制入宪达成一致。这是因为,省的地位日益巩固,省的势力日益发展。另外,袁世凯集权专制的副作用和地方自治思想也有深刻影响。不过,由于国会再次被解散,国会制宪中的论争又暂告一段落。
三、国会第二次恢复与“贿选宪法”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曹锟吴佩孚掌握了北方政权。1922年6月14日,黎元洪通电称以前发布的国会解散令无效,第一届国会应即依法自行集会,继续行使职权。8月1日,国会正式开会,这就是国会第二次恢复。这一时期小党林立,政党分合改组的事件极为频繁。由于政党变换太快,故而难于以政党的政见为标准作为考察此时期国会制宪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论争的根据,而只能以一定的主张作为划分的标准。
这次议宪开始于1922年8月10日,经过讨论,决定以省之地位及权限、省与中央之关系、县制如何规定等三项作为继续讨论的标准。在1923年1月20日会议中因省宪问题发生争议,形成严重政潮。
当时争论的问题为“省是否有制定省宪权”。我们可以把是否赞同省有制宪权作为标准将议员分为赞成与反对两派,即省宪派和反对省宪派。
反对省宪派之所以反对省有制宪权主要有以下一些理由:第一,省宪的要求不是出自民意,而是出自军阀,省有制宪权是帮助军阀,破坏国家统一。第二,只有国会才有制宪权、立法权,其他机关不能制宪。第三,省有制宪权具有联邦制精神,使我国宪法前后不一致,违背了临时约法,违背了国会第一次恢复时期各方通过的草案,违背了以前采单一制的精神。第四,集权于省不能丝毫发展民意。蒋曦明说:“不知只便于接近督军省长者之少数人有作福作威之凭籍,而于全民政治之义渺不相涉,且省之权限大较中央之权大为害于民治尤烈。”[11](P403)第五,背逆潮流。李素说:“世界大势日趋于合,强者不敢逆,弱者不得争,……我乃欲裂一国划分为各个,忘其所长,用其所短。”第六,违反国情。我国的省始于元代,完全为国家行政区域,清末民初省之地位具有两种意义,一方为国家行政区域,一方为最高自治团体,但并没有发展到邦国的程度,而且欧美联邦合众是先有地方宪法后有国宪,由分而合,绝无先有国宪,后有地方宪法,本合而强使之分的。第七,导引革命。他们认为,宪法乃革命、流血的产物,我国革命既未彻底就应该因势利导,若要求省有制宪权,必须再经革命,所以反对省宪。
省宪派赞成省宪的理由主要有:第一,宪法的本意是根本组织法的意思,宪法非国家所独占,省也可以制定省宪。第二,符合地方分权的潮流。刘彦指出:“本席……以为近世潮流所趋无不以地方分权为重,虽间有采用中央集权而全国统一者,然亦仅系专制之小国而已。若我中华民国,幅员辽阔,人民众多,欲操中央集权之制,戛戛其难。[11](P369)籍忠寅批驳了我国过去省无制宪权,所以现在也不应有的观点。他认为,时代不同,如今种种事业比前清多到几十倍不止,若全由中央过问,难免处置失当,所以国家组织应随时代而变迁。国会制宪更应注意国民心理的趋向,他说:“两年以来,国民趋向以为中国如此之国家,完全靠中央集权组织,只有国内事业一日退步一日而已,……故为今日之计,应于宪法上明定对于各省承认有如何之权限,最简单亦须承认各省有制定省宪权。”第三,省宪自治可使人情风俗不同的自治团体自由发展。省宪派还对反对省宪派所说的省宪即为联邦、省宪将破坏统一、省宪将有助于军阀割据、省宪将导致省集权、省宪运动非真正民意等说法进行了反驳。
两派也有共同点。即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地方分权主义。如反对省宪派的蒋曦明曾说他并不主张集权于中央而不分权于省,而是主张省的权限应该在宪法内分配。正如罗家蘅所说:“居今日对于地方分权之主张,任何人均不能反对。”当然,两派的意见也有不同,除了省是否有制宪权问题外,还有两点不同:一是省宪派多主张国权列举,省权概括,而反对省宪派则多主张省权列举,中央概括。二是反对省宪派中多有主张分权于县者。
由于两派的争论,致使宪法会议无法继续。又由于政局影响,宪法会议陷于停顿。1923年10月5日曹锟贿选成功后,国会议员为掩饰受贿之羞,缓和国人的攻击,加快了制宪的进度。10月8日,举行三读会,全案予以通过。10月10日,宪法会议正式予以公布,对这个定名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宪法,人们通常称之为“贿选宪法”。
宪法第五章为国权章。它划分了中央和省的权限,并且双方的权限都采取列举主义。主要有三类:由国家立法并执行事项;由国家立法并执行,或令地方执行的事项,省可于不抵触国家法律范围内就此制定单行法,其中一些事项,省可在国家立法之前行使立法权;由省立法并执行,或令县执行的事项。除以上列举事项外,遇有未列举事项发生时,其性质关系国家者,属于国家,关系各省者,属于各省,遇有争议,由最高法院裁决。
国权章规定了国家对于省权的限制。它规定了国家对于各省课税的种类及征收方法的限制;省法律与国家法律抵触者无效,其解释权属于最高法院;省不得缔结有关政治的盟约,不得有妨害它省或其它地方利益的行为。它规定了省对于国家财政的负担及国家对于省财政的补助、省对于国家军事义务的限制和国家对于省军事设施的禁止事项、国家对于省权力的强制,它还规定国体发生变动或宪法上根本组织被破坏时,省应联合维持宪法上规定的组织。
宪法第十二章为地方制度章。它规定了省组织,还规定省可以制定省自治法,但不得与本宪法及国家法律相抵触。它规定了县组织机构设置及权利义务。它还就国家与省县间的关系做出了一些规定,主要有:省及县以内的国家行政,除由国家执行外,得委任省、县自治行政机关执行;省、县自治机关执行国家行政有违背法令时,国家根据法律规定予以惩戒。从宪法的制定过程,明显地可以看出联省自治运动的影响。在联省自治运动中,许多省份都拟定了省宪法,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即为省事权的规定。八团体国是会议拟定了宪法草案,其中设专章规定了联省政府和各省的权限划分。在联省自治思潮的强烈影响下,地方分权主义成为当时的潮流,致使国会中的两派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地方分权主义,在最后通过的宪法中对中央与地方的权限进行了划分。
四、结语
综观这一时期在国家根本法制定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地方地位日益提升。在《临时约法》中,丝毫未提到地方的地位。在民初正式国会制宪时期,除国民党外,多为主张中央集权、国家主义论者,他们反对地方制度入宪,反对对地方权利给予宪法或法律的保障。国会第一次恢复时期,主张地方制入宪者的势力有所增长,各政团并曾就地方制草案达成协议,同意地方制列入宪法。到国会第二次恢复时期,各派都主张一定程度的地方分权,后来通过的宪法也给地方权利以充分的保障。
第二,人们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焦点已有所认识。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地方政权在国家统一体中的地位问题。从历史发展来看,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地方的地位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国会制宪过程中,一些人提出了以法律而论,省应具有法人资格,必须通过宪法规定保障地方的地位与人格。在具体主张上,在国会第一次恢复和继续议宪时期赞成入宪者提出了省是最高自治团体兼国家行政区域,在国会第二次恢复时期,明确提出了地方分权,省有制宪权。二是中央与地方政权的权限划分问题。这可以说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只有双方权责明晰,互不侵越,才能保障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和谐、健康发展。在正式国会前两次议宪过程中,尽管也有少数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王宠惠、汤漪、丁世铎等,但人们更多关注的则是省制问题,即政府的组织机构设置问题。到了第三次议宪时,人们对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核心即双方的权力划分问题更加重视。宪法起草委员汤漪在说明增加国权章的理由时说:“地方制度不能离国家组织而为单独解决,必以权限划分为前提。”[11](P112)人们还就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原则或标准进行了一些探讨。如国民党提出的以政务的性质及施行的便宜为标准进行分配。在实践中,还把这一关键问题初次规定在宪法中。这体现了近现代以来把中央与地方关系规范化、法制化的趋势和潮流,是国会制宪留下来的宝贵经验。
第三,人们就联邦制与单一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进行了辩论,分析了各自的长处,并注意到了它们与我国国情的关系,他们探讨了哪种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更适合我国。通过论争,澄清了一些理论和实际的误解,如在联邦与统一的关系方面,联邦是否等于破坏统一的问题;再如,建立联邦制必须先有邦的实际存在等。
第四,人们对具体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比如,是用国家根本法还是用普通法律规定地方制的问题;对涉及地方权限的一些问题,如省长是否民选、省是否有制宪权等问题;在一些个案中对中央与地方的权限进行了具体的划分,等等。
第五,通过国会制宪过程,我们可以对影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因素有更多的了解。在国会制宪中,西方政治思潮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如联邦制、地方自治、法制观念等。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军阀政治、政党政治以及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
国会制宪不是孤立的,我们还应该看到它消极的一面。国会的制宪不是被嗜权尚武者所摧毁,如袁世凯之解散国会,督军团之干预制宪,就是被他们所操纵和利用,如曹锟贿选。
可以说,当时的军阀、官僚并不以立宪政治为依归,他们并不准备遵循民主共和国的游戏规则,这就使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论争多成为历史上的一些资料,而对实际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转型却发生不了什么作用,因此,国会制宪的结果只能成为一纸空文。
收稿日期:2002-09-10
标签:国家统一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宪法监督论文; 历史论文; 袁世凯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