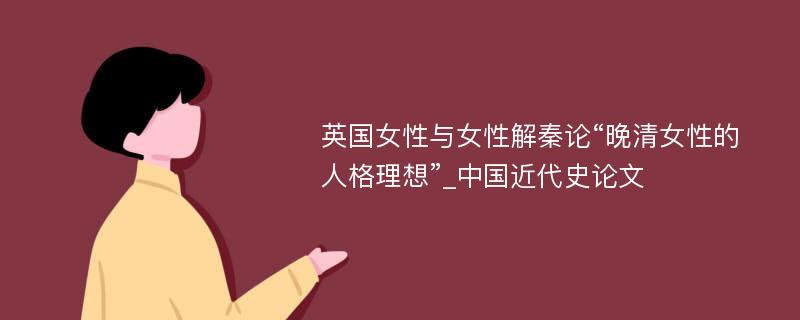
“英雌女杰勤揣摩”——晚清女性的人格理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杰论文,晚清论文,人格论文,理想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妇女观念所发生的变化,晚清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也开始更新。贤如孟光,良似孟母,自然仍有人想望,而接受新思想的知识者,对贤妻良母的囿于家庭已很不满足。适逢其时的女国民意识的发生,使得新女性形象的出现成为可能。而不少诗文中一再重复的“娶妻当娶”与“嫁夫当嫁”套式,以及英雄与英雌的对应,恰好以其丰富的意蕴,为我们提供了可资研究的典型。
探寻“娶妻当娶”与“嫁夫当嫁”的出处, 原与爱国主题相关。 1902年创刊不久的《新民丛报》,便发表了一组题为《史界兔尘录》的杂记,中有一则云:
英女皇额里查白终身不嫁。群臣或劝之嫁,答曰:“吾已嫁得一夫,名曰英吉利。”意相嘉富儿终身不娶。意皇尝劝之娶,对曰:“臣已娶得一妇,名曰意大利。”善哉爱国之言!〔1〕
此故事既传布了新知识,又切合时人的救亡心情,因而在刊物中虽不过聊备一格,不见重要,却还是引起了极大关注。当年,柳亚子便写作了《读史界兔尘录感赋》一诗,单挑此段记事开说,最先将其引入诗歌:
嫁夫嫁得英吉利,娶妇娶得意大里。
人生有情当如此,岂独温柔乡里死。
一点烟士披里纯,愿为同胞流血矣。
请将儿女同衾情,移作英雄殉国体。〔2〕
柳诗本出自一位十六岁的热血少年,于是在本事之外,更渲染出一派慷慨激昂的情调。这也为其后的作者所沿袭。
1906年,高旭与务本女学堂的高材生何昭结婚,“英雄儿女相得益彰”〔3〕。同人纷纷作诗祝贺,《复报》第8期之“诗薮”,因之几成贺新婚专栏。开篇之作为马君武的《祝高剑公与何亚希之结婚》,再次使用了“娶妻”与“嫁夫”对举的格式。不过,喜欢发表独立见解的马氏,对这段史事也有所挑剔:
娶妻当娶意大里,嫁夫当嫁英吉利。
我读欧史每怀疑,知是英豪欺人语。〔4〕
其实,“英豪欺人”的底细,《史界兔尘录》已有揭露:加富尔的不娶是“真不娶也”;至于伊丽莎白女王,则“相传大儒倍根实额里查白之子也”。马君武尽管对此类名人不婚的逸事持怀疑态度,而其将“娶妻”“嫁夫”的对句置于篇首,作为庆婚诗的开头,且由柳诗“嫁得”“娶得”的叙述语调,变为“当娶”“当嫁”的价值肯定,无疑更突出了以何种标准择妻选夫的实在内容。由此,用来宣抒爱国激情的句式,便开始向寻找理想女性转型。
理想女性的模范,在晚清诗文中屡有提及。若为这些古今中外的女子列一排行榜,高踞榜首的中国女性应数花木兰,外国女子,则贞德、罗兰夫人、批茶、苏菲亚大致不相上下。
其实,与花木兰同一类型的还可举出宋代的梁红玉与明代的秦良玉,三人都有过为国抗敌、亲临沙场的英勇行为。因而,在革命情绪昂扬的《女子世界》杂志,便曾分别为三女立传。柳亚子的《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家花木兰传》、《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传》,职公的包括《秦良玉》在内的系列《女军人传》〔5〕,无一例外, 均以现代语汇,强调了各人的女军人身份。军人的本务是保国保种、战场杀敌。若论救国,自以从军手段最直接。其时已萌发国民意识的女性,又屡受外患频仍的刺激,便不能满足于以笔墨、宣讲发抒爱国热情,而对行动充满渴望,军旅生活于是为其所衷心向往。男性作者的撰写中国女杰传记,尚属以之期望于女子;女性自我表述中的英豪情怀,则因决心实践,而更为动人。拒俄风潮中,浙江石门文明女塾教员吕筠青写作的《忧国吟》五首,即吐露了这般情思,所追步的古人,也正不出上述三杰:
沉忧日抱杞人思,怕见江山破碎时。
叹息娥眉难用武,临风空读《木兰词》。
(其一)
千秋女杰有秦、梁,不信军中气不扬。
我愤时艰无死所,拼教马革裹沙场。
(其四)〔6〕
从空羡花木兰到效法梁红玉与秦良玉的描述,真实、完整地展现了晚清女子由文弱到刚强的人格改塑。其诗以留日女学生的报名入拒俄义勇队以及上海对俄同志女会的成立为事实依托,故能缩影式地反映时代女性的感情生活。而像柳亚子一般特别标榜“民族主义”,“祝二万万女同胞,有继梁红玉而起,以助我杀异种、保同种之遗志者”〔7〕,又在抗击外侮之外,揭出排满革命的意旨,是为另一层发挥。其他为时人称颂的古代妇女尚有西施、聂嫈、缇萦、王昭君、班昭等。古来女子有名者本不多,经过晚清文人的大面积发掘,且重新阐释,或表彰其爱国心,或推其救父情以救世,或赞赏其侠肝义胆,或佩服其著述流传史册,故都以新形象榜上留名。
与中国古代女性的举例多半须断章取义不同,外国女杰的事迹运用起来因贴近晚清国情,而更少曲解。所以,中外并举者固不乏人,如金天翮之《女学生入学歌》所歌唱的“缇萦、木兰真可儿,班昭我所师。罗兰、若安梦见之,批茶相与期。东西女杰益驾驰,愿巾帼,凌须眉”(其三)〔8〕,所立女杰楷模东、西各半; 而在以新思想自豪的新人物中,充盈笔下的便尽多西方女英。甚至尚未明了其人身世,也照样称说,畅言无忌。《女军人传》的作者,即赞扬西方女权学说盛行,“遂胎孕二十世纪女权发达之美果,罗兰、贞德、若安、批茶辈女杰乃不绝踵于欧洲”。短短两句话中的错误已不只一处。
被上文作者一分为二的贞德与若安,其实是同一人的不同译名。相对于罗兰与批茶,贞德(St.Joan of Arc,1412—1431)对现代中国人尚不算陌生。这位抗击英军、被俘牺牲的法国农家少女,在晚清也获得了普遍的尊敬。她的名字,因译法出入,而有贞德、若安、若安打克娘、如安打克娘等多种。关于她的介绍,《女报》(《女学报》)登载过《法国女子贞德演说》〔9〕,其传记也屡经编写, 如《中国新女界杂志》发表过梅铸的白话体《法国救亡女杰若安传》,《鹭江报》刊登过天纵子的文言体《法国爱国女子若安传》,后文更被《选报》、《政艺通报》等多家报刊转载〔10〕,使贞德的大名轰传人口。晚清人最赞赏的是贞德以一弱龄女子,而能跃马疆场,挽救国运,英勇献身。所以,《中国新女界杂志》专门选刊了表现贞德英姿的绘画《法国救亡女杰若安打克娘征尘跃马图》〔11〕,各篇传记也都在“爱国”与“救亡”上作文章,以应合中国时势。更有作者将贞德与中国最著名的女杰花木兰比较,而以为木兰有所不如。因木兰的事业,“亦不过代父从军,并没有什么大功劳,能以把一个亡国,都振兴起来。照法国若安那种样子,那真是从古以来少有的女杰哩”〔12〕。贞德因此以“爱国女子”、“救亡女杰”的形象,留驻在晚清中国人心中。马君武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赋诗称赞其“初逢便倾倒”的女士张竹君。所谓“沦胥种国悲贞德”,所要凸现的,乃是张竹君“慷慨国艰”、 救国救种的豪杰志行〔13〕。1903年元旦,吴保初为两个女儿弱男、亚男作诗一首, 希望“女勿学而父,而父徒空言”。吴为其女选择的取法人物,不在中国,而瞩目西方:“西方有美女,贞德与罗兰。”〔14〕着眼之处,仍在其人的爱国能付之行动。
与贞德一同被吴保初举示的罗兰,实指让-马里·罗兰(Jean- Marie Roland)的妻子罗兰夫人(Jeanne-Marie Roland,1754—1793),晚清又译作玛利或玛利侬。其名常见诸诗文。如广东香山女学校的《学约》中,要求女学生“勉为世界之女豪”,所称引的也是“罗兰夫人,若安少女,有为若是,何多让焉”〔15〕。柳亚子则更喜欢并提罗兰与玛利,以赞美革命夫妇。思念刘师培、何震,便作诗曰:
别有怀人千里外,
罗兰、玛利海东头。
高旭与何昭将举行婚礼,柳氏填词寄意,亦有句云:
却羡女权新史艳,
更罗兰、玛利雄心贮。
而且,此称谓既已赠何昭,又再送其妹:
一编布鲁《英雄传》,
玛利、罗兰好定情。〔16〕
其实,持激进革命主张的柳亚子等人之赞赏罗兰夫人,多少有点历史的误会。因罗兰夫人虽参与法国大革命,却属于温和的吉伦特派,最后更被激烈的雅各宾党人送上断头台。她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名言是:“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而柳氏等人的接受罗兰夫人,主要还是梁启超的一篇传记发生了作用。
和这一时期潮涌而来的众多文章风格相同,梁启超以他一枝挥洒激情的笔,为法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性画像,而写作了《罗兰夫人传》。正题前的冠以“近世第一女杰”之定语,表现出梁氏对罗兰夫人的极为推崇。传文中的一段话,更是流传众口的一时名言:
罗兰夫人何人也?彼生于自由,死于自由。罗兰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罗兰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仑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玛志尼、噶苏士、俾士麦、加富尔之母也。质而言之,则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罗兰夫人;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罗兰夫人。何以故?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十九世纪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国大革命之母故。〔17〕
因梁文之言,其时还流传过一则“考试新笑话”,说某考生作文曰:“拿破仑与梅特涅,一母所生,而一则为民权之先导,一则为民权之蝥贼。”〔18〕而晚清寻求新知识的读书人,确少有未读过《罗兰夫人传》者。梁传的感染力,不但来自其所塑造的爱国女性形象,还在于一幕悲剧的完成。罗兰夫人为爱国而革命,又为救国而被革命吞噬,这也使其人对充满浪漫革命理想的文人具有无穷魅力。一首吟咏罗兰夫人的诗,最能体现此种心理:
巴黎狮吼女罗兰,卷地风潮宝袂寒。
我爱英雄尤爱色,红颜要带血光看。〔19〕
崇拜罗兰夫人,于是带有一种爱国与流血交融的悲壮感。
对于救国革命的向往以及壮烈牺牲的渴慕,在这一时期的虚无党故事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露。与中国同处专制统治之下的俄国,当时正是革命风潮迭起,虚无党的暗杀行动捷报频传。这自然给予中国的志士们以极大鼓舞。特别是女性成员之为俄国虚无党中坚力量的事实,尤其令晚清革命者动心。不断见诸报刊的新闻报道以及流传坊间的小说传记,使其事迹广泛传播,为人熟知。以致并非激进党一路的孙雄,也有欧洲国家“无论王党、政党,以及进步、保守、激烈、温和各种党派,几无不有惊天动地之女杰,厕乎须眉之列,以扶翼而左右之”〔20〕的印象,虚无党的故事无疑在其间起了重要作用。柳亚子更认定:“法兰西何以有革命也?俄罗斯何以有虚无党也?欧洲各国何以有无政府主义也?其女侠之赐哉!”〔21〕而虚无党女党员中,最著名的人物便是苏菲亚(Sophie Perovskaia,1854—1881)。不仅革命派的刊物《民报》登载过《苏菲亚传》,金一(天翮)记述虚无党历史的《自由血》中有苏菲亚的事迹,而且,改良派人士对苏菲亚也相当敬重。并且,真正使其广为人知、英名远播的,也是康有为弟子罗普写作的《东欧女豪杰》〔22〕。这部小说虽未完成,在当时却已激起强烈反响。单是《女子世界》杂志,便先后刊出和罗普小说中诗的作品多首,马君武、高旭、蔡寅均有份〔23〕。经过大量渲染,苏菲亚这位血统高贵而又献身革命、流血牺牲的女性,在晚清于是赢得极高崇敬。歌咏罗兰夫人的作者,因而也以同样的热情礼赞苏菲亚。诗中所选取的光辉一刻,正是此女在莫斯科街头指挥刺杀沙皇亚力山大第二的场景:
胭脂队里苏菲亚,枪火丛中墨士哥。
欲为须眉邀幸福,慈肠终比侠肠多。〔24〕
诗人虽然为表彰苏菲亚的救世精神,特别道破其慈悲心怀,却恰好显示出该女子普遍留于国人心目中的女侠形象。
而晚清正是一个侠风高扬的时代,“壮怀激烈”、“热血沸腾”,用于形容此一时期的救国志士,正是异常贴切。其时认同于侠烈精神的不仅为男子,女性亦不例外。即使持论较为平和,如肯定“幽”、“淑”、“贞”、“静”为中国女子传统美德的《女德论》作者,也主张在新女德中加入“侠烈”一品,可见其确为一时风尚。激烈派如柳亚子,更是大张旗鼓歌颂侠女。为此,他不但发掘古籍,为红线、聂隐娘两位传奇小说人物重新立传,而且将贞德、苏菲亚等人一并归入女侠之列,所取者全在“重然诺,轻生死”,“一往不返,一瞑不视,卒至演出轰霆掣电惊天动地之大活剧”〔25〕。
在文人革命的浪漫情调中,以苏菲亚等女侠为榜样,本世纪初诗文作品所歌颂的理想女性便大有激烈者在。柳亚子既已呼吁男子“与其以贤母良妻望女界,不如以英雄豪杰望女界”,并寄语女子“献身应作苏菲亚,夺取民权与自由”〔26〕;署名“一尘”的作者,更直截了当用《理想的女豪杰》作诗题,抒写内心的想望。而其所仰慕的女性,正是“磊磊此身惟嫁国”的“铮铮民党女中豪”:
高风千古慕罗莲,爆弹钢刀在手边。
赤血救回人世劫,苍鹅斫死地中眠。
神州汉种三千姓,铁里新硎十九年。
朝刺将军暮皇帝,谁能无价买民权!〔27〕
在俄国虚无党的感召下,中国革命志士也纷纷开始实行暗杀。有苏菲亚之举的女性在晚清虽终未出现,刺客的妻子们却因共同分担着英雄行为,而具有同样的慷慨悲壮情怀。吴樾刺杀出国考察的五大臣行前,其妻即赋诗三章,以示诀别:
劝君爱国救同胞,几个男儿意气豪。
愧我无才能共济,莫因离别赋牢骚。
诸般讲解殷勤教,领悟无缘恨未消。
从此窗前谁共语,奈何天里度终朝。
茫茫后会知何日,痛哭分离在目前。
好梦岂知容易散,痴心空望月常圆。〔28〕
诗篇有情有义,情足义完,更使其感人至深。与吴樾的《复妻书》合观,吴之语妻,“吾所谓复仇者,非私子于我,而为我复仇也,吾之意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像耳”,并以造成“惊天动地之革命事业”的“区区一弱女子”罗兰夫人相期许,激励妻子“天下事人能为者,我亦能为之”〔29〕,奇情壮采,正可互相发明。
由壮举与情诗相互烘托,吴樾夫妻也成为晚清革命文人追慕的理想配偶。“娶妻当娶”与“嫁夫当嫁”的表述,于是又与行刺暗杀的现实关合,而出现在高旭诗中。这次英烈行为的预备实行者换成女性,诗人写来更辞采飞扬,悲歌激荡。诗题作《报载某志士送其未婚妻北行,赠之以诗,而诗阙焉,为补六章》:
仗卿演出大风潮,东亚虚无帜特标。
左手快枪右炸弹,行看指日翦天骄。
革袋风腥触鼻酸,长途万里报平安。
归来说是蚩尤血,倾入杯中饮合欢。
娶妻当娶苏菲亚,嫁夫当嫁玛志尼。
漫说金闺无国土,黄金铸像古来稀。
万一屠鲸事不成,女儿殉国最光荣。
后先我亦终流血,肯向温柔老此生!
歌成易水赴沙场,始信裙钗有侠肠。
此后国旗扬异采,黄龙摘去绣鸳鸯。
无情风雨落花红,敢恨佳期败乃公?
绾就同心坚俟汝,灵山他日笑相逢。〔30〕
六首诗一气贯下,情、义相融,一如吴樾之妻的送别诗。“黄金铸像”一语更直接承袭吴氏的《复妻书》,证明其诗情确有本源。高旭所塑造的这对未婚夫妻,虽为革命行动而舍弃了已定佳期,然其情却是生死与共,地久天长;且因既是情人、更兼同志的双重关系,而越发浓挚。古语所谓“英雄儿女”,今人所谓“革命加恋爱”,此为最佳范例。烈士吴樾勉励其妻“为同胞复九世之仇”、“生则辱,死则荣,不惜一己之牺牲,而为同胞请命”诸语,也发生了效应。俄国虚无党女杰苏菲亚与“少年意大利”党领袖玛志尼(Giuseppe Mazzini),于是被诗人所代表的革命志士取为选夫择妻的模范。以共同革命为基础的爱情生活,便成为这个时代激进青年理想的结合方式。
渴望人生的轰轰烈烈,期盼实现生命的最高价值,古来视为悲苦的离别,便一转而充满豪情。对文弱的旧国民性的批判,以及对尚武精神的呼唤,更加强了分离在即的亲友为国献身的决心。不少旅东人士亲眼目睹过的日本国内为军人送行而大书“祈战死”的场面〔31〕,尤令晚清志士心折。一反“平安归来”的祝愿,此时的送别诗也往往期以“殉国”,而不讳言死亡。顾灵石便仿杜甫的《新婚别》,反其意作诗二首,极写新婚夫妇相互激励的壮别情。妻子对丈夫如是说:
岂无伉俪情,国雠终难忘。
坐家守妻子,大局沦可伤。
恨我非男儿,梦魂飞战场。
事成当封侯,不成为国殇。
去去好自为,管取家国光。
莫将儿女泪,柔折铁石肠。
词意已够激昂。其夫则更壮烈,以为妻子亦可从军同行:
国民各有任,男女无低昂。
酬子一樽酒,愿子毋相忘。
红飞十字旌,联袂更褰裳。
同袍赴国难,子为疗痍创。
柔情与热血,灿烂而淋琅。
壮士忘其痛,跃起飞战场。
妇人在军中,兵气日以扬。
努力挽陆沉,女权赖尔昌。
须眉到巾帼,国运不可量。〔32〕
与杜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的诗句对比,实为大异其趣。而丈夫希望妻子作随军护士的想法,在其时也带有普遍性。《女子世界》杂志即曾刊出过郑锦湘《致同学某女士书》,因拒俄事急,郑故慷慨陈词:
有义勇队乎?湘愿为义兵。有赤十字社乎?湘愿为看护妇。果能保全吾国,固为幸事;即不幸国灭,吾辈亦当捐此生之躯,以殉我祖国也。〔33〕
张竹君也为此从广州北上,“欲投身红十字会以自效于国”〔34〕。做看护妇既为女性救国的实行途径, 女护士职业的创始人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之名一时为人所熟知,也便在情理中。《女子世界》与《中国新女界杂志》均登载过南丁格尔传,并配发图像,译名亦有南的搿尔与奈挺格尔之不同〔35〕。两传均突出其战场救护的随军身份,显然意有独取。
无论是临阵杀敌,还是火线救人,都有英勇的意味在。令人惊奇的是,晚清不少作者在女英雄的行列中,竟然会加入批茶女士。高旭诗先是歌颂“批茶女,玛利侬,彼何人,树奇功”,末后回顾中国,叹息“谁为女英雄,我泪欲红”;杜清池作诗亦云:
玛利、批茶著美欧,立身当与彼为俦。
救亡事业无男女,几辈英雄亦我流。〔36〕
而此批茶女士并非他人,乃是《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 高、 杜之诗均写于1902年,则与当年《选报》对其人的介绍大有关系。初刊《选报》的《批茶女士传》,又被发行量颇高的《女报》(《女学报》)以及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新民丛报》转载、摘录〔37〕,因而流传更广。传记中关于批茶女士拯救黑奴的一段话,无疑给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十九世纪,美洲有名女子,以一枝纤弱之笔力,拔无数沉沦苦海之黑奴,使复返于人类,至今欧美人啧啧称之为女圣者,则批茶女士是也。
此传之影响,一时竟超过林纾译述的小说《黑奴吁天录》,使斯吐活女士之名也为批茶所掩。谈论斯托夫人的小说,人们提及的往往只是《五月花》,而不是著名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即《黑奴吁天录》)。直到1909年《女报》刊登的一首诗,仍然这样表彰:
女子慈心未有涯,共和祖国早萌芽。
放奴义务高千古,收效原从《五月花》。〔38〕
取意正来自《批茶女士传》所赞述的批茶行事及以《五月花》为其关涉释奴的代表作。斯托夫人的小说《五月花》本与反对奴隶制无关,由于译介的错误,这个误会一直被延续下去。晚清读《黑奴吁天录》的人,也从未将其与批茶合为一说,似乎批茶与斯吐活并不相关。于是,批茶女士便独领放奴之美名,成为众口争传的外国女杰。
传扬其事,意在取法。中国的有志女子因而竞相以批茶为楷模,立誓学步。《香山女学校学约》还只从戒除陋习的角度,反对“虐待奴婢”,而称颂“美国放奴,批茶之力;我辈女流,曷不瞻仰”;立志创办“女界自立会”的云南女子张雄西,则完全是受了批茶事迹的感染,才有此雄心与动议。其《创立女界自立会之规则》即称言:
夫批茶者,不过美洲一女子耳,目睹黑奴惨状,且思有以救之。自《五月花》一书出,未一年而数千百万黑奴,竟能脱离苦海,复返人类,诚千古未有之盛事也。且黑奴与美人,并不同种,而批茶尚能苦口婆心,挽回数百余年圣贤豪杰未及挽回之积习。某睹今日女界之状况,其出于种种下等不堪之事者,又皆我同种也,能不慷慨悲愤泣下沾襟乎?〔39〕
其拟创之“女界自立会”,正是以拯救被鬻卖之女子为主旨,学法批茶,行迹亦求相似。张雄西的思路是因批茶的救拔异种,而反躬自责,起意援救同胞;蒋智由的联想方向正好与之相背,却更具气魄。蒋为《批茶女士传》的译稿润色者,对批茶的推服也在众人之上。他比较木兰、贞德与批茶,将其英雄豪杰之行厘为三等,分别命之为“身家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之代表。木兰替父从军,“未尝曰吾为国则然也”。蒋氏因此“据其知识言之,固只知有身家者”,虽“敬之重之而推为奇女子”,终嫌其不免狭隘。比之贞德的“奋臂大呼,身先士卒,累战克捷,尽返法之土地,而国以不灭”,木兰自然落于下风。而“知有国家主义”的贞德,在蒋氏看来也不能满足,因其所救不过一国耳。更胜一筹的则有批茶在:“夫批茶之与黑人,不同种也,一白人而一则黑人也;不同国也,一美洲而一则非洲也。而批茶一视同仁,不分畛域,此可谓知有世界主义者也。”蒋智由为上海爱国女学校学生演讲,既倡言“今开学堂,则将使女子为英雄豪杰之女子”,自然要“取法乎上”:
木兰能为之,吾何不能为之?贞德能为之,吾何不能为之?批茶能为之,吾又何不能为之?若木兰者,吾行且驾而上之;贞德者,吾将与之比烈,而批茶者,吾将与之相颉颃矣。是则今日之开学堂,主义在此;吾之演说,主义在此;诸女士之来学,主义亦当在此!〔40〕
如批茶一般,以拯救全人类为职志,不许之以英雄豪杰,又当何谓?
受中外女杰榜样的感染,晚清具有壮烈情志的女子日益增多,由此使得以往用于女性的赞美词语大有相形见绌、不敷应用之势。此时因而出现了一批新造用语,试图准确概括这些新女性形象。万昭平、秦浩之称许创立“对俄同志女会”的郑素伊等人为“女中大志士”,《云南》杂志编者之赞美只身赴日留学的女士孙清如为“巾帼而须眉者”〔41〕,终不如高旭诗中喜用的“金闺国士”更精彩。“国士”乃国之精英,世上当得此称号的没有几人。女子而为国士, 自是极高的赞誉。 而高氏1905年作《游爱宕山》(其四)诗所寄怀的“金闺国士”〔42〕,正是其未婚妻何昭。二人日后的结合,为柳亚子比作“罗兰、玛利”,并非毫无来由。不过,无论是“女英雄”、“女志士”、“巾帼须眉”还是“金闺国士”,其构词方式,都是把关联女性的用语叠加在原本指涉男性的语汇上,意在指出,其人虽为女性而有男子气概。与此同时,也有人为了突出女性的中心地位,将上述形式倒置,而成“英雄巾帼”一词,如马君武之“英雄巾帼古来难”、广东女士同怙之“英雄巾帼岂无人”〔43〕,均此例也。其说法仍不过是具有男子一般英雄气概的女性。此类用法,字面上不免互相矛盾,且终究脱不开男性语境的范围。
为避免这一类的尴尬,其时已有人提出彻底解决的办法。《支那女权愤言》的作者便站在女性的立场,主张使用“英雌”一语。文章厉斥“扶阳抑阴”之说流行,而使女子成为男子的“寄生物”,也失去了独立的表述语言:
世世儒者,赞诵历史之人物,曰大丈夫,而不曰大女子;曰英雄,而不曰英雌。鼠目寸光,成败论人,实我历史之污点也。〔44〕
作者为清洗历史污点,便自我创意,自署其名曰“楚北英雌”,以为女界表率。而这一更改,使女性由“女英雄”之类的修饰语变为中心词,并完全摆脱了与男性历来剪不断的语言直至潜意识的依附关系,方始画龙点睛地揭示出晚清女子独立自主的全新精神境界。柳亚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英雌”一语。所言“良妻贤母真龌龊,英雌女杰勤揣摩”〔45〕,实乃其反对“贤母良妻”教育的男性中心立场,要求女子教育以培养女英女杰为宗旨的诸多论述的诗语表述。不过,这一次对男性中心的否定,一直贯彻到与女性相关的词语运用上。因而,其标举“英雌女杰”,便不只是对“贤母良妻”的语词贬抑,还将柳氏对女性一贯的尊重爱敬态度,准确、完满地映现出来。晚清少数先觉之士对于男女平等要求之强烈、思虑之深入,也在以“英雌”与“英雄”对举的语言改造层面上得到充分展示。尽管“英雌”这一新创词语日后并未流行,却无碍于其作为历史遗留物的价值存在。
注释:
〔1〕《新民丛报》7号,1902年5月。
〔2〕《江苏》8期,1904年1月。
〔3〕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第三节《虎丘雅集前后的南社》,《南社纪略》,(上海)开华书局,1940年。
〔4〕《复报》8期,1907年1月。“当娶”与“英豪”, 《马君武诗稿》(上海文明书局,1914年)改作“须娶”与“英雄”。
〔5〕分见《女子世界》3、7、2期,1904年3、7、2月。
〔6〕《女子世界》7期,1904年7月。
〔7〕《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传》。
〔8〕《江苏》9、10合期,1904年3月。
〔9〕《女报》(《女学报》)8期,1902年11月。
〔10〕《中国新女界杂志》3期,1907年4月;《鹭江报》19 册, 1902年12月;《选报》39期,1902年12月;《政艺通报》2年6、7号, 1903年4、5月。
〔11〕《中国新女界杂志》3期。
〔12〕梅铸《法国救亡女杰若安传》。
〔13〕《女士张竹君传》,《新民丛报》7号。
〔14〕《元旦试笔示二女弱男、亚男》,《北山楼集》,(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
〔15〕《香山女学校学约》,《世界女子》7期。
〔16〕《海上题南社雅集写真》,《磨剑室诗词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金缕曲·天梅将行婚礼,制词自纪,属步其韵。意有所寓,情见乎词。世有伯乐,当相识于牝牡骊黄之外耳》,《复报》7期,1906年12月;《贺郁少华、何问湘自由结婚》,《磨剑室诗词集》(上)。
〔17〕《新民丛报》17号,1902年10月。
〔18〕《拿破仑与梅特涅同母》,《新小说》1号,1902年11月。
〔19〕么凤《咏史八首》其七,《中国新女界杂志》3期。
〔20〕《论女学宜注重德育》,《北洋学报》13期,1906年。
〔21〕《中国女剑侠红线、聂隐娘传》,《女子世界》4期,1904年4月。
〔22〕无首《苏菲亚传》,《民报》15号,1907年7月;《自由血》,(上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1904年;《东欧女豪杰》,《新小说》1—5号,1902年11月—1903年7月。
〔23〕《和羽衣女士〈东欧女豪杰〉中作》同题三篇,《女子世界》4期。
〔24〕么凤《咏史八首》其八。
〔25〕巾侠《女德论》,《中国新女界志杂》1号,1907年2月;柳亚子《中国女剑侠红线、聂隐娘传》。
〔26〕《论女界之前途》,《女子世界》1905年1期;《读孟广得韩女士平卿为义女之作和其原韵》,《女子世界》11期,1904年(?)。
〔27〕《理想的女豪杰》三首,《国民日日报汇编》3集,(上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1904年。
〔28〕《吴樾君献身意见书》附《吴夫人送别北上诗三章》,《复报》2期,1906年6月。
〔29〕《暗杀时代》,《民报》临时增刊《天讨》,1907年4月。
〔30〕1908年作,《天梅遗集》,万梅花庵藏板,1934年。
〔31〕见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祈战死》(《清议报》33 册, 1899年12月);秋瑾的《警告我同胞》(《白话》3期,1904年11 月)也有对日本军人送行场面表示羡慕的描写。
〔32〕《反杜新婚别征妇语征夫》、《反杜新婚别征夫语征妇》,《国民日日报汇编》4集。
〔33〕《女子世界》2期,1904年2月。
〔34〕《记张竹君女士演说》,《警钟日报》,1904年5月2日。
〔35〕觚庵《军阵看护妇南的搿尔传》,《女子世界》5期, 1904年5月;巾侠《创设万国红十字看护妇队者奈挺格尔夫人传》, 《中国新女界杂志》1—2期,1907年2、3月。
〔36〕高旭《女子唱歌》(其二),《觉民》1—5期,1904年7 月,杜清池《赠吴、庄、周三女史》, 《女报》(《女学报》)9 期, 1902年12月。
〔37〕分见《选报》18期(1902年6月)、 《女报》(《女学报》)3期(1902年7月)、《新民丛报》12号(1902年7月), 后刊文改题《五月花》。
〔38〕王绍嵚《题词》,《女报》1卷3号,1909年4月。
〔39〕《云南》1号,1906年10月。
〔40〕《爱国女学校开校演说》,《女报》(《女学报》)9期。
〔41〕《女中大志士郑素伊、陈婉衍、童同雪合拍小影》同题二篇,《女子世界》7期:“诗选”栏《编者识》,《云南》1号。
〔42〕诗曰:“手折芙蓉慰所思,夜深露冷倚阑时。征人眠食原无恙,报与金闺国士知。”(《天梅遗集》)。
〔43〕马君武《女士张竹君传》附《赠竹君诗二首》其一;同怙《甲辰春夕,独坐挑灯,偶读羽衣女士东欧女豪杰唱和诗,神韵魄力,迥异寻常,唤起国魂,断推此种,依韵感和》其二,《女子世界》6期,1904年6月。
〔44〕《湖北学生界》2期,1903年2月。
〔45〕《题留溪钦明女校写真为天梅作》(1908年作),《磨剑室诗词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