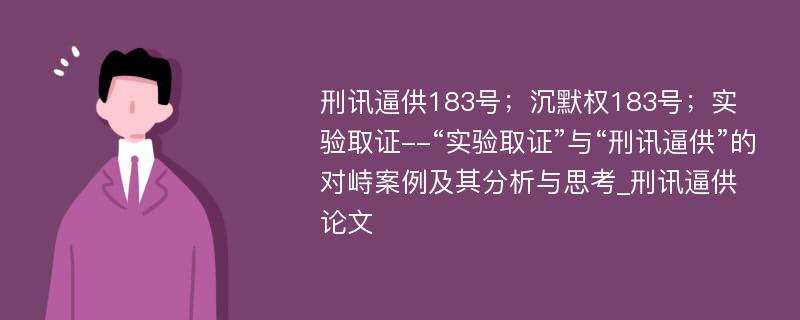
刑讯逼供#183;沉默权#183;实验取证———起“实验取证”与“刑讯逼供”交锋的案例及其分析和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刑讯逼供论文,案例论文,沉默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刑讯逼供是一个世界性的法津问题。在现代中国,它也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客观现实存在,以至于1997年中国新刑法不得不把它作为一个罪名确立了下来。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有很复杂的和很多元的原因,它既有其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也有其现实、制度、政策等因素,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所能予以说明的。本文想通过对一起有关“实验取证”和“刑讯逼供”激烈交锋的典型案例介绍和分析,从“沉默权”及“实验取证”的角度探讨一下防止和禁止刑讯逼供的路径。因此,全文第一部分,我将用较长篇幅介绍由高剑、张闻宇两位记者发表在《文化报》2000年8月2日上的案例报道;(注:此报道我之所以未作删节,是认为记者对案件的报道及其细节都是很重要的,也是很精彩的,对于我们分析“实验取证”问题很有帮助。)第二部分,是我个人围绕此案例所展开的一些分析。
一、一场“实验取证”与“刑讯逼供”的交锋
(一)背景
2000年6月14日下午,安徽滁洲火车站。
31岁的周萍再次登上了开往山东的火车。6个小时之后,火车抵达兖州站。下车,出站,再坐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赶往目的地——济宁。这已是她第22次赶往济宁。
自从去年8月11日,得知丈夫涉嫌盗窃被拘留,尔后又莫名其妙死去的消息后,从没出过远门的她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往返于滁洲、济宁和曲阜间,寻求丈夫死亡的真正原因。
周萍一直认为,丈夫黄公元的死和曲阜公安局刑警的刑讯逼供有关。这一念头的萌生是因为她在丈夫的尸体上看到了大量电警棍电击后流下的痕迹。曲阜公安局解释,使用电警棍是因为黄公元在审讯中逃跑,但公安局的一些异常的举动却让周萍觉得他们的心虚和回避。
“去年8月11日,曲阜3名公安人员(后查明,这3名刑警就是涉嫌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陈新国、徐恒邦、丰宗祥)来到滁洲,通知我们带钱去赎人。我问他们黄公元犯了什么罪,他们也不说,只是让我带3万元去。我问他们3万元够不够,于是他们又说那还是带10万吧。”周萍回忆道。
“可是,我们8月14日到了曲阜,他们又不让我们见人,只是让我们给关在看守所的黄公元送去500元钱。8月24日,我们带着律师又去时,那3名公安就不再和我见面了,换成了一个主管刑事的王副局长接待我们。”周萍说,而这位王副局长见面后,只同他们聊家常,丝毫不提黄公元的事。最后,在律师一再要求和黄公元见面的情况下,王副局长才不得不告诉他们,黄因病重,已被送至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抢救。
周萍和律师随即赶到了医院。两名警察守着的监护室一副戒备森严的模样。周萍赶到医院后不久,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周萍很纳闷,丈夫身体一向很结实,怎么会一下子就垮了?是什么原因导致黄公元的功能衰竭?满身的伤痕是怎么回事?然而,没有人回答她的疑问。
8月31日下午,黄公元终因全身多数器官感染、功能衰竭离开了人世。同日,满怀悲痛和疑问的周萍走进了济宁市检察院,请求该院渎职犯罪侦察局的检察官对黄公元的死亡真相予以调查。
经过调查取证之后,济宁市检察院以陈新国、徐恒邦、丰宗祥涉嫌“故意杀人”向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00年6月14日,周萍第22次赶赴济宁,就是参加法院对此案的第一次审理。
这是一次尝试,尝试的结果是想证明在现行的司法环境下,沉默权是否有存在的可能。
这也是一种挑战。长久以来形成的执法观念难以轻易逾越,传统的侦查手段和证据制度更是一下子难以改弦更张。
尝试和挑战都集中在了一个看似寻常的案件中,交手的双方恰恰又都是熟悉法律的司法人员——检察官和刑警。暗地里的较劲和法庭上的舌枪唇战,让人不禁眼花缭乱。
(二)法庭上的交锋
“审判长,3名被告为了寻求破案线索,长时间对被害人采用固体定位刑讯逼供,致使被害人因伤势过重而引发全身多数器官感染、功能衰竭而死。根据我国《刑法》,我们认为3名被告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不对,事实上,死者黄公元在审讯过程中逃跑,3名被告才被迫使用警械。”检察官的话刚落,被告的辩护律师立即予以反击。“公诉人的指控不符合事实真相。身为警察,在犯罪嫌疑人逃跑的情形下使用警械是合理又合法的。”
“我们有侦查实验的科学鉴定,可以证明被害人黄公元没有逃跑的可能。”
“请问公诉人,侦查实验中的实验者是不是黄公元?实验用的工具是不是案发现场的工具?既然都不是,在一切事情都不具有特定性的条件下做的试验,它的结果怎么能说明问题?!”
“审判长,侦查实验中所用的电警棍、手铐、联椅和案发现场的工具,都来自同样的生产厂家,型号、性能一致。实验者的身高、体重也和被害人黄公元相似。因此,侦查实验的结果具有科学性和可信性。”检察官从容不迫的回应着辩护律师的咄咄逼人的追问,似乎对对方如此早有预料。“侦查实验的科学鉴定结果,可以和证人、证言、尸检等物证、言证、书证相印证,从而形成完整的证明。希望法庭能作为证据予以采用。”
“审判长,依照我国刑诉法,并没有规定侦查实验的结果可以作为直接证据。”
“但是,刑诉法也没有规定侦查实验的结果不能作为直接证据。”
“侦查实验只是一种推测方法,只是一种在侦查过程中使用的手段而已,并不具备证据的性质。”
“但它的结果可以证明3名被告说了谎,编造了所谓的被害人逃跑的故事,以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
2000年6月15日,济宁市中区人民法院。
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在检察官和律师之间进行着。
这是济宁市的一个区级法院。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曲阜市公安局三名刑警涉嫌刑讯逼供、故意杀人一案的公开审理,被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安排在一个区法院的法庭进行。
面对济宁市检察院的三名检察官,被告方派出了5名辩护律师的强大阵容。
尽管不是休息日,但庭审还是吸引了很多的旁听者。上午9时不到,在通往法院的狭窄的巷子里,就停满了大大小小几十辆警车。可容纳近百人的旁听席座无虚席,来得稍晚的人们不得不站到了旁听席两边的过道上。
虽然大多数旁听者并没有身着制服,但下身着橄榄色的警裤以及举止让人明显感觉到他们的身份——警察。庭审后有人向记者透露,曲阜市公安局下属各派出所所长和刑警几乎全部参加了旁听。
与此同时,济宁市检察院不以口供为主要控诉证据的新方法,也吸引了司法系统行家们的关注,一些分管领导也到场旁听。
开庭后不久,检察官们就感觉到了无形的、来自旁听席的压力——对同事们的同情,以及对检察官们“用警察的血染红自己的花翎”行为的痛恨,使得大部分旁听者对检察官满怀着敌意。每当检察官作出不利于3名被告的发言时,旁听席上便“轰”起一片叫骂声。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每当辩护律师作出精彩辩护时,席下会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结果,旁听席上的“表演“惹恼了法官和法庭内维持秩序的的法警:“你们身为警察,怎么这样带头不遵守法律?!”不过,好几次怒目相向和斥责也未能有效的制止“即兴表演”。最后,一位年迈的、被害人的代理律师忍不住大声疾呼:“我抗议……”
法庭调查、举证、辩论——最后,控辩双方的矛盾焦点越来越明晰——究竟是不是刑讯逼供?如果不是,3名被告的行为的性质最多是使用警械不当。如果是,执法者知法犯法,理应严惩。侦查实验的结果——这一对被告极为不利的鉴定究竟能不能作为证据,更是成了控辩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于是便有了开头一幕互不相让的唇枪舌战。
时间在双方的对峙中缓慢逝去,火药味十足的争论增添了空气中的炎热。从早晨9时半开始,除中午休庭外,庭审一直持续至晚上9时半。然而,双方的陈述最终都没有打动法官,侦查实验结果究竟能否作为证据,法官没有当庭作出决断。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所有的人都陷入饥肠辘辘之中。在炎热中煎熬了10个小时的人们最终还是没有迎来法官的判决。面对这样的结果,所有的人都松了口气,毕竟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三)难题和尝试
“这样的结果是预料之中的。”一位检察官庭审后对记者说,“这个案子怎么判,法院还要研究后才能定。但是,我们相信,刑讯逼供确是事实。”
检察官的自信来源于对黄公元尸体的法医鉴定。1999年9月5日,山东省检察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济宁市公安局等数家司法机关曾联合做过一次尸检。尸检中,检察官们注意到,在黄的身体上有多处电击的痕迹。按照被告陈新国的陈述,1999年8月8日,当晚9点钟左右,在对黄的第二次审查中,黄公元突然挣断联椅扶手,拉坏手铐齿,想要逃跑。为了阻止黄逃脱,慌乱中,陈等人用3支电警棍对黄进行了电击。
然而,检察官却注意到一个细节——在黄的阴茎上也有电击的痕迹。检察官们分析认为,人如果不是在身体被固定的情况下,很难会被电击到这么隐秘的部位,即使是在搏斗的过程中。况且,从电击的痕迹看,有明显虐待的迹象。“当时,就凭这一点,我们就认为陈等人在说假话。”一位检察官说。
对于3位被告的动机.检察官们猜测,近两年来,曲阜市陆陆续续发生十几起宾馆盗窃案,但一直悬而未破。黄公元在宾馆盗窃被发现后,他们想以黄为突破口,从黄的身上挖出那十几起未破盗窃案的线索。破案心急,黄不交待,他们就打,结果黄因伤过重,全身功能衰竭而死。
“这几乎是所有造成刑讯逼供的固定模式。”作为专门从事侦查司法人员违法行为的检察院渎职犯罪侦察局的检察官们早已总结出一整套的理论,“从表面上看是办案手段单调,不注重增强侦查的智慧投入。深层次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口供、轻证据的诉讼传统。太依赖于嫌疑人的口供,极易产生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就如黄公元后来也招了供,但结果是有十几起根本就是没影的事儿。”
颇具戏剧性的是,在批判了传统办案思维之后,在指责陈新国等人办案手段单调的缺陷的同时,曲阜的检察官们也突然发现,实际上,他们自己也不得不面临一种选择——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办陈等人的案子?是依赖传统的口供,还是走一条迥异于传统思维、以前从未尝试过的新路?
“讯问,然后在口供中寻找突破,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如果这么做,那我们的行为和陈等人对待黄公元的行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一位主要办案人员如此阐述当初的办案思路,“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另外,从现实情况看,依靠陈等人的口供破案也有很大的难度。
客观条件的限制,加上想寻求办案手段的突破的主观意识,逼着曲阜市的检察官们走上一条以往没有走过的新路——在不依赖嫌疑人口供的情况下,通过其他手段,寻找证据,查明真相。
“你可以不说真话,我们也不强迫你说,但是一旦有证据证明你犯了罪,那么你不合作、不主动交代的态度,将会使你在法庭上遭受不利的判决。”采访中一位检察官的陈词,不由得让人想起美国的警匪片中,歹徒被捕时警察常念叨的一句“名言”——“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
尽管这位检察官并没有明确提到“沉默权”,但事实上,他的观点已明白无误的说明,他们正尝试着给予嫌疑人一项我国刑诉法还没有承认、但确是现代法治国家犯罪嫌疑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沉默权。虽然,这种给予也是出于无奈。
这种尝试从根本上挑战了我们司法人员长期以来对口供的依赖,因为沉默权说白了就是对一个司法人员的讯问是否陈述、陈述什么取决于自愿,任何人都不能施加压力。沉默权从本质上排斥了刑讯逼供。有了沉默权,也许黄公元就不会死去。因为他根本无须担心会受到盘问,也无须考虑是否要逃跑(假设陈新国等人所说的是事实),接受考验的不是他们,而是刑警的智慧和寻找证据的能力。
这种尝试也是给自己出了个难题。“重口供,轻证据”到“重证据、轻口供”毕竟不是词语位置颠倒的问题。
尝试是围绕一系列的侦查实验展开的。
检察官们认为,只要证明在当时的情况下,黄公元没有逃跑,或者黄公元没有逃跑的条件,那么就充分说明陈新国等人所谓“逃跑”一说不成立。如果黄没有逃跑,却被全身电击,唯一的答案就是陈等人对黄进行了刑讯逼供。
2000年1月12日,在有关领导到场见证的情况下,曲阜市检察院模拟了案发现场的情形。他们先从南关派出所调取了同样类型的联椅,又选用了同样类型的手铐。尔后,检察官们把一位和黄公元身高、体重相似的试验者,按现场的情形,双手左右分开拷在联椅上做双手和单手拉扶手的试验,结果是联椅扶手均无破损断裂现象。
针对陈新国所说,黄在逃跑中拉断了手铐3个齿的细节,检察官又找到该手铐的生产厂家作了检测实验,并挑选一爆发力强且一直从事体育锻炼教学的体育老师模拟现场情形,在联椅上用右手腕爆发力往胸前使劲,结果证明黄是无法拉断手铐齿的。
“陈新国他们说用了3支电警棍才制服黄,但通过我们在电警棍的生产厂家对电警棍的性能所作的了解,他们使用的那种型号的电警棍,只要一支一次电击就会让人失去抵抗能力,然而,他们却说搏斗了三四分钟,这显然不可能。”一位检察官如此分析。
一系列侦察实验的结果,坚定了曲阜市检察院对陈等人编造谎言、伪造现场判断的信心。随后济宁市检察院以陈等人涉嫌“故意杀人”向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四)尝试的代价
任何尝试都要付出代价。曲阜市检察院的这次尝试也不例外。舍弃便捷操作的讯问,转用复杂的侦查实验,最明显的代价是办案成本的大幅度增加。请人做实验和四处做鉴定花去的费用,是原先那种坐在家里,靠问口供获取方式的好几倍。
然而,这种代价并非是最大的,最大的是那些看不着且又无法衡量的。一旦检察院侦查实验所得的证据不被法院所认可,那不仅意味着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是白费劲,而且,还会影响后来者对沉默权的探索。
曲阜检察院冒险的同时,也将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推倒了风头浪尖。因为,此案中对侦查实验结果能否作为证据争论的背后,实质上涉及到的却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大问题,这并非一时半会儿能得出结论的事。
二、由此案例引出的分析和思考
(一)由此案例以及其他一些刑讯逼供案例(见本文附件)所揭霹出来的问题,可以看到,刑讯逼供案的犯罪嫌疑人其动机是多方面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共同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从被刑讯人口中索取口供,这在中外酷刑案件中概莫能外。在中外刑事诉讼案件中,口供不仅在过去,就是在现在,仍然是重要的证据形式,也是据以破案的主要依据。因此,当“疑犯”被抓获后,警方的第一件任务就是从“疑犯”口中索取口供。而一般情况下,“疑犯”在开始并不会轻易地供出“案情”,这种情况下,警方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从“疑犯”口中套取口供,于是,刑讯逼供便“应运而生”。“刑讯”的目的是为了“逼供”。这是刑讯逼供的一般来由和一般常人的逻辑思维链条。
(二)按照这样一种思路,要防止和禁止刑讯逼供现象,就得首先解决口供在证据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我们知道,在刑事诉讼中,尤其是在案件侦查过程中,要完全废除口供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改革的是口供的地位和作用,是过去那种视口供为唯一性和至上性的观念和制度(截止目前,许多案件没有口供仍定不了案,或口供变了,案件判决也随之变了。《检察日报》2001年2月15日第二版报道的一个案例就是如此。)口供在我们的刑事诉讼中和刑事侦查中被赋予了神圣的和绝对的地位,以至口供有“证据之王”之称。尽管我们有“重证据,不重口供”的法律原则,但实践中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如何获取口供,就几乎成为刑事警察的主要任务。我们要改变口供的这种地位和作用。
(三)要改变口供的地位和作用,就要建立相应的沉默权制度。但我认为,沉默权制度并不是以废除口供为前提,它们完全可以并存。沉默权制度的核心是“你有权保持沉默”,那么,其中也包含着“你有权可以不保持沉默”,这是疑犯的一种选择权。疑犯愿意招供,可以让他招供;疑犯不愿招供,就不能逼他招供,这完全是他的一种选择权或诉讼权。根据王建成、王敏远两位先生引证的数据,选择沉默权的人,在英国只占4.5%,美国约占4.7%,日本只占7.7%。(注:参见汪建成、王敏远《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述评》,《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146页。)这说明,口供作为证据形式之一与沉默权两者可以并存,可以作为疑犯和被告的选择。
(四)沉默权制度并不是一个单一就可以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制度,而是需要一系列配套性的司法制度尤其是无罪推定制度和相关的证据制度的配合才能存续下去。一旦确立了沉默权制度,疑犯就有权保持沉默,就不能再采取刑讯逼供等手段来套取口供,取得证言,这就需要依靠其他证据来证明案件,就需要相应的取证手段有一个大的进步和进展。而“实验取证”则是应予充分肯定和采用的手段。当然,并不是在所有的案件中,都可以实验取证,而只能在一些有针对性的案件中,比如在黄公元一案中。其实,“实验取证”在中外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中,也曾被大量运用过,比如,在一些案件中,对凶器如手枪射击的距离等等,就曾运用过实验的办法。
(五)如何从法律上给“实验取证”一个定位?我认为,从其性质上看,“实验取证”可以视同我国证据中的“鉴定结论”之证据形式。因为“实验取证”的过程,实际上是用科学的手段,对案件事实进行重复和模拟实验的过程,这种重复和模拟实验的过程就是一个“科学实验”的过程,它同科学鉴定是同种性质的产物,因此,完全可以在法律上给“实验取证”一个合法的定位。
这样,就可以大致上构画一下本文的主要观点和思路:要废除刑讯逼供,就需要建立沉默权制度;要建立沉默权制度,就需要改革相应的证据制度,确认“实验取证”的法律地位,通过完善和有力的证据制度来证明案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有罪,就应无罪推定。我们还应改变一种传统观念,即由过去所信奉的“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改变为“宁可放过一个坏人(罪犯),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无罪的人)”,因为证据制度决定了我们只能如此。一个人有罪无罪,要靠证据来证明,而不是靠刑讯逼供出来的口供来证明。这可能要承受一种观念上的冲击和震荡,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甚至可能使一些有罪的人难以绳之以法,但这是法治、人权保护必须经历的和付出的代价。舍此,我们将永远难以走出一种恶性循环的过程。
附件:两起刑讯逼供案例
第一起案例:吉林省白山市八道江区公安分局刑警队长赵永和、刑警姜伟光刑讯逼供故意伤害致死人命、致残案。
1999年2月22日,吉林省通化市铁厂镇河东村的赵文泰把村边小树林附近的一头没人要的黄色乳牛牵回了家,而恰巧在2月21日晚,与白山市相临的通化市红十崖镇六道岔村七社农民单和昌被人杀死,同时,单家被抢走黄色乳牛一头、鸡数只。白山市八道江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立即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3月12日,专案组得知通化市铁厂镇河东村赵文泰家有一头与此相似的乳牛。分局当晚提讯赵文泰。赵文泰于3月14日凌晨死在分局。他的尸检报告记载:体表90%有创伤,七根肋骨骨折,胸骨骨折,肺部充血,全身上下共有电激伤、木方伤及警绳勒伤共53处,粪便排出体外。但赵文泰在被活活打死之前,没有“招”出一句杀人偷牛的口供,死者的刑讯记录一片空白。
3月12日晚分局还传讯了赵文泰的妻子王贵香及女儿赵欣。据王贵香的亲戚说,王贵香拒绝说其夫杀人、偷牛,于是警察用牛皮带打其脸部、背部和臀部,用木棒打其头部,强行将其按在地上并踩住,用半米多长的三棱木棒打其背部、臀部,王贵香被打得大小便失禁。警察给赵欣“背剑”,在她两臂间塞四五个啤酒瓶,赵欣痛得直叫,警察就用拖布塞赵欣的嘴。
3月14日凌晨赵文泰死后,警察胁迫母女二人承认赵文泰患有心脏病并被牛顶过。母女二人不肯,警察继续恐吓并殴打。最终,母女二人不得不“承认”赵文泰可能死于心脏病等“事实”证据。
在赵文泰死后一个多月,三个杀死单和昌的犯罪嫌疑人焦建新、王成录、张永清因再次犯案被警方抓获,在审讯过程中,他们连杀人、偷牛的事也一并招供了。
1999年7月19日,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赵文泰一案公开宣判:被告人原分局刑警队长赵永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被告姜伟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被告张真无罪。
2000年5月16日,白山市八道江区法院对王贵香、赵欣一案进行公开宣判:被告人张胜利犯暴力取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据记者了解,2000年6月2日,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组为王贵香及赵欣重新作了精神鉴定,系反应性精神病,精神残疾等级是极重度一级。(注:此案例转引自《法制文萃报》2000年7月6日头版。)
第二起案例: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分局刑警赵金元、屠发强刑讯逼供故意杀人案
1998年7月4日,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分局刑警六中队接到洗马路派出所报称,参与一起凶杀案并正追捕的犯罪嫌疑人熊先禄在辖区内出现。六中队探长屠发强立即带员赶到,熊先禄被带回六中队审查。在7月4日至6日连续三天的审讯中,六中队队长赵金元、探长屠发强为了逼取口供,施以种种肉刑对熊先禄进行摧残。
他们先后把熊先禄铐在门房上,使其悬吊空中,或将熊的双手铐在墙的钢管的一端,双脚捆在另一端,使其身体横倒悬空;或把熊按在地上用手铐将其手脚相连进行反拷,当熊疼痛难忍呼喊时,又用抹布将其嘴堵上。7月6日,二人便用铜芯线将重约十余公斤带钢体轮胎吊在熊的脖子上,而熊的双手却被用“十字架”型反铐在钢条上。由于疼痛,为减轻颈部压力,熊只得抬起双腿轮流顶住轮胎,其双腿正面大面积擦伤。而且在三天的审讯中,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休息。7月7日上午7时许,饱受肉刑摧残的熊先禄死于刑警六中队一探组办公室,而其双手仍是“十字架”型反铐在钢管上。
命案发生后,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迅速派人员赶到了现场。事后法医尸体报告证实:“死者熊先禄两手腕上各有两道环型手铐压痕,身上多处软组织损伤,系质量较轻的钝器多次打击形成,后颈部有条状皮肤挫擦伤。并检见死者胃全部空虚,膀胱内尿液点滴无存。”尸检报告的结论是:“熊先禄因外伤、剧痛、饥饿、紧张等过度劣性刺激而休克死亡。”
案发后,赵金元、屠发强二人于1998年8月被依法逮捕。1999年4月26日,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二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判令两人各赔偿附带民事原告、死者家属梁铁梅经济损失5000元。赵、屠二人均不服判,上诉要求从轻发落。二审判决维持了对赵金元的定罪处刑和赔偿判决,而对屠发强维持定罪和经济赔偿部分,处刑改为无期徒刑。据称,这是我国刑法自1979年实施以来,全国法院系统对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处刑最重的一起案例。两位刑警都曾得过多次先进,并荣记功臣。(注:此案例转引自《法制文萃报》2000年4月20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