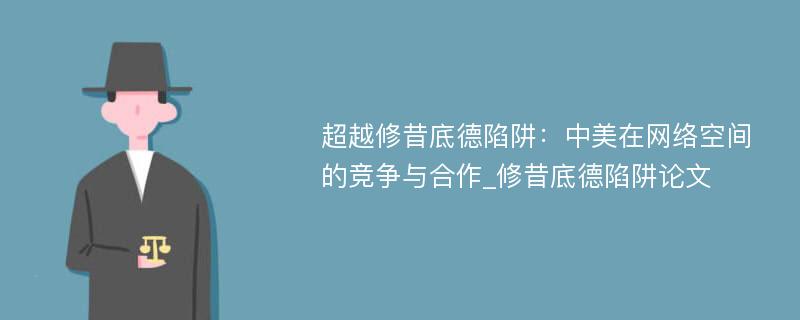
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在网络空间的竞争与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陷阱论文,竞争论文,空间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信息革命狂飙猛进,在推动人类生活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同时,它也给国家间关系、全球治理带来了诸多全新的挑战。不仅如此,互联网的横空出世,根据科技史家的研究发现,“其对人类社会的价值已全面超越蒸汽机革命、电气革命等技术革命范畴,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人类社会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空间——网络空间”,而网络空间安全已悄然演化为亟须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又一重要问题领域。① 中美分别是当今国际舞台上发展最快的新兴大国与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如同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双子塔”,两国对网络空间安全的关切也不可谓不敏感。2013年2月,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曼迪安特发布研究报告,指称一个隶属于中国军方的网络间谍机构,在2006年以来的6年多时间内先后攻击、入侵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至少141家公司及机构的网络系统,窃取了数百万亿字节的商业机密数据。②而后由于某些西方主流传媒、知名政治人物推波助澜,这一报告迅即在国际上掀起了一拨“中国黑客威胁论”的热浪。③而后,2013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揭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棱镜门”监听计划,全球民众对于网络安全的普遍焦虑恰似“一石激起千层浪”,对其关注度与重视度日见升温。中国作为深受网络侵袭之害的“重灾区”,冷酷的现实一再警醒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网络空间安全,主动应对网络空间出现的各种挑战,积极维护网络空间领域的国家利益。可以说,如何稳妥地处理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领域复杂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已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议题。 一、网络空间的中美摩擦 中美关系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的一组双边关系,而网络安全的细胞早已扩散到中美关系的经济与贸易、政治与外交、军事与安全等周身各个关键部位。网络空间的中美竞合态势突出地体现在经济贸易、政治外交以及军事安全这三大“问题”维度,从某些侧面反衬出双方因国际力量变化与世界权力转移而呈现的微妙心态。 (一)经济贸易维度 中美之间经贸往来频密,2013年中美贸易额超过5000亿美元,“截至2013年底的中美双向投资额累计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④经济关系过去一向被视为维持中美紧密联系的“压舱石”和“助推器”,然而在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的新形势之下,这一状况正在发生转变。美国政府近年来不时指责中国政府支持甚至参与针对美国大型公司、研究机构的网络攻击和网络窃密活动,炮制“中国黑客威胁论”。就在曼迪安特公司发布调查报告之后不久,美国政府即公开指责中国政府不但纵容军方参与窃取了美国企业海量的商业机密数据,而且将其所获商业机密、知识产权资料等敏感信息交给了相关的中国企业,由此大大提高了这些中国企业的同业竞争力,进而给美国同行企业造成了数以亿计美元的巨额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2014年5月19日,美方更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宣布起诉5名中国军方人士,指控他们通过网络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公开控告外国政府公务人员针对美国公司实施网络黑客犯罪。⑤这一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做法掀起了中美之间新一轮的外交风波,严重损害了中美合作与互信。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又以网络安全为由,通过立法或行政手段人为设限。干扰中国企业在美国内的正常市场行为,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如中国公司华为集团在美国的一系列遭遇。华为从2001年开始在美国拓展业务,然而无论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计划从华为购买价值数亿美元的下一代电话系统设备,还是华为试图以不足20%的参股比例加盟收购和控股美国网络通信公司3COM,均无一例外地受到了美国政府以及媒体的“过度关注”并最终归于流产。华为受到的最大一项指控是其创始人兼CEO任正非先生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因而华为被认为同中国政府和军方存在着某种未曾披露的密切联系,由此华为的某些市场举措有可能会在特定情况下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对此,华为副董事长、华为美国董事长胡厚崑愤然发表了一封致美国政府的《华为公开信》,逐一驳斥了“与解放军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纠纷”、“中国政府的财务支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等流传甚广的“误解”,并就华为被不公正地挡在美国市场门外而吁请“美国政府能够就对华为所有质疑给予正式的调查”。⑥作为回应,针对华为以及另一家中国电信服务供应商中兴是否适合作为美国全国通信网络供应商一事,2011年11月负责监管国家安全和情报事务的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启动了调查。2012年10月8日,该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电信企业华为与中兴影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调查报告》,其主要论点包括:美国政府应“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中国电信企业对美国市场的不断渗透;美国政府应极力寻找非中国的、替代的通信网络供货商;美国国会应调查中国电信企业的不公正贸易行为;美国国会应通过立法限制那些在修建关键基础设施时无法信任的外国公司对美国通信系统的市场准入。报告最后建议,美国政府应禁止华为和中兴这两家中国电信企业获取美国任何敏感网络的接入权,并阻止其今后实施收购美国资产的市场行为。⑦美国的这一霸道行径迄今并未有任何改观,奥巴马总统第二个任期伊始,2013财年拨款法案第516条明确规定:“未经联邦调查局或其他合适的联邦机构的许可,美国商务部、司法部、美国航空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会等部门不得购买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或控制的相关企业生产、制造或组装的信息技术设备。”⑧ (二)政治外交维度 身为互联网的发源地和技术大国,美国极力鼓吹不受限制的网络自由,试图通过互联网引导他国公民社会进而影响其政治议程,诚如兰德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所称,“作为民主国家的一只领头羊,美国一直致力于打开那些封闭的社会。”⑨而作为互联网世界的一个后起之秀,中国政府认为境内互联网理当属于一国主权管辖范围,“根据互联网的特性,从有效管理互联网的实际需要出发,中国政府主张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发挥技术手段的防范作用,遏制违法信息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未成年人的危害。”⑩双方这种理念层面上的尖锐对立,最终在“谷歌事件”中得到了最直观立体的展露。2010年1月12日,谷歌公司高级副总裁在公司官方博客上发表了一份题为《对华新策略》的声明,宣称由于长期受到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精心策划且目标明确”的黑客攻击,谷歌不愿再对谷歌中国的搜索结果进行审查,并称接下来几周内将与中国政府谈判,以探讨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运行一个没有审查和过滤的搜索引擎的可能性,如若无法协调一致,则将意味着必须关闭Google.cn乃至Google设在中国的办公室。(11)反对“黑客攻击”、反抗“网络审查”,谷歌选择的这一由头显然也是“精心策划且目标明确”的,既冠冕堂皇又似乎言之凿凿,且特别能迎合西方公众舆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可谓是“一方面通过退出这种方式向中国方面发飙,一方面向美国方面和世界舆论撒娇”。(12) 就在九天之后的1月2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题为《互联网自由与全球言论自由的未来》的演讲,首次提出了“互联网自由”概念,并数次点名批评中国的网络管理制度,指责此举无异于构筑“网络柏林墙”。(13)一年多后,2011年2月15日,希拉里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题为《互联网的是与非:网络世界的选择与挑战》的演说,再次指责中国搞“内容审查和技术过滤”,断言这种做法注定要付出沉重的经济、政治代价,是“无法持续的”。她还宣称,“美国在过去三年中已经通过公开渠道向技术人员和积极分子提供了2000多万美元的竞争资助用于奖励研发突破‘网络压制’的方法,今年还将额外奖励超过2500万美元”。(14)对于美方的指手画脚,中方认为在网络空间各国同样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的网络主权应受到尊重和维护,应积极倡导信息自由流动与安全流动相统筹协调的原则,努力避免信息网络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新工具,尤其是不能以“网络自由”之名行“网络强权”之实。(15)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美国政府多次借“谷歌事件”在国际上公然指斥中国的同时,谷歌及微软等美国企业被媒体披露均曾依据《爱国者法案》向美国政府提供用户信息,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美国四处兜售的“不设防的网络自由”的警觉与反思,这一点在“棱镜门”事件曝光之后更是重新发酵、再掀高潮。(16) (三)军事安全维度 相较于经济贸易关系、政治外交关系,军事安全关系无疑是中美关系中的一块短板。一方面,从中美军事关系的整体而言,军事关系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零和关系。即使从技术上讲,任何一国的军事都需要甚至必须有假想敌,追求的目标是战时克敌制胜,平时秣马厉兵”,更何况中美这两个“新老大国之间的彼此防范短期内难以改变,双方都不免采用两面下注的战略,军事上的相关准备因此不可避免”,因而军事安全关系注定是双边关系中最敏感复杂又最危险棘手的部分。(17)另一方面,具体到网络空间来看,各国都在积极发展网络空间作战和防御能力,而实力超群的美国必然走得最快最远。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隶属美国军方的情报机构就已开始筹划强化网络攻击能力,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军又在“先发制人”军事战略指导下加紧开发网络作战武器,奥巴马政府则进一步将网络空间纳入作战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军事力量的组织、训练和装备。(18)不过,在不同政府时期,美国的互联网战略的内容与侧重点有所不同,经历了一个“从全面防御到主动进攻”的演进过程。在克林顿时期,美国互联网政策的主题是强化对网络基础设施的保护,重点在于“全面防御”。在小布什时期,则是网络反恐,侧重于“攻防结合”。而到了奥巴马时期,开始体现出“攻击为主,网络威慑”的特点。(19)特别是在借助社交网络上台的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网络空间相关政策举措:2009年5月,发表了《网络空间政策评估》报告,宣布在白宫设立网络安全办公室;2010年2月,发布《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并于5月合并原网络攻击部队和网络防御部队,创建网络战司令部,高调宣布“将网络攻击视为战争行为”;2011年5月,推出意在攫取网络空间话语霸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7月又发布《网络空间行动战略》,更引入“集体网络防御”的理念以拼凑一个新军事同盟。(20) 美国为确保其在网络空间的“绝对优势”与“行动自由”,在加紧打造网络空间集体防御体系的同时,也越发注重网络武器的研发与实战演练。这不仅会给有关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会给其他国家带来严重的安全威胁。例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之下,伊拉克顶级域名“.iq”的申请和解析工作被终止,导致所有以“.iq”为后缀的网站从互联网上蒸发。2004年,由于卡扎菲政府在顶级域名管理权问题上与美国发生争执,利比亚顶级域名“.ly”随即全面瘫痪,使得利比亚在互联网上“消失”了3天之久。(21)更有甚者,2010年一种名为“震网”(Stuxnet)的蠕虫病毒侵入了伊朗的一个核电站,致使超过五分之一的离心机报废、约3万个网络终端感染。后经《纽约时报》披露,重创伊朗核电站的“震网”病毒正是美国与其盟友以色列联手研发的,并由奥巴马总统亲自下令使用,旨在破坏或延迟德黑兰的核武计划。(22)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震网”事件开启了一个网络战争的新时代,也向世人揭示了确保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建立网络空间合理秩序的紧迫性。“震网”不只震慑了美国的夙敌伊朗,也在中国引起巨大震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1年9月29日即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有关国有大型企业”印发了《关于加强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管理的通知》(亦称“451号文件”)。(23) 综而观之,网络空间安全议题在中美关系整体格局中迅速升温,其所蕴藏的复合潜能或许不亚于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复杂影响。所不同的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出于国际反恐战争的需要对其全球战略予以重新定位,在中美双边关系上更多地表现出合作与交流的一面,而在美国高调宣示“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的新战略布局下,中美双边关系更多地表现出竞争与冲突的一面。大势之下,网络空间同样也需要高度警惕出现“擦枪走火”的安全风险。 二、中美网络竞合与“修昔底德陷阱”风险 2012年8月,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著名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修昔底德陷阱已然凸显于太平洋》的时评文章,直指“中国与美国就是今天的雅典和斯巴达”,“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崭新提法由此产生。(24)抚今追昔,自修昔底德以降,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几已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条“铁律”,一再上演的“修昔底德陷阱”俨然蕴藏着一种颠扑不破的因果循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总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安全困境”,二者之间实力的消长极易诱发彼此战略判断与情感好恶的微妙变化,强烈的恐惧感与不信任感最终可能导致良性互动的竞争关系蜕变成为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并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尽管艾利森将今天的中国与美国直接等同于昔日的雅典与斯巴达,这种“对号入座”的做法不免过于简单粗暴,然而举足轻重的中美关系经不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这种忧患意识,却似乎远未达到人尽皆知、不言自明的地步,在网络空间领域尤其如此。 事实上,这并非危言耸听,也决不是杞人忧天。在波诡云谲的后冷战时代,中美两国面临着更趋复杂多元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在双边互动中更加难以确定对方长期、真实的战略意图。“战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似乎在两国均呈上升的势头,而一旦任由这种观念肆意发酵,就极有可能会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进而诱使中美关系走上一条全面军事对抗的不归路。(25)如上所述,在网络空间这一陆、海、空、天以外的“第五疆域”之中,也已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潜在危险信号。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不仅是现实中美关系在网络空间的映射与再现,还将是一个新型数字领域的竞争、冲突与合作的复合体。”(26)面对全球信息化进程中的机遇与挑战,中美在虚拟世界里的关系状态折射了实体世界中两国长期角力所催生的一种结构性矛盾。 如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追根溯源,“结构性矛盾”这一理念源自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对国际政治体系所作的经典阐释。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从排序原则、单元功能以及权力分配三个层次界定了国际政治结构,认为结构是系统中的一系列约束条件,藉由奖励一些行为、惩罚另一些行为而限制和塑造了行为体的政策抉择。(27)尽管某些行为体或因其整体实力超群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然处于国际体系之中,其同样要受到体系逻辑的规制。英国学派承上启下的代表人物巴里·布赞则指出,随着国际体系中各个单元之间的互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体系确实会变得更大、更紧密,(单元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更强,受到结构性力量的影响也更强。”(28)这是因为,“尽管单元与体系均变得更为强大、更有能力,不过相较而言,体系会变得更具扩张力、更具渗透力,也更具影响力。”“因此,体系结构的作用也愈发强大,左右着单元的发展,并使主导其发展的力量均势由内而外发生转移。”(29)由是观之,所谓结构性矛盾,顾名思义,指的是在特定的国际体系之下,“两国或多国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呈现结构性特征。具体来说,结构性矛盾是指由于历史积怨和现实发展所引起的长期积累且无法短期消除的矛盾,一系列不信任因素会长期、频繁地影响两国或多国关系。”(30)学界最常引证的例子,远者莫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近者则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长期以来,中美关系似乎也陷入了一个发展、停顿、再发展、再停顿的“时好时坏、磕磕碰碰、走走停停”的怪圈。 中国学者对中美结构性矛盾的认知多持谨慎乐观态度,认为崛起的中国与美国霸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最终并不见得会激化为严重对抗甚至升级成惨烈战争。国防大学唐永胜教授认为,当前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指“由于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位置不同及利益需求的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并在一个时期以来主要表现为中国力量上升、利益需求扩展与美国维护其霸权安排的深刻冲突”。具体而言,“中美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三个方面”:首先,美国强化霸权与中国政治影响迅速上升之间的矛盾;其次,美国维护世界经济主导地位与中国拓展发展空间的矛盾;最后,美国追求绝对安全与中国维护日益扩展的安全利益的矛盾。(31)同济大学夏立平教授也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正在崛起的大国,双方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结构性矛盾”。不过,中美“结构性矛盾尽管还存在”,然而“结构性共同利益正在增加”,并且“中美结构性矛盾与中美结构性共同利益在各领域所占的比例是不同的”。“当前中美结构性矛盾在各领域的严重性由大到小的排列顺序是:台湾问题、传统安全问题、人权问题、经济贸易、非传统安全问题。中美结构性共同利益在各领域的重要性由大到小的排列顺序是:经济贸易、非传统安全问题、传统安全问题、人权问题、台湾问题。”(32)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则揭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中国崛起是在美国霸权扩张的历史时期开始并持续的,而美国的霸权地位并没有因中国崛起而受到削弱”。他认为,这一现象本身已经对“美中必然对抗论”构成了有力挑战,坚信“中美关系有望继续维持稳定,并逐渐建立起更为稳定的战略框架”。(33) 而一部分知名美国学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却并不这么乐观,他们将中国视为美国头号的竞争对手,大肆渲染中美结构性矛盾极有可能诱使两国最终兵戎相见。如芝加哥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就认为,中美在国际结构层面上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在21世纪早期,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的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主”,“这种未来的中国威胁最令人头痛的一点是,中国将比20世纪美国遭遇的任何一个潜在霸权国都更为强大、更加危险。”他还“提醒”美国领导人,“中国离有足够能力成为地区霸主的那一刻还很遥远,美国若要扭转这一进程,想办法延缓中国的崛起还为时不晚。”(34)而在名噪一时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两位作者则把结构性矛盾将引发中美对抗的论调推向了高潮,声称中美两国业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敌手,中国对美国在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难以对付的挑战”。正如极为夺人眼球的书名所示,该书作者断言美中两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甚至可能会爆发战争,因而他们反对美国各界有识之士所主张的对华“建设性接触”的既定方针,极力要求从多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35)自苏联解体之后,中美积极联手对付一个共同敌人的局面一去不返,已变身为当今世界唯一霸主的美国,其核心战略是避免出现任何一个新的挑战者。因而,中美结构性矛盾无法调和、两国可能某天因为某个问题而爆发军事对抗,这一看法几乎已成为一个无需证明的定理。联系到冷战结束后的这一大背景,美国最为知名的新生代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江忆恩教授甚至撰文直言,中美关系正处于安全困境之中。(36) 从现实状况来看,网络空间安全在双边军事安全领域中的重要性迅速攀升,这使得中美关系更趋复杂。先不妨考察一下双方的网络综合实力对比。美国率先提出“网络战”、“信息威慑”等概念,最早增设成建制的“网军”,并第一个公开发布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可谓是当之无愧的引领全球信息化浪潮的互联网强国。(37)中国虽然于1994年4月20日才第一次“通过美国Sprint公司连入Internet的64K国际专线开通,实现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如今却也已发展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网民和最大的网络经济市场的互联网大国。(38)尽管中美两国在网络方面的实力并不对称,然而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所言,“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个双边关系比美中关系更能深刻影响未来的国际政治。而在这个双边关系中,没有哪个议题像网络安全一样快速升温,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了种种摩擦。双方对于彼此在网络领域行为的不信任正在增加,而且开始严重影响对彼此长期战略意图的估计。”(39)况且,网络空间已“逐步由信息层面进入国家安全领域”,它的出现更是“带来一种新的军事思想和行动的革命,其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的潜在影响可能比飞机进入战争更加深远”。(40)虚拟世界与生俱来的跨国性以及互联网络的其他固有特性,使很多原本可以通过正常方式建立互信的安全议题变得不再奏效,网络活动在极短的时间内加深了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对彼此意图和实力的怀疑。(41)正因为此,中美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并不只存在于两国关系的诸多传统领域,新兴的网络空间也不例外。 “修昔底德陷阱”的核心特质之一是国际关系中因难以明辨对方意图而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焦虑、愤怒、恐惧、躁动等强烈的不安全感就会随之潜滋暗长,双方你来我往彼此针锋相对,进而陷于相互猜忌的恶性循环,这似乎恰好印证了安全困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对于这种由不确定性引发的紧张关系,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它就像身处同一车厢里的一干陌生人之间的关系状态,每个人都丝毫不敢懈怠地盯着其他人,当其中某个人把手放入口袋的时候,他身旁的其他人也都准备把手摸向自己的左轮手枪,以便能够率先开火。(42)对此,英国学者阿兰·柯林斯在所著《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对彼此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正是导致该地区出现安全困境的关键要素之一。(43)同理,考虑到中美在网络空间中的竞合关系,一个最大的挑战即双方都必须面对彼此在虚拟世界中的真实意图的巨大不确定性,由此造就了网络空间的安全困境。随着竞争、合作的接触面增大,中美在网络空间中仍然面临着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潜在风险,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层面的研判。 首先,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壮大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中美两国在经贸联系方面的互补性逐年走低,相反在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贸易壁垒、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的摩擦日见走高。而中美对网络安全问题的不同认知,更是增加了双方在经贸领域出现摩擦的发生概率与复杂程度,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侵蚀了密切经贸联系在双边关系中所发挥的黏合效用。 其次,鉴于中美之间的一大政治分歧在于网络空间管理政策上的“自由度”问题,美方指责中方限制互联网自由,而中方坚持本国的网络主权不容他国置喙。强调不受主权约束的信息自由流动与强调在信息安全基础上的自由流动,这两种侧重点截然有别的理念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激烈的碰撞。 最后,由于网络与生俱来的隐蔽、快捷以及跨越国境易、追踪溯源难等突出特性,同传统的陆、海、空、天“四维疆域”一样,网络空间这一新兴的“第五疆域”也难以摆脱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魔咒,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乃至网络战争的风险正日益上升。即便有关各方均表示要力避网络空间军事化,但谁也不敢彻底排除这一可能性,故而在网络空间里中美军事安全关系呈现出的竞争性、冲突性以及不确定性更为诡异强烈。 网络空间“修昔底德陷阱”的梦魇,对于中美双方的国家利益、人民福祉的直接威胁以及间接影响均不容低估,也对两国的战略和外交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同一种网络不友好行为而言,究竟是甲方的处心积虑,还是乙方的擦枪走火,抑或是丙方的借刀杀人?一旦出现关键误判,就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极为严重的连锁反应。有鉴于此,在网络空间这一兼具战略利益与战术价值的“新边疆”中,尤须抓紧探索合理路径以有效管控日益凸显的中美结构性矛盾,以期打破“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宿命。 三、中美跨越网络空间“修昔底德陷阱”的路径 能否妥善处理来自网络空间这一新兴疆域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安全威胁,如何积极化解中美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结构性矛盾”,正日益演变为持续影响中美战略互信关系稳定发展的一大新因素。结合中美之间在网络空间里已然呈现的竞合关系情势,笔者主张依照竞争性递减、合作性递增的顺序,沿着以下三个层面的思路去探究中美两国的脱困方略。 首先,在军事安全层面,在中美双方的军事互信取得实质性突破之前,中国仍须不断加强自身的网络力量建设 军事关系向来是国家关系中最敏感也最脆弱的一个环节,一旦两国交恶,最先受到影响的必定是军事关系。长期以来,美国高度关注中国的军力增长,近年来更明里暗里反复表达对中国军费逐年递增的担忧。如在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对网络空间安全与信息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表现出强烈关切。美方认为,中方空间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对美国网络空间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并且事实上已在网络空间展开了针对美国的敌对行为。忧虑过甚则极有可能催化网络空间军备竞赛,最终加速诱发中美网络安全困境的生成,有网络战研究专家甚至引入“凉战”(Cool War)一词来专门描绘这种未来可能出现的中美网络僵持状态。(44)然而越是这样,我们越要清醒地意识到,打铁还须自身硬,中国唯有真正具备令人不敢小觑的网络攻防能力,才有资格去探求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 1991年海湾战争的爆发让中国深受震撼。自这场冷战结束后的第一场大规模高技术局部战争以来,中国从顶层设计与底层建设两个层面,以信息化、网络化为主导目标,加快提升了网络攻防能力。一方面,在顶层设计层面,逐渐形成、确定并宣示网络空间战略。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大体上每两年发表一部国防白皮书,且每部白皮书都具有其鲜明的特点,从中即可看出中国网络空间战略形成和发展的鲜明轨迹。(45)1998年首部国防白皮书面世,尚未出现与信息网络相关的内容,2000年至2008年间的五部国防白皮书则主要强调在世界新军事变革向纵深发展、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军事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要积极依托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加强网络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核心军事能力。(46)2010年国防白皮书,首次提到要密切关注其他大国制定网络空间战略、增强网络作战能力、抢占新的战略制高点的举措,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在“网络空间的安全利益”,并将其纳入新时期中国国防的目标和任务,以求全面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47)2013年4月,最新发布的第八部国防白皮书重申,不断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48)而近期中国高层更是频出组合拳,陆续施展颇具里程碑意义的战略部署。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并在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习近平亲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任副组长,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在保障网络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推动信息化发展上的决心,因而也被舆论视为“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国家战略迈出的重要一步,标志着这个拥有6亿网民的网络大国加速向网络强国挺进”。(49)2014年4月15日,成立不到半年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因此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50)在底层建设层面,中国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网络空间加剧的国际军事竞争,因此将提升网络空间攻防水平作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2010年7月26日,据《环球时报》转引港媒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建成第一个网络战基地(官方称之为信息保障基地),这一新的部队直接由总参谋部领导,它将成为指挥隶属于解放军各个部门的所有互联网战略信息中心的总部,此举被认为是在信息化战争时代中国政府加强军队“数字安全”努力的一部分。(51)2011年5月25日,在中国国防部举行的第二次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在回答香港媒体的提问时宣布解放军已适时组建了专业化的“网络蓝军”,同时表示“网络蓝军”并非黑客部队,而是根据训练的需要为提高部队的网络安全防护水平而设立的。(52)网络空间是高精尖技术的集合体与集散地,相较于一些网络发达国家,中国在网络产业的硬件、软件、人才等多方面尚有后发劣势,网络空间安全还难以摆脱受制于人的尴尬与危险。为此,中国须加大对网络相关研发的投入力度,重点扶持相关优势机构攻关网络空间关键技术,特别是操作系统、终端芯片、超级计算机以及安全防御体系等。 此外,尽管目前中美之间的军事互信建设仍步履维艰,但在提升自身网络行动能力的同时,两军在网络领域的沟通交流同样不可或缺。2012年5月,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访美期间会晤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双方同意就应对互联网安全威胁进行合作,尽管此前不久美方指责中方黑客参与了针对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大规模网络窃密活动。(53)2014年4月7日,来华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则参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这是美方高级官员首次享此待遇,双方均表达了推动两国两军关系向前发展的真诚意愿。(54)在网络空间这一新兴疆域,中美双方还应尽可能多创造一些这样高级别、深层次的交流契机,以增加军事互信、降低战略误判。 其次,在经济贸易层面,要灵活规避中美之间在网络空间中可能形成的安全困境,较为理性可行的莫过于在必要的自我克制之下展开有实质内容的制度性合作 在当今世界上,两个大国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之深实已无须赘言,故而一国在追求本国安全之际必须顾及其他国家的安全,“自己活,也让别人活。”(55)一般而论,相比政治、军事那些比较敏感的领域,对于经济、技术等这些相对不那么敏感的领域共同面临的风险或威胁,各利益攸关方比较容易达成一定的共识,彼此协调形成共同遵守的规则,进而采取立场较为一致的政策措施。正因如此,在网络空间里,“未来中美双方合作可以从不敏感的非军事领域起步,采取多边合作的形式,运用创造性思维开拓新的合作议程,共同构建更稳定的信息空间秩序。”(56)中美有责任同时也有意愿去共同维护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新兴经济增长点,以便不断发掘和发挥经济联系在信息化时代对双边关系的黏合作用,增进双方的国家利益。 事实上,网络空间的异军突起既是一个数字化(digitalization)进程,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化(datafication)进程。(57)数字化将人们生活中的各种影像图文等内容统统转换为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代码,进而转化为可以量化分析的各类数据,这极大地提高了信息处理的效率和传输的速度,使得网络世界的数据呈几何级数暴增。据国外一家互联网机构的估测,“互联网上的数据每年将增长50%,每两年便将翻一番,目前世界上90%以上的数据是最近几年才产生的。”(58)而随着近两年“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的陆续涌现,网络空间日益成长为一个储量惊人且持续增值的数据宝藏。2013年,《外交事务》杂志首次刊载了一篇关于大数据的文章,指出“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对于“大数据的管理极有可能成为国家之间新的角斗场”。(59)信息技术革命今天早已从单纯的科技领域“外溢”到了生产、消费、金融、贸易等人类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世界经济的正常稳定运行打下了重要基础,例如2012年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即已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且继续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60)而技术本身通常是一把“双刃剑”,在便利人类生活的同时,各种计算机病毒肆虐、网络黑客横行,甚至网络恐怖主义势力也渐成气候。这意味着一旦由于某种自然或人为的原因出现世界范围的大面积网络故障或者更为严重的事态,整个国际社会秩序有可能一下子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况,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对网络空间的经济效益与安全风险同样予以越来越高的关注。中美作为世界两大重要的经济体,两国在网络空间的经济安全问题上必然有着无法切割的利益重叠区和结合点,在实际运作中中美也已逐渐形成一些卓有成效的合作机制。仅以共同打击网络犯罪为例。2012年10月,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接到美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投诉,称部分位于中国境内的主机被恶意程序控制,并参与针对美国某银行和大型公司的拒绝服务攻击(DDoS),美方据此请求中国协助处理。中国方面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后,对其提供的75个位于中国境内的IP地址进行了及时处理。(61)诸如此类基于某些具体问题领域的局部合作,对于积累和增进两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的共同利益与合作意愿有着不容低估的积极作用。 当前,电子商务市场发展速度惊人,互联网金融行业也继续保持快速扩张。2013年,在中国商务部监测的3000家重点零售企业中,网络购物销售增长31.9%,网购销售增速比百货店、超市和专业店等实体店分别高出21.6、23.6和24.4个百分点。中国电子商务整体市场规模则达到10.67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33.5%。(62)而英国战略咨询公司欧析企业管理咨询(OC&C)和谷歌的最近一项研究表明,2013年,美国、英国、德国、北欧地区(包括挪威、芬兰、丹麦以及瑞典)、荷兰以及法国的跨境网络贸易总值约为250亿美元。预计到2020年,以美国为首的六大电子商务市场的网络出口总值将增长五倍,达到1300亿美元。(63)在海量、多元的大数据时代,市场规模庞大、增长前景广阔的网络空间,理论上能够、实践上也可以容纳中美两大经济巨人共存共荣,为了两国的根本利益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整体福祉,中美应共同摒弃“零和博弈”思维,携手争创“双赢”局面。 最后,在政治外交层面,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中美要想真正跨越网络空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有必要共同推进网络空间的国际新秩序与全球治理新规则的建构,寻求一个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生长点与安全困境突破口 从中美关系的整体发展态势来看,网络空间问题是当前最有可能对两国关系造成重大冲击的议题之一。如前所述,近年来中美在这一领域中龃龉不断,谷歌事件、“互联网自由”争辩、美国带头热炒所谓“中国黑客威胁论”,尤其是“棱镜门”事件前后双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明争暗斗,网络空间问题已然成为继“3T”(Taiwan、Tiananmen、Trade)问题等长期焦点之外双边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实则反映的是中美之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而能否合理平衡两国在网络空间中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是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大现实考验。中美必须设法破除或降低由对彼此意图之不确定性带来的“战略互疑”,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美好愿景延伸到网络空间并落到实处,强化“战略互信”。 就国家层次而言,中美两国政府都有充足的理由高度关注网络空间安全,这也是双方展开相关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点。从中国方面来看,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4年7月21日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6.3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6.9%。其中,手机网民规模高达5.27亿,手机客户端各类应用App的快速发展则成为2013年以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一大亮点,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64)根据互联网普及率、网民总体规模,中国已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网络大国”。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也首次将网络空间安全与海洋、太空安全并重,提出要从战略高度予以重视。(65)而从美国方面来看,全球互联网运作依赖13台根服务器,其中唯一的主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余12台辅根服务器也有9台在美国,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几乎垄断了域名、IP地址等互联网基础资源的分配权。比如,第二代互联网技术IPv4架构下约43亿个可分配IP地址已于2011年2月分配完毕,此后各国IPv4地址总数基本维持不变。而截至2013年7月30日,美国有15.73亿个,居全球第二位的中国大陆仅有3.30亿个。(66)同样,在被称作“下一代互联网协议”的 IPv6架构下,截至2013年12月底,中国IPv6地址数量为16670块/32,也是位列世界第二位。(67)正因为此,历届美国政府不断提升网络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2013年3月发布的《美国情报界全球安全威胁评估报告》甚至将网络威胁置于美国所面临的全球各类安全威胁之首。(68) 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整体层次而言,任何政府都无力独揽网络空间这一新兴疆域的管控权,目前除了较低程度的国际合作之外,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总体上仍处于一种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的乱局。全球互联网的根服务器均由美国商务部授权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统一管理。ICANN名义上是一个由全球商业、技术及学术专家组成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可委派人员参与政府咨询委员会,但其中关键性的权力如域名控制和否决权仍由美国商务部通过与ICANN的协议加以操控,“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看来, ICANN就是美国攫取网络空间霸权的一个工具。”(69)2001年11月23日,欧洲理事会在布达佩斯通过了首个针对全球网络空间安全的国际公约——《网络犯罪公约》,该公约自通过之日起便向全球所有国家开放签字加入,截至2014年8月,全球共有47个欧洲理事会成员国以及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以色列等国在内的17个非欧洲理事会成员国加入。(70)美国自加入《网络犯罪公约》后即反客为主,以之为蓝本,对外大肆兜售“美版规范”,要求各国签署该公约,让渡部分网络主权以合作打击网络犯罪。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依赖互联网的程度日深,各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网络空间治理关涉一国主权边界与安全利益,包括美国一些盟友在内的部分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均开始呼吁共同分享全球互联网管理权,并建议在联合国框架下设立一个国际组织以取代ICANN。中国也认为,各国都有参与国际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的平等权利,应在现有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多边、透明、权威、公正的国际互联网基础资源分配体系,以促进全球互联网均衡发展。(71)2011年9月12日,中国与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联手在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上提交了一份《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议案,强调“主权国家是有效实施国际信息和网络空间治理的主体”,主张“充分尊重各利益攸关方在信息和网络空间的权利和自由”,呼吁“加强各国的协调和合作打击非法滥用信息技术”。(72)在长期而巨大的国际压力下,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于2014年3月14日发表声明称,美方认识到将ICANN转变为一个“有效的多方参与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求ICANN尽快召集“全球利益攸关者”,提出一个能够获得“广泛国际支持”的移交方案,作为移交全球互联网管理权的第一步。与此同时,声明也特别强调,该移交方案必须遵循互联网开放性原则,美方不会接受任何一个“由政府或政府间机构主导的解决方案”。(73)虽然被迫做出了一些有限的让步,但美国政府仍把持着实质性控制权,并且可以预见即便在移交方案出台之后,美方依然不太可能轻易将其一手操控多年的互联网管理权拱手让人。基于这一判断,中美应秉持务实精神,积极寻求管控分歧、化解困境的新路子,这“不仅依赖于网络主权的相互确认,更在于中美在网络空间的战略互信的建立”。(74)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构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一定离不开中美之间的网络安全共识,而没有中美深度参与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也注定是名不副实的。 略加对照不难看出,对中国而言,化解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的“结构性矛盾”,稳定其竞合关系情势,以上三种路径选择各有侧重而又相辅相成:军事安全路径重在实力,倾向于积极提升国力;经济贸易路径重在秩序,倾向于有效的制度合作;政治外交路径重在建构,倾向于主动的关系重构。每一种路径均有其一定的针对性与合理性。 四、结语 从战略高度着眼,中美两国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是合作伙伴、竞争对手抑或利益攸关者,这一角色定位从根本上制约着双边关系的深化发展。在网络空间这一价值无限化、角逐无序化的新兴疆域里,中美两个大国理当着眼未来、高瞻远瞩,尽最大努力降低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以便在良性的竞合互动中逐步消弭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为缓解乃至摆脱安全困境寻求可能性与突破口。考虑到中美在网络空间中整体的竞合情势,笔者认为双方可以尝试通过“身份的再建构”达成“利益的再界定”:中国尊重和支持美国在网络空间所扮演的主导角色,美国则承认和接纳中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不再视中国为“网络敌手”。而在政策层面,着眼于外交日常运作,中美双方不妨从中美首脑外交、职能机制对话、双边“二轨外交”等层面多管齐下。在首脑外交层面,2013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不打领带”的历史性会晤,之后双方又在圣彼得堡和海牙两次会晤,一致同意共同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75)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双方应该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框架下,通过首脑外交的方式继续公开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更加积极有力地推动在网络空间领域的务实合作,有效管控两国在网络空间的种种分歧。在职能机制对话层面,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迄今已举行五轮,2013年7月网络安全问题被首次纳入“对话框架”,并成为焦点议题之一,中美军事、民事相关部门第一次举行了网络工作组会议,双方同意就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继续加强对话,尽管暂时并未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但类似举措对于防止网络空间问题持续发酵、不断放大乃至对两国关系造成破坏性冲击,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在双边“二轨外交”层面,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从2009年始开展“中美网络安全二轨对话”,截至2014年1月已举行了11次正式会谈,双方官员及知名学者均有参与。(76)2012年12月,双方还进行了合作应对网络攻击的情景模拟演习。诸如这种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灵活对话形式,构成了增进相互理解、减少战略误判、加强公民网络安全观念培育、探讨国际网络空间制度合作的重要途径。总而言之,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美两国仍应继续探索和充分利用各种互动路径去增信释疑,积极寻求双方核心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共同致力于打造数字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此方能最终跨越网络空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注释: ①惠志斌:《中国互联网的法治之路》,《社会观察》,2013年第2期,第31页。 ②“APT1:Exposing One of China's Cyber Espionage Units”,February 2013,http://intelreport.mandiant.com/Mandiant_APT1_Report.pdf. ③李莽:《网络空间中的安全困境》,《亚非纵横》,2013年第3期,第52页。 ④李开盛:《别让军事关系成为中美合作的短板》,《解放日报》,2014年4月7日,第3版。 ⑤“Five Chinese Military Hackers Charged with Cyber Espionage Against U.S.”,The FBI Homepage,May 19,2014,http://www.fbi.gov/news/news_blog/five-chinese-military-hackers-charged-with-cyber-espio-nage-against-u.s. ⑥胡厚崑:《华为公开信》,2011年2月25日,http://pr.huawei.com/cn/news/hw-092878------.htm。 ⑦“Investigative Report on the U.S.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Posed by 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Huawei and ZTE”,A Report by Chairman Mike Rogers and Ranking Member C.A.Dutch Ruppersberger of th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112th Congress,October 8,2012. ⑧“H.R.933:Consolidated and Further Continuing Appropriations Act,2013”,113th Congress,Text as of March 22,2013 (Passed Congress/Enrolled Bill),http://www.gpo.gov/fdsys/pkg/BILLS-113hr933enr/pdf/BILLS-113hr933enr.pdf. ⑨John Arquilla and David Ronfeldt,In Athena's Camp:Preparing for Conflict in the Information Age,Monograph Reports,RAND Corporation,1997,p.483,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880.html. 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2010年6月8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wgk/2010-06/08/content_1622866.htm。 (11)David Drummond,“A New Approach to China”,http://googleblog.blogspot.com/2010/01/new-approach-to-china.html. (12)黄日涵:《谷歌事件与网络外交刍议》,《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第76页。 (13)Hillary Clinton,“Remarks on Internet Freedom”,Washington,DC,January 21,2010,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519.htm. (14)Hillary Clinton,“Internet Rights and Wrongs:Choices & Challenges in a Networked World”,Washington,DC: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February 15,2011,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2/156619.htm. (15)王群:《携手构建和平、安全、公正的信息和网络空间》,纽约,2011年10月20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tytj_611312/zcwj_611316/t869573.shtml。 (16)Zack Whittaker,“Google Admits Patriot Act Requests; Handed over European Data to U.S.Authorities”,ZDNet,August 11,2011,http://www.zdnet.com/blog/igeneration/google-admits-patriot-act-requests-handed-over-european-data-to-u-s-authorities/12191. (17)李开盛:《别让军事关系成为中美合作的短板》。 (18)汪晓风:《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美国研究》,2013年第3期,第18页。 (19)余丽:《美国互联网战略及其对中国政治文化安全的影响》,《国际论坛》,2012年第2期,第8页。 (20)The White House,“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Cyberspace:Prosperity,Security,and Openness in a Net-worked World”,May 2011,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international_strategy_for_cyberapace.pdf; Department of Defense,“Strategy for Operating in Cyberspace”,July 14,2011,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64686. (21)奕文莉:《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分歧与合作路径》,《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7期,第29页。 (22)Davie E.Sanger,“Obama Order Sped Up Wave of Cyberattacks Against Iran”,The New York Times,June 1,2012,http://www.nytimes.com/2012/06/01/world/middleeast/obama-ordered-wave-of-cyberattacks-against-iran.html. (23)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强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管理的通知》,2011年9月29日,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3907/n11368223/14292054.html。 (24)Graham Allison,“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Financial Times,August 21,2012. (25)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No.4,March 2012,pp.1-50. (26)蔡翠红:《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竞争、冲突与合作》,《美国研究》,2012年第3期,第103页。 (27)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Inc.,1979. (28)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00. (29)Ibid.,p.331. (30)张新颖:《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及其转化》,《理论学习》,2009年第8期,第62页。 (31)唐永胜、卢刚:《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化解》,《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6期,第52—60页。 (32)夏立平:《论中美共同利益与结构性矛盾》,《太平洋学报》,2003年第2期,第27—35页。 (33)王缉思:《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外交评论》,2005年第5期,第13—16页。 (34)John J.Mearsh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W & Norton Company,2001,pp.401-402. (35)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Munro,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New York:Alfred A.Knopf,1997. (36)Alastair Iain Johnston,“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 in Sino-US Relations:A Response to Yan Xuetong's Superficial Friendship Theory”,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No.1,2011,pp.5-29. (37)刘伟华:《中美在网络空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研究参考》,2013年第5期,第20页。 (38)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1994年-1996年互联网大事记》,2009年5月26日,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dsj/201206/t20120612_27415.htm。 (39)[美)李侃如、彼得·辛格:《网络安全与美中关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21世纪国防计划”,2012年2月,第vi页,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2/2/23-cybersecurity-china-us-singer-lieberthal/0223_cybersecurity_china_us_lieberthal_singer_pdf_chinese。 (40)郎平:《网络空间安全:一项新的全球议程》,《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1期,第128—141页。 (41)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pp.3-4. (42)Raymond Aron,Peace and War: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and Annette Barker Fox,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6,p.3. (43)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s of Southeast Asia,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0,p.10. (44)John Arquilla,“Cool War:Could the Age of Cyberwarfare Lead Us to a Brighter Future?” Foreign Policy,June 15,2012,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06/15/cool_war. (45)罗铮:《盘点历部国防白皮书》,《解放军报》,2011年4月1日,第5版。 (46)《国防白皮书》,http://www.mod.gov.cn/affair/book.htm。 (47)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中国的国防》,2011年3月31日,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1/Document/883535/883535.htm。 (4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2013年4月16日,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3/Document/1312844/1312844.htm。 (49)《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2014年2月28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info/2014-02/28/c_133148759.htm。 (50)《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014年4月15日,新华网,http://news.xinbuanet.com/polities/2014-04/15/c_1110253910.htm。 (51)《港媒炒作解放军建成网络战司令部》,《环球时报》,2010年7月25日,环球网,http://oversea.huanqiu.com/economy/2010-07/956140.html。 (52)耿雁生:《“网络蓝军”重在防护》,2011年5月26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1-05/26/c_121459780.htm。 (53)“US,Chinese Defense Officials Agree to Work Together on Cybersecurity”,May 8,2012,http://www.infosecurity-magazine.com/view/25654/us-chinese-defense-officials-agree-to-work-together-on-cybersecurity/. (54)《美国国防部长抵京访问》,《解放军报》,2014年4月8日,第2版。 (55)张志刚:《国家间的安全合作与当代中国的安全追求》,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20页。 (56)高望来:《信息时代中美网络与太空关系探析》,《美国研究》,2011年第4期,第62—76页。 (57)Kenneth Neil Cukier and Viktor Mayer-Schoenberger,“The Rise of Big Data:How It's Changing the Way We Think about the World”,Foreign Affairs,Vol.92,No.3,May/June,2013,pp.28-40. (58)张意轩、于洋:《大数据时代的大媒体》,《人民日报》,2013年1月17日,第14版。 (59)Kenneth Neil Cukier and Viktor Mayer-Schoenberger,“The Rise of Big Data:How It's Changing the Way We Think about the World”,p.35. (60)“Ecommerce Sales Topped $1 Trillion for First Time in 2012”,http://www.emarketer.com/Article/Ecommerce-Sales-Topped-1-Trillion-First-Time-2012/1009649. (61)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2012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2013年3月19日,第12—13页,http://www.cert.org.cn/publish/main/46/2013/20130319164944611730684/20130319164944611730684_.html。 (6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编:《互联网发展信息与动态》,2014年1—2月合刊,总第97期,第2页。 (63)同上书,第5页。 (6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年7月,第4页。 (65)《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页。 (66)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互联网发展信息与动态》,2013年7月,第4页,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fzzx/qwfb/201308/t20130826_41331.htm。 (6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年1月,第29页。 (68)U.S.Intelligence Community,“Statement for the Record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March 12,2013,pp.1-3,http://www.intelligence.senate.gov/130312/clapper.pdf. (69)Kenneth Neil Cukier,“Who Will Control the Internet? Washington Battles the World”,Foreign Affairs,Vol.84.No.6,2005,p.7. (70)The Council of Europe,“Convention on Cybercrime (CETS No.185)”,Chart of Signatures and Ratifications,http://conventions.coe.int/Treaty/Commun/ChereheSig.asp? NT=185&CM=8&DF=&CL=ENG. (7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状况》,2010年6月8日,http://www.gov.cn/zwgk/2010-06/08/content_1622866.htm。 (72)王群:《携手构建和平、安全、公正的信息和网络空间》。 (73)NTIA,Office of Public Affairs,“NTIA Announces Intent to Transition Key Internet Domain Name Functions”,March 14,2014,http://www.ntia.doc.gov/press-release/2014/ntia-announces-intent-transition-key-internet-domain-name-functions. (74)蔡翠红:《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竞争、冲突与合作》,第121页。 (75)《习近平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09/c_1110171023.htm#715159-tsina-1-21289-b4627af4aa6de3e8cf9f7d8876a92f2c。 (76)《高级顾问崔立如赴美参加中美二轨对话》,2014年2月18日,http://www.cicir.ac.cn/chinese/newsView.aspx?nid=5751。标签:修昔底德陷阱论文; 修昔底德论文; 军事论文;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网络安全论文; 网络空间安全论文; 中美论文; 中美集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