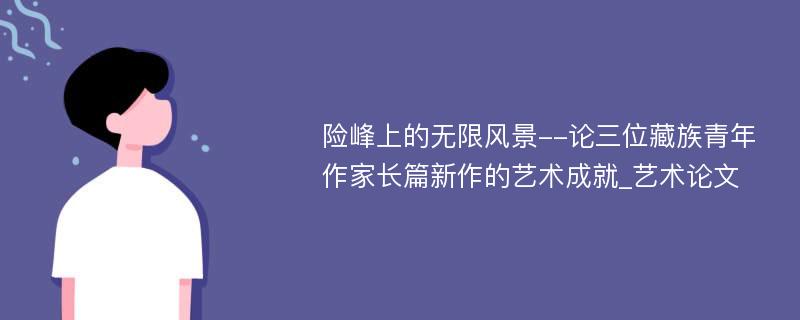
无限风光在险峰——试论三位藏族青年作家长篇新作的艺术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族论文,险峰论文,长篇论文,新作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的案首摆着三位藏族青年作家的三部长篇小说新作,它们是:央珍的《无性别的神》(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梅卓的《太阳部落》(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2月初版)、阿来的《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初版)。前两部作品均于1997年荣获由国家民委、中国作协共同举办的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奖“骏马奖”,似已有定评;阿来的《尘埃落定》的删节本抢先于《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1997年第二辑刊出后,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也被传媒炒得很热,被看作是近年来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有人甚至断言此作“将走向世界”。三部藏族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引起文坛如此强烈的反响,这的确是当今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也是生活在这个共和国里各个民族共同的事业。我们文学事业的繁荣,当然要靠各个兄弟民族的共同努力。生活在青藏高原和川西一带的藏族,是一个古老的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的民族,他们创造过灿烂的民族文化。在读了三位藏族青年作家的三部长篇小说新作后,我惊奇地发现,它们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采,展现独特的文化景观,表现出独特的艺术思维,并都具有较高的艺术质量。可以说,它们是我国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长篇风景线中的奇观。阐释它们,总结他们的经验,对于推动当前长篇小说创作,提高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质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独特的艺术风采
艺术贵在独创。三位藏族青年作家的三部长篇小说新作最可贵之处也在于它们的艺术独创性。这三部作品犹如长在雪山上三朵娇艳的雪莲,它们采撷生活的芬芳,又扎根于藏族这古老民族丰富的文化沃壤,因而又各具独特的艺术风采。
央珍的《无性别的神》被有的论者界定为“一部客观探索西藏心灵历史的小说”(见张趺《神奇的命运》一支,《中国青年报》1995年9月17日),这个评论是准确的。它通过德康家族二小姐央吉卓玛的视角,通过她所看到的帕鲁庄园、贝西庄园、德康庄园等三个西藏贵族庄园生活风貌和拉萨以及外地寺庙生活风貌的描写,通过央吉卓玛从童年丧父、母亲随继父到昌都当官后被寄养于亲戚家过着漂泊的生活,以至后来被送入寺院削发为尼,以及从寺院出来寻找“红汉人”这么一段生活经历的叙述,还有与之相交错的德康家族命运的描述(包括对央吉卓玛生父生母经历的简短补叙),尤其是对央吉卓玛寂寞孤苦而又时时躁动不安的心灵的解剖,勾勒出二十世纪中期西藏的生活风貌,写出西藏心灵历史,也就是写出西藏藏民族的“魂”儿来,让我们撩开西藏神秘的面纱,走近西藏,认识西藏。这既是作者动笔时希冀达到的目的,也是作品客观的审美效应。央珍很懂得以小见大这个写小说的诀窍,也很善于发挥自己生活积累的优势。当代一位著名的小说家这样说过,小说,小说,就是往小里说一说。这话看来好似戏言,其实道出了小说创作的真谛。我们也固然需要一些全景式的作品,但更需要“从小处说一说”的精美之作。因为作为虚构的小说,这种精美的作品,往往更有韵味,也更具审美价值。央珍的《无性别的神》正是这种“从小处说一说”的精美之作。她写的是一个被冷落的西藏贵族小姐的童年到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是德康家族的兴衰,是一个孩子所看到的几个贵族庄园和寺院的生活风貌,但由此折射的则是本世纪中期西藏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并由此深深开掘出西藏的心灵历史,让我们远离西藏对西藏较为陌生的读者走近西藏,认识西藏,并在这种认识中产生一种不可替代的美感。有人说这部作品颇有点《红楼梦》的神韵,如果有的话,我看主要就在以小写大,以一个人的心灵史和一个家族的兴衰折射出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心灵史这一点上。当然,由于央珍生于拉萨,长于拉萨,后来又到内地上过大学,既扎根于西藏民族文化的沃壤,又受到中外文学的熏陶,因此自然有其独特的审美眼光。她对帕鲁、贝西和德康三个庄园的生活风情的描写,精致、传神,具有独到的审美价值。写央吉卓玛在帕鲁庄园见到叔叔的场面和叔叔死后受到的虐待,在贝西庄园受到姑姑的爱护和见到她表哥虐待奴隶的情景,还有在德康庄园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以及在私塾里所受的启蒙教育,这些描写都给人留下深* 的印象。当然,关于央吉卓玛家的贵族生活的描写,关于热振活佛叛乱这个政治背景的描写,关于央吉卓玛进入寺院后看到的寺院生活的描写以及她母亲把她从德康庄园接回拉萨时途经龙布藏绿湖去朝拜这个西藏圣湖这段经历的描写,还有接近结尾时对央吉卓玛等少年寻找“红汉人”时既神奇、猜忌又理解、崇敬的心理描写,可以说是全书中比较精彩的笔墨。这些描写,既表现了这位藏族青年女作家的生活积累,也看到了她不凡的艺术才华。当然,小说中央吉卓玛及其母亲的形象,奶妈的形象,甚至着墨不多的帕鲁庄园主人,央吉的叔叔的形象,都是相当成功的。在小说文体上,《无性别的神》的散文化以及诗意化的叙述在当代长篇小说文体创造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些年来,我把一些善于以小见大,笔墨精美的长篇小说称为长篇中的“婉约派”,诸如上海女作家王安忆的《长恨歌》即是代表作。如果这么说还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央珍的《无性别的神》也是长篇“婉约派”的代表作。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表现生活领域和艺术表现的独特,也在于它文体上的独特和精美。
比起央珍的《无性别的神》来,梅卓的《太阳部落》又有一番艺术风貌。此作写的是青海高原上的伊扎部落与沃赛部落两个部落之间的世仇和恩怨,写生活在这两个藏族部落之中,尤其是生活在伊扎部落之中的一批男女之间的爱情纠葛,写他们的爱与恨。在小说中,那撼动山河、蔚为壮观的天葬仪式,那充满神奇色彩的亚塞仓城堡和城堡里的生活风情,还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例如紫衣黑靴的阿卡奂在黑色的三角石屋前祈求神灵的宗教仪式描写),那惨烈的部落之间的械斗,那错综复杂的爱情纠葛,还有像桑丹卓玛与洛桑达吉在玛冬玛沟里那林子后面一个隐秘的山洞里惊心动魄的幽会和死去活来的性爱,桑丹卓玛的小女儿阿琼与沃赛部落的头人嘎嘎的奇特的爱情和嘎嘎策划的奇特的抢婚仪式,还有那位由于失去伊扎部落老千户继承权而出走浪迹江湖劫富济贫的充满侠义色彩的大侠嘉措,还有作为权力象征的那枚太阳石戒指……这些充满青海高原藏民特有的生活色彩和浓厚传奇色彩的描写是那么吸引人,读后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这么说,浓厚的地方色彩,民族生活色彩和我国古典小说固有的传奇色彩,是《太阳部落》鲜明的艺术特色,也是它独有的艺术风采。小说中对于错综复杂的爱情纠葛的描写,对男女情爱的酣畅淋漓的描写,尤其显得突出。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颇见艺术功力。那个篡夺了伊扎部落千户继承权成为亚塞仓千户城堡新主人的索白,无论是写他篡权以及同沃赛部落争斗中的工于心计和相当凶残,还是写他对妻子耶喜的无奈和对情人桑丹卓玛的缠绵,都把一个藏族头人的形象塑造得颇为丰满立体;那位被迫离开亚塞仓千户城堡漂泊四方行侠的嘉措,虽然笔墨不多,形象也颇为鲜明;至于外柔内刚的千户夫人耶喜,美丽多情的千户情人、嘉措妻子桑丹卓玛,泼辣庸俗的女人尕金,还有雪玛、香萨、阿琼等活泼美丽命运多舛的少女,也都写得颇为鲜活。诸多人物形象的成功创造,尤其是各种类型的藏民形象在作者笔下展示他们多侧面的富于民族性的性格,是《太阳部落》另一重要的艺术成就,也正是在这些艺术形象身上体现了它独特的艺术风采。但是,如果你细心地阅读品味这部作品,你将发现,由于作者过于注意小说故事情节的曲折和离奇,人物关系的复杂与巧合,某些生活场面和地方民族文化的奇特,而对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则注意不够,对于各个人物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开掘不够,于是显得情节过于巧,传奇色彩过于浓,这多少影响到作品的艺术质量。
阿来的《尘埃落定》被定位为一部“展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神秘”的诗化小说。有论者又把它定位为一部“以诗为史”的具有单纯性、传奇性和混沌性等特点的真正的史诗。(参见《尘埃落定》的“内容说明”和洪水发于《读书人报》1998年6月3日四版的文章《以诗为史》一文)我以为,这些看法大致不差。《尘埃落定》讲的是本世纪上半叶川康地区一个藏族土司家族兴衰的故事,也可以说写的是土司制度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瓦解衰亡的历史。小说的故事情节既丰满又单纯,叙述的角度又很独特,作者用麦其土司的二少爷这个“傻子”的视角来叙述麦其土司兴衰以至瓦解的故事,时而第一人称,时而第三人称,把两种叙事人称结合得较好,因而叙述得既从容客观且时有幽默感,同时又有很强的主观抒情色彩。从叙述技巧上来说,这部小说把主观的抒情与客观的叙事结合得较好,也就是把内叙事与外叙事结合得较好。至于情节的安排和提炼,一方面由于作者掌握较多的素材(包括作者的生活感受这种直接的生活体验和来自民间故事的文字资料的间接生活体验),又善于用一种民间故事叙述者的语调讲述故事,因此情节显得丰富曲折,从容多变,且富于传奇色彩;另一方面,作者是位诗人,他又善于以诗为史,把情节提炼得相当单纯而且空灵。我以为,《尘埃落定》之吸引人处,首先在于长篇小说的文体创造方面,它的叙述角度,叙述人称以及叙述语调都很独特,很吸引人,它的情节也提炼得好,很吸引人。再进一步看看《尘埃落定》内在的吸引力。说它写了“土司制度的浪漫与神秘”,说它写了土司制度在本世纪上半叶瓦解和衰亡的历史,都是指的小说主题的基本指向而言。小说的主题是多义的,但就其主题的基本指向而言,主要写的是麦其土司的衰败,写了土司制度的瓦解,而这个过程在小说中主要体现为引进鸦片种植、引进贸易、引进梅毒和“红汉人”的到来等四个阶段,这大概就是土司制度瓦解过程的艺术再现,也是奴隶制度逐渐崩溃,藏族这个古老民族逐步走向现代化过程的艺术再现。这个艺术再现当然具有很独特的认识意义。至于说写出土司制度的神秘,大概指的是那种神秘的宗教色彩下的残酷权力斗争。麦其土司家族中傻子二少爷同他那位聪明孔武的哥哥之间的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看来是在作者轻松带调侃语调的叙述中进行,却是相当残酷的;至于麦其土司同周边十八个土司之间的争权夺利的大大小小的权力斗争,有的甚至酿成规模不等的战争,就更残酷了。例如开卷处写麦其土司同汪波土
司因为麦其土司管辖的某处头人的叛变为索回叛变者和后来为争夺鸦片种子而接连爆发的战争,后来写为粮食问题在南方边界几个土司同麦其土司之间的斗争,尤其为麦其土司同茸贡土司的斗争与联姻,更为典型。这种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也是土司制度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促使它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小说对此做了充分的描写和相当深刻的揭示。小说中运用相当的笔墨写了麦其土司官寨里私生活的浪漫,诸如写老土司在夺取查查头人的妻子央宗后的浪漫行为,写傻子二少爷同侍女桑吉卓玛、塔娜以及后来同茸贡女土司的女儿之间的性爱和情爱,都是相当浪漫的而又是有所节制的。而写行刑人尔依父子在刑场上的行为,则既残酷而又浪漫,写刑场上的行刑写到这个程度,这么有审美价值,这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是很少见的。当然,《尘埃落定》的艺术价值,或者说它的独特的艺术风采也集中表现在它创造了那么多有相当高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上。麦其土司的老土司,傻子二少爷、大少爷、土司的从汉区来的二太太、傻子二少爷的侍女桑吉卓玛,随从索朗泽朗,行刑人小尔依,茸贡土司的女儿,还有从圣城拉萨来的那位格鲁巴新派的僧人翁波意西以及门巴喇嘛、洛嘎活佛等众多的人物形象,不仅是鲜活的,有的甚至有相当的典型意义。说到小说语言,我不仅欣赏它的诗意化,同时也很喜欢其油画的质感。在写麦其土司官寨里里外外的生活画面,写刑场,写傻子二少爷的出巡,尤其是在南方边界的建立贸易等等生活画面,小说的语言都有一种油画的质感。这更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非凡的功力。
上面,我只是对三部藏族青年作家的长篇新作独特艺术风采做了简要的阐释,对它们的艺术成就做了简要的点评。从中可以看到,尽管三部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水平不一,也都还存在一些令人遗憾的不足之处,但是应该说,这三部作品的陆续问世,不仅是藏族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也是我国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不平常的收获。这三部藏族青年作家的长篇处女作,在九十年代文坛以至整个当代文坛占有重要的位置,同时,他们的创作经验也将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
独特的文化景观
三位藏族青年作家的三部长篇小说新作不仅为我们描述了发生在西藏、青海和川西藏区的独具民族风情的动人故事,展示了它们独特的艺术风采,而且展现了一道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开掘了深厚的藏族的民族文化沉积,表现了汉藏文化之间、中外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的可喜的文化现象。
这种独特的文化景观首先表现在地域文化色彩和民族文化色彩亦即不同的藏区民族风情的展现上。《无性别的神》中对帕鲁、贝西和德康三个庄园生活氛围的描绘,对拉萨寺院生活的描绘,都表现出一种活泼的民族风情;《太阳部落》中对天葬仪式的描写,对紫衣黑靴的阿卡奂在黑色三角石屋前祈神仪式的描写,对衮巴寺的转世灵童测定的宗教仪式的描写,对伊扎部落亚塞仓千户城堡里生活氛围的描写,也都表现了一种浓浓的民族风情;《尘埃落定》中的民族风情描写更是用的浓墨色彩,因此也可以说气氛营构得更为浓烈,无论是麦其土司官寨的建筑物和生活氛围,土司刑场上行刑的情状,还是对门巴喇嘛、洛嘎活佛和新教派格鲁巴僧人翁波意西的描写,包括对土司管辖下的领地里种种民族风情的描写,以及他们的爱情与婚姻模式,都是一种民族化了的,充分表现出一种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色彩。反映民族地区生活的作品,可以说都注意到这种民族风情的描写,但过去我们读到的大部分作品,或以猎奇的态度去展示和表现一些奇风异俗,甚至是一些并不具审美意义的带有某种野蛮和落后印记的奇风异俗,写它们仅仅为了猎奇和作为作品的调味品;而有的则是这种奇异风俗的罗列,它们同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并无什么必然的联系。这种民族风情描写,不仅是表层的,也是缺乏审美意义的。我们在这三部藏族青年作家长篇新作中看到的民族风情描写,不仅是有特色的,有审美意义的,而且同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有着必然的联系,成为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作品主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以这些民族风情描写中开掘深厚的民族文化沉积,于是就构成一道独特的民族文化的景观,提高了作品的文化品格。三部作品中,《无性别的神》、《尘埃落定》在这方面达到更高的水平。
在描写不同藏区的民族风情时,三部作品自然都写了一些宗教仪式,写了寺庙和寺庙中的各种各样的神职人员,有的还写了某些残留奴隶制度的颇为残酷的制度和习俗,诸如酷刑和天葬。在这方面,这几部作品大都把它们作为审美对象来写,变丑为美,化腐朽为神奇,赋予宗教活动或残酷的刑罚以审美的意义,使之成为一种有审美价值的文化景观。例如央珍在《无性别的神》中写母亲去德康庄园接她的二女儿央吉卓玛回拉萨,途经后藏著名的龙布藏绿湖,在她们一行朝拜这个西藏圣湖时,那种宗教氛围同艺术气韵就是相互沟通的,可以说二者达到互相渗透、互相交融的程度。这就是善于把宗教活动描写变为具有文化价值的活动,赋予宗教活动描写以审美意义成功的一例。再看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关于酷刑的描写。我很喜欢麦其土司世袭的行刑人老尔依和小尔依这两个人物,作者没有把他们写成通常看到的满脸横肉可怕可僧的刽子手,而是把他们写成忠实于土司的手艺人,同时又把他们的刑场营生写得颇有意思,在看他们行刑时,完全没有血腥感和恐怖感,而是同作者一起去冷静地观照这种作为奴隶制造物的酷刑,欣赏一件艺术品。这大概是作者不是去展示血淋淋的现实,而是用冷静、客观、审美的角度去写酷刑之故。因此,这种酷刑描写,包括行刑人大小尔依形象的艺术创造,也成为一种有审美意义的文化景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把宗教活动或酷刑作为审美对象的描写,比起上述从表层上写生活风情或风俗的部分来,从更深层次上开掘了藏族的民族文化积淀,也具有更高的文化品味。
三位藏族青年作家都是出生、生长在藏区的地道藏族,但他们又都到内地受到同汉族青年一样的教育,受到汉语文学艺术的熏陶,他们在创作中,虽然用藏语进行思维活动,却又都能自由地运用汉族语言文字进行创作。因此,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中原文化即汉族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或者说可以看到汉藏文化的交融。这又是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央珍对《红楼梦》的喜爱和认真揣摩,因此自然可以看到《红楼梦》对其创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其艺术韵致来说,有人把《无性别的神》称之为“西藏的《红楼梦》”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梅卓的身上也许可以看到更明显的汉族文化的影响,她的《太阳部落》,无论是情节的曲折跌宕,还是人物关系某些奇巧的纠葛,抑或是浓厚的传奇色彩,甚至连嘉措这个大侠形象的创造,无不处处表现作者受中国古典小说包括某些武侠小说的影响,因此,在读《太阳部落》时,我们没有通常读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时常有的陌生感和神奇感,在《太阳部落》中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汉藏文化的融合。这是这部小说的长处,也是它的短处。至于阿来,他生活在川西阿坝,那里的藏族同汉族有更多的交往,也可以看到更多的汉族文化的影响,但阿来对汉族文化吸收得更多,也消化得更好,因此在他的《尘埃落定》中,虽然可以看到汉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但没有影响藏族文化为主体的地位,于是,它才更具独特的艺术风采。
更值得注意的是三位藏族青年作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我看来,一些少数民族的青年作家似乎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民族文化以及他们的思维模式似有更多可以同外来文化沟通之处。阿来声称他喜欢美国作家福克纳的作品,受福克纳的影响较大,当然,从他的《尘埃落定》中也可以看到福克纳作品对他创作的影响。但是,从作品的实际来看,无论是就其写土司制度的浪漫与神秘来看,还是从叙述的方式来看,抑或以傻子二少爷形象的塑造来看,似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更大些。这一点,可能是大部分读者所认同的。至于说到央珍,她受到的外来文化影响则主要来自英国文学。读她的《无性别的神》,一方面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西藏贵族社会对印度文化和英国文化的向往,一方面可以明显地看到上一个世纪英国闺秀作家诸如夏绿蒂·勃朗特、埃米莉·勃朗特姊妹和珍·奥斯汀等对她创作的影响,看到《简·爱》、《呼啸山庄》和《傲慢与偏见》等英国闺秀作家的代表作在《无性别的神》中留下的痕迹。诸如作品中所充分描写的德康家二小姐英吉卓玛从童年到少年时代孤独、落寞、苦闷以及躁动不安的心灵,旧玛从童年到少年不长岁月的心路历程,这些描写都可以看到英国闺秀作家的影响。再有作品中那种散文化的笔调,那种抒情性的笔墨,那些精微细致的描写,也都可以看到作者受到英国闺秀作家影响的痕迹。自觉地大胆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主动接受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影响,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提高审美品位、提高文化档次,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三位藏族青年作家,尤其是央珍和阿来在这方面做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独特的艺术思维
艺术思维指的是文学艺术家从事文艺创作时的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有其特殊的规律,包括观察体验生活、概括提炼生活素材,进行艺术构思诸方面的思维活动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要在创作上有所突破,写出好的作品来,除了要有浓厚的生活积累,较开阔的生活视野和艺术视野,较高的思想水平和极强的语言驾驭能力外,很重要的便是突破思维定势,具有崭新的艺术思维。纵观当代文坛,我们可以发现,相当大一部分作家,由于长时间以来受“左”的思潮的毒害,又受到来自政治和艺术的种种条条框框的束缚,艺术思维都趋于封闭化、两极化,他们在观察纷坛复杂的生活现象时,或者在概括提炼丰富的生活素材时,总习惯于把它们纯净化,两极化,好总是绝对的好,坏总是绝对的坏,美与恶,美与丑,好人与坏人也总是两极对立的。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人物总是好坏分明,趋于两极化,类型化,纷纭复杂的生活也不再纷纭复杂,而是简单纯净,一目了然。这种艺术思维上的封闭化,两极化,已成为一种难以打破的定势,它严重制约了作家的艺术生产力,影响到创作艺术质量的提高。大量创作实践经验表明,要提高文学创作的艺术质量,使文学事业取得真正的繁荣,必须打破这种文学创作中的思维定势,以崭新的、多样的、活泼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取代那种封闭的两极的形而上学的艺术思维方式。
我以为,三位藏族青年作家的三部长篇新作之所以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之所以在创作上有所突破,其原因有种种,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艺术思维活动突破当代文坛上原有的思维定势,以一种开放的个性化的思维方式来面对生活和创作。
央珍在谈及她创作《无性别的神》经验体会的一篇创作谈里这样写道:
我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力求阐明西藏的形象既不是有些人单一视为“净土”、“香巴拉”和“梦”,也不是单一的“野蛮之地”,它的形象的确是独特的,这独特就在于文明与野蛮,信仰与亵渎、皈依与反叛、生灵与自然的交织相容;它的美与丑准确地说不在那块土地,而是在生存于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心灵里。(见央珍的《走近西藏》,刊于《文艺报》1996年1月)
从这段话里,我们大体可以弄明白央珍是怎样看待西藏,看待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怎样处理她掌握的生活素材和如何表现她所要表现的生活的,也就是说,可以大体把握她的艺术思维活动的规律。从她已经写出来的作品和她的这一席关于创作的简略的自白看来,她的艺术思维是充分挣脱了那种封闭的两极化的思维定势,以一种开放的、多样的也是辩证的思维方式对待生活和创作的。她的看待西藏,即不单一地视为“净土”、“香巴拉”和“梦”,又不是单一地视为“野蛮之地”,而把文明与野蛮、信仰与亵渎、皈依与反叛、生灵与自然诸多对立的两极交织融合在一起,看到了一个撩开了神秘面纱的平平常常、本本色色的西藏,这是央珍眼里真实的西藏。而她写西藏的美与丑,也不只是写表层的西藏,而是写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的心灵,通过这种心灵的描写,来折射那块土地和那个时代。这样,我们在作品里看到的人物,诸如央吉卓玛和她那位具有贵族太太身份、命运多舛、工于心计的母亲,就都是心灵化了的。央吉卓玛的童年到少年时代,从寄托在外婆家,幼年丧父,母亲再嫁,然后又被送到帕鲁、贝西和德康三个庄园寄养,过着漂泊的生活,一直到接回拉萨后由于她母亲不愿花一笔可观的陪嫁费用又不失面子而把她送进寺庙削发为尼,作者一直注意写她在这些经历中孤独、落寞和躁动的心灵,以至她与伙伴们跑出寺院寻找“红汉人”,也是出于为了摆脱这种孤独的心灵,寻求心灵上的解脱和解放,而不是出于对“真珠玛米”解放了西藏的感激。看得出来,央珍写央吉卓玛寻找“红汉人”以至投奔“红汉人”这段生活经历和内心活动,也不是按照一般政治化的写法,而是遵照她写央吉卓玛性格发展的逻辑,这也表现出她超越一般的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
当然,与央珍相类似,阿来和梅卓的艺术思维活动方式也是打破常规的,独特的。阿来之观察土司制度的“浪漫与神秘”,以及土司制度瓦解的历史,也是用一种非常规的、独特的思维方式,而当他借用一位土司的傻子二少爷的视角来写这一切时,其思维活动的独特性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了。从阿来善于融合藏族的口头文学创作和汉族的文学传统以及外国文学(诸如福克纳的美国南方小说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等等)形成其独特的从容的叙述方式这一点来看,其艺术思维的独特性也就显而易见了。说到梅卓,我们以她的《太阳部落》中对伊扎部落和沃赛部落两个部落之间的争斗,以及伊扎部落内部种种爱与仇的描写来看,也可以看到其艺术思维活动的独特性。
总之,三位藏族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经验再次告诉我们,要提高长篇小说的艺术质量,必须要求作家打破其固有的思维定势,而采用一种崭新的,开放的,多样的,独特的艺术思维活动的方式。
三位藏族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为我们的当代文坛创造了不凡的业绩。这是值得祝贺的。更加可喜的是,他们都还很年轻,三部长篇新作又都是他们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在文学的道路上,他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无限风光在险峰”,祝他们在不断的攀登中能登上艺术的珠穆朗玛!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二十七日
草于北京亚运村寓所
标签:艺术论文; 藏族论文; 尘埃落定论文; 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阿来论文; 太阳部落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央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