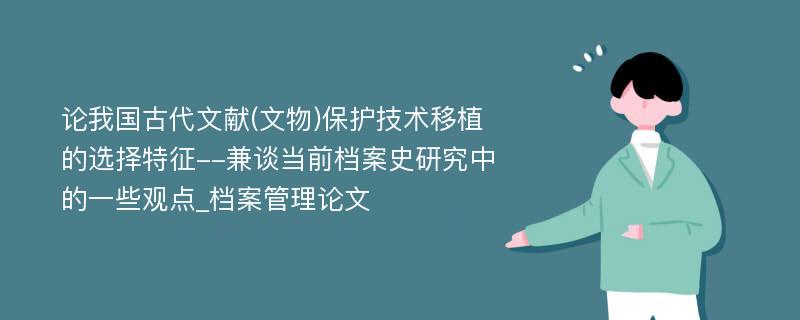
论我国古代文献(文物)保护技术移植的选择性特征——与目前档案事业史研究中的若干观点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选择性论文,文物论文,文献论文,史研究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档案学正在经历转型。学科的结构、内容、重点以至价值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就档案学的某些分支学科来说,这种转型和变化相对来说要小一些。如中国历代档案管理制度嬗变、扬弃与定型、革新等内在发展逻辑,档案管理的制度建设也曾遭遇过如中国科技史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或曰“瓶颈”。那就是:宋代以后,元、明、清三朝从总体上说,档案管理的制度、水平与业务环节的实践探索均未能有所突破、超越,仅仅是某些方面如档案库的设计建造、文件登记等环节有所增损而已,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停滞现象。当然这样说,是需要建立在令人信服的史料及史实基础上的①。然而,在对历史上的档案管理制度及保护思想与实践成就作归纳、总结和评价的时候,我们所依托的史实往往是经不起检验和推敲的。在这门较为传统、且在档案学领域属于较为边缘——有可能还将继续边缘下去的学科也存在“史实重建”的问题。笔者因为长期从事中国档案事业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颇为关注本学科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及学科进展状况,发现在有关探讨我国古代档案管理制度及保护措施的论著中提出的强调档案管理中的“原件”思想及所谓的修复、修裱技术在档案保护技术中的运用则基本上可以说是空穴来风、张冠李戴的结果,是没有依据的。
一、古代档案管理中存在并强调“原件”概念吗
从历史上来看,人们对于文书与档案的性质认识经历了漫长岁月,能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并非轻而易举的过程。因为这涉及档案管理范围的基本问题,同时也直接触及了档案事业史的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笔者以为,中国古代档案事业史从隋唐时期开始,档案工作逐渐脱离文书工作及其他工作的附属母体而独立出来。《隋书》卷七十五《刘炫传》中的记载客观反映了这一历史演变过程。学者刘炫对曾主管过著作、图书典籍典守(秘书监)时任吏部尚书的牛弘有言:“案《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判官减则不济,其故何也?(刘)炫对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虑复治,锻炼若其不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悬也。事繁政弊,职此之由’。(牛)弘又问:‘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舍,其事何由?’(刘)炫对曰:‘齐氏立州数十三府行台,递相统领,文书行下,不过十条,今州三百,其繁一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从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笔者坚信这里所称的“文簿恒虑复治”的对象已经是办理完毕的文书即档案阶段的业务内容了。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的“案”、“文”则既可指文书,也可指称档案材料。《隋书》,唐初魏征等人所撰。隋朝历史极为短暂,只有三十余年,传子不过二代,而档案管理工作的嬗变则绝非一朝一夕的事,因此,隋书中反映的有关史实应当还包含唐朝初年的档案管理的实况。与此同时,历史上最早的专职档案收藏机构——甲库,在唐代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它是古代档案工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不能因为今天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发展趋势而否定在历史上文档区分的内在发展逻辑。文书工作及其后缀部分——档案保管的逐渐繁复是历史的必然。刘炫虽然敏锐地指出了文书工作的细密与繁复、档案工作专职化趋势是国家政治制度(包括国家机构的设置及职能分工)的日趋成熟与完备的产物,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给牛弘提供的对策建议却是逆历史发展潮流的,牛弘当然不会书生意气,只能“善其言而不能用”。
由于档案管理工作的日趋专门化、琐碎细化,一些原先还处于“掌要目而已”阶段的文书档案工作,其业务内容——档案整理工作、立卷工作及提供利用工作等,从隋唐时期开始,比重、地位日渐上升,成为档案管理工作的主要及常规业务内容。在唐代,甲历这种作为官员考核、铨选主要依据的人事档案,其整理工作格外受到重视。
唐宪宗元和八年,吏部侍郎杨于陵起奏:“臣伏以铨选之司,国家重务,根本所系,在于簿书。承前诸色甲敕,缘岁月滋深,文字凋缺,假冒愈滥,难于辨明,因循废阙,为弊恐甚。若据见在卷数,一时修写,计其功直,烦费甚多。窃以大历以前甲敕,岁序稍远,选人甲历,磨勘渐稀;其贞元二十一年以后,敕旨尚新,未至讹谬。纵须论理,请待他时。臣今商量:从大历十年至贞元二十年,都三十年,其间出身及仕宦之人,要检覆者,多在此限之内,且据数修写,冀得精详。今冬选曹,便获深益。其大历十年向前甲敕,请待此一件修毕,续条贯补缉。臣内省庸薄,又忝选司,庶效涓埃,以俾朝典。谨具量补年月,及应须差选官吏,并所给用纸笔杂功费用”②。杨于陵的建议说得很清楚,甲历档案的整理方式是“修写”,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重抄、缮写。整理的范围是时隔上奏当年(813 年)已过去八年至三十八年——775年至805年间的选人甲历,因为“其间出身及仕宦之人”, 即所谓的候选、候补官员均在“此限之内”。而“大历以前”甲敕,由于年龄关系,与这一区间相对应的官员不是去世就是致仕,他们不在这次“磨勘”考虑的范围。“贞元二十一年以后敕旨”,则距离本次“磨勘”时间太近,“敕旨尚新”,则不需要修写。这种整理方法在我们今天看起来,似乎十分原始、简单,但非常有效、实用、经济。当然,前提是从上到下的档案管理者,其观念只注重信息内容的完整与真实,而不强调原件观念。
更进一步说,上述观念及其在这种思想意识指导下的档案整理方法、方式长期有效并被沿用。如,明、清时期的档案管理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整理方式也是录副、缮写。明朝规定,“凡天下臣民实封入递,即于公厅启视,节写副本,然后奏闻”③。这也是档案管理制度的需要。
清代的录副、缮写制度就更为普遍了。如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比原件——朱批奏折还要完整的录副奏折即“月折包”实际上就是档案整理的结果。录副奏折对奏折全文及皇帝的批语一概墨笔照录,各有关人员须“执正、副二本,互相读校”④,以确保录副奏折的内容信息准确无误。乾隆四十年,开始将形成于满族入关前有关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的官方文献记录《满文老档》在时隔近一百五十年以后予以重抄和转抄。重抄本按照原档重新抄写一遍,转抄本则全用新满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对重要档案实行定期修缮制度。从嘉庆十年起,“凡清字、汉字之档,岁久则缮,清字档每届五年,汉字档每届三年,均由军机大臣奏明另缮一份”⑤。有清一代,都把缮写、录副、汇抄作为档案整理与管理的主要方式、方法。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通过谕旨汇抄、题奏汇抄和专题汇抄等途径形成的数万册各类档册便是这种整理与管理方式的直接的成果。习惯上,文书办理完毕归档后,原件不称档案,而曰文案、文卷、案件等,只有那些经过汇抄以后的二次文献才被命名为“上谕档”、“寄信档”、“朱批档”、“现月档”、“纶音档”、“丝纶簿”(这里的“簿”即档)、“洋务档”、“西藏档”、“俄罗斯档”等,冠以“档案”字样。隐藏在这种名称背后的观念与预设前提是,汇抄的过程就是档案整理与管理的过程。由此可见,我们今天在档案管理中十分注重的档案原件意识,即突出强调档案真实性(是否原件)与档案内容真实性相统一的思想意识,在古人那里还是模糊的、不自觉的。
这种观念还直接影响到了近代。北洋政府时期,外交部于1913年8 月制定并颁布施行的《保存文件规则》第十条称:“凡各厅司经办案件于办结时,即由各主管员删繁,摘要编成专档”;第三十条又说:“调取文件,应先就档案取阅,如档案缺漏或有疑义,再调原卷”⑥。对文件、档案内在含义的理解明显带有清代档案管理方式的痕迹,把我们今天所指称“档案”理解为经过编辑而成的二次文献(清代文献中常见的“记档”一词便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即我们今天所称的档案信息)或目录类材料,如清代档案中著名的“随手登记档”。
二、古代书画修裱、修复技术运用子古代档案保护说质疑
先秦及秦汉时期,由于图书、典籍与档案的分野尚不明确,很难说是图书典籍的装帧技术移植到了文书(档案)立卷中,还是文书(档案)的立卷技术被移植到了典籍装帧行业。可以这样说,装帧技术不管是在古代的图书装帧领域,还是在古代文书(档案)立卷工作中,是一项通约的技术,彼此可以移植。但是修复与修裱技术,从来只适用于古代珍稀图书和价值连城的书画作品,即文物,没有任何材料证明在档案保护领域采用了这种传统技艺——修裱、修复技术,或者说,将修复、修裱技术被移植到档案保护技术中来。
原因不外乎主客观两方面。
从客观方面说,前期作为政务工作的直接工具而日后成为政务工作间接参考材料的档案信息,数量极为浩大,尤其是隋唐以后,纸张作为公文载体及制作材料取代了简牍,文件数量更是以几何级数暴涨。举一例子,可能有些极端但绝对真实。据《文昌杂录》卷二记载,宋元丰官制初行时,尚书省六部(类似于今天的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诸司在两个月内,收进了十二万三千五百余份文件。这还仅仅是中央政府若干职能部门两个月的收文量,不包括这些部门的发文,更不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自身在运行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按照如此的速度,一年内形成的文件及随后转化为档案的数量就将以亿计。这些文件,内容记录的无非是中央与地方、官府与官府之间的上传与下达、交流与沟通、布置与贯彻、呈报与准否及统计与决策、人事安排与科举考试等方面的公务活动信息,其本身的价值确实很难与出自于名人、名家或经历了历史上无数次的战乱、灾祸劫难与洗礼的书画及珍贵典籍相比,其对社会的稀缺性程度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学界还普遍认为,不管是图书典籍还是公务文件办理完毕保存在档案收藏机构的转化物,其数量,宋代要比唐代多得多。就图书典籍而言,《宋史·艺文志》根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共著录国家藏书九千八百一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约为唐代国家藏书的两倍,其中大部分是宋人著作。翻开任何一部古籍目录,都不难发现,无论经史子集,还是野史小说,一至宋代就陡然增多。但是,这种增长速度还远远抵不上公务文书或档案材料的增长速度。令人遗憾的是,明清以前历史上数以亿计、几十亿计的纸质公文、档案在今天却几乎没有任何遗存,以致我们今天的档案机构把偶尔存留残余都视作吉光片羽、镇馆之宝。而宋、元、明朝保存下来的图书典籍从绝对数量来说还是相当可观的。
从主观方面来说,人们对于公文、档案资料的价值认识和理解主要集中在公务、政务及皇家事务的参考利用上,即今天档案管理学中所称的档案第一价值,虽然不能说古人没有意识到档案的史料价值或其他价值,但是两者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是有分别及主次的。公文、档案保存时间越长,第一价值越发降低,档案的整体价值与保存档案的积极性也随之下降。有史为证。清末,宣统皇帝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要求查阅内阁大库所藏清初摄政典礼旧档,因检无所获,便轻易认定档案无用,奏请焚毁,并获批准。但是,内阁大库所属两库之一的书籍表章库(又称实录库)所藏的四部图书却不在被焚之列,决定由学部图书馆接收。笔者以为,这一事件透露出了两层含义:一方面,这批公文、档案由于保存时间较长,第一价值(政务利用)已基本丧失殆尽,因此内阁大库所藏档案整体价值有限;另一方面,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书籍的价值与使用价值要高于档案。这也是实情。就一般普通人来说,对图书典籍的需求肯定要比档案的需求大得多,也迫切得多。即使在今天还是这样。
文献(文物)保护技术移植的选择性特征在文书(档案)立卷的形式与古代图书典籍的装帧形式之间表现得十分明显。从现有的文献史料与考古资料来看,秦汉时期至隋唐时期,文书(档案)立卷形式与典籍的装帧形式应该是同步的。笔者曾经撰文讨论过这一问题⑦。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即白色的丝织品——笔者注)。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帛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⑧。实际上,简策收藏时也需卷藏。作为文书(档案)和图书典籍的计量单位和名称都是“卷”,它们都得名于立卷或装帧形式。
本来,档案、文献、典籍同源,有学者甚至认为档案是最早文献形态⑨。我们如今尽管已无从考证出到底是文书(档案)立卷在先,还是典籍装帧形式在先。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共同经历了简策、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三个阶段。
在唐代,图书典籍与公务文书立卷形式仍然是以卷轴装为主,然而至唐中后期,两者的发展轨迹却产生了落差。图书典籍的下一个装帧形式是经折装,而文书立卷的形式并没有相应地同步跟进,而是继续停留于卷轴装阶段。经折装,也称“折子装”,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唐代是佛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鼎盛时期。数以千万计的僧尼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佛教典籍使用之不便可想而知。因为任何一种卷轴,卷久了,都会发生卷舒的困难。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向中间卷起,从而影响阅读。由此,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中肇始,出现了所谓的经折装。元人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但是,经折装也并非尽善尽美,“久而折断,复为簿帙”,于是又出现了旋风装。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是古代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这是一种既未突破卷轴装形制又能达到方便翻检目的的装帧形式。它的出现,又与唐代诗歌、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密切相关。到宋代,为适应印制书籍时一版一页的特点,又出现了蝴蝶装的装订形式。在宋元两代,蝴蝶装也流行了将近四百年。但蝴蝶装与旋风装一样,装帧时书脊均用浆糊粘连,这种书籍作为藏书可以,若是经常翻阅,则容易脱落和散乱。针对二者的不足,装帧形式中又出现了一种既便于翻检又制作坚固的更新形式——包背装。包背装大约起源于南宋,经历元明,直到清末,也通行了数百年。特别是明清时期,官府藏书,几乎全是包背装。当然,古籍中最普遍的装帧形式是线装。在如此众多的典籍装帧形式中,卷轴装以后的其他装帧形式被档案管理与保护环节所借鉴或移植的却相当有限。
有资料显示,宋代的户籍档案还在沿用连粘形式,即卷轴装。每年各户用来登记户口增减的户籍之一——形势版簿要求“县每岁具账四本,壹本留县架阁,三本连粘保明,限二月十五日以前到州;州验实毕,具账连粘,管下具账三本,壹本留本州架阁,贰本限三月终到转运司;本司验实毕,具都帐贰本,连粘州具账,壹本留本司架阁;一本限六月终到尚书户部”⑩。这意味着宋代的文书立卷仍然取卷轴装的形式。除此之外,只有线装在明清时期,某些较为特殊的簿籍类文档如户籍档案(黄册、玉牒——一种特殊的户籍)、地籍资料(鱼鳞图册)与汇编类文档(如上文提及的汇抄后形成的档册)等中使用。那么,为什么隋唐以后,文书、档案的立卷形式没有与典籍的装帧形式一样与时俱进呢?原因也很简单。作为官府政务运作的副产品,文书档案的利用频率与广度远远达不到书籍文献的使用频率及普及性。由此,以方便阅读为旨归(当然也不排除部分收藏、欣赏甚至把玩的目的)的装帧形式的转换,在档案管理领域自然也没有必要如此频繁。
而作为图书典籍装帧形式之一的经折装却在明清时期的折本类文书(如题本、奏折等)制作中被借鉴。但需要说明的是,折本类文书移植经折装,是指单份文书,并非文书立卷的需要。所以从功能上说,更多是出于装潢、美观方面的考虑。
笔者认为,任何制度、技术移植或革新要受相应历史时期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情乃至社会习俗、宗教等方面的制约。政治制度及其技术的移植与革新可能更多地受制于国情、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因素,经济制度及技术的移植则可能会受到原有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阻碍。但有些制度及技术的移植则纯粹是经济及社会物质条件所限。书画修复、修裱技术不可能运用于古代档案保护技术领域就是这种情况。所谓古代档案保护中的修复、修裱思想及运用完全是今人恣意的想象,是以今律古思想的产物,是我们对前人思想观念与做法不能做到“同情之理解”的结果。古代的档案保护工作绝对不会这样做。那样做,既不经济,也无现实可能。如上文提及的数以千万计的官府文书要借助于修复、修裱技术来实现档案保护的目的,是不可想象的。任何技术、制度的移植或借鉴都是有选择性的。古代是如此,今天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那么,古人对于档案保护的目的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的呢?我们说,古代档案保护的意识及有效途径则主要集中于档案库的建筑及防火、载体材料的选择上,即从源头上把握、保证档案信息内容的安全性。当然在可能的条件下也会考虑防潮、防尘及防鼠的要求。如著名的汉石渠阁、元嘉兴路总管府架阁库、明后湖黄册库及皇史宬等古代档案库在建筑规划和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了档案保护的特殊要求。
事实上,原件概念与修复、修裱技术二者存在显而易见的关联性,有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只有在存有并强调“原件”概念或意识及足够的经济物质(人力、物力)条件下,才有可能考虑对文件进行修复、修裱。若档案管理中不强调原件概念,仅注重档案信息内容的真实可靠性,档案保护的手段则通过“修写”——重抄、再录一份或数份就足以适应这种需求,无须移植修复、修裱技术。
注释:
① 笔者准备另撰文讨论。
② 《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三杨于陵《请修写铨选簿书奏》。
③ 《明史》卷七十二《职官二》。
④ 梁章钜:《枢垣纪略》卷二十二。
⑤ 《光绪会典》卷三《办理军机处》。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时期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资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7年7月版。
⑦ 参见拙著《谈谈古代的文书立卷及其案卷标题拟制》, 载《档案工作》1990年第5期。
⑧ 章学诚:《文史通义·篇卷》,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
⑨ 韩宝华、刘耿生:《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4月版。
⑩ 《庆元条法事类》卷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