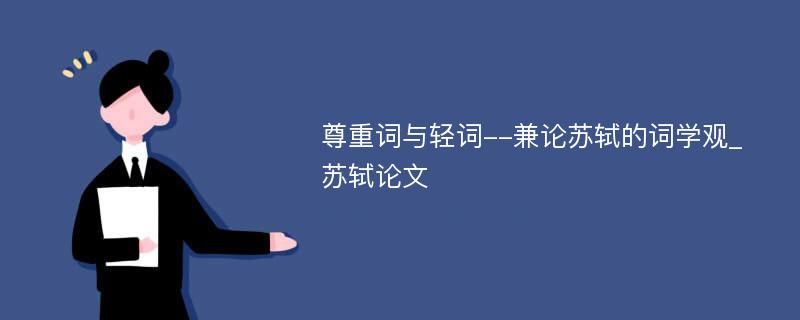
试论尊词与轻词——兼评苏轼词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轼论文,试论论文,词学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论者认为,传统词家和词论家是轻视词体的,“以诗为词”及鼓吹“以诗为词”的人们才是尊重词体的代表。
原因是,前者严分诗词畛域,把词局限在以清切婉丽之辞,写缠绵绮靡之情。后者主张多方打破诗词界限,把词当成“诗的一种”(胡适《词选》语)。词既然是诗,其地位不用说,自然提到与诗同等的高度了。
也许就是这样,人们历来把“以诗为词”的开创人物苏轼看作尊重词体、提高词的地位的第一人。近人陈洵《海绡说词》云:“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
这一观点影响甚巨,龙榆生先生《东坡乐府综论》亦谓:“(坡)于词体拓展至极端博大时,进而为内容上之革新与充实,至不惜牺牲曲律,恣其心意之所欲言,词体至此始尊。”陈迩冬《宋词纵谈》乃云:“词至苏轼,词格始高,词境始大,词体始尊。”
然而对这一定谳笔者有不同看法,不揣拙陋,聊作申说如下。
一、尊词及尊词派辨
何谓尊词?怎样才能够、才算是提高词的地位,使词取得与诗平等的座次?是以诗为词,诗词合流吗?恰恰相反,是严分诗词畛域,恪守诗词之别。
因为,所谓尊体,只能是也必须是致力于建立并严格遵守和尊重一种文体所独具的、与其他文体不同的诸种特性。只有当这些特性被建立起来并得到切实的奉行,这种文体才能像其他文体一样成为一种独立的、真正够格的文体,并以这种独立文体的身份与其他文体比肩抗行。只有这时,这种文体才真正称得上取得了与他种文体完全平等的地位。
而“花间”、“南唐”为代表的当行本色派词人正是这样做的。
我们知道,词在兴起之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与诗的区别是不明显的。除了合乐,在题材上、风格上、表现方式上,新起的词与诗之间多有混融,无严格区分。这对于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词来说,只能是其尚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是一种文体由不成熟向成熟发展必然会有的成长过程。是到了晚唐五代,到了“花间”、“南唐”诸词人手里,才使词开始具有了自己较全面的文体特性,就像诗、文一样,有属于自己擅长的表现方式、创作手法和风味情调。所以我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尊重词体的人。是他们,才从根本上将词提高到了与诗文同等的地位──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
也许人们要问,这些当行本色派作家,他们的创作背景是“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花间集序》),他们的创作意图是“聊佐清欢”(欧阳修《采桑子·念经》),或“期以自娱”(晏几道《小山词跋》),他们的创作内容是“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花间集序》)。这些难道不是他们轻视词体,视之为小道的表现吗?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是一个桎梏人性的社会,封建统治阶级一切有形的规矩和无形的观念都在戕害人们心灵的自由。其结果造成的是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双重人格或曰人格分裂。这种人格分裂的现象,在封建士大夫阶层表现得尤其突出。因为知识分子最具有丰富的锐感深情,他们本有无限的情思需要倾吐,太多的心曲需要发抒。在这一点上,无疑文学家又是知识分子中的突出代表。因而,我们就看到了整个文学史上文学家人格的严重分裂。他们摄于“雕虫小技”、“违道伐性”的封建卫道观念,表面上堂皇地高唱“余事作诗人”,做出夷然不屑的样子,实际上又在那儿“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李谔《上隋文帝革文华书》语)。在“载道”、“贯道”、“明道”老调的掩护下,人们写出了多少情文并茂的好作品。
到了理学思想逐渐形成,道学风气日益浓厚的宋代,人格分裂的现象有增无减。文学家们越是表面上不得不循规蹈矩,道貌岸然,越是需要有其他渠道来渲泻自己压抑心底的情绪之流。当此时,词正成为了解决这一精神需要的最好工具。因而,他们自己口头上也许在贬低、淡化自己的词作,那不过是在为自己可能遭到非议而预设遁词。实际上,词在自身的文体特性得以建立起来的晚唐五代,成为了文学家们最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
郑振铎先生颇带抒情意味的一段叙述是很漂亮的。他说:
他们的不能诉之于诗古文的情绪,他们的不能抛却了的幽怀愁绪,他们的不欲流露而又压抑不住的恋感情丝,总之,即他们的一切心情,凡不能写在诗古文辞之上者,无不一泄之于词。所以词在当时,是文人学士所最喜爱的一种文体。他们在闲居时唱着,在临登山水时吟着,他们在絮语密话时微讴着,在偎香倚玉时细诵着,他们在欢宴迎宾时歌着,在临歧告别时也唱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35章)
就算歌舞酒宴、庆寿迎宾不免于应酬无聊之作吧,当他们将自己对心爱人的恋感情丝、与亲朋好友的依依深情,和文学家敏感的心灵所富有的对人生、对世界的种种幽怀愁绪……一一托付给词这一文体时,怎能说不是最喜爱、最尊重词,反而是轻视词,以词为“小道”的表现呢?
何况本色当行派词家们也不是只能写些题材歌舞欢宴、恋情别绪,风格缠绵悱恻、婉约绮丽的作品。严守诗词畛域,保持词体特性,不意味着词的创作天地一定狭小。词体踏上的这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是既宽且长的。
在这条道路上,词最初是以歌筵酒席间的歌辞身份起步的,随即便以表现爱恋别绪等心灵情绪显示出自身的美学价值。从温庭筠开始,词逐渐融进了作者自己的性情品格、襟抱涵养。南唐时期,李煜使词开始超出一己之私情,向现实社会投去了关注的一瞥。入宋以后,柳永为词带进一股浓厚的生活气息,秦观、李清照、周邦彦、姜夔、王沂孙、张炎,并将家国身世寓于词中,哀怨、感慨、忠爱、愤激、忧生念乱之情,无不于词中发之。在风格上更是不同如面。温词“深美闳约”(张惠言《词选叙》),柳词“曲折委婉”宋翔凤《乐府余论》),秦词“淡雅清丽”(张炎《词源》卷下),周词“富艳精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0),姜词“清刚疏宕”(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所有这些发展变化,并不妨碍其为出色的本色当行之作。因为它们都遵循了一个共同的前提:诗词有别。它们每一次新的变化,都为词体带进一些新的东西,这些东西里甚至不排除有某些诗法、文法、但其变化的目的不是为了打破诗词之间的界限,而是为了丰富和改进词体自身,使之不断提高与完善,这就是与“以诗为词”者的根本区别所在。
举例来说,作为当行本色派词人,姜夔是反对苏辛派词人的,但他对同一派中的前辈,如温、韦、柳、周的华艳软媚亦感不满。因而大胆取过江西派诗桀傲瘦硬的笔法入词,试图以之纠其偏失。他的落脚点是在以严格的音律效果表达一种细美幽约、要眇凄迷的情思,这体现词体本色当行的基调没有变。所以,虽然人们并非觉察不到他“以诗法入词”(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的特点,却从未有人将他视作“以诗为词”者流,反而公认他以“健笔写柔情”的特殊风貌,成为当行本色词派的一枝秀葩。
总之,当行本色派作家们,严守诗词之辨,注重词体的特质的独立性,决不如通常所认为的是轻视词体和以词为“小道”,而是尊重词,提高词的地位,使之不沦没于诗,作为一种独立文体与诗分庭抗礼的表现。清人张祥龄《词论》的这段话:
词,诗家之贼。差以毫厘,失之千里……非谓诗之道大,词之道小,体格然也。
很能说明这一点。他们视词为芳洁之体,无限喜爱,将自己平素隐藏于心底的美好情愫,寓之于词而发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毕生专力于作词,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美好篇章。他们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用自己全部的热情和智慧去发展词、改造词,为当行本色词的锦簇花团添加上属于自己的一分新颜色。他们,才是真正的尊词者。
二 轻词与轻词派辨
真正轻视词,从意识深处视词为“小道”的人当然是有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以诗为词”以及鼓吹“以诗为词”的人们。
这话并非有意立异,而是有事实依据在。我以为,“以诗为词”和鼓吹“以诗为词”者之所以要“以诗为词”和鼓吹“以诗为词”,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词体轻贱,诗体高贵,所以拿较词体为尊为贵的诗体来改造词,替代词。他们轻视、反对前人经过多少年辛勤摸索建立起来的为词体独有的特性,意欲使词的风格面貌回到以前与诗歌混淆不清的状态。而轻视一种文体的特性,取消一种文体的独立发展道路,实质上不就是轻视这一文体本身?
就“以诗为词”和鼓吹“以诗为词”者的言论观点来看,同样清晰地暴露出他们轻视词体的潜在意识,正可与他们“以诗为词”的实际行动相互验证。
不是说“词体之尊,自东坡始”吗?就是这位使词体始尊的词人,对当时著名词家张先有这样一段评论:“张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技耳。”“而世俗但称其歌词……皆所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欤?”(《题张子野诗集后》)
张先的词在当时极负盛名,深为人们喜爱,甚至人们径以张三中(谓其词有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或张三影(其词有“云破月来花弄影”、“帘压卷花影”、“坠轻絮无影”之句)呼之。而东坡却以一句“未见好德如好色”的孔训扫倒众人。显然这不是在一般地评其诗词水平之高下,甚至也不仅是一个为文体分等、尊诗贬词的问题。“词乃诗之余”,一如“诗乃文之余”、“文乃道德之余”的常弹老调,反映出的实在是传统的重道轻艺的观念。
魏泰《东轩笔录》记录了被公认为“以诗为词”另一代表的王安石的一段话:“王荆公初为参政,闲日看晏元献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从这与苏轼若合符契的话语中,不难看出这些“以诗为词”者所具有的轻视词体的真实心态。
与此完全相同的,是那些竭力鼓吹和支持“以诗为词”的后世评论家。不是说他们热情地肯定苏轼“以诗为词”对于词体的革新,表现了进步的倾向吗?可就是在那几段最爱为人们引及的文字中,王灼分明地写道:“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碧鸡漫志》卷二)胡寅分明地写道:“词曲者,古乐府之未造也,古乐府者,诗之傍行也……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向芗林酒边集后序》)王若虚也分明地写道:“公(东坡)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与流俗争胜哉!”(《滹南诗话》卷中)这些评论苏轼的话语,与苏轼对张先的评论,何其相似!他们原本的用意,无一例外地是在颂扬苏轼,却正揭示出苏轼“游戏”为词,以词为“余事”,轻视词体的事实,同时也暴露出他们自己对词体所持有的相同的态度。
正是为了维护词体之尊,陈师道才及时指出苏轼“以诗为词”,“虽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的方向性偏差,晁补之、张耒等弟子以及当时的普遍舆论(“世语”)也以“词如诗”三字对这种实际上危害词体地位的作法进行了规讽。(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38、42)随后,李清照进一步正面打出“别是一家”的主张,公开强调词体的独立地位。词作家们则在创作实践中以实际行动拨乱反正。
确如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所指出:“东坡词在当时鲜与同调。”苏轼的同时以及随后,哪怕与之私交甚洽或对之颇为敬重的人继武“以诗为词”的也不多。苏门四学士中,秦观最有词名,但其所遵循的,仍然是“花间”、“南唐”一派的当行本色,而又加以发展;黄庭坚虽然人称“学东坡,韵致得七、八”(《碧鸡漫志》卷二),但他主要是以生字俚语入词,格调与苏轼不同。并且同时他又大量造作婉约词,以至被法秀道人称为“以笔墨诲淫”(《扪虱新语》,今本无,据《词林纪事》卷六引),连竭力反对“以诗为词”,的陈师道也将他与秦观同观,谓“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耳”(《后山诗话》。张耒存词不多,也是婉约一派。晁补之词风确有似东坡处,但在理论上却是主张本色当行的,不仅微讽东坡“词如诗”,也曾批评黄庭坚的一些词“不是当行家语,是著腔子唱好诗”(见《能改斋漫录》卷16)。后来词家中,“以诗为词”的嗣响更杳。北宋末年的贺铸、周邦彦以及李清照诸大家都是走的与苏轼迥然不同的道路,此乃为众所共知者。
对于这种维护词体之尊的努力,人们并非没有注意到。可他们却将之归结于传统保守势力的强大,看成是词的发展与提高的阻力。因之,其中许多作家受到长期的贬抑、批判。如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都是如此。秦观被指斥为充满了感伤、没落的情调,周邦彦和李清照则被认为形式主义词家和词论家。而在我看来,秦、李诸人,尤其是秦观本人紧随苏轼之侧,却毅然重新回到传统当行本色词派的道路,这不仅对于苏轼混同诗词界限的倾向是一种无言的反拨,同时也具有了对词的固有特性重新加以认定的意义。至于李清照的《论词》,现在对其重新认识并给予新的评价的已越来越多,那种失之简单、偏颇的“落后”、“保守”、“僵化”论已开始成为研究史上的陈迹。这样,使人不解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仍然要对“以诗为词”一味地大唱赞歌呢?
这里不禁联想起词史上号称“尊词”的“浙西词派”。康熙年间朱彝尊创立的浙西词派,不满西蜀、南唐的词风,以为其“言情者或失之俚”,同时也不满苏、辛一派的词风,认为其“使事者或失之伉”(并见汪森《词综序》),因而除以姜、张的所谓“醇雅”拯之而外,就是力图从理论上抬高词的地位。而其使用的主要方法,就是想方设法为词攀上汉乐府、《诗经》,乃至比《诗经》还遥远的古歌谣这几门亲戚。汪森这篇典型地代表着浙派主张的《词综序》开篇便说:“自有诗而长短句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
这种理论后来广为人们接受。乾隆时的李调元,在所著《雨村词话·序》中不点名地搬引了这段话,并从而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故曰词非诗之余,乃诗之源也。”光绪年间的文延式也在《云起轩词钞·序》中云:“词者,远继《风》《骚》,近沿乐府,岂小道欤?”大有欲使词不仅与《诗》、《骚》、乐府平起平坐,还要高出其上而后快的味道。
然而,他们不是理直气壮地肯定词之为体所独具的诸种特性,不愿堂而皇之地正面颂扬词体创作取得的独特成就,而是汲汲于为词争得一个古老的,在他们看来因而也是高贵的正统的出身,似乎这样就使词体的地位提高了。这种尊词方式本身,适足以暴露出尊词者所具有的绝非尊词而是轻词的潜意识。更不用说,他们仅仅从外部形式着眼,以长短句作为分辨诗词的标志,从理论上来讲也是大有悖于词的起源、发生、发展的实际,完全站不住脚的。
继“浙西词派”之后,还有一个同样以“尊词”为己任的“常州词派”。“常州词派”反对历代人们的轻视词体,“小其文而忽其义”(金应珪《词选后序》)的做法,同时也不满“浙西词派”尊词而无力、作词而无物的毛病,提出了影响卓著的“兴寄”理论,企图以此来提高词的地位。
词派创始人、嘉庆间的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认为,前代词家之作,表面虽多缘情绮靡,有伤“鄙俗”,实则“义有幽隐”,兴寄深微,“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因而不得以“小道”视之。他又在《词选》中具体演示了自己对词中寄托之义的“指发”。
欧阳修《蝶恋花》词:“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张氏注云(见卷一):
“庭院深深”,闺中既已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路”,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琦)、范(仲淹)作乎?这样,“风雅之士”就不再会“惩于”这首词的“鄙俗之音”,而能将之“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了。这样,“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词“则近之矣”。这样,词的地位也就自然与《诗》、《骚》同而等之了。所以,“常州派”的后起者谭献欢喜赞叹道:“倚声之学,由二张(张惠言及其弟张琦)而始尊耳。”(《复堂词话》)近人夏敬观《惠风词话诠评》亦云:“张皋文(惠言)、周止庵(济)辈尊体之说出,词体乃大。”
十分明显,“常州词派”将经学家“比兴解诗”的方法移植于解词。本来“当行”“本色”一派的词家确实自有以词发抒家国身世之感的传统,并且为了符合词体独具的要缈细美,往往将之打入艳情,化激昂为幽咽,像《离骚》那样,托寓于风花雪月,残阳烟柳。尤其在身处朝代更迭之时的周、张、王等人的词中,题外之旨尤为显著。因而,“常州派”的“寄托”说并非毫无道理。
但是,问题出在,它不顾作品本身的事实,一味以寻求微言大义为能事,透露出的轻视言情、咏物、写景自身价值的意识是再明显不过的。在“常州派”那里,“兴寄”已不是一种创作的手法,实际上成为内容──并且是偏向与政治、社会有关的内容的代名词。这样,就如同朱自清指出的:“论诗尊比兴,所尊的并不全在比兴本身,而是在诗以言志、诗以明道的作用上。”(《诗言志辨》)经学家们为解《诗》建立了言志载道的诗教,“常州词派”并将词纳入诗教的轨范,造成危害文学的不良影响是同样深远的。不难看出,“常州词派”虽然不满“浙西词派”,却同“浙西词派”一样,意识深处是瞧不起词的。他们的尊词,套用朱自清的话,所尊的并不在词本身,而是在言志明道的诗教上。这不仅不能真正提高词的地位,反而是对词自身价值的歪曲与践踏。
总而言之,不论“以诗为词”和鼓吹“以诗为词”者的本意如何,从其理论中透露出来的,确实是视词为余事,为小技小道的轻词意识。这种思想中的深层意识,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有明确的认识,却无所不在地指导和支配他们的行为。他们“以诗为词”,也许想要以此扩大词的社会功能,提高词的思想境界,实际上却造成了损害词体特性、危害词体独立性的结果。归根结底,这也就是他们意识深处的轻词观念决定的。
三 苏轼词学观新说
本文从一开始便涉及到苏轼。的确,在论述古代词人和词论家的词学观时,无论如何苏轼是一个跨越不过的人物。这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像他在词史上占据那样特殊的位置,没有一个人像他在词学史上引起过那样多的话题。
那么话回到本题,我们根据本文以上陈述的思路,来对苏轼的词学观作一番新的诠释。
不用说,与众不同的是,我认为苏轼的意识深处是轻视词这种文体的。这种轻词的意识在许多方面都有反映。
首先反映在他有关词体、词学的一些见解上。
如前文所引,苏轼在《题张子野诗集后》中认为张先的词是其诗歌的“余技”,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亦谓坡称欧词“犹小技,其上有取焉者”。又,他称自己所作为小词,“近却颇作小词。”(《与鲜于子骏书》)“小词、墨竹之类,皆不复措思。”(《与李公择》)称他人所作为微词:“微词婉转,盖诗之裔。”(《祭张子野文》)众所周知,“余事”、“小词”是那个时代对词的习称,是当时普遍存在的轻词重诗,重道轻艺观念的语言表露。苏轼于此,并无不同。他又批评时人喜爱张先的歌词,是孔子所说的“未见好德如好色”,更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词的见解。
词既“微”“小”,那么在苏轼看来,怎样才能使之高贵、尊严起来呢?那就是“以诗为词”。他在《与蔡景繁书》中赞扬蔡词:“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又《与陈季常书》赞扬陈词:“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就是说,只有像诗人的诗歌那样雄豪,甚至干脆就是诗人之诗,不过句子尚须保持长短不齐,这样的词作才不再是“微”“小”之词。这也正是陈师道指摘他“以诗为词”的理论根据。
数百年以后,“以诗为词”的主张已明确发展成“诗词合一”,“诗词合流”,并被认定是“词的出路”。可以说,苏轼正是其导夫先路者。然而,诗词合流,写出的词与长短句的诗没有区别,如果真的做到了,作为一种独立文学体裁的词还存在哪儿呢?
苏轼提到的蔡、陈二家使他惊喜的词,今天已经不能使我们惊喜了。因为蔡词已全然亡佚,陈词也只剩下味同嚼蜡的《无愁可解》(光景百年)一首。历史的法则就是这样无情。可以一问的倒是,陈慥唯一留存下来的这首词,长期混迹于苏词当中(这也是它得以幸存的原因),被当作苏词传播。其所以至于此,是否传达出一种信息,即苏词当中固有与相近的一类词作,或在公众的感觉上,它就是苏轼的词作呢?
其次,反映在苏轼词创作的态度上。
我们往往讲当行本色派词人视词为卑贱之物,奇怪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用一辈子的精力专意于作词,如柳永便是典型的一例。很难解释这样的人怎么会是瞧不起词的人。
与之相反,苏轼却不是这样。按照王灼的说法,他是“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碧鸡漫志》卷二),词在他全部文字创作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且其开始作词的时间亦较诗文为迟。具体来看他的作词态度,不能说没有严肃认真的一面,可胡寅所说的“谑浪游戏”(《向芗林酒边集后序》),王若虚所说的“滑稽玩戏”、“乐府乃其游戏”(《滹南诗话》卷中),确实道出了他创作态度的另一面。
举例来说,他有《减字木兰花》一词:
郑庄好客,容我尊前先坠帻。落笔生风,藉藉声名不负公。高山白早,莹骨冰肤哪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
人多不晓其意。原来写作背景是这样:“东坡自钱塘被召,过京口,林子中守。郡有会,坐中营妓出牒,郑容求落籍,高莹求从良。子中命呈东坡,坡索笔为《减字木兰花》书牒后……暗用此八字于句端也。”(《东皋杂录》,《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40)在这里,词不仅仅是诗了,它还能当判词来使呢!
又如《戚氏》(玉龟山)一词,赋穆天子宾于西王母事,又是在什么场合下写出的呢?据其门生李之仪记载,他元祐末年在定州时常与宾客宴饮,“方从容醉笑间,多令官妓随意歌于坐侧,各因其谱,即席赋咏。一日,歌者辄于老人之侧作《戚氏》,意将索老人之才于仓卒,以验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而颌之。邂逅方论穆天子事,颇摘其虚诞,遂资以应之。随声随写,歌尽篇就,才点定五六字尔。”(《跋戚氏》,《如溪居士文集》卷38)正因其词是如此诞生的,内容十分无谓,所以后来人对当事人李之仪的确凿记载也心生怀疑,不以之为东坡所作(见南宋费衮《梁溪漫志》卷九)。
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深思。元丰年间,苏轼经过“乌台诗案”的大灾难后被贬黄州,旁人再三告戒慎勿作诗(《与程正辅书》:“子由及诸相识皆有书,痛戒作诗,其言甚切。”),他自己也决心恪守(《与沈睿达书》:“某自得罪,不复作诗文,公所知也。不唯笔砚荒废,实以多难畏人。”),即使偶尔抄录点旧作,也叮咛切勿示人。(《与程正辅书》,“今写在扬州日二十首寄,亦乞不示人也。”)然而,他却有两种文字自作不妨。一是“僧佛语”,另一就是“小词”。其《与程彝仲书》云:“多难畏人。不复作文字,唯时作僧佛语耳。”《与陈季常书》又云:“近者新阕甚多,篇篇皆奇。迟公来此,口以传授。”为什么这两种文字不在深戒之列呢?因为它们都不碍事。“专为佛教,以为无嫌,故偶作之。”(《与王佐才书》)“比虽不作诗,小词不碍,辄作一首,今录呈。”(《与陈大夫书》)不仅作,还盼着别人来读,还直接寄去与别人看!
通常认为,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现实、针贬时弊的社会功能,是其提高词的地位,使之能与诗平等的表现。姑不论这是否算作提高了词的价值,从上面反映的苏轼对于作诗与作词截然相异的表现中,已使我们对这一通常所持的观点产生了怀疑。苏轼对词的看法果然和诗一样吗?他的“小词”所以能“不碍”,与胡、王诸人说他的“游戏”、“玩戏”为词之间是否有相当的联系呢?我以为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苏轼自己在广州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已明确表达了将作词与欣赏词当作“闲居之鼓吹”(《与杨元素书》)的观点。
这样,最后,就来看看苏轼“闲居鼓吹”、“游戏”作词在实际创作中的具体表现。
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取舍,不必要也不可能求得一律。但我想,对于苏词中的这几类词,人们应该是无法为其叫好的,一是回文词,二是嵌字词,三是自创不可解之词,四是集句和隐括词。这些词之所以非属玑珠,是因为它们玩文学,玩技巧,游戏笔墨,完全背离了文学创作、“为情而造文”的基本要求。
苏词中有《菩萨蛮》回文七首,其中四首为春、夏、秋、冬四季“闺怨”,文意扦格,俗不可耐,几令人无法卒读。其《春闺怨》一首云:
翠鬟斜幔云垂耳,耳垂云幔斜鬟翠。春晚睡昏昏,昏昏睡晚春。细花梨雪坠。坠雪梨花细。颦浅念谁人,人谁念浅颦。
可见一斑。邹诋谟《词衷》说:“回文(词)之就句回者,自东坡、悔庵始。”之后陆续有人试作,苏轼可谓始作俑者。嵌字词见前引,将“郑容落籍,高莹从良”八字嵌于每句之首,勉强凑成一阕,以至后人“多不晓其意”(《扪虱新话》卷九),非有知情人解释一番不可。苏轼之后,嵌字词未见续作。苏轼又有《皁罗特髻》一词:“采菱拾翠,算似此佳名,阿谁消得。采菱拾翠,称使君知客。千金买采菱拾翠,更罗裙满把珍珠结……”《词综》谓此词“不可骤解”,明人万树《词律》卷12收之,亦谓“或是坡仙游戏为之,未可考也”。
集句本是诗歌创作中的一种手法,历来人们对其评价不高。黄庭坚称之为“百家衣体”,且曰“匹堪一笑”(见《冷斋夜话》卷三、《滹南诗话》卷中)。刘贡父亦讥其为”譬如蓬荜之士,适有重客,既无自己庖厨,而器皿肴蔌悉假贷于人,收拾饾饤尽心尽力,意欲强学豪奢,而寒酸之气终是不去”(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甚至苏东坡本人也嘲笑集句是乱拉郎配,“天边鸿鹄不易得,便令作对随家鸡”(《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但他虽不作集句诗,却作了集句词四首,为《定风波》(雨洗娟娟嫩叶光)、《南乡子》(寒玉细凝肤,怅望送春杯,何处倚栏干)。他又有隐括词六首,前人评价甚低,连惯唱颂歌的王若虚也不得不谓:“东坡酷爱《归去来辞》,既次其韵,又衍为长短句,又裂为集字诗,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尔!是亦未免近俗也。”(《滹南诗话》卷中)清人贺裳《皱水轩词筌》亦云:“东坡隐括《归去来辞》,山谷隐括《醉翁亭》,皆堕恶趣。天下事为名人所坏者,正自不少。”这些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
苏轼游戏为词的表现除在形式外,内容也有之。这主要指应酬玩笑一类作品。《减字木兰花》云:
唯熊佳梦,释氏老君亲抱送。壮气横秋,未满三朝已食牛。犀钱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坐。多谢无功,此事如何到得侬。
这是苏轼贺其好友李公择生子而作。内中用了《笑林》里的一个典故。“晋元帝生子,宴百官,赐束帛。殷羡谢曰:‘臣等无功受赏。’帝曰:‘此事岂容卿有功乎?’同舍每以为笑。”另有《南歌子》(师唱谁家曲)一首。这类作品,内容上一无可取,却能反映作者的风趣和诙谐。清人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下卷》称“苏长公为游戏之圣”,主要是就这类作品而言。
在内容上苏词还可指摘的一点是,胡寅说他“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这是言过其实的评语。他的作品,妖娆秾丽、格调低靡的艳词并不罕见。他用“嫩脸”、“香喘”描摹女性的情态声气,也不乏“剥葱”(手)、“腻玉”(颈)之类的俗喻。从情调到写法与为人们所诟病的南朝宫体诗和晚唐五代词中的某些绮靡之作没有区别。如他在酒席上赠侍儿的一首《鹧鸪天》:
笑撚红梅亸翠翘,扬州十里最妖娆。夜来绮席亲曾见,撮得精神滴滴娇。娇后眼,舞时腰,刘郎几度欲魂消。明朝酒醒知何处,肠断云间紫玉箫。便是很具代表性的一例。
苏词中的这类作品,前人不是没有看到,却往往为之打圆场。读读这样的话语最有意思。王若虚云:“其溢为小词,而间及于脂粉之间,所谓滑稽玩戏,郦复尔尔者也。若乃纤艳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辈,岂公之雅趣也哉!”(《滹南诗话》卷中)就是说,苏东坡的脂粉绮靡,那是闹着玩的,不像柳永等人,那才真不得了。元好问的一段话则更多牴牾:“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新轩乐府引》,《遗山文集》卷36)既然坡词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怎么还会“时作宫体”?既然“时作宫体”,怎么又不可“以宫体概之”呢?当然,谁也不会说苏词全是“宫体”,其中有相当多的“宫体”成分,这是无法为之解说的。只能说,它是苏轼轻视词体,视之为“小道”的又一表现。
也许有人要说,在本色当行派词家中所谓“脂粉淫媟”之作岂不更多?无疑这是事实。但我以为,二者反映出的实质尚有不同。对于本色当行派词人来说,归根结底是他们精神境界不广、趣味格调不高所致,而不是他们轻视词这一文体的缘故。此类词人创作诗歌,同样多脂粉绮靡之作──其结果是晚唐五代诗风的昌盛,恰恰能够证明这一点。而苏轼则不同。他主张“以诗为词”,本身就是因为他觉得诗大词小,诗庄词媚,所以要以诗歌改造之,而在实际创作中又难免处处流露出对他认为“微”“小”的这种文体的轻视,除上述诸条外,包括这里所说的“时作宫体”。在他的诗歌当中,这类格调低下之作是几近绝迹的。这当然就是他轻视词体思想的表现了。
行文冗赘,不觉已过万言。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愿意声明,以上所论不过是从某种特定的角度对轻词尊词问题所作的一些探讨,意在为沿袭已久的传统观点提供一种参照,以期引起对这些词史上关乎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全面思考。言辞容或偏激,观点抑有过当,尚希方家通人不吝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