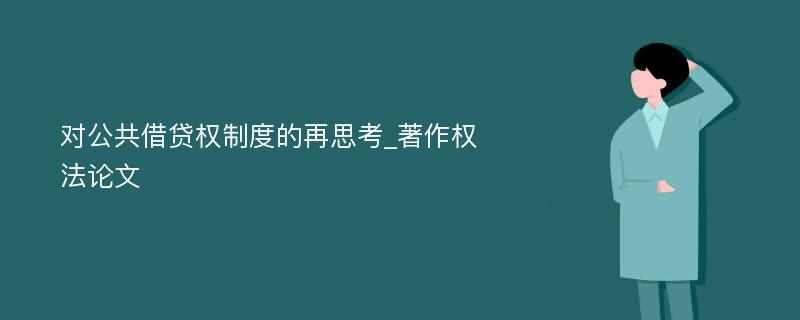
对公共借阅权制度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913.6
1 公共借阅权出现的背景和我国的研究现状
随着版权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越来越大,版权人或者出版商对图书馆传统的外借服务提出了质疑,认为图书馆不能再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而履行其职能,要求拥有某种权利以对抗图书馆的这种出借行为。因为版权人的经济利益(或出版社的利益回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作品的销售而实现的(在传统的贸易条件下)。而图书馆每出借一部作品比如一本图书,就意味着该书籍的销售量要减少一本,尤其是许多畅销小说或仅具参考功能的书籍(不具备一读再读或经常使用价值的书籍),通过图书馆的外借服务,几乎可以取代书籍的销售。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外都讨论过“公共借阅权”的问题以及如何享有这一权利的问题。1946年,丹麦政府在作家Thit Jensen的主张下第一次以行政规定的方式,承认公共借阅权[1]。随后,瑞典(1954年)、冰岛(1963年)、荷兰(1971年)、前联邦德国(1972年)、新西兰(1973年)、澳大利亚(1974年)和英国(1979年)也都分别立法规定作者或出版商享有公共借阅权,要求图书馆每出借一本书,都应当支付作者或者出版社相应的补偿金[2]。在这些国家中,绝大部分是在著作权以外,以单独立法的方式,如在《公共图书馆法》或者《公共借阅权法》中建立公共借阅权制度的,只有德国将公共借阅权写入了著作权法的第27条中[3]。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国也开始了对公共借阅权的关注和研究。特别是加入WTO后,TRIPS(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也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11条明确提出了关于出租权的规定,这就为公共借阅权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契机。因为随着图书馆馆藏作品类型的多样化,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外借。而对于新作品的出借和对传统作品的出借在法律上定位不一样,自然不利于著作权的保护。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我国最早对公共借阅权制度进行研究的是郑成思先生,当时图书情报领域还未真正意识到其对图书情报工作的影响,因此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4]。随着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意识的增强,公共借阅制度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目前,国内对是否建立公共借阅权制度有3种观点:反对建立公共借阅权制度的人认为,这样做违反了图书馆的公益性原则,且影响文献信息的传播,就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设立这种制度确实困难很大;持赞成观点的人主要是从著作权人的角度来考虑的;中间派人士则认为,图书馆应该给受到损失的作者以一定的经济补偿,但反对以立法的形式赋予作者这一新的财产权[5]。由以上的观点可以看出,无论是赞成的观点还是反对的观点,他们的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些对立的观点实际上都忽视了一个原则:在讨论著作权有关问题时,始终应该牢记,承载着法律正义、公平价值观念的著作权法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平衡器(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平衡,作者、传播者、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具体在公共借阅权问题上,就是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平衡。著作权法的精神就是在给予著作权人一定权利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同样,在对待公共借阅权的问题上,也不应该忘记这一准则。在图书情报领域,大多数人不赞同建立公共借阅权制度[6]。但笔者认为:图书馆的公益性并不能成为牺牲著作权人利益的理由,图书馆只有在尊重著作权人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够履行自己的信息传播的职能。同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著作权法只有达到了帕累托标准(注:所谓帕累托标准是指效益的提高必须是对各方都有利,以损害某一方利益为代价,改善他方利益的方法实质上是没有效益的。它是微观经济学中对效益本身的判断标准的一种,是根据19世纪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一概念可以用作评估资源配置的方法,它通常表示为:如果没有方法可使一些入境况变得更好一些而又不致使另一些人境况变得更差一些,那么这种经济状况就是帕累托有效的。(见[美]H·范里安著,费方域译,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4页)。),才算是有效益的。因此,笔者赞成建立公共借阅权制度。在论证这一观点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公共借阅权。
2 公共借阅权的权利归属和本质含义
关于公共借阅权的定义,国内有的文献将其解释为:“指作者按其享有版权的每本图书在图书馆被借阅的次数而收取版税的权利。”[7]可以看出,这里是将公共借阅权定位为属于著作权人的一种权利。而《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实务大全》对公共借阅权的定义是:“公共借阅权是指公共性图书馆向公众借出作品的复制本以及向公众出租唱片或允许公众录制其唱片并向出借方支付一定的费用的权利。”[8],由此可以看出,该定义是将公共借阅权归属于图书馆的。那么到底公共借阅权是谁享有的权利呢?笔者认为,外借是图书馆传统的基础性服务之一,也是图书馆行使其传播信息、知识职能的一种重要手段。公共借阅权是行使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基础。换句话说,其权利应该归属于图书馆,而不是著作权人。前一种定义将这种权利归属于著作权人,笔者认为是很不恰当的。后一种定义无疑是可取的,但该书又认为,“它属版权中的财产权利的一种”,使得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一定的混淆。而且两种关于公共借阅权的定义都将出借的对象限于图书或唱片,笔者认为,这种范围的限定不能反映如下事实:随着信息存贮技术的发展,作为人类智力成果集藏地的图书情报机构,必然会在馆藏作品的种类上反映这种发展和变化,而日益丰富和多样化的馆藏作品都有可能成为图书馆外借这一行为的客体。也就是说,公共借阅对象虽然目前主要是图书,但将来肯定不会仅限于图书。基于此种理解和原因,笔者认为,公共借阅权是指公共图书馆向公众借出固定于一定载体上的馆藏作品并向出借方支付一定费用的权利。
如果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来看,假设所有作品的作者都享有出租权的话,那么图书馆公共借阅行为实质上是将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无偿提供给公众的一种出租行为。也就是说,图书馆在履行其职能时,行使的是著作权人的出租权。如果提供这种出租业务的机构其目的是赢利,那么这种行为肯定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出租权。但是图书馆的这种出租行为的目的是非赢利的(为社会公众提供信息、知识),那么是否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出租权呢?这首先要看出租权的存在是否有效,也即著作权法是否授予著作权人这项权利。其次是必须在平衡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前提下,作出是否对著作权人的这项权利进行限制,以及是否需要对著作权人因这种出借行为带来的经济损失而给予补偿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在尊重著作权人权益的前提下,维持图书馆的正常运作和发展,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而这正是著作权法根本宗旨所要求的。
3 TRIPS及我国关于出租权的规定
出租权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许可他人临时使用其作品并取得报酬的权利。它是著作权人所享有的重要的财产权之一。TRIPS第11条规定,“至少应给予计算机程序和电影作品的作者或作者之合法继承人这种出租权”。虽然TRIPS未明确说明是否所有作品的著作权人都享有出租权,而仅对于出租利润可能很高,可能对著作权人的利益损害比较大的这两种作品授予出租权,但TRIPS考虑的基础却是以是否对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很大损害(指这种出租行为)为标准的。
具体到我国的情况而言,我国以前的著作权法是承认所有作品的著作权人的出租权的,并将其涵盖于发行权之内。旧的著作权法第10条第5款规定:“发行,指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由此可见,按照此规定,任何作品的著作权人都可以享有出租权,任何非著作权人想要将其作品的复制件向他人出租(除法律上有其他规定以外),都必须经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否则将构成侵权。而加入WTO后,我国新修改的著作权法却将出租权从发行权中独立出来,新著作权法第9条第6款对发行权的定义是:“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的权利。”著作权法在这里明确地规定行使发行权的方式只有两种:出售或赠与,从而将出租或其他的方式排除在外。与此相对应的是第9条第7款对出租权的规定:“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著作权法对于出租权不仅规定了出租的目的(必须是有偿的,而且对出租对象作了限制,仅为电影作品和计算机软件)。由此可见,我国新著作权法其实是降低了对作品的出租权的保护水平,因为对受保护的作品的范围和使用作品的目的都做了一些限制。立法者作出这一改变,可能主要基于入世后一方面要遵守WTO中的TRIPS协议关于出租权的规定的承诺,另一方面鉴于出租权如果再包含发行权的话,会与权利穷竭原则发生冲突。所以才将出租权独立于发行权。关于出租权与权利穷竭原则之间的关系,笔者将另外撰文阐述。
4 公共借阅权与出租权之间的冲突和解决办法
由上文可知,图书情报机构公共借阅权的行为实质上是在行使著作权人对其作品所享有的出租权。由于目前享有出租权的作品的类型仅限于电影作品和计算机软件,并且规定出租的目的必须是赢利的。因此,图书馆行使的公共借阅权与著作权人的出租权之间暂时不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但随着数字存储技术的发展,图书馆的馆藏中必定会有大量的光盘、多媒体、计算机软件等作品,任何一件馆藏作品都有可能成为向公众出借的对象,也就是说,以后图书馆的公共借阅对象中会出现享有出租权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的这种出租行为就会对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造成很大的损害。退一步说,即使图书馆的公共借阅权可以作为对著作权人的出租权的一种限制方式而存在的话,也不符合TRIPS第13条关于权利限制与例外的规定:全体成员均应将专有权的限制或例外局限于一定特例中,该特例应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也不应不合理地损害权利持有人的合法利益。因此,尽管目前公共借阅权与出租权之间的冲突不是太激烈(目前图书馆公共借阅的对象主要是图书,而我国并没有赋予图书这种作品类型以出租权,而且这种出借行为对图书贸易额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法律的前瞻性要求图书馆考虑这一问题。这里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4.1 将享有出租权的作品类型的范围扩大
TRIPS目前仅仅要求只对电影作品和计算机软件两种作品赋予其出租权,如果将出租权的作品类型的范围扩大,是否会与我国的国情不符呢?笔者认为是不会的。很多人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只是我国为了适应入世的要求,这种说法只说对了一半。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如我国修改后的著作权法中有关网络环境下的几个条款,增加了对公众的网络信息传播权、增加了对技术措施、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等,这些都不是TRIPS所要求的。所以笔者认为,将享有出租权的作品类型的范围扩大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的。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将来的多媒体作品、光盘等电子作品都能够享有出租权,为什么图书这种作品不能享有出租权呢?虽然著作权法中确实有作品类型不同而不能享有同样权利的规定,如展览权的客体就只限于美术作品和摄影作品,但这种情况存在的前提是有的作品无法行使这种权利或社会通常没有利用这种作品的习惯。对于出租权而言,既然图书可以行使出租权,为什么就不能赋予其出租权呢?笔者认为应对所有能够出租的作品都赋予出租权。
4.2 通过对出租权的权利限制来确立图书馆的公共借阅权
公共借阅权的出现是以承认著作权人能够从图书馆的出借行为中获取一定经济报酬为前提和基础的。而图书馆行使公共借阅权时代表的是使用作品的社会公众的利益,从这个角度出发,公共借阅权和著作权人的出租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实质上就成了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解决这种冲突的办法,就是通过对著作权人的垄断权利作出一定的限制来达到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平衡。针对公共借阅权和出租权的问题,笔者认为也可以运用利益平衡的办法来解决。具体的措施是,首先从权利归属的这个角度确立图书馆享有公共借阅权,然后基于图书馆的这种外借行为,在著作权法中对出租权进行一定的限制。
那么到底是在著作权法中还是在其他的法令中赋予图书馆这种公共借阅权?国际上的做法是,有的国家在《公共图书馆法》或者《公共借阅权法》中作出规定,有的国家是在著作权法中作出规定,如上文提到的德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笔者认为是因为对公共借阅权的权利归属及其与出租权的关系存在着模糊认识而造成的。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法律都有其特定的主体。著作权法的法律关系的主体就是著作权人,而公共借阅权的权利主体是图书馆等机构,而不是著作权人。只有出租权的法律主体才是著作权人。因此,将公共借阅权写入《公共图书馆法》或《图书馆法》中是比较合理的。同时在著作权法的有关权利限制的条款中应该对图书馆的这种出借行为作出特别的说明。
至于是通过合理使用还是通过法定许可的方法来对著作权人的出租权进行限制,也就是是否支付给著作权人一定的经济报酬及如何支付,这要依各国具体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来决定。因为任何一种制度(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在内)的设计都不能脱离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和技术的发展现实。因此,对于公共借阅权的问题也应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目前我国大多数图情机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投资,这与国外的图情机构有着很大的不同。国外许多图书馆的资金虽然有一部分来自政府,但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于企业。因此国外公共图书馆将政府投入的一部分资金用于支付给著作权人,并不会对其运作和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图书馆可以通过与企业合作或提供附加值服务来进行弥补。而我国图情机构的产业化步伐比较缓慢,政府对图书馆的财政支出本来就不够,如果图书馆再从这本不多的资金中抽取一部分支付给著作权人,对图书馆的发展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火上加油。另一方面,图书馆又不能因为资金不足而不尊重著作权人获得报酬的权利。所以笔者建议在著作权法中增加通过法定许可的方式允许图书馆因行使公共借阅权而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同意,但必须支付一定报酬的内容。在具体实践中,可在《图书馆法》中这样规定:图书馆的出借行为可以象征性地给予著作权人一定的报酬,或者通过不定期向著作权人提供有偿性书目情报服务等方式来尊重著作权人的可获得报酬的权利。
这样做,虽然于弥补著作权人的经济损失来说可能效果甚微,但至少在图情机构强化了这样的观念:尊重知识产权。这对于向来重义轻利的中国著作权人来说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至于图书馆具体采用哪种方式,可以在实践中与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进行协商。
标签:著作权法论文; 图书馆论文;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