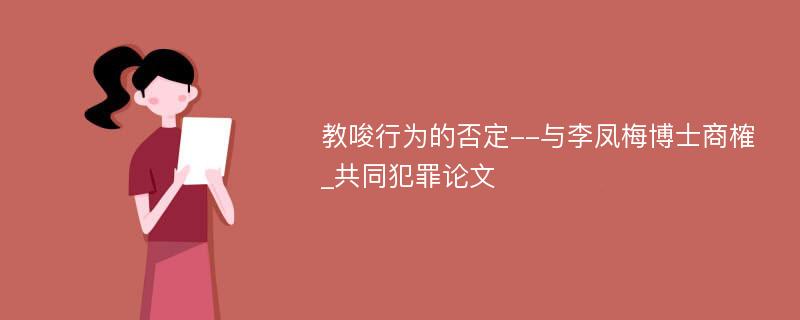
教唆行为的实行行为性之否定——兼与李凤梅博士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博士论文,李凤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教唆行为是指行为人通过授意、指示、纵容、劝说、挑拨、刺激、收买、利诱或其他方法故意唆使他人实行犯罪的行为。关于教唆行为的法律性质,亦即教唆行为究竟是实行行为抑或非实行行为(共犯行为),理论上尚存有争论,《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期所刊的李凤梅博士的《教唆行为:共犯行为抑或实行行为》(以下简称《李文》)一文明确提出“实行行为性是教唆犯的必然属性”的见解,亦即,教唆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实行行为而非共犯行为。①但依笔者之见,除立法者将某些教唆行为特别规定在刑法分则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行为中而使之具有实行行为性之外,教唆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加担实行行为的非实行行为(共犯行为)。本文拟基于实定法、实行行为的构造、共犯的本质以及共犯停止形态认定的视角对教唆行为共犯性予以分析的基础上,并进一步地就《李文》中关于“教唆行为共犯性之检讨”相关论点提出若干辩驳意见,以就教于李博士及诸位专家、学者。
一、教唆行为共犯性之论证
(一)基于实定法上的分析
刑法分则中的构成要件,诸如杀人罪中的“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那样,是以单独正犯(实行犯)的既遂模式而作的规定。但在现实生活中,由数人参与、协作起来而共同实施犯罪的情形并不少见,从实行犯罪的确实性、侵害法益危险性程度来看,应当说这种协作行动具有更高的可罚性。这是因为:从客观上看,相互之间通过角色的分工和作用的分担而使犯罪更容易实现;其次,在主观上,参与协作行动的人之间依托这种“群众心理”发挥作用,无疑使犯意得到进一步地强化。为了准确把握上述协作现象,合理地对他们进行处罚,各国刑法一般相应地规定正犯(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等具体的犯罪形态。例如,日本刑法第60条关于共同正犯要件的规定是“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第61条关于教唆犯要件的规定是“教唆他人使之实行犯罪的”;第62条关于从犯(帮助犯)要件的规定是“帮助正犯的”。“所谓正犯,包括自己直接实行具有实现构成要件的现实危险的行为的情形(直接正犯)和利用他人为道具,如同自己直接实行犯罪的情形(间接正犯);所谓共犯是指自己不直接实行犯罪,而是协同正犯的行为即实行行为从而实现构成要件的。从这一立场来看,《刑法》第61条规定的‘教唆他人使之实行犯罪’的教唆犯以及第62条规定的‘帮助正犯的’的帮助犯即是共犯。”②相应的,“所谓教唆行为是指适于使他人产生实行特定的犯罪决意的行为;所谓帮助行为是指通过实行行为以外的行为辅助正犯以使实行行为容易实现的行为。”③我国刑法中虽无正犯概念的规定,但结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教唆犯、从犯等的规定,理论上一般以各共犯者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情况为标准将之划分为组织犯、教唆犯、实行犯和帮助犯,其中实行犯是在共同犯罪中分担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的人,不分担实行行为而在共同犯罪中进行组织、领导、策划共同犯罪活动或者教唆他人实行犯罪活动或者为实行犯实行犯罪提供帮助的则分别是组织犯、教唆犯或者帮助犯。
由此可见,不论是日本刑法还是我国刑法,分则要件原则上规定的是单独犯既遂类型这种“限制的正犯”的构成要件,而就数人协作加担该犯罪的情形,则根据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予以把握,并通过这种形式扩大了处罚范围(扩张的处罚事由)。理论上一般人认为,这种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就是对分则规定的基本构成要件予以修正的构成要件形式。很显然,分则规定的正犯的实行行为并不包括对作为修正的构成要件行为的共犯行为(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例如,以杀人罪为例,所谓的实行行为就是诸如用枪射杀、用刀砍杀、下毒毒杀等行为,因而无论是作出“杀了A”指示的行为或者提供一把枪给行为人以便于其实施杀害B的协助行为,均不能将之理解成杀人罪的实行行为。所以,从实定法的角度来看,教唆犯是教唆他人使之实行犯罪的人,亦即通过教唆行为使他人产生犯意进而通过他人的实行行为惹起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而其本人并不亲自参与犯罪的实行行为。所以说,教唆行为属于加工正犯实行行为的共犯行为,而非实行行为。
(二)基于实行行为构造的视角分析
1.什么是实行行为?
关于实行行为的含义,大陆法系刑法学一般从形式的侧面和实质的侧面两个方面来把握。例如,大谷实教授就认为,“确定实行行为,靠是否符合构成要件来决定。因此就得判断该行为或事实在形式上是否充分满足法定的构成要件。另外,由于所有的构成要件都是以保护一定法益为目的而被法律规定出来的,因此,成为实行行为,仅在形式上满足构成要件要素还不够,还必须具有实施该行为的话,通常就能引起该构成要件所规定的法益侵害结果程度类型的危险,换句话说,必须是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的实质,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符合特定构成要件。④正因为此,日本多数学者认为,对于不能犯的情形,在外形上或形式上已经开始符合构成要件,但因不具有发生法益侵害的现实危险或者危险性极低,从而被认为欠缺实行行为性。”⑤
关于实行行为含义的认识,我国传统的通说基于犯罪构成的形式立场对实行行为进行界定,亦即,“所谓实行犯罪,就是实施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例如,杀人罪中的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等等,都是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⑥这在理论上被称为形式说。笔者以为,在规范论上看,实行行为首先必须是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这是坚持罪刑法定主义的必然逻辑结论。但如果仅从纯粹形式立场界定实行行为的概念,可能会面临以下诘难和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形式说未能揭示某一行为之所以成为实行行为的实质根据。形式说论者指出,实行行为就是实施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但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何以就是实行行为呢?论者并没有对这一本质性的问题作出回答。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没有侵犯法益的行为不可能构成犯罪,当然也不可能成为实行行为。但由于我国现行刑法规定预备行为具有可罚性,这说明预备行为也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险性,因此,实行行为必然是对法益的侵害危险性达到一定程度的行为。
第二,形式说对实行行为的认定并不具有普适性。例如,对于类似诬告陷害罪这样的“紧密型的复行为犯”,其突出特点就在于:“这类犯罪的成立要求同时具备两个行为,如果只有其中一个行为,则不构成该罪。因此,对于这类犯罪只有开始实施两种行为时,才能认为是整个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⑦何以如此呢?追根溯源,还是在于:行为人单纯捏造他人犯罪事实而未实施告发的情形,虽说已经开始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但尚不具有侵害诬告陷害罪所保护的法益的现实危险性。⑧又如,由于《刑法》对大多数犯罪的构成要件规定得较为明确,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把发生的事实与分则条文规定的定型性的构成要件行为相比较,实行行为的证成就不成难题。但并非所有的犯罪的实行行为都规定得十分明确,特别是类似不真正不作为犯这种开放的构成要件的场合,对分则条文所规定的实行行为进行实质意义上的解释就显得至为重要。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故意杀人为例,刑法条文并未明确必须由作为构成,因而母亲以杀意而不授乳的行为在形式上可以定型为杀人罪的构成要件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母亲开始一两次不授乳的行为就是杀人罪的实行行为。而是只有不授乳的行为对婴儿的生命产生现实的威胁时,才可以认定该母亲实施了故意杀人的实行行为。
第三,形式说不能准确地界分不能犯与未遂犯。一般以为,不能犯是行为在形式上符合了构成要件,但客观上不具有法益侵害的现实危险性的情况,可以说同未遂犯一样,也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不能既遂的情形,但二者的界限就在于行为是否具有实行行为的性质,即是否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具体的危险。⑨例如,A欲杀害B,在国外购买了一把枪支,回国后的一天深夜,向B以前睡的床上开枪射击,而B实际上在一个月前就已死亡。根据形式说,行为人的开枪射击行为是符合杀人罪的犯罪构成的客观行为,因而是实行行为。其实不然,这种场合,由于被害人已死亡一月有余,因而,应否定这一开枪行为的现实危险性,以不能犯处理较为妥当。⑩
由此,实行行为应是形式侧面和实质的侧面的统一。亦即,所谓实行行为是指实施刑法分则类型性规定的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性的行为。(11)由此,就实行行为的构造而言:形式上,行为人实施的是符合刑法分则某一具体条文类型性规定的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的行为(形式上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实质上,行为人实施的符合某种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具有侵害该构成要件预设的法益的现实的危险(实质上的法益侵害的现实危险性)。
2.教唆行为不符合实行行为的构造
教唆行为是实行行为抑或教唆行为的问题,分析的基本路径之一就是从实行行为的概念本身出发。如前所述,从形式上看,实行行为首先必须是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而教唆行为旨在教唆他人实行分则条文规定的某种具体的犯罪,其本人并不参与犯罪的实行。亦即教唆犯的教唆行为并非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的行为,所以,“教唆行为本身不是,也不可能是刑法意义上的实行犯罪的行为。”(12)从实质上来看,教唆行为一般不具有法益侵害的现实危险性,不具备认定实行行为的实质要件。例如,甲对其情人乙女说,你夜里趁你丈夫睡着时将他杀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很显然,在教唆者只是说了一句“杀了某人”时,即使对方完全默认,但仅此还没有处罚的必要性。(13)故而,一般情况下,教唆行为只有同被教唆犯实施的犯罪行为结合在一起时,才会对法益产生紧迫或现实的危险,可以这样说:相对于正犯的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在侵害性上具有间接性、依附性和不现实性,离开正犯的实行行为,教唆行为永远不会对法益造成现实的、紧迫的危险,至于侵害法益的现实结果的不会发生就自不用说了。由此,将教唆行为定位为实行行为的见解不仅具有消解实行行为与共犯行为概念区分之嫌,而且有动摇实行行为理论根基之危险。
(三)基于共犯本质视角的分析
从共犯本质的视角探讨教唆行为的性质及其定位问题,究其实,就是教唆行为的从属性和独立性之争的问题。从属性说基于客观主义的立场,认为共犯(教唆犯、从犯)的犯罪性和可罚性从属于正犯的犯罪性和可罚性。为了共犯成立犯罪,至少需要正犯已着手于犯罪的实行,正犯者没有实施犯罪行为,共犯的犯罪性和可罚性也就不能成立。目前,这在大陆法系国家是通说。而独立性基于主观主义的立场,认为犯罪乃行为人恶性的征表,由于共犯行为(教唆行为、帮助行为)亦是侵害法益意欲的征表,其本身是一种独立的实行行为,而非从属于正犯的实行行为。德国学者布黎、日本学者木村龟二、牧野英一等曾是此说的代表。
关于教唆犯的性质定位问题,我国有学者基于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教唆犯的规定提出了独立性和从属性的有机统一的二重性的见解,这也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通说观点。该说认为,就教唆犯与被教唆人的关系来看,教唆犯具有相对的从属性,因而教唆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共犯行为(第29条第1款);另一方面,教唆犯的教唆行为系行为人本身表现其固有的社会危害性,并对结果具有原因力,所以说教唆犯又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的地位,只要教唆犯实施了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即便被教唆人没有实施所教唆的犯罪,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都构成犯罪(第29条第2款),只不过是未遂而已。(14)这实际上肯定了教唆行为的实行行为性,教唆行为的实施本身就是犯罪的着手。
在大陆法系,基于主观主义、意思刑法立场的共犯独立性说已经衰退,时至今日几无学者支持。在我国,也少有学者采取这一见解。但基于二重性的原理,认为教唆犯的教唆行为具有独立的实行性,因而只要教唆犯故意以言辞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教唆,就应视为教唆犯已经着手进行犯罪,简言之,应以开始实行教唆行为为其犯罪的着手。可以看出,对于教唆犯实行行为及其着手的认定,二重性说与独立性说的结论并无二致,都以教唆者的教唆行为的开始为基准。然而我们注意到,在这一问题上,从属性说主张是以正犯开始实施所教唆的罪的实行行为为着手的标准,而独立性说则主张以教唆犯开始实施教唆行为为着手,可见,两学说是根本独立、水火不相容的,于是二重性说最终无奈地倒向独立性说一边,终究也就陷入关注犯罪人的反社会性或犯罪意思的主观主义的理论窠臼。对于教唆犯的二重性理论,诚如张明楷教授指出,“不难看出,共犯从属性说和独立性说,不论就基本观点而言还是就理论基础而言,都是非此即彼,完全对立的,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二者都可以调和、折中,以行走方向作比喻,从属性说如同走向东方,而独立性说如同走向西方,一个人或者一辆车,不可能同时既向东方行走或行驶,又向西方行走或者行驶。……然而,这种二重性说的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也不存在这样的理论主张与立法体例。总之,教唆犯二重性说以及共犯二重性说不可思议,不宜提倡!”既然共犯二重性说是自相矛盾的,其理论根基本身是存在问题的,那么,以此对教唆行为性质的解读结论当然是不可取的。至于《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的不合理性以及该种情形的教唆行为的性质具体判定问题,笔者将在后文加以研讨。
(四)基于共犯停止形态认定视角的分析
日本著名刑法学家小野清一郎曾指出,区分教唆行为、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乃是近代刑法的一个文化收获。此外,根据共犯独立性的观点,杀人的教唆行为要比杀人的预备行为更进一步地成为杀人的实行行为,这显然与自然的法感情不符。(15)刑法分则条文中的犯罪构成所包含的只是正犯行为,而不包括属于修正构成要件的非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帮助行为等)。就法律性质而言,非实行行为相对于实行行为来说,具有从属性、依附性的特征,非实行行为是依据实行行为而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所作的法定修正,其本身不可能是实行行为。倘若认为教唆犯的教唆行为亦为实行行为,就可能会出现如下不合理的结论:其一,在成立共犯教唆的场合,教唆犯的教唆行为和被教唆犯的实行行为也就都成了实行行为,这样两者均构成共同实行犯。这就意味着教唆者与被教唆者构成共犯的场合,教唆犯与被教唆犯有着各自独立的着手及未遂标准;进一步地,教唆犯的教唆行为实施完毕是教唆犯的既遂,而正犯的既遂则是以正犯完成所教唆之罪,从而教唆犯和实行犯协作、联动共犯的情形就有两个不同的既遂标准,这显然是无视共同犯罪的“共同性”的本质而得出的结论。其二,进一步地假设甲教唆乙杀丙,乙持枪前往丙的单位时,因形迹可疑被保安警察盘问,乙便如实交代全部犯罪事实,此种情形下乙的行为只是杀人预备行为,而甲的行为属于杀人未遂,这显然不合情理,亦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二、对《李文》中关于“教唆行为共犯性之检讨”若干论点的辩驳
为了论证教唆行为的实行行为性,《李文》基于共同犯罪构成要件、立法的协调性以及司法裁量的妥当性等视角就教唆行为共犯性提出了若干质疑。对此,笔者拟逐一辩驳如下:
(一)教唆犯与正犯之间的主观意思内容的不同和客观行为分工形式的不同正是教唆行为与实行行为相区别的根本依据
《李文》认为,认定教唆行为为共犯行为,必得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之间符合构成共同犯罪的要件。但是,从主观要件来看,教唆者表现为明知自己的教唆行为会发生被教唆者产生犯罪决意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被教唆者产生犯罪决意进而实行犯罪行为导致这种危害的发生,而被教唆者则表现为明知实施所教唆的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实施所教唆的行为引起危害结果的出现,其意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与前者有所不同。与此同时,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之间只表现为教唆者对被教唆者进行教唆的单向犯意流动,而非共同犯罪所要求的犯意沟通;从客观上来看,教唆者表现为以各种方式对他人实施教唆以促其犯意形成的行为,而被教唆者则表现为实施所教唆的犯罪行为,在教唆内容不确定或者被教唆者实施的是非教唆犯罪的情况下,两种行为之间缺少共犯行为与实行行为之间的辅助或者加担关系。(16)
《李文》以上论述主要从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角度阐释了不同情形下的教唆者与被教唆者的主观意思与客观行为相异之处。笔者以为,结合我国教唆犯的立法来看,《李文》该段论述的前部分所指的可以说是《刑法》第29条第1款规定的教唆者与被教唆者构成共犯的教唆情形,后部分所指的则可以说是《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的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不构成共犯的教唆情形。(17)诚如《李文》所分析,在非共犯的教唆的场合,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之间只表现为教唆者对被教唆者进行教唆的单向犯意流动,而缺少相互的犯意沟通;从客观上来看,两者之间缺少共犯行为与实行行为之间的辅助或者加担关系。很显然,这种情形的教唆行为充其量只是行为人(教唆者)为了实现犯罪而寻找犯罪同伴、制造“犯罪实行者”的行为,本质上属于为实现犯罪而创造条件的“预备行为”。(18)由此,该教唆行为的实行行为性理所当然地就被否定。对于成立共犯的教唆之情形,主观上分别表现出的是具有唆使他人产生决意的犯意和接受唆使进而实行所教唆之罪的犯意,客观上分别表现出的是仅仅实施教唆行为而不直接参与犯罪的实行和直接实行所教唆之罪的行为。正是由于两者之间的主观意思和客观行为分工的根本差异,才会被区分为共犯行为和实行行为,也正因为此,才有共犯和正犯的区别。
(二)刑法分则中将部分具有教唆性质的行为予以独立成罪的规定不能作为教唆行为一概具有实行行为性的认定依据
《李文》指出,刑法总则中规定教唆犯,已成为各国立法通例,但是通观各国刑法典,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分则中规定若干具体的教唆犯罪,……这种总则认定为共犯行为而分则又例外性地承认为实行行为的教唆行为的立法模式,由于例外地承认了教唆行为在具有依附性的同时也具有完全的独立的地位,因而不能为教唆行为加担于正犯实施的不法而受处罚这一结论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19)
的确,各国刑法总则就教唆犯及其处罚原则规定的同时,又在分则中将部分具有教唆性质的行为予以独立成罪,并设置具体的法定刑。例如,我国《刑法》第103条第2款(煽动分裂国家罪)、第105条第2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第353条第1款(引诱、教唆他人吸毒罪)、第395条第1款(引诱卖淫罪)、第395条第2款(引诱幼女卖淫罪)等,即是适例。显而易见,总则关于教唆犯的一般规定与分则关于部分教唆行为的独立成罪的例外规定是原则和例外的关系,或者说是一般法条或特别法条的关系。立法何以将这些原本属于共犯性质的教唆行为独立成罪,使之具有实行行为的性质呢?究其缘由,就在于立法者考虑到这类被教唆的行为一旦付诸实施,就会足以侵害重大法益,或者由于被教唆人单独实施这类行为时因未实际侵害法益而不构成犯罪,根据从属性说的立场也就缺乏处罚教唆者的理由,但基于法益保护的需要又有必要处罚这类教唆行为。尽管如此,但并不能因此就能简单地得出任何情形下的教唆行为就是实行行为的结论。同样地,刑法分则中将本来意义上的其他类型的非实行行为诸如预备行为、帮助行为予以实行行为化的情形也并不少见。例如,日本刑法将内乱、外患和杀人等八种本来意义上的预备行为在刑法分则中予以特别规定使之被提升为实行行为的性质;我国刑法将资助恐怖活动的行为、资敌罪的资助行为以及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帮助毁灭、伪造证据、协助组织卖淫的行为等等帮助行为予以实行行为化。但是,并不因为刑法分则的这些特别规定的存在,就可认为任何情形下的预备行为、帮助行为都具有实行行为性。否则,就犯了常识性概念的错误,其直接结果就是解构了教唆犯、帮助犯的概念。同时,此种见解亦有彻底动摇实行行为理论根基之虞。诚如我国权威刑法学论著指出:“复杂共同犯罪中有些幕后组织、策划、指挥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也不是犯罪的实行行为。因为这些行为虽然是共同犯罪行为的组成部分,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有些甚至大于实行行为的危害性,但是,它们对直接客体的侵犯,毕竟要通过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才能实现,由于这些行为对具体社会关系的威胁和侵害是间接的,不具有实行行为的本质属性。所以不能是实行行为。”(20)
(三)第29条第2款对非共犯的教唆犯独立处罚的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教唆行为具有实行行为性的法律根据
《李文》指出,在认定教唆行为为共犯行为的场合,对教唆者进行定罪处罚的直接依据是其教唆之罪,但是,这一根据本身即存在理论缺陷:如在被教唆者未实施犯罪的场合,根据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通说认为,这是关于教唆未遂的处罚规定。问题在于,作为一种停止犯罪形态,犯罪未遂必须以实行行为的着手为前提,在被教唆者未实施犯罪的情况下,承认教唆未遂,就意味着承认教唆行为的实行行为性,而这与教唆行为共犯性中认为教唆行为非实行性的观点是相悖的。(21)
在笔者看来,《李文》立足于关于第29条第2款的规定属于教唆未遂的通说这一前提(22),而主张教唆行为属于实行行为的见解似乎无懈可击。但问题在于,通说对第29条第2款所作的教唆未遂的解读本身是不无疑问的:首先,教唆未遂是以教唆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为前提,如前所述,教唆行为只是唆使他人产生犯意的行为,并不符合实行行为的构造。作为同实行犯协作、联动的共犯,其实行性从属于与其构成共同犯罪的正犯的实行行为。由此,教唆犯的着手应以被教唆者(正犯)开始实行其所教唆的罪为标准。但由于这种情形下的被教唆者实际上并未犯被教唆的罪,即便其实施了犯罪行为,也是与教唆犯的教唆行为不发生实质上的关联,由此,教唆犯的着手就无从谈起。其二,该条规定的处罚原则是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这同《刑法》第23条第2款关于未遂犯的“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理论上之所以得出《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的是教唆未遂的结论,还是缘于论者过于强调和重视教唆行为本身的反社会性,将教唆行为视作实行行为,从而混淆了教唆行为与实行行为的概念。实际上,只要承认着手是实行行为的着手,实行行为至少是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行为,就不会承认该款规定的是教唆未遂的问题。
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该如何看待《刑法》第29条第2款关于非共犯的教唆的规定呢?笔者以为,教唆犯并非是通过自己的行为侵害法益和实现犯罪的目的,而是通过被教唆者的实行行为来沟通自身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了实现犯罪的目的,教唆犯必定要选择合适的教唆对象和教唆行为方式,以便使对方产生犯意,进而推动犯罪的发展。显而易见,这种选择合适对象、制造犯罪实行者的行为,同行为人为了有效地实施犯罪而寻找犯罪同伴或者说勾结犯罪同伙,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可见,这种教唆对象的选择、教唆行为的实施就是为了实现犯罪目的而制造条件的预备行为。如最终因被教唆者没有实施所教唆的罪而使犯罪未能进一步地向前发展,毫无疑问这只能成立犯罪预备。对于这种犯罪预备行为,如侵害法益的程度轻微(如甲教唆乙去丙家盗窃,乙未置可否,表示违法的事情不干,或者乙当时应允,但后来反悔未去盗窃)时,完全可以以《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将之出罪,防止刑罚权的不当扩张,从而实现刑法的谦抑性价值和保障人权的机能。对于法益侵害程度严重而有必要动用刑罚时,也只需适用《刑法》关于处罚预备犯的“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而无须画蛇添足,另作“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由此,从立法论上看,第29条第2款的立法的合理性本身是不无疑问的,据此所做的“教唆行为本身就是实行行为,该款规定的情形属于教唆未遂”的解释也就理所当然地站不住脚了。这实际上反证了共犯从属性说的合理性,亦即,教唆行为在性质上是从属于同其构成共同犯罪的正犯的实行行为。
三、结论:共犯性是教唆行为的原则属性
作为犯罪论体系基石的实行行为,是由刑法分则各条文定型性规定的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的行为。从犯罪实施的进程来看,实行行为是与预备行为相区别的重要范畴,具有确立未遂成立起点的机能;从共犯的角度来分析,实行行为是区别正犯与共犯的基准。教唆行为作为实定法上的范畴,其究竟是属于实行行为抑或共犯行为,不宜一概而论,关键取决于这一教唆行为是否为刑法分则某种具体犯罪的类型性构成要件行为所包含:如果行为人实施的教唆行为未被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所包含,那么这一教唆行为就是在客观上对共同犯罪的实行和完成起着加担和促进作用的行为,其本身不可能对法益造成直接、现实的侵害,因之,应属共犯行为,构成犯罪时,应对教唆者以教唆犯论处,即应按照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处罚规定进行处罚。(23)第二,倘若教唆行为例外地被刑法分则定型性规定的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所包含的场合,此即意味着,本来属于教唆性质的教唆行为因特别规定而获得了实行行为的性质。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这一教唆行为就不再属于共犯意义上的教唆行为,对之应按照分则罪刑规范规定的罪名和法定刑予以定罪量刑。
注释:
①参见李凤梅:“教唆行为:实行行为抑或共犯行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期。
②[日]大谷实著:《刑法总论》(第3版),成文堂2006年版,第224页。
③[日]大谷实著:《刑法总论》(第3版),成文堂2006年版,第241、246页。
④[日]大谷实著:《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2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126页。
⑤参见[日]前田雅英著:《刑法总论讲义》(第4版),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第146页;[日]西田典之著:《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250页;[日]大谷实著:《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2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8-339页。
⑥高铭暄主编:《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⑦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445页。
⑧由于单纯捏造犯罪事实的行为侵犯法益危险性程度低,或者说尚未达到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故而可以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将之予以出罪。
⑨参见[日]前田雅英著:《刑法总论讲义》(第4版),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第146页。[日]西田典之著:《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250页。
⑩参见钱叶六著:《犯罪实行行为着手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页以下。
(11)参见钱叶六著:《犯罪实行行为着手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3页;何荣功著:《实行行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张亚平:“实行行为观念之提倡”,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2)姜伟著:《犯罪形态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13)参见[日]前田雅英著:《刑法总论讲义》(第4版),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第418页。
(14)参见陈兴良著:《共同犯罪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4-365页;赵秉志著:《犯罪未遂形态研究》(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7页。
(15)参见[日]小野清一郎著:《刑法概论》,法文社1956年版,第419页。
(16)参见李凤梅:“教唆行为:实行行为抑或共犯行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期。
(17)《刑法》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第29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前款规定的是教唆者与被教唆者构成共犯时处罚教唆犯的原则,后款规定的是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不构成共犯时处罚教唆犯的原则,理论上分别谓之为共犯的教唆犯和非共犯的教唆犯。
(18)关于这一点,后文将有进一步的研讨。
(19)参见李凤梅:“教唆行为:实行行为抑或共犯行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期。
(20)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82页。
(21)参见李凤梅:“教唆行为:实行行为抑或共犯行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期。
(22)通说将第29条第2款的规定解读为教唆未遂的主要理由有二:教唆犯的着手不以被教唆者着手犯罪为转移,只要教唆犯以言辞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教唆,就应视为教唆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因此,在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罪时,教唆犯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当然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未遂的特征,此其一。其二,刑法对于这种情况下的教唆犯罪明示和强调要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与刑法未遂犯处罚的规定相同,可见立法者把这种情况下的教唆犯视为未遂犯。参见高铭喧主编:《刑法专论》(上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页;赵秉志著:《犯罪未遂形态研究》(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页;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6页。
(23)当然,如果教唆者在实施教唆行为之后,又参与犯罪实行的,或者在教唆行为实施之前或者之后,同时又实施了组织行为的,那么就产生了教唆行为与实行行为或者教唆行为与组织行为的吸收关系,按照高度行为吸收低度行为的原则,应以实行行为或者组织行为等高度行为论科,宜认定为实行犯或者组织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