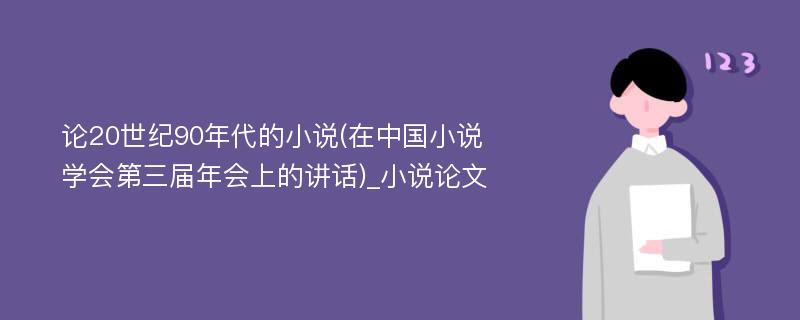
关于九十年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学会第三届年会上的讲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第三届论文,年会论文,中国论文,讲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深感自己老化,写作量是过去的三分之一,读书量是过去的五分之一,对当前的状况不太了解。汤吉夫先生要我谈谈对小说的看法,我就——作为一个读者——建议说我们讨论讨论90年代的小说罢。
为什么提出一个90年代的问题呢?是因为我认为90年代小说创作与过去很不一样。90年代长篇小说是热点,作品大量增加,七八十年代重点在中短篇小说上,如《班主任》、《神圣的使命》、《天云山传奇》等。从我个人来说,也是由中、短篇小说为主而转到以长篇小说创作为主的。90年代由中、短篇为主到以长篇小说为主的转变,反映了时代的变化。70年代后期我们面临着现实主义的回归,我觉得那是浪漫的现实主义的回归,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如《天云山传奇》,很浪漫。一个右派叫罗群,含冤二十载,故事是浪漫的,大家都痛定思痛,迎接新的生活。新的时期,对新的生活充满梦想、幻想,包括我本人写的《春之声》、《风筝飘带》都这样。我可以说说我写长篇和中短篇的不同感受。短篇是它找我,我写它,我写短篇从来没有计划,但有人有计划。有人在年初时和记者谈话就说我今年写七八个短篇。我从来没有计划,我常常比喻我写短篇就像守门员,当足球来的时候,我“梆”地一声顶回去。谌容也说过,短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生活的冲击从各方面带有现实感,当冲击变成小说题材时我抓住了它,虽然还没写出来。也许写出来用了五天、七天、十天,也可能一天,但是我掌握了它。写长篇是我找它,我要想想。是我找它,我总是掌握不住它,是它控制着我。我觉得从我个人经验来说,人们经过新时期的开始,经过浪漫的、多梦的、多感的阶段,经过了倾诉、喷发阶段以后,才会进入一个概括的、追思的、回溯的阶段,长篇才会多起来。但也不见得,有此一说就是了,一家之言,也可能有别的说法。顺便说一下,“90年代小说”这个说法,既是科学的又是不科学的。因为你考察任何一部作品总离不开空间和时间的坐标,离不开作者的境遇,知人论世嘛。但同时小说往往应该是超越的,离不开艺术之神、文化之母,是假作家之手留下来的痕迹。这是和90年代80年代70年代,甚至和你在北京在天津在青岛没有多大关系。有些作家我们很清楚他是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什么背景下写的作品,有的作家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却不影响我们欣赏他的作品。但是大体上这和环境有关系,当然和个人的创作阶段也有关系,包括一批年龄比我们小十五六岁的作家。我指的是这批知青作家,他们实际上是长篇创作的主力。包括王安忆、张炜、韩少功、张宇、余华,他们写的长篇非常多,而且很受瞩目。那么他们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由喷发的、诉说的阶段进入这样一个概括的、追溯的阶段?我不知道。
陆文夫跟我讲过,说他身体不太好,想好好写长篇,写来写去无非是写半个世纪一个人。“半个世纪”指时间跨度,“一个人”写他自己在这半个世纪之内种种的感受。冯宗璞也跟我讲过,她写的是更早一些的事,写抗日战争时期的事,写的是更老一些的知识分子。因为冯的年龄比我们大六七岁。我们这个年龄的好多人是这样。原来是知青的作家现在也进入了长篇创作高潮。
其次一个特点,现在长篇数量大为增加,样式也分化得非常厉害。有一个统计我看过,在文革前17年,长篇小说平均每年是10部,现在每年是500部至600部,平均每天都可以看到两部新长篇。长篇小说有一个特点,普遍销路比较大,经常发生全民争读一部长篇的热烈情况。比如说《红岩》,那时候是困难时期,我记得买书的人从王府井一排排到东单去。还有《野火春风斗古城》,电影正演着,大家却都争着买书看。还有《铁道游击队》、《李自成》、《创业史》、《红旗谱》、《红日》、《红岩》,还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那时写一个长篇就能买一个至两个院子。现在写八个长篇也甭想。文革开始时,我在小报上看到过,揭露“三名三高”,柳青写了《创业史》,得了一万五千元,当时一千元就可以买一个院子。
现在小说数量多了,而且式样也确实非常多。我想总有这么一些式样罢——我这是乱分类,而且是非常不合学理的,请高校的同志原谅我。比如有一类是艺术小说,他们追求艺术价值,在艺术上进行营造,试图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增光添彩。其中又有一部分向国际靠拢,比如向加西亚·马尔克斯学习。这位作家影响太大了,他为我们提供了土洋结合的道路,让你写最土的东西,然后让它具有洋的价值。我们一些作家对马尔克斯极佩服。当然在写到心里变态时又受卡夫卡的影响,在写到人道主义情感时,又受到艾特玛托夫的影响等等。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影响最大,许多作家作品都能看到受马尔克斯影响的痕迹,比如莫言谈到过他读马尔克斯作品时倾倒的情景。有的是向古的靠拢,往古的方面发展,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透出古色古香来,如历史小说,在销路上他们也特别成功,《曾国藩》、《康熙大帝》、《世纪晚钟》,这些历史小说之所以吸引人,是带有史鉴小说的特征,读的时候能够增加对国情的了解,以史为鉴,不是简单的类比、影射,而是讲道理,讲中国发展,权力运作,非常好看。它能增长智慧,增长人们对历史、社会、人生的了解。还有社会小说,突进、逼近社会中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社会小说有的是用了调侃的,有的是用古典方式来写的,比如王朔、刘震云的一些小说也是带有调侃的。有的是用古典方式来写的,比如《苍天在上》。这部小说写得非常古典,戏剧性,在写实方面不如其他一些作品,我将之统称为社会小说。还有一种也可称之为社会小说,就是写特区的企业家、靓女、中产阶级、白领、小资本家,他们不知今夕为何夕,不知该地为何地,但基本上是真实的。还有一些写私人生活的小说,最近我看到陈染的一篇文章,她非常反对人们将她的小说称作“私小说”。日本的“私”就是“我”,如果一个作家写的私小说就是作家自己的经历,这很可怕。如果再加点性描写,会更可怕。我曾在上一届小说学会年会上提出进行认知判断,再进行价值判断。再有就是最近热闹起来的社会问题小说,写农民、农村、乡镇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等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这是从小说的内容、风格上来说的。
从小说作者方面来说,现在变化也非常大,老作家没有停笔,新当红作家不断涌现。代与代之间差别比较明显,有些老前辈在作品中表现对人民革命光辉记忆的铸造,同时也隐约地透露出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担忧。有些50年AI写作作的作家,就是我这一代,在作品中更多的表现为对历史的超越,同时又传达出对历史走回头路的担忧。再往下一代人,更多的是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物质化、科学化、市场化作出批评,追求进一步接轨的环境,自然、大地、公正、终极等。再更年轻一点的作家,对写作没有这么大的激情,游戏性更多点。在如此多种多样的状况下,就没有举国捧读、举国称颂、举国掏手绢擦眼泪的作品出现。有位当司局长的朋友对我说,现在没有什么好作品出现,一本《青春之歌》也没有啊!在80年代初,邵荃麟在讨论我的《青春万岁》出版时就曾对我说:“王蒙同志啊,在我们国家出版长篇是大事情啊!”什么大事情,现在平均一天出两部长篇就是两个大事情,可你仔细看一些作品,显然得承认写得有现在的优点,可现在作品让大家交口称赞太难了。现在有的作品可以看出倾注了作家的激情、生命、语言和财富,思想和光辉,作家是拼了,事后又有几个朋友喜欢写几篇文章,印了一版8000册,又印了一版10000册,再印一版12000册,也就如此而已。这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就是五六十年代,人们的精神需求比较单纯、集中,我们提供的精神食粮也比较单纯集中。现在社会的精神需求多样了,花样多、情趣多、读者多,读者多,读者与读者口味更不同,更挑剔,需求多样化,歧义更多了,因此,在小说园地笔墨官司多得不得了。现在有时作家倾注了吃奶的力气,感觉很好,但称赞者也就那么几个,而且许多是熟面孔,说不准从哪里冒出了一冷枪,给你嘲弄两句。我最近去珠海,从精神生产想到物质生产。50年代出了为大家喜欢、我又非常喜欢的双面卡,60年代我才知道有一种料子叫的确良。从这点可看出当时物质消费也是单质的,集中的,而现在人们需求却是多质的,分散的。不管你作家写得如何好,人们就是不看,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或者他看了一点说看不下去,或者说就是不喜欢,你有啥办法?现在小说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过去一年出二十本不看没得可看,大家也是万众一心,“社会主义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山连着山海连着海”,歌也是一个调,“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那时出一个长篇是一个大事,一年抓10~20部长篇全民轰动,有些即便不太重要的长篇,销路和影响也是很大的,如《晋阳秋》、《苦菜花》,那影响多大啊!这都是60年代初期的,那是多么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啊,对于有着革命精神饥渴的人们是多大的满足啊!现在对文学作品多样又极挑剔的现象,我们还是缺少研究。在谈到这点时,我要补充一下,刚才提到的小说类别,还有一类就是更注意市场的小说,比如包括引进的。最近我看到上海的抽样调查,让读者选出他们最喜欢的作者。第一位是金庸,第二位是鲁迅,第三位是王朔。我进不去这个名次,但有一个调查让我安慰,把我算在编外。调查后边有个说明,说“还有很多人,琼瑶、三毛、席慕容、王蒙等”。金庸现象值得研究。原来人们说金庸的作品如何好看,而我不想再看,因为从小我把武侠小说看得太多了。后来三联送我一套金庸的作品,我看了觉得写得极好。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布老虎丛书”,这些作品也许没有太大的成就,但“布老虎”确实是做成了,它成功了。它要求三条,第一条,城市题材;第二条,给一个故事;第三条,给点理想,不让太消极了,给上面看也给老百姓看,老百姓不喜欢哭哭啼啼的,这现象值得研究。
除了时代特点外,还有超越时代的理论性。小说的歧义是因小说的特性所决定的,小说就是充满悖论的东西,它是虚构的又是真实的,是精英的又是通俗的。小说自古就是通俗的。在中国自古诗和散文是雅的,而小说是通俗的,小说不能没有人间烟火。它有自己的倾向又是含蓄的,小说的本身特性就造成歧义的可能。这是第一。第二,小说的价值观念是统一的还是分离的,是一种还是多种,还是有合有分的?比如你衡量布老虎丛书,衡量金庸的小说,衡量鲁迅的小说,那把尺子你能一样吗?如金庸小说,他不可能摆脱武侠小说的套子,而且写来写去他自己也重复。这套数本身是有局限性的,他能写到这个程度就算不错了,差不多是尽头了。把这套路写到这么精致,包含着真的和假的知识。为什么说假的知识?里面写新疆,但与新疆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由此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小说是否过剩?我们一年出700~800部长篇,看死了也看不完。我们各省都有几个文学刊物,整个社会力量养着刊物。我们许多作家是不需要找食的,找食的也有几个,王小波是一个,最近去世了;王朔是一个,最近走了,呆不住了。我们高等学校上课负担比外国少,这是笔墨官司多的原因之一,大家有较多的时间,互相之间就吵来吵去,吵吧!我去年五月初去英国介绍说我国一年出五六百部长篇,英国人很礼貌,点头,可吃饭时,他们说,中国一年出五六百部长篇,这不算多,你知道我们英国一年出多少呢?我们英国人少,我们英国人一年出一千部长篇小说。大部分都是商业化的,是满足一部分人需要的。过去《人民文学》是满足全体人民需要的,是人民就是读者,现在就不是,如广东的《佛山文艺》被认为是打工仔打工妹的刊物,发行很好,十几万份,二十几万份。如果每一种刊物,每一部小说都是以全民为对象,那就是多了。但每一个刊物每一部长篇的对象比较具体恐怕还可以,就像饭馆,饭馆很多,但都是面对不同需求、不同口味的消费对象开的。这些情况我们还都不太熟悉。小说创作的功能侧重也不同,这也没有互相贬低的必要,如你的小说侧重于宣传教育,这不是非常好吗?你的小说是侧重于对少年儿童普及科学知识历史知识,你的小说宣扬的更多的是一种理想,你的小说是高度精英化。因为也有这样的作家,我们也听到过这种传言,一些精英作家生怕自己的作品成为畅销书。当他的作品只卖到一千册,他觉得非常遗憾,卖到五千册他就感到满足,卖到一万册,他就表示再不能多卖了,再多卖的话我就要惭愧死了,我就要上吊了,害羞了,一万多人看你的书,你的书媚俗到了什么程度!所以作品的功能哪些是愉悦性的,哪些是商业性的,总得有啊。商业性可以为人所不齿。但是完全没有商业性又怎么办?商业性也是为人民服务之一种嘛。作为个人完全可以拒绝商业化,保持文学的矜持与清高;作为文学现象,却必然是多种类型的小说共存。还有探索性的,考据性的,学者型的,既然它分化成多种多样的,必然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那么在这些小说中,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什么?外来的影响是什么?因为任何一部小说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经过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积淀,经过几百年来的社会急剧变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沉淀,不能没有一点影响。有许多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或者可能是很有趣的。总而言之,90年代提供了一些新的情况,提供了一些新的问题。那是不是90年代的人文环境就已经非常市场化了呢?这个就又不是中国了。总而言之,90年代提供了很多新的文化新的技术,但如果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是后现代主义,科学主义,已经是科学主义控制了中国人,大家都崇拜技术,崇拜科学,这种认识又太超前了。在中国是现代多还是前现代多?起码前现代比后现代多得多。在中国现在是科学主义多,还是反科学迷信多?我看也是一样多,迷信科学和迷信迷信。科学是不能迷信的,因为对任何东西一旦成为迷信,它本身就变成了迷信。但是迷信科学比起迷信迷信来说是不是算是一个进步呢?比如说原来我相信算命,现在我不相信了。对于中国的人文环境,因为它是不同时代的东西。几千年前的东西和很新的东西都掺和在一块,也非常难分析。借一把刀砍,砍到这儿本来是砍得对的,又砍到别处去就又砍错了,不该砍的地方很可能又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讨论一下90年代的小说创作呀,还有文学与生活呀,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因为90年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带来小说创作上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出现了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新的契机,出现了某种分化和无序状态,给人们许多困惑。我没有什么固定的看法,我只有上边说的一些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