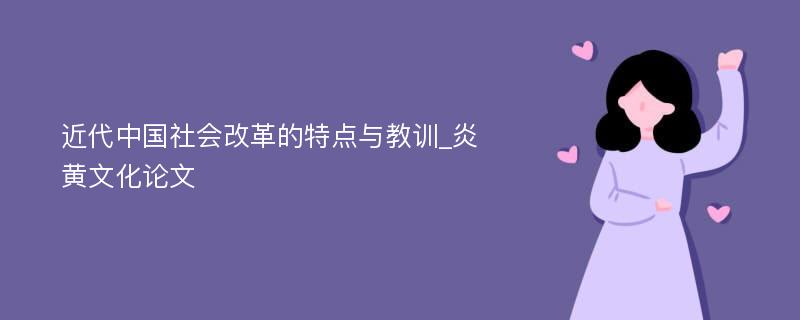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征及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教训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变革特征论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征,卓荦可纪者有三,其中之一为变革的快节奏。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生长在国门被强行洞开、处于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社会之中,国家遭屈辱、人民受奴役的可悲境遇,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情感。先进的知识层继承了古代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和承担“社会良心”责任的优良传统,自觉地肩负起历史的重任,“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苦苦寻觅救国救民的真理。
这种千帆并进的结果是,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很快会变成旧的社会思潮,而为更进者所取代。如维新思潮,流行的时间仅仅是从甲午到戊戌短短的数年;而革命思潮,也不过是在辛亥前后一段时间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当这两大思潮流行之时,社会主义思潮也静悄悄地步入中国,并在“五四”前后取代革命思潮,一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社会变革步伐之快,令人眼花缭乱。正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注:瞿秋白:《俄乡纪程》,转引自《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29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严复、康有为、章太炎等等叱咤风云的弄潮儿,他们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站在时代的前列,不久就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正如鲁迅所说:“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了。”(注:《趋时与复古》,《鲁迅全集》第5卷,第536页。)
与近代欧洲相经更能看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已经跨入快车道。以民主思想进程为例,欧洲从15世纪到18世纪共计经历了四个阶段:人文主义者对人的价值、尊严和个性解放的宣传;加尔文的民主、共和主张,鲍埃西等人的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格老秀斯、洛克等人的社会契约思想、分权说的产生,英国立宪政体的产生;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民主思想的激荡,法国民主政权的建立。上述内容在欧洲的传播及实现经历了300年,而在近代中国只用了80年。
社会变革的快节奏之所以产生,导源于先进知识层的性急心理。如康有为就曾说:“以我温带之地,千数百万之土,四万万之农、工、商更新而智之,其并驾于英、美而逾越于俄、日,可立待也。日本变法二十年而大成,吾民与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序》,《康有为全集》卷3。)性急心理作为近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反映了先进知识层心态的失衡与扭曲。
特征之二是变革的启动源来自于外部,并进而形成救亡与启蒙这一矛盾复合体。
世界各国在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过渡中,其变革分为原生型、次生型、殖民地型、感应型四种模式。原生型也即内生型,英、法为其代表;次生型即移民型,美国、加拿大为代表;殖民地型以拉美为代表;感应型以中国为代表。无论是原生型,还是次生型,乃至殖民地型,其共有的特点是西方式的价值观念、工业文明乃该国的内在因素,而感应型则是例外。
中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后发展型的前现代化封建国家,在尚未接触过近代西方文明这一异质文明的情况下,突如其来、也是被迫面对这咄咄逼人的挑战,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调适、回应应运而生,并引起对传统社会形态的整合,亦即社会变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启动源来自于外部,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在我国的微弱状态,使内在的变革要求只能是汪洋中的一叶小舟。
当然,以西方剑桥学派为代表而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即外因决定论。西方冲击固然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启动源,但是如果我国内部没有走向现代化的因子,其结果也注定不会成功。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西方的影响,中国也会缓慢地步入资本主义。外在的影响只是起了催化的作用,能不能化合取决于主体而非客体。从某种意义上讲,“冲击反应模式”失之片面。70年代以后,Paul A.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以往学者在运用“冲击反应模式”中出现的过于简单化的倾向,就进行了相当系统的批评。
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题之一是救亡图存,此外则为发展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这一主题不能单纯从经济形态上去理解,还应融入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用“启蒙”来代表似更为贴切。启蒙分经济上的启蒙,即由封建经济形态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即狭义上的发展资本主义;也有文化上的启蒙,即向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发起挑战。
救亡与启蒙作为矛盾本身的一个对子,其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又有相互冲突、对立的一面,在近代中国,由于来自西方社会的外在威慑一直存在,且日益加剧,以至于救亡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国人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西方入侵所造成的深深的危机感,显然加大了国人的心理压力。相对而言,启蒙工作因处于次要地位而明显滞后,因此,到了“五四”时期,知识层只好又回过头来补课,进行文化上的启蒙。而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外国资本的竞争,从来就没有一个宽松的环境,纵向地看是发展了,但横向看来,不发展的一面就暴露无疑。
特征之三是传统文化在近代变革中所起作用总体看来是负面效应较大,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综合反应能力,近代社会变革的文化背景极为不利。
综合反应能力是指传统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运用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念、政体结构与经济能力与西方挑战的外部冲击作出有效回应与自我调适的能力,即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政治精英,能否相对准确地对外来挑战的信息作出客观的判断与认识,能否及时有效地动员原有的各种人力、物力与财力等各种社会与经济资源来应付外来的威胁,能否成功及时地对传统政治体制进行自我更新的变革以适应外来的挑战(注: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与日本相比,中国的综合反应能力极差,这其中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传统文化步入近代以后的负面效应则是最基本的。
古代华夏文明居于世界前列,在世界文明史上堪称奇迹。但是,在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经济,几千年来持续的是内向型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格局,生产工具、技术一仍其旧,人们的经济观念核心乃重农抑商、重本轻末,资本主义萌芽难以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中发展壮大,只能自生自灭,成为千年不变的社会体系的补充。政治上,日趋完善、严密的中央集权只是发挥着稳定功能,这一顽石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的窒息一切的稳定性,扼杀了政治制度中的革新功能。思想上,人们为圣贤古训、祖宗成法所束缚,难以逾越。长期缺乏优于本位文化的异质文化的客观现实,巩固、增强并进而形成中国人以本位为中心的内聚意识,这种观念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土壤中,根深蒂固,流被四泽,几乎牢不可破。尤其是“夷夏之辨”的世界观,严重阻碍着我国汲取异质文明,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儒家文化到了封建社会晚期,不仅起着一种伦理功能的作用,而且具有宗教功能,儒家文化日趋宗教化。一层不变的经济,僵化的制度,保守的观念及封闭心态,使得我们难以承认自己的落后,需要借鉴异质文化而改塑自己。费正清说:“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注:《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为炎黄子孙所津津乐道、引以为荣的传统文化,为什么在中国步入近代以后难以对社会变革、进步发挥积极的作用?原因即在于,在社会进化的每一个时期,首先直接起作用的,乃是最切近的前一阶段的条件基础和运动惯性。对于当时的中国,要克服沉沦的惯性,改变僵固的定势,显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二、变革教训论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结果无疑是失败了,虽然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封建帝制的终结等,但这无助于改变总体上的不成功。论及变革失败的教训,荦荦大端者有三:
教训之一是变革必须循序渐进,深入细致,不能奢望一蹴而就。
近代国人在中西大碰撞中,出于富国强兵的良好愿望,而产生了强烈的超越意识。超越是什么含义呢?超越就是超过西方。先进的中国人并未用“超越”这个词,但类似的词语如“制夷”、“驭夷”、“驾乎其上”、“制胜”、“并立”、“争雄”、“并驾”、“问鼎西洋”、“雄视五洲”等,则不胜枚举。如近代中国变革之父魏源,他之所以编撰《海国图志》,其目的就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注:魏源:《海国图志·大西欧罗巴各国总叙》。)。郑观应也说:“诚能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析,译出华文,颁之天下各书院,俾人人得学之,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竭其聪明之才,何难驾西人而上之哉!”(注:《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页。)
超越意识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由此引发的情绪急躁、行为冒进及急功近利。法国史学家高第说:维新派的最大错误就是在太短的一个时期内使中国全然改观,要同时把所有的政权机构都抓在手里,要一举而肃清所有的弊端;维新派的计划太轻率了,太危险了,皇帝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以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9年吃的东西,不顾他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3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这样它就暂时被扼杀了。(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63-165页。)
急功冒进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变革极不深入。以20世纪初十年为例,1900-1902年思想界的主流为改良派的民权思潮,1903-1906年是革命民主思潮的天下,1907年以后,无政府主义思潮又风行一时,十年之中,议题三换,发展不可谓不快,革新势力不可谓不活跃,但是,透过繁荣的表象,即可发现不深入的劣根。西方几百年发展起来的各种主张、认识,像压缩饼干一样被挤压在一起,由各个不同的派别反映出来,洛克、卢梭、克鲁泡特金被请到一起来进行大混战,这种场景看上去蔚为壮观,绚丽多彩,但实际上什么思想也没有真正扎根。浮光掠影、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式的变革,其结果只能是在社会需要时,一切从头再来。一个拥有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度要过渡到民主阶段,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到位的,而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方能完成。将外国的民主模式强加给中国,而缺乏对政治民主化阶段性的深刻认识,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犯的错误。动机本身是美好的、良善的、崇高的,但结果却出人意表,真可谓是“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注:马勇:《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教训之二是政治体制变革应与经济发展水平、民众教育水平等相适应。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人的思想深处,就潜滋暗长着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欣羡与对专制制度的不满。林则徐在《四洲志》中道:美国“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合议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洵谋佥同。”魏源也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比之中国,可谓又“公”又“周”,尽善尽美。(注:魏源:《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三八。)他还称瑞士为“西土之桃花源”。(注:魏源:《大西洋瑞士国》,《海国图志》百卷本,卷四七。)徐继畬称打了天下而不做皇帝的华盛顿为“异人”,“几于天下为公”,像尧舜一样了不起(注:徐继畬:《瀛环考略》卷下,台湾文海出版社手稿影印本,第210页。)。将专制制度改造成民主制度,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共和而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要付诸实践,则不合时宜,因为当时我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起步。
到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在中国化为了现实,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它的诞生,决非瓜熟蒂落,而是一种人为的结果,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辛亥革命乃一早产儿。
从经济角度看,作为新的因素的资本主义还处于幼年时期,甲午战前各种近代企业只有72家,资本额2000万元,还不及《金陵条约》中一次赔款多。这些企业中的工人人数不过5万,只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万分之一点二五。甲午战后,资本主义经济虽有长足进步,但在强大的封建经济面前,仍微乎其微。就国民文化教育水平而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曾说:“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4页。)它在晚年一再抱怨国人民智低下,期望以改造国民性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甚至专门著成《民权初步》,从如何集会、如何选举等常识入手,“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4页。)。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在1917年指出:“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注:陈独秀:《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卷三,第3号。)鲁迅在其名著《阿Q正传》中塑造了农民阿Q的形象,他说:“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他还说:“柿油党”“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注:鲁迅:《〈阿Q正传〉的正因》,《鲁迅全集》第3卷。)Ernest P.Young也著文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一般民众”对于民主“不是毫无所知,就是漠不关心。”(注:Ernest P.Young:《现代的保守主义者——洪宪帝制》,《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第241页。)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帝制的影响太深了。士绅阶层饱受数千年专制和那些赋予历史实质意义、列举不尽的圣王英雄、帝室功勋、劣主昏君诸般故事的熏陶,所以,其帝制意识并未被新近接触的西方共和模式的知识所取代,只是被压抑下去了。至于一般民众,帝制的声歌、故事根植在他们的文化中,连压抑的情况都不存在,数千年的历史积淀而成的皇权心态,辛亥革命并没有革去,康有为说:“共和虽美,民治虽正,而中国数千年未之行之,四万万人士未之知之,从瞽论日,冥行擿埴,吾虑其错行而颠坠也。”(注:康有为:《中国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9页。)这确非寻常之论。
一种体制的产生与运行,是由当时社会的需要决定的。政治体制变革的滞后固不足取,但超前推行也是行不通的,正所谓欲速则不达。
教训之三是领导变革的权力中枢始终未能健全,以致未能击灭反变革势力而推行全方位的革新。
要在社会上推行变革,就必须有担负这一任务的权力中枢的出现。鸦片战争后我国最早产生变革思想的先进人物来自知识界,而非执政的官僚集团,而且人数较少,难以形成一股势力,并发展自己的同盟军,将变革主张付诸实施。林则徐虽然是高级官员,但并不得志,他更多的是作为思想界的人物为我们所认识。
当然,鸦片战争作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变,它对我国以道光皇帝为首的权力中枢,确实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力,战后的“小洋务”的出笼就颇说明问题。但是,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的是“官僚政治”,哈罗德·拉斯基在1930年撰写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将其界定为:“控制权完全操纵在官吏手里,致使他们的权力危及平民百姓的自由。”“这样一种政治体制的特征是迷恋衙门陈规,循规蹈矩而不知变通,决策拖拉,不愿动手试验。”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肯定了哈罗德·拉斯基的观点。(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948年版,第2页。)这种缺乏弹性的权力中枢是难以担负起领导社会变革的艰巨任务的。
应该说,近代中国权力集团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划分不少的派系,如由于政治主张不同,就产生了帝党、后党、洋务派、守旧派、清流派等,晚清重大社会变革如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之所以得以推行,起因即在于此。西方列强的入侵所引发的浓重的危机感,使得权力集团发生内哄、崩裂,深受危机感焦灼情绪煎熬的革新派与坚持传统模式、文化信条的守旧派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冲突与对峙。前者力图以激进的方式重组政治结构与文化价值,后者则希望以传统的儒家教义来维系人心,以阻击西方文明的渗透、列强的侵略,人们从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变革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治两极化这一现象。虽然,在两极派别政治主张不同的表面,笼罩着的是强烈的权力之争,居于两极之间、左右摇摆的关键人物——慈禧太后,竭尽权力制衡之能事。强大的保守势力的长期存在,并且像滚雪球那样成了足以阻止改革的巨大力量,使权力中枢领导变革的任务难以完成。
社会变革首先是人的改变,长远地看,人的素质提高是社会改革走向成功的关键。尽管历史已经证明,顺应历史改革发展方向的乃时代的弄潮儿,反之则成为历史发展的惰性力量,必将为历史所淘汰。但是,在某些特定时期,弄潮儿也并非时代的骄子,甚至会成为国殇的祭品、牺牲品,成为为后人缅怀、同情的人物。社会改革如果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是全面的、全方位的,而非局部的、枝节的,必须是“大变”,而非“小变”。由于守旧派的阻碍,使得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处于无序、无计划的状态,这样,失败的结果就变得十分的自然了。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海国图志论文; 康有为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