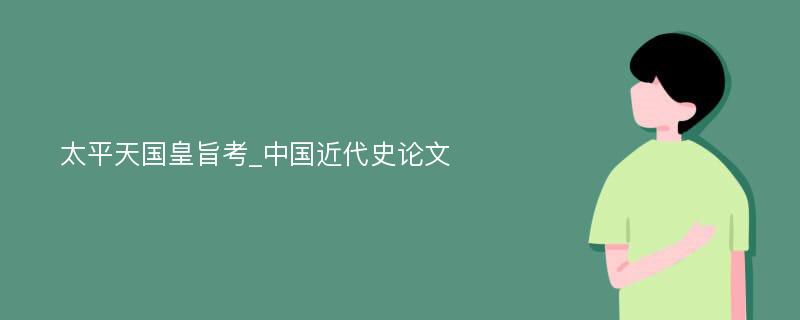
太平天国诏书衙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诏书论文,衙考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诏书衙是太平天国的一个重要文书机构,但有关它的一系列问题,如成立时间、负责人、职能等等,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而有些问题,史籍中还出现了一些错误记载。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太平天国前期权力配置微妙变化的过程。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呈献此文,以求教于史界同仁。
一
关于太平天国的“诏书”一词,一些专家学者作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和探讨(注:参见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第2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605-1606页;郭毅生著《太平天国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238页;史式著《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3-244页;史式著《太平天国词语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王庆成著《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24页。)。他们的观点和解释概括起来就是,认为诏书是太平天国某种级别或某种类型或某种性质的文书的名称。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毋庸讳言,这些观点和解释又是不全面的。长期以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忽视了一个太平天国文书机构——诏书衙的存在。《太平天国大辞典》、《太平天国词语汇释》都未有“诏书衙”条目;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虽提到“诏书衙”,但未展开研究;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增订本)、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对“诏书衙”稍有涉及,但不深入(注:参见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2-143、440页;又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第143页。);其他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者都很少注意到对诏书衙进行研究,由此导致了对“诏书”一词解释的不全面。
史料关于诏书衙的记载较多,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涤浮道人《金陵杂记》、佚名《粤逆纪略》、胡恩燮《患难一家言》均有零星记载,而张德坚《贼情汇纂》的记载达8处之多(注: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7-58、67、101、114、126、127、247、328页。)。关于诏书衙成立的时间,《贼情汇纂》有粗略的表述:“伪地官副丞相黄再兴……辛亥二月升卒长,因开功折明晰,洪贼知其能写字,令入诏书衙编纂伪诏书。壬子十月在长沙,诏书编成,以功升左史,职同将军……”(注:《太平天国》第3册,第57-58页。)
辛亥二月洪秀全令黄再兴进入诏书衙编纂太平天国诏书,这一历史事实可以表明,诏书衙基本上是一个文书机构,“辛亥二月”即1851年3月时已经存在。因此,它的成立时间起码不晚于1851年3月。此时当属太平军移营大湟江口时期。这一时期,太平军先后取得了牛排岭之役的胜利和灵湖大捷(或称三里圩大捷)的战绩,洪秀全趁灵湖大捷之机,在武宣东乡“登极”(注:饶任坤等:《天国兴亡》,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洪秀全为鼓励太平军将士英勇杀敌,从一开始就要求各军记载将士在作战中的表现,作为日后论功行赏的依据,为此洪秀全还于1851年11月17日特地颁布了《令各军记功记罪诏》(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页。)黄再兴身为卒长,负有此责,他可能就是在记载这些战斗中立功人员的表现时得到洪秀全的赏识,并被派入诏书衙编纂诏书的。论者或谓,太平天国不可能如此之早就成立了诏书衙之类的文书机构。笔者以为,黄再兴的升职历程并非孤证。太平天国的另一文书机构——诏命衙成立也较早,甚至在诏书衙成立之前,可为旁证。何震川的升职历程即证明了这一点:《贼情汇纂》载,“伪夏官正丞相何震川……初为广西诸生,曾应北闱乡试。庚戌年洪逆倡乱,被胁入伙,一家二十二口,失散殆尽,仅剩一弟一侄,并震川三人。初封副典诏命,职同将军,掌缮写伪谕。”(注:《太平天国》第3册,第59-60页。)这则资料中两次出现“初”字,从资料的前后文来看,“初封副典诏命”之“初”当指庚戌年即1850年何震川参加起义之“初”,也就是说,有可能在1850年洪秀全等人就成立了以典诏命为负责人的诏命衙。由此可见,诏书衙和诏命衙都属于成立较早的文书机构,它们是为洪秀全等人开展宣传活动服务的。在辛亥二月以前,洪秀全等人有两次重大的政治活动,即金田起义和东乡登极,诏书衙极有可能就成立于这两次重大的政治活动之时。因为,一方面,这两次重大的政治活动都意味着洪秀全地位和身份的变化,而成立诏书衙之类的文书机构,是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另一方面,伴随这两次重大政治活动而来的必然是大量的文书工作和宣传活动,成立这些文书机构也是太平天国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需要。
诏书衙在成立以后随太平军转战各地,并在洪秀全左右从事文书工作。1851年3月至1852年12月,黄再兴就在诏书衙,随太平军从武宣转战到长沙,并一直编纂诏书。不仅如此,诏书衙还随太平军从长沙转战到南京。据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载,诏书衙到南京后设在慧圆庵(注:参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618页。)。因此,太平天国确实存在着诏书衙这一文书机构。
按太平天国文书机构的命名原则,文书机构及其负责人的官职,都是以其所从事的工作来命名的。如通赞之于通赞衙,引赞之于引赞衙,承宣之于承宣衙,典诏命之于诏命衙,典镌刻之于镌刻衙,左史之于左史衙,右史之于右史衙,提报之于提报衙,疏附之于疏附衙,等等(注:参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37页。)。因此,根据诏书衙确实存在这一历史事实,我们有理由认为,诏书不仅是太平天国的一种文书名称,而且也是太平天国的一种文书官职,诏书即为诏书衙的负责人。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载:“不肯作诏书,文人之名无其徒;不肯当圣兵,武人之徒无其名。”(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732页。)这首乐府诗至少表明诏书与圣兵一样,是某种职业或身份,而不止是太平天国的文书名称。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在记载太平天国官职和机构时,将诏书紧接在正副典诏命之后,对两者的介绍内容都可分为对应的三部分:正副典诏命和诏书的任职者来源、职能范围及其衙门所在地。很显然,诏书和正副典诏命一样,是一种文书官职(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18页。)。《金陵杂记》还进一步记载:“(在丞相、检点、指挥)以下又有将军侍卫等伪职,而侍卫伪名甚多,按照干支节气称立名目,故伪侍卫之职,计有六七十人,皆居洪逆巢穴前后……其余仍有伪典诏命正副各一人,伪诏书、伪宣诏、伪国医、伪朝仪、伪引赞、伪通赞、伪绣锦各名目。”(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12页。)这就更明白无误地确认,诏书和其他官职一样,属于太平天国的一种朝内官职。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也有类似的记载:“天贼伪府,有伪侍卫九十六名,亦能带兵,职同伪检点……伪左右史,伪侍臣,均职同伪检点,伪朝仪,伪诏书,伪诏命,均职同伪指挥。”(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57页。)不仅如此,谢介鹤还记录了一些担任包括诏书在内的重要文书官职的具体人物,如殿前诏书傅少阶和胡仁魁、诏命刘盛培、殿前左史赖汉光、殿前右史邓辅廷,等等(注:参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677页。)。由谢介鹤的记载可知,诏书的官品为职同指挥,它和诏命、左史、右史一样,都是直接为天王服务的朝内文书职官,故可前加“殿前”字样。
据张德坚介绍,黄再兴在进入诏书衙前是卒长,而在进入诏书衙的一年零九个月后升为左史,职同将军,我们不知道他在诏书衙中担任何职。应该指出的是,黄再兴从卒长迁为左史,越级太多,他在诏书衙中可能是担任了某种重要的官职,极有可能就是诏书衙的负责人,即诏书。左史在1852年11-12月时是职同将军,但其地位在不断提高,到后来,左史是越过职同指挥而职同检点的。这一点,张德坚和谢介鹤的记载都是一样的。如按左史地位提高的速度,诏书在1852年11-12月时当职同总制。诏书与典诏命后来的官品均为职同指挥,而何震川最初任典诏命时是职同将军的,按理诏书最初的官品也当职同将军。但黄再兴在1852年11-12月时由诏书升任职同将军的左史,所以,诏书最初的官品当为职同总制,还不可能职同将军。如果黄再兴在诏书衙中担任诏书,负责诏书衙的工作,诏书编成,自是他的劳绩,升官非他莫属,而从职同总制的诏书升为职同将军的左史也比较正常,就不存在什么越级太多的问题了。
在诏书衙中,除有诏书负责全衙的工作外,还有协理协助诏书。李寿春就曾担任过诏书衙协理,据张德坚《贼情汇纂》载:“伪殿前丞相东殿吏部一尚书李寿春……粗通文墨,颇有心计。初为诏书衙协理。”(注:《太平天国》第3册,第67页。)那么,在诏书衙工作的是些什么人呢?《贼情汇纂》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论述太平天国招贤制度的社会影响时指出:(部分知识阶层响应太平天国的招贤榜)“然所至之地,惟医卜星相,稍知字义,及乡俗浅学、市井狷才、江湖落魄、生计无资者,赴其招为一时衣食计,既至江宁,皆使入诏书衙,任以佣书之役,或徒困辱之,终不得美职。”(注:《太平天国》第3册,第114页。)应当说,在诏书衙工作的都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识阶层,“终不得美职”正好反映了他们长期在诏书衙工作的历史实际。这些人在诏书衙干些什么工作呢?也就是说,诏书衙有哪些职能呢?除前述负责编纂诏书外,诏书衙还有以下职能:
第一,负责为太平天国各部门挖掘和培养文书人员。《金陵癸甲纪事略》载:“贼不识字,传伪令:凡读书识字者,悉赴伪诏书,否则斩,搜出匿者同罪,乃得数百人,使为诗及对,又试以伪示,合贼式者,分入各贼馆为书使,亦不打仗。”(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54页。)由于诏书是负责诏书衙工作的,因此,人们还常用它来代指诏书衙,正如一些地主阶级文人知识分子用典诏命代指诏命衙、用典镌刻代指镌刻衙一样。很明显,这里的所谓“伪诏书”不是指太平天国的文书名称,而是代指诏书衙。
第二,负责管理太平天国的官册、兵册和家册等册籍簿本。张德坚对太平天国家册和兵册的介绍表明,诏书衙是太平天国管理家册和兵册的最高档案机构。他的记载说:“伪兵册,每一两司马造一本,呈本管卒长。每卒长合四两司马兵册,汇造一本,呈本管旅帅。每旅帅合五卒长兵册,汇造一本,呈本管师帅。每师帅合五旅帅兵册,汇造一本,呈本管军帅。每军帅合五师帅兵册,汇造一样四本,分送本管监军总制将军,及伪诏书衙。如有逃走增添,随时改造,节节呈送。”(注:《太平天国》第3册,第126页。)“伪家册,每军自军帅始,至伍卒止,人各一页,亦由两司马造送,层层汇转,如伪兵册之制。各军典官所属,亦造兵册家册,由各典官迳送本管总制,总制汇造送伪诏书衙。”(注:《太平天国》第3册,第127页。)涤浮道人《金陵杂记》有关诏书衙的记载也表明,其职能之一为管理家册和兵册:“贼掳得两广两湖稍知文字者为伪诏书,又掳胁各处能写字者为其抄写。逆等并掳得男女名册,月月抄写,在逆等以为名已入册,无处可逃,然逃者愈众,听其注册,人数既多,亦无处报查,贼营之多寡虚实,此馆按月皆有总数。”(注:参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618页。)因此,诏书衙负责管理家册和兵册当毋庸置疑。据胡恩燮《患难一家言》载,张继庚因图谋叛乱被太平天国逮捕,在被审讯的过程中,他企图进一步施展挑拨离间的诡计,使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他向当时负责审讯的胡元炜索要太平天国的名册,“而诏书衙靳不发”(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353-354页。)。可见,诏书衙对张继庚的要求是有一定警惕性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张继庚所要的“名册”是官册,还是一般的兵册和家册呢?罗尔纲先生认为张继庚所要的名册即是官册(注: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4册,第2689-2691页。)。另据《金陵张炳垣先生举义文存》之卷首《事实》载:“继庚欲剪其心腹死党,使自相屠戮,佯曰:‘我受刑甚惫,不能尽记,得尔官册,则可一一指’。册至,每指一人,贼辄杀之,横尸于东门者三十五人。”(注: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4册,第2703-2704页。)罗先生所见正确。可初步断定,诏书衙也是一个管理太平天国官册的机构。
第三,诏书衙还是一个为知识分子提供学习机会的场所。《贼情汇纂》载:“癸丑七月,安徽望江县伪军帅禀奏保荐望江县生员龙凤翴有安邦定国之才,龙凤翴偕其父至江宁上书洪逆,不下数万言,内引周武、汉高为比,狂悖已极。洪逆批数字曰:‘周武、刘邦是朕前步先锋,卿知否?’龙凤翴不解所谓。旋送入诏书衙学习,并未擢授伪职(考伪诏书稿及程奉璜说)”(注:《太平天国》第3册,第328页。)。关于龙凤翴上书太平天国之事,佚名《粤逆纪略》亦有记载:“龙凤翴,望江人也,为贼划策,上书数千言,大约劝其勿浪战,婴城固守,以老我师,分股出掠,以牵我势,用安庆为门户,以窥江西。书上,授伪承宣职。”(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39页。)笔者以为,这两处不同的记载并不矛盾,龙凤翴的两次上书内容不同,而数万言上书在前,数千言上书则可能是他进入诏书衙学习后的又一次上书。因此,太平天国也改变了当初对他的态度,并授予官职。
第四,初期与诏命衙分工负责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诏书衙负责天试文科,而诏命衙负责天试武科与东试(注:关于诏命衙负责天试武科与东试的情况参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112、113页与《太平天国史》第2册,第1305页。)。佚名《粤逆纪略》载:“贼设诏书衙,令通文者就试,听候录取,其考试题目皆伪书中字句,取中则勒带行李到馆歇宿,并令出城抬米,就试者大半散去,余仅六十余人,以为抬米外无苦差矣,乃忽传令,威逼上船充当贼兵,一时文人无可如何,含泪而去,自是无就试者。”(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33页。)
由此看来,诏书衙的职能较多,它既是一个文案、秘书机构,也是一个教育、培训机构,同时还是一个档案机构;而诏书不仅是太平天国的一种文书名称,也是太平天国的一种文书官职,它有时还用来代指诏书衙。
二
关于诏书衙的负责人,张德坚的《贼情汇纂》有不同的记载,他指出:“伪左右史正副共四人,主记事记言,如古制……朝内疏附二人,题报二人,主接递文报。典簿书正副共四人,即伪诏书衙。典诏命正副二人,主缮写伪诏旨。宣诏书正副又正又副共四人,主收发伪书。”(注:《太平天国》第3册,第101页。)从张德坚的记载来看,诏书衙的负责人又应当是典簿书,这就与笔者前文的分析相矛盾。但张德坚的这段记载决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所提到的左右史、朝内疏附、典诏命、宣诏书等都有明确的职掌,惟独典簿书没有明确的职掌,只留下了令人感到困惑的“典簿书正副共四人,即伪诏书衙”的记载,而关于诏书衙的职掌,也没有明确的说明。论者或谓“典簿书正副四人,即诏书衙”系《贼情汇纂》排版时的遗漏,但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因为张德坚《贼情汇纂》的太平天国职官表里根本就没有诏书这一官职。如按太平天国文书机构的命名原则,典簿书所掌管的应该是称为“簿书衙”的机构,也就是说,典簿书当为簿书衙的负责人。事实上,太平天国存在着这一机构,张德坚的《贼情汇纂》有二处提到簿书衙,其中一处出现在张德坚抄录的东王杨秀清命黄再兴出师湖北时发给他的将凭中:“兹蒙天父天兄大开天恩,本军师在朝奏天王旨准,特命地官副丞相黄再兴前赴湖北地方,扫灭妖魔,抚安良善,恐军中兵士以及该统下人等有不遵条命任意犯科者,许尔佐将审实口供,将该犯先行斩首,游营示众,再将所犯情由粘供具禀回朝,候本军师详核定拟,转告簿书衙将该犯官册除名,以昭慎重。”(注:《太平天国》第3册,第199页。)东王命黄再兴出师湖北,时在甲寅六月(注:参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58页。),可以断言两点:一是直至甲寅六月,簿书衙的机构仍然存在,或者说,至甲寅六月,簿书衙的机构已经存在了;二是簿书衙的职能之一为管理“官册”。另据张德坚《贼情汇纂》载,簿书衙还负责一般家册和兵册的管理:“贼兵卒有兵册、家册,每月终送簿书衙稽查人数。如有逃人,下月造册,即将其人名下写三更二字,初甚不解。既而访知系杨贼诡称天父说过变妖之人谓之三更逃黑夜,并造言曰:‘任尔三更逃黑夜,难逃天父眼睁睁’(考自伪文告)”(注:《太平天国》第3册,第317页。)。这则资料中张德坚“考自伪文告”的注脚似乎更为有力地证明了簿书衙管理家册、兵册的真实性。由此看来,簿书衙是太平天国管理官册、家册、兵册等簿本册籍的稽查、核实机构。诚如前述,诏书衙也负有此责。两* 个机构具有同一职能,而作为这两个机构负责人的典簿书与诏书的官品又均为职同指挥(注:按:《太平天国》第3册第87页《职同指挥伪官名目十三·伪天朝各典官》里有“典簿书四人”。)。这就极易使人们将簿书衙与诏书衙混淆起来。
据佚名《粤逆纪略》载,簿书衙还有“主批文本”的职能,不能说他的记载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他关于通赞衙、引赞衙、承宣衙、参护衙、疏附衙、左史衙、右史衙、镌刻衙、诏命衙职能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的(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34页。)。但是,关于“主批文本”这一职能,张德坚《贼情汇纂》的记载与佚名《粤逆纪略》也是不一样的:“伪批式,凡禀事由伪丞相拟批送进,准行发出交伪尚书录批粘于首逆头门。”“凡其下具禀奏杨逆阅后发出,交伪丞相拟批,伪尚书誊批,伪侯以次则由所属六部书六部掌书拟批誊批,然所批字不誊于原禀之后,故另有此式(指太平天国批示格式——笔者注),既誊之后,则张贴伪署门首,间有用封筒递回者。”(注:《太平天国》第3册,第200页。)也就是说,批复文本的职能是由丞相、各殿尚书、六部书以及六部掌书分工负责的,而非由簿书衙负责。事实上,各殿批复文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曾水源是“凡东贼事代批代行,每晨见东贼议事者”(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72页。),黄再兴是“凡翼贼事代批代行、每日见翼贼议事者”(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73页。),而罗秘芬则是“凡北贼事代批代行、每晨见北贼议事者”(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73页。)。东殿文书的批判权在一段时间内则又是由女簿书负责的,谢介鹤的《金陵癸甲纪事略》载:“女簿书,东贼逼取民女识字者充之,以代已批判。”(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63页。)实际的操作就是“意出东贼,批由女簿书”(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67页。)。关于“主批文本”职能的不同记载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与以上问题相关的是,太平天国不仅存在典簿书的官职,而且还存在簿书的官职。曾水源于壬子十二月始任东殿簿书,李寿春于癸丑二月始任东殿簿书,李寿晖于癸丑三月始任东殿簿书,卢贤拔于癸丑七月始任东殿簿书,黄启芳于壬子八月在长沙始任北殿簿书,罗秘芬于壬子十二月始任北殿簿书,刘承芳自至江宁始封翼殿尚书(注:参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53、57-60、64、67-68页。)。不仅如此,在东殿还有女簿书,或称内簿书,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载:“贼目禀事(于东王),交女伪簿书,盖逼取民女通文墨者为之,计数十人”(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67页。)。所有这些都说明从壬子年在长沙时起,到刚进南京城时,各殿设簿书官职是比较普遍的。关于簿书,据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载:“杨韦石等诸逆统下伪职名目,如伪东、北殿丞相(各一贼,皆广西人,为贼主办文案)、伪东、翼、北殿簿书(不知若干人,两广两湖之贼,归伪东、北丞相所系亦系写贼文者)、伪左右仆射、伪东、翼、北承宣(皆两广贼,能操土音登答传话者)……以上除裁缝簿书外,余皆首逆等亲信之贼也。”(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20页。)涤浮道人载簿书非诸王亲信恐非真实,曾水源和罗秘芬都曾任职簿书,但他们在东王府和北王府里的地位较高,与东王和北王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则资料的重要性在于,它指出了簿书为各殿丞相所属,是各殿丞相的文书人员。因此,簿书的命运应当与各殿丞相的命运息息相关。
丞相为太平天国的最高官职,有恩赏丞相(在外带兵作战称殿前丞相)、平胡丞相和六官丞相三种类型,而在同职官中,没有职同丞相,职同检点为最高的同职官,因此,丞相这一官职是比较特殊的,对天王和太平天国来说,具有某种不同一般的意义,往往作为最高奖赏(注:参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89页的《东王杨秀清通令朝内军中人等禁酒诰谕》与第114页的《北王韦昌辉招延良医诫谕》。)。既然丞相的地位如此尊崇,那么,对诸王来说,特别是对东王来说,在自己的王府里亦应当有丞相官职的设置。但东王位居人臣,又不能僭越而设置六官丞相,只能设置左右丞相2人,其余诸王也只能设丞相1人,以示东王低于天王而高于其余诸王的等级地位。揆诸现存文献,东殿丞相曾由曾水源与曾钊扬担任过,癸丑四月,曾水源又由检点升职东殿左丞相,曾钊扬也由右掌朝仪升职东殿右丞相,职同检点。北殿丞相曾由罗秘芬担任过,癸丑四月,他由北殿簿书升北殿丞相。翼殿丞相则曾由刘承芳担任过,癸丑八月,他由翼殿簿书升翼殿丞相,职同指挥。张汝南认为“东贼伪丞相二人,伪制与洪贼伪朝丞相同”是不对的,因为天王有六官丞相的设置。然而,东王为了显示自己日益提高的地位,又不甘心于这种状况,遂废丞相,而设尚书。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昔有今废伪官名目》中就列有东殿丞相、西殿丞相、北殿丞相与翼殿丞相(注:参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98-99页。),可见各殿丞相到后来是被撤销了。从表面上看,诸王没有了丞相,似乎是降低了职官设置规格,隐藏了东王图谋扩大权势的野心;而从实质来看,一方面,殿前丞相作为一种荣衔,各殿官员仍可继续授予;另一方面,各殿尚书的同职官品较原来各殿丞相、簿书的同职官品并未降低,东殿六部尚书职同检点,北殿尚书与翼殿尚书职同指挥(注:参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83页。)。而原来的东殿丞相也职同检点,北殿丞相与翼殿丞相职同指挥,东殿簿书职同检点,北殿簿书与翼殿簿书职同总制(注:参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57、58、64页。)。对于刚刚产生的新官职,东王杨秀清极力维护其权威,甲寅年间曾将冒犯东殿兵部尚书侯谦芳的职同总制的北殿参护李凤先处以死罪(注:参见《太平天国》第2册,第387-388页。)。更为重要的是,天王有六官丞相,诸王有六部尚书,实际是在向天王的职官设置看齐,而且,诸王的六部尚书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凡伪王侯丞相检点指挥,有六部尚书、六部书、六部掌书诸名色。其六部尚书所属,又各署六部掌书* 、六部书。六部掌书,又各有掌书书理。惟伪东殿各尚书之掌书,颁给印信,其余掌书书理六曹执事,若吏胥而已。”(注:《太平天国》第3册,第96页。)而东殿“其六部尚书,又各有六部掌书,如胥吏,但冠带而给印,伪东王权重事繁,故属官视他人以倍”(注:《太平天国》第3册,第102页。)。在东王府还有专门的东殿尚书挂号所(注:参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165页。),诸王特别是东王的地位得到大大的提高。
既然簿书为各殿丞相所属,而各殿丞相后来被撤销,那么,我们可以初步推断簿书官职也随着各殿丞相的裁撤而被撤。太平天国废丞相、簿书而置尚书的历史事实可从两个方面得到证明:一是关于簿书官职的具体任职者,在史料文献中记载较少,有史可考的仅前述7人,特别是癸丑十月以后的任职者至今尚未发现。二是关于尚书官职的具体任职者,史料文献中的记载却较多,有史可考的尚书任职者有24人(注:参见《太平天国》第1册第387页,第3册第59、67-68、72-74页,第4册第643-644、676-677页;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1册,第279-280页。)。各殿丞相与各殿簿书被撤销后的去向大致如下:
1.各殿簿书→各殿六部尚书→六官丞相或恩赏丞相。如黄启芳和李寿春:黄启芳于壬子八月初被封为北殿簿书,后改为右二簿书,至癸丑十月时升北殿吏部尚书,甲寅四月升春官正丞相(注:参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58-59页。)。李寿春初为诏书衙协理,癸丑二月被封为东殿簿书,嗣后改为吏部一尚书,十月被封为恩赏丞相(注:参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67页。)。
2.各殿簿书→各殿丞相→六官丞相。如刘承芳和罗秘芬:刘承芳自癸丑至江宁(约三月左右)始封翼殿簿书,八月升翼殿丞相,职同指挥,十月升地官又副丞相。罗秘芬于壬子十二月授北殿簿书,癸丑四月升北殿丞相,癸丑十一月升地官又正丞相。
3.各殿簿书→六官丞相等其他官职。如李寿晖和卢贤拔:李寿晖于癸丑三月任东殿簿书,癸丑十一月授殿右六检点。卢贤拔于癸丑七月调为东殿簿书,十月升秋官正丞相,仍理东王府事。
4.各殿丞相→六官丞相。如曾水源与曾钊扬:曾钊扬于癸丑十一月由东殿右丞相改为天官又副丞相,仍理东殿事。曾水源于癸丑十月亦由东殿左丞相改为天官又正丞相。
据上述可知两点:一是在被撤销的各殿簿书与各殿丞相中,只有各殿簿书改任各殿尚书,而各殿丞相则无改任各殿尚书者。所以,罗尔纲先生指出:东殿初设簿书,后置尚书,始废簿书(注: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1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81页。)。其实不独东殿如此,其他各殿也大抵一样。只是他没有探究簿书是怎么被撤的。二是各殿丞相的撤销时间与簿书的撤销时间是一致的,约在癸丑十月至十一月间,据上述8位任职者(李寿春除外)的官职升迁时间就可以明了这一点。其实,簿书改职的酝酿时间当在癸丑八月至九月间。从李寿春的职官升迁时间来看,他由东殿簿书改为东殿吏部一尚书,是在癸丑二月至十月间。这期间,李寿晖于癸丑三月始任东殿簿书,而卢贤拔于癸丑七月始任东殿簿书(注:《太平天国》第3册,第53-54页。)。因此,李寿春改任东殿吏部一尚书的时间,当在癸丑七月以后,但也不会在癸丑十月,亦即在癸丑八月至九月间。这一时期,只有少数的簿书改职,属于酝酿时期。至癸丑十月至十一月间,才是所有的各殿簿书与各殿丞相改职的正式时期。由于簿书人员较少,仅依靠簿书改职来建立各殿尚书机构是远远不够的,此后,各殿尚书机构特别是东殿尚书的建设仍在继续,需要调动其他职官来担任各殿六部尚书,大约至甲寅三月,各殿尚书机构的建设全部完成,在甲寅三月,侯谦芳调为东殿吏部二尚书,侯淑钱由总圣库协理升为东殿吏部三尚书,而侯裕宽亦由指挥调为东殿户部二尚书。
簿书的撤销是通过改任各殿尚书来完成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史料中不应当出现将各殿簿书与各殿尚书同时并提的记载,但事实上,《贼情汇纂》和《金陵省难纪略》在介绍太平天国的职官时,就同时记载了各殿尚书与簿书(注:参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172页,第4册第709页。)。如《贼情汇纂》载:“一切军务皆由杨逆主裁,仅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与之计议……贼多市井无赖,识字不多,厌见文字,悉任掌书裁处。于是则多设簿书掌书诸伪官,而被胁充先生者,似可渐操其柄也。”(注:参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172页。)这将如何解释呢?
在张汝南的记载中,诏书衙是在介绍天王朝内官时提到的,接着就谈及各殿六部尚书:“各王又添六部尚书,称某殿某部尚书,如东殿吏部尚书。”(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709页。)这就是说,诏书衙与各殿六部尚书是同时并存的,张汝南的记载也提到簿书,这表明各殿簿书改任各殿尚书有一个过程,即前文所言从最初的酝酿至最后的完成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可能出现将各殿簿书与各殿尚书同时并提的情况:但他的记载没有提到簿书衙,这可能也不是偶然,因为张汝南记载太平天国的各种职官数目较多,也较全面,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漏记簿书衙的,没有记载簿书衙只能反映太平天国在簿书改职过程中没有簿书衙这个机构。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对女簿书记载尤详,而对各殿簿书和簿书衙没有记载,在他所列举的太平天国人物中,亦无担任各殿簿书者。这表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太平天国在完成簿书改职后仍无簿书衙这一机构,因为簿书改职后簿书之官职名称不再为人所知;二是女簿书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在簿书官职被撤后,仍继续存在,起码直至甲寅正月(注:参见王庆成编著《天父天兄圣旨》,第101-102页。)。而涤浮道人的《金陵杂记》记载了许多太平天国机构的负责人任职对象、职能范围和馆址所在地,其中也未提到簿书衙,但他的记载提到了各殿簿书官职,这似乎又表明簿书衙这一机构在簿书改职前后一直没有存在,而前文业已论证簿书衙这一机构在甲寅六月时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对于史料记载中的这些矛盾现象又将如何解释呢?
三
笔者以为,对以上全部问题的惟一解释就是,簿书衙这一机构存在的时间太短,在它刚刚成立后不久很快又被撤销了。簿书衙存在期间,代行诏书衙管理官册、兵册和家册的职能与六官丞相、各殿六部尚书、六部掌书批复文本的职能,由此导致了同一职能的执掌对象在史料中有不同的记载。
佚名《粤逆纪略》为什么会有“簿书衙主批文本”的记载呢?一个原因可能是《粤逆纪略》的作者认为,典簿书为簿书衙的负责人,而簿书则是簿书衙里的工作人员,前文所述各殿负责批复文书的除黄再兴外,大多担任过簿书职务,而女簿书也负责东王府的文书批复。但从现存史料文献中并未发现簿书与簿书衙之间有若何关系,而簿书是属于各殿王府的,不可能由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管理,否则就会冒犯东王的权威,这是东王所不能接受的。簿书作为各殿丞相所属,参与诸王文本的批复当是可能之事,但由此推断簿书衙即有主批文本的职能,还缺乏有力的逻辑推理环节和充分的史料依据。笔者以为佚名的记载绝不是虚构出来的(前文已有说明),必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簿书衙确实曾经负责过主批文本。关于这一职能的执掌对象史料中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记载呢?这就得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簿书在未被撤销时可能参与了批复文本,但在被撤销以后,主批文本的职能,如前文所提到的,是由六官丞相、各殿六部尚书、六部掌书来负责的,簿书衙成立后又代行了他们主批文本的职能。这样,《粤逆纪略》的记载才找到了事实的根据。
簿书衙存在时间很短,代诏书衙管理官册、兵册和家册,也是张德坚将这两个机构混淆起来、出现一些错误记载的根本原因。关于簿书衙的记载仅有三处,其中两处见于张德坚的《贼情汇纂》,一处见于佚名《粤逆纪略》;而关于典簿书的记载也只有《贼情汇纂》中记载的两处(注:参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87、101页。)。张德坚自癸丑起记载所谓的“贼情”,甲寅十一月始受曾国藩之命编辑《贼情汇纂》,中间屡有增补修改,约至乙卯七月编成,编成后仍继续增补修改。他的记载起始时间较早,依据的大多是他所搜集到的太平天国文书与他所采访到的资料,编辑时又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因而,相对于张汝南和谢介鹤等人来说,他对太平天国各方面情况的了解应当是比较深入细致和全面的,在《贼情汇纂》中出现典簿书和簿书衙的记载是在情理之中。由于后来簿书衙被撤,他可能也有所风闻,就对有关簿书衙的内容进行了删改,但他又不能确知被撤的时间和具体情况,故而在记载中出现了前后矛盾的现象。佚名《粤逆纪略》亦系纪述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前期的各项政策措施,簿书衙在这一时期曾一度存在,《粤逆纪略》提到簿书衙也是正常的,但他对簿书衙了解不多,故而只能简单地提到“簿书衙主批文本”。张汝南的后人在介绍《金陵省难纪略》的成书过程时说:“是书成于咸丰六年,先君子馆于杭时之所述也。当癸丑二月城破之后,先君子两觅死不得,遂日谋所以脱身者,辗转至次年八月间,始得率眷属出重围,越三年丁巳,馆于杭,课余忆及,信笔记之;故书中所载皆咸丰三四两年贼中情状。”(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86页。)而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的写作背景则是:“介鹤于癸丑春为贼虏至金陵,置粮馆中,曾与金陵张炳元,槜李金丽生,及同志数百人谋内应,卒不成,炳元死之,介鹤乃以计逸出,依今观察静山赵公于凤山行馆,因忆陷贼时所见所闻,笔之于书,起自癸丑正月二十九日,止于甲寅七月三十日。”(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49页。)这就是说,张汝南的《金陵省难纪略》和谢介鹤的《金陵癸甲纪事略》都属于亲身所见所闻的追忆之作。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则是作者的亲历亲闻:“《金陵杂记》一卷,为某陷贼时所作,耳不绝锋镝声,目不绝愁苦状,欷歔涕泪,痛何忍言。聊述夫在城生灵被贼戕害之惨,并伪制伪令伪改作诸端”(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09页。),可谓是亲历之纪实。
张汝南、谢介鹤与涤浮道人癸丑和甲寅年都在天京,都有其所见所闻的记载留传于世,三人的记载中都提到簿书而没有提及簿书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太平天国内部细微的职官变动可能不会引起外部的任何反应,簿书官职的撤销就没有引起张德坚和谢介鹤的注意。他们以为在出现各殿尚书后,各殿簿书仍继续存在,二者同时并存,他们对各殿尚书与各殿簿书的记载缺乏时间概念,将不同时间的职官放在一起,使人不能明了这些职官设置的先后时间,从而产生这些职官是同时并存的错觉,前引张德坚将东殿尚书与簿书一起记载的资料就说明了这一点;二是一个机构或官职存在时间的长短与它在史料文献中记载的数量和频度是密切相关的,簿书、诏书与诏书衙存在的时间较长,所以史料文献中的记载就较多,而典簿书与簿书衙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未能引起外界的充分注意,所以史料文献中的记载就极为少见。这就进一步否定了典簿书与诏书衙存在某种关系的可能性,而说明了典簿书与簿书衙有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典簿书作为簿书衙的负责人,既然簿书衙存在的时间短暂,那么典簿书存在的时间也必然短暂,两者在史料文献中的记载极少也就顺理成章了。一个极有可能的情况是,簿书衙在癸丑年至甲寅年六月前不久尚不存在,也就是说,簿书衙的成立是在甲寅六月的不久前成立的,但在甲寅六月后不久又被撤销了。关于簿书衙旋建旋撤的推测也很符合所谓“贼令暮四朝三,纷更不定”(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86页。)的历史实际。当然,在“纷更不定”中,也有一些“令”、“制”是基本延续不变的,诏书和诏书衙即其一例。簿书衙在其存在的一段时间内,代行了诏书衙管理官册、家册和兵册的职能和丞相与各殿六部尚书、六部掌书等批复文本的职能,致使张德坚将簿书衙的负责人与诏书衙的负责人混淆起来,而未能加以修正。
簿书官职的撤销消除了簿书、典簿书与簿书衙之间的混乱关系,这时“典簿书”与“簿书衙”中的“簿书”已无官职之义,乃纯指太平天国的簿本册籍,所谓的簿书衙就是太平天国中央主管簿本册籍的文书机构,因此它的负责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典簿书”了。因此,簿书官职的撤销并不妨碍簿书衙的存在,反而使其存在更符合太平天国文书机构的命名规范,而且在太平天国东王集权的政治体制之下,也只有在各殿簿书撤销之后,才能出现簿书衙的机构。前文业已指出,全部完成簿书改职是在甲寅三月,那么,簿书衙的成立当在甲寅三月以后。张继庚企图使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的险恶用心被诏书衙识破后,据《患难一家言》载:“(胡)元炜谓炳垣(指张继庚——笔者注)曰:‘尔姑以所记者言之。’炳坦以三十四人对,三十人者,皆猛悍死战,纵横数省者也。北贼告东贼,立令骈诛,不许一人脱。已而贼悟为所绐,乃趣斫之,炳垣遂遇害,时咸丰四年三月六日也。”(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353-354页。)咸丰四年即为甲寅年,这说明,在甲寅三月初,官册还是由诏书衙管理的,因此,在甲寅三月六日之前,簿书衙一直没有成立。由于甲寅六月簿书衙已经存在,所以簿书衙的成立时间当在甲寅三月六日至六月间。
簿书衙为什么会旋建旋撤呢?簿书衙的成立主要是为了缓解诏书衙的工作压力,代行诏书衙和其他文书机构的部分职能。但是,其成立后便日益形成了不利于东王集权的局面。一是,前文已经指出,诏书原为天朝典官,诏书衙本为天王府的文书服务机构,但它正逐渐被东王僭夺,在向着为东王府服务的方向转移,从诏书衙前张贴的对联就可看出这一点:“诏出九重天那怕妖魔施毒计,书成一统志岂容狐兔竟横行”(注:《太平天国》第3册,第247页。)。这里的“九重天”是指东王府(注:《太平天国大辞典》,第103页。)。因此,诏书衙正日益成为东王府的代言机关(天京事变后,随着东王势力的消亡,诏书衙也寿终正寝。天京事变后诏书衙的情况,史籍中无所记载,可为明证)。簿书衙成立之初当属天朝典官,代行诏书衙的部分职能无疑是在向东王争权。二是簿书衙成立后,女簿书仍然存在,并代东王批判文书,如从规范机构命名原则的角度看,女簿书也不应再继续存在,而女簿书的批判权也应交给簿书衙了,而代行六官丞相、各殿六部尚书、六部掌书主批文本,也是对东王权威的侵犯,也是在向东王争权。三是管理官册、兵册与家册,事关国家的人事档案和用人大权,而主批文本更是直接关系到军政决策,两者均非一般的权力。所有这些都是东王所不能容忍的,由此也就决定了簿书衙的命运,在它刚刚成立不久就被撤销了,并将它代行诏书衙的那部分职能再移交给诏书衙。
从上面的考辨中可以知道,东王杨秀清为了逐步夺取天王的权力,在癸丑十月至十一月间撤销原来各殿的丞相和簿书官职,另设各殿六部尚书;至甲寅三月,在完成各殿尚书建设的情况下,为减轻诏书衙的工作压力,又另设以典簿书为负责人的簿书衙代行诏书衙和其他文书机构或职官的部分职能。各殿六部尚书的设置提高了诸王特别是东王的地位,但簿书衙的设置却妨碍了东王的集权。因此,簿书衙在刚刚成立后不久又被撤销。由于簿书衙代行诏书衙的部分职能,而地主阶级文人对于簿书衙旋建旋撤的情况又不甚了了,他们或对典簿书和簿书衙记载较少,或将簿书衙与诏书衙这两个文书机构、典簿书与诏书这两个文书官职混淆起来,从而导致了一些错误的记载。所以,典簿书为簿书衙的负责人,而不是诏书衙的负责人。
标签:中国近代史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六部尚书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黄再兴论文; 洪秀全论文; 丞相论文; 金陵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太平天国运动论文; 远古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