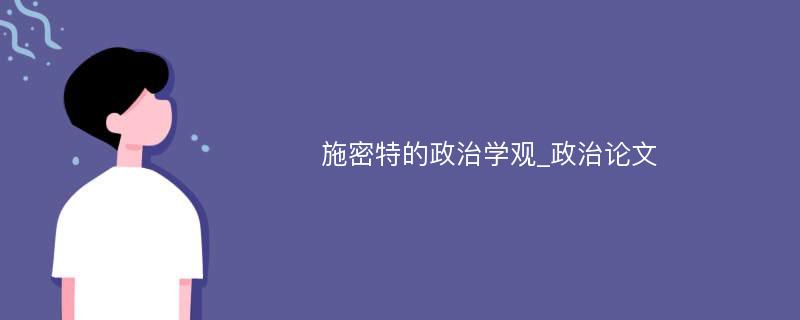
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念论文,政治论文,施米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友爱的政治”与“敌友之分”
德里达在1994年出版的《友爱的政治》中说,1927年有两本重要的经典著作问世,一 本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而另一本就是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注:Jacques Derrida,Politics of Friendship.Trans.George Collins.London:Verso,1997.)同 为经典著作,两者后来的命运却迥然不同。《存在与时间》已稳稳地成为二十世纪西方 哲学的第一经典;而《政治的概念》则在其问世后的六七十年间,逐渐从西方主流学界 和知识大众的话语中销声匿迹,仅仅在一些二十世纪政治哲学的读本中才能看到这篇经 典之作。1985年这位97岁的德国大师赫然仙逝。出人意料的是,施米特却在谢世后奇迹 般地迅速重回二十世纪西方大师级思想家之列,其在德国和美国两地急剧上升的势头令 人大跌眼镜,连当世大哲德里达也加入到对施米特的追逐与挪用之中。施米特的幽灵开 始在美国和欧洲游荡。(注:Gopal Balakrishnan,The Enemy: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of Carl Schmitt,London:Verso,2000.)
然而,与施米特不同,德里达试图解构“友爱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友爱”对存在和自 然之爱的迷恋;因此他也在解构政治,解构那种自然共同体的封闭的友爱政治。施米特 在《政治的概念》中所说的“敌友之分”正是德里达的“他者的哲学”要解构的靶子。 (注:迈尔:《神学抑或哲学的友爱政治》,载于刘小枫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 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65-300页。)对德里达来说,敌友之分的友爱政治将为差异的 “承认的政治”所取代。由此,解构主义者不再是为了无限的能指的差异而汗流浃背的 解构运动员,他将成为“无限异质性”的“未来的民主”的政治实用主义者。在德里达 看来,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实在“太古典”了,德里达用列维纳斯的“他者”和“无限 ”的概念及其责任伦理学给施米特的“敌友之分”施洗。然而,从施米特的视角来看, 如果取消了“敌友之分”,尤其是取消了主权国家之间的敌友之分的话(用德里达的话 来说就是取消了“作为他者”的主权国家,用霍布斯的话说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自然 状态”),战争与和平、内政与外交、武力和文明的区分以及国家、主权、战争和敌人 等概念也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其实质就是以“人类”、“权利”、“和平”、“秩序 ”或者“责任”、“未来”、“正义”等名义消除政治,或者说,消除“伟大的政治” 。
二、“非政治化的时代”与“政治的概念”
然而,政治是人的生存的基本境域和总体境域,是精神与精神的斗争的基本境域和总 体境域,是生命与生命的斗争的基本境域和总体境域,是生存与生存的斗争的基本境域 和总体境域,因而是永远不可消除的。最重要的是,政治生活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本领 域,是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命运的存在方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前提。“以为一个不设 防的民族便只有朋友,极其愚蠢;设想敌人或许能因为没有遇到抵抗而大受感动,则无 异于精神错乱。比如说,没有人会相信,如果放弃所有的艺术和经济生产,世界就能进 入一种纯道德的境界。人们更无从希望,如果逃避所有的政治抉择,人类就能创造出一 种纯道德或纯经济的状况。即使一个民族不再拥有生存于政治领域的能力或意志,政治 领域也不会因此而从世界上消亡。只有弱小的民族才会消亡。”(注:施米特:《政治 的概念》,刘宗坤等译,《施米特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9、242 页。)认为政治会消亡,国家会消亡,战争会消亡,斗争会消亡,在施米特看来都是“ 非政治化”时代的谵语,若不是为了别有用心地骗人,便是愚昧无知。因此,施米特认 为要在一个“非政治化的时代”重申“政治的概念”,以及政治作为人的“极端状态” 或者说“人的命运”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誓死批判自由主义对政治的中立化、技术化 、规范化、道德化、经济化、和平化,一言以蔽之,“非政治化”。
施米特的“文化批判”与海德格尔、恽格尔、卢卡奇等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同样是对 技术化时代的批判,尤其是对技术化时代中自由主义经济与文化理论的统治地位及其非 政治化后果的批判。(注:John P.McCormick,Carl Schmitt’s Critique of
Liberalism:Against Politics as Techn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施米特对西方现代性独特的历史诊断为他的末世论的调子提供了一副鲜活 图景:这是一个中立化的时代,这一时代是西方四百年现代性的巨大变革的结果。西方 四百年的现代性是一个剧烈的世俗化进程,这一进程可以为分四个阶段:十六世纪的神 学,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十八世纪的人道主义和道德信念,十九世纪的经济。无休无 止的神学争论和宗教斗争使西方从十六世纪开始寻找用技术手段消除冲突的中立化领域 ,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开辟的中立化领域成为重心不断转移的新的斗争领域。中立化的 进程导致了现代技术的形而上学信念对人类的主宰和控制。“今天,工业化国家的大众 仍然依从于这种麻痹人民的宗教,因为他们像所有大众一样,寻求各种激进的结论,而 且下意识地相信,人们可以在此找到追求了四个世纪之久的绝对非政治化,普遍的和平 便从这里开始。但是,技术既能强化和平,也能强化战争,二者的机会相同,除此之外 ,技术什么也做不到。就此而言,无论是以和平的名义讲话,还是利用和平这类虚假的 套话,都不能改变什么。今天,我们已经看透了,大众意见的心理-技术机制如何利用 各种名目和言辞的迷雾来运转。今天,我们也可以看清那种玩弄言辞的隐秘的手段,懂 得了人们以和平的名义来发动最残酷的战争,以自由的名义来施加最沉重的压迫,以人 道的名义来制造最可怕的非人道。最后,我们也看清了那一代人的情绪,他们只看到技 术时代精神的死亡以及没有灵魂的机械论。”(注: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 等译,《施米特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9、242页。)
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既是针对着四个世纪的西方现代性历史进程的世俗化,也是 针对作为其后果的政治浪漫主义的政治技术化。十九世纪自由主义不仅发展出“管理而 不统治”的中立化的国家概念,不仅在法国大革命后发展出私人生活的审美化和浪漫化 的领域,而且二者在政治的技术化、中立化和自由化的整合之下,形成了形形色色的“ 政治浪漫主义”,如缪勒和施莱格尔之流。政治浪漫主义和技术化的政治最集中的表现 就是:国家成为法律秩序,而法律成为“国家理性”。然而,对于施米特这位欧洲首屈 一指的公法学家来说,宪法要从国家的统一体及其主权来理解;(注:David Dyzenhaus ,Law as Politics:Carl Schmitt’s Critique of liberalis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而在这位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家看来,国家的统一体及其主权要从“ 政治的概念”来理解。“在法律生活的现实中,至关重要的是由谁来作决断。权限问题 总是与实质的正确性问题并驾齐驱。法律形式问题就存在于决断主体与决断内容的对比 中以及主体的正确含义中。它没有先验形式所具有的先天性空洞,因为它完全产生于法 律的具体性。法律形式也不是技术性的精确形式,因为后者具有要达到某种目的的功利 性,它在本质上是物质性的和非人个性的。最后,它也不是审美产品的形式,因为后者 对决断一无所知。”(注: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施米特文集》卷 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页。)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从普遍的意义上 来说,是对技术化、中立化、非政治时代的批判;从特殊的意义上来说,是对议会民主 、形式主义法学、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以及自由主义的各种政治法律理论的批判,尤其是 凯尔森的法律实证主义和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注:David Dyzenhaus,Legality and
Legitimacy:Carl Schmitt,Hans Kelsen and Hermann Heller in Weimar,Oxford.1997 ;Gary L.Ulmen,Politischer Mehrwert:Eine Studie ueber Max Weber und Carl
Schmitt,Weinheim:VCH Acta humaniora.1991;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 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425-488页;施米特:《政治的概念》, 第340、527页。)
三、“自由的技术”与“威权的政治”
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被当今的自由主义者视为对自由主义的最大挑战,同时也是 最大推进。当今西方最热衷施米特理论的乃是那些自由主义者。施米特在“历史的终结 ”和“文明的冲突”的时代氛围中复兴,这一现象本身就耐人寻味。施米特目光如炬, 他深刻地看到自由主义没有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只有从伦理和经济对政治进行批判; 没有国际政治,只有国内政治或政党政治。“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自由主义对国家和 政治的否定,它的中立性、非政治性以及对自由的主张,同样具有某种政治的含义,在 具体的情况下,这一切便会导致激烈地反对特定的国家及其政治权力。但是,这既非一 种政治理论,也非一种政治观念。尽管自由主义并没有激进到否定国家,但从另一方面 看,它既没有提出一种实际的国家理论,也没有靠自己找到改革国家的途径,它只是试 图把政治限制在伦理领域并使之服从经济。自由主义创造了一套‘权力’分离和制衡的 学说,即一套监督和制约国家和政府的体制。这既不能被看作一套国家理论,也不能被 看作一套基本的政治原理。”(注: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施米特 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2页。)施米特深刻地洞见到,自由主义将 政治局限于伦理,也即局限于批判国家的专制、限制政府的权力、保护个人的权利之上 ,并进而使政治服从于经济。他深刻地指出,自由主义以人权的名义抵消了主权,以自 由的名义消除了民主。在自由主义那里,没有真正的政治的风险和政治的极端状态,也 没有真正的政治的概念。自由主义从权力、法律、权利、公共事务、国家等角度界定政 治的概念,导致的结果,一言以蔽之,即以行政和治理吸纳并消除政治。然而,政治是 永不可消除的,也不可避免;在施米特看来,声称所有的政治和权力都是恶的、因而必 须加以限制和消除的学说,如果不是真正的无知,就是有意的欺骗。自由主义的意识形 态仍然没有走出两个多世纪前对专制国家和封建贵族的批判性建构的形式。自由主义没 有意识到自身正在成为最为危险的武器。
施米特试图超越和克服自由主义主流的意识形态。施米特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技 术时代、世俗化的批判并不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的,更准确地说,不是以“无政府 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名义,而是从超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也即“威权 的社会主义”的立场。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投机于纳粹的威权社会主义,成为“第 三帝国桂冠法学家”。(注:Joseph W.Bendersky,Carl Schmitt:Theorist for the
Reich,Princeton University.1983.Andreas Koenen,Fall Carl Schmitt:Sein
Aufstieg zum“Kronjuristen des Dritten Reiches”.Darmstadt.1995.)德国“文化 战争”时期的天主教保守主义是施米特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技术时代、世俗化的殊 死为敌,并站在“威权社会主义”的立场的根源之一。
克里斯蒂将施米特视为一个平衡自由与民主、民主与权威的哈耶克式的“威权自由主 义者”(注:Renato Cristi,Carl Schmitt and authoritarian liberalism:strong
state,free economy,Cardiff: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1998.),这是一个戴上了 霸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眼镜的学者的意见。克里斯蒂认为施米特的关怀是,对于魏玛 民国的市民社会的宪政而言,没有权威也没有民主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自由,因而是危 险的自由。因为,自由并不是一种政制,也不是一种合法性。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自 由可以在不同的政制中实现,自由也完全可以在威权的保障中实现;相反,多元论的自 由价值观却完全可以毁掉削弱国家的主权并毁掉一个虚弱的国家。克里斯蒂因而断言, 施米特的冲动并不是反对自由主义,而是加强政治自由主义;这一关怀与韦伯非常相似 ,尽管施米特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语汇和批判形式。
对于施特劳斯来说,施米特真的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自由主义,他只是以霍布斯的自由 主义批判了此后两个世纪的发达自由主义。“我们必须承认,对自由主义的批驳看起来 就是施米特的最终论题,而且他往往纠缠于对自由主义的批驳之中,因而迷失了自己真 正的意图,停留在自由主义划定的水平上。这种纠缠不清决不是偶然的失败,而是施米 特所奉行的原则的必然结果。这种原则就是‘精神领域的一切概念只能通过具体的政治 现实来理解’,‘一切政治的概念、理念和术语均具有敌对的意义’。……施米特是在 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上承担起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在此,我们是指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发生在自由主义的视界之内。他的非自由主义倾向依然受制于无法克服的‘自由主义思 想体系’”(注:施特劳斯:《施米特<政治的概念>评注》,舒炜编《思想与社会》第 二辑《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2-233页。)
尽管如此,如果无视施米特来自天主教的政治神学之根,我们就无法同情地理解他一 生中对自由主义的怨恨以及他批判自由主义的激情,尤其这种怨恨与对资本主义和技术 时代的仇恨揉合在一起,就加倍地强烈。按照他的敌友之分,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技 术化时代都是他的殊死的敌人。没有这一殊死的敌人,施米特的整个政治理论就失去了 方向。
四、“恶魔的敌人”与“总体的战争”
施米特把自由主义确认为自己的殊死敌人,可见,施米特本人就是对区别敌友这一政 治标准的最好的运用者。这一确认乃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他也是自由主义的“高贵 的敌人”。《政治的概念》里面并没有谈到朋友。与施米特不同,柏拉图在《法篇》中 以及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是从友爱来谈论政治的。施米特之所以从敌人来谈论政 治,乃因为是敌人而非朋友才是政治得以可能的条件。极端状态的战争的现实可能性是 政治的可能性条件,而政治又是国家和宪法的可能性条件。施米特并非一个鼓吹战争的 人,相反,战争并不是政治的内容,也不是政治的目标;战争仅仅是政治得以与其他的 人类活动领域区分开来的条件。没有敌人和战争,没有潜在的敌人和战争,也即没有了 敌人和战争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了政治。更甚至,没了敌人,也就没有了高贵的朋友, 友爱变成了两个孤独的灵魂之间的私人情感之事了。
1927年版本的《政治的概念》无疑具有强调政治的自律以及区别敌友作为政治的自主 领域的独特标准的新康德主义的倾向。该书出版后,遭到了施特劳斯的严厉的批判。施 米特吸纳了批评意见,并在1932年的版本中不动声色地修正了那些具有康德主义色彩的 句子,因为,对“政治领域的自律”的追求恰好是施米特所批判的自由主义的根本特点 。1933年版的《政治的概念》强调:政治不仅仅是相对独立自主的领域,而且也是至高 无上的领域:“一旦出现政治单位,它就是权威性、总体性和至高无上的单位。政治单 位是总体的,首先因为每一事物潜在的都是政治的,并因此受到政治决断的影响;其次 因为人类就其总体而言,在生存上是通过参与政治而得以理解的。政治就是命运。”( 注:迈尔:《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朱雁冰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 第21页。也见舒炜编《思想与社会》第二辑《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2年,第245页。)只有政治才能要求对生命从肉体上的消灭,才能要求中断所 有其他领域的活动,才能拥有对极端状态的决定权。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建立在战争这 种人类生存的极端状态之上,能作出决断者拥有战争法权,也就是国家主权和宪法的权 威,也同时具有道德上的高贵和精神上的崇高。施米特把克尔凯郭尔的极端情境中的生 存决断全盘转移到政治的领域之中,(注: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14页。参见洛 维特:《施米特的政治决断论》,刘小枫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 02年,第27—76页。)并同时接受了韦伯的“理智的诚实”的现实主义与崇尚冲突和高 贵的英雄悲观主义。施米特的政治神学和公法理论富有一种战斗的英雄主义伦理的激情 。在他看来,自由主义只不过是试图逃避任何伟大的政治所伴随的风险的资产阶级情调 而已。
施米特自视区分敌友的政治概念是继续了马基雅维利的事业,这不仅仅是指强调政治 的独特理由并使之与道德分离,更重要的是指对人道主义的“正义的言辞”的现实主义 批判。马基雅维利之所以担负“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恶名,是因为他要与当时的人文 主义的意识形态作战。人道主义或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运用堂而皇之的“正义的言辞 ”,坚持人性善的革命理论,把敌人妖魔化为“恶魔的敌人”,试图发动一场终结一切 战争的“总体的战争”,也就是彻底征服和消灭敌人的殊死的战争。然而,不承认敌人 的存在的权利,就意味着否定了敌人同样具有人性,并把同等尺度的人性的敌人视为价 值上低劣的、理应被消灭的十恶不赦的恶魔。战争由此演变成一场史无前例的残酷的非 人性的“人道主义战争”。这不仅仅适用于纳粹,也适用于意识形态的冷战,也同样适 用于文明冲突中的各种极端的民族主义。1963年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的再版序中写 道:“这个时代在抹去战争与和平的区分的同时,又在制造核杀伤武器:在这样一个时 代,怎么可能停止反思划分敌友?最大的问题仍然在于限制战争;但是,如果战争在两 方面都与敌对性的相对化脱不开干系,限制战争不是玩世不恭的游戏,就是发动一场狗 咬狗的战争,再不然就是自欺欺人的空谈。”(注: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125页 。)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政治的概念》的许多深刻的洞见:承认敌人只是政治上的公敌, 而不是道德上的恶魔;只有实际的敌人,没有绝对的敌人;承认战争和冲突永久的不可 消除性,而不是廉价的和平主义;否定格劳修斯所说的“正义的”战争的可能性;承认 国际政治的多元主义,而不是普世政治,或“国家的消亡”、“历史的终结”。(注: 据说,亨廷顿也受到过施米特的影响,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中似乎可以看出一点痕迹 。他和德里达都反对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但是出发点各不相同。)在施米特看来 ,那都是一些宽宏大量而又自作多情的政治浪漫主义。
五、别一种的“政治浪漫主义”
在施米特看来,伯克、贡斯当、夏多布里昂这些老牌自由主义者都是浪漫主义者绝非 偶然。不过,我们也可以从施米特本人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看到另一种浪漫主义,它可 以追溯到那些反大革命的保守主义浪漫派那里:波舒哀、迈斯特、伯纳德、科特,甚至 还有费希特、黑格尔。德国浪漫派和黑格尔主义对施米特及其同代人的影响根深蒂固。 施米特的悲观现实主义和战斗英雄主义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不同于那种流于表面 的浪漫主义。不仅仅诉诸克尔凯郭尔的“例外”、“具体性”、“特殊性”是一种浪漫 主义,而且诉诸天主教人性恶和霍布斯的人性恶也是一种浪漫主义。当然,我们不能确 定这种浪漫主义是否是施米特诱惑或宣传的表达策略,就象我们在面临马基雅维利的素 朴的风格不好判断一样。施米特的浪漫主义还能从施米特早年对表现主义作家多伯勒的 《北极光》研究上看出来。哈贝马斯说施米特的东西是“政治表现主义”,很是精辟。
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的文体风格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同属于那个表现 主义时代的典型文风。如果我们把这篇简洁有力的宣言/檄文的各个小节的标题或第一 句话列出来,就会看到它与《逻辑哲学论》同样的文字魅力:一,“国家的概念以政治 的概念为前提。”二,“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三,“战争是敌对性的显现形式。 ”四,“国家是政治的统一体,因多元论而出问题。”五,“战争法权,即在特定情况 下决定谁是敌人的现实可能性以及运用来自政治的力量与敌人作战的能力,属于在本质 上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国家。”六,“世界并非政治的统一体,而是政治的多样体。”七 ,“所有的国家理论和政治概念均可按照它们所依据的人类学检验之,并由此分为两类 ,即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假定人在本性上是恶的,以及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假定人 在本性上是善的。”八,“伦理与经济的两极导致的非政治化。自由主义运用某种特定 的系统方式改变了所有的政治概念。”
施密特在《政治概念》第七部分说,所有的国家理论和政治概念均可分为两类,即假 定人性恶的以及假定人性善的。施米特自己的主权与专政论、区别敌友、政治不可消除 性等理论都基于“人性恶”的形而上学或哲学人类学之上。也就是说,神学及其原罪论 是施米特的政治理论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在这个无神论的时代中,将自己的全部学 说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是否会面临着自毁长城的危险呢?或者,这只是施米特的策略? 我们不得而知。神学与政治的一致决不是道德的,而是政治的,尤其是罗马天主教的神 学政治。在施米特早年精彩的《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施米特阐发了与韦伯所说的 新教伦理的世俗化和理性化针锋相对的天主教反现代主义、反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 反技术时代的政治精神。这是施米特公法理论和政治理论的神学渊源。上帝还是魔鬼的 区分与敌友之分不仅是结构上的相似,或者说是上帝的主权的世俗化而已,而是在生存 论上的一致,也就是对人性的立场一致。施米特把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托克维尔、迈 斯特、科特、费希特、黑格尔、尼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都归为性恶论或悲 观主义或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们都认为人是危险的,邪恶的,权力和统治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人的自由决不象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是人类最高的价值。他们根本不喜欢或者说 不能忍受善良人的乐观的、性善的、和平的、理想主义或犬儒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生活 方式,因为这无关道德问题,这意味着取消了敌友之分和政治。
因此,《政治的概念》的第七部分其实是全文的根基,而第八部分以及《中立化与非 政治化的时代》中对自由主义的中立化、非军事化、非国家化和非政治化的批判无疑是 从第七部分的人类学批判得出的结论。施米特并没有简单把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政治学说 ,而是把它视为一种世俗化的浅薄的形而上学和人类学;而施米特本人的公法理论和政 治理论也不仅仅是一种法律和政治学说,而是一种深刻的政治神学,或者更准确地说, 一种基于罗马天主教政治神学传统的政治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