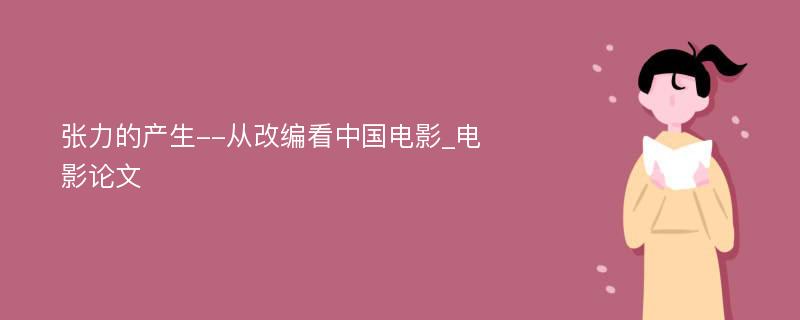
张力的生成——从改编再思中国电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电影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中国有两部有影响的电影是由文学改编的,但它们改编的来源却有极大的差别。这两部电影其实喻示了电影从文学作品中改编的深刻的变化,标定了两种不同的改编,也意味着电影从文学中获得的想象力的转化。一部是2014年张艺谋的《归来》,一部是2012年郭敬明的《小时代》。 事实上,这两部电影是两个极端。一个是“五四”以来传统的将电影视为大众、通俗艺术,仅仅是转化或延伸文学的想象,而作为其自身难以有独特的特性。这就是将电影的“高雅”视为文学的“衍生”过程。无论张艺谋走了多远,这个观念仍然是他最基本的意识。二是将具有视觉性的电影视为终极的作品,因为它和更为广大的观众有了交集。而和它相关的文学作品则或者仅仅是出现最终的“结果”之前的“草稿”或“蓝图”,将电影视为文学的“衍生”抑或是“结果”。这个差异其实是不同时代的话语在处理电影和小说这样的文类关系的不同的选择结果,也是当下电影和文学关系的投射。我们可以从探讨这两部电影的文学改编的意义来探究今天电影与文学、知识分子和大众文化之间新的内在张力。 《归来》是张艺谋在奥运会开幕式的高峰之后经过了多次尝试和一个较长时间的停顿之后,回到了他的电影的起点处的“归来”之作,连女主角都回到了《红高粱》里的巩俐。当年《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为张艺谋自己、也为莫言开启了一个“走向世界”的传奇之旅。今天这部《归来》改编自海外归来的“流散”作家严歌苓的小说。可以说,严歌苓本人其实就是从“海外”归来的。她早就“走向世界”,这些年来已经“归来”开始完全在中国本土写作。 《归来》既是张艺谋回到自己电影最初起点的作品,也是他回到了我们共同的走向改革开放起点的作品。在当年,这样的伤痕作品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也是当时我们通过对于历史感伤的凭吊来面对未来的努力,但今天,它似乎变成了已经老去的张艺谋对于自己来路的那些经验的回溯。这些经验对于张艺谋或严歌苓来说都非常熟悉,但对于中国今天的以80后、90后为中心的电影观众来说,是一些相当遥远的故事。这里的“改编”所起到的最为关键的作用,是张艺谋对于严歌苓复杂、微妙的小说的简化和强化。这种简化和强化正是“第五代”导演和中国当年的“伤痕”以来的“新时期文学”的关系的一种典型策略。这一次张艺谋还是回到了20世纪中国的“伤痕”的表述。他把小说《陆犯焉识》中通过孙女讲述的家族史的相对复杂而漫长的故事,简化为了一个人生命中的一段故事。其实,张艺谋在经过了这些年的摇摆和对于“新文学”的疏离之后,又回到了以文学为灵感源泉和叙事支柱的状态。严歌苓的故事的丰富性当然是张艺谋的故事“母本”,也是他的精神和灵感的源泉。在这里,文学仍然和“五四”以来的状况相似,置于文化的中心,而电影的想象力则源自文学。这产生了某种强烈的等级意识,也就是文学是电影的母体,文学是独立的自在之物,它完整地呈现一切。而电影则是“简化”和“纯化”的结果,是一种虽然有巨大影响却是比小说简单的文本。 这仍然是一个有张艺谋惯用的推向极致的美学追求的作品。这个关于记忆与遗忘的故事有似乎让人难以置信的强烈的感觉。失忆的母亲、归来的父亲和盲目而又天真的女儿,都在承受着记忆和历史的痛苦,在痛苦的故事已经过去的时候,他们却依然难以从伤痛中走出来得到康复。这是20世纪中国人无尽的苦难中平凡的一章,在那个时候,大历史是如此地横亘在每个人的生活之中,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让他们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但这却是以伤痕的难以平复、美好的一切已经难以追寻为代价的。母亲的痛苦在于她忠贞于感情,由于记忆过于刻骨铭心而不得不失去了记忆本身;父亲的痛苦在于他力图回到他已经离开的生活,归来会让生活恢复常态,但这常态是永远不可恢复的;而女儿的痛苦则在于她由于正常的自我争取,却是以出卖父亲为代价的。这个故事的复杂性来源于母亲对父亲感情的坚持只剩下对于“陆焉识”的符号的坚持,但真实的陆焉识出现的时候,却无法和这个符号对应。她对于符号的执著和对于“陆焉识”和方师傅的混淆、误认造成了绝对的痛苦。由此,语言脱离了实在,符号脱离了现实。而那个以“恶”的面貌通过母亲的恐惧作为符号出现的方师傅,却也由于新一波的政治变化而脱离了家庭,让父亲没有了复仇的机会和愿望,这是真切的悲哀。这里的大历史对于人的命运的捉弄让这些普通的生命变成了一段历史的牺牲。 张艺谋其实是希望带着我们重回20世纪的中国的苦难之中,他试图在这个新世纪里重述那个关于伤痕的老故事,也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和中国人在20世纪所承担的历史的痛苦相遇,在这里凭吊历史,让隐在心中的历史的伤痛得到一个超越的机会。《归来》的改编将“失忆”作为电影的唯一支柱,而原作中陆焉识人性的复杂和微妙反而无从彰显,这就使得原作中微妙和难以控制欲望的陆焉识,在影片中成为了一个执著于家庭的圣者。 其实,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更多地来自女儿丹丹的视角,这个女儿的见证、争取、承受。事实上,丹丹和张艺谋等人是同一代人,他们的青春错失了许多,但在一个新时代找到了新的可能性。我突然想到这个新时代给了丹丹和张艺谋这样的人新的机会,让他们在新的历史中扮演新的角色,于是才会有《红高粱》和《英雄》,才会有奥运会的开幕式。故事的最后母亲没有康复,她和真实的陆焉识仍然到车站的大门前等待一个符号的陆焉识。当那扇大门关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2013年的电影《中国合伙人》,在那里,一扇大门打开了,这是为成东青和他的两个同伴开启的大学之门,从那时开始展开了一个天翻地覆的中国故事。陆焉识夫妇停在那个关闭的大门前,但新的大门从此为中国人开启,于是我们走到了今天。 我突然觉得,经历了这么多的张艺谋老了,他终于有机会回去看看那扇关闭的大门,去厘清他的记忆和过去,他已经历经沧桑。和黑泽明或安东尼奥尼一样,在老年时回到自己的记忆去讲述,但他所面对的今天的中国电影却是有《中国合伙人》和《小时代》的新格局。他回到了严歌苓的小说,其实是回到一个以“文学”为中心的历史情境之中,也是重温“第五代”的恢弘的旧梦。其实,今天的写作也改变了,当下以类型文学和网络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写作也是历史的变迁带来的,我们终于有机会有了更为平常的人生、更为世俗也更为具体的生活。 2013年,《小时代》和《小时代2》连续上映,变成了一个“事件”。一面是粉丝的热捧,一面却是激烈的抨击;一面是电影院中的观影人流,一面是媒体的口诛笔伐;一面是飙高的票房;一面却是文艺爱好者和评论者的尖刻嘲讽。郭敬明导致了某种舆论的分裂,而这种分裂贯穿于从纸媒到互联网和移动多媒体客户端的整个舆论。这里似乎一面是代际的分裂,年轻人和老一代在郭敬明的面前态度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在老一代抨击他的作品的时候,年轻的粉丝是支撑起他的最主要的人群;另一面则是趣味方面的分裂,更为专业的文艺趣味的人往往对于郭敬明的电影持批评态度,而许多普通的年轻人却是郭敬明的拥趸。但《小时代》却是异常清晰的当下的电影,它的青春表达就是以当下为原点的。 它要向观众表达的是一种宣言般的展示,展示的是今天的“小时代”的种种形态。这里没有可以缅怀的过往,只是正在青春面前展开的日常生活,就像电影里一个突兀地插入的片断:杨幂扮演的林萧从一个我们熟悉的老式的弄堂出来,沿着她的视线望去,一个巨大的类似金属般光洁透亮、一尘不染的巨大的广告般的大字呈现在高楼林立的背景之下,这就是电影的片名“小时代”。这三个大字从侧面开始直到占据了整个银幕,这似乎是郭敬明用格外大的方式将“小”时代凸显在我们面前,让忽略了时代之“小”的人们不得不正视这难以面对的“小”。 这个“小时代”是以缤纷的色彩、迷人的光洁度展开的。《小时代1》的中心故事是一场由这些女孩子参与的大型的时装秀,而这场秀所引发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的复杂正是这部电影的故事高潮。时装秀是城市的最佳象征,也是这部电影的最佳象征。它隐去了背后的一切痛苦、焦虑、追逐和争斗,最后所呈现的是美轮美奂的一切。这些都是在看不见的“资本”的流动和生产、消费的链条之中的“展示”环节。这一切中的漂浮感和光洁度都让人产生时髦的印象,而这种金属般的非常的时尚感是这部电影刻意要展示给我们的感觉。它好像是一幅抽象的绘画,只有线条、面块和色彩,就好像是一个飘浮在现实的城市之上的抽象城市,城市里的那些黯淡、混乱、庸常和乏味都已经消失了。景观的抽象与漂浮,是这部电影让我们印象深刻之处。所有的人和事都飘在现实的城市之上,好像是城市的未来在现在的展开。 这个形象是抽离了城市的历史和记忆的无可置疑的“当下”,它是在新的消费和时尚的生活方式之中的现世性的展开。这是刻意渲染的当下之“酷”。这种“酷”并无现代性的那种深度,而是在一个亮丽的平面上滑动的景观和故事的展开。其实,这也正是以文化创意支撑的当下的消费城市的特性。工业生产的支撑体系在此早已隐在了都市的消费生活之后,这个体系虽然仍然不可缺少,却像当年农业被纳入了工业化之后就隐在了工业之后一样,现在是以消费为中心的、以文化创意为先导的时代了,这就是所谓的“后现代”的空间感的出现。因此,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做《M·E》的杂志就绝非偶然。这里没有传统的工业大亨出没,也没有那种庸俗的炫富的气味,而是在优雅和精致中所显现的以文化创意为主导的、以时尚的展示和表演为中心的新的生活方式和空间。这些让生产隐在看不见的后景之中,这其实喻示了今天的社会真正的“后现代性”的呈现。 而这个杂志的主导者宫洺很像是郭敬明的自我想象,他引领着时尚的潮流,主导着时尚杂志,从而规划了都市人的生活轨迹。而他又富于文艺气质,有优雅的品味和奢华的生活。他的家就在一座透明的、金属般光洁的房子中,他孤独而冷静,但在和林萧的接触、对周围世界的感知中又刻意地彰显了他的文艺气质和敏感的心灵。这样的状态似乎是郭敬明本人自我想象的一部分。这本叫作《M·E》的杂志,何尝不是郭敬明以“最”为系列的出版业的象征。几个年轻女性既是现实的人物,她们有现实的苦恼、现实的追求与期望,但她们又是抽象的符号,是当下都市青年女性的某种表征而已。 四个女生的不同性格,其实是有点刻意地模仿《欲望都市》中四个成熟女性,是其青春版,而和她们发生感情和事业纠葛的男性,都异常的潇洒和英俊。这些人在亮丽外表下的追求其实还是和我们现实的世俗生活并无不同。他们的事业和爱情也还是基本的“人性”的展开。分分合合、恩恩怨怨之间既有金钱和名声的世俗挣扎,也有真切的欲望和渴求;既有小白领遇到的现实困扰和苦恼,又有优雅品味和文艺气息的展开。这些都是回归到“个体”的感受之中的表达。在郭敬明的电影之中,个体性的“自我”始终是一个最现实而具体、超验又浪漫的神秘之物,他的世界就存在于个体与周边的“小时代”的关系之中。而小时代折射到个体感受之中的感觉才是中心,个体性在郭敬明这里并不受到群体性的制约,而是在一个以感觉为中心的世界中存在。但这种感觉却是以与小时代的潮流之间的契合为中心的。其实,郭敬明所受到的赞美和批评都来自这种个体性的存在。一方面这种个体性推崇自我感觉而有某种超俗的意味,但另一方面又以迎合时代的时尚潮流和消费风尚而相当世俗。这种矛盾性其实是郭敬明内在的复杂性的所在,也是赞美和厌恶的来源。 这部电影的有趣之处是它来自郭敬明本人的小说。作为小说,《小时代》仿佛仅仅是电影的一个“草稿”、一个前奏,或是一个初稿、轮廓、一个初步的展示。郭敬明点明:“在刚开始写《小时代》这部小说的时候,就已经笃定地看见了它被影像化的那一天:‘我是把小说向适合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路线去写,包括人物构架、剧情发展和画面感等等,这样改编起来难度就没那么大。’”①而作为电影,对于郭敬明来说,他多次陈述这部电影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它标举的小时代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的时代在许多人来看是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是以世界的剧烈变化为标志的,而在这些变化之中,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崛起正是大时代的一个最为明显的象征。大时代里有许多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事情已经而且正在发生。世界在激变,权力在转移,格局在重组,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大事件正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周围世界的变化似乎是最大和最快的,但与此同时,这个时代又难免是一个“小时代”。这里剧烈的历史变化不再来自金戈铁马、气壮山河,反而是在全球的普通人追求舒适的生活的欲望的满足而形成的全球性的生产和消费的链条之中实现的。这个时代从过去人类恢弘的历史来看,肯定自有其平庸性。因为这里没有“现代性”的恢弘革命和动荡的宏伟图景,而是一种后现代的平面性和日常性的生活,一种被消费主导的感性的生活世界。“大”不再是轻易地、直截了当地作用于每一个人的命运的真实之物,而是一种在“小”中渗透和展现的隐秘的历史的趋势。而“小”才是随时浮现在我们身边的状态。因此,我们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小”里见“大”、“大”在“小”中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基础正是在“小”中展现的,也只有从零散化的、点点滴滴的“小”,我们才可能发现“大”的踪迹。 事实上,郭敬明是一个传奇,是十年来“青春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对于他,从来就有诸多争议,但他的小说所引起的持续的关切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他的故事如果从一个“大时代”的走向来说可能仅仅是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但如果从一个“小时代”的角度,却是当下社会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对于时代的“大”,可能他和他的《小时代》是“小”的,但对于时代之“小”,这本书和这个人就可以说自有其“大”影响和“大”作用了。《小时代》当然是郭敬明前几部小说的延续,但又是独特的发展,我们也从中可以看到郭敬明强烈的企图心和把握他的读者的能力。小说一开始就以一种对于都市的整体把握的气势描写了上海,但这和《子夜》开头的那段对于上海的描写其风格大相径庭。《子夜》里是一种中国“现代性”和工业化在20世纪30年代那个第一个时期的大全景,茅盾力图以此写出历史的高度的整体性,从此展开的是一个城市的“大历史”的全景展示,而郭敬明此处则是从上海的今天的景观出发,引出的还是几个年轻人琐碎的日常生活,从他们的感情纠葛、人情恩怨之中引出了这部小说对于今天的小时代的浮世绘般的描写。小说中的感情和生活看起来都是在今天的消费时代的生活和文化形态的最为直接的呈现。他们的故事如同碎片般地缺少整体性,是被诸多时尚和商品所呈现出的一种独特的都市经验。 郭敬明用许多品牌和生活风格的描写点缀了他的小说,由此形成了一种当下上海的氛围,而这种氛围在郭敬明的笔下也是和全球的年轻中产阶级的趣味和潮流相适应的,是当下全球化的一部分。这些人虽然生活在一个具体的上海,但他们的故事却是在一个“无地域”的空间中发生的。上海虽然有其具体性的呈现,但这里的背景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抽象。这里的商品都是在全球移动之中的“全球商品”,这里的本地生活其实也是抽掉了本地性的人生。因此,影片中所出现的对于这部小说的“迷”的青少年的现象其实是对于一种新的、跨出本地限制的全球性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其实以上海为媒介,跨向一个抽象的全球商品的展现。如果说,《子夜》要将上海“缀入”到全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加以呈现,那么,《小时代》则是直接将上海抽象化为全球性的消费关系。 这里的故事和纠葛都是在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梦想和困扰之中所呈现的。这里的人生活奢华时尚、多愁善感、趣味高雅,似乎有一种“不及物”的抽象感。他们的名字和生活都好像是在移动的影子,但这些故事里其实所纠缠和扭结的依然是人类基本的情感,有爱恨情仇、痛苦焦虑和快乐欣慰,而这些情感的背后却依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财产关系和血缘关系,这些关系和中产阶级梦想的生活状态是一种奇妙的结合。我们在时尚杂志或者时髦的电视节目中所见到的那种“高端”生活被郭敬明写得相当生动和有趣,这些似乎已经是在全球的顶端上发生的。这里的一切不像中国现代小说如《子夜》般是“大时代”的投影,而仅仅是一个小时代里的悲欢离合,郭敬明所操心的不是“大时代”的是是非非和历史抉择,而是已经生活在这个状态中的人们所构成的小时代的剪影。他的人物一方面生活在“现实”之中,但另一方面,这现实又如同在橱窗或者从玻璃窗外面看酒店内一样是一个抽象、一个具体之外的空间。这些在小说中都是“草稿”,而在电影中最终有了“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郭敬明和他的读者正在一个新的日常生活之中,需要新的可能性。他们现在需要新的想象和梦想来构筑自己生活中超越具体性的部分,郭敬明能够给予他们的,就是这样的想象。这其实是一个“小时代”真正的自我想象和自我认同的呈现。看起来虚幻,其实真实。于是,郭敬明以“全球性”商品其实达到了一种“全球本土性”的产品,这似乎是某种历史辩证法的呈现。小说和电影都是郭敬明的产品,而电影成为了《小时代》最终的结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电影对于文学新的支配力,这里的文学已经远非严歌苓式的“纯文学”,而是一种以“青春”为基础的“类型文学”。电影在这里比小说更具有高度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张艺谋和当年他所持有的文化逻辑的颠倒和解构。 从张艺谋和郭敬明,我们看到今天并置的关于电影和文学不同的想象和现实关系。这个关系所构成的张力其实不是今天的社会中所独有的,而是现代中国内在的文化张力的一种展开。 在中国现代文化中,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已经是一个长期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被柯灵多次进行过深入、透彻的阐发,我在多年前将其称之为“柯灵命题”②。这个命题的核心观念,就是中国电影的历史是“启蒙论”超越“娱乐论”的历史。“柯灵命题”从根本上认为文学是电影的中心,电影就是文学的衍生之物。柯灵曾经用极为生动的方式比较了文学和电影在“五四”之后的差异性: “电影与文学各有自己的炎凉甘苦,不可同日而语。‘五四’以科学、民主为旗帜,西方文学名著的介绍传译,对新文学的思想倾向、艺术风格,产生极大的推动力,欧风美雨,起了精神上滋润催化、吐故纳新的作用。而电影却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品,带有资产阶级烂熟期的气息,不邀自来,充当‘铁盒里的大使’,其使命是垄断落后国家的市场,实行经济和文化双重渗透,喧宾夺主,给新生的电影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种处境,和文学事业也截然不同……电影群众性最广,但当时几乎局限于小市民圈子,被正统的文艺界鄙视为不入流的玩意,不但新文学读者与旧电影观众自成畛域,河水不犯井水……左翼文学运动与进步电影运动,本质虽并无差别,情形却大不一样:前者可以靠作家在亭子间里用笔呼风唤雨,后者却需在摄影棚里和红男绿女各色人等打交道,而且不得不受制于资本家的生意经络,用夏衍同志简洁的语言来说,就是‘寄人篱下’。革命与艺术的崇高理想,老板的钱袋实际,观众庸俗口味的惯性,要三者兼顾,难度之大,不问可知,何况还有残酷无情的政治压力。”③ 这些表述都指向了一个电影是文化的次等类型的文化秩序的确立。“五四”新文学被凸显为思想和艺术自由追求的产物,而电影则是一个被观众和资本所限制的类型。它在早期和“新文学”当然不能比拟,但就是到了左翼进入的上世纪30年代,也仍然是不能和文学相比的类型。 “柯灵命题”可以说一直是中国电影和文学关系的基本的思考框架。多年来,这一命题似乎从未动摇过。电影从当时到“第五代”都是以一种次等的文化产品,难以产生文学这样丰富的意义。“第五代”从《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红高粱》直到今天时空已经完全转换的21世纪的《归来》,文学是加在他们身上难以摆脱的魔咒,也是无尽的灵感和激情的来源。这是“柯灵命题”的“现代性”意义的展开,它建立了一个“电影观众”和“文学读者”的等级关系,从而建立了一个关于“电影”和“文学”的等级关系。“文学读者”是“现代性”的精英知识分子,而电影观众则是大众化的“市民”。我曾经点出,这个“市民观众”的存在,和他们的观念似乎是对于精英的“现代性”的对照: “中国‘现代性’自晚清以来在都市区域所创造的‘市民大众’对于电影的决定性的作用。这些都市大众观影者的存在和居于主导地位的状况,正是中国电影一百年来一直存在的历史景观,所以,‘现代性’一方面生产一种‘启蒙’和‘救亡’的宏大的叙事,另一方面,还生产一种平庸的、以现代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为基础的日常生活和市民生活。‘现代性’创造关于自身的宏伟的历史图景和‘大历史’的壮阔画面,但也创造了都市的、脱离了传统农业社会的平庸的日常生活。而都市的市民观众正是置身于这种平庸的日常生活之中的。他们当然会受到启蒙和救亡的感召而参与大历史的进程,但仍然大部分时间生活于自身平凡的‘小历史’之中,这种‘小历史’即使在中国语境中也类似齐美尔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所描写的状态。由于现代都市完全破坏了原有的传统社会的结构,现代市民不得不面对个人的复杂的生存环境,他们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精于算计、以世俗的理性对付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的市民和传统社会的人不同,它们的社会性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形态,是以财产的存在为基础的。个人的权利和生存状态,都脱离了传统社会的有机的结构,而是变成了独立的劳动力,存在于现代的工业社会的‘现代性’之中。 “这种‘市民观众’的存在,正是中国电影的基本的存在条件。这种条件当然来自于电影的工业化的程度和对于都市生活的依赖性。电影的工业化程度决定了它的生产必须在大规模消费的基础上才可能得以延续,而‘影院’的文化则始终是与都市生活相联系的。影院一方面是城市生活的象征之一,它其实表明了都市性的聚会的特征,个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地置身于幽暗的厅堂之中,体验一种梦幻般的感受。另一方面,在物质上,电影院本身依赖于整个城市系统的支撑,是电影产业的消费的最后的环节,电影的物质性的实现不得不以所谓‘票房’的方式得以展开。这说明,电影不得不在自己的‘市民观众’的存在中展开自身。”④ 在这里,文学是“深度”和“精神”的象征,而电影则是次等的,是对于文学的影像的阐发。这里的观念深深地受到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观”的影响和支配。“文学读者”是“现代性”的启蒙精英的“知识分子”,而“电影观众”则是现代社会芸芸众生的“市民”。电影其实是一个“转换器”,它的功能就是将文学所传达的高深而丰富的内容“转化”为“市民”观众易于理解的影像。这个观念其实在张艺谋这里也并未改变。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不少文学界人士对于张艺谋对待文学改编的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张艺谋利用电影和传媒的优势调用文学了。但今天看来,张艺谋的所作所为仍然是在“柯灵命题”的“现代性”疆域之内,而郭敬明则超出了“柯灵命题”,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之中。 这个新的状态一是来源于中国文学“新世纪”以来的深刻变化。目前,一方面是纸质出版和“网络文学”双峰并峙,另一方面在纸质出版方面,传统的“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青春文学”的共同发展也已经成为新的趋势。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郭敬明和韩寒等人为代表的“80后”作家出现到现在,“青春文学”的在传统纸质出版业的市场已经显示出了自己重要的影响力。目前的情况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简单,“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崛起并不是以传统的“纯文学”的萎缩和消逝为前提的,其实三者不是一种互相取代的关系。传统的文学写作仍然在延续和发展,我们发现传统文学界仍然相当活跃。这是新的文学市场的出现,也是文学的一个新的空间的发现,它们和传统的文学界其实是共生共荣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它是文学总量的增多,而不是文学的萎缩。它们和传统文学既有重合、相交和兼容的一面,又有互不兼容、各自发展的一面。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结构性的要素,而不再是一个时间滞后和空间特异的“边缘”的存在。它已经不再是巨大的被忽略的写作,而是一个全球性文学的跨语言和跨文化阅读的必要的“构成”,是所谓“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文学不仅是全球华语文学的中心,也是新的“世界文学”的新空间。 这个新的状态二是源于中国电影的新的崛起。电影和它的观众在“新世纪”大片时代之后,特别是近年来经历了电影的“全国化”⑤的进程。中国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电影未来最大、最具吸引力的新的空间。它一方面是全球电影未来的大市场,另一方面则是全球电影最具增长性的生产和制作的电影运营和制作中心。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这一前景已经越来越清晰了。中国既是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市场,同时又是最有吸引力的制作空间。这种双重性其实正是这个新空间所呈现出来的,而这种新空间正在改变电影百年来的整个格局,其意义难以估量。它意味着中国电影在全球文化中的意义已经凸显了出来,但这个意味深长的崛起,却有诸多突破2002年以来的“大片”所形成的既定格局的新的趋势。在这些新趋势中,最具有关键意义的是二三线城市和县城的观众的崛起以及互联网造成的电影的新变化。这种崛起和变化决定了中国电影的未来,也决定了世界电影的未来。如果说,我们在过去一直看到的电影的“全球化”的趋势对于中国的冲击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电影开始展开了自己的新的力量,它开始对于全球电影形成冲击。这种冲击当然未必是中国电影本身的影响力在全球的冲击,而是中国内部的结构性的变化影响和制约了世界电影的未来走向。 由此看来,文学和电影的关系还是居于这样一个内在的张力之中展开,但这不仅仅是张艺谋和郭敬明之间的张力,也是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张力。我们还需要在这一张力之中继续探究。 注释: ①电影档案:郭敬明和他炮火连天的〈小时代〉.http://enjoy.eastday.om/c8/2013/0705/2717602232.html. ②张颐武.超越“启蒙论”和“娱乐论”——中国电影想象的再生.当代电影.2004(6). ③夏衍电影剧作集(序言).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1. ④张颐武.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6. ⑤从2011年6月开始,我连续发表了关于中国电影的“全国化”的系列文章,系统阐释了三四线城市电影的崛起的意义和可能带来的中国电影格局的变化。可供参考:“全国化”与电影.当代电影.2011(6);“全国化”的常态化.当代电影.2012(3);在“全国化”的平台上突破瓶颈.当代电影.2012(9);全球化的全国化:2012年中国电影图景.当代电影.2013(3).标签:电影论文; 文学论文; 郭敬明小说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小时代论文; 郭敬明论文; 归来论文; 张艺谋论文; 红高粱论文; 子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