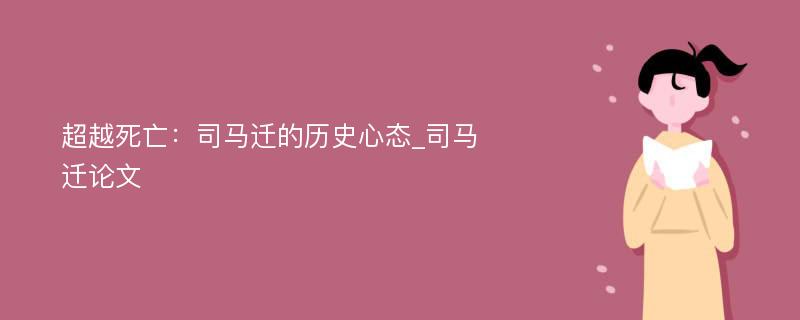
超越死亡:司马迁的著史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马迁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从司马迁对死亡问题的思索中,探讨他坚定著史的信念和著史的心态。作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本身就是人超越死亡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拚搏,与命运对抗,以获得永存的、不朽的人生价值,从而也就取得了对死亡予以否认的胜利。司马迁的人生历程及著史心态正是如此。
生与死,是人生面临的永恒难题。“人固有一死”,活活的生命面对这一逃避不了的灾星,不能不思考人生的价值问题:人如何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让生命具有意义?又怎样超越有限的人生,使生命获得不朽的价值?本文从司马迁对死亡问题的思索中,探讨他坚定著史的信念和著史的心态。
一 生死之间的抉择
在普通人的一生中或许很少思考死亡问题,孔子所谓“未知生,焉知死。”即代表了中国文化“重生轻死”的思维取向和注重生存实践的人生态度。但是,当人们直接面对死亡的时候,再也回避不了人生中这一难堪的问题。司马迁对死亡问题的思索正源自于他的悲剧命运。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酿成他个人生活中的最大不幸。天汉三年,汉将李陵兵败塞外降于匈奴,被视为“失节”,在朝臣一片非议声中,司马迁仗义执言为之辨白,想以此宽慰汉武帝,不想反而触怒武帝,蒙获“诬罔主上”之罪,按《汉律》“当死”。依汉代旧例:死囚可纳钱赎死,或以宫刑代死。而司马迁因家贫“财贿不足以自赎”,亲朋故交、朝中大臣又“莫为一言”为之说情,因此,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引颈就戮,要么下蚕室受腐刑。生死抉择的关头何去何从呢?
求生的欲望与对死亡的避离是人类共有的天性,“人情莫不贪生畏死。”[①]正是司马迁道出了这一人类共同心理。面对生与死的抉择,司马迁又是如何想的呢?在他看来,生为世人,最起码要保持做人的尊严,“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②]因此,如果选择腐刑来逃避死亡,将受人生最大的污辱,无异于人格上的自杀。而对于死,司马迁当时是并不畏惧的。他自言:“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③]因此,也就没有常人面对死亡时对家庭的萦怀牵挂;而作为史官世家出身的司马迁,也是信奉“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准则的,他说:“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④]在生与死的选择时,连身份卑贱的奴婢还知道为保持人格尊严而“引决”,何况身为士大夫而又死罪在身的司马迁呢?从现实情形和保持生命的尊严上而言,司马迁是没有畏死之心的。
但是,真正面对死亡时又逼使他思考生命的价值:“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⑤]正是在对生命价值“泰山”与“鸿毛”的轻重比较中,司马迁产生了求生的愿望。
身陷囹圄的司马迁回顾个人的人生,以中国文化中“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衡量,深感自己是不能轻易放弃生命的。从个人道德上言,“孝”为五伦之首,“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以孝之大也。”[⑥]而此时的司马迁,功名未成,父亲遗命的修史事业“草创未就”;从社会责任而言,身为史官而“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坠先人之言,罪莫大焉。”[⑦]因此,在这个时候“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⑧]正是出于做人的基本道德与社会责任心,使司马迁觉得必须活下来,“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⑨]
生死之间,司马迁终于选择了生。但是,他对生的选择,并非是对生的简单贪恋与对死的尽可能远的避离,而是在对人生价值思索后获得的一种抗拒死亡的意识,他的这种对死亡的抗拒决不是本能的、下意识的,而是高度自觉的。因此,可以说司马迁对生的追求,是他在面对死亡的命运时所获得的一种生命意识,他要以坚韧不拔的生命力量,赢得做人的尊严,赋予人生以不朽的价值,这不正是对死亡真正意义上的对抗,和对死亡的胜利与超越么?
二 忍辱偷生为著史
司马迁虽然活了下来,但作为“刑余之人”、“闺之臣”,面对世俗的“谤议”,乡党的“戮笑”,可以想见是多么艰难,“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匆匆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⑩]死亡刺激他思考生命,痛苦逼使他反思人生,悲惨的处境激励他寻求出路。正是肉体与心灵的巨大创伤,促使他的人生观发生了变化,在其余生中,他以顽强的毅力完成“千古绝唱”的伟大史著,从而超越肉体的死亡,谱写出一曲生命不朽的颂歌。
李陵事件之后,司马迁人生观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绝意仕途,超脱于世俗功名之上的心态。司马迁生当汉武帝时代,在这个国力鼎盛、开拓疆土的时代,也正是英雄辈出,士大夫建功立业的时代。时势所趋,青年时的司马迁也如同时代的士大夫一样,走着一条读书做官,建功名于世的人生之路,他大约25岁时就“仕为郎中”。在汉代官僚系统中,郎中一职虽不过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的宫廷侍卫官,但因为亲近皇帝,时常侍从皇帝出巡,常有机会由“内廷”外调,得为“长吏”,因此成为许多官宦子弟追求仕进的捷径。年轻的司马迁也很得意于“出入周卫之中”,并很快表现出他的才干,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在元鼎六年曾代表朝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11)元封三年,他终于由内廷外调,继父职为太史令,从而真正侧身“卿大夫”之列了。正式步入仕途的司马迁,更加热心于功名事业,以至于“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12)这时的司马迁,不仅自己在仕途上锐意进取,还写信劝隐居的朋友挚峻出来为朝廷建功,他称赞挚峻“材能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荷累其名,固己贵矣。”(13)但绝不赞成那种“独善其身”的处世态度,对挚峻宁为山隐士不肯出来做官的作法大不以为然,从中可见当时司马迁热心功名的心态。
及至出狱之后,司马迁对世俗功名的态度发生根本的变化。他虽已“身亏不用”,但汉武帝仍然任命他为中书令,“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14)这比“秩六百石”的太史令可谓位高禄重了。但是,大劫之余的司马迁却自认中书令一职不过“为扫除之隶”、“闺阁之臣”,并不以这个“尊宠任责”的职位为荣,他虽无法拒绝汉武帝的“宠任”,但行事无非奉命而已,再也没有从前那般主动、热心了,过着一种“隐于朝廷”的官宦生活。他的这种“应世”态度曾引起朋友任安的不满,写信给司马迁“责以古贤臣之义”,并“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面对朋友好心的诘难,司马迁只以“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15)为托辞,来表明自己无意仕进,甘心寂寞的淡泊心迹。
他的这一人生观变化还体现在他对“史官”一职的认识上。先前任太史令时,他对自己史官世家及现任职务是颇为自得的,虽然位卑秩轻,但他认为自己担当的是绍周公、孔子之绪业,正历代得失兴亡,品评古今人物的重任,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16)一副天降大任、义不容辞的豪迈之气,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出狱之后,惨痛的经历使他得以重新审视“史官”的现实地位,从而认识到:“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17)这一认识的变化正是他厌恶世俗功名、绝意仕进的心理动因。
在经历了从热衷仕进到“隐于朝廷”的心态转换之后,司马迁虽然泯灭了追求世俗功名之念,但他并没有由此否定人生、走向颓废和避世之途,而是重新标定自己的人生方向,重建人生价值观。他以古代遭厄之士的人生追求激励自己:“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18)从中吸取到一种超脱于命运之上的精神力量。因此,他能勇敢地面对世俗的眼光和自己悲惨的处境,将余生寄托于著史的事业上,以舒其心中之郁结。正如他的自诉之言:他之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19)尤其是在对“史官”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之后,他执着于著史的目的决不再是求取世俗的功名利禄,而是将它作为一项不朽的人生事业,来实现对肉体死亡的超越,所以,他在写完之后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赏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20)
司马迁在遭李陵之祸后的“破悟”,既是他在逆境中求生的人格自觉和人生价值的自我发现,力图以著书立言求得不朽来洗刷耻辱,重新搏得人格尊严的追求,更是他在对死亡问题的沉重思索之后,为实现生命的价值和对死亡超越的人生选择。
三 秉笔直书写信史
史家著史,应当客观公正,如实直书,因此,“善恶必书”是对中国史家的基本要求,“信史”、“实录”成为评价一部史书优劣的重要标准。
司马迁之前,中国史家著史精神的最高境界是“南董风范”。据《左传》载:晋国发生内乱,执政赵盾出逃,其族人赵穿射杀灵公,晋太史董狐敢于当面指斥赵盾,并坚持在史书上直书“赵盾彤其君”。公之于朝。表现了董狐不惧权势,坚持直书的史家精神。尤其令人敬佩的是齐国太史:齐国执政崔杼杀庄公,“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上,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21)齐太史兄弟与南史氏这种前仆后继、以死抗争,坚持写史原则的精神,为后代史家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孔子称他们是“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史家不惧权势,敢触时讳,如实直书,难免招来杀身之祸,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象董狐、齐太史、南史氏那样的“良史”并不多见。许多史家为自身免祸往往采用“曲笔”或“隐讳”的方法,连孔子也不能例外。孔子修《春秋》,因其“善恶必书”而使“乱臣贼子惧”,但这仅局限于写往古史事上,由于与现实关系较远,可能无所忌讳,一旦涉及当时的人与事时,孔子又主张“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一主张也反映在他的史著中,正如司马迁所指出的:“孔子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22)由此可见,史家要真正做到书法不隐,善恶必书是多么不容易。然而,司马迁写史却敢于“直书”,为后人留下一部堪称“实录”的信史。历代史家写史时,最难下笔的是本朝历史,尤其是当朝权贵的一些不光彩的历史,而《史记》从远古一直写至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全书用一半的篇幅重点写西汉的历史,这已是司马迁的过人之处。尤其在史书内容上,真正体现了他敢于“直书”的写史原则。如写汉代开国之主刘邦,司马迁既写他足智多谋、知人善任的一面,又写了他阴险狡诈、无信无义、轻侮士人的流氓无赖的一面,为后人留下一个真实的汉高祖形象。特别是对于“今上”汉武帝,司马迁敢于指谪他好大喜功、迷信方士、刻薄寡恩,以及任用“酷吏”,滥杀无辜等方面的过失。如在《汲郑列传》中,司马迁借汲黯之口揭露汉武帝假仁义的面孔,直言“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主要写了十个凶残的酷吏,其中除绰号“苍鹰”的郅都为汉景帝时人外,其余全是汉武帝所任用的,通过写张汤创立“腹诽之法”,王温舒的“好杀伐行威”,来揭露汉武帝严刑峻法的残暴统治。正因为司马迁坚持这种著史的原则,其人其书得到后人很高的评价,刘勰称《史记》“实录不隐”,连对司马迁多有批评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迁有良史之才”,《史记》“不虚美、不隐恶。”(23)
古代史家秉笔直书而惨遭杀戮的历史教训,司马迁是相当清楚的,但他又为什么敢于“直书”,真正做到“书法不隐”的呢?对此,有人认为是司马迁借写史来发泄自己对汉武帝的“私愤”,因而称《史记》为“非贬孝武”的“谤书”(24)。这显然是偏颇之辞,因为司马迁同样写了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疆土的丰功伟业,并非只贬不褒。我认为,司马迁之所以能做到“善恶必书”,除了中国史家传统精神的影响外,与他的悲剧命运和人生态度实在有着极大的联系。一方面,在司马迁的生活历程中,已经受了一次死亡的考验,对死亡有了清醒的认识,从而具有了不惧死亡,并超越死亡的意识;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能够忍受常人不可忍受的痛苦,苟活于人世之中,是他将修史作为余生唯一的寄托,必须为后人留下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方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洗刷自己的耻辱。因而,他也就获得了一种敢于迎向痛苦,触犯死亡,从而超越死亡的精神力量。秉笔直书,敢触时讳,正是他的生命意识和人生价值观在修史笔法上的体现。
四 慷慨悲歌颂英雄
司马迁的悲剧命运促使他思考死亡,反思人生,从而坚定了著史的信念。他不仅以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来实现其人生价值,阐释与宣扬个体生命对死亡的超越,而且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感受、哲理溶入史学作品的人物形象之中。
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记》称得上是一部“英雄史诗”。在这个历史大舞台上,上至帝王君主、王侯将相,下至迁客骚人、游侠刺客,无不以其人生历程展示个体生命的价值。尤其引起司马迁心灵共鸣的是那些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据粗略统计,在全书120篇人物传记中,以被杀、自杀而终的人物标题就有37篇,加上没有标题而命运相同的人物共约70余人,他们的人生命运都充满悲剧色彩。在作品中,司马迁以同情的笔调叙写他们的坎坷经历,为之悲愤、感叹,更以充满激情的史笔颂扬他们为实现人生理想与追求九死不悔的精神,其中倾注着司马迁以血泪溶成的人生感受。在司马迁所称颂的“英雄”中,大致有如次几种类型:
一是敢于与命运抗争至死不悔的英雄。司马迁笔下的世间人杰,往往命运多舛,生活道路坎坷曲折。虽然他们遭受人间诸多不幸和苦难,甚至于肉体毁灭,但没有一个人在精神上走向崩溃和颓废,反而以昂扬的生命与命运抗争,充溢着至死不悔的英雄气概。比如项羽,司马迁着力表现他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之气,虽然最终失败,夜走乌江,英雄末路,但他至死还在执着地呼喊:“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写出了一个敢与命运抗争的英雄形象。又如孔子,司马迁写他一生困顿、潦倒,但他百折不回,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到处奔走游说,“皇皇然若丧家之犬”,是一个以韧的精神与命运抗争的英雄,司马迁破格升其为“世家”,并以“高山仰之,景行行之,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25)。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情。
二是为保持人格视死如归的英雄。在现实生活中,人生命运无常,难免遇到各式各样肉体上的打击与精神上的挫折,人格与生存的冲突往往成为人生中的一大难题,司马迁自己的命运即是如此。他自己虽然选择了受辱而生,但他对那些为保持人格不惜一死的英雄仍是十分景仰的。比如《伯夷列传》写身为殷商遗民的伯夷、叔齐,发愤不食周粟,避于首阳山中,“采薇而食”,终至饿死。司马迁并不是从二人对前朝的愚忠去称赞他们,而是称赞其“积仁洁行”的高尚人格,将之置于“列传”之首。
三是为实现人生价值忍辱负重的英雄。面对人生的困窘,死是一种解脱,相对而言,在屈辱中生存更需要勇气和毅力。司马迁为完成其“名山”事业,不惜隐忍苟活,他的这一选择在当时真可谓“可为智者道,难与俗人言。”而他的一腔悲愤也只是寄情于作品中的人物身上了。因此,他一面赞叹、景仰为保持人格而死的英雄,一面又发出“勇者不必死节”(26)的沉痛呼喊,称赞那些为追求人生价值屈辱而活的英雄。西伯被拘,孔子困厄,屈原放逐,左丘失明,孙子膑脚,不韦迁蜀,韩非囚秦而发愤著作,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而韩信受裤下之辱,终成一代良将;伍子胥“隐忍就功名”,不愧为“烈丈夫”,司马迁由此而感叹:“向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27)何尝不是司马迁的人生写照。司马迁以自己的不幸去推测他们的心境,以他们的遭遇印证自己的不幸,在为古人鸣不平时,也是在为自己高唱人生悲歌。
四是舍生取义,反抗强暴的英雄。司马迁人生悲剧的深层原因就是封建专制统治,在这种制度下,人命如草芥,无所谓个体生命的尊严与价值,也不容许独立人格的存在。司马迁激于义愤为李陵辨白所造成的人生悲剧,也正是历史的悲剧。在专制统治开始强化的汉武帝时代,司马迁虽然还不敢公开挑战专制强权,但他从自身命运的思索中真切地体会到专制统治的冷酷和对人性的扼杀,并将这种批判意识体现在其作品中,通过描写那些敢于反抗强暴,为自己认定的“正义”不惜生命的侠义英雄,讴歌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在《史记》中他专为“游侠”、“刺客”立传,称赞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28)的侠义精神。在《刺客列传》中,写豫让不惜漆身吞炭、毁容变姓,两次行刺不成而自杀成仁;聂政刺杀侠累,事成后自破面皮,挖眼剖腹而死;荆轲行刺嬴政,临行前一曲“易水寒”唱出人生的悲壮和大丈夫气概。司马迁由衷地赞叹:“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29)司马迁对游侠、刺客的称颂,虽受到班固“是非颇谬于圣人”(30)的指责,但其中所蕴涵的真意又哪里是批评者所能理解的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本身就是人超越死亡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拼搏与战斗,与命运对抗,以获得永存的、不朽的人生价值,从而也就取得了对死亡予以否认的胜利。司马迁的人生历程及著史心态不正是如此么!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⑧⑨⑩(11)(12)(15)(16)(17)(18)(19)(20)(23)(26)(30)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⑦ 《史记·太史公自序》。
(13) 《高士传·与挚峻劝进书》。
(14) 《唐六典》九引卫宏《汉旧仪》。
(21)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22) 《史记·匈奴列传》。
(24) 《三国志》卷六《魏志·董卓传》注。
(25) 《史记·孔子世家》。
(27) 《史记·伍子胥列传》。
(28) 《史记·游侠列传》。
(29) 《史记·刺客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