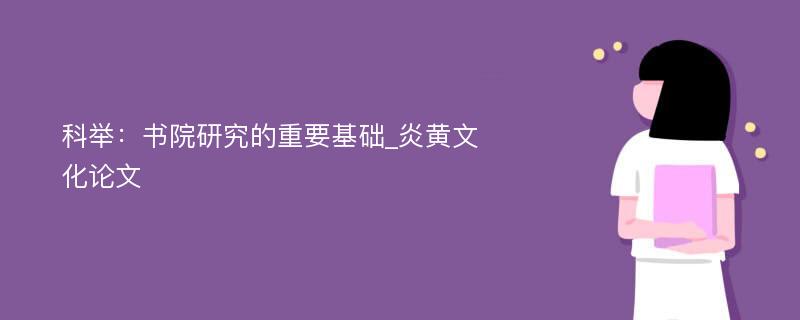
“科举学”:“书院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书院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举制度与书院都是曾经影响中国历史达1000年之久的制度或者机构,1905年和1901年清廷分别宣布废止科举和书院改制,二者几乎同时从中国的历史大舞台上消失了。在其后的百年时间内,对科举制度和书院的批判和反思越来越多,涉及科举和书院的各个层面。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相继提出建立“书院学”和“科举学”,以整合各自的研究基础,以使研究成果能与二者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相称。由于科举与书院存在着天然的联系,“科举学”与“书院学”也存在密切的关联。值此纪念科举废止100周年之际,笔者试图阐释“科举学”对“书院学”研究的重要影响,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科举学”与科举场域理论
刘海峰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建立“科举学”,并对“科举学”的研究领域进行了界定:“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注: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 由于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的基本制度……传统中国官僚政治、士绅社会与儒家文化皆以科场为中心得以维系和共生,科场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与人文教育活动的一个关键场域”,(注:刘海峰:《科举术语与“科举学”的概念体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因此,“科举学”须将科举—知识—社会关系的研究作为构建学科的主要架构。
按照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科举制度在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具有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即所谓的“科举社会”。如果套用布迪厄的理论,即是科举场域。
在布迪厄的理论中,社会是在所谓的“场域(field)—资本—惯习(habitus)”三者的互动关系中展开的。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在场域背后贯穿着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斗争的逻辑,而各种社会力量的依靠则是所谓的“资本”。“资本”在他看来主要有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它既是场域内被争夺的目标,同时又是各种力量赖以展开竞争的手段。资本与场域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在与一个场域的关系中,一种资本才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而惯习则是场域在行动者身上体现出的一种性情倾向(disposition),它一方面是为场域所形塑的,另一方面又使得场域不断地生成出来。他认为这三者是密切关联,不可分离的。
与其理论相一致,布迪厄认为在对场域进行研究时,必须采取如下三个步骤:其一,“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即场域自身的发展逻辑或存在的合理性;其二,必须分析出场域中“行动者或机构”在场域中的地位,以及为控制这一场域的合法形式的权威;其三,还必须分析行动者的惯习。(注:[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从布迪厄的这一理论出发,对科举场域的自身发展逻辑、资本和惯习进行分析和解构,进而将科举—知识—社会的关系凸显出来,以此确定“科举学”的研究领域是研究“科举学”与“书院学”关系的理论前提之一。
在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构型的科举场域中,科举制度的内在发展逻辑在于其选拔和控制功能的存在,它是各种力量互相角力的结果。从选拔功能而言,科举制度通过建立健全各项制度,选拔出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来充任管理者,(注:尽管科举制度能否通过选拔人才来促进社会流动的问题一直是科举学研究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笔者认为科举制度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考生的社会流动的,否则不但很难解释那些寒畯子弟通过科举获得一定地位的历史记载,而且诸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古代俗语亦都成为虚构,显然是有悖于常理的。) 帮助统治者实现对全国的管理,这既是对掌握“规范知识”(注:费孝通:《皇权与绅权》,载《费孝通文集》第五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76页。) 士人的最高奖赏,也是统治者实现文官治国战略思想的需要;从控制功能而言,统治者通过规范儒家知识,不仅使士人从思想上认同其统治,而且通过考试选拔少数读书人出仕做官来诱导数以万计的士人埋头苦读,达到其“牢笼”士人的最终目的。正是由于科举具有这两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功能,使得其在千年历史进程获得持续发展的空间,并形成了自身的发展逻辑。
在科举场域中竞争的各种力量中,统治者、士人和非科举出身的官僚阶层是最重要的力量。士人要想在科举场域中求得生存或者占有一定的空间,必须通过潜心学习“规范知识”,以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文化资本。一旦实现金榜题名,士人便可以获得包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科举资本(我们将科举场域中存在的资本姑且称之为科举资本)。科举资本只有在科举场域中才能存在,其内在的张力才能得到彰显。
对于社会流动途径以及职业选择都相对单一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士人来说,通过在科举场域中的竞争,获得科举资本是一种具有巨大诱惑力的选择。这样,社会自然就产生了对科举及第的渴望和崇拜,进而会内化为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并且以生活习俗、行为表现、文学形式、物质遗存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以文化遗产的形式固化下来,我们称之为科举惯习。科举惯习是在科举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它是科举场域存在与发展的潜在推力。
二、科举场域与“科举学”的研究领域
按照科举场域理论,“科举学”须将科举场域、科举资本和科举惯习的各自研究领域明确下来,以便能运用本领域的学科方法和观点开展研究,使“科举学”研究的多学科性充分表现出来。
科举场域是“科举学”研究的基础和核心。科举场域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科举的起源、科目的设置、考试内容的选择、录取的方式与名额、及第后的待遇、关防措施的建立与完善、科举文体的选择、科场大案的处理、科举的改革与废止等议题,其核心内容在于把握科举制度的发展脉络及其发展规律。科举制度在保持其自身发展轨迹的同时,必然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制约,进而会直接影响科举的发展轨迹,这是科举场域研究中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如北宋建立政权之后,为让士人认同赵匡胤通过兵变而建立的政权,并满足“杯酒释兵权”后所遗留的官员空缺,统治者极力提升科举制度的地位,采取扩大科举录取名额、直接授官、刻意选拔寒畯等措施,使科举制度的地位比唐代有明显的提高。在科举场域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少有学者留意,即科举考试的内容的选择,与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且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对学术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举场域与中国古代学术之间的关系亦应是科举场域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在参与科举场域角力的各种力量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士人的主要依靠是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主要是通过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来获得。因此,研究科举资本中首要的问题是从教育学的视角,对官学、私学和书院的科举教育进行系统研究。但文化资本显然不是唯一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会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场域的争斗中去,最典型的是家族或者宗族对士人读书应举的帮助,家族不仅能集聚经济力量,为士人提供经济资助,而且还能利用其社会地位来帮助士人,正如李弘祺先生所云:“家族之所以能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就是因为有官职的人之外,许多属于士绅阶层的人也能参与地方事务。”(注:李弘祺:《中国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及解释:从艾尔曼(Benjamin Elman)对明清考试制度的研究谈起》,载《中国书院》(第五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这表明需要对家族经济与教育、教育与科举风尚等属于科举资本的领域展开研究。
与科举场域、科举资本的研究领域相对集中相较,科举惯习的研究领域则显得相对宽泛,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科举文化、科举习俗、科举文学、科举建筑、科举文物、科举与现当代考试制度等等。这需要我们运用文化学、民俗学、文学、建筑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等相关的知识来进行挖掘,使之能更好地体现科举场域和科举资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刻影响,也反映出科举场域在传统中国有深厚的文化根基。
与科举场域、科举资本和科举惯习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一样,在“科举学”研究领域的划分上,三者的研究领域亦存在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关系。
在科举场域中,书院作为科举场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存在,或者说是科举场域中帮助士人角力的重要因素。科举是选拔人才的制度,而书院是培养人才的机构,科举场域直接和间接影响书院的发展。作为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书院而言,它是从属于科举资本研究领域的范畴。作为传播和普及儒家文化的书院,受科举惯习的影响十分深刻,是科举社会中重要的文化景观,应当与科举惯习联系起来研究。正是由于科举场域与书院有着如此密切的关联,根据科举场域所确定的研究领域的视角来深入剖析“科举学”与“书院学”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书院改制为近代新式学堂之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开始研究书院。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有学者倡导建立一门类似于敦煌学、红学、科举学等专学的“书院学”,(注:万青:《谈中国书院学》,载《岳麓书院通讯》(纪念岳麓书院创建1010周年特刊)1986年第2期;刘海峰:《“书院学”引论》,载《教育评论》1994年第5期。) 其目的在于建立书院的研究内容体系、拓宽研究领域、转换研究视角,使“书院学”取得更大的研究成果。从科举场域理论的视角出发,将“书院学”纳入“科举学”研究的范畴,目的在于进一步拓宽“书院学”的研究领域,从而更有效地转换“书院学”的研究视角。
三、科举场域是书院史研究的基础理论
作为“科举学”研究核心内容的科举场域既是认识科举制度历史真实的基础,也是把握科举发展脉络的关键。而科举制度发展、变化的轨迹不但直接导致书院的产生和改革,也是造成书院发展、起伏的直接原因,而这正是“书院学”的基础理论——书院史应该研究的最主要内容。
作为教育组织形式,书院一产生便与科举取士制度的发展密切关联。唐末五代,为获取参加进士科所需要的诗赋文学知识,不少士人隐居山林,在藏书、读书场所的基础上逐渐衍生出书院这一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可以说书院是因科举而生。北宋以后,书院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以科举为核心的文教政策的调整。北宋赵匡胤“陈桥兵变”之后,实施通过科举制度来提高知识阶层地位的政策,在朝廷无力兴学的背景下,士人们纷纷选择书院作为求学之所,这一时期出现了创建书院的热潮,涌现出多所著名书院。但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兴学之后,作为官学替代性质的书院逐渐衰败,以宣讲学术为主要功能的书院则日渐兴起。
明代朱元璋立国之初,将文教政策的重心置于兴办各级官学之上,并以入官学读书作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前提,科举与学校教育一体化,将书院排斥在科举教育体系之外,使得书院失去了唐宋以来为科举服务的功能,书院因此沉寂了将近100年之久。明代中后期,随着官学的衰败,书院再次因为适应培养科举人才的需要,而获得发展空间。
清代书院的发展受朝廷以科举为核心的文教政策影响更为明显。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代最高统治者改变了抑制书院发展的政策,将书院作为培养科举人才的主要承担者,层次不一的3000余所书院遍布全国各地,大多数书院成为培养科举人才的机构,书院承担了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清末,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之下,中国社会迈开了近代化的步伐,将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成为向教育近代化迈出的重要一步,然而书院改制的进程依然受制于科举取士制度,无法满足社会对实用技术人才的需要。直到1905年,清廷宣布废止科举取士制度之后,书院改制的进程明显加快,可以说科举停罢是书院改制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注:关于清末科举革废与书院改制的关系,请参阅拙文《清末书院革废对书院改革的影响》,载《教育研究》2005年第6期。)
元明清书院的发展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推动力量,即程朱新儒学的科举化。程朱新儒学是以书院为重要研究基地的学术学派。在元代被列为科举考试内容之后,明清八股文更是将程朱新儒学作为法定的考试内容,书院的地位便逐渐从政治边缘向政治中心迈进,其存在的合法性得到了政治认同,这是书院发展的重要内在逻辑理路。
不仅如此,“科举学”还是从微观层面深入研究“书院学”的重要前提。如书院规制的变化直接受制于科举制度的变化,为改变科举考试头场的分量太重而二三场则过轻的局面,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对考试内容的次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乡试第一场,仅试以《四书》文三篇;第二场经文四篇;第三场策五道,论、表、判等文体的考试都取消。岳麓书院根据这一变化适时地调整了教学内容。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的学规规定:“乡试第二场专试经义,不比从前附在头场,仅出拟题……嗣后官课、馆课,俱不出旧拟经题,各宜潜心研求,不可仍前止看拟题也。”(注: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48《申明书院条规以励实学示》。)
清代中晚期,科举考试重书法的倾向也直接影响到书院的教学,书院规制将书法教学提高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台湾文石书院《学约八条》提出“书法不可不习也”,其理由就是书法是场屋竞争的重要形式,“制艺俱佳则较其诗,诗律俱佳则较其字,而去取以分。”并且认为殿试、朝考都是重视楷法,要求生徒“取古今名迹,悬挂壁间,或斜置几上,细玩其用笔起止,配搭疏密长短之法,队伏整列,笔气连贯而下,无错综不匀之弊,务期意在笔先,神与俱化”。这一学规不仅对书法学习作出了严格规定,而且还要求生徒养成卷面整洁的习惯,将其作为决胜科场的必备条件。由此可见,“科举学”不仅是宏观把握书院发展史的重要前提,也是从微观层面研究“书院学”的重要知识储备。
因此,深入研究科举场域所涉及的研究领域,能极大地促进“书院学”中书院发展史、书院地理分布、书院规制、书院与官学、书院学术等研究领域的深入,而这些研究领域是构建“书院学”的重要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科举场域是研究“书院学”的基础理论。
四、科举资本是研究书院教育与管理的关键
如前所述,科举资本包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些资本是士人获得科举功名的重要依靠。作为教育组织形式的书院主要通过教育教学活动为士人提供文化资本,帮助其掌握儒家经典、科举考试各类文体的写作和基本程序之类的“规范知识”。当士人获得科举功名之后,他们往往会利用其科举资本来推动书院发展。
研究书院教育规模时,有必要借助“科举学”的相关知识,从士人获得文化资本的角度展开研究。由于科举及第的无限魔力,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士人竞相追逐文化资本。各省乡试应试者的数量是反映读书应举者人数之多的最有力证据。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赵佑担任江西乡试主考官时,应试者有八千余人之多,而这8000多人是学政翁方纲通过科试、录遗、大收等方式从全省的生员中选拔出来。(注:赵佑:《清献堂集》卷九《万寿恩科江西乡试录序》,转引自《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六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页。) 人文荟萃的江南(包括江苏和安徽两省)应乡试的生员数量比江西还要多,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超过了10000人。(注:《清史列传》卷九《傅拉塔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98页。) 按照明清科举程式,参加乡试者只占生员比例的相当小的一部分,而求学的童生数则远远超过生员数量。
不仅江南、江西这样的教育事业比较发达的省份生员人数大量增加,而且教育事业相对落后的地区读书应考者的数量也不少。如处于泰山西北的长清县虽然是一个“土瘠而民贫”的地区,但读书应考者数量却相当多,每年“应童子试者八百有奇,学使者岁取十五人入黉宫”。(注:舒化民:《宝研堂集》卷二《长清宾兴记》,转引自《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六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46页。)
在官学的数量、招生名额和生徒身份资格都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前提下,如此庞大的求学群体必然需要有数量众多、招生名额相对宽松、对生徒身份基本上没有限制的教育机构来为其获得“规范知识”提供场所,这种需求促使书院的数量、规模和社会地位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因而,书院数量的增减、地理分布、层级分布和教学内容的调整都深受士人获取文化资本需求的影响。
更值得研究的是,在科举社会中,书院是如何获得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资助的,以及这些资助对书院发展的影响、资助经费来源及管理都是“书院学”研究题中之意。为帮助家族和当地子弟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文化资本,个人和社会资助成为书院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不少人直接出资创办书院,以开展科举之学的教育。如安徽旌德县洋川的商人谭子文出白银15600余两,创建毓文书院,规模相当宏大,聘请洪亮吉、夏炘、包世臣等著名学者执掌书院,招四府一州的士人肄业其中。生徒初无定额,肄业数百人。后谭子文又补捐白银1500两,发典生息作为生徒膏火,由学政和山长选拔内外课生各50名,每人每月给银1两和5钱。毓文书院虽然由著名汉学大师主讲,但实行严格的考课制度。
乡绅和商人资助更多的是乡村书院和家族书院,他们将这些书院作为培养本地和家族子弟读书应试的场所。如湖南浏阳洞溪书院是乡绅张良赞之妻陈氏于道光末年出资创建的,书院建成之后,延请名师教导,以科举知识考课生童。(注:《浏东洞溪书院志》之《洞溪书院志序》,清光绪二十六年刊本。) 由此可见,正是士人为获取参加科举考试的文化资本需求,使得书院也获得了发展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如果说商人、乡绅资助书院是为帮助子弟获得文化资本的话,那么通过科举获得一定地位的官员利用自身的实力和地位来资助书院发展,则是科举资本对书院的反哺。明清时期,不少科举出身的官员积极参与书院的修复、创建与管理,成为书院发展的主要支持力量。
明代中后期,在可以确知创建者或修复者的书院中,明代中后期由地方官吏创设或者修复的占69%,数量达到了872所。(注:见拙著《书院教育与科举关系研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196页。) 清代不少地方大员都直接参与书院的建设。陶澍乾嘉之际就读于岳麓书院,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及第后,历官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要职。他一生十分关注书院的发展,直接参与书院的管理、建设与讲学。道光六年(1826年),率领下属捐廉,于嘉定倡建震川书院,并亲自参与考校。道光十七年(1837年),修复敦善书院,作为盐籍子弟的求学之所。次年,仿照阮元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创建江宁惜阴书舍,并制定了《惜阴书舍章程》10条,规定其讲求汉学的教育方针。为满足士人的求学需求,他捐资苏州紫阳、正谊二书院,以增加学额。
不仅像陶澍这样曾经就读于书院的高级官吏热衷于书院建设,级别较低的地方官吏也十分重视书院的建设,甚至大量捐资建设书院。乾隆年间,安徽歙县的紫阳书院出现了“堂屋墙垣年久倾颓”的局面,县官候选人、府同知、进士徐士修决定独自一人捐白银15172.9811两,用于修复、扩建书院。(注:(安徽)《歙县志》卷十五,卫哲治:《紫阳书院建设号舍膏火题疏》,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与这些官员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角度资助书院不同,不少科举出身的士人成为书院山长,亲自执掌书院的教育教学活动,以文化资本贡献于书院。在明清时期浓厚的科举氛围中,获得较高科举功名的士人即使没有入仕为官,也因科举资本而成为士绅。张仲礼先生通过研究发现,通过科举获得功名成为绅士是获取教职的重要条件,而且是比较基本的条件。(注: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9、106页。) 而在书院谋取教职又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实际上,科甲出身是书院延聘山长的基本条件,特别是层次比较高的书院,山长基本上都是由科举功名较高的学者担任。
不仅层次高的书院选择获得较高功名者作为书院山长,层次相对较低的书院选聘山长时,也明确要求被聘者为科甲出身。甘肃五泉书院明确规定:“书院掌教宜择品学兼优、专以训课为事之举人、进士,由兰州府以礼聘请。”(注:(甘肃)《兰州府志》卷三《五泉书院规条》,清道光十三年刊本。) 层次较低的书院选聘山长时,对其科甲出身的要求相对较低,府州书院一般由举人以上出身的人担任,县级、乡村书院一般是由举人、生员担任。这也就是说科举资本不仅为书院提供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而且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文化资本。
科举资本甚至还成为书院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直隶昌黎县的碣阳书院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由知县王应奎捐建的,这所书院成为当地的科甲鼎盛之地。同治三年(1864年)甲子科乡试,书院“中举五名,齐麟玉、董树柏、董光耀、孙岳龄、罗庆云,院中悬有‘五凤齐飞’匾额。”六年(1867年)丁卯科“中举三名”,其中齐锡朋为经魁。十二年(1873年)癸酉科又中举五名,副榜两名,其中经魁一名,书院悬“斗宿腾辉”匾。“至光绪年间,捷春秋榜者踵相接,皆得力于肄业考课也。”(注:(河北)《昌黎县志》卷五,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书院以科举为荣耀,也因科举而兴盛。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显然可以看到,把握科举资本的深刻内涵和基本知识是研究“书院学”中经费筹措与管理、内部运作与管理、经费与地域经济、经费筹措与科举风尚等等重要内容的理论基础,亦能拓宽“书院学”的研究领域。
五、科举惯习与“书院学”研究
科举惯习的形成是科举制度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积淀的结果。科举惯习的种种形态也在书院中得到反映,成为书院与科举结合的物质与文化的重要表征,这亦是“书院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书院学”研究过程中,将其与科举惯习的研究结合起来,不仅能深化和拓展书院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能丰富科举学的研究内涵。
考棚与书院结合是科举与书院结合最典型的物质形态。一般而言,科举考试是由官府设立专门的考试场所——贡院和考棚,书院官课和甄别考试也在贡院、考棚或者官署进行,只有师课一般则在本院进行。随着科举惯习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少书院为便于进行科举考试训练,在书院修建供考试用的考棚号舍,在为书院生徒提供考课之所。如道光二年(1822年),叶健庵重修福建鳌峰书院时,为书院建有专用考棚,规模十分宏大,可以同时容纳四百人考课。
为充分发挥考试专用场所——考棚的作用,不少地方书院与考棚合二为一,即在平时作书院教授生徒,县试、岁试、科试和考课时作考棚用,将书院和科举的融合在物质形态上推向极致。同治癸亥年(1863年),广西平乐知县方炳奎在筹划建立考棚时,建议扩充道乡书院的现有规模,使其能成为书院的组成部分。有的书院创建时就是从书院和考棚两用目的出发的,如广西柳城的鼎新书院的建筑设计是考棚和书院的结合。在清代中后期的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书院既是教授场所又是考试场所的情况不在少数,这反映出科举惯习已经对书院建设以及管理者的行为等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科举题名碑是对科举及第者的精神奖励,在中国、越南至今都还留有科举题名碑,它也是科举惯习的有形存留。这种科举题名的惯习在宋代就已经影响到书院了,徽州绩溪的云庄书院立有两块题名碑,“其一自嘉祐丙申科至端平甲午科,其一自淳祐丙午科至咸淳癸酉科。”前一块题名碑记载了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至端平元年(1234年)的178年间书院及第者的名单。另一块所记载的则是自淳祐六年(1246年)至咸淳九年(1273年)间书院登科第者的名单。(注:(安徽)《徽州府志》卷七《书院》,清道光七年刊本。) 科举题名碑既是对科举及第的褒奖,亦是对读书应举者的激励。
不仅如此,科举惯习已经成为影响书院建设者、管理者的潜意识,书院祭祀和风水的选择都要考虑科举及第的影响就是最好的证明。
清代书院一般有固定的祭祀活动,除祭祀孔子及其弟子、书院相关的先贤之外,还要祭祀执掌科名的文昌帝君。书院一般都建有文昌庙或魁星楼,出现了“文昌之祠遍天下”的局面。康熙年间,岳麓书院山长车万育、潘如安、陶汝鼐、陶之典等湘中“耆旧同建文昌阁”,供奉文昌帝君神像,并规定凡岳麓书院“诸生获隽者,悉得题名其间”,以示表彰。为保证祭祀活动的正常进行,岳麓书院设有专门用于祭祀的经费,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规定:“岳麓书院文庙春秋二祭,银一十四两。每月朔望,文庙、朱张祠、道乡祠、六贤祠、文昌阁五处香烛银共一两二钱。总共银二十八两四钱。”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湖广总督毕沅“指书院前坪田中土阜曰:‘斯地若建魁星楼,可以发甲’”,(注:(湖南)《姜化县志》卷十一,清光绪三年刊本。) 于是又增建魁星楼,以祈求岳麓书院生徒能在科场中夺魁问鼎。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十三年后的嘉庆十年(1805年),岳麓书院生徒彭浚在殿试时一举夺魁,成为从岳麓书院走出去的唯一的状元。可见,修建文昌阁、魁星楼的目的完全是为书院科举服务。
书院创建或修复者还将风水理论应用于书院选址活动上,将其视为振兴科举事业的重要因素。有的书院设置人工景点,以满足风水理论的要求。按照风水理论,若书院选址依山傍水,背靠大山(称为“主山”),而与之相对的又有一小山(称之为“案山”)则必然科甲发达。书院选址时对案山的形状尤其有讲究,如形如几案、笔架、三台、三峰、天马、文笔、文峰等都是绝妙形状,即使选址时,没有“笔架”、“笔峰”之类的案山,也需要选择有塔的地方,或者重新建塔,甚至采用人工的方法增加类似“笔锋”形状的突出点,以弥补书院选址没有案山的缺憾。侯绍瀛也为睢宁书院建立了类似的建筑,他“于尘埋中掘得巨石,玲珑透瘦,移置书院,以为文峰,曰滴泉石,作诗三章,用东城雪浪石韵,勒石纪事”。(注:(江苏)《睢宁县志》卷八,尹安儒《重修睢宁书院碑记》,清光绪十二年十本。)
正是由于科举惯习对书院有如此大的影响,在研究“书院学”的书院与儒学普及、书院与各地文风、书院祭祀、书院藏书、书院的刻书、书院与民俗等重要内容时,必须将科举惯习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展开,才能使“书院学”的研究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科举学”是“书院学”重要理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