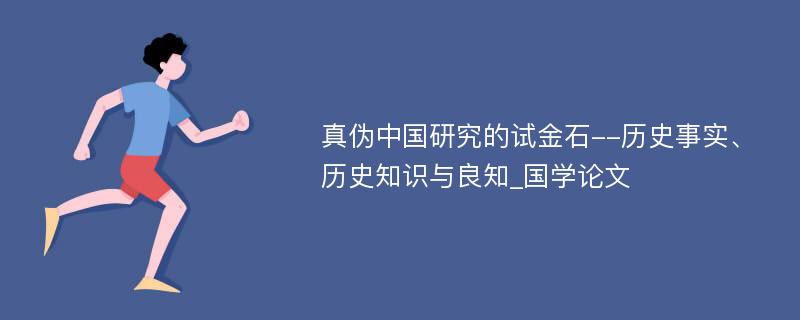
真假国学的试金石——史实、史识与良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金石论文,史实论文,良知论文,国学论文,真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过:“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态,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帝国,没有任何一个教派、没有一个星宿比这三种发明对于人类发生过更大的力量与影响。”
最近,“国学”研究趋于热闹。各种各样的新刊物,各种各样的组织,都打着“弘扬民族文化”等旗号。但是冷静地看一看,想一想,我们会发现这当中是有很多问题的。有的只是为了拉赞助,有的只是为了图名利。坦率地说:本人不仅不反对,而且极力主张国学应该提到重要位置上,只是真“国学”与假“国学”必须分辨。什么是试金石?依我个人的看法,可概括为三点:一曰史实,二曰史识,三曰良知。本文即是我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反省与思考。
何为文化遗产
并非任何传统学术都是值得大加宣传的国学。譬如我看到一本上海知识出版社的书,叫《世界文化遗产》,就发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全世界“文化遗产”的概念,似乎是很有问题的。列入名单的中国“文化遗产”是长城、故宫、秦始皇兵马俑、黄山等,这跟我心中的文化遗产以及我准备讲给学生的文化遗产之间,距离实在太大,我心中的这个概念至少是一笔遗产,它应对中国文化产生过作用,对世界文化产生过作用。而联合国的“文化遗产”干脆就应译为“文化遗址”(Cutural ruins)或“文化景点”。后来我发现康德在谈到历史的观察角度时,有一段话可以用来支持我的看法:“几个世纪之后,我们的后代将如何容纳我们留给他们的历史重负呢?毫无疑问,他们只会从自己感兴趣的、即从出自世界公民意图各民族和各政府所贡献或损害的东西的观察角度出发,来评价最古老时代的历史”(《关于一种出自世界公民意图的普遍世界历史观念》)。这分明是一个智者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看法。
孔子作《春秋》,曾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在我看来,首先是一个“深切著明”的历史事实问题,而不是一个“载之空言”的价值判断问题。换言之,即中国文化为世界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曾见之于行事,著之于史册。这一点,习惯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西方学者不会承认,也不愿承认。有是,习惯中国中心思考方式的中国学者也忽略了,也不愿承认与肯定了。我指的中国中心思考方式,是指习惯于从自己的本位考虑问题的学者,无论启蒙也好,救亡也好;激进也好,保守也好,都无一不是站在中国本位立场看待西方文化,都是将西方文化看作一个外来物,或紧张地考虑如何对待这个外来物,或迫不及待地拿这个外来物来取代自家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中国学者与某些西方学者是有共同点的。为何从并不相同的出发点,会如此有趣地走到同一个地点来呢?关键在于,他们都以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二分法来看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旦有了这种框框,中西文化都变成一种静止状态的抽象物了,所以,他们都看不到,或不愿意过多地承认我上面所提出的那一句话:中国文化为世界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我举有关史实的两个例子来说,一是丝绸之路,一是宋代理学。
丝绸之路是讲中外关系史的常识。但我觉得其中的文化涵义还有待于深度的揭示。丝绸之路不仅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条横贯欧亚的大通道,更重要的是须认识到,丝路的交流并又是完全对等的,是中国文化的动力与源泉第一次真正对西方历史与文化发生重要助力。据专家研究,已经可以证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中的前两项,确然无疑是由丝路传入欧洲的,第三项的可能性,也极大。可以说,两千年前的中国人,将他们的高科技文化,无保留地向欧洲世界开放。鲁迅先生说:“遥想汉唐多少宏放”,一般人总是理解为“对外开放的接纳心态”,依我个人的理解,更应理解为“对外无封锁的贡献心态”(对比今天发达国家的作法,真令人感叹人心不古)。这是丝绸之路作为文化史的真正要义所在。如果我们想到,两千年前的西域丝路上来来往往的骆驼商队中,由西往东的东西只是一些胡椒、瓜果、毛皮之类物品,也许还有别的一些什么东西,而由东往西的物品却除了漆器、丝绸之外。更有火药、纸张、印刷术,──如果我们想到英国近代科学之父Francis Bacon曾说过:“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态,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帝国、没有任何一个教派、没有一个星宿比这三种发明对于人类发生过更大的力量与影响”(《新方法论》第一册第一二九节);──如果我们再想到另一个伟人马克思也说过:“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推动力”(《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如果我们想到这一层文化意义,就不会怀疑我前面说到的“中国文化曾对世界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这句话的真实性了;历史学与文化学所要求的不仅仅是证伪,更重要的是证实、证真,证明真实的历史文化里头的活的生命的存在。
至于儒家理性主义对十八世纪欧洲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已有西方学者、日本学者、以及中国学者写出了一批有说服力的专著,已成众所周知的常识。最为著名的例子是伏尔泰。伏尔泰1752年写成的《自然法赋》一书,据日本学者小林市太郎和我国学者朱谦之先生分析,确认许多论点和论证方法都是中国宋儒理学的翻版。伏尔泰将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然法论,视为与中国儒家哲学精神一致,有的中国学者说这是伏尔泰的一厢情愿和郢书燕说,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伏尔泰是能真正了解中国儒学道德哲学精义的少数西方思想家之一。天赋人权论的最主要的基石即自然法。自然法“是被一个‘立法者’所规定的,而这个‘立法者’同时也就是一个仁慈的天意”(罗素《西方哲学史》上P321-332)。康德这样说过:“我们将遥遥设想:人类是如何通过努力,最终达到将自然赋于自己的全部胚芽完全地发展出来,在世间实现自己规定性的那种状态的。”而且康德在这里更明白地将“自然”说成说是“天意”(见《重新提出问题:人类是否在不断地向善进步?》)。了解中国思想史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自然法──天赋人权的思想,以及后来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的最终依据,与中国从原始儒家到宋明理学的人性思想──即天道人性本质一致的思想,应是相通的;他们从人道追到天道,又对天道存而不论,其基本的理路,本质上是相同的。从历史看,自然法思想,是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启蒙运动被公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准备。伏尔泰《哲学辞典》中说:“孔子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法则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中。”而罗伯斯庇尔也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作为道德格言,写入1793年的《人权和公民宣言》。这个文献上的小例子,正是可以用来说明中国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相关联的一条最简明的证据,亦有助于理解我上面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曾经为世界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观点。
历史文化是一个生命的活的存在
我并非只讲传统文化的昨天,而不讲传统文化的今天。但是我认为历史文化是一个生命的活的存在。第一,你不可以对于这个生命视而不见。第二,既然文化曾经有过这样的重大交流,重大作用,重大相通,你就不可以把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僵硬地打成两截,你就不可以说他们在今天、在未来不会再发生重大的交流、汇通与相互作用。所谓“西方文化是普遍性”,“中国文化是特殊性”,这是十分有害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不仅伤害了世界文化中的共同遗产:诸如:“自由”、“人性”、“公正”、“民主”等,而且窒息了中国文化的活的资源。只要我们不是用这样简单的二分法去看问题,那么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汇通可以说是在在皆有的。譬如,康德说:“现在,我向人类宣布:人类的向善从今以后不再逆转。人类历史中这样一种现象不会再忘掉自身,顺为在人的本性中发现了一种向善的禀赋和能力。……按照人类内在的权利原则,唯有它把自然与自由统一起来”(引同上),这一段话,以“创世本身的终极目的”来预卜人类向善生命,与熊十力先生《新唯识论》中的揭示《大易》生机洋溢、清静纯洁、健动满盈 宇宙大生命的思想,何其相似乃尔!再举一个不被人注意的例子:我最近读到梵高的书信体自传《亲爱的提奥》,发现梵高不仅是一个传大的画家,而且是一流的思想家。他说:“画家的生活中有不幸、烦恼与痛苦,但却有好处,包含着善意、真诚,一种真实的人的感情;只是没有好名誉。离开这个所谓文明进步的世界,这种世界只是一种幻想而已。我说这句话是不是由于我轻视文化呢?恰巧不是那样;我看重与自然和谐一致的、具有真正的人的感情的文明,而不是违反自然的文明。我要问:是什么使我成为一个好人呢?”梵高认为,朴实的农民、挖煤炭的工人,比城市人更有理性。“人们愈靠近大城市,他就愈深地陷入堕落、愚蠢与邪恶的黑暗之中,”“我的判断是人性的,理性是神性的,但二者之间有联系。”他对他的兄弟说:“你与我都真正象是我们同类中的羊。……我不是不关心金钱,但是我对狼却不以为然”(P335-336)。一个对于中国儒家的人性思想有真切了解的人,读到梵高的这些话,会引发一种深切的心灵共鸣,一定会有“吾道不孤”之感。王元化先生近著《清园夜读》有这么一段话:“一旦我弄清楚了性恶论的实质,我不禁对这种惨刻的理论感到毛骨悚然。它给天下苍生带来多少苦难!我始终怀着人是神圣的信念。我相信罗曼·罗兰说的心中的光明。我发现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也有几乎是同样的说法,这就是心本身所具有的‘明几’”我引这段话不过是表明,中西思想在根源处的汇通,几乎是在在皆是的。第三,近来东西方学人常说到Theeconomic"wonders"of EastAsiancountries and regions(东亚经济奇迹),我不愿意简单地据此肯定或是否定儒家伦理在东亚起到的作用,但是至少可以用来证明所谓“昨天”与“今天”也不是可以截然打成两截的。既然民族文化的昨天与今天不应简单打成两截,那么她的今天与明天也不是打成两截的。同样,我不愿意简单地赞同或是反对季羡林先生关于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他的乐观主义是有深厚的史学素养作为背景的。顾炎武早就批评过那些没有历史文化通识的人:“何以万古之心胸,区区天旦暮?”(黄侃《日知录校记》)日本的池田大佐有一次问汤因比:“您希望生在哪个国家?”汤因比回答说:“我希望生在公元一世纪佛教已经传入的新僵”(《展望二十一世纪》)。这都是体现出了对人类文化历史有深刻了解与宽广视界的史家的相同心事。罗素也讲过,人类文化交流史中有一条通则:作为学生的落后国家,总是后来居上,最终超过作为先生的先进国家。罗素这段话毕竟是由通晓人类文化史而来的深刻洞见,如希腊超过埃及,罗马超过希腊,阿拉伯超过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又胜过阿拉伯,文艺复兴的欧洲胜过拜占庭帝国等等(《中西文明比较》)。或许将来的世界文化发展情况可能会远比两千年以来的历史更为复杂而充满变数,,但用中国史学的术语来说,史家的通古今之变”至少具有重大启示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正是建立在对这样一条文明通则的不安与忧虑之上的,就此而言,政治家的亨廷顿的智慧,已远远胜于整整一打二三流的文化史家。只是亨氏显得极狭隘,不仅只见冲突而不见融合;而且太急于将他的忧虑与偏见转化为政治实践操作,这是政治家的通病,我们不必过多与他认真。亨廷顿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当然是我们不能赞同的。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心和乐观主义。季羡林先生在《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一文中呼吁:“我们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从最大的宏观上来外来考虑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已经起过的作用和将来能够起的作用。”我觉得像季先生那样的知识分子,应是属于能“识大体”的知识分子。
讲到“识大体”,我又联想到与这个话题相关的另一个问题: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区别。鲁迅对中国的国民性有极深的解剖,而托尔斯泰则将俄罗斯民族最好的东西呈现为具全人类意义的思想贡献。我们当然需要鲁迅,这已经为近百年的历史所证实,但是我们为何不同时也需要我们自己的托尔斯泰呢?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无疑是近化知识分子的一个极痛苦纠缠的情结。但是依我个人的看法,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向,都仅仅是“我们如何接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其中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把这个问题转变为:“我们如何向世界文化提供我们最佳的部分,或可能的贡献?”(我这里的划分,绝无高下轩轾,只是说明一个事实)我们所提供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中医、烹调、气功、太极拳(并不是说这些不是中国文化中的好处),还应有更高层次的思想。譬如熊十力先生正是属于这少数人中的一人。他在六十年代体衰孤寂的情况下撰写其最重要的作品《存斋随笔》,是每天凌晨一、二点钟起床,然后写作不辍。他的儿媳劝他以身体为重,勿动脑过甚,他回答说:“你们不读我的书,我的学术思想,等我百年后,自有人来研究,你将可以见到,我要写,我不能停……”(万承厚《记父亲熊十力》)。还有钱宾四先生可能也正属于这少数人当中的一人。他未完成的遗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尽管只有短短的一两千字,尽管我或许只能读懂其十之六七,但我读后很感动。他写作这篇文章时曾对他的夫人说:“学术思想岂能以文字这之长短来评价,又岂能人人能懂,个个赞成。我老矣,有此发明,已属不易。我自信将来必有知我者,待他来再为我阐发吧!”面对这两个毕其一生心血坚持自己思考方向的老人几乎相同的临终嘱托,将来的中国学子,不能不为之感动而深思。最近听说《存斋随笔》将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同时又听说曾被痛加批判的《国史大纲》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应是中国学界一南一北的两件非常大好事。另外,染任公先生亦是能识大体的史家,他将中国的历史大而化之地分为三个时代:“中国之中国的时代”,“亚洲之中国的时代”,以及“世界之中国的时代”,这一划分无疑是把握了中国历史文化全幅大势。而且我注意到每一时代的过渡与转型,约有两百年的时间,这一点与胡适之先生晚年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一个相同的看法有关,在此不能详论。总之,倘若此言不虚,那么,从1840年至今,已一百五十年矣,眼前正是在门槛上。
最后我想简单谈谈我近年来读陈寅恪文集的一点心得,我以前总认为陈寅恪先生是一个文化悲观主义者。其实我们仔细体会他的心情,他内心的希望仍是十分深沉执着的。他写于1951年的《论韩愈》,被余英时先生称为“中国文化的宣言”,有很深远的寄望和很强烈的现实关念。他的《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学术预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科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暧,萌芽日长,乃至盛夏,枝叶扶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只是他的思考更为深沉,而且晚期更有些变化。但是,在《赠蒋秉南序》一文中,虽以为民族文化复兴之希望,如“方丈蓬莱,渺不可期”,却又依然“寄之梦寐,存乎遐想”,依然执着地反问:“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寒柳堂集》中有一篇不被人重视的《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短短四五百字,却包含历史文化的许多大见识。寅恪先生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在于此诗第二至第六首之间,而此诗第七首所言,“则邈不可期,未能留命以相待,亦姑诵之玩之,譬如遥望海上之仙山,虽不可即,但知来日尚有此一境者,未始不可少纾忧生之念。”我只记得第七首中有“六龙一出乾坤定,八百诸侯拜殿前”;“纷纷海客整装归”,几句(《病中呓语》预示数世纪之后事),须知一生“读书有不肯为人忙”的寅恪先生,是不会有兴趣于今之所谓“预测学”即古之所谓“推背图”之类神秘主义的,但是他却认真地相信“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既为当然,则因有右以前知之理也。”我认为这正是寄托了顾宁人氏所谓“万古之心胸”。古代的犹太先生知们曾经预言他们的国家或迟或早,将会衰败,而且将要彻底解体;而中国文化却从来没有预言过自己会衰败,会解体,这是一个极鲜明的对比。康德说:犹太人的预言之所以准确,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种命运的发起人。康德说,“一种先天的历史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预卜者自己正在制造并且不断实现预言中所报导的事件。”“如果我们赋予人一种生而俱有的,虽然有限但却始终不渝的善良意志,那么,人就会能够有把握地预告人类向善的进步,因为这涉及到一件他自己能够制造的事件”。(同上引康德书)。未来的中国学子,面对康德的深刻提示,面对文化老人的深重心事,有待于他们理智的深思,更有待于他们良知的照察。
1994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