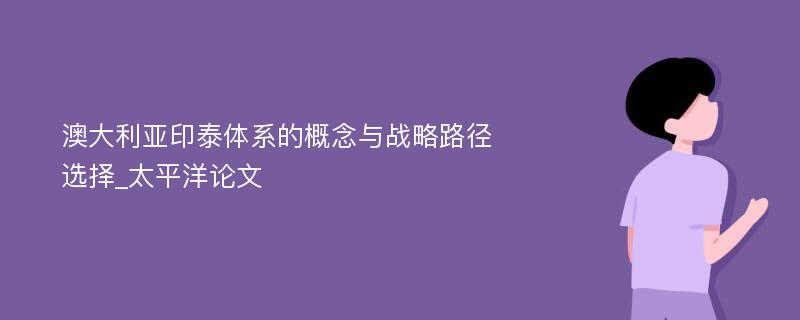
试论澳大利亚的印太体系概念与战略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大利亚论文,试论论文,路径论文,概念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806/j.cnki.issn 1008~7095.2016.02.002 在国外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中,“印度-太平洋”(Indo-pacific)或者“印度-太平洋亚洲”(Indo-Pacific Asia)的概念正在逐步取代原有的“亚洲-太平洋”(Asia-Pacific)概念。这一概念的兴起不仅具有学术上的含义,就如许多研究印太概念的学者所指出的,虽然围绕着哪些国家属于这一地区仍然有着不少的争议,但是它本质上是一个战略体系或一种地区秩序。①不管印太体系的构想是否包括中国,这一战略体系所要应对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和印度崛起所带来的全球地缘政治重心的转移。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不仅意味着亚洲乃至全球实力对比结构的实质变化,也使得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面貌发生了实质变化。印度洋已经成为全球最繁忙的海域之一,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密切海上交通,将原本相对分隔的两个大洋联成一体。美国在搞“亚太再平衡”,印度在向东看,而澳大利亚、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在向西看。尽管中国有保留意见,但是2005年12月召开的东亚峰会已经纳入印度这一南亚国家。可以说,东亚峰会的机制本质上就是一个印太体系机制。 在这个新出现的地缘政治区域中,澳大利亚处于一个十分显著的地位。作为一个地域广大(769万平方公里)、人口稀少(截至2015年3月,2378万)的国家,澳大利亚在国际关系中长期以来处于身份模糊的尴尬境地。它出身于西方,曾经有过很强的“白澳情结”,但地理上属于亚洲,是“被放错了位置的一块英国领土”;它经济发达,疆域辽阔,但是人口稀少、军事力量不强(现役兵力不到6万人),属于潜在的“大国”。②而在地缘政治的棋盘上,澳大利亚长期以来是一个边缘国家。虽然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冷战后的伊拉克战争中,澳大利亚都在盟国中率先响应、与美国在战场上并肩作战,但它所处的这一区域始终不是美国的优先战略区域。不过,随着印太概念的提出,澳大利亚处在看护印太地区公共领地的理想位置,一直以来的尴尬局面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一些学者认为,随着澳大利亚和美国战略优先区域的重合,两国关系可能成为21世纪最为特殊的关系。③因此,长期以来以“中等强国”自居的澳大利亚,十分积极地推动印太地区(体系)的概念,将其融入自己的国防和外交战略之中。那么,澳大利亚的印太体系构想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基础,具体内涵又是怎么样的?澳大利亚在建构印太体系方面面临哪些现实的路径选择?本文将首先总结澳大利亚的印太体系概念和战略,然后分析这一构想所具有的意义,最后分析澳大利亚印太体系战略的具体路径选择。 一、澳大利亚的亚太体系战略:印太概念的基础 尽管地理上而言澳大利亚是一个独立的大洲,但澳大利亚的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本国不应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大洲;澳大利亚应该被视为一个“大陆规模的岛屿”(continent sized island)。这一对国家的定位表明了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对自身孤单处境的忧虑。虽然身边还有一个小伙伴新西兰以及一些散布于南太平洋的岛国,但是它远离国际舞台上其他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或者经济意义的区域。这种孤单带来了澳大利亚的身份焦虑,也造就了澳大利亚政治家所提到的“战略焦虑”(strategic anxiety)或者说“没有理由的担心”(unreasoning fearfulness):虽然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得澳大利亚处于一个相当安全的位置,但领土广袤而人口稀少、远离文化的起源地以及过去几十年中周边地区相对贫穷、混乱,这些因素让澳大利亚并不能够放松。为了寻找朋友、保障安全,澳大利亚先是托庇于英国霸权的保护之下——直到现在它也是英联邦的成员,澳大利亚总督代表英国女王作为国家的元首;当英国霸权衰落之后,澳大利亚积极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二战期间,日军对澳大利亚本土的轰炸使得后者认识到,仅有英国的保护已经不足以保障自身的安全了。 整个二战期间,数十万美军进驻人口只有700万的澳大利亚。1942年下半年,盟军所需资源的65%-70%是由澳大利亚提供的,同时还给临近的南太平洋战区运送了大量的资源。④战时的紧密合作奠定了后来澳新美军事同盟的基础。《澳新美安全条约》规定,缔约国要通过“持续有效的自主和互助的方式来保持及发展它们单独及集体的抵抗武力攻击的能力”;当缔约国在太平洋地区受到武力攻击时,其他缔约国将“依据各自的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应对共同的危险。”⑤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积极参与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朝鲜对韩国的侵略是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张计划的一部分,而太平洋、印度洋和东南亚则是对澳大利亚安全有着根本影响的区域。截至1967年东盟成立之初,澳大利亚派往越南的军事人员已经达到8000人。越战期间,近500名澳大利亚军人阵亡,4000多人受伤,对军队规模非常小的澳大利亚而言可谓代价惨重。⑥“由于其人口规模和地理位置,澳大利亚靠自身力量保障不了其海上航线的安全,因此澳美同盟对于维护澳国家安全和海洋利益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此外作为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也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获得安全保证并提升地区影响力。所以无论哪一种政治光谱的澳大利亚政府——保守的自由党与国家乡村党联盟或是中间偏左的澳大利亚工党——都将与美国的同盟视为‘澳大利亚安全的根本保证’和澳大利亚国防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⑦ 美澳同盟能够保证澳大利亚的安全、一定程度上提升它的国际地位,但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目标显然并不局限于安全范畴。身份焦虑和对国际影响力的追求也构成了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主要驱动因素。澳大利亚前外长埃文斯(Gareth Evans)曾明确强调:“澳大利亚是一个中等国家……虽然不是强国,甚至也不是主要大国……但也不是什么小国或无关紧要的国家,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中等强国。”⑧为了寻求更大的国际影响力,澳大利亚通过主导建立一些地区机制来追求其中等强国的领导权,其中包括1947年成立的南太平洋委员会。但是,南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意义十分有限。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东亚开始成为地缘经济格局的重心之一。澳大利亚虽然是一个经济发达国家,但主要出口的是农业和矿业产品。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显著地加强了澳大利亚与这些亚洲国家之间经济联系。澳大利亚的周边不再是贫穷混乱的邻居,而是它需要平等相待的经济和安全伙伴。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澳大利亚开始为自己寻求一个新的身份定位,即亚太国家。1989年1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倡议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国家部长级会议”,这一倡议得到了美国和亚洲国家的积极回应。1989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第一次部长级会议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由澳大利亚外长担任会议主席。亚太经合组织这一跨地区机制的创设,从根本上解决了澳大利亚长期以来的身份焦虑,也使得澳大利亚能够更顺畅地参与到蓬勃发展的东亚经济进程之中。 亚太区域合作在很长时间里构成了澳大利亚地区政策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实际上旨在构建一个亚太体系,这一体系既具有地缘政治意义,也具有地缘经济意义。通过把美国、中国、日本等新旧大国都纳入进来,澳大利亚可以在一个地区性的政治框架中发出声音、获取更大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影响力;同时,这一框架便利了澳大利亚与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虽然许多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没有能够得到实现。“APEC之父”霍克在担任总理之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说:“决定未来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澳大利亚与亚太区域的融合程度,尤其是中国。”霍克后来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我明显感觉到世界的贸易中心正向太平洋转移,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潜力,将使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催化剂,而亚洲经济的潜力只有区域合作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把亚太地区联合起来。”“当时我的想法很明确,没有中美两国的参与,APEC就没有意义。”⑨阿里·阿拉塔斯在谈到澳大利亚的亚太体系战略时表示:“澳大利亚已成为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建设性力量……积极的地区融入政策,表明澳认为其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希望系于亚洲国家……其命运在于亚太,而非其他地方。”⑩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设,澳大利亚开始发挥作为中等强国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一直以来的身份焦虑和战略焦虑。 二、澳大利亚的印太体系概念 在传统的地缘政治视角下,“太平洋和印度洋被视为相互独立的两个世界,但新的发展开始激发一种更为整体的视角”,也就是说,太平洋与印度洋被看作一个战略上的整体,而不再是两个分离的区域。(11)贸易全球化将印度洋与太平洋紧密联系在一起,亚洲内部贯穿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国际贸易网最终催生了印太战略弧的形成,其中印太航道安全是很多国家的核心战略利益。(12)印度洋集中了全球一半的集装箱运输,70%的石油产品运输需要通过印度洋由中东运往太平洋地区。印度洋航线分布着诸如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对全球贸易有重大影响的战略要点,其中40%的全球贸易运输经过马六甲海峡,40%的原油贸易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13)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11月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指出:“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驱动力。这个地区从印度次大陆一直延伸到美洲西海岸,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由于交通运输和战略因素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4)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海上交通的日益稠密,澳大利亚的对外战略开始从亚太体系转向印太体系,将印度和印度洋区域纳入进来。澳大利亚学者普遍认为,印太是一个比亚太更有用的战略框架:它将印度纳入其中,并将印度洋、太平洋及两大洋间的海上走廊包含在一个无缝的运作区域。(15) 2012年10月,澳大利亚在《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提出“印度-太平洋战略弧”概念,并将其作为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重点。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首先是印度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外交和经济行为体——尤其是印度对外战略的“向东看”——的出现,然后就是从印度洋到太平洋这一广阔地区日益增长的贸易、投资和能源流动,大大提高了地区国家间的相互依赖。(16)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埃文斯认为,以印度的规模和经济增长率,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看到经济重心从亚太到印太的进一步转移。(17)2013年4月发布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也广泛使用印太地区的概念,指出:“一个通过东南亚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新的‘印太战略弧形带’正在形成。”这一白皮书还提到,大亚太地区(wider Asia-Pacific region)的稳定是澳大利亚的持久利益,印太则是这一概念的逻辑延伸,是一个正在出现的体系。而所谓的印太战略弧,是指从印度到东南亚再到东北亚的这一弧形地带,包括海上的交通线。(18)澳大利亚国防军司令戴维·赫尔利(David Hurley)则认为,从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到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都属于“印太”区域。(19)而在学者麦迪卡夫(Rory Medcaef)看来,印太概念不能排除中国,中印美三国构成这一广袤海域的安全动力,是最主要的利益攸关方。以经济为例,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经贸关系的前景可观;中国海外进口能源约80%通过印度洋,绝大部分外贸由海道运输;中国与中东地区的贸易有望在2020年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也是非洲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之一。(20)因此,对于印太体系的范围界定,澳大利亚国内官方和学者基本一致,但在是否要扩展到非洲东海岸方面有所分歧。 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印太体系概念,中国自然是其中的一员,而且应该是主要的成员;但是,如果从战略体系的角度来理解,那么中国可以被包括进入,也可能不被包括进去——日本所力主的四国集团(美日澳印)或“民主安全的菱形”就是这样一个体系。一些学者认为,印太战略弧地域概念不仅暗含着将中国排挤在外的考虑,还透露出美国希望由澳大利亚和印度分担其维护印太两洋海上安全责任的战略安排。(21)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澳大利亚的印太体系概念肯定包括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家;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印太体系已经构成澳大利亚新的主要的地区战略。不管是自由党政府还是工党政府,都频繁提到、主张这一概念。例如,2013年11月16日,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Julie Bishop)在印度孟买发表演讲时讲到:“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印度洋国家。我认为我们所处的地区应该叫做‘印度-太平洋’,这意味着我们的战略焦点必须包括印度,而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共同利益一直在不停地增长和融合。”(22)澳大利亚国防部的2014年《防务问题文件》——这一文件旨在为2015年《国防白皮书》打基础——中指出:“澳大利亚更广泛的战略环境由于印太地区许多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增长、寻求塑造其战略环境而变得更加复杂。”“诸如弹道导弹防御和通信卫星以及太空资产的安全等问题,在印太地区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保护我们的贸易利益不是什么新关切,全球相互依赖的性质意味着印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分享着需要保护的利益——海上交通线和空中航线。”(23) 澳大利亚有关印太体系的最新论述来自其外交贸易部的秘书长瓦吉斯(Peter N Varghese AO)。2015年8月20日他在澳大利亚著名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的演讲中十分具体地论述了有关印太体系的问题。尽管他自己说这次演讲表达的是个人观点,但是他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重大影响以及这篇演讲被放在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网站首页的信号都表明,它代表了澳大利亚政府对印太概念的最新观点。因此在这里值得大段引述瓦吉斯的讲话。瓦吉斯认为:“对澳大利亚安全利益构成严峻考验的是亚洲。这里有着我们的核心经济和战略利益。传统上,我们的亚洲概念集中在亚太地区,这是一个有着连贯性的战略体系:美国横跨太平洋,战略重心在东北亚,而我们更亲近的邻居分布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最近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应该如何接纳印度的问题。”“随着印度在东亚利益的扩展以及东亚的安全形势采取更加制度化的方式,把印度当作印太战略体系中的关键玩家是合理的。这一体系也包含了美国、东亚和南太平洋。”“一种印太的架构也能够更好地符合我们的预期,即本地区大的战略问题是在海上,例如海洋领土主张的冲突以及保护对贸易至关重要的海上航道开放。……通过把太平洋和印度洋联结起来,印太架构也承认了澳大利亚作为两洋大陆的独特地缘战略地位。”(24)瓦吉斯的发言表明,印太体系的概念仍然是澳大利亚政府当前奉行的主要地区战略。 三、澳大利亚印太体系概念的战略意义 印太体系的概念反映了中国和印度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为澳大利亚发挥中等强国作用提供了新的、更广阔的平台。众所周知,澳大利亚外长伊瓦特在参加1946年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时,提出并推动了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中等强国战略。(25)南非学者爱德华·乔丹(Eduard Jordaan)认为,“中等强国所开展的外交政策行为,是要使国际秩序稳定化、合法化,而典型的途经就是它们主动倡导并推动多边合作行动。”(26)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秘书长瓦吉斯和其他一些学者都认为,印太体系有着现成的制度基础——那就是东亚峰会(EAS)。东亚峰会目前采取的是“10+8”(东盟十国加上中、日、韩、澳、新、印、美、俄)的形式,涵盖了印太体系的所有核心国家。因此,推动东亚峰会的进一步制度化和完善,也就成为澳大利亚建构印太体系的核心途径。通过把本地区的核心国家都拉入一种战略体系的建设之中,有助于这一地区在安全和经济领域上的制度化,从而促进印太地区的稳定。而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它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就是维持一个开放和稳定的安全和经济秩序。 除了发挥中等强国作用、促进地区秩序的开放和稳定之外,印太概念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有着更大和更具针对性的战略价值,那就是提升澳大利亚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Spykman)指出,地理虽不是决定因素,但构成条件。……人的唯一自由就只是对此种可能性做好的或坏的利用,把它变得更好或更坏。(27)对澳大利亚的地缘战略地位,美国原来只是当作扇形结构中的一个点,即“设想以美国关岛为基轴,通过稳定美国与日本、韩国、东盟和澳大利亚等一系列双边同盟关系,并以此为轴线来稳定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28)而“印太概念将澳大利亚置于地缘上的战略中心,而传统的亚太概念则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利用这一概念,澳大利亚可以名正言顺地进一步深化与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并证明其不断强化对印度洋地区接触的合法性。”(29) 在印太体系的概念中,澳大利亚同所谓的第一岛链(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连成一线,美国在太平洋重要的海空基地关岛在它的正北边,飞机从澳大利亚北部到关岛约5个小时;西北面越过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可从海陆到达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等重要的交通要道,陆地可到达中南半岛即东南亚各国;西面通过印度洋,可直航到南亚半岛的印度、中东地区以及非洲。这个位置使它成为美国在印度洋最重要的海空基地迪戈加西亚大的后勤基地。(30)的确,印太体系的概念有助于提升澳大利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2011年11月,在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的军事合作新协议中,澳方同意开放布里斯班、珀斯和达尔文基地给美国使用。2012年8月,澳大利亚将军理查德·珀尔(Richard Burr)被任命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作战副司令,这是美国军人在历史上首次由外国司令官指挥。(31)2014年8月,美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长期军事合作协议。该协议敲定了2011年达成的意向,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协议规定,美国在2017年之前将向达尔文派驻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32)就如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尹汝尚(Joseph Yun)所言:“美国以连贯和整合的方式看待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印度洋地区和东亚,这种新视角将有助于美国应对地区内的关键性挑战和机遇。……从战略的角度看,美国实施战略再平衡,实际上就是对正在形成中的新‘印太’世界事实的确认。”(33) 这一战略也迎合了印度、日本等国家的利益和心理;后者均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印太概念可以使它们顺理成章地在一个战略体系内加强合作。有分析家认为,中国对西太平洋的美国和印度洋的印度带来相似的挑战。(34)2012年,印度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员国的贸易总量约为170亿美元,而中国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员国的贸易总量达到250亿美元。印度对于中国在印度洋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十分警惕。日本和澳大利亚长期互相支持以实现各自的战略利益,澳大利亚公开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日本也帮助推动澳大利亚成为亚洲的一员以及参加亚欧会议。(35)两国在2010年5月签署双边防务后勤协议,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与日本签署类似协议的国家。 四、澳大利亚印太体系战略的路径选择 不过,正如澳大利亚外交官员和学者注意到的,印太概念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中国纳入这一体系之中而不加重其他国家的安全焦虑。其实,不仅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感到焦虑,中国方面对于澳大利亚所提出的印太概念及其现实路径选择也可能感到焦虑。客观来说,印太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相对下降,毕竟更广阔的区域、加上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的加入,自然会稀释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虽然这一概念意味着中国也有合理合法的权利进入印度洋地区,但是中国影响力的相对下降无论从心理上还是战略利益的角度来说都构成并不轻松的挑战。从目前来看,现实中正在演进的印太战略体系暗含着一种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联合起来束缚中国的倾向,尤其是日本表现得最为明显。2013年1月,当选日本首相不久的安倍晋三就发表文章说:“我构想出一种战略,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组成一个菱形,以保卫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地区的公海。我已经准备好向这个安全菱形最大限度地贡献日本的力量。”(36)2013年3月,澳大利亚外长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明确表示,澳不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四国集团”设想。印度长期有着不结盟的传统,而且考虑到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也对安倍的这一提法保持距离。短期来看,遏制中国的美、日、澳、印战略体系不太可能出现。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以中国为假想敌,建构一个民主国家的印太战略体系的确是有诱惑力的,毕竟美国、日本和印度都潜在地欢迎这一路径,甚至澳大利亚的许多政府文件也公开提到中国军事力量增长的潜在威胁。早在1997年12月,澳大利亚发表的国防政策中提出“保持一种有力的安全态势,避免这个地区的主要大国之间的不平衡竞争”,而且还说中国力量的增长是澳大利亚战略环境的一个新因素。(37)许多中国学者和官员对于陆克文的“无情的现实主义者”依然印象很深。但是这一路径无疑也有着重大的风险,即可能会实质性地恶化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2014年,中澳双边贸易额1369亿美元。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38)而且,这样一个战略路径本质上偏离了原有的中等强国外交,不利于地区局势的稳定,从长远来看并不有利于维护澳大利亚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澳大利亚只会停留在作为一个美国阵营内小伙伴的角色,而不能真正获得独立的世界角色,更不用提崛起为世界大国。 墨西哥学者冈萨雷斯曾把中等强国分成三类:扮演霸权强国的代理人和帮凶;要求限制霸权,主张地区革命性变革;要求地区自治,与霸权强国既有一致又有冲突。(39)事实上,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已经十分紧密。例如,2000年,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在国防装备和工业方面加强合作的原则协议》,从而使澳获得了与美国分享国防高科技的特殊地位,之前仅英国有此待遇。澳大利亚没有必要通过一个反华的战略体系把自己限定在第一种角色之中。而从地理位置、国土面积和经济基础等角度来看,澳大利亚是有希望崛起为新的全球大国的。澳大利亚是一个被太平洋、印度洋和南极海域所环绕,“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海事管辖范围,是一个潜在的海洋超级大国。”(40)截至20世纪60年代末,“拥有仅1200万人口的澳大利亚,已是世界第13大出口国和第14大进口国。1969年,亚洲仅有日本位于澳大利亚之前。”(41)2014年,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为1.45万亿美元,服务业十分发达,并不仅仅是一个初级产品出口国。澳大利亚的GDP排名基本稳定在全球第12位。随着人口的增长,澳大利亚的经济地位还会进一步上升。如果澳大利亚要做一个有着世界角色的中等强国或者说成长为全球大国,那么就应该以更加独立的协调者形象出现。 曾任霍华德政府外交部长的唐纳(Alexander Downer)十分恰当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我不相信中等强国这个概念能够对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做出公正的描述。……这是在妄自菲薄,完全忽视了澳大利亚在国际上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所具有的巨大潜力……不如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关键(pivotal)’国家,而且澳大利亚外交的众多面之中,它作为国家之间关键性的联系角色是我们应该积极推进的。”(42)通过扮演关键的联系协调角色,塑造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地区体系,是澳大利亚印太体系战略的第二种路径选择。这样一种路径不仅延续了澳大利亚长期以来的中等强国外交传统,也是澳大利亚发挥更大世界作用的可行途径,尽管可能会遇到不少困难。从目前来看,澳大利亚的外交官员和代表性学者明显倾向于这一路径。虽然还不清楚如何做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包容、有效的体系,但他们都表示不应该将中国排除出去,相反中国应该是建构印太战略体系的主要大国之一。就如瓦吉斯所说:“中国完全有权利寻求与其经济分量相匹配的更大的战略影响。中国的追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和平地包容,将最终影响到中国的国际行为模式,以及现存的国际和地区秩序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明智地为中国留出更多空间。”(43)麦迪卡夫在讨论中国和印太体系关系的时候指出:“如果说印太观念带有某种排斥中国的含义,那么这确实错了。它没有,而且恰好相反。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有着不容置疑的重要利益。”(44) 澳大利亚政府倾向于认为东亚峰会是目前建设印太体系的最好地区制度基础,但是如何能使这一制度更加具体、有效,成为本地区各国最优先的选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诸如麦迪卡夫这样的学者承认,建构一个有效的印太战略体系必须在包容性和效率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中美印“印太协调”(Indo-Pacific Concert of Powers)需要说服其他国家,而过于开放的体系则缺乏效率。麦迪卡夫提出,印太安全秩序除了同盟和多边主义之外,还需要第三层次,即注重实用的“少边”(minilateral)对话、演习以及安全行动。这一层次的参与者是自我选择、易于协调的伙伴,有些时候包括中国,有些时候不包括。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这些行动拥有否决权。(45)麦迪卡夫认为,界定印太地区成员的标准包括:第一,是利益攸关;第二,拥有能力及准备使用这些能力;第三,有意愿协助制定并遵守确保地区稳定和安全的规范。他把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列为印太战略体系的核心玩家。(46) 在多边协调方面,澳大利亚有着良好的声誉和历史经验。它在柬埔寨和东帝汶的和平过渡中都发挥了关键角色,提供了大量资源。例如,在东帝汶问题上,澳大利亚成为联合国主持的公民投票的主要捐资者,还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资。在安理会1264号决议之后,澳大利亚司令官率领9000人的维和部队进驻东帝汶,部队中有一半人员是澳大利亚派出的。(47)澳大利亚同其他所有大国的关系都处于相当不错的状态,甚至澳大利亚海军和中国海军之间也有着良好的关系。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国家实力或者现实关系来看,澳大利亚是唯一有可能促成一个开放有效的印太战略体系的国家。但这需要时间、磨合、技巧以及运气。如果能够形成这样的一种地区秩序,那么澳大利亚的世界角色而将开始超越中等强国而进入全球大国的层次。 澳大利亚把自己定位为中等强国,希望能够在地区秩序的建构方面发挥作用,而亚太地区长期以来是澳大利亚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重心。因此,冷战后澳大利亚的地区战略本质上是建设一个亚太体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就是澳大利亚倡导的产物。在亚太体系中,澳大利亚也获得了自己的地区身份。随着印度经济的崛起,澳大利亚开始重新对世界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地图进行界定,提出了印太概念。印太概念是澳大利亚认识到印度和印度洋现实重要性的产物,但这一概念有着重要的战略后果,那就是重构一个地区体系,即印太体系。印太体系战略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政府新的主要地区战略。 在印太体系中,澳大利亚由于其地理位置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已经在这一概念之下加强了与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关系。但澳大利亚的印太体系战略并不排斥中国,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的关键意义,排斥中国只会损害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外交目标是做中等强国,致力于建设地区秩序,而不仅仅是做遏制中国的美国同盟体系中的小伙伴。只有通过将中国有效纳入印太体系、发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澳大利亚的印太体系才能从长期和根本上有利于其国家利益,并提升澳大利亚的世界角色。因此,澳大利亚的印太体系概念与日本所提出的美、日、澳、印四国同盟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如何建构这样一个开放而有效的地区体系仍然没有明确的框架或答案。澳大利亚认为东亚峰会是较好的地区制度基础,但显然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限制了这一制度的作用。同时,中国、印度等对于这一概念都还有着相当的疑虑或者保留。即便明确了一条包容中国的战略路径,这一体系的实现仍然需要长期的努力和时间。 注释: ①Rory Medcalf,“The Indo-Pacific:What’s in a Name,”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Vol.9,No.2,2013,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3/10/10/the-indo-pacific-whats-in-a-name/. ②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dyz_608952/1206_608954/。 ③Jim Thomas,Zack Cooper,and Iskander Rehman,“Gateway to the Indo-pacific:Australian Defense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the Australian-U.S.Alliance,”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Washington,DC,2013,p.1. ④[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⑤《澳新美安全条约的由来》,《国际问题资料》1985年第7期,第19页。 ⑥李凡:《冷战后的澳大利亚与美国同盟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⑦杨小辉:《“中等强国”澳大利亚的海军政策与实力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40页。 ⑧G.Evans,B.Grant,eds.,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Melbourne: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92,p.32. ⑨“APEC之父:没有中美两国APEC就没有意义,”http://news.sina.com.cn/c/sd/2014~11~18/121431163175.shtml。 ⑩曹云华主编:《东南亚国家联盟:结构、运作与对外关系》,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401页。 (11)C.Raja Mohan,“Indo-Pacific Naval Partnership Open to Delhi and Canberra,”The Australian,November 2,2011. (12)肖洋:《“印—太战略弧”语境下澳大利亚安全空间的战略重构》,《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17页。 (13)Robert D.Kaplan,”Center Stage for the 21st Century: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Foreign Affairs,Vol.88,No.2,2009,pp.19~20. (14)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November 2011,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15)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第16页。 (16)胡欣:《“澳大利亚梦”:做“印—太”地区的中等强国》,《世界知识》2013年12期,第32页。 (17)Gareth Evans,“Global Issues of the Future:Challenges for South Asian Policymakers,”October 30,2011,http://www.Gevans.org/speeches/speech451.html. (18)Australian Government,Department of Defence,Defence White Paper 2013,p.7,at: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WP_2013_web.pdf. (19)Sergei DeSilva-Ranasinghe,“Australian Military Expands Indo-Pacific Profile”,The Diplomat,March 13,2013. (20)Rory Medcaef,“Whose Indo-Pacific? China,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egional Maritime Security Order,”May 21,2013,at: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whose-indo-pacific-china-india-andunited-states-regional-maritime-security-order. (21)Dennis Rumley,Timothy Doyle,Sanjay Chaturvedi,“Securing the Indian Ocean? Competing Regional Security Constructions,”Journal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Vol.8,No.1,2012,p.6. (22)Bishop,“Speech to 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ies,”http://www.foreignminister.gov.au/speeches/Pages/2013/jb_sp_131117.aspx?ministerid=4. (23)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Defence Issue Paper 2014,at: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docs/DefenceIssuesPaper2014.pdf. (24)http://dfat.gov.au/news/news/Pages/an-australian-world-view-a-practitioners-perspective.aspx. (25)C.Ungerer,“The‘Middle Power’Concept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Vol.53,No.4,2007,p.540. (26)Eduard Jordaan,“The Concept of a Middl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Vol.30,No.2,2003,pp.165~181. (27)[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1页。 (28)James A.Baker III,“America in Asia: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Foreign Affairs,Vol.70,No.5,Winter 1991,p.9. (29)Nick Bisley and Andrew Phillips,“The Indo-Pacific:What Does It Actually Mean?”October 6th,2012,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10/06/the-indo-pacific-what-does-it-actually-mean/. (30)刘新华:《略论澳大利亚的地缘战略地位和美澳军事同盟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3年第3期,第78页。 (31)杨小辉:《“中等强国”澳大利亚的海军政策与实力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40页。 (32)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8/13/c_126866800.htm. (33)Joseph Yun,“The Rebalance to Asia:Why South Asia Matters(Part 1),”Testimony Statement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Washington,DC,February 26,2013,at: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13/02/205208.htm. (34)David Scott,“The‘Indo-Pacific’—New Regional Formulations and New Maritime Frameworks for US-India Strategic Convergence,”Asia-Pacific Review,Vol.19,No.2,2012,p.86. (35)Neville Meameu,Towards a New Vision—Australia and Japan through 100 Years,Sydney:Kangaroo Press,1999,p.139. (36)“安倍吁组‘民主安全菱形’抗衡中国,”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1/12/c_124222063.htm。 (37)殷汝祥:《澳大利亚研究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 (38)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6/17/c_1115644007.htm. (39)G.冈萨雷斯:《何谓“中等强国”?》《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第44页。 (40)Sam Bateman,Anthony Bergin,Sea Change:Advancing Australia’s Ocean Interests,Canberra: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2009,p.9. (41)G.Greenwood,Approaches to Asia:Australia Postwar Policies and Attitudes,McGraw-Hill Book Company,Sydney,1974,p.115. (42)C.Ungerer,“The‘Middle Power’Concept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Vol.53,No.4,2007,pp.548~9. (43)http://dfat.gov.au/news/news/Pages/an-australian-world-view-a-practitioners-perspective.aspx. (44)Rory Medcalf,“Whose Indo-Pacific? China,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egional Maritime Security Order,”21 May,2013,at: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whose-indo-pacific-china-india-and-united-statesregional-maritime-security-order. (45)Rory Medcalf,“Whose Indo-Pacific? China,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egional Maritime Security Order,”21 May,2013,at: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whose-indo-pacific-china-india-andunited-states-regional-maritime-security-order. (46)Rory Medcalf,“Whose Indo-Pacific? China,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egional Maritime Security Order,”21 May,2013,at: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whose-indo-pacific-china-india-andunited-states-regional-maritime-security-order. (47)刘鹏:《冷战后澳大利亚对东帝汶政策的评析》,《东南亚南亚研究》2009年第2期,第19~20页。标签:太平洋论文; 亚太再平衡战略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 印度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