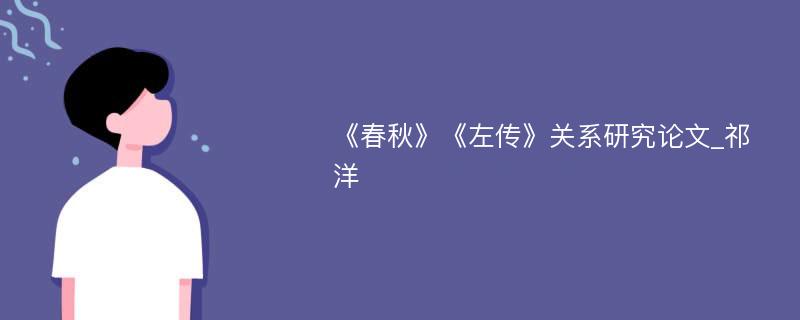
摘要:《左传》的成书目的并不是为了解《春秋》,而是以《春秋》所记录的史实为纲,对鲁国隐公至哀公的历史有一个顺序上的把握,利用收集的材料对《春秋》进行补充阐释。其目的是从历史中总结经验,表明自己重视礼制、仁义、忠勇、勤政爱民等价值观与思想倾向,借此作为君主与臣子的行事标准和行为规范,并阐释礼乐道德的重要性。
关键词:经传关系;思想倾向;礼乐制度
《春秋》与《左传》的关系历来一直争论不休。笔者认为二者的原始材料是有联系的,但是二者的成书目的、书写系统、价值倾向却又是相互独立。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春秋》记史,《左传》言志
有很多学者认为《左传》的成书目的是为了解《春秋》,笔者的观点与此相异。如果《左传》的成书目的是为了解《春秋》,那么书中的内容应对历史事件进行详细叙述,然而纵观全书,作者对事件的记述十分简洁,作者将叙事的重点由事件转到人物上,让人物成为道德的承担者,作者想以此来阐明整个社会主流价值,使君臣行事有套可参考的标准和规范。因此我认为左传作者书写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记录事件本身和对历史的阐释,而是想借所述人物之口表达自己对事件的态度,体现自己的道德标准跟思想倾向,以史为线索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观甚至确立新的社会价值,指导现实。
《左传》中的语言描写不仅仅局限于只是对君臣话语的记录,而是通过记叙君臣政治日常和生活行为对礼乐道德进行维护,阐释君与否而导致国家兴衰的事实来为君臣进行警戒。
《左传》中提到关于“礼”次数非常多,这说明《左传》作者的重礼倾向。虽说春秋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是君臣的行为准则还是礼,《左传》中多次提到君臣的礼制标准,详细的描述什么行为是符合礼制的,什么行为是不符合礼制的,按照礼制,这件事情应该如何进行。在春秋时期人们的观念中,礼乐道德的维护与否是国家兴衰的根本。国家按礼行政就会兴盛,反之则会灭亡。人们探讨国家、家族、个人的成败,也多以礼伦理道德为原点。
二、《春秋》与《左传》是两种不同的书写系统,具有不同能职能
《〈春秋〉的文本性质及记事原则》一文中提到,《春秋》是告庙文本,具有通灵的功能,其作用是向神灵传达国家所发生的大事件并寻求祖先庇。因此《春秋》的叙事呈现出孤立的、片段的,松散的特征。《春秋》语言十分简洁并且有固定的格式:日期、国家、参与人员,具体事件等依次排列,这样的格式与先秦时期铜器铭文上书写的内容大致相似,都是呈条目式。《春秋》记录的内容也是固定的,有会盟、丧葬、战争、灾异、朝聘、嫁娶等,都是根据国君、夫人、姬妾,诸侯等人的事迹编写。《春秋》只是客观公正的记录事件,并未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和对事件的评价态度。
《左传》的叙事详尽完整,运用多种叙述手法,逻辑清晰,层次分明,有明显的段落。《左传》的阅读对象是人,因此作者除了记载和补充历史资料外还明显的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倾向,希望构建的一个政治清明、尚礼尚德,君臣和睦、兄友弟恭、注重忠信贤孝的社会蓝图。
如《左传•成公十七年》:“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做乱。矢兹三者,其谁与我?’”
可以说《左传》是作者有意的编纂出一部具有教化作用的史书。可以证明这个推论的是作者大量引用《尚书》《诗经》的语句和“子曰”“君子曰”等名言,借此表达自己的评价和思想倾向。例如《左传•文公四年》引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左传•文公五年》引《尚书》“沉渐刚克,高明柔克”表达作者敬畏天命、遵从礼法、强调君子怀德的价值倾向。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三、《春秋》与《左传》所记载的事件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这些异同便成为研究经传关系的关键切入点
本文认为《左传》的编写是以《春秋》为纲,选取的时间与《春秋》重合,大部分事件的选择也是以《春秋》的记载作为参考,以编年的体例对事件进行整合补叙,因此二者有相同的是很正常的。《春秋》和《左传》的原始形态应该是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二者又出现许多不同的部分,解释这一现象的关键就是二者的材料来源不同以及二者的记事原则不同。《春秋》与《左传》的作者职位不同,所收集信息的渠道不同,材料来源不同,因此所记载的内容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四、《春秋》与《左传》的记事原则,书写标准不同,本文将从有经无传跟有传无经两部分进行分析
(一)有传无经:本文试分析某些事件在《左传》中出现却没有记载于《春秋》的原因和规律。
《〈春秋〉的文本性质及记事原则》中提到《春秋》的礼仪实录性原则,即有告庙仪式,鲁国之事才能载入;有正式赴告文书,也有告庙仪式,列国之事才能载入。因此,没有经过告庙仪式的事件便不会被《春秋》载入。但是《左传》的史料选择并非是以礼仪实录性为原则,史官收集到丰富的材料后判断其是否具有叙述和记录的价值,然后进行补充。
《春秋》记事遵循内外有别,严格遵奉宗法等级的原则。《春秋》中所载录的人物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诸侯大夫、与皇室有血缘关系的贵族、公子,“《春秋》只记载与鲁公室有血亲、姻亲关系的的人事,只记载能给鲁公室带来荣耀的人事,哪怕记载敌人,也要与鲁公室门当户对。”
《左传》中的等级制度明显削弱。《左传》中不仅仅记录有身份地位的贵族,也开始出现平民的身影,如“触槐而死”的鉏麑,知恩图报的灵辄,舍身护主的提弥明等等。作者的选择视角已经发生了转变,不再以身份地位和高贵的血统为选择标准,而是更加注重人物的品质道德。这是作者思想倾向的转变,也是等级制度逐渐弱化的标志。
《左传•成公十六年》:“晋侯使郤至献楚捷于周,与单襄公语,骤称其伐。单子语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怨而阶乱,何以在位?夏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将慎其细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二)有经无传:有的事件在《春秋》中记载却没有出现于《左传》中,本文试分析其规律和原因。
不能体现礼制的事无传。比如记述文姜与齐侯的丑闻一事,经传皆有记录,经的目的在于记录,传的目的在于批判这是非礼的行为,并且添补了符合礼制的做法。在后来《春秋》中多次记录文姜与齐侯的丑闻,但是《左传》中对于这些不合礼制的事件没有任何记。
“狄侵某地”无传,“伐某地“无传。对于夷狄侵伐中原国家,“狄侵郑”,“狄侵齐”等《左传》没有记录,这表现中原国家对夷狄的轻视和维护中原国家尊严的心态。在《春秋》中提到的没有收到王命去侵伐谋国家,如“伐邾”这类师出无名的战争,《左传》作者不予记载,这体现了作者不赞成不道德的战争。
丧葬无传。对于不能体现作者价值倾向的事件不书。一般诸侯或外国国君丧葬的事件不会作传。
有特殊事件发生的会简略书写一下。
灾异无传。《春秋》中多次出现的灾异在《左传》中很少有记载。这些灾异包括:日食、虫灾、火灾、雨、雪、雩等自然灾害或者自然现象。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造成大的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左传》都没有记载。但是发生异象之后成灾、有祭祀活动或者君主出面进行治理,《左传》会有记载。这体现了《左传》的作者不书常事,重视礼祭和君主的作为。
本文从《春秋》与《左传》的叙述方式、叙述内容的侧重点、二者的职能、书写系统以及经传不同这些方面浅要的分析了《春秋》与《左传》的关系,二者是有联系友有区别的。
论文作者:祁洋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9月31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7/16
标签:左传论文; 春秋论文; 事件论文; 作者论文; 礼制论文; 倾向论文; 目的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9月31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