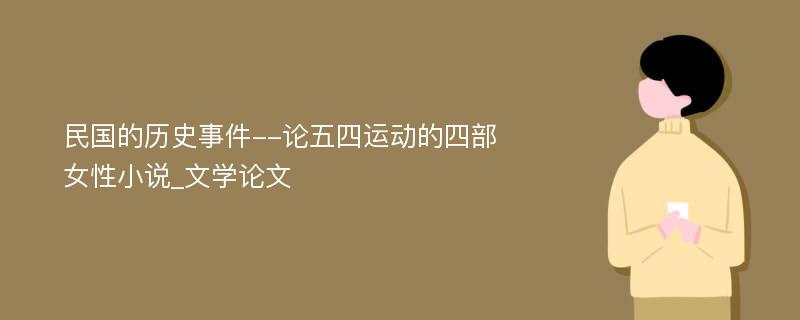
民国往事:论五四女性小说四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论文,四家论文,往事论文,女性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意识:论冯沅君
以笔名“淦女士”登上现代中国文坛、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63年)、在“十年文革”中 也像其兄冯友兰教授一样被册封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冯沅君(1900-1974),其文学实践只 有6年(1923-1929)。虽然苏雪林曾“认为她是一个在故纸堆中讨生活的人物,与文艺创作是 无 缘的”,[1](P218)但从“边缘诗学”的视野来看,她对于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叙事的贡献同 样不容忽略。沈从文曾写道:“用有感情的文字,写当时人所朦胧的两性问题,由于作者的 女性身份,使作品活泼于一切读者的印象中,到后就有了淦女士。”他还将她同冰心作过一 番十分贴切的比较:“年青人在冰心方面,正因为除了母性的温柔得不到什么东西,而不无 小小的失望;淦女士的作品却暴露了自己生活最眩目的一面。这是一个传奇,一个异闻”; 虽然她“缺少冰心的亲切,但她说到的是自己,……因此淦女士的作品以崭新的趣味,兴奋 了 一时代的年青人。”[2](P371-372)虽然冯沅君同样也十分关注母爱主题,但她的叙事特色 仍在于对青年男女炽热的性爱的表现,是一位“大胆的爱情故事作者”(夏志清语)。被沈从 文以“华美”与“放纵”两词来形容的冯沅君的文笔,正体现了她的叙述话语的浓烈性。这 份浓烈来自于其文本所具有的一种“展览自己的勇敢”,和对植根于肉体欲望的性爱冲动的 表现,也与作者所选择的第一人称的书信体叙述不无关系。在她看来,“文学作品必须作者 的个性”,而“至于书信,我以为应较其他体裁的作品更多含点作者个性的色彩。”所以, 尽管冯沅君的小说写作历时不长,但其作品在精神内涵方面较冰心有显著的开拓与深入。有 道是“俏丽的女子不难得,而美而韵者为难”。借其作品里的这段话来说,冯沅君所着力 的乃有“韵味”的人生,故其叙述不仅进入到女主角的内在自我;而且以今天的立场来看, 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已具有了所谓“欲望写作”的一些特色。
比如因表现叔嫂之恋而曾倍受关注的《潜悼》。小说以一位青年男性的视点展开叙述,真 切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在内心对堂兄之妻的刻骨铭心之爱。虽然主人公的这种情感基于一 种崇敬心之上,但明晰地同躯体与生理相关联,是一种既具有东方文化的含蓄、也具有真正 的“现代性”的男女情爱。叙述者对自身已有情人的交待使这个主题对常规伦理更具挑战性 ,其所作的具体叙述也十分开放。小说不但以“男人们见了少女的睡态而不涉绮思的,除 非是心如铁石,简直是不近人情”这样的议论,和对牌局在严男女大防的中国社会具有“可 使男女们领略到夫妻以外的性的安慰”这一事实的叙述,对人的自然反应作出了坦然的肯定 ;而且还对这种来自人的性驱力的“诱惑之美”进行了生动的描绘:“你看她沉沉熟睡着, 桃色的绒毯半掩着她的躯体,粉红的衬衣,从窄瘦的地方,可隐隐约约的看出她的身体上许 多部分的曲线美来;鬓发蓬松着披拂在额颊间;唇间的浅浅笑痕可证明她梦中的甜美。”当 然,这部作品中最具魄力之处,仍在于对年轻男女间健康直率的性心理的诗化把握。文本以 “四壁如雪,充满了桔红色灯光的房间,炉中熊熊融融的火焰,数尺高的菱镜,罗账半垂, 锦被横陈的床铺”等景物描写为铺垫,逐渐进入到对人物意识的表现:“你的流盼使我的灵 魂兴奋,你的微笑使我的灵魂得到安慰。我的手曾接触过你的手,在我发牌给你的时候;我 的脚曾接触过你的脚,当我指点你的错误的时候。你的连娟的秀眉,你的细腻的肌肤,你的 柔语,你的巧笑,……我鉴赏了你的各式各样的娇态——含有诱惑的,放纵的,平日人所不 见的娇态。”这种对男女情欲交流所作的真实却不低俗、挑逗但不淫秽的展示,在猛男倩女 们一旦有意便直奔主题的今天不但仍有意义,而且已具有了一种经典意味。在观念上也超越 了一般所谓的“反封建”范畴,进入到了表现基本人性的领域。
冯沅君小说再一个突出之处,是对由来已久的“男优女劣”格局的颠覆。在很大程度上, 这也是作者自身气度的艺术转换的结果。据说“五四”时期冯沅君在北京女高师就读时,曾 第一个出来砸碎校门上的铁锁,与同学一起上街游行。所以她笔下的女主人公都较男性更具 丈夫气。如曾被鲁迅称赞为“精粹名文”的《旅行》同《隔绝》和《隔绝之后》,是一对自 由相爱的青年男女的悲剧三部曲。小说取材于作者表姐吴天的婚姻遭遇,都以故事里的女主 人 公为叙述中心,她是这段爱情的施动者和主体,最终也由她的自杀来成全这个故事。作为其 恋人的男主角士轸除了在她为爱殉身的精神的感动下作了同样的选择外,基本上无所事事。 更说明问题的是《缘法》:在妻子玉贞死后男主角雄东一度因思念过切而神情恍惚,但在家 庭的压力下重又娶妻后他在前妻的坟上哭得死去活来。同事明夫因他婚后不再上班,怕他伤 心过度特来看望,却见到一个“红光满面得意洋洋”的雄东。《我已在爱神前犯了罪》看似 和《潜悼》一样都涉及情外情,对人类丰富敏感的性意识的神秘性作了独到的表现。但内在 地也对男性既容易见异思迁,又缺乏选择勇气的怯懦性格,作了颇为深刻的揭示。小说里那 位20多岁的男教师虽已有“温柔明慧”的女友碧琰,还是又爱上了“秀外慧中”的十八九岁 的女学生秋帆。与他陷入缠绵之中难以自主相比,其女友碧琰显得果敢而大气。她在信里虽 流露了一些不安的情绪,仍表示了理解。她从“双方的绝对自由是爱情的重要的属性”出发 ,以只要他们彼此出于真情“道德上不发生问题”,来替这位在青春的诱惑面前六神无主的 男友减负。其女性立场与性别写作的特色显得旗帜鲜明。
但冯沅君的小说叙事不仅比冰心更受抽象的爱的观念的拖累,而且还为一种内在矛盾所分 裂。《隔绝》三部曲所表现的一个基本主题是性爱与母爱的冲突。叙述者一方面对这种冲突 中所表现出来的传统儒家伦理观的似是而非有所体会,意识到“世间种种惨剧的大部分都是 由不自然的人与人间的关系造出来”(《旅行》),发现世间最亲密的母女关系同样也掩饰着 一种自私性;但另一方面却又让女主人公陷入不孝的内疚中难以自拔。这种精神局限使作品 的艺术价值受到损失。当传统意义上的母爱亲情最终在作者的思想中占据了上风,她在创作 上便走向说教,如《慈母》与《误点》等。两篇作品里的母亲似同一个作为传统伦理化身的 人物,而面对那种抽象空洞的观念,作为“女儿”的叙述者却想“只歌颂在爱的光中的和乐 家庭”(《慈母》),因为她“深深感到母亲的爱的伟大”(《误点》)。此种情形让我想起当 代一位英年早逝的批评家对儒家家庭伦理作出的一番清醒批判:“这并不是深沉伟大的母爱 ,在血缘伦常的和谐的表象中,子女的独立意志的人格的发展机会已经在‘爱’的关系中被 融化乃至完全消失了。”[3]意识与情感中的这种从暧昧到愚昧的演变,使作者在小说《贞 妇》里作出了无逻辑的叙述,让何姑娘以其忠心耿耿感动了将她虐待后又抛弃的前夫慕凤宸 ,使他“用向来对她不曾用的诚挚、温柔的声调含泪地叫她一声”,这篇作品最终成了一个 不伦不类的对传统伦理的颂歌。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隔绝》三部曲与 《潜悼》等篇既“是冯沅君创作的起点,也是她的顶点”。[4](P196)这些作品艺术表现力 的下降已昭示出她作为一名浪漫主义小说家的创作冲动的衰退,也是其后来走上学术研究道 路的一种迹象。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不承认,冯沅君一度所扮演的小说家的角色是成功的 ,她完成了自身所负的一段历史使命。
二 感伤意象:论庐隐
沈从文在谈论“五四”女作家时,虽视凌淑华为女性叙事的佼佼者,却也指出其文字上存 在着因谨慎而略显滞呆的缺点,“故年青读者却常常喜欢庐隐与沅君,而没有十分注意淑华 ”,[2](P374)给了以“庐隐”为笔名的女作家黄英(1898-1934)的小说创作一个客观肯定。 与其曾同学二年加同事半年的苏雪林也曾有言:“五四运动初起之际,人们都知道谢冰心是 当时文坛一颗乍升起的光芒四射的明星,却不知还有一个庐隐女士,与冰心同时崭露头角。 庐隐享名之盛虽不如冰心,不过我们要谈五四时代最早的女作家,冰心之外不得不推庐隐了 。”根据她的见证,“一开笔便写小说”的庐隐的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也曾获得当 时女中学生狂热的爱好”。[5](P353)虽说读过去时代女作家的传记常让人生出许多感叹, 但 庐隐的身世尤其令人叹息。这位自出生之日起就“不曾享受到母爱”、童年回忆只有痛苦与 不幸,曾表示“愿将我全生命供献于文艺”的小女子,似乎生来就注定了要成为一名“文学 女性”。她在《自传》里将其毕生创作划为三个时期:以《海滨故人》《灵海潮汐》《曼丽 》为代表的“悲哀时期”,以《归雁》和《云鸥情书集》为代表的“转变时期”,以《女人 的心》和《情妇日记》等为代表的“开拓时期”。贯穿其始终的基调可用一个词来概括:伤 感。所发生的变化在于由第一期的“薄浅和想象的哀感”经由第二期的“由伤感的哲学为基 础,再加上事实的伤感所组成的更深的伤感”,到第三期的“不愿意多说伤感”。用她的话 说 ,这并不是已不伤感,而“只因我的伤感已到不可说的地步,这情形正好以辛弃疾的《丑奴 儿》辞来形容之了。”[6](P214)
一般说来,庐隐的小说创作之旅,正式起程于1921年2月《小说月报》发表的短篇《一个著 作家》。这篇让苏雪林“不能赞一词”的作品,以第三人称讲述了一对青年恋人的不幸故事 。但庐隐小说叙事的基本方式是“抒情自传体”。周作人当时在《新青年》上曾撰文说道: “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认为“这抒情诗的小说,虽然形式有点特别,但如 果具备了文学的特质,也就是真实的小说。”[7]庐隐的小说艺术正可作如是观,大多取材 于自身经历,倾吐一腔深情。如成名作《海滨故人》里的露沙是自指,兰馨系其同事舒畹荪 ,云青、玲玉、宗莹分别指她大学同学王世瑛、陈定秀和程俊英。这使得她虽在身份上属于 注重写实风格的文学研究会,但其小说观与作品所表现的主旨却接近推崇情感宣泄的创造社 。在她看来,“文学创作是重感情,富主观,凭借于刹那间的直觉,……情之所至,意之所 极,然后发为文章。”[6](P60)这种审美选择显然正是作者自身性格的折射与体现。苏雪林 眼里的庐隐“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外表虽显得有些难以亲近,其实“ 胸无城府,光明磊落”,是一个“生在20世纪写实时代却憬憧于中世纪浪漫时代幻梦的美丽 ”的人。由于这种情绪弥漫于整个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社会,所以充满主观色泽的庐隐的文 学叙事,却客观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就像茅盾在《庐隐论》里所说:“庐隐与‘ 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 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徊,我们又看见 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8]也有文章以当代 “新时期文学”与之相比,认为“庐隐小说是‘五四’时期的‘伤痕文学’。”[9](P276) 而其叙事方面的最大特色则如苏雪林曾评价的那样,是文字的热烈奔放,“颇类昔人批评苏 东坡诗,如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出,从不扭捏作态,其豪爽至为可爱。”[1](P219)
但这种缺少必要节制的叙述同时也带来了故事拖沓、结构散乱等缺点。正如一些批评文章 所指出的,庐隐小说里的叙述话语都是作者本人的一个声调,“作为小说家,她始终拙于小 说的组织,叙述往往失之平直,几无‘技巧’可言。”[10](P375)这让苏雪林在对庐隐本人 作了充分肯定后仍坦诚地表示:“对庐隐的创作小说,我还改不了眼高手低的老毛病,不敢 故作违心之论的夸奖。”[5](P363)夏志清则干脆宣判道:“黄庐隐,一个相当拙劣的短篇 和长篇小说作家。”[11]这样的批评不能说毫无道理,个中原因除了作者所采用的抒情方式 外,也在于生活压力过重。作者曾承认:“我的创作生活都不是很悠闲的。这样的努力,我 自信是为兴趣,有时也为名,但为钱的时候,也不能说没有。”不少文章“不是为了要几个 稿费而作的,便是被朋友逼出来的。”[6](P209)但如果我们以此作为庐隐小说的盖棺之论 ,对于这位愿以毕生作代价来创作一二本成功之作的小说家则是极不公正的。在我看来,庐 隐文学叙事的最大价值在于,她自身的经历使其较当时其他女作家有更自觉也更到位的女性 视野。她曾专门撰文指出,当时流行的妇女解放实质只是将女人由一架“泄欲制造孩子的机 器”,变成了一只“可以引起男人们超凡入圣的美感”的花瓶;她提出“人类只有个性的差 异,而无男女间的轩轾”,要求女人们“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她认为“不能再妄 想从男人们那里求乞恩惠”,女人的命运只能靠自身,因为男人一方面所要的是“含辛茹苦 作一个无个性的柔顺贤妻,操持家务的良母”;而另一方面即使女人做到了这些,她还得“ 含笑地送他去同情人幽会,她站在门口,看着那天才的丈夫,神光奕奕地走向前去。”[6 ](P80-89)即使在今天,这样的言论仍显得相当的深刻。
所以从边缘诗学的立场来看,全部庐隐小说都体现了一个主旋律:理解女人。这构成了庐 隐小说的当代性,其作品是借知识女性的人生苦闷探索身为女人的生命归宿。如果说关注女 人 是绝大多数女作家们的共同点,那么庐隐的特色则在于试图深入女性生命深处,去把握她 们的人生之路。用她作品里的一段话来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结婚,生子,作母亲,… …一切平淡地收束了,事业专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这原来就是女人的天职。但谁能 死心 塌地地相信女人是这么简单的动物呢?”《何处是归程》)比如作者自述是“忠实地替我的 朋友评梅不幸的生命写照留个永久记念”的《象牙戒指》,作者讲述了女大学生沁珠同 两位男性大学生伍念秋与曹子卿均无结果的爱情经历。表面上,沁珠由于在同有妇之夫伍君 的初恋中受到了伤害,妨碍了她后来在同曹君的再恋中的投入,结果导致了对她倾尽身心的 曹君的早逝,而他的死反过来又促成了沁珠因心力憔悴而亡。但在深层次上,这部叙述重心 始终在沁珠身上的故事,是试图通过进入这个女主角的心灵世界,来表现女性主体的生命意 识与人生追求;作品围绕女主角而展开的种种关于爱情的思考,只是引领我们进入其内心的 一个媒 介。如作者不仅让沁珠在同故事的讲述者之一素文的对话中,多次对被视为神圣的爱情表示 出疑虑:“纵使有爱情,也仅仅是爱情而已。”“在今日的世界,男人或女人在求爱的时候 ,往往拿‘死’作后盾,不过真为情而死,我还未曾见过一个。”甚至还让素文也成了沁珠 的替身说出同样的话来:“这个世纪的年青人,就很少有能懂得爱情的,男的要的是美貌, 肉感,女的呢,求的是虚荣,享乐,男女间的交易只是如此罢了!”女人们对于爱情较男人 更慎重,是因为这对于她们常常意味着人生唯一的寄托,沁珠在爱情上的犹豫正是其生命困 惑的一种体现。小说通过对这个主题的揭示,表现了身为女人的作者热切渴望读者能够同其 一 起,对天下女人的命运予以理解的愿望。
这在《女人的心》里表达得更为明晰。小说的女主角素璞先后同两位留洋男士贺士和纯士 结婚,又先后离异,最终让幸福生活从自己手上滑落。故事里的两位男子显得宽容大度,女 主角的行为不仅难以接受,而且作者最终还让她自惭形秽地承认:“我是一个过渡时代的女 人,我脑子里还有封建时代的余毒,我不能忍受那些冷讽热骂,我不能贯彻我自己的梦想。 ”但进一步来看,小说的真实意图其实在于让我们对这样一位知识女性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 ,仍给予某种理解。这也是进入《一个情妇的日记》与《丽石的日记》的叙事话语的一个基 点。在前一部小说里,参加了革命党的青年女性美娟爱上了有妇之夫的本党领袖仲谦。虽然 在故事结尾时,作者让女主角作出“一天到晚集注全力在求个人心的解放,这是多么自私” 的自责,与整个叙事显得很不谐调。但这也恰巧表现出这部作品前面部分大胆表现年轻女性 旺盛的生命力,和她们对爱情不顾一切的渴望,具有十分难得的意义。相形之下,男人们的 生命则显得那样的虚伪与僵硬。这足以表明庐隐所具有的已不是一般性的女性意识,而是迄 今仍未过时的真正的女性主义立场。最能说明问题的,便是讲述一对女性同性恋间具有性爱 成份的情谊的《丽石日记》。小说以女主角丽石的视点展开,直白地表示“我从不愿从异性 那里求安慰,因为和他们的交接总觉得不自由。沅青她和我表同情,因此我们两人从泛泛的 友谊上,而变成同性的爱恋了。”这种叛逆行为自然无法为社会所容。虽然沅青也曾热烈地 作出了回应,在一封信中抱怨丽石“为什么不早打主意,穿上男子的礼服,戴上男子的帽子 ,装作男子的行动,和我家里求婚呢?”但最终还是回归传统,向丽石进言:“我们从前的 见解,实在是小孩子的思想,同性的爱恋,终久不被社会的人认可,我希望你还是早些觉悟 吧!”而丽石却执迷不悟最终以生殉爱。但小说的主旨显然不在控诉社会伦理的滞后,而着 重于表现女性对于生命体验的敏感与率真。所以虽然故事的处理显得稚嫩,其独具的诗性意 义迄今仍闪烁着光芒。
上述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效果,是由于叙述主体的价值取向都从女性本位出发。 所以女批评家赵园认为:不同于一些试图超越自身女性身份的作家,“庐隐在她的作品里彻 头彻尾地是个女人。”[10](P374)能够坦白地将一个女人内心最隐秘和真实的需要与愿望以 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庐隐作品的所长。茅盾在《庐隐论》里曾称赞说:“庐隐作品的 风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但重要的是看到,在 庐隐这种流利自然的叙述话语中,畅开着一个真切的女性世界。比如《沦落》,女主人公松 文身边有两个男性:一个是曾救过她命的海军军官赵海能,另一个是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女 性化的美青年,男权中心是他们的共同点。这个叙述十分杂乱的短篇象庐隐其他作品一样, 缺少结构的整体感,其意义在于展示了女主角内心对男性的欲望:她既为前者魁梧的身干、 刚武的男性气质和热烈的情感所吸引,又对后者那种青春美与温柔体贴的文人情感所倾心。 庐隐以其文学叙事向我们表明:所谓女性主义立场,就是设身处地与无条件地,对一直在男 权专制文化阴影中生活的女性的行为方式与生活态度,以一种宽容的精神给予理解。这同样 也是评价庐隐小说所需要的前提,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庐隐通过她的不宽的视野、不大 的格局的恋爱悲剧的描写告诉我们:女人的根本出路在于自己战胜自己,在于精神世界通过 自我改造、搏斗最终完成自己。”[6](P6)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庐隐这些作品恰好为女权 主义文学批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证明:人们只有抛开通常采用的好作品与伟大作品的尺度, 才能够从这些“富于热情而缺乏思想力”的并不成熟的叙事中,提取出其所蕴含的文学价值 。曾提出“庐隐的际遇与作品原应为女性主义者大书特书”的王德威教授也颇有同感,他认 为只有从女权批评的视野出发人们才能够意识到,“庐隐的作品以缠绵奔放见长。在抒发女 性抑郁的深情、困蹇的处境方面,庐隐比诸今天的许多女作家并不逊色。”在他看来,常常 被一些批评家视为冗长枝蔓与感伤滥情的《海滨故人》,“正是以其姿肆的忧伤、绵延的情 景,凌驾彼时男性作家的作品。”[12]这一见解值得认真对待。
三 生命之旅:论石评梅
不少熟悉中国新文学史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五四”文坛上的人物往往比其作品更有魅 力。所以,一些批评家论述那时的文学现象,常常会舍弃并未成熟的作品而选取充满活力的 作者。这种情形对26岁就辞别人世“在一般文学史中少见经传”的石评梅(1902-1928)身上 表现得尤为突出。与庐隐以60多个短篇4部中长篇小说成为“五四”女作家第一高产作家相 反,生前没出过一本集子、身后诗与文加起来不过十余万字的石评梅,大概是最低产的一名 成名女作家。苏雪林当年在论到她时,以一句“其文字明丽哀怨颇为动人”匆匆而过。[1]( P220)在许多时候,她似乎是作为庐隐小说中最具叙事意味的《象牙戒指》的生活原型出现 于“五四”文学史。虽然历史上的石评梅出身门第高贵家庭氛围开明,但或许是同庐隐的亲 密关系,她的个性与文学创作套路与庐隐十分相近。她同北大学生领袖高君宇之间生前不愿 成双死后永远相伴的凄美爱情悲剧,通过庐隐的文学作品而成为佳话广为流传。对于其中原 委,她以两个作品《弃妇》与《林楠的日记》作了某种暗示。但如果回顾中国“五四”女性 文学叙事历程,在1921年就已发表新诗的石评梅仍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
曾有研究者指出,“五四”时期的小说家往往在小说中追求“诗趣”的同时又追求“理趣 ”。[10](P383)此话可以用来点评石评梅的小说创作。在她数量不多的文学叙事中,表现出 两个审美维度。其一是借文学的形式对当时尚在行进中的“革命”作出反思。比如她写道: “专制的帝王虽推倒,依然换汤不换药的是一种表面的改革,觉悟了中国人的思想,根本还 是和前一样。”“革了这个社会的命,几年后又须要革这革过的命。”(《白云庵》)以及“ 一般不得志的人,整天仰着头打倒这个铲除那个,但是到了那种地位,无论从前怎么样血气 刚强,人格高尚的人照样还是走着前面的人开辟的道路,行为举动和自己当年所要打倒和铲 除者是分毫无差,也许还别有花样呢!”(《偶然来临的贵妇人》)其二是表现女性的生命困 惑。如写女性间发生的柔情蜜意的《惆怅》,将一个年轻女性内心对另一个女人的情欲表现 得十分细腻透彻,没有结果的收尾显示了作者良好的叙事意识。庐隐在《自传》里承认自己 的内心常有矛盾:有时“感觉人生无趣,满心充塞了出尘之想”,但“遇到高兴的事情时, 仍然起劲得很。”石评梅也是如此,《白云庵》里的隐居老者一方面向年轻的“我”表示, “宇宙本无由来,主持宰制之者惟我们的意欲情流;人生的欢乐结果只留过去的悲哀,人生 的期望结果只是空谷的回音。”另一方面却又鼓励准备投身于革命事业的“惠”,“正该这 样去才是光明正坦的大道,才可寻得幸福美满的人生。”创作于她逝世前一年的《匹马嘶风 录》,更以一对年轻的大学生恋人为了社会改革事业而牺牲个人私情,为后来风行一时的“ 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但就文字表达与叙述能力而言,石评梅作品的艺术意味其实在庐隐之上。如《红鬃马》, 短小的篇幅里将大革命时代里一个叫梦雄的青年军人的传奇人生收束眼底,故事虽浪漫离谱 但却真切地传达出了一种沧桑感。又如《惆怅》,就题材看这篇作品所表现的与庐隐的《丽 石的日记》如出一辙。但庐隐所表现的只是一种建立于丽石的自我表白上的抽象情感,我们 只是一再听到丽石在那里诉说:“沅青是我的安慰者,也是我的鼓舞者,我不是为自己而生 ,我实在是为她而生。”但未能切实地感受到这一切。与此不同,《惆怅》虽然采用的也是 一种独白的语调,但具体地将一种属于女人间的委婉柔情传达了出来。在诸如“愿你允许我 不再见你,为了你的丰韵,你的眼辉,处处都能憾得我动魄惊心”的倾诉里,以及在“你伴 着别人跳舞时,目光时时在望着我”,“我走进大厅时,偷眼看见你在呆呆地望着我,脸上 的颜色也十分惨淡”,和“我独隐帏幕后,灯光辉煌,人影散乱中,看见你穿着一件翡翠色 的衣服,坐在音乐台畔的沙发上吸着雪茄沉思”等这样一些描述里,我们能够体会到故事里 的两位女性间的那种细腻的心灵交流。所以读石评梅的作品常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若假以 时日,她会为现代中国的女性小说增光添彩。
四 知识话语:论苏雪林
作为五四女作家中最长寿者,创作历程长达70多年的苏雪林(1897-1999),一度以“反鲁迅 ”在现代中国文坛闻名,也曾因此而遭许多大陆批评家的唾弃。将她后期未能在小说创作上 有所成就归咎于人品的低落,认为是“正义感沦丧,艺术味荡然”[9](P296)的结果,这样 的观点迄今仍有影响。但平心而论,这一说法有欠公允。苏雪林虽和五四文学密切关联却“ 不是这一运动中的主要角色”,[13](P389)其小说写作生涯的短暂与其在文学事业上的毕生 投入不成比例等,这些不仅是事实,也是她自己所承认的。半个世纪前她就曾撰文写道:“ 若干年以来,我虽写了一堆烂文章,出版过几十种单行本,纯粹文艺作品实着墨无多,在文 坛始终居于打杂地位。”[5](P115)但究其原因,主要还得从其个人气质与生活兴趣方面去 看。她曾明白说过:“我自开始写文章时,便不想做一个文学家,若说我薄文学家而不 为呢,也未尝不可以。我是欢喜学术的,只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为了不大瞧得起文学,故 亦不肯在这上面努力。”这虽然有些自我解释的味道,但无论如何,她对李商隐研究的独特 贡献和写作时间前后达半个世纪共160多万字的《屈赋新探》,使我们对她一再重申的“我 写学术文章的兴趣比写文艺性的文章,兴趣不知浓厚多少倍,也不知迅速多少倍”,[1](P6 5-68)不能不予考虑。
苏雪林在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界的独特性,在于其是为数不多的集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和文 学研究者三种角色于一身的人。相对而言,她在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方面的业绩似乎比起其 文学创作更让人折服。得益于率性而发的个性与所培育的开阔的审美视野,苏雪林具备了一 位优秀批评家的条件。当年她提出沈从文小说的优点“第一是能创造一种特殊的风格,要鲁 迅、茅盾、叶绍钧等系统之外另成一派。第二句法短峭简练,富有单纯之美。”尽管有时候 “过强的想象力变成了他天才的障碍,左右逢源的妙笔也变成他写作技巧的致命伤”,但仍 认为“作者的天才究竟是可赞美的,他的永不疲乏的创作力尤其值得人惊异。”显得十分有 眼光。她批评“郁达夫除自叙体小说外不能写别的东西”,以自我主义、感伤主义、颓废主 义为作品的基本原素,文字缺乏“气”和“力”;指出虽然“因为热情太无节制,所以巴金 的作品常不知不觉带着浪漫色彩,”但他“究竟是个很可爱的作家”;认为“老舍的思想以 现代人的眼光看并不新颖,对于妇女和婚姻的意见也很陈旧”,其讽刺小说虽滑稽有趣但“ 意味浅薄”,觉得其“讽刺的技巧虽不及鲁迅但比鲁迅可爱得多”;以及封鲁迅为“中国最 早 的乡土文艺家,而且是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等等,观点虽不无偏激之处,但也鲜明地表现 了一位极具个性的批评家不人云亦云的独特见地。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轻视作为一名 文学家的苏雪林的存在。这不仅如阿英所指出过的,苏雪林在文学领域曾四面出击“作品很 多,她写诗,她创作小说,她写剧本,她也作散文”;也在于她的身上有一种真正的诗性气 质。这种诗性气质与她性格中的学术兴趣的结合,使她成为了一个“作家型的学者”和“学 者化的作家”。
作为小说家的苏雪林与冯沅君与黄庐隐是北京高等女师同学。虽然在回忆录里,她自认其 小说写作“比不上那个家学渊源,胸罗万卷的冯沅君,又抵不上锋芒发露,活跃文坛的黄英 。”[14]但其叙事艺术仍自成一体,别具一格。根据作家本人的自述,她在17岁时就以故乡 一个童养媳的故事为素材,写过一篇题为《姑恶行》的小说。这个作品虽不为她的同窗好友 冯沅君看好,却得到了其兄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赞赏。抗日战争期间,她在编写历史传记《 南明英烈传》的基础上,从中取材写成历史小说集《蝉蜕集》。其后又出版了以希腊神话为 题材的短篇小说集《天马集》。但代表她小说艺术最高成就的,仍是其广为批评家所称道、 有“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小说”头衔的长篇小说体自传《棘心》。所谓“小说体自传”,乃是 由于事过境迁来看,这部作品迄今作为小说的意味已不如其作为文学性的自传作品。不仅作 者自己曾表示过这一意思,承认这其实是一个“用小说体裁写的自叙传”,也因为它对于现 代读者的意义,主要是通过一个处于新旧时代转折与过渡期的知识女性的求学海外、抗婚入 教最后又因母女亲情而返国成家的生活经历与成长道路,对一个永远过去了的时代的精神轨 迹作出了真实投影。耐人寻味的是,苏雪林曾十分贴切地批评冯沅君的《春痕》:“故事没 有小说的结构,倒有事实之自然的进展,与其将它归入‘假定’的小说里,不如归入表现自 己的抒情小品。”[1](P218)只要将这句话里的“抒情小品”改成“叙事散文”用于这部长 篇自传体作品,似乎也具有同样的准确性。正如一位女性批评家所指出的:“《棘心》基本 上是流水帐式的平铺直叙,唯因其文气畅达笔致自然,叙事抒情常有意到笔随之妙,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作品的缺陷。”[4](P335)
苏雪林在谈到陈源时曾指出,集新观念与旧伦理于一身、既向往开放的现代又留恋保守的 过去,是许多五四人物的一大通病。在她看来陈源就是一例:“他虽是个留学西洋的人,脑 子里中国伦常礼教的观念却保留得相当浓厚。”[5](P335)但读了《棘心》,你不能不说, 这种矛盾同样也正是作者自身的写照。阿英在这部作品发表不久就指出,“和其他的女性作 家一样,苏绿漪所表现的女性的姿态并不是一个新姿态。”他认为从其作品里能够看到作者 世界观的狭小:“她只是浸在母性以及家庭的爱里,她对于人生的问题,并没有获得确切的 解决。”[13](P396)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意见仍显得十分贴切。从母女关系来表现新旧 时代的矛盾,这在五四文学中并不少见。不同于冯沅君《隔绝》的悲剧处理对这种关系作出 的否定,在《棘心》中作者努力以母女亲情来化解故事中同样存在的那种悲剧性冲突,为主 人公放弃自立人生的行为进行辩解。叙述主体价值观念的陈旧,使这种辩解不仅缺乏艺术味 而 且也不具有思想性。因为作者所欲极力讴歌的这种古老的中国家庭伦理,其实也就是“孝” 本位文化。对此作者自己事后有着清醒的认识:“圣经贤传累累数千万言,大旨只教你一个 ‘孝’字。我不敢轻视那些教训,但不能不承认它是一部‘老人法典’,是老人根据自私自 利的心理制定的。”在这种传统里,“儿女简直成了父母的奴隶。”[5](P288)但尽管存在 着这些缺陷,这部长篇自传体叙事所表现的那种母女间的亲情,具有一种个体真实性。表现 母爱固然是以冰心叙事为代表的五四女作家们的共同所好,但往往失之抽象与虚幻,所表现 的只是母爱的理念。《棘心》所表现的母爱虽还不够宽广,但却具体可触。用书中女主角杜 醒秋的话说:“我忆念母亲,如此缠绵,如此颠倒,真出乎我平生经验之外,想古人之所谓 离魂病,男女陷落情网之时,其况味也不过如此。”(第十二章)文本第七章所描写的母亲心 中一直挥之不去的想识字读书的情结,读来让人感慨万千,也给文本所表现的母亲形象增添 了一份亮色。作者曾以《母亲》为题写道:“我的性灵永远不成熟,永远是个孩子。我总想 倒 在一个人的怀里撒一点娇痴,说几句不负责任的话做几件无意义的令人发笑的嬉戏。我愿 意承受一个人对于我疾病的关心,饮食寒暖的注意,真心的抚慰,细意的熨贴,带着爱怜的 口吻的责备,实心实意为我好处而发的劝规……这样只有一位慈母对于她的孩子能如此,所 以我觉得世界上可爱的人除了母亲更无其他,而我爱情的对象除了母亲,也更无第二个了。 ”[5](P269)
这应该是我们把握苏雪林自传体长篇叙事《棘心》的一个诗学通道:以一种永远依恋于母 亲的童心,来咏叹来自于母亲怀抱的那种永恒而无条件的关爱。它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美学底 色,也是其诗意之所在。其次,这部作品也具有叙述方面的文气通畅与情真意切的优点。苏 雪林曾批评“女作家们写的文章,大多扭扭捏捏,不很自然。”《棘心》虽还称不上是大气 之作,但一派坦诚直率的叙述语调确也胜出于一般女作家的风格。作品以说理议论驾驭叙述 ,结构上也并非一无是处,如同赵景深当年所言:故事“以出国起,以归国终”,表现出叙 述还是“经过一番精心安排的。”[15]作品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议论虽然有损于抽象叙事的自 律性,但也突破了女性叙述通常的小格局,有一种哲理散文的情趣与诗意之美。
作者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时曾说,她的文思启动相当慢,“一定要一面在纸上写,一面才 剥蕉抽茧般,将文思慢慢自脑中引出。”所以她“宁愿写长文而不愿写短文。”[1](P53-54 )事情看来正是如此。只有写到这个份上作者才真正显得自在起来,不再停留于一般性的关 于 中国传统母爱之伟大的“宏大叙述”,进入到了具体而显示个性的“微小叙述”里去,将其 独特的生命体验传递出来。但将苏雪林的这部作品放到百年中国女性叙事来看,它更大的 特色或许还在于开创了一种“智性叙述”文体。这部小说充满着许多优雅的知识意象,可以 被 当作一个思想文本来读。不能不说这是“学者化作家”苏雪林对于现代中国女性叙事的一点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