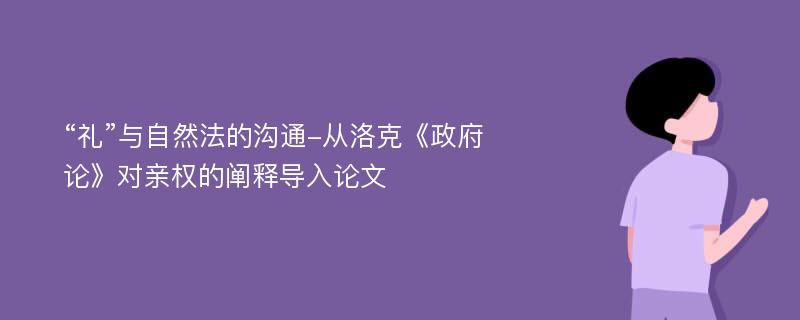
“礼”与自然法的沟通
——从洛克《政府论》对亲权的阐释导入*①
荆月新
( 山东师范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
摘 要: 约翰·洛克的自然法思想和儒家的礼法哲学,均将亲权置于上帝或者神意的支配之下,宣示自然伦理的合法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家族和社会伦理。与之并行的另外一条发展线索则是:以神权法或者神法为逻辑起点,主张国家法或制定法是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的投射。近代以来的法治文化变革,可能片面夸大了中西法律哲学之间的异质性,对两者共性的认知则略嫌不足。
关键词: 礼;自然法;亲权;约翰·洛克;《政府论》
“礼”是儒家哲学的核心范畴,“礼法合一”的法律哲学成为传统中国法的重要特征。在近代以降的文化革命尤其是“西法东渐”运动中,“礼法合一”受到批判和指摘,其理论依据便是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然法观念以及围绕其所建立起来的法哲学体系。“礼”与“自然法”被置于完全对立的两面,相互间的隔阂似乎天然存在、不可弥合,中西法律文化的异质性成为常见的论题。本文以欧洲启蒙时期的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代表作《政府论》为例,从他对“亲权”的讨论入手,结合中国“礼法”观念下的“亲权”观念,予以比较分析,借此来揭示“礼”与“自然法”两个法哲学范畴在立论前提、起源与理论归宿以及法治文化塑造功能等方面的诸多相似,以此探讨其沟通和对话的基础。
一、立论前提——在经验理性上寻求超越
在古希腊,自然法或指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或指国家与政治社会产生之前的“自然状态”下即已存在并通行的规则及规则体系。人们通常认为,自然法是人类在上帝引导之下通过理性来感知、发现和适用的,是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基本准则。至十七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们从自然法观念出发,展开论述一系列命题,形成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的哲学基础,如“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以及权力分立理论等。作为欧洲启蒙思想家代表人物的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对自然法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读,许多论述即是以“亲权”为例证展开的。
所谓“亲权”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缘和生育关系产生的、以父母为权利主体、对子女在人身和财产方面拥有的支配性资格。就内容而言,亲权包括监护权、抚养权以及尊礼权三种不同的权能。在洛克看来,监护权是父母对儿女的管理与控制权;就儿女而言,父母监护权的存在是基于培养未成年儿女心智的需要;至于监护的期限,“直到理性取而代之并解除他们的辛苦为止”[注] [英]洛克:《政府论》(下),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6页。 。可见,洛克的“监护权”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监督并保证子女行为的正当合法性,并对处于监护之下的子女的行为代位承担法律责任;二是代子女(也即以子女的名义)行使某种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抚养权,常被视为亲权当中的财产权利,是指父母从物质上对子女的扶助与养育。对于抚养权,洛克是这样表述的:“教养儿女是父母为了他们儿女的好处而不容推卸的职责,以至任何事情都不能解除他们在这方面的责任。”[注] [英]洛克:《政府论》(下),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2页。 所谓尊礼权,是指以父母为主体,所受到的来自子女的尊重与礼敬。尊礼权存续于儿女一生的各个时期和一切情况下,不似监护权那样局限于子女未成年时期或者精神疾病发作期间。洛克认为:“尊礼和赡养,作为儿女应该报答他们所得的好处的感恩表示,是儿女的必要责任和父母应享的特殊待遇。”[注] [英]洛克:《政府论》(下),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3页。
我露出欣慰笑容,用心良苦地挑选一个个合适的教材对象,发出让人家来游玩儿的盛情邀请,这是我背着乔振宇做的功课,其他都是真实自然发生的,乔振宇的大丈夫保守思想,就是在这些真实的婚姻个案里,一点点土崩瓦解的———面子上的虚荣和热闹终究抵不过婚姻内部的自由、尊重,信任和舒适来得重要。
与古代希腊的自然学派一样,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并不否认先验理性的存在,洛克也不例外。在阐释了“亲权”及相关概念以后,洛克以先验理性作为理论前提展开论述。洛克对先验理性的认识建立在对上帝意志的超验特征之上,即他在认同上帝意志超验属性的基础上,又有将自然法赋予上帝意志的色彩。从这一角度讲,洛克的政治哲学并未完全摆脱中世纪教会法学的影响,他坚持“上帝意志”的决定性意义。对亲权的来源,与大多数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一样,洛克在承认“上帝造人”的前提下,强调人的第一本性是“自我保存”。他指出,为了实现自我保存的目的,人类需要繁衍和接续自己的后代。为了保证子女的成长的健康与安全,他说:“上帝使父母怀有对儿女的天生慈爱。”[注] [英]洛克:《政府论》(下),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04页。 这种“天生慈爱”便成为亲权的最初来源。可以发现,在洛克对于“亲权”来源的论述中,“上帝意志”成为逻辑的始点和直接的依据。
“礼”从一开始即与由血缘构成的“家庭”“宗族”存在密切的联系,家庭和宗族都是由血缘这一自然纽带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组织,血缘关系的亲疏、高低也就决定了所采仪礼的不同。生育与繁衍后代是人类扩大再生产的自然法则,而血缘关系则是因此形成的自然秩序,礼的内容和方式即由此决定。父母生育子女这一自然过程,就使得作为“尊亲属”的父母对作为“卑亲属”的子女享有“亲权”。融合了“礼”的传统中国婚姻家庭法带有浓厚的伦理法色彩,因此,通常被称为“家庭伦理法”。又因为家长、族长在家庭与宗族中的绝对权威和支配地位,而将“亲权”称为“家长权”。“家长权”制度包含如下内容:父母对子女的婚姻决定权和财产的决定权、对子女的抚养教育权、对子女的惩罚权。与洛克的“亲权”观念类似,“礼”主导下的“亲权”或者“家长权”体系,作为权利主体一方的父母处于优势地位,代为处置子女的财产,在承担教育抚养子女义务的同时,有权决定子女的婚配对象,对于子女不尽尊礼的行为,父母可以对其施以重罚。并且,当这一问题上升至国家刑法层面的时候,为体现“亲权”的优势地位,国家不仅可对子女采取刑事处分,还可加重处罚。“礼”从自然血缘的角度,论证了子女对于父母的“孝”与“服从”的合理性,传统中国的立法者采纳了这一观念,并从此出发论证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所存在的等级差异。子女对父母的服从与尊敬,以及父母对子女的人身权与财产权所享有的决定与支配权利,均由此延伸而来。人们从“礼”出发,论证了“家长权”的合理性,同时,凡是违“礼”的行为都要受到责罚。“礼”既是家庭内部伦理秩序的理论原点,也是归宿。恰恰是由于两者在起源上的相似性,也就决定了“礼”与“自然法”这两个东西方法律哲学的基本范畴,在内容以及在差序性的社会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具有极强的相似性。
同理亦然,“自然法”也并非塑造近代西方法律精神和法律制度的唯一要素。在以自然法为主要思想脉络的法治发展进程中,也曾出现具有绝对支配意义的“父权”内容,如作为西方法制文明发源地的古代罗马,父权的内容与传统中国儒家法律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根据中国的礼制制度,父子之间是不能诉讼的,即“父子无狱”;而根据古代罗马时期的“家父权”制度,父以及在父权下之子相互之间,亦不能提起诉讼。二是根据中国古代儒家化的法律制度,父家长对于所属卑亲属或家庭奴隶的伤害行为,被认为是与国家公共秩序无关的“非公室告”;无独有偶,在古代罗马,则有“家父权不涉及公法”的古老法谚。三是根据中国古代的礼制和法律,禁止“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古代罗马法则禁止在父权下之子和父分开持有财产。四是根据中国古代法律,父家长有权将其卑亲属送交官府并要求给予刑罚;罗马的帝政时期家内惩罚的无限制的权利已变成为把家庭犯罪移归民事高级官吏审判的权利。五是在中国古代与古代的罗马,父家长都曾有过对子女的无限支配权,其中包括生死之权、肉体惩罚之权、婚姻决定权,等等。[注] 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1页。 罗马时期也曾盛行自然法的思潮,西塞罗是罗马时期自然法学的创始人,作为执政官的他,既接续了源自古代希腊的自然法传统,又开创了自然法的罗马时代,对罗马立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世学者认为他“使自然法理论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即变哲学的自然法为法学的自然法,将法哲学世界观发展成为法学世界观”[注] 何勤华:《西方法学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8页。 。古罗马法学家盖尤斯曾言及父权的特权性质:“我们在合法婚姻中生育的子女处于我们的支配权下。这是罗马市民特有的法。”[注] [古罗马]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即便是在这样的文化和哲学背景之下,古罗马的“亲权”仍然具有绝对性,这一点同样是由当时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诸要素所共同决定的。同理,也不能将欧洲启蒙时期法律革命的平权精神和契约理论仅仅归因于自然法观念的影响。当市场经济高度发展、传统的封建经济和自然经济被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经济取代,市民社会逐步形成以后,近代法律文化所需要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基础同时具备的时候,蕴含于自然法中的平权精神和契约理论,才为人们接受并得以形成法治实践。
在国际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一些企业已经认识到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并试图建立许多预算管理机制。切实的到企业中运营和实施,而预算管理不仅对预算本身有着很高的需求,而且还需要有完善的监管机制来实现有效管理。在预算管理机制实施的过程中,我国企业主要关注预算工作的细节和内容,对预算管理的监督体系缺乏了解,使得企业预算管理不可能实现全面有效的落实。
整体地看,尾库治理工程着眼于根本治理。新修的排水、泄洪沟渠如同蛛网、混凝土坝路环绕库区,固砂抑尘的绿化工程正在进行、坝体安装了电子监测感应系统,坝体是主体工程,坚实程度难直观判断。
二、渊源与归宿:自然法则与自然秩序
仍以“亲权”为例。洛克认为亲权源于自然法则的安排:“如果有人问,父亲支配他的儿子的权利是根据什么法律的,我可以答道,那无疑是根据‘自然’的法则。”[注] [英]洛克:《政府论》(上),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4页。 在洛克的论证体系当中,他认为初生的孩童因其幼弱而无法自我供养,父母便理所当然地担负起养育与扶持的责任。在洛克看来,父母生养和抚育子女,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亦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因为连普通的动物都会选择繁衍和养育后代。为了证明这种生育过程是自然秩序的安排,他强调了父母在生育子女行为过程中的无意识状态,并以此证明自然法和自然理性对人的这一行为过程的支配。他说:“上帝以他的无限智慧,把强烈的性交欲望安置到人类的体质之中,以此来绵延人的族类,而人类这样做时却大都并没有这项意图,而且生育儿女还往往是与生育者的愿望相违反的。”[注] [英]洛克:《政府论》(上),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6页。 除了繁衍后代是自然规则和自然法则的规定,洛克以自然规律和自然秩序来阐发人类监护子女的必要性:遗弃子女,“连狮子洞里和豺狼窝中都没有这样残忍的事……难道唯独人类有特权比最犷野不驯的动物还要反乎自然地从事活动吗”[注] [英]洛克:《政府论》(上),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8页。 ?同理,尊礼和赡养也是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像存在于自然界中的所有动物之间的亲子关系一样,父母由于生育和抚养子女的这一自然过程,使他们有权支配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并获得子女的尊礼,以至于在子女成年、父母年迈以后,父母有权获得来自子女的赡养。
在古代希腊,受低下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局限,人类难以揭示蕴藏于自然现象背后的科学规律,顺理成章地产生了自然崇拜,这也成为早期西方哲学的一个共同特点。“几乎所有的早期哲学家都以‘论自然’作为他们著作的标题,用自然事物或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类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生活。”[注] 何勤华主编:《西方法学流派撮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页。 与之类似,“礼”起源于先秦的农耕社会,所谓“三代之礼”指的即是礼的萌芽时期。彼时的人们对自然界、对天等一切自己无法准确认识的世界和现象,都充满了神秘与敬畏之感,并从主观上赋予其超自然的力量,各种山川神灵的崇拜以及超血缘的部落内祖先神的权威崇拜,也随之产生。以此为基础,出现了富有自然主义特质的原始自然宗教和哲学。经年累月,人们将这些具有多神崇拜意义的原始宗教信条以及氏族、部落的习俗继承下来,成为先民行事做人的规范与准则,并构成礼的最初来源。今世学者对此评价说:“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水平与科技文化极端低下的条件下,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生老病死都充满了敬畏与神秘感,因此最早的礼与天地鬼神相通是很自然的。”[注] 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4页。
“礼”和自然法均源起于早期人类文明,并与自然崇拜有着密切关联,被视为自然规律和自然秩序在人类社会中的规则再现,并成为此后人们论证社会和国家治理问题的出发点乃至归宿。
植物诱导抗性近年研究较多的是抗病、抗虫性和抗寄生性杂草,其中利用抗坏血酸提高番茄对弯管列当的抗性,利用矮壮素(chlormequat)和赤霉素(GA3)增强番茄对分枝列当的抗性及利用烯效唑(uniconazoze)、苯并噻二唑增强向日葵对向日葵列当的抗性,但上述诱抗剂均未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本研究是国内首次在向日葵上应用植物诱抗剂-IR-18,明确了该药剂对向日葵列当具有显著的抑制寄生和生长作用,减缓了列当对向日葵营养竞争的影响,从而提升了向日葵的产量和品质。
传统中国的婚姻家庭法制带有浓厚的伦理法色彩,因此,常被称为“家庭伦理法”,“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睦家庭氛围常被称为“天伦之乐”,被赋予“天理”之下的“人伦”色彩。与自然法学派一样,儒家也将生育子女看作是自然的安排,《周易·系辞下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注]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30页。 人与世间万物都是天地自然化育的结果,天地自然化生、养育万物与人,是天地生生之理的体现。所有生命同出一源,万物皆生于同一根本。“礼”源于早期人类祭祀祖先神的仪式,是家族内部的行为规范,它规定了祭祀典礼所使用的器物、所穿着的服装以及所行的仪式等。“礼”最早是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从事宗教活动所遵循的仪式和规范,其中融合了早期人们对于强大的自然界和人类先祖的敬畏。从卜辞来看,商代的祭祀对象很多,大凡山川河岳、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高祖先公、先王先妣,都在祭祀之列,祭名和祭仪近200余种。后来,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礼”的内容逐步扩大化、系统化,人类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礼节仪式逐步被纳入“礼”的指导范畴。“礼”的意义也随之扩大,从宗教领域扩展到政治、法律、社会伦理等领域。
在自然法与上帝的关系上,洛克认为,自然法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人(包括立法者本人及其他人)的“永恒的规范”,正所谓:“自然法也就是上帝的意志的一种宣告。”[注] [英]洛克:《政府论》(下),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84页。 据此,他断定:自然法是天然合理的,教导着遵从理性的人类。人类通过自身的理性认识自然规律、自然秩序,发现自然法,并以其作为最根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事实上,启蒙时期的古典自然法学家们在坚持自然法的先验属性方面是一致的。孟德斯鸠曾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注]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页。 这种关系从本质上是事物的规律。而“自然法”乃是“在所有这些规律之先存在着的……所以称为自然法,是因为它单纯源于我们生命的本质。”他又说:“自然法把‘造物主’这一观念印入我们的头脑里,诱导我们归向他。”[注]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4页。 这一观念之核心在于:自然法代表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内在规律,其在位阶上高于人类社会的世俗法律,统治者只能发现它,而不能根据主观意志和需要创造它,这一思想在当代也得到了继受。詹姆士·塔利在《为〈政府论〉定位》一文中写到:“在自然状态中,人民通过自治的形式直接运用政治力量。所有人都有权利和公民的责任在非正式裁判所(ad hoc tribunals)中对被指控违反了自然法的人作出判决,并且执行根据其犯罪程度所判定的惩罚和征收定额补偿款。”[注] [英]尼古拉斯·菲利普森、昆廷·斯金纳主编:《近代英国政治话语》,潘兴明、周保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2页。
“天”与“天道”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张岱年指出:“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天,在不同的哲学家具有不同的涵义。大致说来,所谓天有三种涵义:一指最高主宰,二指广大自然,三指最高原理。”[注] 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在这里,“天”与“天道”扮演了西方哲学中“上帝”与“神意”的角色。儒家以积极和入世的态度,用人道来重释乃至塑造天道,使天道符合自己所追求的人道理想,又以伦理化的天道来论证人道,以此来达到沟通“天道”与“法”的目的,“礼”在这里即是沟通的桥梁。可见,“礼”的存在,解释了“天道”这一超自然力量对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的支配过程,实现了自然法则与人类社会治理之间的连接。
三、功能有限性:解读法文化和法制度建构要素的多元化
从制度设计角度而言,儒家“礼法”框架下的“家长权”与洛克自然法基础上的“亲权”有若干相通之处,如:在内容设计上,作为尊长的父母在与子女的关系互动中处于优位;基于监护的理由,对子女的人身与财产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支配权,并享有来自子女的尊礼,等等。但是,也有区别,如:“礼法”特征下的“亲权”具有绝对性——亲权处于永久性的支配性地位。以父母对子女财产的支配权为例,儒家的礼法哲学认为“父母在,不私财”,它所强调的是:只要父母尚在,即便是成年子女,亦不能别籍异财,显示了亲权的支配地位具有绝对性的特征。而在洛克的“亲权”体系中,除“尊礼权”之外,其他内容的亲权仅具相对性,当子女成年并具有了“完整的理性”以后,具有支配性特征的亲权就会从相关领域退出。又比如,与“礼法”体制下对“父权”的特殊强调不同,基于母亲在生育子女当中所承担角色的特殊重要性,洛克的自然法理论主张父母享有平等的“亲权”。
正因为如此,近代以降,受西方学术体系熏染的人们多将“礼”“礼治”“礼法”与“等级制度”联系起来,在政治与法律领域则由此产生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传统中国法律中的政治独裁、文化专制以及贱视人权等法文化和法制度的形成,源自“礼”或者“礼制”的塑造,甚至将“礼治”等同于专制。事实上,就“礼”而言,它仅是影响法治文化的价值走向以及法律制度设计的众多要素之一。法治文化以及制度设计的最终内容及其现实样态是若干要素综合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当代学者将具有家庭伦理特征的法文化和法制度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结构是其得以产生的经济原因;二是中国的宗法制度由来已久;三是儒家的“礼法”思想是以等级制度为特征的封建伦理法体系的理论凭据;四是封建统治者从其长期的统治经验中,总结出父权、族权在社会稳定与社会治理中的特殊作用。[注] 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30-133页。 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只有一个方面与“礼”相关,且其作用仅限于为伦理法思想提供了“理论凭据”而已,伦理法思想的产生,还有其特定且必要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原因,恰恰是由于上述诸种要素的综合影响,乃至于在法文化产生过程中的竞争与博弈,才最终使得传统中国社会的法文化打上了“伦理法”的印记,并被赋予了“伦理法”的特征。除此之外,也有当代学者将“家长权”绝对性的产生归因为中国的自然经济形态,“在中国古代,父系家族首长对土地财产的支配是终生的,因此父对子的人身支配也是终生的”[注] 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29页。 。因此,“在自然经济的支配下,以父系特权为核心的宗法家族秩序被加工成神圣永恒的法律”[注] 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29页。 。可见,“礼”在传统法治文明塑造当中的功能是相当有限的,将传统中国法治文明中的“问题”或曰“弊端”完全归结为是“礼”的原因,失于偏颇。
与洛克对自然法的解读一样,儒家对“礼”的解读,同样以先验理性为前提。《礼记·礼器》中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注] 杨天宇:《礼记译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85页。 在这里,将“礼”与神秘莫测的超自然力量联系在一起,使其具有了先验属性和自然理性基础。当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政治哲学的正统之后,“礼”在传统中国文化的话语系统当中,代表了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永恒规律和宇宙法则,并成为维系人际关系的无所不在且又颠扑不破的行为准则。人们赋予了“礼”以神秘莫测的超自然力量,是规训民心民情的普世规则。对于先验原理的承认恰恰也是儒家哲学的特点,牟宗三曾将先验原理的存在视为哲学讨论的前提。他说:“一哲学系统之完成,须将人性全部领域内各种‘先验原理’予以系统地陈述。”[注] 牟宗三:《历史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就儒家而言,礼,上接天理,下应民情,沟通天与人。既代天立法,又代天治民。同时又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理在某种程度上亦是民意的现实反映。因此,“国法”必须“应天理”,“应天理”就是“顺民情”“从民心”,而“礼”则是“天理”与“人情”之间的沟通桥梁,其地位类似于联结上帝意志与人定法的自然法,是带有先验特质的概念和范畴。
综上所述,无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还是在传统中国社会,法治文明的形成都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作为法律哲学范畴的“自然法”或者“礼”的一因之果。将近代以来东西方法文化和法制度的相向发展,完全归因于诸如“礼”或者“自然法”之间的差异,既不客观,也有失公允。
结论:沟通是法治文化“和而不同”的基础
就以“礼”为核心范畴的传统中国法治文化与以“自然法”为核心范畴的近代西方法治文化而言,差异性的存在并非意味着某种法律文化是强势的,或者是相对于另外一种文化而言是更为优秀的。差异性既是文化多元的表征,也是文化多元的根由,更是不同法治文化进行沟通的必要性前提和基础。近年来,我们在社会文明的构建中,提出中西文化“和而不同”的命题,所谓“不同”,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理解:一是从静态角度,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范畴的客观描述;二是从动态角度,对不同文化之间变化与发展过程的对比观察。“不同”所反映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这既是客观事实,也将长期存在。所谓“和”,既是目的,也是前提。所谓“目的”,它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处;所谓“前提”,是指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沟通和对话的基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和而不同”的要义在于:不同文化之间只有友好沟通,方能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沟通,是不同法律文化之间实现“和而不同”的基础。
在传统的中国法治文化体系当中,“礼”是规范社会运转以及人生安排的典章制度和行为模式。《礼记·曲礼上》曾对“礼”的功能作如此概括:“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注] 杨天宇:《礼记译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页。 “礼”的功能范畴及于道德、宗教、世俗、司法事务,牵涉至国家、社会以及家庭的生活及制度安排。与之相类,自然法是近代欧洲政治与法律哲学的逻辑起点。在西方法哲学的发展史上,每当人类开始自我反省既有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或者探索未来法制发展的可行性时,自然法从来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主题。对于自然法的这一特殊地位,亨利·梅因指出:“如果没有自然法……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了。”[注]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3页。
学习效果评价对教师教学和学生知识技能掌握情况具有双向调节、促进作用。目前广泛采用期末统一考核评价的方式,这种先学习再评价的方式失去了评价的促进作用。如果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不能很好地掌握学生学习情况,该教学活动可能采用一个进度、一种方式进行下去,对学生的学习结果造成较大负面影响[2]。学习是一个过程,评价也应实时伴随,发现问题立即调整,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
当然,我们不能仅凭“礼”与“自然法”这一对法律哲学范畴之间的可沟通性,来断言东西方法治文化之间的趋同。但是,当影响法文化与法制度的其他要素如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诸条件齐备的时候,法治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在所难免。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法律移植的正当性。
Communication between “Ritual ”and Natural Law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Parental Power in Locke’s Concerning Civil Government
Jing Yuexin
(School of Law,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Both the thought of natural law by John Locke and ritual-law philosophy of Confucians put parental power under the control of God or the will of gods, which declares the legitimacy of natural ethics, and based on this, the family and social ethics is established. Another developmental clue in parallel with it uses the theocracy or the divine law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advocating that the state law or the statute law is the projection of the natural order and the natural law in human society.The reform of the culture of rule of law in modern times mayone-sidedly exaggerate the heterogeneity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egal philosophy, while the understanding of commonality between them is a bit inadequate.
Key words :ritual; natural law; parental power; John Locke; Concerning Civil Government
中图分类号: D9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9)02-0098-07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OI) : 10.16456/j.cnki.1001-5973.2019.02.008
* 收稿日期: 2019-01-06
作者简介: 荆月新(1969— ),男,山东东营人,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
①基金项目: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乡里制度转型中的法治文化研究”(16BFX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王盛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