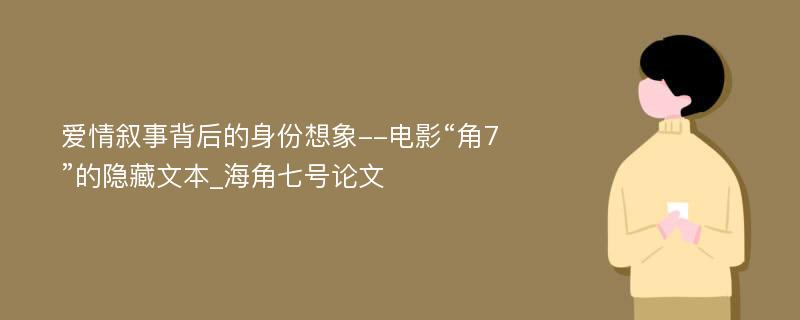
爱情叙事背后的身份想象——电影《海角七号》的潜文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角论文,七号论文,文本论文,身份论文,爱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魏得圣执导的电影《海角七号》在台湾电影凋零的当下创造了票房奇迹,并在金马奖中收获丰厚,成为2008年台湾的重要文化事件之一,热潮甚至传递至内地。本文试图穿越电影的表层叙述,通过性别/身份视角以及精神分析的方式复原导演刻意隐藏在内部的潜文本,从而揭示这部电影引发的台湾文化热潮背后值得仔细玩味的意识形态。
一、吊诡的爱情故事
《海角七号》用交叉叙述的方式讲述了两个时间维度发生在同一地点(台湾恒春)的爱情:一个是60年前日本殖民台湾时期,一名日本教师由于日本战败被迫放弃与之相爱的台湾女孩友子,在回日本的轮渡上写下了7封思念女孩的情书;另一个发生在当下,恒春即将举办一场海滩音乐会,需要组建一支本地民间乐队做暖场演出,曾经在台北玩音乐,现在回到家乡做代班邮差的年轻男子阿嘉,在参与乐队的过程中与担任演唱会监督的一名日本女孩相识相爱。将两个故事联系在一起的是60年后由死去的日本教师的亲属寄到台湾的那7封情书。由于时过境迁,昔日台湾女孩不知何处,阿嘉担负起寻找的责任。
前一个爱情故事用画外音的方式通过日本教师阅读自己写的情书展开,两个人物没有正面镜头,大多用远景和背影的方式出现,呈现出虚写状态。但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画外音既可看做故事内叙述(因为他是其中一个故事的参与者),又可以看做是故事外叙述(相对于第二个故事来说),在电影中日本教师的声音自由出入,成为整个文本的实际操控者。
这不仅仅因为画外音/日本教师的存在使得整部电影呈现出历史的纵深,更重要的是它成为后一个爱情故事讲述下去的基点,以及其合理性的全部依存。我们不难发现后一个爱情叙事呈现出的空白点和漏洞,都由画外音恰逢其时地予以填充,比如阿嘉与日本女孩之间爱情发展几乎没有铺垫,因此仓促且突兀地上床情节显得难以令人置信,但此时正是马上切入的日本男子画外音以及渡轮送别的画面,使得上床情节似乎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观众在款款情深的朗读声中进一步认同60年后的爱情。
可以这样说,相对于实写的第二个爱情故事,第一个爱情故事应当更重要。其一:第二个爱情故事是第一个爱情故事的注脚和连续,《海角七号》与其说讲述了发生在当下的一个爱情,不如说是导演用第二个故事表述对过去的那段爱情的深切怀念和延续的渴望。其二:用朦胧化、唯美化处理方式描述的第一个爱情故事是导演刻意为观众“制造”的一段美丽的历史(这恰是这段爱情的吊诡之处),没有这段历史叙事,后一个爱情就成为虚空。因为用乔纳森·佛里德曼指出的建构族群认同的有效方式,就是用过去的故事进入现在故事,①没有这种进入,观众无法对发生在台日之间前生今世的未了爱情产生认同。
詹明信指出第三世界文化必定是寓言性的,台湾的朦胧身世同样适用于这个论断。故事刻意选择了台湾人与日本人之间的爱情,敏感的国族身份很难不让人联想起政治隐喻,下面从两个层面来阐释这个“爱情”神活背后的意味。
二、成长中的身份主体意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逐渐清晰的本土意识诉求是台湾新电影的核心活语,《海角七号》可以看做是其中最为明朗的一个。为此,我们可以用类似知识考古的方式从侯孝贤、杨德昌、魏德圣的电影中勾勒一副有关“子”的“成长”谱系,伴随期间的是关于反叛、暴力以及父的死亡,这种关于“子”与“父”之间关系的展示是台湾本土意识的最好隐喻。
侯孝贤电影被称为“台湾电影里为台湾历史及台湾人身份寻求定位的精神地图。”②他执导的电影中有关个人成长的记忆自觉地同台湾主体意识联系在一起。《童年往事》中“阿孝”的成长伴随着来自中国内地的父亲、母亲和祖母的相继去世,随着父辈的远离,“子”与有关中国内地的联系也就渐行渐远。有一个镜头正体现了这种意味深长的情绪:父亲在深夜开往内战前线的战车轰鸣声中辗转反侧,家国忧思使其无法入睡,呆立在茫茫夜色中,而此时他的孩子则安然深睡。侯孝贤用画面诉说出:与父辈对母国的血肉连接相对应的是“子”一代对大陆的疏离。即使如此,侯孝贤仍然表达了一种针对中国内地的挥之不去的乡愁和隐隐眷恋,那是希望带着孙子回归故土拜祖宗的老祖母给“阿孝”们留下的一抹温馨的记忆。
如果说侯孝贤展示了少年的断乳与最初的自我意识,那随着“父亲”离去,获得空前自由的,在乡镇中到处游荡的少年,在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已经进入了充满叛逆的青春期。电影中城市里人与人的冷漠取代了侯孝贤的最后一抹乡土家园的温馨,主人公小四在父性衰微、失去庇护的环境中充满寂寞的成长。
我们知道,父权使父亲处于尊位,文化意义上父亲意味着典范、权威、秩序。大部分的男孩会在成长过程中,意识到来自父亲的权威和威胁,用精神分析的表述,便是阉割威胁。如果“父”强大,被阉割威胁的“子”对“父”就充满敬仰、认同、仿效,为了想要“父”所拥有的一切,“子”将“父”的律法内化为超我,这样“子”战胜了俄狄浦斯情结,成为“正常”的儿子/继承人;如果父性衰微,对“子”的成长无法完成精神的指引,“子”对“父”无法完成认同,那么父子关系往往陷入失序状态,“子”张扬的叛逆性、暴力性使其往往成为意图“弑父”的逆子。这样看来,表面温和安静的小四在青春期的成长中必然蕴涵着暴力的因子。当他用刀子捅向小明时,其实“父”的形象也便訇然倒塌,而“子”在青春期寂寞空虚的成长经验从另一个侧面展示出无可言说的台湾的挫败感,这是暴力背后的悲情。
曾经的懵懂少年在《海角七号》中已经长大成人,剧中“子”与母共同生活,母亲与一个男人同居,这样的一个家庭组合中“父”没留下一丝印痕,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完全性缺席。影片开始于有着寓意的“去你妈的台北”的骂声,阿嘉骑着摩托回到台南恒春。他独立健壮英俊,个性十足,有点玩世不恭,重要的是他有才华,充满魅力,家乡的乐队就是以他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在日本姑娘的帮助下,乐队在沙滩音乐节上获得成功,阿嘉也获得了日本姑娘的爱情。
魏德圣浓墨重彩地在电影最后用一种“仪式”来声明“子”的成人,从而完成了从阿孝、小四到阿嘉的成长诉说。笔者认为《海角七号》中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这个仪式——演唱会。由客家人、闽南人、原住居民、少女、经历过日本殖民的老人等组成的乐团,似乎有意展示出一幅充满差异和多样的后现代图景,隐喻当下充满冲突的台湾,阿嘉是这个乐队的灵魂人物。导演在对乐队差异性和多样化的迷恋之间并没有任由台湾身份自由漂移,表面上似乎在叙说一种多样性经过混乱后的和谐(电影前面仔细描写了乐队如何由混乱到和谐的过程,其中蕴含着诸多的商业桥段),其实更重要的是导演企图通过演唱会进行阿尔杜塞所说所谓的“召唤”和建构,③借用阿嘉写给日本姑娘的情歌《国境之南》,“将那一年没有完成的故事讲完”,使台上台下的人最终确认自己身份,最后台上台下共唱一首日本的民谣,使得这种确认更加明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演唱会成为群族认同的场所(place),在这场召唤的仪式中,阿嘉(台湾)完成了他的成人礼;在这样一个狂欢一样的成人仪式中,演唱会的观众通过对乐队的“凝视”获得满足和认同。
三、可疑与分裂的性别认同
《海角七号》虽然用隆重的仪式叙说“子”的成熟,在文本中却表现出自我矛盾的一面,这主要体现在“子”可疑的性别认同,一定程度上使得“子”的主体性呈现分裂状态。
回溯台湾六七十年代的许多影片,不难发现有一种几乎固定的叙事模式:流浪与归家,所有的悲情都发生在寻找归家的路程中,表现出经历日本统治后大多数台湾人失去家国归属后的无奈惶惑,电影中的主人公多为孤女、丫鬟、酒女、舞女。众所周知,文学作品中的男女性别所反映的并不是纯自然的东西,而是历史、社会、文化、种族、民族以及意识形态等范畴密切相关的东西。很显然,这些影片中“女性”形象成为曾经被殖民的台湾的准确的自我象喻。《海角七号》亦同样将日本殖民时期“爱情”中的女性形象赋予台湾。引人深思的是60年后爱情中台湾将自身确认为“男性”,在一部电影中从友子到阿嘉,从男到女,完成了台湾的性别转换过程,这种性别的转换明确集中地暗示着台湾由“他者”向“主体”的转移。正是由于性别的转换,随之带来的是将作为女性被抛弃、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悲情转换为“似乎可以掌握主动”的男性赢得圆满爱情的喜剧。
之所以说“似乎掌握主动”是因为电影中的“男主人公”的性别认同呈现出暧昧和含混。作为一个男性角色,阿嘉的社会性别更偏向于女性,也就是女性化,或可称之为“阴性”男人,相比之下日本女性则应该是“阳性”女人。在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上,日本女孩很明显是主动的一方,并且处于实际“掌控”的位置,这不仅表现在她主动将阿嘉拉到床上,尤其表现为给阿嘉戴上“勇敢之珠”,鼓励阿嘉摆脱身份的困惑和焦虑,确认其作为一个成熟的独立的男性主体。正是在日本女孩的鼓励下,阿嘉做出爱的表白:“你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可惜无论是几十年前的恋爱还是现在的爱情,台湾的被动性再一次展示出有趣的性别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这一点在电影最后演唱会中层露无遗:只有日本男歌星的加入才使得“阿嘉”们获得真正的高潮,日本男歌星是“阿嘉”们成为真正男性的雄性荷尔蒙。曾经的被殖民地的主体性和性别认同在此呈现出虚妄的底色。
电影中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仔细分析阿嘉与日本女孩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阿嘉并没有超越俄狄浦斯情结,这种情结只是被转移了,因为他像个孩子一样离不开情人的母性关系。因此,与其说《海角七号》竭尽全力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男性身份的最终确立,不如说展示了性别想象与确定之间的暧昧含混和焦虑,这种性别身份的自我确认呈现出拉康所说的镜像阶段中的理想的自我想象特质。另言之:电影在客观上为我们展示出有关自我怎样沿着匮乏而抵达到“自我长大成为男人”的想象。
综上所述,电影中的爱情叙述既是台湾自我身份确认以及台日结合的修辞策略,也是票房的有力保证。依靠在商业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平衡技巧,导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是需要清醒的是《海角七号》在台湾热映不仅是因为凭借这种平衡技巧,讲述了一个“爱情神话”,而是讲述这个“神活”的年代,以及这个年代中台湾人通过类似宗教体验般地观影,所得到的自我想象和想象性的自我救赎,这是问题的关键。
注释:
①[美]乔纳森·佛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郭建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8页。
②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2页。
③阿尔杜塞指出,文化通过渗入人们的认知结构召唤个体进入场所(place)给予她/它定位和身份。参见王晓路等:《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