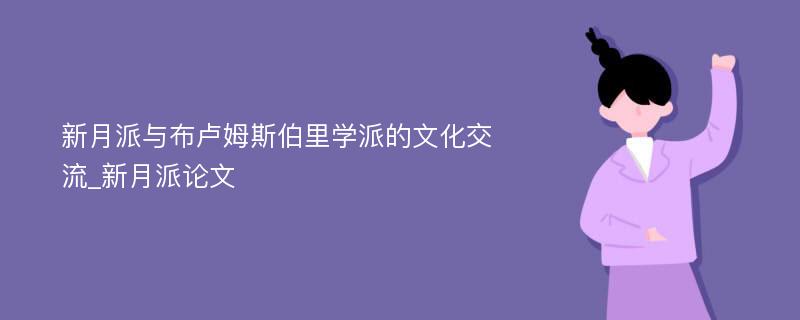
新月派与布鲁姆斯伯里派的文化交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月论文,布鲁论文,姆斯论文,文化论文,伯里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3/7-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3-0179-07 新月派和布鲁姆斯伯里派都是一群精英知识分子,崇尚卓越心智、趣味高雅与精神独立而聚集起来的社团。他们没有明确的文学或艺术宣言,没有一致的社团立场,而以气息相投和心智交流为旨归。他们喜欢在信函、日记和相互传阅的作品等话语中谈论和记录彼此。他们都在各自国家的现代主义文化转换中弹奏出独特而回响不断的音弦。在此意义上,本文首先平行比较二者的成员习性、精神特质及其不合时宜的主张,继而观察他们之间的交流关系。二者实质上的对话以及彼此欣赏,成为我们观察20世纪上半叶文学的多元化现代性追寻的重要文本,当然也成为解读跨语际交流中文化想象的书写见证。 一、两个社团的缘起和松散的形态 1904年,范尼莎、弗吉尼亚(以后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两姐妹在父亲、传记家勒斯利·斯蒂芬(《大英传记辞典》的作者)去世后,随哥哥索比、弟弟安德连一道,搬到伦敦市区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一带的戈登广场46号居住。虽比他们之前居住的肯辛顿区的环境略差,布鲁姆斯伯里仍然属于舒适的中产阶级居住区。不过,与过去父亲家里雇佣众多仆人、气氛压抑不同,这一带的老房子主要由年轻人租住。为了摆脱维多利亚式生活方式,范尼莎把家整个粉刷成白色的,在桌椅上铺印度风格的棉布,“我们不停地实验和革新,甚至准备不用桌布,我们开始绘画,着手写作,在餐后喝咖啡而不是九点钟饮茶”。[1]大约在1905年,索比·斯蒂芬开始邀请他那些剑桥大学的朋友来家里喝茶。范尼莎和弗吉尼亚虽然不能进入大学正式读书(弗吉尼亚后来在《莎士比亚的妹妹》等文章里批评过),然而两姐妹在批评家父亲的熏陶下,饱读诗书,风趣优雅。这个靠近国王十字火车站,从剑桥到伦敦的火车出站不远就能走到的房子,很快成为索比和他的剑桥才子们乐于聚会的地方。 1906年,索比死于一场意外的发烧,这促使范尼莎决定嫁给他的朋友克莱夫·贝尔(艺术批评家和后印象派理论家)。6年后,弗吉尼亚嫁给了另一位剑桥学生伦纳德·伍尔夫(出版人、政治家、“和平主义”的信奉者和实践者)。出入布鲁姆斯伯里沙龙的人五花八门,然而多年来,真正相投合拍的核心成员有:小说家E.M.福斯特,《印度之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作者;批评家、美学家、鉴赏家罗杰·弗莱,著有《视觉与构图》《东方艺术》[他先后策划了两期后印象派画展,将塞尚、高更、梵·高、马蒂斯的艺术介绍到英国,产生巨大争议,同时也改变了英国人的视觉趣味,后来范尼莎和弗莱发起欧美伽工作室(Omega Workshop),试图改造英国的工艺美术];传记家林顿·斯特拉齐,著有《维多利亚名人传》;画家邓肯·格兰特,受弗莱的美学观念影响,积极探索现代主义绘画(他是两次大战之间,英国最重要的画家);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倡导者;伦理学家G.E.摩尔,著有《伦理学原理》,影响布鲁姆斯伯里几代人的伦理探索;哲学家伯特兰德·罗素,后来到过中国与俄罗斯进行观察和讲学;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初出茅庐,其诗歌观念与布鲁姆斯伯里成员多有龃龉,不过他仍是这里的常客,他的诗集《荒原》最初由弗吉尼亚和丈夫伦纳德经营的贺加斯出版社付梓;此外还有政治学、历史学家高尔密斯·路易斯·狄更生,小说家大卫·加涅特等等。谁是布鲁姆斯伯里派的核心成员?这个名单当然是流动的,随着第二代成员长大,老一辈的辞世,这个因心智交流而聚合的同仁团体经历了许多变动。就其影响而言,布鲁姆斯伯里群体无疑是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团体。 留学英国剑桥的徐志摩,于1922年回国,本是为了跟林徽因共结连理,同赴英国完成学业,然而老天不成全,这位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只能在先生所办的松坡图书馆做英文干事。当时的北平已有两个较有影响的社团:一是郑振铎、沈雁冰等在1921年1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他们提出“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二是同年6月,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组成的“创造社”,针锋相对提出“为艺术而艺术”。回国后的徐志摩与两个社团皆有接触,但都不甚契合,落寞而爱好交游的徐志摩,慢慢有了“结社”的想法。新月社是个松散的团体,最初并没有确切的宗旨,不过是以徐志摩的“朋友”身份,因参加石虎胡同七号的聚餐会而聚合起来一群人,他们中有教授、作家、诗人,也有政界、金融界的人物,还有一些附庸风雅的社交人物。据梁实秋、叶公超等回忆,比较常来的人,大约有三类人,有提供经费的徐申如、黄子美;有银行家张公权,有开明政客,很多也是文人,如梁启超、林长民、张君劢、蒋百里等;文人或知识分子则包括胡适、徐志摩、叶公超、梁实秋、陈源(西滢)、林语堂、丁西林、凌叔华、林徽因、王庚(美国西点军校毕业,时任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哈尔滨警察厅长等职,陆小曼之夫)、张歆海、李四光等。闻一多自1925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后,也加入新月社的活动。[2]徐志摩回忆初办新月社的情形,“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了‘7号’俱乐部,结果大约是俱不乐部。”[3]从新月社到新月俱乐部,地址从石虎胡同7号变为松树胡同7号,但后者的论题多涉及经济、政治等方面。 可以说,新月社的主体基本是当时的知识精英与上层社会的聚合,与布鲁姆斯伯里派一样,并不是纯粹的文学社团,而是一个带有情感因素和社交性质的开放团体。徐志摩在《新月的态度》里,解释“新月”的得名,“它(新月)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这一取自泰戈尔《新月集》,颇具徐氏风格的名字,为新月派打上一层浪漫的光辉。从1924年开始于松树胡同的聚餐会,到1926年后胡适、徐志摩等人纷纷南下上海,新月社俱乐部算是解散,此后徐志摩先后筹备和创办新月书店、《新月》月刊,以及接手《晨报副刊》,与闻一多、饶孟侃、朱湘等倡导和实践“格律诗”、排演话剧等等。新月同仁更是在世事岁月的激荡和淘洗中离散聚合,然而以徐志摩为主线,连缀在一起的文人雅士仍被后人视为“新月派”。最典型的就是卞之琳,他仅仅是因为被徐志摩赏识,在《晨报副刊》发表诗歌而被视为新月派;至于叶君健,他最初是武汉大学文学院学生,受来华任教的布鲁姆斯伯里第二代成员朱利安·贝尔赏识,亲炙教诲,也被视为新月派外围成员,这应该算是新月派的延伸和扩展。 自1923年底始于胡适家的聚餐会到1927年新月社告终,这段时期一般被视为新月派的前期。前期新月社的主要成员胡适、徐志摩、叶公超、闻一多、饶孟侃等,也是后期新月派的基本成员。前期新月社偏向于以文艺的抒发争取自由,从影响个体趣味来改良社会;而后期新月派主要是以胡适、梁实秋、陈梦家、罗隆基为核心的《新月》杂志的作者群,在他们的影响下,《新月》杂志偏重于政治与社会讨论。考虑到新月派前后期不同时段的成员及其精神变化的复杂性,本文更倾向于以徐志摩为“连索”的新月派,着重考察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在趣味、习性和精神类型方面的转换,以及他们与布鲁姆斯伯里派之间的文化交汇。 二、知识分子文化认同的迁移与习性的转变 无论是辗转于北京、上海双城间的新月社,还是迁移在伦敦和查尔斯顿庄园的布鲁姆斯伯里派,相对松散,由趣味、情感和心智交流连缀在一起的精英雅集,均因“连索”人物的迁移发生地理空间上的变动,但外在场所、空间的变化并未动摇社团的凝聚力。当我们打开这些成员不同时期留存下来的岁月记忆,当我们将许许多多碎片式的“话语”,还原到彼时的处境、场所和气息中,我们“看见”由于知识分子的认同发生迁移,经验得以更新,其习性转变而生成新的主体性,在东西文化交汇时,彼此阅读,交相呼应,从而显示出多样的现代性追求。 梁实秋多年后写《忆新月》,仍然否认自己属于什么有组织的团体,“狮子老虎永远是独往独来,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伙”;正如布鲁姆斯伯里的松散集合使得不少成员并不认同一个整体社团的存在,克莱夫·贝尔不断质疑是否有传说中的布鲁姆斯伯里派,福斯特否认自己是布鲁姆斯伯里派成员。[4]许多当事人对松散共同体的回忆有不少出入,对于社团的界定更是见仁见智,甚至不承认从属于社团,个中原因,多半起因于由松散集会而形成的公共空间边界的晦暗性。新月派和布鲁姆斯伯里派不是有组织的集体行为,他们尊重主体性,珍惜多元经验的交流与合作,本文的考察试图回望这些“话语”穿梭而建构起的空间,以期将文化精英的精神与习性的巨大转型还原到某个历史场所和文化处境中。 胡适在《追悼徐志摩》中重复陈西滢之前的话,徐志摩是“黏着性的、发酵性的”,“朋友缺不了他”,“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5]徐志摩在前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上给新月同仁写信,他深情地说,“我不仅想念我的朋友,我也想念我的新月”;继而他还以“发起这志愿最早的人”的身份,为新月同仁筹划,“跳蚤我们是不用怕的(“跳蚤”指讥讽新月的人),但露不出棱角来是可耻的。这时候,我一个人在西伯利亚大雪地里空吹也没用,将来要有事情做,也得大家协力帮忙才行。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6]徐志摩等创办新月就是要露棱角,就是要在彼时沉寂的中国大地,在苦闷忧郁的文化空间寻找新的可能性。 新月派的重要成员,除了后来加入的凌叔华、沈从文等,几乎是英美留学生,如胡适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博士,陈西滢为伦敦大学经济系博士,叶公超为剑桥大学文学硕士,丁西林为伯明翰大学理学硕士,梁实秋为哈佛大学文学硕士,饶孟侃留学于芝加哥大学,闻一多留学于科罗拉多大学,潘光旦为哥伦比亚生物学硕士,罗隆基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徐志摩与他们年龄相近,交游广泛的他自然成为新月社的凝聚人物。诚如陈西滢所言,新月社是“志摩朋友的团体”。我们注意到胡适与徐志摩在志趣方面的投合,他们成为新月社的核心也在情理之中。在这则日记中,徐志摩记载了他们的友谊:“昨写此后即去适之处长谈,自六时至十二时不少休……与适之谈,无所不至,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适之是转老回童了,可喜!”[7]胡适既欣喜于志摩的诚挚的理想主义,与之畅谈和分享人生、情感的辗转起伏,又很赞赏徐志摩在白话诗文方面的理想,这正是他发其新声而未就的事业。 20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分子逐渐经历从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换。现代传媒的兴起,现代大学的逐渐制度化,海外留学生不断增多和归国,在大都市空间中,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习性经受了巨大的冲击和转换。如果说传统士大夫以血缘和地缘为联系而聚合起来,形成以私塾、会馆、青楼和书院等空间为依托的同乡会等文人骚客群体,那么现代都市知识分子共同体的产生,改变了这种依傍自然宗亲或地缘乡族的聚合关系,而是以性情气息的投合、教育背景的相似、观念趣味的认同为基础,而催生出一些交往共同体。[8]在伦敦、北平、上海这类大都市的陌生人社会里,知识分子彼此的交游,参与的文化、社会、政治活动既有公共性也兼具私人性。观察知识分子群落的批评与文化实践,诸如聚餐、办刊、演剧、论争、文化巡游等,我们可以发现社团知识分子的新性情和习性的生成,从而感知新的主体性建构。如果说海外教育成为一种关键性的象征资本的话,留学则是20世纪初叶中国都市知识分子彼此辨识的重要标志。新月诸君最初几位核心成员皆留学英美,相似的教育背景使他们与留学法德、俄国、日本的知识分子形成了区隔,依托留学空间而形成的人脉、学术、思想谱系,奠定了这些知识分子回国后立身、立言的重要前提。 在政局混乱中,北平的教授因“欠薪潮”影响而纷纷离去,胡适、叶公超去了上海,与陆小曼结婚后的徐志摩,备感苦闷,不久也受胡适之邀南下上海。在那里有梁实秋和余上沅加入,在社会学家潘光旦家,小组成员筹备办刊物。1928年初,徐志摩募集资金开设了新月书店,同年3月初第1期《新月》出版。《新月》杂志共出版4卷43期,持续到1933年,实为不易。新月杂志的形式最初试图效仿英国的《黄面志》(Yellow Book),而办刊的6年中,先后介绍了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济慈、罗塞蒂、先拉斐尔派、布莱克、勃朗宁夫人、曼殊菲儿、哈代、W.H.戴维斯、高尔斯华绥、萧伯纳、奥尼尔、爱伦·坡、欧·亨利、泰戈尔、易卜生、波特莱尔和莫洛亚等诗人作家,涵摄欧洲文学从浪漫主义到现代派的重要代表。[9] 20年代后期,左翼知识分子关怀政治和社会时局,日益变得激进之时,新月文人却偏好文学,从而被视为“象牙塔”的“绅士”趣味,此评语在当时自然含有讥讽之义。1928年,《新月》创刊号上,徐志摩发表《〈新月〉的态度》,提出追求“健康”与“尊严”的文学原则,接着检视当时的思想市场,一口气罗列13种行业,认为这些思想行业要么源于人类下流根性的放纵,要么属于国外思想的转口贸易。徐志摩的态度是理性的,倡导自由,尊重个体经验和个人尊严,由于接受现代西方教育而禀赋一种理性与自由主义气质。在当时文人益发激进的时流中,新月文人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专注于他们热爱的文学艺术。诗歌方面,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发起“格律诗”运动,以古典式的秩序感、韵律感建构新诗的“三美”。在这场影响中国新诗的格律诗试验中,闻一多以其整饬的诗行、苦涩凝练的意象、锤炼精省的用字,形成一种沉郁精熟的风格,而徐志摩则凭借自然之子的率性天然,将放任不羁的情绪、缥缈虚幻的感受与“自然”意象和古典韵律结合,他的诗歌自有一种融合古典理想的现代感伤之美。 新月派超然旷达的风格直到擅长文艺理论、有批评家风范的梁实秋走向前台才有所改变。与徐志摩专注文艺不同,梁实秋擅长论辩,随后梁实秋就翻译、女师大风潮等文化与社会问题与鲁迅等展开了论战。1931年徐志摩飞机失事前后,《新月》实际上主要由罗隆基主持,大量刊发政论文。罗隆基的激进与狂妄致使《新月》之前的理性、平和之风大加折损。最后即使有叶公超的超然与苦撑,1933年,因徐志摩去世、经费困窘等诸多原因,《新月》停刊。 新月社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化与政治场域里,显得不合时宜,守着“象牙塔”趣味,过着雅士的生活。如若追溯他们的自由主义主张和文艺趣味,则必然注意到他们受其影响,并与之有所过从的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派,而后者也被当时的英国人视为不合主流价值观的一群异类。布鲁姆斯伯里派有意识地与此前的时代、此前的知识分子气质区隔开来,并且与同时代的价值观念保持理性的距离,这种特立独行、崇尚心智和艺术之美的原则,也是该群体的理性选择。沉稳的伦纳德·伍尔夫在他80岁时追忆这段过往,他说: 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萌动时期,我们有意识地反抗父辈和祖父辈的社会、政治、宗教、道德、心智和艺术的制度、信仰与标准。简言之,这是一场针对所谓的维多利亚主义的战争,我们虽然并未完全赢得战争,但让我们感到极兴奋的是,我们就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而胜利与失败端赖于我们如何说,如何写。[10] 一战前,当四个孤儿从肯辛顿的家搬迁到布鲁姆斯伯里,新家从室内陈设、墙面修饰都一改其父辈的风格。父辈权威的缺失一方面给孩子们带来焦虑,以后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与朱利安·贝尔等下一代的书信中,曾提到她年轻时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但另一方面,他们与哥哥索比在剑桥“使徒社”结识的朋友一道,探索新的亲密关系、新的艺术与文化形式,开启了自我追寻的心智与灵魂的冒险之旅。岁月流逝,布鲁姆斯伯里圈子像传奇一般,被人们议论至今,斯特拉齐这样描述他们,“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居所中,舒适并不是非常重要的(赏心悦目才是最重要的),精美的法国菜肴和葡萄酒通常是不可或缺的(经常成桶买回然后装入瓶中),还有自制的面包和果酱(弗吉尼亚擅长于此)……他们珍惜友谊,但不可思议的是这并没有消磨他们的批判意识和能力。于是他们经常相互取笑,但都充满善意,也会讲述一些朋友的故事,看起来颇有恶意。他们只把婚姻视为一种社会习俗,从不在教堂举行这类仪式。爱,无论萌生在异性还是同性之间,对于他们而言都是复杂的,远非一个简单的字眼可以表达。”[11]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风格和价值观念的拒绝,使得现代主义的新风能够流畅地涌入布鲁姆斯伯里派那些离经叛道的艺术家的心灵。这种重新起航的坚毅,促成利顿·斯特拉齐写作《维多利亚时期的名人传》;这种智性的英勇,推动伍尔夫在禀有维多利亚后期的怀疑的同时,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趣味大加怀疑,促成她探索新的小说,并在《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和《现代小说》等名篇里,提出为新时代创作属于自己的小说的宣言;当然,由于对现代风格的探索,1911年前后,罗杰·弗莱在伦敦举办两次法国后期印象派作品展,并在纽约博物馆、泰特艺术馆作演讲,弗莱的美学引介不啻一场现代主义视觉艺术的地震[12];这种对形式的敏感,也促成克莱夫·贝尔探索“有意味的形式”的新美学。布鲁姆斯伯里人无疑发现了新矿,这群才华横溢的冒险者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新的艺术之路。 三、文化旅行与想像:同情性误读 文学与文化书写,总是面对着流动的意义。他者是自我界定不可或缺的参照物,只有当彼此凝视的主体,发现自己正“在通向他者的边界上”或在“边界之外”的他者之中,主体的内在体验发生在主体间的边界或过渡空间中。这一发现其实为我们理解当中西文化相遇,互为“他者”的两个主体,如何在文化时空的转换中,借助想象进入“他者”的上下文,借助想象,一种有价值的、同情性误读而抵达建构性的彼此理解和主体的迁移与重构。“当边界僭越成为最明显、最关键的审美体验形式时,它与无意识的关系随之而变……这些变化不定的边界似乎标志着想象和文学主体性的文化功能的大变化。”[13] 徐志摩是新月派与布鲁姆斯伯里派相遇的连缀人物,种种机缘促成这两个不无相似与呼应的中西社团交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处于新旧更替的历史漩涡,政治动荡和战争阴影肆虐处身其中的知识分子;而此时的英国,经历了一战的侵蚀和欧洲内在矛盾的激化。虽然相隔万里,但这两个与本土主流话语保持距离的社团,跨出文化的边界,搁置殖民主义政治格局,而从文明与文化的视角,在对话中阅读对方,重构自我。徐志摩在那些广为流传的散文中,曾动情地、不无溢美地赞美剑桥对他的启蒙之功,他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14]徐志摩与剑桥的因缘屡屡不绝,对于我们而言,徐志摩是剑桥神话的重要缔造者之一。今天,徐志摩的诗句已被镌刻在剑河畔的石头上,与不远处象征中国文化的孔子雕像遥相呼应,这个新月派的创办者也被剑桥大学载入他们的历史,《剑桥的文学史》这样评述: 通过狄更生,中国诗人徐志摩(1896-1931)于1921-1922年进入国王学院学习,他被介绍给布鲁姆斯伯里社交圈。与此同时,徐志摩对雪莱产生了兴趣,逐渐相信灵魂的探索和猎奇是人生的最高理想……此后他回忆说,只有1922年春天,“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徐志摩后来成为最先创作中国“现代”诗歌的诗人之一。他有两首名诗和一篇散文是写剑桥的,在他笔下,有着座座拱桥、行行金柳的剑河是“世界上最秀丽一条河”。他的诗文使得剑桥城在中国人的情感中占有独特的位置。徐志摩还将他的中国帽送给了狄更生。[15] 在剑桥时期,徐志摩与国王学院的历史学家狄更生建立了深厚友谊,后者曾著《中国人约翰的来信》,此书批评大英帝国镇压义和团运动,与彼时的英国官方、主流意见相左。狄更生在1910年代曾两次游历中国,在写给罗杰·弗莱的信中,他坦陈: 我的感觉是如此亲切,我相信我一定曾经是中国人。……他们是多么文明的一个民族啊!现在,疆土的流失对他们来说是怎样的不幸啊……[16] 狄更生对中国文化的痴迷则影响了乔治·弗莱、T.S·艾略特、利顿·斯特拉齐和翻译家亚瑟·韦利等。在E.M·福斯特的《狄更生》传里,作为他的好友,福斯特中肯地评价了狄更生对中国文明的崇拜:源于他对帝国文明和“野蛮主义”的厌恶,“中国”这个有高贵而深远文化的国度,被他奉为拯救之药。[17]就像徐志摩走向隽永秀美的剑桥,走向现代人文荟萃的英国,寻求心智启迪和身心纾解一般,狄更生、艾略特等人对中国古文明深情推崇,并将此视为化解欧洲工业文明、自以为是的物质主义顽疾的良药。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份带着误读的彼此激赏和想象,推动了二者之间的文化理解。 剑桥自由、闲淡的人文教育启迪了徐志摩的心智,他非常感激狄更生先生,回国后,在为南开大学暑期班开办的“近代英国文学史”讲座中,他将狄更生的《中国人约翰的来信》列入学生的必读书目,并这样介绍恩师的作品:“笛肯生是中国人最好的朋友,他这本书的文字美得不曾有,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像涧水活流一样。此人我也认识他,他在这本书里盛称中国文明。”[18] 就文学方面,徐志摩翻译和评述了不少近现代英国作家、诗人的作品。早期他介绍拜伦、雪莱、济慈等浪漫主义诗人,这与他自己徜徉自然,舒卷唯美的天性颇为相合,他亲近的英国文学是感伤主义的。而彼时,乔治时代的文人们,如弗吉尼亚·伍尔夫试图遗忘和远离的恰恰是19世纪感伤的自我、浪漫的情感和叙述方式。朱利安·贝尔以晚辈的视角评价伍尔夫对于现代英国文学的意义时说,“任何其他的书都没有像她的书那样,以如此入木三分的方式表达我们时代的感性。这不仅仅包括潜藏在这些作品背后的时间、悲伤和人类的渴望等概念,还包括她表达观念的方式,以及她的作品中体现出的技术变革和实验的极端重要性。”[19]迄今没有资料显示,在英国时徐志摩见过伍尔夫夫妇。当他为曼殊菲儿倾倒而著文时,他提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但是很不屑地将其视为有怪癖的新潮女文人,是“背女性的”,“头发是剪了的,又不好好收拾,一团糟地散在肩上,袜子是永远是粗纱的;鞋上不是有泥就是有灰,并且大都是最难看的样式……总之她们全人格只是一幅妇女解放的讽刺画。”[20]直到1928年,徐志摩第三次访问英国,他阅读了《到灯塔去》等作品,意识到伍尔夫的价值和意义,并请求弗莱引介他拜访伍尔夫。[21]此后,在苏州女子中学,他发表演讲稿《关于女子》,力图启蒙女性心智,倡导女子独立,文中有三处与伍尔夫有关,可以说,这也是一篇受到布鲁姆斯伯里派女性主义观念影响的重要论文。 由于狄更生的引荐,徐志摩得以结识布鲁姆斯伯里一些成员,包括他从美国寻声而至的分析哲学家罗素。徐志摩与罗素的交往始于1921年,加拿大麦马士德大学罗素档案馆仍保留了徐志摩写给罗素的七封信。①罗素对中国的看法集中表述在他的《中国问题》里。尽管不像狄更生一样感伤,但罗素对中国文明的好感同样建立在与欧洲的物质文明、好战主义做对比基础上,“说他见到湖南的种田人,杭州的轿车夫,头目那样欢欢喜喜做工过日,张开口就笑,一笑就满头满脸地笑,他看到此情此景,几乎滴下泪来,因为那样清爽自然的生活,在欧美差不多已经绝迹了。”[22]本对苏维埃革命抱有好感的罗素,在游历俄罗斯后,革命的残暴和专制令他颇感失望。此时,目睹与西方工业文明以技术、效率为核心的生活判然有别的中国,罗素与当时那些同殖民主义价值观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一样,视古老的中国文化为解功利文化之毒的清凉药。徐志摩对罗素的中国观察的回应,主要有三篇文章:《罗素游俄记书后》《罗素与中国——读罗素著中国问题》和《罗素又来说话了》。徐志摩感受到罗素对于中国文化的真挚之爱与敬,这不比传教士的隔靴搔痒,罗素通过欧洲战争而觉悟其文明的错漏,因而对中国的未来尤为担忧,怕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复又走上物质主义和盲目发展的路。尽管作为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徐志摩质疑罗素对中国并未深透地理解,他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与生活何以如此,然而徐志摩对罗素的世界主义视角和中国情怀是钦佩的。 布鲁姆斯伯里的成员中,与徐志摩有直接过从的还有罗杰·弗莱。弗莱是狄更生的挚友,徐志摩因而结识了这位影响英国现代主义的美学家。弗莱的美学观受到布鲁姆斯伯里派的支持,在他看来,“艺术不是寻求模仿形式,而是创造形式;不是模仿生活,而是发现生活的等价物”,艺术的独立与自足性,便是“艺术作品的形式,是它最根本的性质”。这个颇具演说才华和感染力的先锋艺术批评家,用“后期印象派”命名塞尚、梵·高、马蒂斯、毕加索等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遂进入英国公众的视野,大大地冲击了维多利亚时期讲究写实的美学信条。他的《视觉与构图》《艺术与社会主义》等书很看重艺术与观众的关系。而在《中国艺术面面观》《中国艺术》等专门文章中,弗莱梳理了中国艺术的历史演进,介绍了青铜器、佛教造像、文人绘画以及古典建筑等专题。[23]弗莱的评析精湛透彻,少有学究气,与弗莱的交往无疑影响到徐志摩对现代艺术的理解。1929年4月,徐志摩与友人筹备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同时编辑出版《美展》。同月,该杂志在第5期发表徐悲鸿的《惑》和徐志摩的长篇回应文章《我也“惑”》。文中,徐志摩先肯定徐悲鸿的人格与气节,然后婉转提出对塞尚、马蒂斯等后印象派画家的支持,质疑徐悲鸿对现代艺术的蛮横拒斥,这显然与他受弗莱启发,对现代艺术的熟稔有关。回国后,徐志摩还积极推动弗莱到中国演讲,可惜弗莱忙于在英美的展览事宜未能成行。设想如果当年弗莱应邀前来中国,作了关于后期印象派等现代艺术的演讲,那会对20世纪的中国艺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因徐志摩的连缀,因他的“爱、自由、美的单纯信仰”,新月诸君与布鲁姆斯伯里派有了更多的交汇,此后布鲁姆斯伯里派第二代朱利安·贝尔到武汉大学教授英国文学,继而结识和爱恋陈源的夫人凌叔华,与这位能书擅画的直隶布政使的女儿一同翻译和创作小说。在贝尔的引荐下,凌叔华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往来传书,也是因伍尔夫和姐姐范尼莎的鼓励,凌叔华完成她的自传体英文小说《古韵》,朱利安·贝尔、伍尔夫的先生伦纳德·伍尔夫、玛乔里·斯特拉齐等人的鼎力相助,最终促成凌叔华文稿在英国发表,凌叔华继而在移居英国后举办个人画展、个人收藏展等等,俨然成为布鲁姆斯伯里派外围的中国成员[24];伍尔夫的意识流写作间接地影响了徐志摩和林徽因;40年代,萧乾在伦敦做战时记者时,常到剑桥大学修学英国文学,并与E.M·福斯特建立了深厚友谊,萧乾从福斯特那里直接获得了大量作家本人授权的第一手资料,但政治风云和十年文革将萧乾带回国的书信、日记和研究卡片毁于一旦,福斯特研究令人痛心地胎死腹中。[25]萧乾后来回忆道,新月派确实受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作家的影响,“中国的新月派在英国被视为‘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因为他们为艺术而艺术,也从不写宣传文章”。[26]在《丽莉·布里斯珂的中国眼睛》和卞之琳晚年为《徐志摩诗集》写的长序中,我们还可以读到丰富的书信、回忆和文字断片,至今这些未被历史尘封的心灵对话,在文化书写和误读的空间中依然熠熠闪光。 如今回望两个跨越万里,被历史偶然连缀起来的文学社团,无论是发现“新月”寂寞而别样的现代性追寻背影,抑或感受“布鲁姆斯伯里”知识分子的现代主义建构中的世界主义倾向,都让笔者感叹在他们彼此互为“他者”的主体间阅读中,透过文化想象而生成的文化理解的弥足珍贵,即便我们愿意更准确地称这份理解为——同情性的文化误读。然而,正是由于他们彼此间勇敢地跨越封闭的文明之墙,观看他者,并借他者之眼回望自身文明,他们为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留下了一笔可资借鉴的宝贵遗产。 ①参见梁锡华《徐志摩英文书信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标签:新月派论文; 徐志摩论文; 布鲁姆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胡适论文; 大学社团论文; 梁实秋论文; 伍尔夫论文; 罗素论文; 剑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