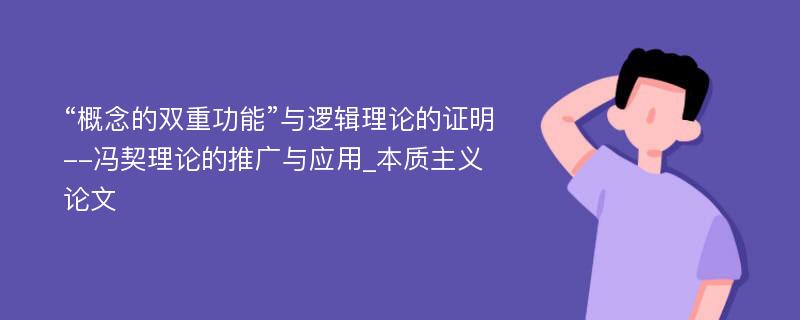
“概念的双重作用”与逻辑理论的证成——对冯契理论的一点引申与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逻辑论文,概念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7)02-0009-06
金岳霖提出的“意念对所与的摹状与规律”的思想[1](pp.354-416),在冯契的广义认识论中被发展成为“概念的双重作用”这一理论。在阐述概念的实质和作用时,冯契不仅从主观与客观、被动与能动的角度解说了概念对现实的摹写与规范,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借助后验性与先验性、内在性与超越性诸范畴进一步阐明了概念双重作用的不可分割与交相为用,并且化理论为方法,探讨了逻辑原则之后验性与先验性的统一,已经触及到了当代逻辑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逻辑理论的证成(the justifi cation of logical theory)。基于此,笔者尝试在本文中展开“‘概念的双重作用’与逻辑理论的证成”这一论题,以期能够从一个侧面来帮助我们把握冯契这一理论的多向度的理论潜能。
一、概念:摹写现实与规范现实的统一
在金岳霖的影响下,冯契认为,“相对于对象来说,一切概念都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摹写现实,另一方面规范现实。”所谓摹写(description),强调概念作为思维形式,乃是对现实对象的特性或本质的反映;所谓规范(prescription),侧重的是概念是具体事物的规矩、尺度,即可以用概念来衡量、辨认和说明具体事物。就二者的关系说, “概念的规范作用和摹写作用是不能割裂的,只有正确地摹写才能有效地规范,也只有在规范现实的过程中才能进一步更正确地摹写现实。”[2](p.62)
有见于金岳霖对意念的理解还不是彻底的辩证法,仅仅注重对人类知识经验作静态的分析,冯契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对金岳霖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一方面,概念的双重作用表明概念既是主观的(就其是认识主体对对象的反映而言),又是客观的(就其是反映和摹写的对象、内容而言);既是被动的(就其只能如实摹写对象,而不允许有任何主观的附加而言),又是能动的 (就其可以成为衡量与识别对象的规矩、尺度而言)。另一方面,概念并不是一次抽象就能取得完成形态的,它还有一个从前科学概念到科学概念,从低级阶段的科学概念到高级阶段的科学概念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概念既摹写现实又规范现实,所以人的整个知识经验无非是‘即以客观现实之道,还治客观现实之身’。摹写与规范反复不已,概念越来越深入事物的本质,而经验越来越因经过整理而秩序井然。这种根源于经验,反映事物本质而秩序井然的知识就是科学知识。”[2](p.64)
更为重要的是,冯契还借助“后验性”(a posteriority)与“先验性”(apriority)这对范畴对“概念的双重作用”作了解说。他指出,“从概念对所与、理论对经验的关系来说,理论和概念都具有后验性,也都具有先验性。”[3](p.165)就前者说,概念、理论(由反映概念间联系的普遍命题所表示)总有其被动性,即思维之所得正来自经验,摹写必须是对现实的如实摹写。从后者看,当人们把概念和理论作为规矩、尺度来整理经验,赋予经验以秩序时,这些概念和理论又总是先于当前的具体经验。冯契概括为:“先验性指普遍概念独立于在其适用范围内的特殊事例、特殊时空关系。”[3](p.210)
与摹写作用、后验性相关联,冯契认为,概念和理论还具有内在性(immanence)。“概念若是科学的,则又必然与事实经验有巩固的联系,它反映的是现实事物间的本质的联系,故也有其内在性。”[3](p.188)尽管不同于个体的存在,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仍具有不可否认的现实性和实在性,而现实的和实在的总有其时空秩序,因此无论是自然史、社会史的历史法则,还是物理、化学、生物等的规律,其内容都包含有时空尺度或适用的时空范围的规定。这就是说,概念和理论总是内在于事实经验之中,有其特殊的时空范围的限制。而与规范作用、先验性相联系,概念和理论又具有超越性 (transcendence)。从概念和理论思维的角度看,感性认识到抽象认识的飞跃,正表现在抽象知识不受特殊时空限制,不受个体和事实的时空界限的限制。如“人”的概念不受张三、李四等特殊个体的时空关系的限制,无论古代、今人或是中国人、外国人,都可用“人”的概念加以摹写与规范。质言之,“思维形式本质上具有不受特殊时空限制的超越性,因此它才能有效地规范现实。”[3](p.188)
历史地看,在概念和理论的摹写作用、后验性、内在性与规范作用、先验性、超越性这两个序列的关系问题上,经验论的哲学家对前一序列予以了较多的重视,但由于片面强调知识来源于经验,对科学抽象不能做出正确解释,否认概念和理论可以摹写事物的本质,往往贬低了概念和理论的先验性与超越性,贬低了它们规范现实的作用。另一方面,持先验论观点的哲学家虽然对后一序列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但由于对规范作用作了片面理解,过分强调概念和理论赋予经验以秩序,割断了它们与感觉经验的联系,往往否认概念和理论摹写现实的作用,当然也就否认了它们的后验性与内在性。有见于此,冯契明确指出, “规范和摹写是统一的,先验和后验是统一的,越是正确地摹写就越能有效地规范,越是有效地规范,就越是正确地摹写,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经验论和先验论对于概念的双重作用各有所偏,他们把规范和摹写割裂开来,把先验和后验割裂开来,各执一端,夸大了一面。”[3](p.166)
二、“概念的双重作用”与逻辑理论的证成
对于冯契的这一理论,为数不多的研究多着眼于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着眼于人们把握具体真理、获得具体概念的过程,认为它科学地揭示了概念的实质和作用,清楚地展示了概念在思维形式辩证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概念自身从抽象概念向具体概念发展的一般途径。[4](pp.137-149)不过,在笔者看来, “概念的双重作用”的理论意义远非上述论断所能范围。事实上,以这一理论为分析工具,冯契化理论为方法,又对逻辑原则(主要是形式逻辑的同一律、辩证逻辑的“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的接受原则等)的后验性与先验性的统一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关于逻辑原则的后验性,冯契提供了两个论证。其一,通过强调逻辑的本质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他从逻辑的客观基础角度论证了逻辑原则的后验性。“逻辑原则有其客观基础。同一原则的客观根据在于概念和对象有一一对应关系,因而思想有其相对稳定状态,正如客观现实的运动有相对静止一样。而‘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则是实践基础上的认识运动的接受总则,它与客观世界的辩证运动是相一致的,正是通过主与客、实践与认识的交互作用的运动(即以得自经验者还治经验的辩证运动),人们越来越深入地把握了现实之道(即客观世界的辩证运动)。”[3](pp.215-216)其二,援引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关于行动模式先于思维模式的思想,以及列宁关于逻辑起源于社会实践的观点,冯契又从逻辑起源的角度论证了逻辑原则的后验性。他明确指出,“思维的逻辑是行动的逻辑的内化,公理是人们亿万次实践重复才在人脑中固定下来的。”[2](p.246)“行动模式内化为思维模式,这种模式有它的逻辑结构,正说明逻辑按其来源说,是后验的。”[3](p.214)
关于逻辑原则的先验性,冯契认为,无论是同一原则还是接受总则,“这些逻辑原则是独立于经验,决不会被经验所推翻的,是知识经验的必要条件,是科学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在理论上的担保。可以说,它具有先验性。”[3](p.215)但是,逻辑原则的先验性仅仅是指它们先于具体经验,不受特殊时空的限制,并不能否定其在来源上的后验性。他进而指出,要防止因否认逻辑原则的后验性而可能导致的两种倾向。其一是先验论倾向,即把逻辑原则归结为形而上学的理念世界或主体所固有的先天形式;其二是约定论倾向,即把逻辑原则看成是约定俗成的、与事实无关的语言符号的规则。[2](p.245)质言之,强调逻辑原则的后验性与先验性的统一,也就是强调逻辑原则本身体现着概念、理论之摹写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统一。
尽管冯契论证的还仅仅是一些基本的逻辑原则而非具体逻辑理论的后验性与先验性的统一,但这一工作已经为我们摊开了“‘概念的双重作用’与逻辑理论的证成”这个论题,同时也为科学地解决逻辑理论的证成问题指明了方向。
所谓逻辑理论的证成,就是去证明一种逻辑理论是合理的、正当的。就现代逻辑而言,形式化的工作方式使其理论成果往往表现为各种逻辑系统。而证成一个逻辑系统的标准程序,就是去证明它的可靠性和完全性。不过,正如陈波所指出的,这种证成是建立在所谓绝对主义逻辑观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逻辑观看来,“用演绎推理建构起来的逻辑真理是绝对正确、普遍适用、不容修改的;它们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是其他一切真理的标准,但其本身的真理性是清楚明白、毋庸置疑的。”[5](p.86)基于绝对主义的逻辑观,现代逻辑学家认为逻辑是纯形式的,逻辑学家只应关注一个逻辑系统的形式或技术方面:如果能证明一个逻辑系统的可靠性,那么它就是可以成立的;如果还能证明其完全性,该系统就近乎完美了。
事实上,关于可靠性与完全性的形式证明,仅仅是证成一个逻辑系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了可靠性和完全性,还有一个正确性的问题,即“一个形式系统是否正确地表示了它打算加以形式化的那些非形式论证。”[5](p.86)究其实质,正确性问题涉及的是逻辑系统与经验之间的关系。由于逻辑系统总是通过其逻辑常项的解释而与人们的日常语言和思维实践的经验存在联系,因此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经验的成分或经验的色彩。又由于可靠性和完全性证明总是针对已给定的逻辑常项的解释而言的,逻辑真理的必然性也仅仅是针对不同的假定、原则、解释或模型而言的,因此逻辑系统的相对性又是不可避免的。总之,“逻辑学家并不是理性领域的立法者,他们不能随便地造逻辑或逻辑系统,然后像颁布律令一样把这些系统颁布给大众,并强迫大众遵守。实际上,逻辑学家在构造逻辑系统时,也要受到许多限制,除形式方面的限制——如可靠性、完全性、可判定性等等之外,还要受到实质内容方面的限制,即从大众日常使用的逻辑中进行提炼、抽象与概括,其造出的逻辑系统也要接受大众的日常语言实践和思维实践的检验。在认识论上,与其他自然科学家相比,逻辑学家并不具有任何特权。”[5](pp.94-95)
从概念的双重作用的角度看,绝对主义的逻辑观及其对现代逻辑之证成的理解,因割裂了逻辑理论之后验性与先验性的统一,而对自身的先验性和规范作用作了片面的夸大和绝对的理解。与之相反,强调证成一个逻辑系统的正确性维度、揭示逻辑系统或逻辑真理的经验来源或经验成分、主张逻辑理论在原则上的可修正性,则代表着一种在后验性与先验性的统一,因而也就是在摹写现实与规范现实的统一中来证成逻辑理论的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逻辑理论的后验性,或者说逻辑理论与经验之间的联系,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就各种形式化的逻辑研究而言,逻辑系统主要通过对其逻辑常项的解释而与语言实践和思维实践保持着十分间接的联系。逻辑学家一旦选定了逻辑常项,选定了对这些常项的特定解释,并给出了与这些解释相应的公理与推理规则,剩下的从公理根据推理规则推出定理的工作则是完全形式的,与任何经验无涉。而就各种非形式化的逻辑研究来说,逻辑理论与经验的联系则更多地表现为在研究推理和论证时采取一种经验的进路(an empir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reasoning and argument),通过结合与人的心理、思维、认知、言语交际和各种行动相关的各门经验科学,在描述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的往复运动中来研究推理和论证,从而达到逻辑理论之后验性与先验性、摹写现实与规范现实的统一。[6](pp.46-50)正是着眼于“概念的双重作用”对逻辑理论之证成所提出的要求,下文将对关于论证的不同逻辑理论的证成问题展开更为具体的讨论。
三、现代逻辑的论证理论及其普遍主义、先验主义倾向
苏珊·哈克在其《逻辑哲学》一书的开篇指出:“逻辑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在有效的(valid)论证和无效的(invalid)论证之间做出区分。形式逻辑系统,例如人们熟悉的语句和谓词演算,旨在提供有效性的精确规则和纯形式的标准。”[7](p.1)此所谓“逻辑”侧重的是现代逻辑。就试图对论证给予评估来说,现代逻辑无疑是一门规范性科学。这种规范性不仅表现为去确定论证的结论是否被接受,更重要的在于去确定是否应被接受。由此若说现代逻辑拥有一个自觉的论证理论尚存争议的话,那么它拥有一个隐含的论证理论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在现代逻辑的视域中,论证(argument)通常被区分为非形式的(informal)和形式的(formal)两种。所谓非形式论证,往往表现为由自然语言语句所组成的一个序列,它借助“因为”、“所以”、“由此可见”等导入词来实现由前提向结论的过渡。而形式论证则通过由合式公式组成的一个有穷序列来表明由前提向结论的过渡。作为一种逻辑理论,论证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非形式论证,不过形式化的工作方式却使现代逻辑更为青睐形式论证。至于前者,现代逻辑主张用精确、严格和可概括的名称将其翻译为形式论证并给予形式化的研究,而且认为“一个可接受的形式逻辑系统应该是这样:如果一个给定的非形式论证借助某种形式论证在这个形式系统中得到表述,那么,形式论证在系统中应是有效的,仅当该非形式论证是在系统外的意义上有效的。”“一个形式逻辑系统一旦确定了,它就能制约人们关于非形式论证的有效性或非有效性的直观。”[7](p.15)
论证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论证的评估。长期以来,逻辑学家把好的论证理解为前提真实且推理有效的论证,由于现代逻辑认为“逻辑关心的是论证本身的有效性,即不考虑论证的题材”[7](p.5),因此较之前提的真假,论证的有效与否更受重视。哈克甚至说:“如果人们是完全理性的,那么他们应该只被那些具有真前提的有效论证所说服,但事实上,人们常常被那些无效的论证或者被那些具有假前提的论证所说服,而不是被可靠的论证所说服。”[7](p.11)显然,有效性在此不仅充当了判定一个论证是否合乎逻辑因而是否为好论证的标准,而且构成了判定一个人的思维和言行是否为理性之思维和言行的标准,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标准。
由于认为可以把非形式论证翻译为形式论证进而在形式化的框架下开展论证研究,显然,基于这种方式建构起来的现代逻辑论证理论(如果可能的话),最终仍然要面临与在绝对主义逻辑观支配下的现代逻辑之证成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即正确性的问题。按陈波的理解,一个逻辑系统的正确性问题指的是一个形式系统是否正确地表示了它打算加以形式化的那些非形式论证。具体到论证理论,这一问题关注的则是一种论证理论是否如实地摹写了实际论证、能否有效地规范实际论证。鉴于笔者已以“现代逻辑的规范性及其问题”为题对现代逻辑论证理论在正确性问题上的诸多失误有过更为深入的讨论[8](pp.25-50),下文对此仅作一扼要的论述。
首先,把非形式论证理解为无关紧要的语句序列,没有切中非形式论证的本质。现代逻辑往往把由自然语言表达的非形式论证看做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语句序列,就像哈克所说的“或者7+5=12,或者狗喵喵叫,所以狗喵喵叫”之类的。[7](p.22)事实上,为了解决彼此之间的意见分歧,协调彼此的行动,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科学研究、课堂教学、法庭论辩、公共决策、商业谈判、专家咨询等不同的对话或交往领域中,人们往往诉诸论证来替己方意见的合理性与正确性辩护,劝说他人接受己方的意见,或者对自己所不赞成的他人的意见加以批评和驳斥。因此,实际的非形式论证总是以一种在双方(或多方)之间进行的,以解决意见分歧、谋求共识、协调行动为目的的言语交际或论辩 (argumentation)为其表现形式。据此,我们就决不能把非形式论证仅仅理解为一些无关紧要的语句序列,而应该把它置于言语交际或论辩的语境中来把握其实践本质与语用维度。
其次,将非形式论证翻译为形式论证,剥夺了自然语言的直观性、复杂性和表现力。正如斯特劳逊所说,“与形式逻辑研究并肩而行,并与之部分重合的是另一种研究,这就是对日常言语的逻辑特征的研究……在结果中我们不指望会找到为形式逻辑的句法关系所具有的那种精致和系统性,但是,同样真实的是,日常言语的逻辑提供的是一种在丰富性、复杂性及吸引力方面都无与伦比的知识领域。”[10](pp.239-240)就此而言,借助自称为精确、严格和可概括的名称把非形式论证翻译为形式论证,无疑牺牲了自然语言的直观性、复杂性和表现力。另一方面,经过形式化处理,非形式论证丧失了其实践本质与语用维度,变成了一种无主体的、独白式的纯粹运算。或是有见于此,赖尔曾指出, “试图把任何有效的推论以这样或那样的改写方式化归为某一种预定好的模式,把每一错误的推论化归为一种设计好的笑料,这样做虽然很自然,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也是极端错误的。”[9](p.222)
再次,以有效性为评估论证的核心规范,导致具体的评估实践面临诸多困难。譬如,对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省略三段论来说,有效性根本无法胜任对其予以评估的任务。因为一个省略论证或者是有效的,或者总是可以通过补充出恰当的(但未必是合乎直观、易于人们接受的)前提而变得有效。换个角度说,现代逻辑论证理论强调的无效性 (invalidity),对于一个论证之不好或错误来说,其实既不充分也不必要。一方面,某些运用了有效推理的论证其实是错误的,如循环论证。证据和论点的彼此支持,虽然使循环论证满足了有效性标准,但是由于不能为论点提供异于论点的支持,因而是一种不好的论证。另一方面,某些使用了无效推理的论证却不能认为是错误的。按有效性标准,所有归纳论证都是无效的,但日常生活中大量归纳论证被当作好论证而为人们接受,却是不争的事实。
最后,现代逻辑论证理论具有一种普遍主义、先验主义的倾向。按哈克之见,现代逻辑“渴望表达适用于任何题材的推理的原则,并要求这些原则在范围上囊括一切(to be global in scope)”。[7](p.228)推理的题材与经验有关,强调自身表达的推理原则“适用于任何题材”、“在范围上囊括一切”,凸现的正是现代逻辑及其论证理论试图超越任何来自经验方面的限制,以确保一种论证研究的普遍主义立场。后者进一步表现为现代逻辑学家似乎可以超越一切个人、族群甚至人类的局限,以完全理智的观察者身份,在实际论证过程之外,以不涉及论证具体内容的方式来对论证加以描述,展开研究,给予评估。现代逻辑论证理论的普遍主义立场,又折射出它自我期许的所谓全人类性。如同为自然立法的理性在康德那里是以先验理性的面貌出场的一样,现代逻辑对非形式论证的形式化处理、对题材中立原则的片面理解及其自我期许的全人类性,一言以蔽之,其普遍主义立场则从为思维立法的角度暴露出了它所具有的先验主义倾向。
四、非形式逻辑的证成:后验性与先验性、普遍性与情景性的统一
鉴于现代逻辑论证理论无法有效地规范实际论证,有必要对其普遍主义、先验主义的倾向予以反思。然而,在批判普遍主义、先验主义的同时也要防止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相对主义。作为一门规范性科学,逻辑固然要描述论证,更要评估论证。一旦倒向相对主义,极端言之,现代逻辑论证理论坚持的有效性这一普遍标准将被由个人癖好任意决定的标准所取代。然而,按照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之不可能的论证,这种相对主义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对这些任意决定的标准是否被正确应用加以检验。显然,要彻底清算论证理论中可能存在的这种对峙,不借助一点辩证的智慧是不行的。这就是说,逻辑学家应该按照“概念的双重作用”的要求去证成一种论证理论,即一种合理的论证理论应该体现理论之后验性与先验性、摹写现实与规范现实的统一。
在这方面,非形式逻辑的若干理论尝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有见于有效性标准并不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的论证——这正是现代逻辑论证理论对自身之普遍性、先验性所作的片面理解的结果,图尔敏在论证中采取了一种经验的进路,尝试通过对具体的法律论证的实证研究来寻找现代逻辑论证理论的替代物。一方面,论证理论必须具备某种先验性、超越性,才可能对具体的论证实践进行有效的规范和评估。由此,图尔敏坚持论证具有一种普遍的结构,即任何可接受的论证都必须遵守不依领域的变化而变化的(field-invariant)、为支持主张而制订的程序,这就是由主张、理由、保证、佐证、反驳和模态限定等要素构成的所谓“图尔敏模式”。另一方面,就有效的规范应建立在如实摹写论证实践的基础上来说,论证理论又须具有某种后验性、内在性。正是注意到实际生活中存在着法庭、学术会议、董事会会议、医生会诊、讨论班、听证会等不同的语境,根据对这些语境的功能分析,他把这些语境进一步归结为法律、科学、艺术、管理以及道德等领域,强调出现于其中的实际论证之可接受与否,还需取决于那些将随领域的变化而变化的 (field-dependent)特定的实质性的正当理由。[12](p.15)
相异于有效性实质上是现代逻辑论证理论先行于任何具体的论证实践而制定出来的普遍模式,图尔敏的如上做法较好地体现了理论之摹写现实与规范现实的统一。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对实际论证出现于其中的不同领域的这种划分,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关于论证的普遍概念架构的建制性分化 (institutional differentiations of a general conceptual framework)。[13](p.33)而这种普遍与分化的统一,折射出的正是图尔敏对于论证理论之后验性与先验性、普遍性与情境性的统一的坚持。
在非形式逻辑领域,沃尔顿是另外一位致力于从普遍性与情境性的统一中来建构论证理论的逻辑学家,他提出了一套被称为新论辩术(new dialectic)的论证理论。“在新论辩术中,我们总是从用以实现构成一会话交际之基础的某种对话的目的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估论辩。每种对话都有其自己的衡量一论证是否得到成功使用的似真性与合理性标准。由此,新论辩术就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相对主义,后者使其和古典的实证主义哲学(the classical positivistic philosophy)相区别。不过,它也提出了评估论证之使用的逻辑标准的结构,而正是这种结构又把它和后现代的反理性主义(postmodern antirationalism)区别开来。”[14](p.71)
实证主义哲学是一种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它把欧几里得几何所体现的演绎逻辑看作是正确推理的典范。由于把在日常权衡、法律和伦理学等领域中所使用的推理看作是完全主观的,这种哲学实际上就预设了一种对于推理和论证理论的普遍主义理解。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新论辩术自称具有的某种程度的相对主义,其实反映了它对现代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普遍主义立场的某种否定。不过,沃尔顿并没有从否定普遍主义走向后现代反理性主义所代表的相对主义。他所谓的某种程度的相对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相对主义,而是一种有普遍性的诉求包含其中的情境性。
作为论证理论,新论辩术之所以是普遍的,是因为处于不同类型的对话之中的任何论证均可通过识别论证、识别对话语境、举证责任和评估批评四个步骤得到评估。这些步骤构成了使新论辩术区别于后现代反理性主义的那些“评估论证之使用的逻辑标准的结构”。而这种方法之所以又是情境的,则是因为它主张结合论证所处的特定对话类型来具体的评估。一旦识别出某论证所属的对话类型,就可结合其使用的特定的论辩模式(argumentation scheme)及其配套的批判性问题来评估该论证。
为了避免重蹈现代逻辑论证理论不能有效规范实际论证的覆辙,沃尔顿对论证理论如何做到后验性与先验性的统一极为重视。针对诸如“论辩模式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How were the argumentation schemes constructed?)之类的问题,他指出,尽管目前已提出了诸如诉诸专家意见、诉诸范例、诉诸无知等二十余种不同的论辩模式及其配套的批判性问题,但论辩模式的完全性仍然是一个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不过,虽然现阶段还不可能给予论辩模式以系统的证成,但借助个案研究(case study)的方式还是可以为其提供一个语用的证成(a pragmatic justification)。简言之,最初是收集那些在传统上被划入谬误的论证类型的重要例证,然后将其付诸比较性的考察和分析。在大量此类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借助假说的形式提出一些普遍原则,来解决诸如如何把具体论证区分为不同类型、如何识别论证的前提和结论、如何确定每种论证所需的批判性问题之类的问题。这些假说代表着那些用以分析和评估实际论证的技巧、工具的现状。“随着越来越多的案例被收集并得到分析,这些分析工具的分析能力将得到增强,它们所代表的原则将更加有效。”[15](p.11)不难看出,对新论辩术的这种语用的证成,使其拥有了冯契所强调的“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之身”的本性,即通过对实际论证之描述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的往复运动,使自身达到了后验性与先验性、摹写现实与规范现实的统一,从而避免了现代逻辑论证理论之普遍主义、先验主义立场对非形式论证的简单而片面的理解。
总起来说,本文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了“‘概念的双重作用’与逻辑理论的证成”这一论题:“概念的双重作用”要求逻辑理论的建构必须坚持后验性与先验性的统一;现代逻辑论证理论的证成具有一种普遍主义、先验主义的倾向;非形式逻辑则尝试从后验性与先验性、普遍性与情境性的统一中去证成自身。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概念的双重作用”与逻辑理论的证成之间确实存在内在的关联。本文既是对冯契所提出的“概念的双重作用”这一理论的引申与应用,也是对“‘概念的双重作用’与逻辑理论的证成”这一论题所作的初步探讨,进一步的研究将有助于更为深入而全面地理解和展示这一论题的丰富内涵。
收稿日期:2006-11-28
标签:本质主义论文; 系统思维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普遍联系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评估标准论文; 形式化方法论文; 逻辑学论文; 科学论文; 推理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
